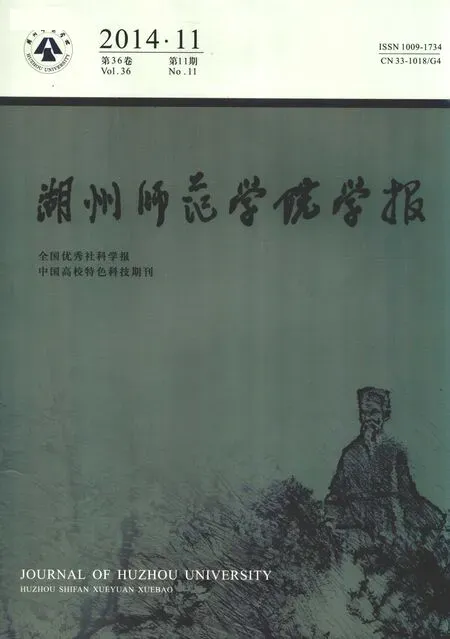少女·人性·天浴*
——严歌苓《天浴》解读
李 岩
(滨州学院中文系,山东滨州 256600)
少女·人性·天浴*
——严歌苓《天浴》解读
李 岩
(滨州学院中文系,山东滨州 256600)
《天浴》是严歌苓文革叙事中直接以知青生活作为表现对象的短篇小说。作品紧紧围绕“天浴”这个核心意象,在两次“天浴”的叙事中贯穿了少女文秀的文革经历,将基于少女视角的“祛欲望”化的“天浴”以及政治与“性”交织下人性恶的裸露相互辉映,籍由个人的文革经历与命运浮沉呈现了极富象征与寓言性的人性与历史内涵。
文革叙事;《天浴》;少女;人性
严歌苓有多篇写到文革的作品,不管是虚构性很强的《天浴》(作者听来的故事)、《雌性的草地》(女子牧马班的故事)、《白蛇》,还是更多带有回忆纪实性的《一个女人的史诗》、《人寰》以及《穗子物语》中的《拖鞋大队》、《老人鱼》、《小顾艳情》等,这些有关文革的叙事均非直指社会现实的批判和控诉,而是“向其中的生活打开了风景的窗口”。[1](P8-9)出国前的长篇《雌性的草地》、出国后的短篇《天浴》是严歌苓代表性的作品。与《雌性的草地》相比,《天浴》反响较大,与被陈冲改编为同名电影并获得第3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有关,但更多的还是小说本身的成功。笔者很好奇的是,严歌苓如何在一个较短的篇幅内完成一个与文革“背景”更为直接的故事叙述,在框定的文本意向下如何赋予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以重大而又独特的人性与历史叙事内涵。
一
在《天浴》中,少女形象的选择十分巧妙,题目本身极具象征性,是一个笼罩全篇的核心意象,纯洁、天真直接关联着罪恶与清洗。《天浴》直接和间接提到的洗浴共有六处。可概括为两类关于“天浴”的叙事:基于少女视角的“祛欲望”化的温情与人性善,政治与“性”交织下的人性沦丧。以“天浴”始,以“天浴”终,一实一虚,亦实亦虚,两相对照中夹杂的是文秀命运的逆转,小说整体上可谓去芜存菁,气韵浑然天成。
小说开头并未直接写人和事,而是先用极为经济的笔墨写了大的自然环境:“云摸到草尖尖。草结穗了,草浪稠起来。一波拱一波的。”[2](P59)简洁又极富动感的镜头从天上摇到地下,焦点落在山坡的文秀身上,藏民老金挖空心思要让女知青文秀洗个澡,由此进入小说叙事中的第一次洗浴,一次真正的“天浴”。按照故事发生的脉络,作为小说开头的这次“天浴”并非是文秀实际的第一次洗浴,把这次洗浴放到小说开头并花大气力去描述,体现了作者的叙事策略。首先,“对于整体结构而言,某句或某段话语处在此位置,而不处在彼位置,本身就是一种功能和意义的标志,一种只凭其位置,不需要语言说明,而比起用语言说明更为重要的功能和意义的标志。”[3](P40)小说开头直接切入了“天浴”,老金忙碌着想法子让文秀洗个澡的故事在广袤的自然中展开。漂亮的文秀、勇猛的老金,蓝天,草原……天、地、人和谐共存,宁静而富有温情。此时的文秀有着少女的矜持和天真烂漫,神清气爽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这场洗浴象征了一种极为自然、原始、温情而又能抚慰人心的感情与关系,与后文进入历史与社会层面的生活相互辉映,也为文革生活的展开埋下了伏笔。其次,这次“天浴”中极为巧妙地铺垫、倒叙了文秀真正的第一次洗浴,凸显了一个无辜、单纯甚至不乏稚气的少女形象。第一次,“文秀仍是仇恨老金。”没有前后的铺垫,这个“仍”字很突兀,是本不该恨却有恨,还是本来有恨,经过一些事情后这种仇恨的感情有所缓和却仍然存在……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不是老金拣上她,她就伙着几百知青留在奶粉加工厂了。”故事继续推进,在文秀看来,是老金改变了她的命运,将她拽离了熟悉的集体,置身被隔绝的危险处境中。她对老金以及自己命运背后的政治与历史一无所知。第二次,“有时她恨起来:恨跟老金同放马,同住一个帐篷,”这第二个恨有些具体了:小姑娘文秀是和老金住在一个帐篷里。第三次,是文秀与老金同住一个帐篷的第一个晚上由于洗涮带来的尴尬和怨恨。“她是从那一刻开始了对老金的仇恨。”少女文秀带着情绪的第一次洗浴“摔摔打打”地在一系列铺垫中慢慢出场了。
作者在开头“天浴”中倒叙了少女文秀第一次洗浴的故事,构成了整篇作品叙事中的第一次“天浴”:少女文秀对“性”的想象性罪恶的清洗。藉由这种“祛欲望”化的仪式,这次“天浴”成为少女心中理想感情与完满人性的想象性实现。漂亮的文秀,是男人的欲望对象,包括老金在内的许多人都趁学上马下马的时候揩过她的油,文秀自己摸摸被人偷偷摸过的地方,感觉便在心灵上维护了原初的本真与圣洁。看电影无疑是物质、文化贫瘠时代最具文化与精神色彩的娱乐与盛宴,而趁着放电影时乱占女知青的便宜是这娱乐与盛宴中的狂欢,几千支捅向天空的手电筒的光柱子具有了双重象征意味,它既是男性“性”的写意,也是文化禁锢、贫瘠时代不多的精神犯禁。即便是这种不乏意淫似的“性”,也是少女文秀难以接受的。少女通过洗浴保持了天真与纯洁,老金赐予的“天浴”尽管被赋予了男性窥探的眼睛却因为老金的被阉割而极度纯洁化了。“祛欲望化”的视角来自少女文秀,也来自少女时代的严歌苓,是其童年文革经历的折射。[4](P105)严歌苓和一群女孩曾自发地守护着吃安眠药“畏罪自杀”的女作家,替因抢救插管子而不时赤身裸体的她盖单子,这期间有个二流子为掀起被单看她故意把烟头掉到被单上,“很脏的男人的眼光”在还是女孩的严歌苓心中刻下很深的印痕。这些难以磨灭的童年文革记忆经过长期的人生反刍演绎为“人性丑恶的一个符号”,而这种形而上的意念又转化为具体的文秀与张三趾的故事。
二
一次“天浴”成了文秀放牧生涯“美好”生活的象征,作者用约占整个作品三分之一的篇幅写了第一次“天浴”,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天真、纯洁的少女形象,而当这纯洁的羔羊作为历史的“献祭”被一次次推至政治肆虐与欲望泛滥交织的人性丑恶面前时,少女命运的逆转与变化就愈加令人触目惊心。“祛欲望”叙事中纯洁的少女,在人性本能与原始欲望的恐惧中渴望洁净的文秀当面临更为丑恶的罪恶时还能获得曾经的“天浴”吗?
“位置是历史和现实的错综,生存和命运的较量,偶然和必然的遇合。它给人物和事态以某种难以选择的选择契机,给人物和事态以选择中的牵引力和扭曲力。”[3](P87)预期半年后可以回场部的希望落空了,文秀被历史和现实推至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着生存的选择。此后,故事急转直下,事态发展让人措手不及:没有阴谋与单纯的较量,没有复杂与简单的胶着,甚至来不及在纯洁与堕落中纠结,读者还没回过神来,文秀已经被裹挟着陷入了泥沙俱下的历史洪流,为走门路回成都献身给了到各个牧点卖货的供销员。这仓促的献身没什么技术含量,也无斟酌和利益权衡可言,单纯的文秀慌不择路地交出了唯一的筹码。在文秀和供销员的交谈场景中,作者将这场对话设置成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独白,文秀始终没有说话,对供销员的“启蒙教育”唯有“听得嘴张在那里”,“朝他眨巴眨巴眼”。她被剥夺了话语权,而供销员成了掌控话语权的人。是谁赋予一个小小供销员这种权力?是荒诞的历史?是人的蒙昧与无知?还是人面对权力本能的顺从?文秀的第一次献身是“祛欲望”化叙事中纯洁少女的第一次“堕落”,对读者而言,不啻于突然的迎头棒喝,而要洗清这“堕落”,唯有洗浴。老金夜里赶了十里路在那条曾经给过文秀“天浴”的河中取来了水,文秀宁可不喝也要洗,“她不洗不得过,尤其今天。”从这之后,许多男人来找文秀,其作为人的尊严与理性几近丧失,可她再也没水可洗了。
供销员以及场部那些“关紧”的人都是没有面孔的抽象的人,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历史权力与荒诞理性的象征,借助政治权力获得了文秀的“献身”。被老金烧了皮鞋的场部重要人物对文秀连句客套话都没有,“来都是瞎着灯火”,上来就办正事,连文秀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文秀已然成为一个性符号,一个非具体的概念的“女人”,一个公然“卖”的“破鞋”,人可共享却无需承担任何伦理与人性的风险。老金对文秀是个“卖货”的指责出自内心深切的爱与痛,从另一个侧面也凸显了文秀生存与命运的悲哀:首先,“在女人的性奉献中存在着这样的反常现象:这种最一般的、对人性所有层次都一样的行为,事实上——至少对女人来说——被感受为最个人的、涉及内心世界的行为。”[5](P84)何况,文秀的献身绝非一般意义上性的发生,而是作为个体的人对“人”与“世界”的认知与交付,是发生在其精神内部的一次严重挫败;其次,“卖”需要货币或利益回馈,而文秀从这场交易中得到了什么?文秀的“卖身”彻底失败了,她不能获得哪怕是一个妓女应得的“卖身钱”——换得她回城的资格。除了空虚、绝望,只有远甚于妓女的更多的屈辱与难堪。
除了自上而下的与政治权力纠结在一起的“性”迫害,还有普通民众顺从某种历史理性而彰显出的人性丑恶。张三趾性侵事件一方面折射了民众加诸一个弱女子身上的恶意,一方面也使得文秀命运的悲剧性在强有力的对比中得到了强化。刚刚打胎三天的文秀在医院里受到了二流子张三趾公然的性侵,试图踢开门的老金却被护士掐住,而面对张三趾“老金排头一个”的公然挑衅,老金也只是用铜头靴子跺了张三趾仅剩两趾的脚趾头。同为女性的护士们非但不同情文秀,反而极尽侮辱与谩骂之能事,“破鞋”、“怀野娃娃的”,“弄头公驴子来,她恐怕也要!”为什么一个女孩子想回城遭受了凌辱反而是可耻的?为何人们能忍受像畜牲一样的张三趾,即便他公然的道德败坏,为了回城不择手段——故意把自己的脚打残?这与文秀的女性身份有关。“交媾不可能发生在真空中。虽然它本身是一种生物的和肉体的行为,但它深深根植于人类事务的大环境中,是文化所认可的各种各样的态度和价值的缩影。”[6](P32)米利特在这里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所体现的“性政治”,她用现成的代表权力关系的政治概念来表述两性的相对地位和关系的实质,张三趾性侵事件则更深入地体现了男性对女性所具有的权力结构关系。在人们看来,张三趾的欲望是不证自明的合理,而文秀即便是作为被动的受害者参与了“欲望”事件也是不道德的,只能得到人们的指责和鄙弃,她所遭受的不幸并非社会“恶”的结果,而是她道德败坏应有的下场。
三
面对身陷政治与人性丑恶的“文秀”,老金再也给不了“天浴”。老金对文秀的感情是借助白描化的语言隐隐约约透露出来的,听到文秀说满六个月就可以回场部,“老金手腕一松,柴都到了地上。”一个“松”字,仅仅是一个寻常动作,作者将这感情处置得若隐若现,似有似无,在这细若游丝的空间中却充满了情感的张力,细心的读者会在这微妙处与作者有种彼此明了的默契和欣喜。目睹文秀的献身,“老金不知他自己以完全不变的姿势已站了一个多小时,直站到帐篷里外全黑透。”如果说前面的白描是个看似全不用心的苦心经营,这里则近乎直白,老金对文秀的感情明朗、清晰起来,可作者并不代其抒情,也不深入其内心,但就是这种极经济的语言带来的强烈暗示性使得感情深厚了无数倍。当读到文秀招呼老金,老金“踏动几步,表示他一切如常”时,一个内心受到强烈震撼与打击的并不“如常”的善良汉子已经呼之欲出了。
在小说开头,老金无疑是一个很彪悍的人,被劁的经历不过是曾经很“凶猛”的证明,增加了传奇性却无损其威猛。文秀洗澡过程中用枪击退两个心怀不轨的男人是他勇武的一个例证,这时的老金凶狠、无畏、冷静,颇具男子气。但面对文秀后来的受辱,他的行动不过是烧掉了一只甩在帘子外的男人的鞋,或是在门口放置干刺藜这样近乎孩子气的行为。一旦原始的草原置换为政治权力的血雨腥风,老金的英勇与传奇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他非但成不了救美的草原英雄,反而柔弱到甚至无力介入某种话语和社会现实。小说叙述中的老金可谓惜字如金,即使说也是再简略不过的几个字,几乎是失语的。他对文秀的爱都体现在为她做点什么的行动上。文秀献身供销员的那个晚上,受到致命打击的老金对文秀的问话更是退化到了简单的“嗯”和机械的肢体动作,他出离愤怒的指责也不过是一句无力的“你在卖”,而这指责远没有“那也没你份”的回击简洁有力,在文秀看似轻描淡写却一针见血的攻击下只能败下阵来。“烧皮鞋”事件被讲述的过程中插入了文秀对老金的一次看似敞开心扉的谈话,可谓名副其实的文秀一个人的独白。文秀在讲,老金点头,却始终无语,与其说这是文秀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卖”,还不如说这是迷茫的文秀绝望中的呼救——内心满是恐惧和慌乱,她想在明知无望的诉说中得到一种放心的确证或决绝的否定——这样“卖”能换来回城的结果吗?除了“卖”还有别的路可走吗?老金是个在历史权力之外的草原上的藏民,质朴木讷到不懂人心险恶,遑论良知泯灭、黑白混淆的历史的荒诞与恶。他面对的不再是一个能理解、可视的具体敌人,不知道自己需要和什么作战,其英武全无用处,只能无知与无奈地任由这外在于良善以外的恶之手戏弄与把玩。茫然的文秀,还有比她更无知与茫然的老金,真的只能相顾两茫茫了。
老金无法承担救赎的重任,文秀的命运结局成为读者期待但作者最难刻画的结点。从医院回去的文秀决心学张三趾自残身体,可无论如何舍不得打自己,只有哀求老金帮她。一直在苦苦哀求老金的文秀面对老金的枪口一下子决心要死,细究起来,这不完全符合文秀性格的发展逻辑,作者在作品中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铺垫与暗示,严歌苓自己也说《天浴》最初的构思中并未想到让女孩去死,“写了三天,牧民最后打死了女孩。”[7](P51)这一情节设计并非浑然天成,有人工斧凿的痕迹,但这个逆转突兀中有合理性的因素,挑战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将文秀的悲剧之美推向高潮,让人在震惊之余有所回味。对比张贤亮《绿化树》中的章永璘和李国文《月食》中的伊汝,文秀显现的是更为弱势的女性群体的遭遇与命运。章永璘、伊汝在苦难的历程中有马缨花、妞妞,“他们之所以能从历史灾难中走过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受到女性奉献式的爱护和拯救。”[8](P88)女人只是过程的见证者和修炼时的必需品,这些男性超越女性的“性奉献”与爱,最终的价值追求指向客观的、形而上的观念世界。而文秀身为一个女性,从老金那里得不到性,从其他男人那里只能得到污蔑的“性”,残缺的老金不足以使其获得拯救,只能在充斥着恶意与鄙弃的环境中走向死亡。还有什么能比置身于关联着政治与历史的“性”场域更能彰显人性的善与恶呢?《天浴》中的“性”并非仅仅只是写实,被阉割的老金也不仅仅只是个具体的人,人性沦丧与兽性狂欢交织在一起的是拯救的缺席。纯粹的人只能死去。严歌苓曾说她不会随随便便让她笔下的主人公去死,只有最美的人才有这个资格,某种程度上,少女文秀是作为“人类”的至善与至美、纯洁与正义的象征而存在的,当这种极善与社会、人性的“大恶”相逢,美与善的毁灭就洋溢着极具震撼力的悲剧美,纯洁精神与至高人性就是深陷苦难沼泽中的人们期盼的一场“天浴”!也许,这也是陈冲之所以说《天浴》是一个寓言的原因所在吧。
[1]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
[2]严歌苓.天浴[M]//金陵十三钗.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
[3]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严歌苓.严歌苓谈人生与写作[J].华文文学,2010(4).
[5]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顾仁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7]江少川.走进大洋彼岸的缪斯——严歌苓访谈[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3).
[8]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Girl,Human Nature and Bath in Heaven——On Bath in Heaven Written by Yan Geling
LI Yan
(Department of Chinese,Binzhou University,Binzhou 256600,China)
Bath in Heaven is a short novel which focuses on the life of Chinese educated urban youth working in the rural areas.This novel concentrates on the image of“Bath in Heaven”and tells the story of a girl named Wenxiu which happened in the period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y using two different ways of narrative.By comparing two different images,one being based on the girl’s perspective of desexualizing and the other being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s and sex,the novel displays us symbolic and fable meanings of human nature and history by telling a story of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fate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arra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Bath in Heaven;girl;human nature
I247.7
A
1009-1734(2014)11-0044-04
[责任编辑 陈义报]
2014-06-10
李岩,讲师,从事文艺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