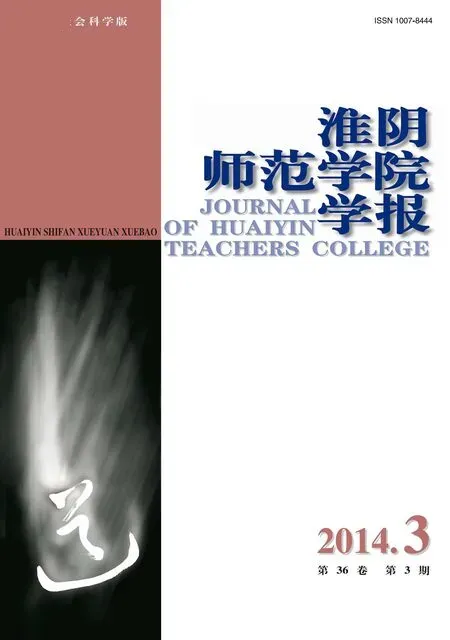中外合译的文化选择
——以英文杂志《天下月刊》上的现代文学作品英译为例
黄 芳
(1.南通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2.南京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博士后工作站, 江苏 南京 210093)
《天下月刊》*《天下月刊》,即T’ien Hsia Monthly,1935年8月在上海创刊,1941年终刊,是中国现代历史上著名的国人自办英文期刊,以英文翻译及评论等形式译介中国文学及文化经典,推动中国文学及文化向外传播。该刊总编为吴经熊,主编为温源宁,属于中山文教馆的机关刊物,主要编辑作者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钱锺书、林语堂、姚克等。被誉为民国时期最具文化与学术水准的国人自办英文杂志,在促进并推动中西文化深入交流的过程中,将中国文学及文化经典译成英文向海外传播,其中包括大量的现代文学作品。《天下月刊》刊载了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的沈从文小说《边城》、李广田诗歌《旅途》及凌叔华小说《疯了的诗人》等作品的英语译文。笔者试图通过比较分析这些英语译文对其汉语原文的文化传达程度,揭示出邵洵美与项美丽、陈世骧与哈罗德·艾克顿、凌叔华与朱利安·贝尔等中外译者所采用的不同翻译策略,及其表现出的多样化的文化选择。
一、邵洵美与项美丽*1935年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原名艾米莉·哈恩 Emily Hahn)作为《纽约客》杂志的记者来到中国,经弗里茨夫人的介绍认识邵洵美,很快发展出亲密恋情,同时也开启了他们共同的文学及文化合作之旅。他们先后创办出版了中英文双语的《声色画报》、抗日宣传刊物《自由谭》月刊及英文版Candid Comment(译为《直言评论》)。此外,邵洵美与项美丽还共同进行小说创作与文学翻译,合作翻译《边城》便是他们中西文化合作之旅中重要的收获。合译《边城》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邵洵美是个多面手,集作家、编辑出版家、翻译家于一身。在文学翻译方面,学界更为关注邵洵美汉译西方名著的贡献,而忽略了他英译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文化实践。邵洵美曾经有过丰富的英语写作及翻译活动,其中包括与项美丽英译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向外传播中国文化。《边城》描摹湘西地域民俗风情,揭示了纯朴、自然的人性特征,带有浪漫主义艺术风格,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因题材与风格之新颖而独树一帜,也赢得了邵洵美的喜爱。“洵美非常喜欢沈从文这本《边城》,有一个时期一直将它放在枕边,睡前总要读几段,仔细琢磨”,“为了向外国人介绍沈从文这部成功之作,洵美萌生将之译出来的念头。他知道自己的英文翻译水平还有一定的不足,所以跟项美丽合作,其实是他译好之后请她修改润色而已”[1]。项美丽在《边城》译文前言中,阐述了她对该小说及其作者的解读。她认为因其创作风格与人生经历的独特性,沈从文小说别具一格:带有田园牧歌情调,文字简洁流畅,充满音乐般的抒情意味。此外,项美丽还从中国古代小说观念演变、西方小说在中国的翻译等角度,揭示出《边城》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邵洵美与项美丽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较为谨慎的态度,他们深知任何一本中国书的英译都将招致大量的批评,汉语与英语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每个句子都可能有上百种的翻译。但在翻译方法与策略上,邵洵美与项美丽显示出较高的一致性,即采用自由灵活的翻译策略,尽可能在英语译文中保留原作文学及文化意蕴。如在译《边城》开头一段时,译者基本上以直译的方式进行翻译,从行文顺序到句式结构,都紧密扣住原文,较好再现了原文简洁流畅的风格。原文与译文对照如下:
……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边城》,原载《国闻周报》,1934年1至4月)
…… beyond which is a little stream. Near the stream is a little white pagoda, and close to that there is a cottage where once lived an old man, a young girl, and a yellow dog.
(“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 T’ien Hsia Monthly ,Vol. 2 No. 1 January 1936,P93)
邵洵美、项美丽在对原作中特有的名词进行翻译时,大部分保留原有文化意味,最大程度体现湘西的文化风情。《边城》的标题未被译成带有西方色彩的地域名称The Border Town和The Outlying Village,而是以小说主人公“翠翠”的名字作为标题,译成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有力凸现小说的人物形象,也较好传达原作的文化内涵。沈从文以简洁平白的语言来引入小说开头部分,邵洵美与项美丽在英译过程中紧扣原作,使用最为简单的语言与句式。此外,为了保证读者阅读的连续性,译者没有采用名词术语注解的翻译方式,而是直接在行文中进行阐释,“当在文章遇到中国人熟悉而外国人不了解的习俗或事物时,我们在文中做出解释,它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糟糕,沈先生的行文风格就是带有诸多解释性的特征,他提供了如此多的释例,以至于我们三次插入解释性内容,都未被察觉”[2]92。如在端午节习俗中,湘西妇女小孩子要在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王”字,邵洵美、项美丽在译文中对“王”字没有进行另外注释,而是直接在文中予以说明,“like this-王-because tigers wear this pattern of wrinkles on the brows ,and they thought it would frighten away all the devils who come out for Dragon Boat Feast”[2]105。邵洵美与项美丽采用灵活的翻译方法,使得《边城》的英语译文有效地保存了原作的文化风貌。尽管沈从文小说的文体风格难以在译文中呈现,但从原作文化传达的意义上来说,两人的译文无疑是成功的。由于邵洵美在翻译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因而《边城》的英译较好体现出了邵洵美的文化选择。
二、陈世骧与哈罗德·艾克顿*1904年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1932年起开始游历日本、中国等地。曾在北京大学任英国文学教授,与梁宗岱、朱光潜等多有往来,陈世骧、李广田、卞之琳等曾受其教益,并与陈世骧合作英译中国现代新诗,并结集出版Modern Chinese Poetry(《中国现代诗选》)。合译中国新诗
哈罗德·艾克顿20世纪30年代曾在北京大学担任英国文学教授,经由张歆海、温源宁的引荐,融入北大的文化圈,与青年学生如陈世骧、废名、卞之琳及李广田等人交往甚密[3];此后在年轻诗人卞之琳的建议下开始着手翻译中国现代新诗,并得到陈世骧的协助。陈世骧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曾积极参与各种文学活动,并成为朱光潜所主持的“读诗会”的成员,曾写作《对于诗刊的意见》参加当时的文学讨论,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拥有更为真切的体察与认知。因而可以说陈世骧是哈罗德·艾克顿进入中国现代诗歌的重要引领者,“选译工作当然艾克顿无法胜任,他至多把世骧的译稿加以润饰而已”[4],“后来二人更日夕研讨中国现代诗的英译,据艾克敦回忆,他对现代中国文学的了解主要得自陈世骧。1935年11月艾克敦在《天下月刊》发表《现代中国文学的创新精神》。这是早期以英文论述‘新文学’的一篇相当有见地的论文,其中不乏陈世骧的意见”[5]65。哈罗德·艾克顿与陈世骧合译了邵洵美的《蛇》、闻一多的《死水》、卞之琳的《还乡》、戴望舒的《我的记忆》《秋蝇》、李广田的《旅途》《流星》等现代诗歌作品。《天下月刊》上所刊载的两人译作主要是新月派与现代派诗人作品,这一方面体现译者对中国新诗发展过程的把握与认识,即中国新诗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之后进入到借鉴西方文学手法与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阶段;同时还揭示出哈罗德·艾克顿作为西方读者更侧重于中国新诗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内容,“他抱持艾略特式的‘传统观’,以为有成就的诗人必与传统互动,既取资于传统,又创新以丰富传统。中国新诗除了承受西方的影响以外,还得活化传统故旧,以建立现代风格”[5]67。哈罗德·艾克顿在《中国现代诗选·导言》中也指出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应该保持历史感”,“除了欧洲的影响,也存在着中国庞大传统中的一些大诗人的影响,两方面的影响‘已经完全化合,并经过了二次提纯’,必将贡献于现代诗人的风格特征与感觉能力”[6]。现引用艾克顿与陈世骧合译的李广田《旅途》一诗作例证来解读两人的翻译思想,原文与译文对照如下:
旅途(李广田)
不知是谁家的高墙头,
粉白的,映着西斜的秋阳的,
垂挂了红的瓜和绿的瓜,
摇摆着肥大的团扇叶,苍黄的。
……
两扇漆黑的大门是半开的,
悄然地,向里面窥视了,
拖着沉重的脚步,又走去,
太阳下山了,蠓虫在飞,乌鸦也在飞。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
(《汉园集》,1936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A JOURNEY
Who high white walls are these,
Set on a flare by the autumnal sunset,
With pendulous vivid gourds of red and green,
Round yellow-speckled fan-leaves floating over them?
……
Two dark doors ajar,
Quietly the traveler peers through
And then, with heavier footsteps, plods away,
The sun sinks: birds and insects suddenly flitter,
Flecks in the afterglow.
(“Two poems”, T’ien Hsia Monthly,Vol.1,No.4,November 1935,P423)
《旅途》体现了李广田诗歌质朴自然的风格,诗中的意象多为平常的自然与生活物象,如“高墙头”“团扇叶”及“大门”“蠓虫”“乌鸦”等,语言也十分平易通俗,如色彩及动作词汇“粉白”“苍黄”“摇摆”等。该诗在诗歌构思上也没有大的情感的跳跃,而以细腻的心理变化过程,来点染出苍茫迷惘的心情。陈世骧与艾克顿以直译的方式保留了原作的语言特色与文体形式,英语译文中的画线语汇较好译介汉语诗歌中的物象及其特征。这首诗带有鲜明的中国传统诗歌的韵味与特色,注重对自然物象的描写,契合了艾克顿对中国现代诗歌中的文化思想认知倾向。在陈世骧与艾克顿的合译过程中,陈世骧的文学及文化思想也开始逐渐受到艾克顿影响,如注重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在诗歌研究过程中注重对自然意象的阐发等。陈世骧曾在《中国诗歌中的自然》一文中指出,中国诗歌的显著特征在于自然与人生的高度融合,这使得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迥然相异,而具有了独特内质,“我们已经讨论过遥远的、无生命的天体以及风霜雨露怎样与人生密切地交织交融,我们不难想象人生与自然界的生物之间的交融和相互象征的程度,以致中国诗歌更因充满奇异的生活而显得五彩缤纷,借用一位现代中国诗人的话,简直‘浓得化不开’”[7]。因此可以说,早年的与艾克顿的翻译经历,深刻影响了陈世骧离国赴美之后的文学研究路向与思想,确立了陈世骧对传统文化的选择与认同倾向。
三、凌叔华与朱利安·贝尔*朱利安·贝尔是英国现代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子,毕业于剑桥大学。朱利安·贝尔1935年9月来到中国,受聘为武汉大学英语文学教授。在此期间,结识中国女作家凌叔华,并发展出密切情感关系。合译凌叔华的小说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凌叔华是一位具有独特写作风格的女作家,她的文学作品将传统文化意蕴与现代人的精神融合为一体,形成既温婉细腻又深邃别致的品范。她的小说引起了1935年来到中国并任教于武汉大学的英国教师朱利安·贝尔的关注,《写信》《疯了的诗人》《无聊》等作品相继被译成英文发表在《天下月刊》上;除《写信》署名为凌叔华独译之外,其余两个小说由凌叔华与朱利安·贝尔共同翻译完成。在翻译过程中,凌叔华先将自己的小说译成英语,朱利安·贝尔再对其译文进行修改。凌叔华认为在自己的汉语创作基础上进行英译的翻译模式,让她拥有更多文学创作与翻译的自由。但由于凌叔华与合译者朱利安·贝尔拥有完全不同的文学及文化背景,这使得他们合作进行的文学翻译产生出较大的文化冲突。朱利安·贝尔对凌叔华的译文进行大幅度的修改与删减,最终出现了与原作“信息不对称”的英语译文。如在《疯了的诗人》开头的片段中,凌叔华以细致清丽的笔调,状写出男主人所看到的自然美景,从整体意境的营造到人物心理的描摹都流溢出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情致。凌叔华特别运用了一些饱含色彩质素的词语如“濛濛漠漠”“缥缈轻灵”“浓淡”来形象展现自然之景的多彩维度,使得该小说带有浓烈的绘画艺术风格。而《疯了的诗人》的英语译文则大量使用简短句式、普通词汇,内容显得简洁流畅,但却消弭了原作所蕴含的文化意味及艺术风格。原文与译文对照如下:
原来对面是连亘不断的九龙山,这时雨稍止了,山峰上的云气浩浩荡荡的,一边是一大团白云忽而把山峰笼住,那一边又是一片淡墨色雾气把几处峰峦渲染得濛濛漠漠直与天空混合一色了,群山的脚上都被烟雾罩住,一些也看不见。
……
痴望了一会儿,手触到画箱,正欲打开取出画具,忽然抬头一看,目前云山已经变了另一样。他自语道:“拿这样刷子画这云山够多笨!况且这缥缈轻灵的云山那能等你对写呢?他一分钟里不知变多少次,纵使你能够赶快的擒着东边的一角,西边已经不同了。这色彩浓淡也因雨云的厚薄,天光的明暗变化的,这天地迅速的化工那能让你凡眼追随呢?……
(《疯了的诗人》,原载《新月》,1928年第2期)
In front of him was the unbroken ridge of Chu Lung Shan. The rain had stopped, and the clouds were flowing across the mountains in a broad tide. At one place a group of white clouds hid their shoulders, in others the watery grey mists covered them, making mountains and sky of the same colour. Their skirts could not be seen.
……
As he looked, his hand touched his paintbox, but while he was getting out his brush the mountain he was watching was no longer the same.”How can one ever hope to paint clouds and mountains in this way? They are so impalpable, smokey, and variable that in a single second there are an enormous number of changes; even if you catch a bit of the east side, the west will have changed. The colours change with the rain and mist, and the tones with the light from the sky; it is more than the eye can follow.
(“A Poet Goes Mad ”,T’ien Hsia Monthly ,Vol. 4 No. 4,April 1937,P402)
朱利安·贝尔在修改凌叔华的译文过程中,摒弃了凌叔华营造文化情境的描述性文字,如原作中体现自然世界光影、色彩变化的“濛濛漠漠”“缥缈轻灵”等语汇未能有效译介与传达。朱利安·贝尔此举旨在消除这些语句带给英语世界读者的文化陌生感,但却极大削弱了凌叔华小说所具有的文体特征与文化意味。“朱利安和凌叔华的翻译合作之所以有趣,不仅在于它集中体现了一个浪漫和文学的时刻,还在于这些文本揭示了跨文化的痕迹。他们之间除了具备通常这类合作的特质之外,还加入了一个维度——文化和语言的误解。”[8]因此可以说,在朱利安·贝尔与凌叔华合译过程中,凌叔华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她小说中所呈现出的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在英译中遭到删除与摒弃。1938年后凌叔华开始进行英文写作,1953年其英文自传小说《古韵》在英国出版并迅速成为畅销书,获得英国文化及评论界的关注与好评。当时英国著名的报纸《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对《古韵》的评论是:“叔华平静、轻松地将我们带进那座隐蔽着古老文明的院落。现在这种文明已被扫得荡然无存,但那些真正热爱过它的人不会感到快慰。她向英国读者展示了一个中国人情感的新鲜世界。高昂的调子消失以后,‘古韵’犹存,不绝于耳。”[9]那些被朱利安·贝尔所摒弃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在凌叔华的英文自传中得以保留并展现,由此凌叔华通过英语写作将具有独特魅力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英语世界。
四、结语
中国文学作品在被译成英文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不同的翻译者会采用迥然相异的翻译策略,产生出思想内涵及艺术风格不同于原文的英语译文。倘若是独译者,作为熟谙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西方译者或是具有流畅英语表达能力的中国译者,他们更多从自身的文化倾向与对作家作品的喜好等角度,以直译或改写的方式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译介;如果是中外译者组合形成的合译者,他们则需要兼顾各自的文学及文化思想倾向,协调不同的文化选择,采用更为灵活的翻译策略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译介。综合考察邵洵美与项美丽、陈世骧与艾克顿、凌叔华与朱利安·贝尔等人合作进行的文学翻译实践,我们可以发现译者的文化选择在翻译过程中起到较为关键的作用。合译者双方的文化选择与文艺思想倾向,不仅影响着翻译文本的选择,还决定了翻译策略及方法的运用。当二者的文化选择与翻译思想切近时,他们的翻译方法及策略较为一致。如在邵洵美、项美丽合译《边城》与哈罗德·艾克顿与陈世骧合译中国新诗的过程中,合译者都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趋向,因而选择较能体现传统文化内容的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并以多样化的翻译策略较好保存传统文化内涵,促进中国文化向外传播。但当彼此的文学思想及文化观念显示出较大差异时,外国译者将对原作进行重大改写,以迎合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文化心态。如凌叔华与朱利安·贝尔在合译小说《无聊》《疯了的诗人》的过程中,朱利安·贝尔对原作中饱含中国传统文化内质的语言进行了改写,使其译文更简洁而有利于英语读者的接受。本文所述几个中外译者组合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英译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体现出不同的文化选择趋向。希冀本文能为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策略研究提供有益的经验与启示,也为译者主体性文化选择研究提供有效的历史参照。
[1] 邵绡红.我的爸爸邵洵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149.
[2] Emily Hahn(项美丽).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Preface[J].T’ien Hsia Monthly.Vol.2 No.1 January 1936.
[3] 赵毅衡.对岸的诱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20.
[4] 夏志清.陈世骧文存序二——悼念陈世骧并试论其治学之成就[M]//陈世骧文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3.
[5] 陈国球.“抒情传统论”以前:陈世骧与中国现代文学及政治[J].现代中文学刊,2009(6).
[6] 哈罗德·阿克顿.《中国现代诗选》导言[J].北塔,译.现代中文学刊,2010(4):78.
[7] 陈世骧.陈世骧文存[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70.
[8] [美]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M].万江波,韦晓保,陈荣枝,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135
[9] 傅光明.凌叔华:古韵精魂[M]//凌叔华.古韵.傅光明,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