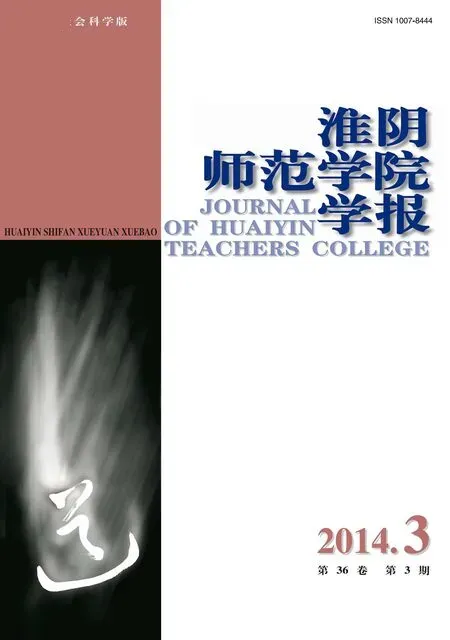体大思精 继往开来
——评李士金《朱熹文学思想研究》
周桂峰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无疑是一位巨人,他不仅对中国古代哲学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中国文学理论建构也产生过积极影响。然而,近一百年来,却因为时代、社会等诸多原因,对朱熹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全盘否定到否定中有所肯定、再到基本肯定中有所否定的历程,研究得很不深入,存在问题很多。不过,否定较多的是朱熹的理学思想,对于其文学思想则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与肯定,因而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多。自1969年张健出版《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1994年吴长庚出版《朱熹文学思想论》,到2000年莫砺锋出版《朱熹文学研究》,都代表了当时这一方面研究的最高成果。
要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研究领域有所斩获,进而占有一席之地,良属不易。然而,我们惊喜地看到,李士金竟然能在这一强手如林的研究队伍中脱颖而出,他的《朱熹文学思想研究》[1],便是在这一领域中无愧于时代的又一高峰。
一
学术研究的生命是创新。没有可以预期的创新,研究将失去动力;没有成果的创新,研究的价值便难以体现。李士金的这本专著可谓体大思精,创见迭出,是他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书中关于朱熹文学思想的创新性见解,不但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而且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本书先以三章分块剖析,分别探讨《诗集传》、《楚辞集注》和论历代作家作品。关于《诗集传》,李士金从微观起步,仔细地分析了朱熹对许多单篇作品的评价,总结出朱熹“《诗经》研究思想和艺术兼顾的特点”,并进而指出“朱熹在《诗集传》中,注解《诗经》时对每一首诗都分三个层次加以分析。第一层面是诗的语言文字,包括音韵、典故、文物、礼俗、历史背景等,这是正确理解诗的前提。第二个层面是总括诗的大意,主要是语言文字所反映的客观具体历史内容。第三个层面就是在以上两个方面研究的基础上探索诗的言外之意、启发意义及其诗的内在意蕴”[1]8。从具体的材料中得出了公允的结论,真正发掘出了《诗集传》的阐释学意义。关于《楚辞集注》,本书首先辨明朱熹“阐释《楚辞》意蕴之背景目的”,通过述评前人看法:“对此理解之深,评价之高,莫过于钱穆:‘今读其《楚辞集注序》,性情义理,相通兼得……俯仰今古,彼我死生,真如一体。就文论心,即心见道……诚非仅止乎文章之著述而已也。’张健在其研究专著中认为朱熹《楚辞集注》‘就文学批评的立场看,亦只吉光片羽而已’,理解不深。束景南谈朱熹的楚辞研究比较深切……”[1]61然后指出学界研究的欠缺之处:“纵观学界之研究,最欠缺者乃是对于朱熹楚辞研究具体的思想意蕴作深入的阐发。”[1]62进而指出,“党锢之祸使他在生活实践中更深一层地理解了屈原的伟大人格和充满艰难险阻的奋斗”[1]62,这是他集注《楚辞》的原始动机。“朱熹研究《楚辞》特别重视对于屈原伟大人格的阐述,把作家人品与文品联系起来加以深刻讨论,并且以扬雄为反面教材作比较,使得中国文学研究之深广度大大拓展,对现实人性之引导熏陶得到加强。”[1]65同时指出,“朱熹研究《楚辞》,深受其诗学研究之影响,尤其喜欢将二者进行比较”[1]63。关于朱熹对历代作家的评论,本书详细胪述论析了朱熹广泛而零星的文学见解。朱熹有大量的文学评论,散见于与学生的对话及其他文章中。这些见解虽然较为零碎,但蕴含其中的文学主张、审美取向则一以贯之,是他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前人在这一方面做过一些工作,如张健、吴长庚、莫砺锋等先生均曾在专著中论及。本书则以“竭泽而渔”的态度,对于朱熹文集和《朱子语类》中的关于文章、文学的认识,仔细爬梳,再分析归纳,从许多看似矛盾的论说中抽绎出朱熹的文学理论主张,揭示出“他在随机议论中自有其内在逻辑性”:“以时代论文关注国家盛衰,以义理论文兼及作家人品,以文道论文主张合二为一,以文辞论文提倡冲口而出,以风格论文赏鉴自然实在”[1]170,可谓用心良苦,用力诚多。
第四五章是分条纵论。第四章探讨朱熹的文学批评和文学欣赏,准确地抓住了朱熹研究文学、批评文学的特点:他“不放过一字一句的小节,不放过一字一句的音韵,不放过对文中事典的正确认识和理解……然后进一步从语言形象深入到思想意蕴的内部,探幽烛微。他提倡不要以自己的一己之见,代替文中的客观思想,要尊重客观的文学描写所反映的历史内容。作为批评家,还要以深刻严整的眼光,看出文学中的缺点和错误,无论是思想方面的,还是艺术方面的,这是对历史和社会应有的负责态度。朱熹还联系社会影响、全面地批评一个作家、全面地评价一个作家的具体作品都是相当独到的见解”[1]173。第五章探讨朱熹的广义创作论。朱熹的创作论是一个很少被人研究的课题,本书作了开创性的探究,分别从对当时形式主义思潮的批判、学习与模仿、态度和方法、创作主体的德行修养、生活体验与创作灵感等方面作出深刻的阐论。进而高度集中地指出:“朱熹深知作家本人心性修养的‘根本功夫’与作品之艺术性关系甚密,文学创作要驰骋而有法度,合乎中道,奇正结合,离开卓越的见识和通达的理路是无能为力的……关于写作态度和写作心理……他不赞成‘寻常好吟者’,对‘作诗间以数语适怀’表示理解,最好是‘真味发溢’,不得不作,不吐不快。在创作心态上也讲究自然而然,水到渠成。[1]232”较为完整地发掘出了朱熹的创作理论。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本书第六章“朱熹文学理论专题研究”,从朱熹的文学思想中选出几个最具特色的“点”来,进行深入探讨,分别探讨了朱熹的文道关系论、文体学说、“平淡”“自然”和“巧”、文气论、“天生成腔子”等。这几点可视为朱熹文学思想的支柱,其中尤以“天生成腔子”带有极强的独创性。本书于此也用力尤多。书中首先辨析国内四种主要的文学批评史对“天生成腔子”的解说,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说话写文章也好,搞文学创作也好,在文字修辞上恰到好处的就是‘天生成腔子’。”[1]340“‘天生成腔子’不但是总体的艺术性要求,而且也是以思想内容的正确与深刻为其核心的。‘天生成腔子’是对文章文学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容的综合的完美性要求,是朱熹理想主义文学观的一种生动形象的表达。”[1]348这是到目前为止对于朱熹“天生成腔子”的最充分的解释。
纵观全书,作者实现了对朱熹文学思想的全覆盖式的探究,既有“面”的广阔,又有“条”的贯穿,更有“点”的深邃,展示给读者的是对朱熹文学思想的全景式观照。其不断呈现的新见,使人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而宏大缜密的理论架构,又使人心悦诚服。
二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科学研究的使命就是要不断发现新的领域、新的境界,就是要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就是要不断刷新原有纪录,就是要不断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因而,求新成了科学研究者所永恒追求的目标。科学研究需要出新,但出新的根本目的是得实——最终揭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和本质;研究者应该求新,但求新的最后旨归是求是——掌握事物客观存在的内部规律。求新与求是应该是相互依存、高度统一的,‘新’只有在‘是’的前提之下,才有价值、才是可取的;‘新’而不‘是’,则徒然而为异端邪说,最终只能背离科学研究的宗旨。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自然也应该在不断求新的过程中实现求是。”[2]而求是必须从具体、可靠的材料入手,没有材料便是无米之炊。李士金的这部著作在资料的积累、甄别、分析和运用方面,可谓资料翔实,基础雄厚,堪称典范。
朱熹的研究资料极多。首先是朱熹著述丰富,涉及门类极广,《朱子语类》卷帙浩繁;其次是研究资料极多:朱熹生前,便不时地与人发生争论,产生了大量的论争记录;朱熹身后,800多年来的研究资料堪称汗牛充栋。要研究朱熹就必须熟读精研朱熹的著作,就必须充分占有相关的第一二手资料。十多年来,李士金同志朝斯夕斯,不仅仔细研读了朱熹的著作,还参看了不同版本,更搜集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尤其是为了确保资料的准确性,下了很多考订的功夫。他不仅确保自己引证资料的准确,其所引朱子原著资料和各种学界成果900多条,均确凿无误。还注意纠正其他论者的引文错误,曾专门撰作《从引文错误看“编辑”责任的失落》[3]。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在学风普遍浮躁的今天,显得尤为可贵。
众所周知,研究朱子学十分不易。因为,朱熹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家,具有多方面的成就与贡献,非潜心日久、积淀深厚、学力雄博者不能措手。同时,近百年来对朱熹的研究充满了武断的贬抑、荒唐的误解和随意的评释,更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因此,研究朱熹,不仅需要具有顽强的毅力、持久的定力,而且需要具备雄厚的学识基础。而李士金同志在大学毕业之后,先是师从南开大学朱一玄先生研修明清小说,获硕士学位;继而师从复旦大学王运熙先生研修中国文学批评史,获博士学位;最后进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精研古代哲学,进一步增强了学术研究的能力。尤其是当他仔细研究过朱熹的生平经历与哲学思想之后,回过头来研究其文学思想时,便如骏马入平川,一日千里已不在话下,撰作此书可谓水到渠成。
三
学术发展至今,已很少未经开垦的处女地。今天的绝大多数研究都是要在前人已经开垦好的“园地”里,精耕细作,有所发现。因此,学术研究必须正确对待已有的学术成果,在充分肯定、继承前人学术成就的前提下,推动学术向前发展。李士金的这本专著在对待前人研究成果方面,既能充分尊重前人心血,有一言可取,绝不遗漏;又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实现理论的超越。可谓融会贯通,继往开来。这为当下浮躁的学界立一标杆,具有示范意义。
本书对近百年来相关研究成果高度重视,引证数十百家,多所辨析批评。尤其是对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张健《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钱穆《朱子新学案》、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几部著述,引证辨析最多。在撰作本书之前,士金同志阅读研究了近百年学界200多篇关于朱熹文学的研究论文,对于有价值成果亦多所引证和评述。这种“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严谨治学精神在今日尤其难能可贵,这种精神也与士金同志淡泊荣利的内在修养密不可分。
尤其值得推崇的是,士金同志对于学术的公正公平的态度。他既不会因地位显赫而让步,也不会因感情亲近而阿私,更不会因资历卑微而唐突。例如,在论“天生成腔子”时,他历举国内四种重要的文学批评史对于“天生成腔子”的理解并加以评析时,对于其博士研究生导师王运熙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毫无回护之意。他在引用了其书关于“天生成腔子”的解说与评论之后,当即指出:“这里说‘信口恁地说’皆成文章,‘那只是古之圣贤才能办得到,后世之人则断然不能’[4]775,这显然不是朱熹本来的意思。朱熹认为作者只要达到一定思想境地和修养德能,就可以自然平易地说出好的文章……另外,本书著者把‘天生成腔子’与‘有个文字腔子’混为一谈,显然是错误的,朱熹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况下,针对不同问题谈的‘腔子’完全是两码事,而且是褒贬不同的两种情况。本书说‘什么是天生成腔子?朱熹没有讲明。’然后引用完全相反的内容来证明说:‘可见所谓腔子即一种类型化的风格或创作模式,相近于后来批评中所常用的格调、格套。’这在逻辑上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前后讲的两种情况根本不是一回事!如果说‘天生成一种类型化的风格或创作模式’,或者说‘天生成格调、格套’绝对是说不通的。朱熹说‘文字自有一个天生成腔子’。是形象的说法,即是他说的‘开口见心’‘自胸中流出’的意思……简单地说,‘天生成腔子’是美的最高体现,是理念的形象显现,但是形象显现的具体方面却是千姿百态、仪态万方的,不可能只是‘一种类型化的风格或创作模式’,也绝不是一种‘常用的格调、格套’。”[1]338议论中颇有“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精神。对于他的这种精神,王运熙先生大为赞赏。他在为本书所作的序言里说:“士金同志作为我的学生,在博士论文中批评过我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有关朱熹文学批评研究中关于‘天生成腔子’的内容,杨明同志在具体指导的时候不但没有表示异议,而且加以鼓励和欣赏。学术要求公论,这也是朱熹本人一贯的理学原则。”可以说,正是王运熙先生、杨明先生这样的科学态度,更进一步地推动了士金同志的研究工作,使他能够跳出许多人情的藩篱,以更加平和公正的心态来对待学术问题,从而得出较为接近于事实本相的结论。
总的说来,李士金的《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以创新的见解,翔实的资料,严密的论证,科学的态度,成为这一领域不可忽视的里程碑。他既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敢于超越前人,从而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李士金.朱熹文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2] 周桂峰.求新与求是[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5).
[3] 李士金.从引文错误看“编辑”责任的失落[J].编辑学刊,2007(3).
[4]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