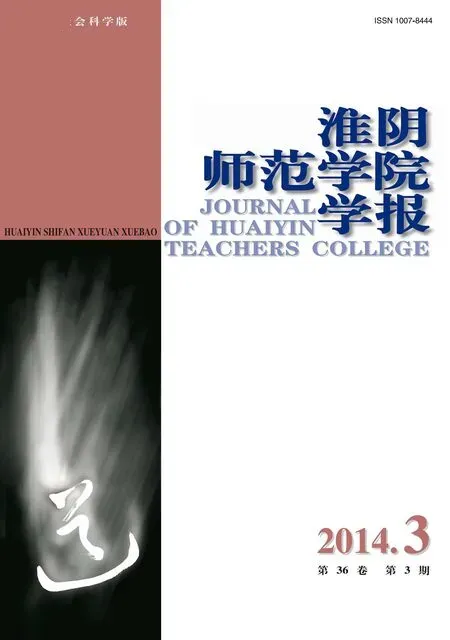智者的选择:曾国藩文献阅读择取观研究
郭平兴
(1.惠州学院 政法系, 广东 惠州 516007; 2.南京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93)
近代以降,国门洞开,思潮涌动,对于时人的阅读亦产生深刻影响:“读物的生产方式、读物内容和形式,阅读思想与阅读教育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1]547总体而言,影响阅读思想者有二:一是“封建正统文人,承接乾嘉余绪,继续就古代经书、古文、诗词等的阅读问题进行探讨,或阐发前人之微意,或补苴前人之缺失,使传统阅读理论更为完善,严密”;一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以一种全新的观点审视阅读活动,提出若干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1]548。现今普遍的观点认为,曾国藩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代表*关于曾国藩的评价问题,详见笔者博士论文《曾国藩文献阅读理论与实践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他终身酷爱阅读,其阅读思想包括文献选择观都体现在其日记及家书之中。
书籍的选择过程,是文献阅读与比较的过程,也是使阅读得以更有效进行的过程。就曾国藩而言,书籍的选择成为其阅读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曾国藩毕生的阅读经历,不论是其开列的书目,还是其所收藏的书籍,都可见出,他并非穷守一经,在书籍选择标准与要求上,内化了其对于书籍内容与版本等愈加深刻的理解,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择书观:广博与求善。36岁时,他总结道:“若夫读书之道,博学详说,经世之才,遍采广询,自度智慧精神,终恐有所不逮。”[2]448岁时,提出“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3]476。广博与求善是曾国藩阅读经验的凝练与升华,他常以此来指导自己及亲朋好友的阅读。广博与求善的书籍选择观,与其人生阅历和思想融通息息相关。广博的书目选择观念,主要形成于其中年以前,在阅读过程中不受门派的限制,经、史、子、集均有所涉及;及至“不惑之年”,伴随阅读境界的提升与思想的渐自融通,对书籍的选择逐渐转向“求善”,即针对某一具体学问时,按其自身要求而有所选择,或针对书籍的版本,或书籍内容等。
一、曾国藩书籍选择之广博观念
诚如上文所言,广博的择书观念,不限经、史、子、集,不分门派,是曾国藩而立之年之前择书的真实写照。依笔者之见,他之所以形成“广博的择书阅读观”,原因有二:
其一与曾国藩所立之志不无关系。“寻道”与“问道”是曾国藩毕生之志,不论是后人评价其为桐城学派的代表人物也好,还是评价其是“同治中兴”的重要功臣也罢,都是曾国藩在文献阅读中不断“寻道”的结果。曾国藩23岁提出“文以载道,文道并重”的观点,“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4]1375-1376;27岁表达自己需“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5]5;30岁时,希冀自己“可以无愧于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他认识到即使“今世雕虫小夫”,都能“溺于声律绘藻”,然作为读圣贤书者,更愈观其心所载之“道”。所谓“道”之内涵,既包括政治方面的“道”,亦含有文化视野的“道”。对书籍阅读来说,当然是越博越好。
其二与曾国藩的人生经历有关。与清代众多科举入仕之人一样,因科举之需,他必须涉猎经、史、子、集;28岁中式,可见其用力之深;散馆后久居翰林院,此尚可理解其为“文人”之身份;后来“身份”屡变:33岁时任四川乡试主考,执掌一省文柄,从37至41岁,先后任职礼部、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五部职能不一,所需知识亦不同。43岁投身军营,历经十余载,终获功成,身列“肱骨之臣”直至终生。如此经历,使其不得不广泛阅读,既完善自己,更能为其职守有所帮助。
具体而言,曾国藩的广博阅读观主要体现在书籍内容选择与所收藏书籍两方面。从书籍内容的选择方面,对待儒学而言,曾国藩不限儒家门派,均纳入其阅读视野之中;对于诸子百家而言,主张兼师并用;对于古文,五古、七古、五律、七律等文献都详加阅读。正如后世学者认为:他“既不算是一个纯粹的理学家,也不算是一个纯粹的儒学家,而是一个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集中国古今思想文化之大成的杂家”[6]1。从某种角度上说,不论何门何派,也不论是中国传统还是外来思想,他都广为博览,加以融会贯通,切己体察而心领神会,吸收对统治阶级有用的、对自身修养有用的思想,从而形成了自己复杂而又颇具特色的思想体系。从曾国藩所收藏的书籍亦可见其所选择书籍的广泛,根据建国初陈浴新在接收富厚堂(即曾国藩藏书之处)书籍形成的《公记书目》所载,曾氏藏书虽遭庚子之乱,但经曾纪泽取书于京后,达数千余册,该书目录中,分设“天”“地”“元”“黄”“宇”“宙”“日”“月”“海”“咸”“河”“淡”“鳞”“潜”“羽”“翔”“鸣”“凤”“在”“树”“白”“驹”“食”“场”“万”“草”“木”“被”“比”“盖”“方”等31部,各部之下分设“四号”,内含经、史、子、集等,涵盖甚广,其中除少部分为曾国藩后人收藏之外,大部分都是曾国藩自己收藏。
二、曾国藩书籍选择之“求善”观念
年至不惑,鉴于阅读经验与思想融贯,曾国藩对于书籍的选择,不再坚持之前所强调的“广博”思想,而是走向“求善”。48岁时他在《谕纪泽》中说道“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3]476。51岁时,他强调择书而阅,“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他认为“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7]738-739。曾国藩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择书“求善”,既有其“求善”标准,亦体现其善择的书籍品位。具体而言,可表现为“善择”与“择善”。“善择”是指从诸多的书籍中依据自己的兴趣与经验而选择,而“择善”则强调对所选书籍的版本等方面的要求。此二者,看似文字组合不一而已,实则可形象表达曾国藩中年后的书籍选择观念。
曾国藩之书籍“择善”思想,突出表现为其对书籍版本的追求。书籍版本的优劣,直接影响到读者的阅读行为。47岁时,曾国藩对袁芳瑛表露这一倾向*关于袁芳瑛藏书思想研究,见李日法《湘籍藏书家袁芳瑛》,《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袁氏号称“咸丰时期三大藏书家”之一,藏书有其独特之倾向,正如曾氏评价“阁下购书,专取宋、元人佳刻”,曾氏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可取,他说“仆意时代不足计,但取校刊尚精,刷印最初者为妙。苟宋、元、明之板而刷印于今日,犹汉唐碑帖而今日拓之,剥落补凑,夫何足贵?苟有佳纸初拓,则官板如康熙之《周易折中》、《书画谱》,乾隆之十三经、廿四史之类;私版如国初之汲古阁,近日之黄丕烈、孙星衍、秦恩复、胡克家、张敦仁诸影本,亦何尝不可奉为至宝?”[2]715曾国藩鲜明表达出自己对于书籍版本选择标准的看法:书籍版本的优劣与否,不能仅取决于时代远近,而更重要的是建立在书籍的“校刊”和“刷印”两个方面。有趣的是,曾国藩虽对袁芳瑛谈及自己对书籍出版时间“不足计”,但纵观其藏,却也收藏了众多宋元明时期的书籍。
具体而言,“求善”的择书观在曾国藩的文献选择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清代以前的书籍。清代以前的书籍,因其时间久远关系,除书籍内容之外,其书籍本身亦具价值,年代越久远,价值越高。曾国藩自身非常重视选择清代以前的书籍,据《曾氏公记书目》的著录,以及湖南省图书馆、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曾氏藏书核对印证,曾国藩收藏的清以前古籍甚多,宋元明刻本无所不具,诸如“宋绍熙刻本《公羊传》3部共11册,宋刻本《仪礼疏》、宋抚州本《礼记》16册;北宋本《前汉书》64册,《后汉书》6册,还有宋本《庄子》、《笺注陶渊明集》等;元刻本有《文献通考》,明刻本有《周易传义大全》、《仪礼注疏》等100余种”[8]127。在书籍的选择与对比中,曾国藩形成了自己对古书的看法,上文其对藏书家袁芳瑛所说尚且为一,除此之外,他甚为推崇北监本,认为“北监本最为精雅,故乾隆初武英殿刊全史,即照北监本模样,而殿本有不及北监本者”[2]32。遗憾的是,在《曾国藩全集》中,笔者只找到曾国藩帮其好友陈岱云购买的一部北监本《廿一史》,并无其他更多记录,曾国藩却对此津津乐道,形同己购。笔者以为,曾国藩在“贬低”与“推崇”古书的矛盾心态中,体现了其在不断收藏书、不断选择与对比书籍中所形成的经验积累,这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驱使其收藏更多的古籍,一方面又更为重视清代当朝的书籍。在这种对比中,加深了他对当朝书籍的认识,比如重视殿本书、私家名刻等,虽时间不可比攀,却在版本等方面平分秋色。
第二是清代殿版初印本、单行本及私家名刻。殿版书均为精刊精校,初印之书则版本更好,因而倍受爱书人青睐*关于清朝殿版书的研究很多,见翁连溪《清宫武英殿刻书》,《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4期。。曾国藩认为“殿板书初印者,多可取也”[2]715。在《曾国藩全集》中,笔者发现他数次论及殿本书,主要体现在他和诸多友朋书信往来之中,表达他对于殿本书的看法,以及广而求购殿版之书。如37岁时,他在《致陈源衮》中说:
北监板最为精雅,故乾隆初武英殿刊全史,即照北监本模样,而殿本有不及北监本者。辽、金、元三史,殿本将各传原名一一改译,如‘脱脱’改‘脱克脱’之类,令人不识其为何如人。故买殿本全史者,仍须买北监本辽、金、元三史以便宜读。[2]32
此时,他拿北监本与殿本书相比较,指出殿本书的诸多不足。笔者以为,此时曾国藩对殿本书认识还不够深刻。之后他对殿本书的评价即可管窥一斑。
49岁时,他在《加刘良驹片》中说:“敝处书籍太少,江西如有殿版初印二十四史,敬求代为购买,虽重价不惜也。如不能得全书,即购得零种,或一史、二史、三、五史、十余史皆可。总以初印为佳,后印者则不足取。国朝刻书,远胜前代。殿版如《十三经》、《廿四史》、《全唐诗》、《图书集成》、《五经萃宝》、《书画谱》之类,凡初印者,无不精雅绝伦。”[4]1334
54岁时,他在《复何栻》时说“殿本《二十四史》收到,精雅绝伦,容日备价奉纳”[9]4303。57岁时,他在《复薛福辰》时说“《续三通》若无旧印者,即可不必刷印新者。凡刷殿本各书,动须邀集数十人醵资凑办,为首往往不免赔垫,而刷成之后,缺叶难于抄补,以不印为是”[10]6579。
信中,曾国藩列出数种初印本书籍,认为是“精雅绝伦”,也将初印本与后印本进行比较,认为“后印者不足取”,因为“缺叶难于抄补”。现据统计,曾国藩先后收藏的清精刻有清内府五色套印本《朱子大全》,殿版《二十四史》《怀鹿堂全集》《御制文全集》《张文贞公集》《二希堂集》《李榕村全集》《自田草堂稿》等1 000余部。其中有100多部已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8]127。
清代有很多的私家名刻。私家所刻之书,或涉家中先辈之作,或乡邦先贤之书等,视为非营利性出版行为,往往非常重视版本,讲究版刻质量,且印数往往不多,颇具收藏价值,曾国藩甚为喜欢,在其丰富的藏书中有清抄本数十种,清人诗文集304部5 360余册。足见其对于清人诗文集的喜好程度。52岁时,他向郭嵩焘阐述了自己对私家名刻的观点,他说:
国藩尝谓乾、嘉好事诸君刊刻古书,其精雅实超轶宋、元善本,就余所见,如黄荛圃、卢抱经、孔巽轩、孙渊如、比秋帆、阮伯元、胡果泉、朱竹君、秦恩复(忘其号,江都人,刻《法言》等书)、汪孟慈、吴山尊诸家,所刻书箱,每一玩把,使人穆然意远,阁下若遇诸家初印本,幸以重价购寄,言明不打把戏也。[4]1196
从中可见,曾国藩熟悉清代私家名刻,对清代十位刻书名家所刻之书,甚为赞许,且愿广为收藏,“若遇诸家初印本,幸以重价购寄”,足见其喜好之至。
第三是曾国藩对各地的地方志,也情有独钟。他将自己所历任官职之处的地方志都广为收藏加以阅读,现据统计,曾国藩“先后收藏的方志多达56种60部”[8]127,如日记里曾提及的方志有《清河县志》《曲阜县志》《邳州志》等。
其他书籍如稿本、抄本,曾国藩依据自己所好也进行了有选择性的阅读,他一生中收藏的清抄本有数十本之多。如他在1868年,请朱兰对邵晋涵先生的《孟子述义》《韩诗内传考》等书的尚存稿本进行寻访代购。
此外,曾国藩对于书学之书亦为偏好,也常寻访诸多名家之书帖。如1859年,他与朋友书信中言及“恳慈民便中觅购《书谱》一册、西安、同州《圣教》各一册,皆须略旧者。此外,如《三坟记》《迁先茔记》《张猛龙碑》《道因碑》及昭陵各碑,能为觅得二、三种为荷”[9]3569。
三、开列推荐书目:曾国藩所择之书之分析
曾国藩在不断的书籍收藏与阅读过程中,逐渐养成了阅读求博求善的观念,遍览其日记,可见他从中式之后,即有意开始向家人、朋友推荐书目。这种书目的推荐,或出于科举应试之需,或出于家庭教育之要,亦有发自内心的高度认可而广为推荐。具体来说,他推荐书目有阅读日课、开列书单两种形式。
阅读日课即每天要阅读的书目。曾国藩中式较早,在其家族及其朋友圈中,可算是学业早成,随后其弟跟随其学习。他结合自己的阅读体会,推荐书目,定为日课,是为常事。在其家书及日记里常会对所阅读的书籍进行总结性评价,认为是熟读书目。日课书籍主要是为应试而定的,诸如《易》《文选》等。在阅读诗类书籍的过程中,33岁的他就说过应该从专集开始,并列出了自己选择的诗学阅读书目,“于五古则喜读《文选》,于七古则喜读昌黎集,于五律则喜读杜集,七律亦喜杜诗”[3]65。
开列书目,即是直接向他人推荐书籍。按现有文献记载,曾国藩在其日记、家书、与朋友书信中比较系统地列出了六次书目,从34岁(道光二十四年)的第一个书目,至52岁(同治元年)的最后一个书目,书目由简单到详细,品述愈加清晰,指导色彩与作用更趋明显。
如曾国藩第一次列出的较为系统的熟读书目:“《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3]83该书目中,书名非常简单,内容涵盖经、史、子、集。结合现代阅读心理学,可分析其所选择书目之理由:重视《易经》,乃是追求完善的人生之道;推荐《史记》《明史》史学著述,说明其有总结研究历史的兴趣;列《庄子》《屈子》为其熟读内容,说明此时他已注重自身修养的多重性,追求上进但并不激进;熟读《诗经》、杜诗、韩文,说明他非常重视文学修养;其中未列“礼”学的书籍,说明此时的他还没有重视“礼”学文献。
咸丰八年五月时(48岁),曾国藩在《致沅弟》信中再开书目,对“本末之学”的书籍勾勒说明。“学问之道,能读经史者为根柢,如两《通》(杜氏《通典》、马氏《通考》)、两《衍义》及本朝两通(徐乾学《读礼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皆萃《六经》诸史之精,该内圣外王之要。若能熟读此六书,或熟其一二,即为有本有末之学”[3]393。担任过礼部侍郎的他,之后又历事兵戎,对于同样身处军营的弟弟,如何讲求内圣外王之道,认识已是深刻,把经史列为根柢,必须熟读一二;此外,“礼”学书籍开列其中,说明他已充分认识到“礼”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由此也可看出,此时的曾国藩,书籍的阅读与选择更加趋向经世致用。
咸丰八年九月时(48岁),曾国藩在《谕纪泽》信中,总结性说明自己嗜好之书,实则为其子列出阅读书目:“十三经外所最宜熟读者莫如《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余生平好此四书,嗜之成癖,恨未能一一诂释笺疏,穷力讨治。自此四种而外,又如《文选》《通典》《说文》《孙武子》《方舆纪要》、近人姚姬传所辑《古文辞类纂》、余所抄十八家诗,此七书者,亦余嗜好之次也。凡十一种,吾配之《五经》《四书》之后,而《周礼》等六经者,或反不知笃好,盖未尝致力于其间,而人之性情各有所近焉尔。”[3]430推荐书目细致入微,内容涵盖甚广。所列书目有几个特点,一是经部文献,已含十三经内容,较之前的经部文献阅读量加大,应是曾国藩对其子科举应试有所希冀;二是“礼”学文献并未出现其中,究其原因,应是纪泽当时年仅二十岁,年轻尚轻不宜阅读艰深难懂的“礼”学书籍;三是曾国藩不仅列古人书籍,还将“近人”姚姬传所选的《古文辞类纂》及自己所选的十八家诗,列为熟读书目,究其原因,应该是曾氏认为此两书都是阅读经验的总结,对于其子学术能力尤其是文学能力很有帮助;四是曾国藩将体例完备的政书《通典》、地理学巨著《方舆纪要》、兵学圣典《孙武子》、著名字书《说文》列入书目,表明其希望纪泽能有较宽广的阅读视野。
曾国藩在同一年内,给弟弟和儿子各列一书目,其间差异明显。笔者以为:沅弟此时已为军中将领,而纪泽尚为科举而谋,两者身份有异,阅读的书籍自然有所不同。
咸丰九年(49岁),曾国藩在《谕纪泽》信中,以韩退之、柳子厚、王念孙父子为例,详细告知读书宜有所选择。曾氏详细列出了韩、柳、王氏父子的阅读书目,再次将自己所好的十余种书籍告之,并说“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3]476。这对于被教育者曾纪泽而言,均具有指导作用。
咸丰十年(50岁)两次列出书目。闰三月,曾国藩在给友人何栻书信中说:
鄙人尝以谓四部之书,浩如渊海,而其中自为之书,有原之水,不过数十部耳。“经”则《十三经》是已。“史”则《廿四史》暨《通鉴》是已。“子”则《五子》暨管晏、韩非、淮南、吕览等十余种是已。“集”则《汉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来二十余家在而已。此外入子、集部之书,皆赝作也,皆剿袭也。入经、史部之书,皆类书也。不特《太平御览》《事文类聚》等为类书,即《三通》亦类书也。《小学近思录》、《衍义》《衍义补》,亦类书也。[4]1335
同年四月,在他给李续宜的一封信中,列出了其人生最后一次综合性书目,名为指导他人购书,实可看作其择书观的总结。信中说:
鄙人尝谓古今书籍,浩如烟海,而本根之书,不过数十种。“经”则《十三经》是已。“史”则《廿四史》暨《通鉴》是已。“子”则《十子》是已(五子之外管、列、韩非、淮南、鹖冠),“集”则《文选》、《百三名家》、暨唐宋以来专集数十家是已。自斯以外,皆剿袭前人之说以为言,编集众家之精以为书。本根之书,犹山之干龙也,编集者犹枝龙护砂也。军事匆匆,不暇细开书目。阁下如购书,望多买经史,少买后人编集之书,为要。[4]1375-1376
曾国藩的这两个推荐书目,可视为其人生中最完善的推荐书目,突出特点有二:一是推荐书目全面且具体,经、史、子、集均列入其中,且对类书进行了说明,完全符合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对其亲人友朋的阅读教育所需;二是同类文献进行总结比较,得出“自为之书”“赝作、剿袭”之书,这种比较,可视为其自身的阅读经验的言传身教。甚为可惜的是,其中部分书籍名称未完全列出,如“‘集’则《文选》《百三名家》、暨唐宋以来专集数十家是已”,其中,他并未列出唐宋以来的数十家专集之名,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或是因为当时众人熟知之故,或是举一反三之感叹。
曾国藩数次所列书目,大致可分五类:一是四书五经,各书目都有所收录,其中《易经》《诗经》提及频率更高,此乃传统士大夫之身份使然;二是《廿四史》和《资治通鉴》,在前四史中,曾国藩突出了《史记》和《汉书》,之后历代史书中,他更强调《明史》,身处乱世的他,深谙总结前朝历史经验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三是先秦诸子,《庄子》《屈子》等书,很早就进入其阅读视野,身入兵戎之后,《孙武子》亦成为其重要的文献资料;四是诗文系列,曾国藩爱好古文、诗,他认为杜诗、韩文、唐宋以来数十家专集,均应熟读,且五古、五律、七古、七律予以对应性阅读,如“七古则喜读昌黎集,于五律则喜读杜集,七律亦喜杜诗”[3]65;五是其他类书籍,如《说文》《方舆纪要》等。笔者以为后两类的书籍选择,更多是的出于其修身、修文之需。
总而言之,曾国藩所选择的书籍是其认为必须阅读之书。在其日记里及其读书录中,大部分围绕这些书籍而展开。这些书籍的选择,其实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一种推荐书目,是曾国藩多年的阅读心得,时至今日,亦不失为今人从事古文阅读之门径。
[1] 曾祥芹.阅读学新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
[2]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M].长沙:岳麓书社,1995.
[3]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M].长沙:岳麓书社,1995.
[4]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M].长沙:岳麓书社,1995.
[5]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M].长沙:岳麓书社,1986.
[6] 罗益群.曾国藩读书生涯[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
[7]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M].长沙:岳麓书社,1995.
[8] 谢晓波.论曾国藩的藏书楼思想[J].图书馆学刊,2008(5).
[9] 曾国藩全集·书信(五)[M].长沙:岳麓书社,1995.
[10]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M].长沙:岳麓书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