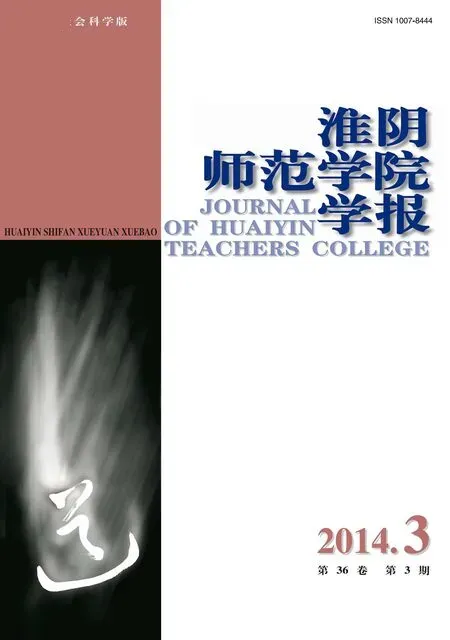旧调新声,竞胜一时
——略说清代民歌时调的内容与特点
周玉波
(江苏邮电报社, 江苏 南京 210037)
在通行的文学史语境中,“明清民歌”如同“明清小说”,几成固定搭配,而因为有卓珂月“我明一绝”(陈宏绪《寒夜录》)的表述,清代民歌似乎存活于明代民歌的阴影之下,自身面目难得彰显。事实上,与明代民歌相比,清代民歌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前辈学者傅惜华先生以为其“犹承明季余绪,旧调之外,复出新声,竞胜一时”[1]59,私以为堪称定论。
一
人们今天讨论的明代民歌有两个特点,一是除冯梦龙辑《山歌》《挂枝儿》外,其他民歌更多地是以“寄生”于各类戏曲选集的形式流传于世;二是文献记载的明代民歌,以江浙民歌为主,鲜见北方民歌(如“打枣竿”)身影。逮及清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各朝虽例禁森严,申明凡造作、刻印、市卖、买看“琐语淫辞”(清魏晋锡纂修《学政全书》卷七《书坊禁例》*见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2月版。下转引《史料》不注。)者科以重罪,但是效果甚微,民歌时调传播方式繁多(口传、刻印、抄写),传播范围广泛(城市、乡村),而且南北方民歌均展现了各自的姿彩。
清代南方民歌的代表性文献首推《新镌南北时尚万花小曲》。《万花小曲》目录尾有识语,谓“此集小曲数种,尽皆合时,出自各家规式。本坊不惜重金镌梓,以供消闲清赏”。傅惜华所见为乾隆九年(1744)京都永魁斋刻本,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所依底本则是郑元美梓行之金陵奎壁斋本,书末署“岁在丙申秋月”。论者由郑元美的刊刻活动时间,推定此“丙申”为清顺治十三年(1656)[2],如是,则奎壁斋本《万花小曲》当为现今所见最早的清代民歌专辑。
《万花小曲》辑录“小曲”“劈破玉”“西调鼓儿天”“吴歌”“银纽丝”“玉娥郎”“金纽丝”“十和谐”“醉太平”“黄莺儿”等时调小曲,傅先生云“材料丰富,足资研讨”[1]13。私以为“足资研讨”者三。一是因其面世较早,内容与风格均与明季民歌相近,此或即“余绪”说由来。二是“小曲”“劈破玉”“吴歌”“银纽丝”等地域特征明显,由金陵书坊印行,可谓契合,京都书坊随后翻刻,说明民歌的生命力无远弗届。三是《万花小曲》保留了民歌由明入清的痕迹,清晰昭示了其虽处异代仍“平滑演进”的轨迹,即保证了时间链条的完整无缺。
奎壁斋本《万花小曲》之后,另一南方民歌的代表性文献是由“姑苏王君甫”梓行的《新镌南北时尚丝弦小曲》。傅惜华云虽为姑苏刻本,所载小曲“不尽为江南产物,燕赵俗曲,亦多采摭”,并云原书未著刊刻年代,“观其版刻形式及其内容所录,确知为乾隆初期之书籍”[1]81。按王君甫尚刻有《时尚小曲 万家合锦》与《大明九边万国人迹路程全图》等,其中《全图》印行于康熙二年(1663),由是知“乾隆初期”或可上推至康熙朝。《丝弦小曲》起首亦是“小曲”,数量为11首,少于《万花小曲》的36首,疑一是全璧,一是在其基础上的删减版。
同治八年(1869),方浚颐(子箴)理两淮盐运。方着意时调小曲,论者以为《晓风残月》即为其编撰[3]。《晓风残月》辑有“滩簧”“南京调”“淮红调”“碧波(破)玉”“满江红”等南方俗曲,“俏人儿你去后,如痴又如醉”“俏人儿人人爱,爱你多丰采”,等等,直接又见于道光年间扬州艳情小说《风月梦》中,另有一些则成为扬州清曲的流传曲目。
实际上的南方民歌种类、数量远远超出文献所载,如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查禁淫词小说札,所列“小本淫词唱片目”计有“杨柳青”“男哭沉香”“龙舟闹五更”“五更尼姑”“十送郎”等共111首,大部均在《万花小曲》《丝弦小曲》《晓风残月》之外。
较早的北方民歌代表性文献是乾隆六十年(1795)梓行的《霓裳续谱》。《霓裳续谱》共8卷,收曲调约30种,共计620余曲。前3卷是其时北方流行的“西调”,后5卷虽包罗众调,仍以北曲“寄生草”与“岔曲”为多,少量的“银纽丝”与“扬州调”等,扮演的是“移民”角色,由此亦可见出文化融合时代南北方民歌交融发展的情形。
嘉庆、道光年间小曲集《白雪遗音》,是底层文人着意搜罗、集腋成裘之作,曲调有“马头调”“九连环”“八角鼓”“南词”“玉蜻蜓”等,仍是北方民歌汇编,曲词有些则直接袭自明季南方民歌(如“熨斗儿熨不开的眉间皱”等)。
道光年间刻本《时调雅曲初集》《时调雅曲二集》,内中标名“马头调”,实则也有其他曲调,如《二集》中有“勾调”“荡韵”“扬州歌”“湖广调”等。
乾隆以后,各地书坊争相发行时调小曲,文人、民间艺人亦有意识地予以收集、整理,较为著名者,书坊有北京的百本张(持续时间长)、聚卷堂,文献有《京都小曲钞》《偶存各调》《万曲选锦》等*均见浦泉、群明辑《明清民歌选甲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11月版;《明清民歌选乙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8月版。。
二
民歌是私情谱,明代如是,清代亦如是。
私情民歌中两情相悦的倾诉,相当一部分堪称“真挚动人”*见赵景深为《霓裳绪谱》所作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版。。这一点可以南方民歌为代表。如《万花小曲》:
这两日不曾见,未知亲人安不安。从离了你泪珠儿就何曾断,数归期十个指尖都掐遍。你遇着有窍的人儿尽着和他顽,欢娱去对着镜儿把我念一念。
做了一个蹊跷梦,梦儿中会我亲人。那亲人说的话儿知轻重,又未知亲人心顺不心顺。觑着你俊庞儿一似莺莺,喜杀了我把衾儿枕儿安排定。
从南来了一行雁,也有成双也有孤单。成双的欢天喜地声嘹亮,孤单的落在后头飞不上。不看成双只看孤单,细思量你的凄凉和我是一般样。
此类民歌,与明代的“挂枝儿”“劈破玉”在精神上一脉相承,“旧调”云云,当亦有此意在。
总体上看,与明代民歌相比,清代民歌“去文人化”、世俗化倾向越发明显。细而言之,傅先生所谓“新声”,私以为可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一是在私情的内容上,清代民歌较明代有所拓展,在冯辑《挂枝儿》里还有些遮遮掩掩的风月题材,在清代民歌中得到了张扬,标题即为“偷情”“调情”乃至“烟花”的篇什比比皆是。如《晓风残月》有《南京调 淮红调·烟花自叹》:
许多人不趁奴的心,冤家才如奴的意,可惜会迟了你。佳期事暗约你还须暗的里去,莫被妈儿来生疑。风月场中姊妹多,少只(这)一个来那一个,代(待)你都是虚情假意,比不得奴代你。真心同你好,你已不知道,久后共了心腹才知晓,你验我的心机好似不好。非是奴夸口句话,爱你必须爱到底,那才等个有情的。疼你必须疼到底,几世不分离。
俏人儿奴爱你干净□认正,说出句话来疼煞人。还爱你人前装老实,避地里会调情,引动奴的心。你想与奴佳期事,只要你言儿有信,谩(瞒)着奴的母亲。奴家还未接过客,年纪轻小就与客梳嘴未曾梳身。冤家哎,爱上你这个人,倘若是奴家身子梳了你,怕的冤家嘴不稳,酒后乱告诉人,句句话儿都是真。冤家嗳,怕你败坏了奴的名声。
二是在语言风格与情趣取向上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北方民歌而言,“西调”“马头调”的大规模参与,使得原先以细腻、清新见长的民歌充斥着浓烈的“胡同味”。如《时调雅曲初集》中的《带靶马头调·雏嫩的妞儿》云:
有一个雏嫩的妞儿乍出门子刚十五,喜相端庄长的一督。不爱浓妆天然的素,微搽点儿胭粉淡而不俗。茉莉花儿戴一嘟噜,越显的头发墨锭乌。穿一身娇滴滴儿的洋蓝布,拾朵(掇)的狠(很)干古。要是有客儿来时,他替你把汤儿出。或喝酒或喝茶或是开铺,你要净打白仗儿,那可算不了一出。你要走他往你动一点儿,米汤开一点儿,唙咕,你可就上了他的鬼画符,一睁眼他就有了主心骨。你若是来打糠灯,他也会指东说西,嘴头儿刻薄狠挖苦,不怕你心里犯思乎。再不然酒瓶子把你泡起来,动了那子咧子腔儿大气,数一句给你六晆不舒服,你好似怯粮斛的谷子坐不住,走道儿罢别在这儿假买熟。他的那玩艺儿真不少,会唱曲合二簧琵琶弦子掸(弹)了飞熟。
满纸方言,绕口令式的贫嘴,尖酸的调侃与幽默,所有这些,与“俏冤家我待你如金似玉”“一见乖乖把念头起”的软款温存式南方民歌大异其趣。
三是清代民歌中社会题材内容的比重加大。私情是民歌的主流,私情之外,清代民歌开始有意识地涉猎更为广阔的社会题材内容。这些内容,与其时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可以说是照应了乐府民歌的传统,也大大延展了清代民歌的民俗学、历史学价值。如聚卷堂唱本有《马头调·代(带)病姑娘》:
代了病的姑娘儿哟闷坐在良房,又是那秋雨儿初晴寒蛩儿唧唧,弱体儿当不起晚风儿彻骨凉。独对孤灯虽然不是个悲秋儿佳人,似这等断魂的景况,也难免那意中的凄凉,暗说道最苦苦不过这烟花柳巷,无语暗悲伤。自从那卖身落水,可怜我奶黄未退背井离乡就撇舍我爹娘。那老鸨儿他凶如虎恶似豺狼,他那管举眼无亲朝打暮骂,为演风情也受过些冻饿,学弹唱挨了些棍棒。缠丝脚疼痛难当,无病吃药为的是不生不养。总有那万分的委曲,在无人之处何曾敢痛哭过一场,不过是暗暗想我的爹娘。十三岁是我那倒运的年头,难星降遇见了个狠毒的魔王。他倚仗有银钱买转老鸨儿,喝令咱交接全无一丝半点惜玉怜香。
此类妓女哀叹身世遭逢的民歌,前代少有,清代尤多。《烟花自叹》《雏嫩的妞儿》等虽然也说烟花故事,却以自怜、谑笑为能,《代(带)病姑娘》则是劝世、骂世、醒世。另如光绪间钞本《小童生》云:
一更里个小童生进考场,手提着考篮儿眼泪汪汪。怨着一声爹,恨着一声娘,不该哟将孩儿逼进考场。眼瞌塞(睡)真难过,肚皮里贼忒忒急急忙忙。二更里个小童生到考场,忽听得点名儿人语喧嚷。挤得一身汗,手臂酸汪汪,无端哟吃苦头实在难当。张三李四多点过,点到哟自己名如见阎王。三更里个小童生坐考场,呆顿顿等题目,要做文章。点起红蜡烛,急忙开考箱。题目到翻老文,仔细端详。大小文府多翻过无对题,只好要大家商量。四更里个小童生坐考场,手拿着笔管儿搜尽枯肠。多谢老枪手,送你两只洋,替我哟做一篇救命文章。水烟考食凭他吃,方能够做完篇真真叨光。五更里个小童生出考场,居然哟交卷儿,得意洋洋。跨出高步槛,绷豁裤子裆,叫声老头儿接去书箱。归来夜饭就吃罢,困一忽到明朝,偏要轻狂。
再如《摇船》:
水里摇船水里歇,水里摇船能得几个大铜钱。六月晒得泥鳅黑,十二月冻得紫蝴蝶。水里摇船水里歇,水里摇船能得几个大铜钱。穿身破衣千个穷心结,头上带个井乃圈。伸脚伸去到灶前,缩脚缩在下巴前。水里摇船水里歇,水里摇船能得几个大铜钱。绿汪汪水当褥子,丝草蓑衣盖身体。万台眼浪当枕头,罗非眼里望青天。
景况凄凉的落难女子、为博功名“眼泪汪汪”的小童生与靠“几个大铜钱”谋生养家的辛苦船工,混杂于众多的痴男怨女当中,使得清代民歌画卷的底色较前代更为繁杂厚重。清末民初,此类民歌与文学革命、社会改良等思潮相呼应,俨然成为一道惹人注目的文化景观。
三
与明代民歌相比,清代民歌最为突出的个性特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曲调(牌)更为丰富。受限于文献,今天可见的明代民歌的常用曲调(牌)只有“挂枝儿”“罗江怨”“劈破玉”等10多个,而且其中有一部分离文人小曲不远。到了清代,一方面,曲牌较明代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民歌曲调与曲牌的关联度降低,“湖广调”“南京调”“利津调”“济南调”“福建调”“西调”等地方曲调与传统的“挂枝儿”“银纽丝”一起,争奇斗艳;八角鼓、子弟书、鼓词(大鼓书)、弹词等“叙事长歌”[4]各擅胜场,四方民众“你唱我和”,“恋恋不舍”(余治《得一录》卷十一之二)。
二是与地方戏曲的联系更为紧密。本文行文虽曰“民歌”,实则如标题所示,是“民歌时调”并称,因为与明代相比,清代民歌“唱”的成分加大,表演功能得到强化,与“曲艺”的分野愈发模糊,常规的“民歌”概念已经难以涵盖全部内容。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各地民间小戏、小唱兴起,其中一些受欢迎的唱腔、唱段乃至表演形式,慢慢地演变成为独立意义的“俗曲”即时调,其与此前更近散曲的“民歌”,在形制与篇幅上均有差异。著名者如莲花落(闹)。莲花落本是乞丐走村串户乞讨时所唱歌曲,光绪初张焘《津门杂记》则载有“妙龄少女登场度曲”事,曰“粉白黛绿,体态妖娆,各衔所长,动人观听”,“坐客点曲,争掷缠头”,后“复有作者”,竟改名为“太平歌词”云。“太平歌词”之前,莲花落的基本功能,始终没有进化到多演绎完整故事的鼓词(书)的程度,是以本集仍将其视作时调一种。其二,因缘际会,民歌时调也会发展成为地方戏曲,或为地方戏曲提供营养,成为地方戏曲的重要因子。如滩簧。滩簧原是江浙一带的民歌曲调,后流传到北方,《霓裳续谱》卷八辑录有弹黄(滩簧)调三种,其一云:
昨宵同梦到天台,今晚冤家还未来。风弄竹声归晓院,月移花影上瑶阶。莲步稳,立妆台,迢迢长夜实难挨。壶中漏滴更将尽,案上灯残门半开。郎嗄,你莫非别恋着闲花草,莫不是先生严禁在书斋。早难道被人识破了机关事,因此上阻住蓝桥未得来。教奴这一猜,那一猜,多因是你薄幸不成才。明宵若得重相会,我要问问你,会少离多该不该,休要在我的跟前再卖乖。[清江引]一夜无眠,多情不在,寂寞好难挨。今晚等他来,同解香罗带,今宵勾却昨宵的债。
此种滩簧,虽然有人物,有对话,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但是短小精悍,与“挂枝儿”“劈破玉”曲并无二致。滩簧调向戏曲发展,繁衍为沪剧(上海滩簧)、锡剧(无锡滩簧)、甬剧(宁波滩簧)、姚剧(余姚滩簧)等,形成戏曲的滩簧声腔系统。另有一些滩簧,则保持时调小唱形态,长期存活于民间[5]。
北方流行的岔曲,表演时固然有一定的程式,有角色的分配(拆岔),其中的小岔,亦仍然具备时调的身份。
清代民歌与戏曲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贴近关系,最为直接的结果是鼓书(鼓词)、弹词那样的“叙事长歌”强势进入民歌园地,民歌、曲艺、戏曲的界限开始模糊,进而成就了民间文化演进史上俗曲、戏曲众体兼备、通达朝野(清宫设升平署,专为承应帝王后妃听戏娱乐)的传奇。
三是清代民歌的本体特征更为鲜明。说及明代民歌,通常是在文学演进的框架内讨论其价值、功用,研究其与晚明文学新思潮的互动关系,冯梦龙所说“发名教之伪药”(《叙山歌》),亦是这个意思,换言之,明代民歌更多具有的是工具作用。清代民歌的情形有所不同。论者以为,在与文学的关系上,清代民歌所起作用不像明代那么重要,清代文学总体偏雅,文学、文化风尚与明代不同,虽也有“格调”“肌理”等流派之争,但主要着眼于“内部挖潜”,少有“真诗在民间”(李梦阳《诗集自叙》)、“闾巷有真诗”(袁宏道《答李子髯》)那样的闳通识见,前说方浚颐以及吴调元(辑《粤风》)、招子庸(辑《粤讴》)诸人对民歌的喜好与鼓吹,其成绩与影响有限,远未达到冯梦龙、李开先诸公的层次。到清末黄遵宪重视民歌,则“已经是很迟的事了”[6]。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可说尤多。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犹如文学的一体两翼,虽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如梁实秋所说民间创作对文人创作的“刺激”[7])是常态,其实各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有清一代,民歌以固有形态生长发育,无论是“真情”的追逐还是“私情”的宣泄,甚或是肉体的狂欢,均表现出向其本体与生命原初的回归——《诗经》、两汉乐府乃至明代民歌,均是其曾经的黄金时代。只不过到了清代,民歌的生态与其时的社会生态一样,更为复杂多样,更为气象万千,前文所谓曲调(牌)丰富、与地方戏曲联系紧密,都是例证,传播加速、受众与影响面逐渐扩大引发一轮又一轮的讨伐、禁绝,亦是例证;“旧调新声,竞胜一时”云云,所指亦大体如是。
综而言之,清代民歌在内容、形式、传播与接受方式等诸多方面,有着自己的特点,尤其是存世数量及介入民众日常生活的深度、广度上,均为以前历代民歌所不及,清代民歌与近代戏曲乃至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等,更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课题。
[1] 傅惜华.曲艺论丛[M].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
[2] 尤海燕.《歌林拾翠》刊刻年代考论——兼论奎壁斋郑元美的刊刻活动时间[J].文献(季刊),2010(3).
[3] 柯美而.清代俗曲集《晓风残月》研究[D].台中:台湾静宜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2009.
[4] 胡怀琛.中国民歌研究:第七章[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5] 齐森华,等.中国曲学大辞典[G].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71.
[6]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573.
[7] 梁实秋.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