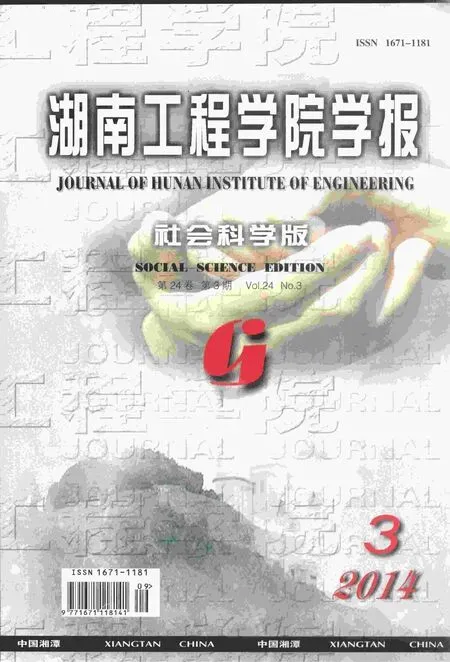东方式魔幻中的现代隐喻——论田瑛的《大太阳》
周会凌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东 广州510303)
田瑛的小说将古老的民间传说与隐喻化的现代思维融合在一块,如他的小说集《大太阳》中的《早期的稼穑》、《金猫》、《仙骨》等篇都以原初神话般的讲述与奇谲的情节设置,凸现出潜伏于人性深处的诡秘与愚钝、乖张与暴烈。他笔下的乡土中国凝聚着复杂的生存伦理和文化纠葛,还释放出狂放不羁的生命野性和张扬奇诡的飘逸想象。田瑛笔下的故乡——湘西边地,蕴藏着神秘而丰富的生命传奇,其蛮荒残酷的生存环境,严酷恶劣的自然状况以及尖锐的族群矛盾,形成了湘西边民强悍野性、愚钝蛮拗的生命品性,也使他们在蒙昧与文明之间演绎出许多奇特的生存景象。田瑛以一种隐喻的方式,突显出匍匐于灰色大地上的生命存在的惨烈感与卑微感,从某种意义上深刻地表现出了我们的民族性内涵。
一
法国思想家萨特在《制造神话的人》一文中认为剧作家是“制造神话的人”,戏剧则是用“神话方式”向观众讲话。[1]138田瑛的小说中就时常以原初神话的形式来讲述属于民族与区域的苍老记忆,同时又是一则则现代寓言,是人性与社会失落的言说,表达创作者对于自然与人类存在体悟思考的结果。
《大太阳》有着浓烈的东方式的魔幻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迁徙”是其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大太阳》中的酋长在半个世纪前因为一个梦而带领着部落迁徙到“龙洞”这个地方。酋长被一个牛贩子的现代价值观影响,明白了黄金的价值,而牛贩子在被酋长砍下头颅时仍充满了对黄金的贪婪,他的头颅在滚动中不停地发出尖锐的哨音并喊着“金子!金子!”酋长带领着全部落的人疯狂的焚毁山林冶炼黄金,并发誓要造出一座金山,追逐财富的疯狂导致龙洞的水源枯竭、瀑布干涸,老酋长在一场无效的求雨仪式之后站立着死去。部落不得不在新酋长的带领下再一次的迁徙,但这一次迁徙的终点却是死亡,最终在让人疯狂的干渴中,人一概成了化石,而执著地追逐着天空的一丝云彩而去的牛却活下来了。小说犹如一个龙钟的老人在讲述着他无比苍老的记忆,但却是意义隽永的现代寓言。马克思·韦伯曾认为:“自从有了人,就有了对黄金的贪欲。有一些人让黄金欲成为不受控制的欲望,并全身心地顺从它”。[2]40在黄金之山耀眼的光芒中,人性中对财富的执念与对生命的轻蔑终将导致灾难与毁灭性的后果,这也深刻地指出了潜伏着的“生态危机”,显示出作者对于人与自然、自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的失调或生态环境的变异与恶化的深沉忧虑。
《早期的稼穑》是史前时代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演化过程的神话式讲述,充满了奇异而又朴实的想象,形象生动地演绎了刀耕火种的远古之时,人类先祖的生活图景。太是部落的女酋长,原始生殖崇拜决定了初民社会中女性普遍受尊敬的地位,太在部落的男人面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焦灼与无厌的情欲让她在面对名为太的男人时一步步放弃了自己的权威与地位,最后完成了父系对于母系的性别权力交接,同时也是男性对于女性的征服。正如同小说开篇那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不详,任何一个年份似乎都可以作为它的背景。故事的不确定性就在于此,它既是一段历史,又是一种现实,然而更像一个预言。”[3]71这也正如王蒙对小说的分析,“小说的背后呢?又有‘言外之旨,象外之意’,它的蕴含应该是很丰富的,很概括的,很具有普遍性的。”[4]125田瑛小说丰富的审美内蕴就源于其文本中设置的众多隐喻与蕴涵的多重寓意。
中国传统社会十分重视“孝”这一观念,强调以孝立国,以孝立身,《论语》有云:“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因此在民间故事中有“兄弟分家”这一类型。在田瑛的《独立生涯》中以“兄弟分家”的传说母题为叙事核心,向大与向二两兄弟因为财富与土地而反目成仇,导致老父亲因为两兄弟的骨肉相残痛心而亡,刻画了向氏兄弟对待父亲不孝、兄弟彼此之间的冷漠还有乡土的薄情。小说中向大与向二两兄弟分家之后,黄狗犁地、卖香屁、打官司等情节是对于民间传说的生动演绎,诙谐的言语间又沉淀着对于乡土与人性的严肃思考,当为向家老人出殡的队伍久久的停歇在路上,帮工们因为没有肉吃而以“歇脚”的名义不肯上路,向大向二这两位不孝之子绝望之后反倒坦然,与众人有说有笑,最后惊雷响起,让人们为乡土淳朴人情的颓败而叹惋,乡土中曾经最为美好温暖的朴素道德早已失落。小说揭示了乡村的贫困愚昧是造成人性异化、孝道沦丧的根源所在。
《仙骨》中的巴洞人停留在原始的生存状态,不愿意接受外来的现代文明与生活方式,原始的巴洞人在一次奇妙不已的城市旅行中受到了现代文明的诱惑,最终不愿意再返回从前的生活状态,而跪在山垭口等待着再一次接他们的车,最后成为了五十具白骨。体现出现代文明与原始文明的冲突,当乡村面对城市的经济、文化、观念意识等方面的侵入时,那种抵抗、犹疑到趋附的复杂心态,五光十色的现代文明对于古老文明的致命诱惑,而最终乡村传统固有的生活方式、文化心态与观念意识失衡,从而导致自身的困惑与迷失。
颇有奇幻色彩的《沉棺》中,驼子的家族晦气沉沉,代代出残疾之人,驼子将改变家族命运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死亡与孙子的出世上,他亲自选定了酷似龙头的岩穴作为自己下葬的风水宝地,亲手开辟了走向死亡的路途。驼子目睹了自己整个葬礼的喧闹过程,最后从容地躺在棺材里,在波浪的簇拥下消失在旋涡深处,同时,在响雷之中驼子的一双孙儿出世,但一个花脸一个黑脸,村人以为不祥而将之装入麻袋扔到河里。不久之后一瞎眼算命先生到来,告诉寨民响雷时双生之子是文武二相,这让所有人惋惜不已。奇幻的生存氛围氤氲着浓郁的宿命的神秘气息,在具有强烈寓言意味的虚幻与真实交织的文本中,荒诞与现实间形成了一种张力,增加了小说文本的传奇性与厚重感。
在小说中,充满了古老的民间意象:部族、酋长、山寨、悬棺、天坑祈雨、族群迁徙、祖先托梦、民谣、乌鸦、喜鹊……,浓厚的东方魔幻的绚彩的背后,充满了讲述民族寓言的渴望。虽然《大太阳》里处处是南方边地、深山老林与洪荒岁月,便是“每个词后面都联系着一种久远的历史,并把它的阴影拖进了现代”。[5]43
二
田瑛小说中的湘西总是笼罩在饥饿、缺水、械斗的灰暗阴霾之中。祼露着干涸、焦裂的灰色大地,对于人的存在是一种严酷的生存拷问。
古人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礼记·礼运》)身体的苦难一是食、二是欲。饥饿是中国乡土书写中永远的一抹阴影,田瑛笔下的湘西边地也无法摆脱它。《风声》里“我”的父亲一生坚守着自己的道德信条——不偷不抢不为匪不成盗,宁愿与老母亲在板土里拖犁耕种,也不愿学那些同村之人跟在抢犯后面做不冒风险不劳而获的“背笼客”。在饥馑的日子里,3岁的妹妹饿死前的唯一心愿是“想要吃饭”,年幼的“我”趁食堂的管理员苦斑鸠不在偷拿了一把稻米想为妹妹煮一碗稀饭,最后在苦斑鸠的追赶与父亲的责问下退还了这一小把米。乖巧年幼的妹妹变成了一个小坟包,老实巴交的父亲得知“我”行窃的原因之后,下定决心做一回贼,去公家的包谷林偷包谷,最终却只敢偷摘一把包谷须,一种巨大的时代的悲怆感在这个痛苦的父亲的形象上浸透开去。作者田瑛曾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就是他自己童年的真实经历,饥荒年代的饥饿与死亡以文字的方式刻骨铭心。而“欲”的苦难同样存在,《煎熬》中那对贫苦的夫妻也无法摆脱饥饿对他们的折磨,夫妻俩在“食”与“性”之间承受着巨大的历史不幸,最后迎来了“食”的富足,摆脱了饥饿的威胁,却又不得不面临“性”的缺失。原本是人类最为寻常的本能,却在残酷的环境与生活面前悲剧性地缺失,人的存在显得份外悲怆与无奈。
《干朝》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干朝的地方,“干朝,或曰干槽,一个干旱的槽”,缺水少田。以少年时代的“我”的视角,真实地写出了在干涸的土地上,人的生存本能中掺杂着的残虐与卑微,“真正值得可怜的恰恰是这些干朝人,我的家族成员们,他们为抢先喝到一口凉水只差打破脑壳,动物间争食也莫过如此”,在那令人疯狂的干旱到来的季节里,干槽人常常为了争抢水而火拼械斗,“队上大大小小的官司,几乎无不和水有关。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没有哪个的死重如泰山,而一概轻如鸿毛”。[3]43-44触目惊心的一场场火拼械斗之后,干槽人用绯红的鲜血来滋润干涸的荒蛮大地。
当年田彭两家的先人结伴在干朝住下,曾经“如人类的一对孪生兄弟”般亲密无间,但正是因为水而生隔阂,后来田彭两个家族,或者说两支军队,用手中原始的武器血拼,田家留下了彭家惟一的幸存者——一个守水的小孩。后来这个小孩在城里成为了局长,他为了感谢“我”的父亲田天福在文革中阻止村人挖彭家祖坟,而愿意出钱为干朝人修筑一个大水池,解决困扰了干朝人祖祖辈辈的用水问题,但居然被父亲拒绝了。因为“父亲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得好处,而是如何不让别人得好处。假如一件事情自家受益再多,只要有一点好处给了别人,他也是不会干的。”[3]52在这个看视自尊的拒绝举动的背后,其实显现的是干朝人的见识与逻辑,也是深埋在灰色乡土之中的人性的拘囿与劣根。
田彭两家的恩怨在另一篇小说《炊烟起处》也出现过。田彭两个家族由当初的结伴而居到后来势同水火,在两个家族的械斗中,田家人用身躯阻止了彭家人的火枪。多年之后,田公托付教书先生带走的田家孙儿成为一支军队的指挥官,带领着他的部队返回被自己先人的鲜血浸红的故乡,包围了彭家屋场。最后,面对包围在外的仇家,彭家人将屋场的大门侧门全部钉死,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一把火,全家族的人在烈火中自焚而亡。面对此情,来复仇的田家后人在想“这样也好”。“天亮了,太阳从东边山坳口露出笑脸,瞩望着这个余烟未尽的屋场。”在乡村的炊烟袅袅的诗意之下却有着如此惨不忍睹的苍老往事,颠覆了沈从文式的诗意田园牧歌式的湘西形象,也并不执著于韩少功式的强悍理性反思下的湘西形象,而是勾勒出坚硬冷酷的另一种湘西图景。
我们为田瑛小说中湘西边民的种种苦难而震惊,更被他们在苦难魇影下的挣扎、狂暴与疯狂而震撼。这一切图景让人想起了贝克尔对于农民这个群体的冷静审视:“农民的精神远无不如蒙田要我们相信的那么浪漫。农民的平静通常沉浸在一种有着真正疯狂无奈的生活方式之中,因而它通过这样一些事情给他以保护:以世仇、欺凌、争吵、家庭纠纷所表现得持续不断地相互仇视和刻薄的暗流、狭隘的精神、自我贬低、迷信、以僵化的专断主义对日常生活进行的强迫性控制等等。”[6]440曾经在湘西这片灰色大地上成长的田瑛,在对真实生活与严峻现实的书写中,流露出强烈的苦难意识甚至是一种莫名的宿命感。作者对于湘西的情感是混沌而又深切的,或者是爱恨交加的。爱是因为这里是他的生命之源,恨是因为洞察到它的残缺与阴冷,因此在冷峻的真实与无羁的想象中弥漫着一种悲凉的乡愁情思。
三
在湘西恶劣的自然环境、尖锐的群族矛盾下,暴力成为一种自然存在,暴力的背后是一种残酷的生存的竞争,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猴……,山民们强悍的野性与执拗的愚昧的生命个性显露无疑,同时,在残酷的生命较量背后显露出作者复杂深邃的精神指向:一种人类生存的现代性焦虑与思考。
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如《炊烟起处》田彭两家间的血腥械斗、《干朝》中田彭两个家族因为水而结成世仇。田瑛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缺水”有一种象征隐喻意味,一种生理上饥渴的背后是人类心理对于生存的焦虑感。
此外田瑛小说中的自然是一个庞大而神秘的存在,是被神化的自然,是湘西巫楚文化中“万物有灵”观的体现。田瑛小说中很多篇目都是在神化自然背景下对于人与动物关系的描写,如《大太阳》中人与牛的相处与相较、《悬崖》中王家三人与猴之间的血腥较量、《独立生涯》中人与狗的相处等,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悬崖》。《悬崖》中带着自己一双儿女来到老木山的王家父亲面对破坏庄稼的无知顽劣的山野之猴,表现出了人类最阴狠毒辣的一面,让人震悚齿寒。当如顽童般的五只小猴被王家父亲用粑粑引入圈套抓获之后,用极其机巧而残忍的方式先吃猴精:
人砍来一截细细竹管,削尖,然后抓住小猴的阴囊用劲一捋,捋出两粒饱满的睾丸,睾丸状如圆枣,很诱人,人恨不能即刻摘了囫囵吞下去。人自然懂得更妙的吃法,那截竹管帮助了他。当竹管头刺进睾丸时,猴的精血从另一头溢出,人急忙用嘴巴去接住,跟着婴儿吃奶般咂吮起来。咂吮咝咝声,但和猴的疼喊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猴把一串颤音由高至低拖得很长,那是令人心碎的声音,悠悠的,最后变成短促的喘息。[3]28
然后再是吃猴脑:
刀沿着猴的头盖划了个圈,然后整张头皮像一顶帽子被人揭开,或者说失去头皮倒更像戴了一顶小小圆帽。小猴这时并不觉疼,甚至头颅破裂也能忍受,要命的是木勺搅动脑髓的感觉,那才是痛不欲生的。当天灵盖被彻底敲开,猴脑出现了,原来猴脑和一碗完整的豆腐脑并无多大区别,所不同处是猴脑仍在起伏搏动。人撒一把盐进去,再用木勺搅匀,方止住那动。人一勺一勺舀吃起来,神情很专注,他没有理会一张近在咫尺的猴脸,那脸已经扭曲变形,上面安装了两只两样变形的眼睛。如果人稍稍移动一下目光,就不难发现一只猴临死前的某种欲望。猴生性贪吃,死也不当饿死鬼恐怕更适用猴类,小猴此刻的眼神便是例证。人如此吃法实在是一件残忍的事情,小猴眼巴巴望着他吃,就是没有一勺喂给它,真正的痛苦莫过于此。[3]29
用淡然细致的言语,表现一种“生存竞争渐渐脱去了文饰的面具,露出原始的狠毒”[7]65的动物性的生存竞争。对于王家父亲吃猴脑与猴精的精细过程的描摹中颇有一种暴力美学的意味,对于人的残虐狠毒凸显无疑,人性中某些冰冷而尖锐的东西闪烁着凛冽寒光,而对于猴在临死前贪婪食欲心理的揣摩更是诡谲邪恶。
王家哥哥用诡计想要掳去妹妹王妹的大猴的性命,谁知王妹不仅在黑洞洞的枪口面前救了猴的性命,最后还选择了与猴相伴,当哥哥听到了枪声响起之后满怀着喜意去查看时,“抵近山边,他站定,眯起眼睛朝悬崖睇望,一望望出了意外,猴仍活着,它安然无恙地蹲在崖畔,与之相依的是王妹”。[3]39最终王妹选择了与猴相伴,而远离人性的凶恶残虐。以人与猴的相处与相较,描摹出人类与自然的紧张关系。
颇具民间传奇色彩的《金猫》中,当地一霸向阴鸷狠毒,他像个土皇帝一样巡视属于他的土地时,“一群狼狗尾随着他。狗一概不声不响,沿路只顾嗅地。这是一群哑巴狗。向养狗与众不同,狗自小被割掉舌头,从此只长身坯不长声音。你一定见过哑巴人但未见过哑巴狗,路人皆知不会吠的狗意味着什么。狗的沉默给向家大院构筑了一道无形防线,历来无人敢轻易靠近半步”。[3]159向还有一种隐秘的癖好,他经常让管家彭去市场上买回那些穷困潦倒的乡人的婴孩来满足他吃人的嗜好,向吃人肉吃熏腊的,肉完全是年猪肉的做法,他家里有一个专门熏制人肉的大坑,一年四季柴烟不断。
贫苦的王有一天挖到了一只金猫,他以为自己的穷日子终于熬出头了,但他老婆却因此恐惧不已,最终死去。阴鸷凶残的向来找王索要金猫不得,就带走了王的幼子。王在走投无路之时将金猫扔下天坑,自己离乡投军去了。十年后,背井离乡的王返回故土,当年的穷汉子成为带着队伍的军官,王开始从容地报仇,他让士兵准备铁锅与油盐酱醋等物,以极为残忍的方式折磨向。王先将向的头皮撕下,“人们隐隐听见了类似裁缝铺里撕裂布匹的声音。向的整块额头皮翻开,耷拉下来,遮住了脸,失去头皮的部位咕咕噜噜泛着无数美丽的血泡”。王再用刀割向的舌尖,“由于刀刃很钝,且缺了齿,王割得很费劲,像拉锯一样割了半天,才割下小小舌尖。手一扬,舌尖划一道漂亮弧线,准确地落入早已烧沸的油锅里。舌尖如一条活泥鳅在锅里翻滚不已,顿时空气中浸透了人肉的奇香。眨眼间,炸熟的舌尖再次通过王的手蘸完佐料送到了王的嘴里,王咀嚼着,品味着。”[3]171田瑛的文字就如同利刃一样剜开了人性中某个脏污不堪的地方,让人读来齿冷,心胆皆寒。最后王取代向成为当地的霸主,他重金悬赏找人下天坑找回他当年扔掉的金猫,应征的人动却是他失散的儿子。动被一根长绳送下了深不可测的天坑不见了。在命运的安排之下,父子相见却不相认。人的惨烈的挣扎仍无法摆脱一种宿命的困顿。
《独木桥》中讲述了一种卑微刁钻而又值得怜悯的人生。矮子形容丑陋猥琐,又一无所长,在身边人的奚落与嘲讽中,心理与生理的残缺逐渐暴露出来,他将自己的仇恨施放在比自己更为弱小的对象身上,如鸟。[7]他终于以一种残虐阴毒的方式来报复乡人,在一次与队长为地界发生的纠纷中伤了脚踝,凭着小聪明装了七八年的跛子,靠讹诈队长而生活,最后却在队长的下跪中逃离了乡土。《大太阳》写出了山民在艰难环境中的韧性,也显出了他们的偏执狭隘、执拗凶狠。《干朝》中父亲的质朴仁义却又显出了自私与愚昧。
在乡土生存环境之中,心理暴虐、行为凶残的生命负面品性并不少见,当与无序的时代、莫测的命运与逼仄的生存环境相互撞击之后,终将导致个体生存悲剧与人性沉沦。田瑛对于暴力与死亡的想象方式是诡谲的,他在丑陋尖利却充满内在真实感的文字王国中,还原乡土上生存着的人们的精神质地与灵魂状态,也在更深的层次里揭示了来自文明、环境、习俗、乃至于集体无意识的对于生命个体的蛮横毁灭与残忍屠戮。
田瑛在青年时代离开自己的故土——边地湘西,但沉重的“原乡记忆”却被他扛在肩上、烙在心里,如影随行,因此他的小说从文字的深处呈现出一种“根性”特征,独属于某一民族或某一地域的感性气息与美学特征。曾有论者认为田瑛小说中的边地湘西是继沈从文与孙健忠书写的边地湘西形象之后的“第三种湘西”。[9]86-88田瑛笔下的湘西形象是“前现代”式的,是生命主义、存在主义的,是一种反诗意的,残酷狰狞,艰难阴郁,在这块灰色大地上充满了困囿的宿命,弥散出一种乖戾的气息,根本性的解构了沈从文建构的精神乌托邦般的湘西形象。挣扎在宿命与乡土苦难之中的群体存在,这些乡土的生命,有时会丑陋暴戾到让人不忍卒读,但同时,那深重的苦难、莫测的命运与精神的极端扭曲,无不昭示着民间生存的芜杂的精神生成与存在形态。可以说田瑛正是以一种东方魔幻式的寓言化写作,来审视乡土边地、民间生命与民族历史,从而指涉那个在现代性观照下“民族的自我”,并呈现出凝聚着复杂的生存伦理和文化纠葛的乡土中国。
[1]萨 特.制造神话的人[A].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3]田 瑛.大太阳[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4]王 蒙.关于小说的一些特征创作是一种燃烧[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5]程德培,吴 亮.探索小说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6]E·贝克尔.反抗死亡[M].林和生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7]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8]郭小东.第三种湘西——评田瑛中篇小说《独木桥》[J].民族文学,19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