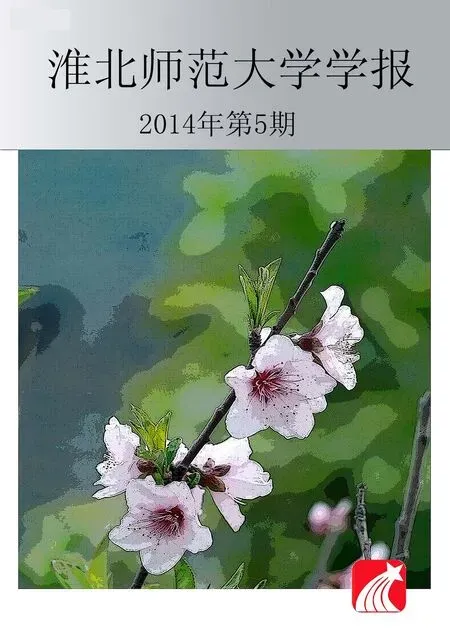经典重构:现代性的欲望
——芥川龙之介小说《齿轮》的阐释
李东军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一、芥川龙之介与现代性
达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提出了“世界文学”新定义:其一,世界文学是一种流通模式;其二,世界文学从翻译中获益;其三,世界文学是一种阅读模式,一种跨越时空与世界交流的方式[1]。因此,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创作的小说《罗生门》以及其它148部短篇小说成为世界文学经典只是时间问题,他的小说已经被近五十个国家和地区所译介。2006年英语圈最具影响力的企鹅图书集团出版了《罗生门及其它十七篇》,该书的译者乔伊·罗宾道:“其作品经受住了被剥离写作语境的暴虐”[2]。小说《齿轮》(1927年)被该文集收录,这是一篇具有后现代主义特点的短篇小说,它摒弃了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使用记忆碎片、梦境、意识流等空间叙事策略[3],描写了主人公“我”面对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感性与理性等现代性的精神困境,让人联想到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
“现代性”是指建立在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理想和机器文明基础上,以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制度为标志,以实现“经济繁荣、生活基本保障、生活质量的总的提高”为目标,与科学技术同步增长所确立的“中心化、组织化、专业化、制度化”的文明发展的基本原则[4]。现代性释放了人性的本能欲望,使其不受道德伦理、宗教政治的遮蔽,现代文学可以露骨地描写人的欲望话语。但另一方面,现代性也带来了负面后果,人类面对现代化工业与大机器生产显得如此渺小,精神受到物质的压抑与异化。芥川龙之介是日本最早表达现代性反思的作家之一,他在自杀前几年集中创作了一批这类作品,如《海市蜃楼》《大导寺信玄的半生》《玄鹤山房》《河童》等作品,引发了日本人对现代性的关注,即所谓的“近代超克”。但现代性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如今人们将希望寄托于后现代性的文化反思上。
二、“人工”与“自然”
《齿轮》主人公“我”因精神压力大,右眼会看到齿轮状的旋转物,严重时会遮住整个视野,并伴有幻视幻听等精神分裂症状,甚至希望有人将自己“掐死在睡梦里”。当主人公“我”听说有“穿雨衣的幽灵”出没之后,便多次遇到“穿雨衣的人”或被丢弃的“雨衣”。“穿雨衣的幽灵”的灵感来自果戈理的《外套》。芥川龙之介非常崇拜果戈理,他的小说《芋粥》(1916年)与《外套》存在影响关系[5],个体的欲望受到外界压抑便外化成“芋粥”或“外套”。《齿轮》则反其道用之,“我”对“雨衣”避之不及。
英国学者凯恩斯对人的欲望进行过心理分析,人类的需求(need)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绝对需要,是维持人类生命存在的“生理欲望”;第二种需要即是欲望(desire)[6]。法国学者基拉尔将“第二种需要”称为“模仿的欲望”,而模仿的对象是他者的欲望,对象不同决定着欲望的性质与层次。基拉尔说:“选择,永远不过是为自己选择模式,而自由则只存在于人的模式和神的模式这个基本选择之中”[7]。尼采高喊“上帝死了”,“人的模式”取代了“神的模式”,现代性启蒙开启了个体解放与自我主体性的时代。然而现代科技满足不了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但是人放弃了彼岸的精神追求,只能在此岸寻求欲望模仿的对象,结果导致了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物欲横流,人情冷漠,“世纪末”的悲观情绪在世界弥漫开来。
日本的现代性不同于欧洲,为了“脱亚入欧”“富国强兵”,明治维新实行全盘西化。在这种宏大叙事下,主张个性自由与自我解放的审美主义启蒙严重滞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经济出现短暂繁荣,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迅猛涌入日本,传统文化受到剧烈冲击。为了调和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日本人提出“和洋折衷”的策略。这些矛盾在小说中有充分反映,主人公“我”在咖啡馆喝着廉价的可可饮料,看着墙上贴的“鸡肉盖浇饭”“蛋包饭”等菜单,感叹铁路沿线乡村的巨大变化,电气列车在田间飞驰而过。T君的一段对话充满寓意。在谈到经济不景气时,T君说:“没想到法国没有受影响,虽然法国人的德性就是都不想交税,内阁说倒闭就倒闭……”。“我”说:“哪里啊,法朗不是暴跌了吗?”。T君说:“报上是那么说。可是在法国看报纸,你看到的都日本发生大地震啦,大洪水啦”。这对话透露出的信息是,欧洲的民主与自我意识程度高,反到是日本的现代性问题严重得多,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发展严重不平衡。
谈话间,一个“穿雨衣的人”坐到了我们对面,我心里感到很不舒服,便将“穿雨衣的幽灵”故事说给T君,可他指着一个女人给我看,“对,抱着包袱的女人。今年夏天在轻井泽(著名避暑地),她当时穿着时髦的洋装”。但我看到现在的她却衣着寒酸,眉宇间的神情让人感到她有些精神异常。T君接着说道:“在轻井泽的时候,她和一个年轻美国人跳舞。摩登……那个词儿是这么说吧”。那么,这个精神异常的女子由“摩登”到“落魄”,这可以解读为是作者对日本全盘西化的担忧。二人分手时,“穿雨衣的人”不见了,但我眼中出现了齿轮状的影像,干扰我的视线,并引起剧烈的头痛。这隐喻着“我”的思想出现了混乱。“我”走在高楼林立的街道上,忽然想起了“松林”(自然)。钢筋水泥的“森林”(高楼)是现代化的标志,也是现代性的结果,“高楼”与“松林”对峙,换言之便是芥川龙之介所说的“人工”与“自然”的矛盾。芥川龙之介所说的“自然”并非指自然界,而是指一种自然无为的、感性主义的东方思维模式。“人工”则是指工具理性,它取代了价值理性,造成现代社会的道德伦理下滑、物欲横流的恶劣局面。
这种矛盾是由现代性造成的。人的本性中存在相互矛盾的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前者产生于人的物质存在,它往往使人屈从于感性本能。后者是人的理性本能对自由的渴望,它要求人在任何状态中都保守人格不变,它是一种对永恒的向往。席勒认为:“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8]。现代化的社会劳动分工造成了人性的分裂,使人的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对立愈加剧烈。这在主人公“我”的身上有突出表现。“我”右眼视网膜中出现数个齿轮状物体的影像,随后引发剧烈的头痛。可能这只是一种叫飞蚊症的常见眼疾,但应该是作者的叙事策略,每当“我”眼中出现“齿轮”都会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并伴随着幻视幻听。在朋友婚礼上,“我”与一名汉学家争论起来,“我”说:“麒麟就是一角兽嘛。另外凤凰是一种叫菲尼克斯的鸟……”,其用意是用西方理性主义解构东方传统。随后,“我”又故意说:“尧舜是虚构的”“春秋也是后人假托”。汉学家终于掩饰不住愤怒,反驳道:“如果尧舜不存在过,那孔子就是说谎了。但圣人是不说谎的”。“我”哑口无言,拿起刀叉正想吃牛排,却发现一只蛆虫在肉中蠕动,但蛆虫却在我脑中唤起了英语单词“worm”,它除了“蠕虫”之义外,还可指“火龙”“大蛇”,与麒麟、凤凰一样都是传说的动物,此外还可指“潜藏的监视者”。这段话表达了作者对西方的语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质疑与消解,“蛆虫”或“蠕虫”是自我主体性、本能欲望的一种能指,它是对等级秩序与传统权威的对抗与消解。理性主义与自我主体性是现代性的两大基本原则,但自我主体性天生具有反骨,在现代性内部如同蠕虫一样苏醒,反噬着、抗争着,用审美主义、感性主义对抗工具理性的暴虐。
三、精神分裂患者的抗争
“欲望”源于拉丁文“desirare”,原意是“对缺乏者的缺憾”。弗洛伊德用“俄狄浦斯”将欲望本能封闭在“父—母—我”三者的家庭关系中,忽视了欲望生产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等文化内涵。德勒兹和伽塔利的“反俄狄浦斯”则将欲望与机器结合,提出“欲望机器”的概念,欲望主体的人可以被视为一种无意识的欲望机器,精神分裂是一种生活和思维方式,而精神分裂者是反俄狄浦斯的集体性的主体。德勒兹说:“这样一个主体,其欲望自由奔放的主体,将成为一种爆炸性的革命力量”[9]。在资本主义社会,“俄狄浦斯”的父亲、母亲与儿子的关系转化为“资本”“土地”与“劳动者”的关系[10]287。俄狄浦斯是我们头脑中和日常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的源头,导致人们对权力的渴望,“去俄狄浦斯化”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挣脱内在的与外在的法西斯主义束缚。因此,福柯在《反俄狄浦斯》序言中道:“基督教道德家寻出了深藏在我们灵魂之中的肉体踪迹。德勒兹和伽塔利,就其所为,则是在身体中追踪法西斯主义的蛛丝马迹”[10]15。由此推断,“穿雨衣的幽灵”就是权力与与资本结合后生出的怪胎——法西斯主义。芥川龙之介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遗书中的那句“说不清楚的莫名不安”表达的正是这种忧虑。事实上,他自杀后不久,1929年经济大恐慌爆发,德意两国法西斯主义登上政治舞台,而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也趁机抬头,残酷镇压无产阶级运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了深重灾难。
在现代性启蒙之前的传统社会里,欲望话语受到宗教、政治等势力的遮蔽,只能以隐晦、变形的形态出现在文学叙事中;而在现代性启蒙下,个体的自我意识得到张扬,但是现代化机器催生出畸形的消费主义文化,人们对物质的欲望崇拜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资本主义机器的压迫导致欲望主体的精神分裂,这种“精神分裂化”可以“打碎俄狄浦斯的铁衣,重新发现遍及四处的欲望生产的力量”[10]153。小说《齿轮》的主人公“我”一直逃避着物欲“幽灵”的精神压迫,出现严重的幻视幻听等精神分裂的症状。婚礼结束后,“没人的走廊里就像监狱一般令人压抑”,“我”逃避回到自己房间,墙上挂着自己的外套,让“我”感到好像是自己站立的身影,便慌忙将它丢进衣柜里。“我”来到镜前,镜中映出自己脸皮下的骨肉,令“我”想起来牛排上的蛆虫。“脸皮下的骨肉”代表假面伪装下的真实自我,“蛆虫”暗指人的欲望。“我”冲出房门来到宾馆大堂,看到绿色的灯罩,内心感到一些平静,我坐下来开始思考问题,但没过五分钟,便发现身旁的椅背上搭着一件被人丢弃的“雨衣”。很显然,“我”的精神状态已经不正常了,然而,正是这种精神分裂症的出现使“我”暂时摆脱了物欲、工具理性的束缚,身旁被人脱掉的“雨衣”就是一个隐喻。“我”姐夫买了大额火灾险后房屋失火,他被怀疑骗保,穿着“雨衣”自杀了。“雨衣”与“幽灵”结合在一起,对人进行精神控制,暗示它给人带来毁灭与死亡,“雨衣”便是物欲的符号。虽然欲望是人的自然属性,包括精神与物质两个方面,但不能缺乏必要的伦理限定或终极关怀。否则,欲望就会成为“魔鬼”,现代性启蒙在解放人性的同时,也热情地拥抱了欲望这个“魔鬼”,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却导致了贫富差距扩大,人情冷漠,物欲横流,人们心甘情愿地成为欲望的奴隶。
小说主人公“我”在出现精神分裂症状后,受物欲、“俄狄浦斯”等压迫的个性自由与自我主体性便得以苏醒,它是一种具有巨大破坏能量的革命力量。日本文艺评论家小林秀雄指出:“自杀是芥川的宿命,也是时代的悲剧”[11]。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它把人性从神性束缚下解放出来,却也释放出欲望的魔鬼。面对现代性困境,大正时期日本人陷入了“西洋憧憬”与“回归传统”的争论不能自拔。对此,芥川龙之介认为文学不关乎“主义”或“道德”,他在《某傻瓜的一生》中写道:“我没有任何良心——甚至没有艺术的良心。然而我有的只是神经”。其意思是说他只是客观地叙述人的欲望话语。但这不应该是其本意,如果没有审美救赎的追求而甘心沉溺,他就不会留下那句“说不清楚的莫名不安”的遗言而自杀。受困于理性与感性、传统与现代、以及理想与现实的对峙,他无法超越现代性所带来的生存困境,各种矛盾冲突集于一身,焦虑与躁动折磨着芥川龙之介的羸弱神经,等待他的命运是“要么自杀,要么发狂”(《某傻瓜的一生》)。但另一方面,精神分裂患者可以摆脱资本主义机器的压迫,“由于不断漫游,尽其所能四处漂泊,因此越来越陷入非疆域化领域,……精神分裂患者精心寻求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它是其臻于实现的内在倾向、剩余产品、无产者,也是其灭亡的天使”[12]。通过德勒兹的精神分裂分析法对小说的文本分析,“齿轮”“雨衣”“幽灵”“火”“人工之翼”“松林”等意象组成的能指链便有了清晰的指向性,它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本质,并为我们超越现代性困境提供了审美救赎的方向与可能。
四、原罪意识与审美救赎
《齿轮》原名为《索托姆之夜》,后改为《东京之夜》,最终定稿为《齿轮》。索托姆是《旧约》创世纪篇所记载的约旦的一个商业城市,因罪恶与淫乱被上帝焚毁。在芥川龙之介的构思中,“索托姆”是“东京”的隐喻,暗指东京是一个“欲望都市”,作者将“东京之夜”改为隐晦的“齿轮”,它巧妙地掩盖了作者的真实意图,增添了小说主题的多重歧义与可读性。主人公“我”的精神分裂过程是对俄狄浦斯对欲望机器压制的抗衡与消解,从而释放自我的主体性,实现人类对自我的超越。
小说《齿轮》中透露出一种原罪意识,“复仇”一节中,“来来往往的行人,不知罪为何物,他们欢快在行走着,这今我感到不快。……我认为我犯了所有的罪”。芥川龙之介对基督教思想非常关注,创作了大量“切支丹物”小说,甚至自杀时枕边摆放了《圣经》。但理性主义使他没能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我”将自己比拟为《包法利夫人》中的包法利先生、《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尼可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罪恶与痛苦的根源在于现代性启蒙所带来物欲膨胀的负面性后果,当神不在时,人发现自我迷失于物欲横流的世界,这几部世界名著的主人公因为经不起欲望诱惑才犯下了婚姻出轨、杀人弑父等罪行。“我”不愿成为迷失的羔羊而受到牧羊神的庇护,便将救赎的希望投向了“松林”(自然)。“自然”是与人工(工具理性)相对的概念,是一种感性主义的思维模式,而非自然界的“自然”。
为了逃避现实的痛苦,“我”埋头艺术创作。但在商品社会,艺术受金钱逻辑的限制,最终沦为一种商品,从而丧失审美救赎的能力。“我躲入房间里,坐在桌前,开始写新的小说。钢笔畅快地在稿纸上滑动着,毫无凝滞阻碍,这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二三个小时之后便被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抑制住停了下来。我不得不离开桌子,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子。我的胡思乱想在这个时候最有效了。在野蛮的欢呼中,我没有了父母双亲,也没有了妻子儿女,我感到唯有从我的笔端流淌出来的灵魂”。“野蛮”是与文明相对的概念,这里是指人的原始激情与生命感动。芥川龙之介在《文艺的、过于文艺的》的“野性的叫喊”一节提到高更的《塔提希少女》时说:“从视觉上令人感到橙色的少女身上散发出一种野蛮人肌肤的味道。这多少让我感到不快,……。随着岁月的流逝,高更画中的橙色女人逐渐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压迫感。事实上,塔提西女子身上似乎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威力”。在另一部小说《梦》(1927年)中,主人公画家“感到了一种异样的压迫感。……这愈发让我觉得她的体内有种野蛮的力量”。所以,用“野蛮”对抗所谓的“文明”,逻辑上与“自然”抗衡“人工”(工具理性)是一脉相通的。
小说最后一节“飞机”与第一节“雨衣”在叙事上形成了封闭的环形结构,“我”从东海道铁路的某车站换乘汽车赶往内陆的某避暑地,这与小说开头的叙事正好相反。在现代社会,想逃避物欲的压迫是不可能的。阿多尔诺说过:“摆脱和逃避日常生活就像私奔一样,从开始就决定了,一定会回到原先的出发点”[13]。“我”离开东京返回家乡,但并不能摆脱物欲“幽灵”的追踪。“汽车司机不知为何穿着一件旧雨衣,我对这种巧合感到毛骨悚然,努力将目光转向车外,却见到一队送葬的人群经过古老街道”。回到远离城市的家乡,主人公“我”获得了短暂的内心宁静。但是,这里也并非世外桃园,“我虽然只在这里住了一年,但对于这里发生的罪恶与悲剧是了如指掌。有投放慢性毒药想杀死患者的医生,有对养子夫妇家放火的老太婆,还有想争夺自家妹妹资产的律师,等等,目睹这些人家的悲剧,无疑是让我看到了人间地狱”。小说最后叙事人说道:“那是我一生中最恐怖的经历。我没有勇气再继续写下去了。……谁能在我睡眠中悄悄地扼死我呢?”可见,对于主人公“我”以及芥川龙之介本人而言,各种救赎的努力都失败了,就像是希腊传说中折断翅膀的伊卡路斯一样,自杀是他无法逃脱的宿命。
结 语
大正时代的日本社会已经显现现代性困境的征兆,芥川龙之介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为了不使自我主体性湮没于历史理性、社会理性的宏大叙事中,他坚持“诗性文学”的创作,反对将文学视为现实生活的一种复制与重现,用个人的生命伦理对抗工具理性的权威与暴虐。小说主人公“我”向艺术哲学以及宗教寻求救赎的力量,但最终这种审美救赎仍然被工具理性与物欲主义的“幽灵”所打败,主人公“我”只能逃离充满物欲的城市,投向“松林”与“大海”,投向传统与自然的怀抱。但在现代性语境下,自然已经不是从前的自然,商品经济与物质主义无孔不入,艺术受金钱交换逻辑的压制,逐渐沦为一种商品,最终失去审美救赎的能力。虽然小说《齿轮》的知名度不如卡夫卡的《变形记》,但芥川龙之介用自己的人生体验与生命伦理揭示了现代性困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今天重读与阐释这部小说经典仍具有启示意义。
[1]李滟波.全球化语境下的“世界文学”新解——评介大卫·达姆罗什著《什么是世界文学》[J].中国比较文学,2005(4).
[2]宫坂觉.国际化作家芥川龙之介研究的可能性[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5).
[3]李东军.芥川龙之介小说《齿轮》的空间叙事学研究[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1(3).
[4]崔伟奇.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N].光明日报,2007-07-10.
[5]平冈敏夫.芥川龙之介——抒情的美学[M].东京:大修馆出版,1982:152-167.
[6][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22.
[7][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M].罗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61.
[8]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80.
[9][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M].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76.
[10]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Anti-Oedip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M].Continuum,London,2004.
[11]小林秀雄.美神与宿命,《文艺读本 芥川龙之介》[M].东京:河出书房,1976:12.
[12]江怡.理性与启蒙——后现代经典文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336.
[13][德]特奥多·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