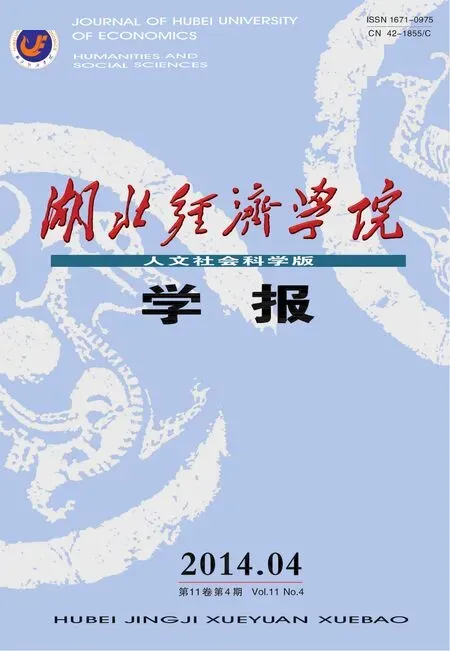国族的过程:“生活”的变迁
曹媛媛
(云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一、历史的过程
广义的进化论强调宇宙、生物世界及我们的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性,更重要的是强调人类意识的进化和社会发展的“目的性”。[1]“中华民族”这一符号的建构以及其组成部分56个民族的识别,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其目的是要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建设国族,“国族是民族国家的根基……国族并非民族群体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政治构建的产物。”[2]抹平了经济、社会与意识上的差异,淡化了从与生俱来的角度考察的族性,一律以政治的视角定位56个族群为“民族”。比如满族人由旗人转化而来,但旗人首先是个职业身份。而回族的民族身份一度遭到质疑,但“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应用了斯大林的定义,赋予回族民族身份”[3]。这样的实践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族裔原生性的理念,有利于重建历史,有利于民族主义民主化。民族国家的建设目标是民主化。“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架构,以民主制度为基本准绳,人民和民族实现完美的结合,由此实现了现代政治身份系统与民族形式、国家制度的大一统。”[4]19世纪的民族运动与自由运动之间的有些勉强的联合[5],将个人权利与归属需要调适在一个框架内,毕竟不存在抽象的个人。
“少数民族”在清末“光复”思想下,含有“多而优美之汉族”与“少而恶劣之满族”间的对立;又有用“少数民族”分析欧洲的民族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少数民族”有了“弱小民族”之意,并主要在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用于指称国内非汉民族。[6]而传统中国用以区分华夏族与周边族群的关系的模式是“夷夏之分”,一方面用以区别异质的文化共同体;另一方面也是汉族政权对有接触但不能控制的族群的称呼,是正确界定自己实力边界的做法。蒙疆、苗疆、回疆,这些名称即反映出土地、族群与政权的结合,反映出中央政权对这些权力系统的认可与疏离。汉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扩散与中央政权对边缘地区的控制力度呈同方向变化。汉族人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向西南的扩散比较顺利,则中央政权也较早对其施以土司制度,再后来是流官改革。而蒙回藏等地,清政府存着利用这些少数民族牵制汉族的企图,“排斥汉人移居当地及这些少数民族的政治和宗教领袖与汉人的接触,甚至规定这些地区不许学习汉文,禁止儒家文明在这些地区的传播。[7]”在这些方向,民族交流受阻。汉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扩散即是“夷夏”的边界的推移。从蒙古勒旺诺尔布领导四子部落旗经历近代变迁,特别是在外蒙“独立”中的前后态度,可以看到农业的生产方式在其地渗透与推进遇到的阻力,并可以看出汉族生产方式的扩散是维系中央政权对该部向心力的重要因素。[8]
某种程度上清末民初“合种”的提法不过是继续了被清政府所强力中断的历史进程。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的概念。国民党意识到了这个历史趋势。根据他们的判断,国民党持民族同化政策,称中国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蒋介石把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把其他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形容为“汉化”。[9]国民党的实践失败了。其时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族的文明已经不是一种优势文明了。天下体系的崩溃到界定边疆的民族国家,这是一种保守的状态。而在一个对权利的诉求高涨的时代,与主体民族一起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也是少数民族的 “选择”。虽然民族自决在国际法中的地位是模糊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已经做出了“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也肯定了少数民族在建立国家中的功绩。费孝通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既是历时性描述也是共时性描述,不能只关注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过程;一体之下的多元也是这个格局中重要的一面。作为中华民族整体的自觉与内部群体差异性自觉并不相悖。[10]多元与一体在一个框架中的不同层次上发挥各自的作用。
二、民族之合理分歧与次级族群之多元化
现代性使得民族之间的界限越发清晰起来。现代性的矛盾性产生于语言的命名和分类功能。“分类就是赋予世界以结构:控制其或然性;使一些事件较之另一些事件更具可能性;作用时就像事件并非随机,抑或限制或消除了事件的随机性。”[11]“最终,我们不是重构那个‘他世界’,我们不过是建构我们这个世界的‘他者’。”[12]但现代国家以传统政治共同体族裔化为建构前提。多民族国家在整合成为现代国家之前,往往先存在有着自己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民族共同体,需要在“容器”中施展多元主义。
“多元”隐含着对概念的批评。“概念天性上倾向于‘篡改’直接的流”。[13]多元主义,特别是强势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普遍原则并不相容。强势多元论者否认价值等级制度。“自由制度只是对多样的生活方式中的共存问题的一种解决办法。”[14]当包含不可通约的善的生活方式冲突时,所寻求的是妥协,而不可能是被所有人接受的解决办法。
查尔斯·拉莫尔指出了多元主义的危险。“在西方思想史上,多元主义一直是一种边缘性的观点,它与那种始终要在上帝那里寻求善的单一而最终和谐的起源的——宗教正统观点是不相容的。假如政治自由主义是在根本上依赖于对多元主义的接受肯定,那么它本身也就成为一种非常具有争议的学说。”[15]他提出了“核心道德——合理分歧”的模式。“核心道德”对所有的人都有约束力,不管他们在特定生活方式的价值上有多少差异。“自由主义寻求以一种核心道德来奠定政治联合的原则。”[16]这种道德知识通过反思而不是实践理性获得。
将核心道德与合理分歧连在一起的是我们的“生活形式”。“生活形式”的概念承认了归属的差异,这是合理分歧的一个焦点。对某种具体生活方式——包含目标、意义和行动等的忠诚,常常是历史偶然性造成的。忠诚植根于归属感。“共同的习俗、地点和语言的联系以及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可能在于它们塑造了对价值的理解,而我们正是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做出我们所做出的选择的。”[17]这种原有的道德观念通常不需证成,除非有充分的理由对其质疑。“因此,在决定是否要接纳一种新的信念之时,我们要探索的问题是增加这个新信念是否可以根据我们已经认定的信念来证成。”[18]因为存在“合理分歧”,“才引发了对一种核心的、绝对的道德的需要,对于普遍(即使最低限度的)道德的承诺担当,这本身已经成为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本质的部分。”[19]这又避免了相对主义的陷阱。
作为对自由主义的重塑,政治自由主义区分了人与公民。不同于社群主义者关于共享价值之上的共同生活的假定,政治自由主义肯定了不同的语言、地域、文化、尤其是历史记忆,是追求核心道德的条件。在人们能够根据自由主义原则进行“理性对话”而安排政治生活之前,往往已经先结成某种共同体,比如民族。“平等的尊重正是使得民主自治成为政治联合的恰当形式的东西。平等尊重的道德原则属于我们的道德意识的最深层的内核。它是我们的道德反思的具有历史情境的出发点,是我们能够在其中设想道德论证的框架。”[20]不能低估作为个人归属的族群。对自由民主制的忠诚与持有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并不相悖。
理性对话的结果是形成公共理性。罗尔斯声称,“事实上应该预期在公共理性内存在分歧,因为恰当考虑的话,公共理性的共同观点并不是由任何一种政治正义观所界定的……在公民行使公共理性的过程中,他们可以诉诸各种自由主义观中的不同视角……但不能超越他们与其公民同胞所共享的共同观点的界限。”[21]即使联合的原则得到一再强调,这个原则需要塑造而不是非反思性的。
道德与文化的差异是否应进入公共领域?族群、公民、职业都是差异的来源。除了公民权利,群体区别的权利也是需要的。但哈贝马斯认为,如果“赋予少数群体以涉外保护的集体权利时,不可避免地又会在内部产生新的少数群体。”[22]差异不光是在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这个层次上,也存在于汉族与55个少数民族之间的层次上,也存在于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于少数民族内部。传统社会的多元多由于封闭社会(地理、人文)阻隔交流而形成,“今天的多元越来越多地是建立在个人主体性的多元之上”。[23]今天社会的发展体现在经由现代主体意识的不断自我强化而发生的分化,并由此而形成社会的主体多元与差异区分的形态。个人选择机会的多样造就此种主体多元社会形态,而且是最为重要的因素。[24]公民共和主义“把公民的自由同他们在一个历史地形成的共同体中参与自治和实现他们共有的共同的善联系起来”[25]私人利益在公共利益中得以实现。
后现代理论是一种影响巨大的挑战的理论,提供视角让我们反思自己的行动责任与方式。如何看待他者,是作为秩序之外的事物不得不宽容,还是纳入秩序之中。后现代主义主张用培育他者来补充自由主义式的宽容原则。[26]差异不是被无可奈何的接受,而是强化我们对日常生活的崇高的感觉的方式。人要承认有限性,他者被理解为自我掌控之外的东西。他者将带来快乐。后现代的感觉方式是一种建构方式,一种包含各种对立情感的方式。在现阶段及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中华民族呈现多元一体的格局。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由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需要认同与制度方面的持久建设。认同的促进部分要靠制度安排的保障。制度要能容纳共识与差异。
三、民族认同:“自我实现”的预言
特伦斯·兰杰通过对非洲进行族裔研究,发现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族性是最近才被发明或构想出来的。[27]“血缘”亲属关系、语言和宗教不必与族性或部落认同联系在一起;(在族性出现之前)非洲人的认同通过地域、家庭、联系、职业、政治、朝拜和地位表现出来,非常像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人。[28]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或社会团结应该建立在一系列抽象而普遍的法律规范之上,而不应该建立在如民族主义者所主张的那种前政治的血缘、种族、语言、文化或传统生活方式基础之上。”[29]建国初期对少数民族的识别是一个对其整合的过程,势必影响民族认同的范围与内容。在建国初期,大多数境内族群还处在前现代水平,但在政治上一律统一为“民族”,而非“部族”。此举弱化了血缘、遗传等因素的,加速这些族群向现代民族的转化。这个新塑的过程使得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更加清晰起来。科学识别的过程就是身份建构的过程。
“身份是‘内部认知’与‘外部环境’互动的产物。从建构主义学说而言,身份建构了体系,同时体系也反过来使身份的形成意义化,并形成“自我实现”的预言,因此,观念和规范体系得到有机的融合并形成集体认同,因此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讲不仅仅停留于理念,也成了一种代表物或社会事实。”[30]不少少数民族在识别为现代民族之后,重塑了自己的历史和并发展了自我认识。在近代以前,所谓的“苗”是对现今的贵州、云南、四川、湖南、广西等省区的非汉系的族群的泛称。“苗族作为中国境内历史最为悠久的古老民族的形象,是在20世纪初期形成的。但是,作为苗族这一民族共同体内部的自我认同意识的建构过程,却是在近百年以后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兴起的。”[31]比如对蚩尤形象的塑造。而80年代还有空前的满族历史和文化热。[32]关于满族的历史,满族语言的保护,以及学术期刊的创办,都有了长足发展。曾经回族的起源与历史都有争议,但是确定了回族的名称之后,回族的自我认识越发清晰起来。回族的身份很大程度上因宗教而明晰。“回族形成的关键在于结合了伊斯兰文化的高层(伊斯兰教)与汉文化的基层(汉语口语)。”[33]
民族国家的建构与稳固之根本在于集体意识的形成。这不是一个“齐一”的概念,而是种种次观念的整合。一方面是话语的建设,另一方面是制度的设计。“整合”的概念既不同于“同化”,也不同于“融合”,它是一种“弱”的概念,使少数民族在从事自己民族建构的同时,“平等地参与生产、分配和管理的实质性过程”[34]在个体层面,主体性多元化使得反思之后的认识与传统的集体规范发生冲突,有助于接受现代性之宪政国家政治理论。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的范式转换是“集体认同的负担由传统社会的预先设定转到共同体成员自身的肩上。”[35]
异质对照下的自我认识可能会引起挑战行为,一种对与“父亲”同义的强势文化的反叛。历史造成了少数民族的弱势地位,不管是政治还是文化,也固定了其进入现代社会之始的地位与格局。后现代主义反对历史造成的秩序,否认有方向的历史过程。[1]力图突破“中心文化—边缘文化”的模式,往往少数民族通过强化自我认同,变“我”为“我们”,加强自己的文化力量。
后现代艺术是“无特定深度的典型表象呈现”[36],摆脱权力关系的暗示和各种形式的束缚,追求感官的满足。这为少数民族艺术文化的流行提供了契机。
人在日常生活中才是具体的人,是展现具体“生活方式”的人。对自己是谁的探索努力,是对目前普遍的经济生活做出的回应,是对物的依赖的反抗,对日常生活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
对外物——主流文化的抵制(少数民族的身份即是一种疏离的标志),是一种追寻自由的方式。未必会付诸于创造性的行动。“异乡人”的身份本身获得了价值,坚持其差异,他们建构了自己面对强势群体时的一种对于主导价值观坚定忠诚的捍卫者形象。[37]
“后现代主义把对于人类自由的观点转移到对于人类自由的可能性方面,并把这个方面当做是人的自由的最本质内容。”[38]自由不需要形式。追求自由就要免于实现某种形式,而是要永远处于追求的过程中。少数族裔追求自由,也许只会在内心对国族符号的构建保持疏离与排斥,而不会采取行动反对民族国家的制度安排。又或者将这种情感宣泄在非政治性的文化娱乐活动中。
认同源于类似的“生活形式”。现代性支解了传统的生活形式,有些碎片会寂静下去,有些碎片又会在现代生活中得到加强。文化因素是变迁的。“定义文化意味着冻结多元的和变化着的认同过程。它是不可应用的,因为法律定义和社会进程之间的差异会不断增长。”[39]各族体的传承会在现代国家这个“舞台”上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是一种组合的方式。中华民族的建构历史还不太久,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组成民族的自我认同之解构与重构都是顺应这个过程的。中华民族从各族体间的差异及其碰撞中找寻整合的契机。
四、加强还是削弱:少数民族文化要素
民族共同体是集合的人、扩大的人,具有人格属性。此在之存在没有任何理由,但此在必深思自己的生存结构并积极筹划。“此在永远是有情绪的……此在既是活生生的有情感的处世,它就包含了对世界的看法和认识。”[40]聚落是族群设计自己价值与文化传承的制度安排、是族群历史延续性的见证与载体。往往聚落消亡,文化消亡;而聚落繁荣,文化繁荣。
干栏式建筑是我国民族建筑最有代表性的形制之一,曾经广泛流行。隋唐已降,干栏发展日渐式微,地居式木构建筑综合南方干栏及北方木骨泥墙的优势,成为建筑形制主流,进而为汉式正宗建筑体系,干栏建筑最后只保留住西南的阵地。干栏建筑渐与“深广之民”或“僚俚蛮夷”联系在一起。反映出族群之变迁与进退。但发扬其优点:适应地形、解放地面、良好的空间内外交流、框架结构灵活等,可以寄希望现代干栏式建筑的流行。[41]
现代文化也会对传统文化造成冲击。旅游业发展对泸沽湖的人文环境造成影响。作为应对,对摩梭村落的改造方案要多方面考虑。改造的思路是保持居民传统生活习惯、保留传统布局并丰富功能、增加现代生活设施、提高卫生水平、改进建筑材料、改进景观设计等。[42]这是传统民族要素与现代生活之间的调适。对传统少数民族聚落的保护,终极目标是以人为本,宜居的人居环境,而不是大舞台;其价值取向是“文化”的,更是“生活”的。[43]这之中首要的不是“汉化”对民族因素的破坏,而是“现代化”使民族聚落更适宜生活,因而有了新的生命力。
“生活”是结合共同价值观与差异分歧的场景。人是在具体的生活中诠释自己,传播自己。民族性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民族性并不拒绝变迁。如果一种生活方式已经过时了,文化也失去了生命力。将少数民族纳入成为国族的组成部分,对其差异与多元的整合,其民族认同的塑造,这些新塑的内容都具体的集中在少数民族的“生活”上。权力架构、共识、归属差异和人的发展都在这个场景中有所展现。
注 释:
①后现代的历史范畴除了特指20世纪60年代后的西方当代社会历史阶段,也可以指任何一个符合后现代特征的历史阶段。参见高宣扬《后现代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1][30]张全义.世界国家生成机理初探——全球集体认同的生成与模式转换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37,130.
[2]周平.民族国家与国族建设[J].政治学研究,2010,(3):85-96.
[3]张淑娟.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民族理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172-173.
[27][28][39][英]爱德华·莫迪默,[英]罗伯特·法恩.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C].刘泓,黄海慧,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28,39,89.
[4][34]李红杰.由自决到自治——当代多民族国家的民主政治经验教训[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41,122-123.
[5]暨爱民.“自由”对“国家”的叙述: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30.
[6]杨思机.“少数民族”概念的产生与早期演变——从1905年到1937 年[J].民族研究,2011,(3):1-11.
[7][8]陈理,彭武麒,白拉都格其.中国近代边疆民族问题研究[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30-31,67-80.
[9][32][美]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M].王琴,刘润堂,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31,337.
[10][23][24]赵旭东.一体多元的族群关系论要——基于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构想的再思考[J].社会科学,2012,(4):51-62.
[10][12][37][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M].邵迎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4,9-10,126.
[13][14][25][爱尔兰]玛丽亚·巴格拉米安,埃克拉克塔·英格拉姆.多元论:差异性哲学和政治学[C].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20,107,176.
[15][16][17][18][19][20][21][美]查尔斯·拉莫尔.现代性的教训[M].刘擎,应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168,182,275,65,61,242,265.
[22][29][35]马珂.后民族主义的认同建构及其启示:争论中的哈贝马斯国际政治理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65,3,49.
[26][美]斯蒂芬·K.怀特.政治理论与后现代主义[M].孙曙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148.
[31]杨志强.从“苗”到“苗族”——论近代民族集团形成的“他者性”问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6):1-7.
[33]董波.世界的才是民族的——回族形成的历史启示[J].理论导刊,2011,(12):41-43.
[36][38][40]高宣扬.后现代论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0,17,131-132.
[41][42][43]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族群·聚落·民族建筑: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专题会以论文集[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7-16,564-573,622-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