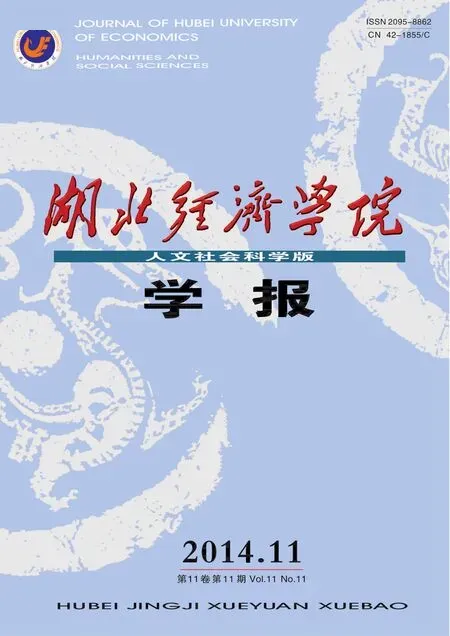《封锁》中的多重二元空间
薛梅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封锁》中的多重二元空间
薛梅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封锁》中的空间结构值得关注:电车内/电车外作为表层空间,构建起作品的象喻系统,是作者对未被封锁的世界的否定;公共空间/私人空间作为深层空间,解构了前一重二元对立中对被封锁世界的微妙认同,形成对被封锁的世界的否定;上海/中国作为潜在空间,是这双重否定的集中传达,也是作者悲观主义的整体呈现。
张爱玲;《封锁》;二元空间
《封锁》大概不算张爱玲最出色的小说,却无疑是一篇足够彰显张氏功力的作品。该作品意蕴的丰厚性,视角的多重性,表达的反讽性,都一向为论者所称道。《封锁》是关于时间的故事,它呈现了封锁前、封锁中以及封锁结束后人在平庸与激情间的游荡徘徊回归。而值得注意的是,它同时也是空间的故事,通过观察其多重二元空间的建构,也许能帮助我们更立体的看待这部被誉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1]的作品。
一、表层空间:电车内/电车外
《封锁》中最为明显的空间标志当然是电车,以此为区分,我们看到了两个空间:电车内的空间与电车外的空间。
封锁发生前,电车外的空间与电车内的空间是一致的,它们都代表冗长、单调、重复、让人几欲发疯却终究没有发疯的日常生活。文章开篇非常直接的用电车的行进来隐喻我们的生命状态: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
封锁的发生,使得这种一致性开始变化。电车停了,电车外的世界和电车内的世界也开始变化:电车外的世界是混乱的,电车里的世界则“相对镇静”。经过最初的分割,电车外“人声逐渐渺茫”,电车内的声音却被放大开来,我们听见公事房的人在讨论他们的同事,一对夫妻在絮絮叨叨,电车内的画面也开始变得清晰:用报纸托着菠菜包子的吕宗桢坐在了我们面前。
接下来的故事为我们所熟知,在这个电车内的封闭空间,吕宗桢与吴翠远开始上演他们的“艳遇”,呈现他们在日常世界里无法铺展开来的反抗与欲望。“封锁期间与世隔绝,外界现实的无情压力暂时被隔离开了,人们在突然脱离了习惯的生活轨道后,获得了极大的内心安全感,因而,车厢成了解放身心束缚的桃源世界。于是,平常被常规行为掩盖了的人的真实欲望现出原形,封锁之后的电车车厢变成了人得以真实活着的场所。 ”[2]
一方面,我们说,现实中的“封锁”,使得电车内外附近区域处于一种被隔离的状态,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作为这种被隔离区域的一个缩影,此时,电车内的空间又同时遮蔽(或者说是“封锁”)了电车外的空间,它变成唯一的,真实的,让人从平庸中暂时脱身的所在。当然,它也是暂时的。
当封锁结束,“电车当当当往前开”,宗桢起身离开,结束了与翠远的故事。电车外的世界也再此呈现到我们面前:
黄昏的人行道上,卖臭豆腐干的歇下了担子,一个人捧着文王神卦的匣子,闭着眼霍霍地摇。一个大个子的金发女人,背上背着大草帽,露出大牙齿来向一个意大利水兵一笑,说了句玩笑话。
小说在这里有一句奇怪的话:翠远的眼睛看到了他们,他们就活了,只活那么一刹那。车往前当当地跑,他们一个个的死去了。
这句话是颇为费解的,但如果以这种电车内外世界的关系来看,则并不意外:它只是对宗桢离开的仿写与重复罢了。对于宗桢的起身离开,小说使用的是极为相似的表述:“他走了。对于她,他等于死了。”故而,我们说,这是一次仿写,电车外恍若真实、浪漫、奔放的生命,是对之前宗桢给予翠远所有感受的一次勾勒,而从转瞬即逝的程度来说,宗桢与翠远的这场梦,与电车外景物的飞驰而逝也是一致的。
至此,电车内的世界也好,电车外的世界也罢,随着封锁的结束,再次连接为一个整体。如果说小说的结构是由封锁前后的时间线索来组织的,那么,小时的隐喻性主题,则是在电车内外世界的一致与断裂中完成的。电车内的世界是电车外世界的一个表征。它提醒我们,电车内的世界中发生的封锁,其实在电车外的世界也发生过。
二、深层空间:公共空间/私人空间
《封锁》呈现的第二层二元对立空间是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对立。
公共空间中的人们,是相互疏离,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封锁发生的时候,大街上,“商店一律地沙啦啦拉上铁门。”“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而电车里,即使处在困境之中,陌生人之间也拒绝交流,“有报的看报,没有报的看发票,看章程,看名片。任何印刷物都没有的人,就看街上的市招。”作者将之描述为一种思想的匮乏,但同时,它也呈现了公共空间中人们的互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不仅流淌在陌生人之间,熟悉的人之间也是如此。吕宗桢看到熟人董培芝时,立刻想到的便是躲开。而当他坐到吴翠远对面的时候,翠远的姿态显然也是戒备的。
陌生人之间即使有了交流,这种交流也往往充满误解与错位。电车上画人体骨骼简图的医科学生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三三两两聚拢来的人却自以为是的误认之为西洋画,并加以品头论足:那医科学生细细填写每一根骨头,神经,筋络的名字。有一个公事房里回来的人将折扇半掩着脸,悄悄向他的同事解释道:“中国画的影响。现在的西洋画也时兴题字了,倒真是‘东风西渐’! ”
宗桢与翠远的交流也是错位的。宗桢一番逼不得已不着边际甚至心不在焉的调情,却被翠远想象为这是一个让她“炽热、快乐”的“真的人”。而翠远带着几分嘲弄的倾听,则半真半假演绎成宗桢倾诉“我太太——一点都不同情我”的开端。更大的错位则在于,两人以此为基础,渐入佳境,甚至开始谈婚论嫁。当然,紧接着,随着封锁的解除,作者狠狠嘲弄了这种公共空间中,看似亲密关系被建立后的迅速坍塌。“她震了一震——原来他并没有下车去!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陌生人依旧是陌生人。
与此相对应,私人空间里人与人的关系又是如何呢?“家”自然是这种私人空间的代表。小说结尾,男主人公吕宗桢回到家中,“正赶上吃晚饭。他一面吃一面阅读他女儿的成绩报告单”。“晚饭”,“女儿的成绩报告厅”,似乎蕴含了十分明显的交流信息。然而恰恰是这句话暗示了交流的缺失,吕宗桢一边吃饭一边阅读——这是一顿无声的晚餐。我们还会注意到,晚饭后,“他接过热毛巾”,既然是“接过”,那么,是谁递过来的呢?照理说,应该是妻子。作为“家”这一空间,妻子的角色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这个必然应该并事实上也是有妻子存在的空间里,妻子却凭空消失了,成为了一个缺乏能指的空洞所指。这,似乎是对“家”这一空间的解构:妻子是存在,但妻子与丈夫是无法交流的。吕宗桢抱怨妻子不能“同情”理解自己。电车里那位反复提醒丈夫注意“裤子”的太太,俨然成为吕宗桢式家庭生活的补充与映照。
回头审视女主人公吴翠远与“家”的关系,同样也充斥这种拒绝感。翠远对家庭的心态直截了当:“她家里的人——那些一尘不染的好人——她恨他们!”
这样一来,我们将发现,公共空间也好,私人空间也罢,人与人之间始终是疏离、隔膜的,这种隔膜不因距离的缩进而变化,也不因关系的密切而消失。小说有个十分有意思的细节:
开电车的放声唱道:“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可怜啊可……”一个缝穷婆子慌里慌张掠过车头,横穿过马路。开电车的大喝道:“猪猡! ”
张爱玲是一位特别擅长重复的作家。解构主义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提出重复理论,提醒读者注意“重复”的普遍性与差异性,“识别作品中那些重复出现的现象,并进而理解由这些现象衍生的意义。”[3]上述所引段落正是一个值得分析的案例,它正是对封锁刚刚开始时一个情景的局部重复。
“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这句仿佛“从一个世纪唱到下一个世纪”的歌谣,在封锁刚刚发生时,一个山东乞丐唱过,开电车的山东人也唱过,仿佛充满了某种阶级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的暗示,然而,封锁结束片刻,开电车的山东人却一边唱着这句“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一边对慌里慌张掠过车头的“缝穷婆子”喝骂“猪猡”,音犹在耳,共同体的幻想却已瞬间消失,作者似乎不依不挠的告诉我们,即便在同一话语系统中,疏离仍然是无所不在的。
三、潜在空间:上海/中国
张爱玲的小说,其实有非常浓厚的“封锁”情结。这或许与她少女时代的经历有关,相关研究众多,这里就不再敷衍笔墨了。[4]她的封锁,大多首先建立在空间封锁的环境基础上,《金锁记》是姜家对曹七巧及其子女的封锁,《倾城之恋》是战争的炮火对白流苏范柳原二人的封锁。这种空间封锁意识,除了个人经历外,恐怕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张爱玲创作时所处的地域环境——沦陷的上海,之于中国的其它地区,它显然也是被“封锁”的。“电车是沦陷时代上海的缩影。从历史背景来看,沦陷区的上海空间和封锁中的电车空间恰如“孤岛”一样孤零零地存在着。沦陷区的上海空间跟历史隔断了,完全丧失了未来的时间,像时间停止的电车一样空荡荡地留下来了。被封锁的电车正是“空间封锁”、“时间封锁”的上海。”[5]上海/中国,这是小说的背景,我们不妨将之视为小说呈现出的第三重二元对立空间。
要解读这重二元对立空间所传达的意义,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前面的论述。第一部分结论中,我们说过,电车内/电车外的对立,形成了对主题的隐喻性表达。作者似乎要提醒我们,被封锁的世界和未被封锁的世界,在封锁前,他们是一致的——一致的冗长、单调、乏味、让人发疯,而封锁后,被封锁的世界反而产生了某种激情,如果这种封锁解除,激情便会退位,人们重新回到冗长、单调、乏味、让人发疯的生活中。这种隐喻性表达,是否也将被我们看做张爱玲对被封锁的上海和未被封锁的其它地域关系的一种象征呢?
我们不能武断做出这样的回答。因为在第二重空间对立中,作者又解构了这种封锁中产生的“激情”。在第二重空间对立里,作者呈现给我们的是:即使是在被“封锁”的状态下,人与人之间仍然是疏离,不被理解,拒绝沟通的。即使某种密切关系诸如爱情、婚姻、阶级的建立,激情迸发,最终也被证明不过是一种随时会被击溃的幻想。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爱玲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她不相信封锁之外的“正常”的世界——因为那是一辆永远不停下来的电车,她也不相信封锁之内的世界——因为那不过是打盹时候做的一个不近情理的梦。那么,何处是我们的安身所在呢?“然而思想毕竟是痛苦的。”蝇营狗苟的人生,像宗桢在灯下看到的那只整天爬来爬去的乌壳虫,在灯光的映照下,在避无可避的思想的拷问里,不如装死罢。
[1]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钱理群.20世纪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58.
[2]胡亭亭,杨庆茹.封锁:对生存困境的言说[J].学术交流,2009,(2):169.
[3][美]J.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王宏图,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5.
[4]可参见李培.论张爱玲《传奇》中的“封锁”情结[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05,(4).
[5][韩]郑雪瑞.张爱玲封锁的空间形式[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11,(3):5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