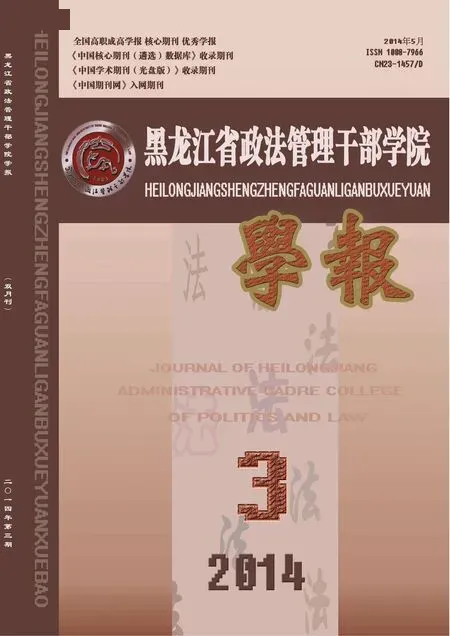刑法第63条第二款之“案件的特殊情况”认定
程先权,阮建华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北京100089)
刑法第63条第二款之“案件的特殊情况”认定
程先权,阮建华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北京100089)
为了实现刑罚的个别化和量刑的轻缓化,我国刑法的酌定减轻处罚情节规定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酌定减轻处罚情节中的“案件的特殊情况”包括“政策性特殊情况”和“情节性特殊情况”。在认定上,“政策性特殊情况”从打击犯罪的需要和社会普世价值两方面考虑;而“情节性特殊情况”则应考虑法益侵害性、非难可能性和预防必要性三要素。在适用时应先考虑“情节性特殊情况”,再考虑“政策性特殊情况”,以确保案件认定上的准确性。
案件的特殊情况;政策性特殊情况;情节性特殊情况
一、问题之提出
我国刑法第63条第二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但何为“案件的特殊情况”,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规定,导致了理论界对其适用范围和认定标准争论不休,让司法人员无所适从。在司法实践中,为了避免可能因认识不准确而导致的司法误判,很多法官对酌定减轻处罚规定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尽可能地少使用甚至不使用此规定,影响了酌定量刑情节功能的发挥。笔者将从一则实际案例出发,探讨“案件的特殊情况”认定问题。
2003年4月,被告人曾某因无力还债而产生保险诈骗的念头,并于同月18日至22日间,在我国多家保险公司以自己为被保险人,投保了保险金额为41.8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险。为了诈骗上述保险金,曾某劝说被告人黄某砍掉其双脚,用以向保险公司诈骗,并承诺将骗得的部分保险金还给债权人黄某。黄某在曾某的多次劝说下答应与其一起实施保险诈骗。同年6月,黄某按照曾某的要求将其双下肢膝盖以下脚踝以上的部位砍断。后二被告尚未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即先后被公安机关抓获。经鉴定,曾某属三级重伤。法院一审判决黄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黄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1]。
本案中,黄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争议不大,主要的问题是在量刑上。本案中黄某故意砍断曾某双足,致其三级重伤,应当属于“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理当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法定刑幅度内量刑,但这一刑罚明显畸重,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在实现法定刑以下量刑的问题上存在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黄某如需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理由是本案中黄某的行为并无法定减轻处罚情节,如需在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内量刑,只能依据刑法第63条第二款之“案件的特殊情况”规定履行报请程序。另一种观点认为审理本案的法院即可径行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无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理由是本案中被告人曾某的承诺不属于刑法第63条第二款中的“案件的特殊情况”范畴,故没有适用报请核准程序的余地。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是指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案件,本案不涉及国家利益,故不适用。此外,在司法实务中,被害人承诺事实上已成为一种减轻处罚事由,即只要案件中存在被害人的真实承诺,法院就可以在法定刑以下量刑。
笔者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曾某承诺重伤这一情节是否属于刑法第63条第二款规定中的“案件的特殊情况”?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其法理依据何在?如果持肯定的态度,其理由又是什么?上述问题的研究直接涉及“案件的特殊情况”解释和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因此对统一司法适用和实现个案公正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废除酌定减轻处罚规定观点之检讨
一般认为,我国刑法第63条第一款规定的是法定减轻处罚情节,而第二款之规定称为酌定减轻处罚情节。虽然我国现行刑法明文规定了酌定减轻处罚情节,但由于立法规定模糊和司法适用不统一,学界对其存在的价值提出质疑。有学者认为,此规定损害了法律的统一性,许多应当判刑的经济犯罪,因适用此规定而被免予刑罚或判缓刑,同时也容易滋长审判人员徇私枉法的现象[2]。有学者认为,此制度牺牲了法的安定性,为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犯保留了制度空间,是罪刑法定理念的破坏,应当废除[3]。
上述废除论者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一是现行的酌定减轻处罚规定有其严格的适用条件。即在实体上,酌定减轻处罚情节要求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但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又需要适用时才能适用;在程序上,地方法院的酌定减轻处罚判决都要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而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标准是一样的,一定程度上可保证法制的统一。由于适用条件的严格规定,并不会导致法官的滥权。
二是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和行为人的非难可能性相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行为的法益侵害性较小或行为人的可非难性较小时,适用酌定减轻处罚情节规定免予刑罚或判处缓刑未尝不可。否则会导致处罚过重,有将犯罪人当作工具之嫌。
三是酌定减轻处罚规定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法对犯罪和刑罚的规定尽可能明确化,但由于文字表述本身的缺陷,无法绝对明确。因此,罪刑法定原则由绝对的罪刑法定主义转向了相对的罪刑法定主义,进而允许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一定限度内自由裁量,而酌定减轻处罚规定正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体现。
笔者认为,酌定减轻处罚规定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其一,酌定减轻处罚规定有利于实现刑罚的个别化。由于立法者无法预测社会的所有情形,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严格依照法定减轻处罚情节进行量刑,那么可能会造成个案的不公正,而酌定减轻处罚规定正好缓解此矛盾。其二,顺应刑罚轻缓化的需要。我国历来有重刑的倾向,伴随着刑法轻缓化时代的到来,我国也开始积极转变这种重刑主义的做法,如《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十三个死刑罪名。即便刑法规定了众多的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但社会的犯罪是复杂多样的,刑法不可能完全囊括,酌定减轻处罚规定仍有其存在的空间,如许霆案。
三、“案件的特殊情况”之解释
何为“案件的特殊情况”?这涉及酌定减轻处罚情节的适用范围,必须予以厘清。对此,学界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此“案件的特殊情况”是指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情形(后文称“狭义说”)。根据立法者的解释,该“特殊情况”指案件的特殊性,如涉及政治、外交等情况[4]。又如《人民法院报》指出“所谓‘特殊情况’,主要是对一些案件的判决关系到国家的重大利益,如国防、外交、民族、宗教、统战以及重大经济利益”[5]。另一种观点认为,刑法第63条第二款依然是考虑到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判处法定刑的最低刑还是过重的情形而设定,而不是为了政治、国防与外交的需要(后文称“广义说”)[6]。换言之,只要判处法定刑的最低刑仍然过重,就可援引“案件的特殊情况”规定减轻处罚。
笔者以为,“广义说”相对更为可取。理由如下:
其一,立法原意是否存在值得质疑。“狭义说”基于对立法原意的考察,将“案件的特殊情况”限制在事关国家利益的范围之内,但立法原意来自哪里?是立法者中某个人的意见,还是所有立法者的意见?若是所有立法者的意见,那么又如何获得?若只是某个人的意见,将其称为立法原意并不合适。事实上,获得立法原意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即便我们承认立法原意是存在的,“狭义说”也是当时的立法原意,当立法原意规范化后,就具有相对独立性,为了使刑法规范适应不同的案件,应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前提下作客观解释。此外,将“案件的特殊情况”解释为对案件量刑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在文义解释的角度上看并无不妥。
其二,从司法实务的判决看,有将“案件的特殊情况”解释为不限于国家利益的情形。有些案件虽然不涉及国家利益,但最高人民法院依然适用了酌定减轻处罚规定来量刑,如许善新等走私普通货物案、程乃伟绑架案和洪志宁故意伤害案等。如果严格采取“狭义说”,上述案件是不可能适用酌定减轻处罚规定的。
其三,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采“广义说”是可行的。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在“犯罪情节轻微”的情况下可适用免予刑事处罚,此处对“犯罪情节”无限定,应将其解释为“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所有情节”,并非仅是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情形。换言之,处罚较轻的免予刑事处罚都不以“特殊因素”为要件,而处罚较重的酌定减轻处罚却要求具备,从体系解释上看是不合理的。
四、“案件的特殊情况”之认定
明确“案件的特殊情况”内涵后,有必要对其认定标准进行探讨。波斯纳指出:规则会要求有特例处理,而标准可以说就是要将这种特例处理制度化[7]。故明晰“案件的特殊情况”标准对其认定尤为重要。“案件的特殊情况”认定所考虑的因素,学界有不同见解:
第一种观点认为,“案件的特殊情况”认定需考虑以下因素:(1)犯罪的常发性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2)被害人的过错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3)行为人意志自由的程度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4)民众的法感情影响行为的可罚性及其程度[8]。
第二种观点认为,量刑时应否减轻处罚,主要依据:一是客观违法性的大小,二是主观有责性的大小,三是预防必要性的大小[9]。
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判断案件是否具有特殊情况时,还应坚持综合判断的原则,既要考虑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还要根据人民群众的反映及当时的时空环境,考虑刑罚预防的必要性和适度性等问题[10]。
第四种观点认为,这里的“案件特殊情况”包括“政策性特殊情况”和“情节性特殊情况”。“政策性特殊情况”即事关国家重大利益的政策性因素,应遵循补充性原则指导对其理解和适用。“情节性特殊情况”指非法定的,反映社会危害性或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较小,应当据以减轻处罚的事实情况,又包括“单一的情节性特殊情况”和“综合的情节性特殊情况”。前者的适用原则应当是“相似情节等价比较原则”,后者则应当根据“服判效果最大化原则”加以理解和适用[11]。
第一种观点将社会危害性纳入“案件的特殊情况”的认定之中,具有合理性,但亦存在问题。社会危害性是客观要素还是主观要素不明确。如果此处的社会危害性包括主客观因素,那么与通常将社会危害性作为客观要素对待不同,且将主客观要素混同不利于对犯罪的认定。如果此处的社会危害性是指纯客观的要素,那么其标准中又无主观方面的内容,存在欠妥之处。此外,论者虽将民众的法感情作为“案件的特殊情况”认定中的一个因素,但民众的法感情本身无具体的量化标准。
正如提出第二种观点的学者自己所言:基于政策理由而减轻处罚的情形,并不适用于这一标准。换言之,论者的认定标准只能解决情节性特殊情况,并不能解决政策性特殊情况问题。而“案件的特殊情况”中正好包括“政策性特殊情况”,将第二种观点所倡导的标准作为“案件的特殊情况”认定标准并不全面。
第三种观点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及刑罚预防的必要性和适度性纳入“案件的特殊情况”的认定中,有其优势,但亦并非无疑问。首先,“案件的特殊情况”包含人民群众的反映存在不确定性,不易把握。其次,将当时时空条件作为考虑因素不合适。因为当时时空条件可能会影响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将其纳入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之中即可,无须另外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考察。最后,该标准以“等”为结束语,未穷尽其内容,难以统一适用。
第四种观点将“案件的特殊情况”区分为“政策性特殊情况”和“情节性特殊情况”,并区分情况进行处理这一见解非常具有见地,笔者原则上赞同此观点。理由如下:
首先,将“案件的特殊情况”区分为“政策性特殊情况”和“情节性特殊情况”,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认定的准确性。“政策性特殊情况”和“情节性特殊情况”存在差异,一个是在刑事政策的角度,一个是在规范法学的角度,理当分类讨论。将二者适用同一标准,虽可简化问题,但由于二者在法律性质上不同,适用同一标准不妥。因此,只有区分情况探讨,才能保证标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而解决其认定问题。
其次,对于“政策性特殊情况”的判断,由于其是在极其例外的场合适用,所以以置后适用为原则。因为“政策性特殊情况”主观性大,需要严格限制,否则容易滥用。由于“政策性特殊情况”不可能从规范法学上追寻减轻处罚的根据,所以只能从刑事政策上寻找。其主要考虑两个因素:打击犯罪的需要和社会普世价值。为了打击犯罪,有时必须在政策上对犯罪人予以从宽处罚,如为了引渡犯罪人而对其作出减轻处罚的承诺。社会普世价值较抽象,但还是能够把握,如基于“亲属间和睦”而减轻处罚就属于此情况。通过上述要素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可防止恣意认定“政策性特殊情况”,进而准确量刑。
再次,对于“情节性特殊情况”,笔者不赞同“情节性特殊情况”按照“服判效果最大化原则”来适用。“服判效果最大化原则”太抽象,不易操作。对于“情节性特殊情况”的认定,笔者认为应该从法益侵害性、非难可能性、预防必要性来考虑。犯罪是违法且有责的行为。因此,“情节性特殊情况”的认定当然需要考虑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和行为人的非难可能性。首先,犯罪是侵害法益的行为。因此,是否属于“情节性特殊情况”,当然需要考虑行为人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如果行为人的法益侵害性较小,依照法律规定量刑明显过重时,可认定为具有“情节性特殊情况”。其次,非难可能性作为犯罪的必备要件,在认定“情节性特殊情况”时也应考虑。如果行为人的非难可能性小,那么其被认定为“情节性特殊情况”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行为人主观上不具备有责性,根本无须承担责任,当然也无须考虑是否具有“情节性特殊情况”。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并无期待可能性,当然不应处罚。期待可能性比较小时,亦可将其认定为“情节性特殊情况”,进而减轻处罚。许霆案即可根据“情节性特殊情况”而减轻处罚,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期待许霆不取钱的可能性比较小。最后,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情节性特殊情况”的认定要考虑预防犯罪的需要。“情节性特殊情况”的认定需要考虑行为人的再犯可能性以及减轻处罚是否可以足以预防一般人犯罪,从而充分实现刑罚保护法益的目的。
最后,在考虑案件是否具有特殊情况时,应以“情节性特殊情况”为原则,以“政策性特殊情况”为例外。因为“情节性特殊情况”规范性强,认定标准较明确,不易发生偏差;而“政策性特殊情况”政策性较强,标准相对模糊,主观性强。因此,在适用时应该优先考虑“情节性特殊情况”,再考虑“政策性特殊情况”,才能尽可能地保证案件适用的准确性。
五、“案件的特殊情况”认定之具体分析
在明确“案件的特殊情况”认定标准后,需要结合具体案例检验上述标准。分析如下:
首先,判断案件有无“情节性特殊情况”。针对文章开头所述案例,被告人黄某是基于被告人曾某的承诺而实施的伤害行为,与一般的伤害行为存在区别。若仍按一般的伤害行为处理,对黄某显然过于严苛。鉴于此,可以考虑适用刑法第63条第二款之“案件的特殊情况”。其一,从法益侵害性的角度看,黄某的行为造成了被害人曾某重伤的严重后果,其法益侵害严重,但基于被害人的承诺,其违法性又有所降低。其二,从有责性的角度看,黄某基于实现债权目的而实施的行为,期待可能性较小。其三,从预防必要性看,黄某并非累犯,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小。从一般预防的角度看,这种情况下对其减轻处罚亦足以防止一般人犯罪。综上,黄某案具有“情节性特殊情况”,属于“案件的特殊情况”范畴。
其次,判断案件有无“政策性特殊情况”。在某些案件中基于“情节性特殊情况”考虑所获得的减刑幅度可能还不能满足政策上的需要,这时就需要进一步考量“政策性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情节性特殊情况”,当然更需要考虑有无“政策性特殊情况”。如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贪污巨资后潜逃国外,由于被请求国要求我国作出刑罚量刑的承诺。鉴于本案中的被告人无“情节性特殊情况”,可以考虑适用“政策性特殊情况”而减轻刑罚,实现打击犯罪的目的。由于文章开头所述案例并不涉及国家重大利益,故不存在“政策性特殊情况”。
最后,确定是否具有“案件的特殊情况”。如果案件具有“情节性特殊情况”和“政策性特殊情况”之一,即可适用酌定减轻处罚规定。文章开头所述案例虽无“政策性特殊情况”,但由于有“情节性特殊情况”存在,同样属于“案件的特殊情况”范围。
六、结语
综上,笔者认为黄某案中被告人曾某的承诺属于刑法第63条第二款规定中“案件的特殊情况”范围,在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基础上,当然可以对被告人黄某减轻处罚,即在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裁量刑罚。此外,被害人承诺事实上已成为一种减轻处罚事由并不能成为酌定减轻处罚不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理由。因此,文章开头所述案例中的法院未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就径行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的做法,笔者认为是违反现行法律的,应予以纠正。
[1]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等.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310-315.
[2]高铭暄,赵秉志.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下)[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2207-2208.
[3]蒋熙辉.论特别减轻制度[C]//陈兴良.刑事法判解(第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97.
[4]胡康生,郎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第3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61.
[5]颜茂昆.关于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N].人民法院报,1997-04-22.
[6]张明楷.“许霆案”的刑法学分析[J].中外法学,2009,(1).
[7][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57.
[8]徐立,胡剑波.“许霆案”减轻处罚的根据与幅度分析[J].法商研究,2009,(5)。
[9]张明楷.许霆案减轻处罚的思考[J].法律适用,2008,(9).
[10]仇晓敏.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几个问题[J].人民司法,2009,(21).
[11]金福,王志远.刑法第63条第2款之“案件的特殊情况”解析[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2).
[责任编辑:李洪杰]
Identification of"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in The Second Paragraph of Article63 of The Criminal Law
CHENG Xian-quan,RUAN Jian-hua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penalty and the mitigation of sentencing,it is necessary and reasonable to stipulate discretionary mitigated punishment circumstances in our criminal law.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of the discretionary mitigating punishment include"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in policy"and"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plot".While being recognized,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in policy need to be considered o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the necessity to fight crimes and the common social values;as to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plot,the infringement of legal interests,th e possibility to be blamed and the necessity of prevention are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For the sake of the accuracy in recognizing the cases,we should first consider the"special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plot",and then consi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in policy.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in policy;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plot
DF521
:A
:1008-7966(2014)03-0055-04
2014-03-27
程先权(1989-),男,贵州遵义人,2012级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阮建华(1988-),男,陕西商洛人,2012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