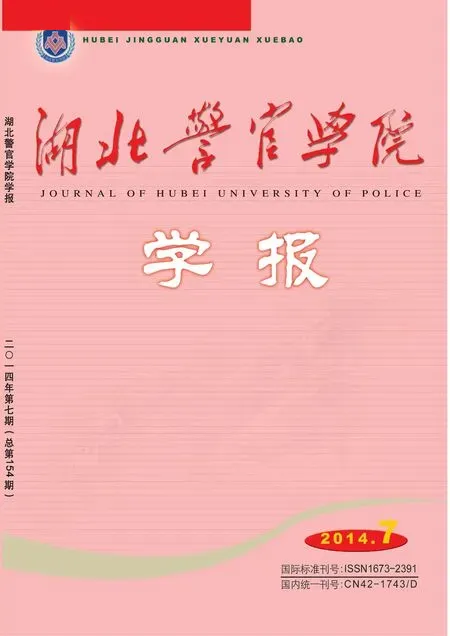主犯认定中两个问题的探讨
刘世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
主犯认定中两个问题的探讨
刘世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
主犯的确认决定着共同犯罪人的作用大小和责任的轻重,是其他共同犯罪人尤其是从犯认定的依据。由于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模糊,我国对于主从不明以及只有主犯的共同犯罪,一般不再作主犯的认定。这种做法看似合理,实际上不符合刑法认定主犯、区分主从的立法精神。因此,应加强主犯的认定。
共同犯罪;主犯;主犯认定
一、主犯的划分方法
为了实现对共同犯罪人刑事责任的科学划分,对共同犯罪人的种类进行合理区分是十分必要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共同犯罪人。目前除了极少数采用单一制的国家没有对共同犯罪人进行分类外,①单一制是指单一的正犯体系,又称为排他的正犯概念或包括的正犯概念,是指将所有共同参与实行的人均视为正犯,对于各个参与者,依据其参与的程度和性质来量刑。中外划分共同犯罪人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分工分类法,是以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为标准进行分类的立法例。[1]这种分类方法被大多数国家所采纳。二是作用分类法,这是我国独有的分类方法,是以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为标准对共同犯罪人分类的立法例。[2]虽然学界对本罪的划分仍然存有一些争议性见解,但通说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实际是以作用为基本分类标准,兼顾分工情况,将犯罪人划分为四类,即: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主犯和从犯的划分主要是依据第二种分类方法,即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
二、主犯的类别
从我国刑法第26条规定中不难看出,我国将主犯分为两种:一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二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根据刑法第97条,在犯罪集团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被认为是首要分子。由于立法上用词的近似性与模糊性,首要分子与主犯关系在学界一直争议不断。有人认为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和主犯并无二致,前者即是后者,后者即是前者。[3]对此,有论者提出质疑,认为如果仅仅将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认定为主犯,便会导致对那些不起组织、领导作用的,但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无所适用,进而提出,犯罪集团中的主犯范围应该包括那些在该组织中不起组织、领导作用的,但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4]笔者认为,刑法虽然明确了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作为主犯,但并不排斥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之外的主要参加者也是主犯,因为完全可以从第26条的第二种主犯中作出合理解释,即“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既包括在一般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和聚众共同犯罪的首要分子及其他聚众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也应该包括犯罪集团中除首要分子外的主要犯罪分子。[5]否则,就会出现将犯罪集团从共同犯罪中剥离的情况。刑法之所以将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单独列出,是因为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在犯罪集团的作用更大,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另外,我国刑法分则的相关条文也是将首要分子与积极参加者并列,只是在量刑上有所区分。主犯的分类还有三分法和多分法等争议,但这不过是形式上的区别,并无实质差别。
三、司法实践中主犯的认定问题
理论上关于主犯的划分和分类相对容易,实践中关于共同犯罪的问题则层出不穷,很多共同犯罪无法确定主从关系。据此,一些司法解释认为可以分清主犯的应当要区分,如果不明显的,可以不区分。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是否区分主犯、从犯问题的批复》:在审理单位故意犯罪案件时,对其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不区分主犯、从犯,按照其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处刑罚。《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项也规定:对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根据其在单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节,分别处以相应的刑罚,主管人员与直接责任人员,在个案中,不是当然的主、从犯关系,有的案件,主管人员与直接责任人员在实施犯罪行为的主从关系不明显,可不分主、从犯。立法上的模糊和司法解释上的倾向导致很多起诉书和判决书避重就轻,没有对主犯和从犯作出区分,只是简单地认定为共同犯罪。①2001年1月至2004年9月间山东省某两级法院共审结案件中,明确主犯从犯区分认定的285件775人占共同犯罪案件的14.1%和16.1%。数据源自吴光侠著:《主犯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页。根据我国共同犯罪的划分体系,主犯独立于从犯,可以单独存在,没有主犯便不可能成立共同犯罪,只有主犯而且是二人以上,没有从犯也可以成立共同犯罪。据此,有学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共同犯罪中所有共犯都是主犯,还要不要认定主犯?[6]
笔者认为,以上既不言明主犯也不言明从犯的做法是极其不规范的。首先,我国现行刑法已经取消了79年刑法关于主犯从重处罚的规定,而现行刑法第27条第2款却规定,对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种主犯不从重、从犯却从轻的立法模式其实是默认这样一个事实:只要没有对共同犯罪分子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那么这个犯罪分子一定就是按主犯来处罚的。其次,在现有划分体系下,无法辩明主从的情况下,其实一概不作区分的结果便是所有的共同犯罪分子被认为是主犯,尽管司法者在具体裁量过程中会采取区别量刑的态度,但仍然无法回避这样一个困境,即没有主犯之名却有主犯之实,没有从犯之据却行从犯之事。再次,司法实践中这种没有主从区分的共同犯罪占据多数的现象,正如有学者所言,明显是对刑法中区分主从立法精神的违背,难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不利于对共同犯罪进行瓦解、惩治和预防。[7]
四、主从关系不明的共同犯罪中一概认定主犯的探讨
对于主从不明的共同犯罪,正如之前所讨论的,司法实践中大多形式上回避主、从的明确区分,本质上是按照全部主犯的态度定罪量刑的。对于这种做法,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在主从关系不明的情况下,根据疑罪从无原则,以及我国刑法中对从犯从宽处罚的精神,对其应以从犯论处。第二种观点认为,既然难以区分主从,就不加区分,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各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具体情况定罪量刑。这种观点也是目前司法者所普遍采纳的。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在无法区分主从时,应当将全部共同犯罪人认定为主犯。[8]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有消极应对之嫌,不利于办案人员积极主动查明案件事实,准确定罪量刑。的确,疑罪从无是一项重要的刑事法原则,但其意义主要存在于犯罪构成的范畴内,而不是在量刑上。主、从的区分是在成立犯罪的基础上对共同犯罪人作用的判断,更多的是刑事责任的划分问题,而不是犯罪成不成立的问题。同时,如果存疑定从犯,则会造成这种情况:犯罪人相互包庇、相互隐瞒,和办案人员打掩护战,以求最后的从轻处理,从而不利于对共同犯罪的瓦解和惩治。另外,从司法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没有主犯便没有从犯,从犯的认定是以主犯为前提的,从犯是与主犯相对应的概念,如果都是从犯,明显违反基本的逻辑。
第二种观点虽然为目前司法实践所普遍采用,而且我国相关司法解释也倾向于这种做法,但这种做法明显违背了我国当前的共同犯罪制度,虽然这种制度在立法上和司法上存在一定的差距与不协调之处,但这绝不能成为不区分主从的理由。其实,从实施效果上来看,不区分主从的第二种观点与第三种观点将所有共同犯罪人认为是主犯并没有根本差别。因为,这两种观点在具体操作中都是需要根据各个共同犯罪人的具体情况定罪处罚。不做主从认定从效果来看只是形式上规避了主从认定上的矛盾,正如之前所论述的,不言明主从的实质就是默认了犯罪人为主犯。笔者认为,与其默认共同犯罪人为主犯,倒不如明确地将主从不明的犯罪人都规定为主犯,也就是采纳第三种观点。这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从共同犯罪的主、从关系构成上看,主从关系的区分是依据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来区分的,起主要作用的就是主犯,起次要作用的就是从犯,并不存在介于主犯和从犯之间的第三种犯罪分子。如有学者所言:只有主犯没有从犯可以成立共同犯罪,但共同犯罪中不可能只有两个以上的从犯而无主犯。[9]既然存在共同犯罪,就必然存在主犯。所以,在认定共同犯罪的过程中,没有找到主犯其实是对共同犯罪本身的一种否定。
其次,刑法中的从犯是比照主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97年刑法修改以后,主犯只需根据其在具体犯罪中的分工和情节定罪量刑即可。在这种量刑制度设计之下,立法者其实是将一般的形态当成主犯来看待,如果没有对主犯的一般规定作为参照,我们就很难说对从犯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实践中很多共同犯罪并不是所有共同犯罪人一同到案,但无论先到案的是主犯还是从犯,都毫无疑问要对之进行定罪量刑,尽管主犯没有归案,但在事实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对从犯依然要比照刑法中关于从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定罪量刑,这种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基准正是主犯的量刑标准。
再次,在不能区分主从的共同犯罪中,将所有人当做主犯来对待符合宽严相济的政策和刑事立法精神。如前所述,主犯是存在“首要分子”②这里的首要分子,指的是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和聚众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而非指刑法第97条所指的一般意义上的首要分子。和主要参加者之分的,根据刑法第26条第三款的规定,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在刑法分则的相关罪名中也规定了首要分子的独立量刑区间。而其他主犯则并未在总则中对量刑予以规定,只是在一些分则条款中对“积极参加者”和“其他参加者”做了量刑的区分。相对于主犯,对从犯奉行的是“必减主义”。从这种立法设计上来看,只有明确确定是“首要分子”和“从犯”时才能依据刑法第26条和27条以及相关分则条文定罪量刑,因为这种区分将会对犯罪分子的定罪量刑造成实质性影响。而不加区分地认定为主犯,按照其具体情况定罪量刑,并不会对其罪刑造成实质性影响。这样一来,采取这种折中的处理方式既不会放纵了可能是“首要分子”的犯罪分子,也不会重责了可能是“从犯”的犯罪分子。也许有人会质疑这种戴主犯帽子的做法似乎有些多余,而且有违背主犯定义之嫌。如有人提出,根据刑法对主犯的定义,只有那些在犯罪集团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和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才是主犯,而难以区分主从的共同犯罪中,并不是所有人都一定符合这种定义上的要求。[10]笔者认为,主从不明显不等于将从犯认定为主犯,而只是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是主犯还是从犯。这种认定从本质上讲是量刑意义上的界定,对于共同犯罪本身不具有决定作用,无论是主犯还是从犯都要对共同犯罪的成立负责。一般情况下,证明主从的证据不够明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具体情况也是不够明确的,即使不将其认定为主犯依然面临这样的问题。而认定为主犯并不妨碍对主从不明的共同犯罪人定罪量刑,法官依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自由裁量,并不会因为主犯认定而加重其刑罚。有学者也注意到,在共同实行犯场合,如果主次不明的话,实际上说明各个实行犯的地位相当,不相上下,都应当作为主犯看待。[11]至于主犯的概念是否涵盖“主从不明”的情况,前文已做过论述,即在当前犯罪人分类体系下,不认定为从犯便是主犯,这种犯罪分类体系本身有其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权衡各方面利弊,权宜之计下将“主从不明”归入主犯的范畴内考量显然要比归入从犯的范畴内更合适。并且司法实践中长久以来的做法,表面上回避了主从的争议问题,实质上走的还是主犯路线。正如有学者所言:很多判决书没有认定主犯、从犯,实际上是把这个人认定为主犯的。不说出来只是一种心理安慰。[12]
五、只有主犯的共同犯罪中明确主犯地位的必要性
共同犯罪按照主从区分无非分为两种:一种是既有主犯,也有从犯;另一种是只有主犯,没有从犯。关于主从不明问题,上文已做了粗浅的探讨。对于第二种都是主犯的共同犯罪,也是有必要逐一列明主犯地位的。
首先,主犯不仅对于从犯有着重要的意义,主犯对于主犯也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主犯的类型上来看,主犯有“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和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犯罪分子”之分,而且“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又可继续区分为“一般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分子”、“聚众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其他聚众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分子”和“在犯罪集团中除首要分子以外的主要分子”等等。这种划分不仅可以对法条内容和司法实践中主犯的表现形式作出科学的说明,也体现出了我国刑罚的科学性,能更好地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13]由此可见,主犯并不是一个终极意义上的划分,当一个共同犯罪有几个主犯时,虽然他们都是起主要作用,但其作用会有区别,其行为的危害性也不完全相同,因此量刑时应有所区别。[14]所以,在认定各个共同犯罪人都为主犯的前提下还要对各个主犯进行进一步的区分,以求做到罪责刑相适应。从这种意义上讲,逐一列明主犯不仅是进一步明确主犯共犯人关系的前提,也是对主犯共犯人定罪量刑的需要。
其次,在认定共同犯罪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各个共同犯罪人的分工和作用进行区分,尤其是对于只有主犯的共同犯罪,各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都起主要作用,在起诉或者判决过程中,一方面对各个共同犯罪人的犯罪事实进行认定,另一方面却又不说明作用关系,那么有很多问题就难以克服。例如,根据刑法第28条,如果犯罪人是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其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但在某些被胁迫参与犯罪但起了主要作用且情节恶劣的情况下,完全适用“应当”,显然会造成对行为人的放纵。对此,通说认为,被胁迫参加犯罪却在共同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就成立主犯且不再适用第28条。[15]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认定其主犯地位便成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必要前提。不然,单从犯罪事实上看,客观上显然更贴近第28条的规定。同时也使得法官难以名正言顺地对这种犯罪人进行合理的量刑。
再次,从主犯的立法意义上看,立法之所以要规定主犯,不仅仅有着技术上的意义和作用,同时也是一种犯罪人地位的象征,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对整个共同犯罪恶性程度的反映。不明确主犯地位不仅容易给人以主从不分的混淆,而且不利于对共同犯罪性质的认识,也不利于对共同犯罪的惩治和预防。另外,无论是起诉书还是判决书,都讲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论证和说理都要求逻辑清晰,前后一致。那么在没有从犯的共同犯罪中毫不遗漏地明确各个共同犯罪人的主犯地位不仅是一种严谨态度的表现,也是法律论证和推理的需要,这也符合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中增强判决说理性的要求。
[1][2]陈兴良.规范刑法学(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41.
[3]高铭暄,赵秉志.中国刑法学研究的历程[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26-27.
[4]董邦俊.刑法中的主犯研究[J].现代法学,2003(25):5,47-51.
[5]高铭暄.刑法专论(上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347.
[6][12]刘宪权.中国刑法学讲演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387-3 88.
[7][11]杨开江.主犯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2:160.
[8][10]彭辉.论共同犯罪人的“主”与“从”[D].长春:吉林大学,2012.
[9]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90-91.
[13]陈兴良.共同犯罪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92.
[14]张明楷.论主犯[J].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7(2):14.
[15]任海涛.论胁从犯之应然理论定位[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22.
D914
A
1673―2391(2014)07―0068―03
2014-02-12 责任编校:陶 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