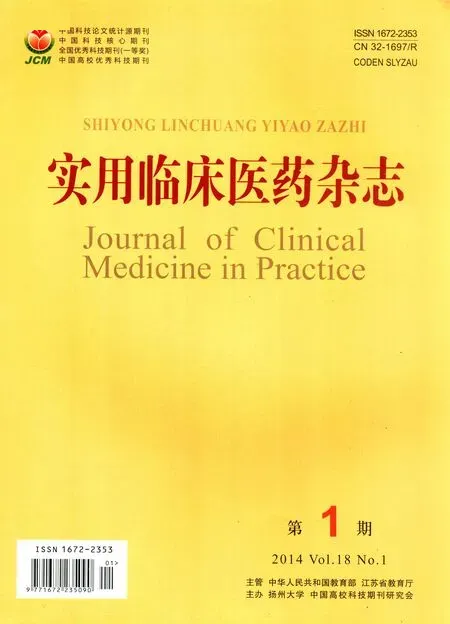非小细胞肺癌分子靶向治疗药物的研究进展
赵 颖,王 芮,付桂英
(解放军第307医院药学部,北京,100071)
肺癌是最常见的致死性癌症之一,其死亡数几乎占所有癌症死亡数的30%左右[1]。随着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复的日益加重,肺癌的发病率也在逐年上升。其中,有大约15%肺癌属于小细胞肺癌,其余均属于非小细胞肺癌(NSCLC)。现今治疗肺癌患者的方法主要有手术治疗,放疗,化疗以及免疫治疗等手段。手术治疗主要对未发生转移的肿瘤原发病灶切除才能更有效,但因肿瘤发现的时候一般都是晚期,手术治疗很难达到理想疗效。癌症的早期诊断并不能降低肺癌患者的死亡率。传统的放化疗以及免疫治疗对肿瘤细胞的选择性差,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连带机体正常细胞也受其害,引起各种不适反应。实际上有很多癌症患者都是药源性致死,而并非死于癌症本身。近年来,由于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的靶向性、低毒性和特异性,其开发越来越受到医药工作者的关注。作者通过查阅国内外文献,对非小细胞肺癌治疗的有效靶点以及对应靶点的抗肿瘤药的发展情况进行综述。
1 抑制肿瘤血管新生
肿瘤血管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以及转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肿瘤在没有氧气和营养物质供应下,长不到2 mm3就会从内部开始坏死,肿瘤塌陷萎缩甚至消失。只有肿瘤内部血管形成,为肿瘤细胞的无限制繁殖提供充足的氧和营养物,肿瘤才能迅速生长。肿瘤血管的形成受到诸多细胞因子的动态调节过程。随着影像肿瘤血管形成的特异性靶点不断被发现,相继开发出了一系列针对靶点的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
1.1 VEGF靶点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作为现今发现的最重要的血管促成因子,能促进肿瘤血管的生成,间接促进肿瘤的转移。研究中发现,肿瘤内部内皮细胞与正常组织中内皮细胞在基因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2],肿瘤内皮细胞存在特异性VEGF,且在肺癌患者中,VEGF表达量明显高于良性和正常组织[3]。这项发现为药物的特异性提供了依据。通过阻断其传导信号而抑制肿瘤血管新生成为肿瘤治疗的重要方法。
VEGF单克隆抗体可以阻止VEGF引发的下游信号转导,抑制肿瘤血管的生成。Swisher[4]等人进行的一项Ⅰ期临床试验显示,大剂量的应用VEGF单抗安全性好,且可耐受。贝伐单抗(Avastin)是人的重组单克隆抗体,作为VEGF为靶点的抗体,可以与VEGF-A配体结合。一方面促使肿瘤血管退化,另一方面纠正相对正常血管的正常化。对于长期服用贝伐单抗的患者,贝伐单抗可以持续抑制肿瘤血管的再生[5]。
1.2 血管形成抑制因子
肿瘤血管的生成是由血管形成促进因子和血管形成抑制因子共同调节的失衡引起,肿瘤的微环境会引起肿瘤局部的血管形成促进因子的增加而导致肿瘤血管的新生。血管形成抑制因子的增加可逆转肿瘤微环境造就的结果,抑制肿瘤血管的生成。
Endostatin作为内源性抗血管形成抑制因子,现今研究已较为透彻,其相关产品恩度在中国作为一线用药应用于临床。恩度[6](Endostatin)可以通过抑制肿瘤新生血管迁移等抑制血管新生,同时通过对肿瘤内皮细胞VEGF表达的调节等发挥多靶点抗血管生成的作用。恩度联合培美曲塞方案治疗NSCLC的研究[7]显示,联合化疗组(恩度+培美曲塞)与单纯化疗组(培美曲塞)的有效率分别为14.3%、10.0%,2组无显著性差异。2组临床安全性相当。但联合化疗组(恩度+培美曲塞)的疾病控制率57.1%,明显高于单纯化疗组(培美曲塞)控制率30%。恩度的联合使用增加了培美曲塞对晚期NSCLC的治疗的效果。
1.3 蛋白酶抑制剂
基质近视蛋白酶(MMPs)是现今研究较为透彻的肿瘤相关的蛋白酶,在其作用下可激活多种生长或抑制因子,进而对整个肿瘤环境造成影响。如MMPs可以降解肿瘤外基质细胞,释放一系列的促血管生成因子VEGF、TGF-β、bFGF等促进血管生成,同时也有一些血管抑制因子产生,从而双向调节肿瘤血管的新生。除此之外,MMPs还可以影响细胞的免疫反应[8]。
文献[6]中报道有两种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选择性 MMPIs-Prinomastat,广谱 MMPIs-BMS-275291。有研究[9-10]结果显示,这两种抑制剂与其他某些化疗药物联合给药治疗NSCLC,与单独使用某些化疗药物相比,联合使用蛋白酶抑制剂并没有使疗效增加,甚至毒性反应反而增强。恩度(Endostatin)还可以通过调节蛋白水解酶的活性而调节肿瘤血管的新生。
2 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EGFR家族是由4个结构相似的酪氨酸激酶受体组成,属于细胞表面跨膜蛋白,酪氨酸介导的信号传导。其家族成员分别为EGFR/c-ErbB1/EGFR1,c-ErbB2/HER2,c-ErbB3/HER3,c-ErbB4/HER4。在正常组织中,EGFR参与细胞的分裂分化等细胞活动,而在肿瘤组织中发生突变,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和预后等有紧密的联系[11]。有研究[12]表明,在NSCLC中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阳性表达率为53.1%~69.7%。而过高的EGFR表达导致NSCLC对常规的化疗药物(顺铂等)不敏感[13]。
2.1 小分子酪氨酸酶抑制剂
小分子酪氨酸酶抑制剂(TKI)是一些直接作用于EGFR受体,与ATP竞争性地结合EGFR特定结构域,抑制酪氨酸酶磷酸化,从而抑制下游信号传导,达到对肿瘤的抑制。代表药物有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埃罗替尼等。
吉非替尼是FDA批准最早用于口服的选择性EGFR酪氨酸酶抑制剂。Janne等[14]发现,肿瘤对吉非替尼的敏感性与EGFR的基因突变有紧密联系,这导致了吉非替尼对不同种族、不同性别的治疗差异。其优势人群为亚裔、腺癌及不吸烟的女性患者。吉非替尼可单用用来治疗晚期NSCLC的一线药物,疗效明显,但会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痤疮样皮疹、皮肤干燥等不良反应,尤其对虽罕见但却致命的间质性肺炎给予高度重视[15-16]。对于吉非替尼的原发耐药机制可能由于EGFR通路下游的信号分子K-ras突变引起,另一种机制可能与一种抑癌基因PTEN功能丧失有关[17]。对于吉非替尼激发性耐药机制有以下两种说法[16]:一种说法为在吉非替尼治疗过程中,EGFR基因会发生二次变异而导致耐药;另一种说法是原癌基因MET扩增引起的耐药。有文献[15]提示,吉非替尼和厄洛替尼之间不存在交叉耐药,提示可以用厄洛替尼治疗对吉非替尼耐药的NSCLC患者。
2.2 抗体
同TKI靶点类似机理的抗体,其机制是配体介导的细胞免疫毒性消灭肿瘤,包括单克隆抗体。单链Fv抗体、双特异性抗体等[18]。西妥昔单抗(Cetuximab)是人鼠镶嵌型的IgG1单克隆抗体,它是由人属IgG1重链轻链恒定区域及鼠属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抗体组成,可特异性作用于EGFR,阻断酪氨酸激酶活化及其介导的下游信号传导,从而对肿瘤的血管新生、肿瘤生长及转移进行调节,达到对肿瘤的治疗抑制作用。陈志伟等[19]对吉非替尼和西妥昔单抗联合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体外实验证实,二者均能够一直肺癌细胞的增长、迁移,且联合用药时相互间协同作用。提示临床吉非替尼和西妥昔单抗联合用药治疗肺癌的潜力。
3 EML4-ALK融合基因
间变淋巴激酶(ALK)是一种胰岛素样受体酪氨酸激酶。目前的研究[20]结果显示ALK参与形成的多种融合基因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密切相关。融合蛋白的形成可以激活关于细胞生长繁殖的细胞因子,有利于肿瘤细胞的生长繁殖。Soda等[21]在肺腺癌患者中首次发现了EML4-ALK的融合基因,虽然之后该融合基因在乳腺癌等也被发现,但仍以NSCLC中表达最高。初步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EML4-ALK融合基因在NSCLC中的阳性率约为3%~5%。
克唑替尼(crizotinib,商品名XALKORI)是FDA批准的首个作用于EML4-ALK融合基因的抗肿瘤药物,用特定检测方法诊断为ALK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的NSCLC。临床试验中,对于晚期的ALK阳性的NSCLC的客观缓解率为50%~61%。EML4-ALK融合基因作为区别于EGFR突变和K-RAS突变而发现的新靶点,抗肿瘤机理上相对独立,推测克唑替尼或许可以用来治疗EGFR突变和K-RAS突变患者耐药的NSCLC患者。克唑替尼初期临床得到了较好的疗效,耐受性好,进一步的临床研究工作正在进行。
与克唑替尼同时申报的EML4-ALK特异性荧光探针(Vysis ALK Break-Apart FISH探针试剂盒)同时获批,只有被此方法诊断为ALK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的NSCLC患者,应用克唑替尼方能达到其应有的疗效。这在证明了分子标记物在个体化给药的重要性,是个体化疗研发导向的重要里程碑。
4 小 结
传统的化疗药物毒性大,对肿瘤细胞的靶向性较弱,而分子靶向药物具有靶向性、安全性和耐用性等优势,对缓解癌症病人的病情、减少病人的痛苦尤为重要。没有一个肿瘤是完全相同的,基因的微小差异都会导致同一种NSCLC对不同分子靶向机理的抗肿瘤药的敏感性存在迥然差异。而判断肿瘤基因突变的类型或敏感靶点,缺乏对应的诊断方法,即个体化给药治疗肿瘤疾病仍存在着挑战。多靶点作用可避免因单一用药产生耐药性而使治疗失败,临床多用多种药物联合给药,如吉非替尼等分子靶向药物联合顺铂等传统药物联合给药,诸多临床试验在验证二者合用所产生的疗效及安全性。虽然分子靶向药物存在着难以诊断的问题,但其临床结果是令人鼓舞的。开发肿瘤新靶点、开发多靶点抗肿瘤药、确定基因突变类型的有效诊断方法以达到对肿瘤病人个体化给药,为抗肿瘤药开发的主导方向。
[1]Suchita Pakkala,Suresh S,Ramalingam.Combined inhibition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nd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signaling in 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 therapy[J].Clinical Lung Cancer,2009,10:17.
[2]Witz I P.Tumor-microenvironment interaction:dangerous liaisons[J].Adv Cancer Res,2008,100:203.
[3]Mcdonnell Co,Hill A D,Mcnamara D A,et al.Tumor micrometases:The influence of angiohenesis[J].Eur J Surg Oncol,2000,26(2):105.
[4]Swisher S G,Roth J A,Komaki R,et al.A phaseⅡtrial of adenoviral mediate p53 gene transfer in conjunction with radiation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localized 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J].Proc Am Soc Clin Oncol,2002,19:461.
[5]Willett C G,Boucher Y,Tomaso E,et al.Direct evidence that the VEGF-specificantibody bevacizumab has antivascular effect in human rectal cancer[J].Nat Mel,2004,10:145.
[6]薛聃,周彦斌.非小细胞肺癌分子靶向药物的研究进展[J].国际内科学杂志,2008,35(7):419.
[7]耿丽,王瑞.恩度联合培美曲塞方案二线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观察[J].医药论坛杂志,2011,32(12):63.
[8]Coussens L M,Fingleton B,Matrisian L M.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inhibitors and cancer:trials and tribulations[J].Science,2002,295(5564),2387.
[9]Bissett D,O'Byme K J,von Pawel J,et al.PhaseⅢ study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inhibitor prinomastat in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J].J Clin Oncol,2005,23(4):842.
[10]Leigh N B,Paz-Ares L,Douillard J Y,et al.Radnom ized phaseⅢstudy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inhibitor BMS-275291 in combination with paclitaxel and carboplatin in advanc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of Canadar-Clinical trials Group Study BR.18[J].J Clin oncol,2005,23(12):2831.
[11]FRYDW.Inhibition of the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family of tyrosine kinases as an approach to cancerchemotherapy:progression from reversible to irreversible inhibitors[J].Pharmacol ther,1999,82:207.
[12]王洋,梁岳培.抗VEGF和抗EGFR靶向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研究进展[J].临床医学工程,2011,18(2):312.
[13]Hirsch F R,Varella-Garcia,Bunn P A Jr,et al.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in non-small-cell lung carcinomas:correlation between gene copy number and protein expression and impact on prognosis[J].J Clin Oncol,2003,21(20):3798.
[14]Janne P A,Engelman J A,Johnson B E.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mutations in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implications for treatment and tumor biology[J].J Clin Oncol,2005,23:3227.
[15]卢宝安,张新伟,任秀宝.吉非替尼在非小细胞肺癌治疗中的研究进展[J].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2010,17(1):78.
[16]吴洪斌.吉非替尼不良反应的临床表现及其处理[J].药物不良反应杂志,2006,8(1):28.
[17]张婷,许海柱,卢俊彦,等.吉非替尼在非小细胞肺癌治疗中耐药机制的研究[J].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2013,20(2):189.
[18]YADEN Y,SLIW KOW SKIMX.Untangling the ErbB signaling network[J].Nat Rev Mol Cell Biol,2001,2(2):127.
[19]陈志伟,虞永峰,李子明,等.吉非替尼和西妥昔单抗联合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体外实验研究[J].中国癌症杂志,2010,20(4):275.
[20]Kelleher F C,McDermott R.The emerging pathogenic and therapeutic importance of the 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 gene[J].Eur J Cancer,2010,46(13):2357.
[21]Soda M,Takada S,Takeuchi K,et al.A mouse model for EM L4-ALK-positive lung cancer[J].Proc Natl Acad Sci USA,2008,105(50):19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