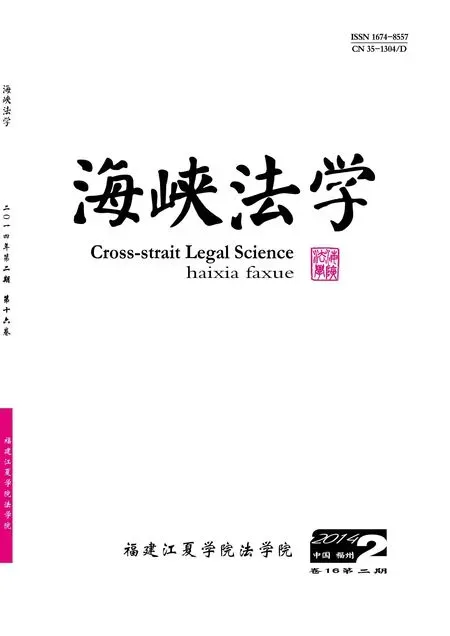我国刑法立法根据的反思
葛奕君 ,马荣春
我国刑法立法根据的反思
葛奕君 ,马荣春
我国刑法立法的特色可以简单概括为四个方面,即注重政治依据、注重实践经验、注重法律根据和注重吸收国际刑事立法经验。采取这种立法思维,利弊兼具。因此,对其进行深刻反思有助于明晰我国未来刑法立法之完善方向,从而促进刑事法治的进一步发展。
刑法立法;政治根据;实践经验;国际公约;立法科学性;权利保障
引 言
我国79刑法典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宪法为根据,依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结合我国各族人民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而我国97刑法典第1条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这两个条文都是对我国刑法立法根据的表述。刑法的立法根据是制定刑法的基础,其在根本上反映了刑法的价值取向,也是衡量刑法立法科学性及其程度的尺度。然而,刑法理论界对刑法的立法根据问题关注远远不够。学者们忙于挑剔刑法个别条文的瑕疵,对于刑法立法根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问题则欠缺思考。而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刑法条文的瑕疵源于其立法根据的缺陷。因此,着实有必要反思一下我国刑法的立法根据问题,这是刑法本身进一步完善的需要,更是刑事法治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一、我国刑法立法政治根据的反思
现代国家的存在需要四个要素即人口、领土、政权和主权。其中,政权和主权合称为“权力”,“权力”是维持一个国家运行的工具,没有“权力”将导致“国将不国”。虽然法律包括刑法越来越是“权利意志”的体现,但法律特别是刑法同时也是“权力意志”的体现,故刑法立法不可能缺少一种政治性根据或“因子”。只不过,刑法立法的政治性根据或“因子”必须被掌握在一定限度内,否则会导致“权力意志”完全取代“权利意志”,从而导致“权力刑法”代替“权利刑法”,以致于刑法蜕变为“洪水猛兽”。
我国刑法立法的政治根据,是指我国刑法立法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考量,其对我国刑法立法也具有着根本性的宏观指导意义。众所周知,79刑法第1条之所以确立政治思想的指导地位,除了受制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之外,还与人们的“政法意识”以及整个司法机制的架构有关,如我们早期的法律院校均是以“政法学院”命名;再如作为公检法“上司”的政法委,在功能上不仅强调协调三家的分工,更重要的是承担着政治导向的任务。
尽管以政治思想作为刑法立法的指南,可以实现刑法对政权的稳固功能,但其流弊也是非常明显:其一,政治思想导致刑法在品格上偏向于“政治刑法”或“国权刑法”,正如学者指出:“国权刑法理论由于其国家的本位立场,总是道义地或政治地把一部分公民(尤其是严重的犯罪人)放在国家权力对象的一面。也就是说,无论以何种理论形式,国权刑法是以‘假设敌’为出发点的。”①李海东著:《刑法入门原理(犯罪论基础)》,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换言之,在“国权刑法”之下,刑事诉讼的结构是单向性的,即由代表国家的控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形成“合力”,直接针对犯罪人采取纯粹暴力性的、压制性的制裁。笔者以为,在这种控罪模式中,其实是不存在真正的或平等的刑事法律关系。之所以要设立诸如刑法、刑诉法、行政法等公法,其根源在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力量是天然地不平等的。相对于势单力薄的个人而言,国家拥有着庞大的国家机器和物质基础作为后盾,故其在物理力上绝对优胜于个人。因此,需要设立刑事诉讼法等程序性法律来加以矫正他们之间的这种力量上的不平等。由此,不难看出,刑事控权应当是刑法裁判机能的首要旨趣;其二,政治思想导致国家在控制犯罪中的策略失当,其突出体现便是“严打”。而“作为中国刑事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对严重刑事犯罪的‘严打’政策,则是基于刑事犯罪日益猖獗的具体国情的战略选择,其目的是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控制犯罪。”②许道敏著:《民权刑法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从“严打”的基本要求即“从重从快”来看,“严打”是重刑主义思潮下的司法策略。尽管在特定时期内,“严打”能够有效遏制一些犯罪,但就建国以来的历次“严打”来看,其效果并不乐观。诸如黑社会性质犯罪、腐败犯罪等严重的刑事犯罪并未得到根本的治理。相反,以运动的方式来突击犯罪,使司法实践突破了刑法的边际,也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刑法。而从“严打”的实际操作模式来看,其主要是通过政党红头文件的形式来部署。因此,这种依靠政治力量发动控罪的策略,是典型的“革命思维”,属于非常态化的治理措施。当然(虽然)97刑法修订时,已经取消了79刑法明显的政治火药味,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注重政治根据的思维已经得到根本或彻底改观。尤其是在司法领域中,这种思维还有很大的市场;其三,政治思想割裂了刑法的继承性。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废除国民党时期的《六法全书》,这便使得刑事立法陷入长期的停滞状态。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主要依靠变动性极强的政策来对付犯罪,可谓是中国刑事立法中的一大特色。当97刑法修订后,学者们在为我国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而欢呼时,却并没有太多的人关注到早在1929年即民国17年由国民政府颁行的《中华民国刑法》第1条就开宗明义地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即“行为时之法律无明文科以刑罚者,其行为不为罪”。③郭卫著:《六法全书》,上海法学编译社1928年版,第353页。由此可见,对政治立场的过分强调严重地阻滞了中国刑法立法的发展进程。
我们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出,对犯罪的“惩罚”和对“人民”的保护仍然呈现着我国现行刑法的“国权刑法”或“政治刑法”之色彩,但“权力刑法”向“权利刑法”的嬗变应是刑事法治发展的不可阻挡的“大势”。
二、我国刑法立法实践根据的反思
注重实践经验是“国情观念”的一种典型体现,而注重实践经验是我国刑法立法的又一个明显的特征。如当时主持79刑法起草工作的彭真同志就反复强调:“法律的制定只能随着实践经验的成熟逐步走向完备,不能匆忙,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主观地片面地贪多求全,并且要防止过于繁琐,以致难以通行,也难于为干部、群众熟悉、掌握。”①《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7~476页。此外,从97刑法的修订来看,许多先前实行的有关刑事方面的规范性文件,都被吸收到刑法典中。正如有学者指出:“经过修订以后,基本实现了中国刑法的统一性和完备性。这就是说1979年刑法典实施17年以来,凡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有关刑法的修改补充(有的叫决定,有的叫补充规定,有的叫条例,统称单行刑法),经过研究、修改、整合以后都纳入到了这部刑法典。”②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上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毫无疑问,以实践为基础制定刑法易于刑法的贯彻实施,但却可能由于生活实践的错综复杂性和快速变动性而极易致使刑事立法变动不居,从而有伤刑法的稳定性。况且,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刑法规范并不能穷尽生活中的所有“琐细”,正如学者指出:“认为刑法典可以毫无遗漏,是荒唐的幻想;希望刑法典做到毫无遗漏,是苛刻的要求。承认刑法典必然有遗漏,才是明智的观点。法律有时入睡,但决不死亡(Dormiunt aliquando legs,numquam moriuntur)的格言,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表述了法律必然有漏洞的观点。”③张明楷著:《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那么,既要维护刑法的稳定性,又要保证刑法适用不偏离实践,便显得迫切而重要。而实现规范与事实相互吻合的有效方法莫过于刑法的解释,正如学者指出:“有的国家刑法制定了近百年。近百年来,无数的学者、法官、检察官、律师都在解释刑法;而且,只要该刑法没有废止,还将继续解释下去。”④张明楷著:《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当然,由于解释者选取的解释方法、解释立场不同而可能会使刑法规范出现纷繁的含义。因此,在刑法解释中,应当规定解释的一些基本底线,如对文字的解释不能违反国民对刑法规范的可预测性,并且应当考虑文字的生活含义等等,并且在解释中要锁定或坚守刑法解释的价值定位,正如学者指出:“刑法规范解释的价值定位一般而言,存在社会保护优先和个人保障(权利保障)优先的两种模式”,但“刑法客观主义的立场应当是我们的首选,而刑法的客观性、确定性、可预测性等,则必须在刑法解释中予以贯彻。”⑤周光权著:《法治视野中的刑法客观主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209页。通过严格的刑法解释,在促成刑法规范与生活事实相互一致的同时也保证了刑法的稳定性。因此,基于刑事法治理念,我国刑法立法在谨慎立法之时,应当注重发挥刑法解释的功能。
但是,完全依赖实践经验的刑法立法会导致刑法解释假借“扩张解释”之名而行“类推解释”之实。因此,面对着纷繁复杂的犯罪现象,一方面,刑法立法宜采用“适度超前的立法”,正如现行刑法对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和走私核材料罪的规定,因为刑法的“适度超前的立法”意味着刑法立法既要有着现实的社会生活基础即行为类型化基础,又要有着必须依靠刑罚干预所反映的刑事必要性,故其符合并体现着刑法立法的“求真务实”⑥马荣春、王超强:《论犯罪化与非犯罪化》,载《犯罪研究》2012年第6期,第22页。;另一方面,刑法立法宜在类型化思维下采用“概括式立法技术”,因为概括性强的刑法立法往往能够达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刑法的“适度超前的立法”,还是刑法立法采用“概括式立法技术”,最终要符合作为“刑法帝王原则”的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注重实践经验与强调“国情”密切关联,而强调“国情”常常被批评为“政府不作为”,但实际上,注重实践经验即强调“国情”是在“有所不为”之中而“有所为”。然而,注重实践经验即强调“国情”不能完全无视法治包括刑法立法的一定范围或程度内的“全球化”。如就强奸罪而言,目前我国强奸罪的加害对象只能是妇女,但现实中出现的情况已经说明男性也可能成为性侵害的对象,并且这一现象正呈现增长之势,英国则已经将男性纳入强奸罪的对象,体现着一种越来越普遍化的立法趋势。在这样的立法趋势中,中国关于强奸罪的刑事立法当然不能无动于衷。
三、我国刑法立法宪法根据的反思
无论是79刑法,还是97刑法,都明确规定了宪法是刑法制定的法律根据。这固然肯定了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对部门法的统领地位,但宪法对刑法的有效制约机制并没有在我国形成。因此,我国刑法中的“以宪法为根据”只具有标识意义,而没有体现宪法对刑法的真实制约。相反,在刑法条文中,不乏与宪法抵触的规定。如根据我国刑法第54条之规定,剥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是剥夺政治权利内容之一。但“宪法规定可以剥夺或限制选举权、被选举权、人身自由权、通信自由及通信秘密权,其他所有权利自由,宪法并未许可可以依法剥夺或限制。国外刑法中的资格刑也不包含对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剥夺。”①胡云腾主编:《刑法条文案例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因此,在未经宪法授权的情况下,刑法作出上述规定有“违宪”之嫌。此外,尽管《立法法》授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撤销权,但在面对相互冲突的法律规定,尤其是司法解释之间的相互抵牾,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迄今为止并未主动行使法案的撤销权。这便在无形之中使得宪法在部门法中的法律依据“被虚化”或“被虚置”。
在宪法领域内,诸如“孙志刚事件”等个案能以独特的方式来唤醒宪法对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制约。这表明“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只依赖某一个制度,而需要的是一套相互制约和补充的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包括成文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包括了社会中不断形成、发展、变化的惯例、习惯、道德和风俗这样一些非正式制度。”②苏力著:《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增订版,第55页。因此,要发挥宪法对刑法的制约功能,除了要倡导宏大叙事的违宪审查制度外,更多的是需要以个案等实务的方式予以“兑现”。易言之,通过法官的技术性知识,来有效回避冲突法律的适用,进而在另一层面上来实现宪法对部门法的掣肘功能,或许更为务实。当然,这不仅需要法官有丰富的技巧,更需要的是政治胆识。
可以肯定的是,刑法立法的最大合法性只能是来自宪法,或曰刑法立法的最大合法性即其“合宪性”。
四、我国刑法立法国际根据的反思
经济的全球化在加强世界各国往来的同时,也使得各国之间的法律冲突日益频繁。与此同时,各国在众多领域都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而迫切需要开展法律合作,其中包括立法上的相互吸收与借鉴。特别是晚近以来,恐怖主义犯罪、毒品犯罪、贪贿型犯罪等日益成为危害社会的严重犯罪。因此,我国在刑法立法中需要及时地吸收世界各国、地区以及国际社会上的相关立法经验。实际上,我国历来就重视加强与国际社会的立法合作。早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大会上,董必武就代表中国政府承认了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宗旨。中国对1945年6月26日签订的《联合国宪章》和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都投了赞同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不仅明确承认了联合国大会关于禁止和制裁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决议,而且为此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包括根据该决议的精神作出对在华日本战犯的审判。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批准参加的国际公约更为繁多,先后批准或加入了《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道的待遇或处罚公约》、《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国际公约》、《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等。③参见张智辉著:《国际刑法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392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2005年批准参加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在此后的《刑法修正案(七)》中吸收了公约的相关规定,其代表性的做法就是关于受贿罪的立法修改。修正后的受贿罪在行为主体、行为方式等方面都较之我国刑法原来的受贿罪规定更为完善,这显然是公约影响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国刑法立法在借鉴国际社会方面取得初步的成就,但仍然有许多制度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完善。典型的如我国的死刑制度,虽然我国已经确立了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基本政策,但在刑法上规定死刑的罪名仍然居高不下。尤其是针对财产犯罪等非暴力犯罪适用死刑,既不经济,又无必要。因为此类犯罪完全可以通过财产刑等刑罚措施加以遏制,其社会危害性远远逊色于暴力犯罪。因此,学界普遍呼吁应当以废除非暴力犯罪死刑为切入点来逐步限制死刑。正如有学者不无理性地提出:“中国刑法应该将死刑的适用限于所侵犯的权益的价值不低于人的生命的价值的犯罪范围内。具体地说,中国现行刑法中的死刑罪名应该缩减到只限于有致死的结果的暴力犯罪、具有直接导致国家分裂或颠覆现政权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导致战役失败的严重军事犯罪的范围之内。除此之外的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死刑都应予废除。”①邱兴隆著:《刑罚的哲理与法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99~500页。这既符合国际社会的立法趋势,也是我国应承担的相关国际公约的职责所在。
总之,我国刑法立法的发展应顺应国际社会发展的“大势”而不应游离于国际社会发展的“大潮”之外,而这里所说的“大势”和“大潮”是指人权发展的“大势”和“大潮”。
结 语
我国刑法立法的根据问题最终可以归结为刑法立法的人权性即民主性和科学性问题,而其人权性即民主性和科学性又是相互说明的。79年刑法的诞生处于文革刚结束的大背景下,中国仍然处于重政治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氛围之中,故法律,特别是刑法,基本上是纯粹服务于政治的工具。政治型刑法所反映的刑法立法重视政治功能的价值观,立于人权保障和立法科学性而言,无疑是存在偏颇的。立于人权保障,民是国之本,立法的目的应当是服务于民众和保障人权,即国家设立刑法最重要的是保障人权而非维护政权。立于立法科学性,如果刑法立法根据中政治性因素偏多,那么刑法立法的任意性就会增大,而政治任意性就会增强,则刑法立法的规律性便会减弱,从而刑法立法自身的科学性便相应减弱。可以肯定的是,97年刑法在价值取向上所体现出的在人权保障和立法科学性方面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立于科学性,97年刑法强调经验和实际情况而非政治,有利于科学地进行刑法典的体系构建,但其科学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仍有待增强;而立于人权保障,“保护人民”因“人民”概念的政治性而无法逻辑地将“罪犯”纳入保护的范围,从而显示出人权保障的局限性。总之,既要肯定新中国刑法立法在立法根据上所体现出来的进步,更要看到其仍然存在的不足,而这是由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刑事法治的要求所决定的。
(责任编辑:林贵文)
D924
A
1674-8557(2014)02-0057-05
2014-03-18
葛奕君(1993-),女,江苏东海人,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学生。马荣春(1968-),男,江苏东海人,法学博士后,扬州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