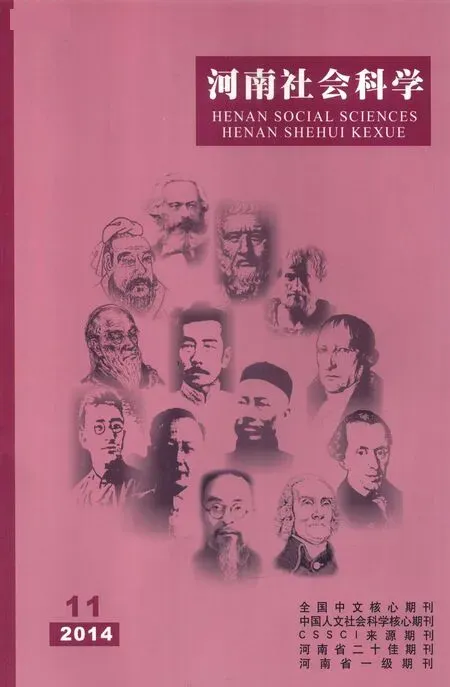美国大陪审团功能问题再思索
潘 侠
(中国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一、大陪审团概述
(一)大陪审团功能演变
大陪审团制度发轫于英国,由国王亨利二世在1166年颁布的克拉灵顿敕令中确立下来。敕令规定,每个郡挑选出12人专门负责向政府报告公民触犯刑律的事件并直接听命于国王。这12 人经过宣誓,对本辖区内发生的抢劫、谋杀、盗窃等案件依据自有知识和能力进行判断①,他们并不需要冗繁的证据审查,也无需认真甄别追诉理由是否充分,其主要任务是给出某人是否有刑事犯罪的报告。当时的大陪审团更多充当着国王的御用政治工具。敕令规定,在大陪审团对公民提起诉讼时,只有王座法院享有管辖权。国王通过限制法院审理案件的方式与教会法庭及封建贵族作斗争,加强王权②。
1215年英国大宪章则明确赋予公民享有由大陪审团进行起诉的权利,即在没有大陪审团起诉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以叛国罪以及其他死罪对公民个人提出指控。大宪章是在中央高度集权,英王约翰肆意践踏封建法制,遭到贵族武力胁迫下所签署的法律文件。整个宪章彰显着限制王权、崇尚法律及保护公民权利的可贵精神。然而令大陪审团收获“防止公民免受任意指控的保护伞”的美誉则源于1681年伦敦两个大陪审团先后抵制国王查理二世的要求,拒绝对Shaftesbury 伯爵及属下Stephen Colledge提出指控事件③。虽然案件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但人们看到了大陪审团所具有的保护无辜民众免受政府滥用控诉权迫害的不争价值所在。此时的大陪审团被视为近代意义上的大陪审团起源。但随着大陪审团运作日渐显现的冗长拖沓、华而不实、开销庞大等弊病,其愈发遭到英国国内学者的诸多质疑。自功利法学派代表人物边沁对其发起猛烈抨击始,大陪审团的去留就一直是英国国内讨论的热门话题。大陪审团在几个世纪的进程中苟延残喘,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辉,英国最终于1948年正式废除大陪审团制度而代之以检察官制度。
然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大陪审团发展却呈现另一片态势。1635年北美第一个大陪审团首先在英属马赛诸塞殖民地建立并迅速在其他殖民地普及开来。促使大陪审团威名远扬的著名案例是1734年John Peter Zenger 被诉案④。该案中政府僭越大陪审团对案件进行处理的行为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广泛不满,人们深刻意识到发挥大陪审团在刑事司法中作用的重要性。受此案鼓舞,1765年出现了波士顿大陪审团拒绝起诉为反对臭名昭著的印花税法案而进行暴动的殖民地人民。此后,一件又一件关于大陪审团拒绝当地不合理殖民法律的事件不断出现。由于殖民地大陪审团的据理力争,致使英当局不少苛刻法案在北美沦为泡影。大陪审团作为反对殖民压迫的有力武器,逐渐在殖民地人民心中树起了显赫声望。鉴于大陪审团在美国独立战争前所发挥的不可磨灭的作用,建国后,诸多州代表提议在宪法中规定大陪审团制度,继续承担其防止任意追诉、对抗政府压迫的职能。1789年6月8日,詹姆斯·麦迪逊向第一国会提交了在宪法中规定大陪审团条款的法案,其建议经过修改获得参、众两院通过,大陪审团制度最终于1791年12月15日的宪法第五修正案中确定下来⑤。
(二)大陪审团在美国的适用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明文规定:非经大陪审团提出报告或起诉,任何人不受死罪或其他不名誉罪的惩罚。具体而言,大陪审团制度在美国的适用如下:
1.适用范围: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的大陪审团制度仅在联邦司法范围内适用,对各州适用与否并不加以干涉⑥。在对待大陪审团制度的态度上,各州做法有别:一、明确允许立法机关废除或修改大陪审团程序;二、赋予法院废除大陪审团控诉职能的权力;三、保留大陪审团或者效仿联邦的做法,规定某些罪行必须由大陪审团提出控诉。到目前为止,除联邦外,美国共有18个州明文规定了重罪案件被告人非经大陪审团起诉不出庭受审的权利。另有4个州规定,部分严重犯罪必须由大陪审团起诉⑦。
2.案件种类:案件是否适宜大陪审团起诉,其决定性因素并非在于犯罪的性质,而是根据犯罪所可能被判处的刑罚。宪法第五修正案把大陪审团负责起诉的案件限定于“死罪”及“不名誉罪”。前者是指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惩罚的犯罪行为;而“不名誉罪”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则指可能被判处一年以上徒刑或强迫劳役的监禁刑。最高法院特别强调,哪些犯罪应归为“不名誉罪”是社会价值观的反映,因此,“不名誉罪”的范畴也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调整。
3.适用程序:无论联邦还是州,大陪审团的运作机制大致相同。首先,召集大陪审团。在公共利益需要时,法院应召集大陪审团。大陪审团由16至23人组成,其中必须由至少16人参加大陪审团会议才能开展。其次,审查证据。检察官首先向陪审团说明其指控的内容,并建议需要传唤的证人,大陪审团根据案件需要可传唤其他证人。大陪审团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听取证人证言来判断证据是否足以提出指控。证人将被依次传唤。通常情况下,由检察官首先询问证人,接着是陪审团团长询问,其他陪审团成员如有合适问题也可以接着提问。“如果证人拒绝回答,应由记录员记录在案,征求法院的意见,以决定是否强制证人做出回答。”⑧再次,做出裁决。在听取检察官陈词及证人证言后,陪审团团长组织各位陪审员发表对案件的看法,经过集体讨论后投票表决,只有在12 名以上陪审员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做出支持起诉决定。
二、大陪审团的功能及其角色定位
(一)大陪审团的尴尬处境
在对抗制程序中,联邦大陪审团处在一个难以言明的中间地带,介于控诉主体与司法主体之间。不像小陪审团,后者的功能不偏不倚、消极地行使事实法官的职能,而大陪审团审查刑事控诉的角色却很难界定。询问证人、收集发现犯罪信息本身是积极行使控诉职能的一种体现,然而大陪审团中立地审查证据以决定起诉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支撑的行为又可被视作发挥司法官超然公正的裁判职能。承担的职能不同,服务于职能所遵循的规则自然也有别。
虽然各法院都不否认大陪审团行使的重要职能,但对其职能的认识却仍处在一种朦胧、肤浅层面上。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在于最高法院从未选择从单一视角来阐释大陪审团所承担的宪法职能,而是重复着历史上的定位,即大陪审团担负着双重职能——控诉机关,纠察刑事犯罪;公民权利的保护机关,防止刑事诉讼过分干预公民生活。且最高法院也从未着手融合与两项职能相伴生的规则于单一的主体之中,而是选择在不同的情境下分别界定大陪审团角色,或行使司法职能成为司法主体,或行使控诉职能成为控诉主体。这种杂糅模式引发了相互矛盾的做法。如,最高法院允许剥夺被告人司法听证的权利,理由是大陪审团审查起诉就相当于司法审查。但与此同时,最高法院又声称大陪审团起诉具有控诉性质而非司法性质。大陪审团徘徊在不同的职能之间,不明朗的角色定位使其职能行使带给人们不少困惑。
(二)大陪审团角色定位的争论
1.司法主体模式。将大陪审团角色定位为司法主体,其重要支撑是大陪审团与治安法官承担的职能相似。大陪审团通过审查起诉,确保检察官提交的案件有足够证据支持,从而保证将嫌疑人诉诸审判具备正当性;拥有司法审查权的治安法官也依法对检方预起诉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案件是否符合起诉条件,应否交付审判。具体而言:首先,在司法主体模式下,大陪审团的角色所需就是进行司法审查,而非纯粹地给出法律执行意见。其次,大陪审团起诉书也不再仅仅是刑事控告,而是作为司法意见对待。既然大陪审团是与治安法官作用相当的司法主体,那么二者功能相重合,会不会导致程序的冗繁和资源的浪费?这是司法主体模式论必然带来的困惑。综观美国的审查起诉制度,存在四种模式:大陪审团审查模式;预审听证模式;预审听证和大陪审团审查相结合模式;预审听证和大陪审团审查择其一模式⑨。为解决这一难题,在两种模式并存时,赋予检察官提起公诉时的程序选择权。
2.控诉主体模式。一方面承认大陪审团行使职责具有司法性质,一方面在设置大陪审团程序过程中最高法院又同时引入不少控诉模式下该有的规则,体现如下:首先,最高法院将大陪审团审查起诉置于整个检察权体系中,认为大陪审团起诉书是其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结果,而不单单是司法认定。在大陪审团给出最后意见时,它并非局限于审查案件是否达到“合理根据”标准,仍需考虑其他方面。另外,大陪审团起诉不受必须使其支持控诉的案件获得法庭有罪认定的限制。在此意义上,最高法院认为大陪审团起诉书是多方面因素综合衡量的产物,而并非对证明标准的简单适用。它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并非完全消极。其次,大陪审团在审查证据时,即使存在“合理根据”,其也有权拒绝指控。在控诉模式下,大陪审团如检察官一样,享有起诉与否的正当权力。此外,大陪审团起诉并不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束缚,它不仅能根据自己的认识做出判断,还可以使用传闻证据,甚至可以关注新闻媒体的报道。检察官无需向其提供对嫌疑人有利的证据。所有这些皆因为其对起诉审查的目的并非要做出有罪与否的判定,而仅是为控诉把关,其职责履行具有控诉性质而非司法性质。
3.模式争论引发的问题。检察官在大陪审团面前享有绝对的豁免权,不能对其行为提起诉讼;嫌疑人不允许在大陪审团面前为自己辩护,不允许律师在场,却允许检察官为控方陈词,允许其提交以非常手段获取的嫌疑人有罪证据,缘由是大陪审团程序不具对抗性,此时强调其控诉职能。然而,另一方面,又要求大陪审团不偏不倚,在公民和检察官之间扮演保护盾角色,防止嫌疑人受到大陪审团和检察官的双重追诉,保持居中裁判。在大陪审团程序与预审听证择一模式中,嫌疑人无权再启动预审听证程序,强调大陪审团起诉书的司法裁决性质。大陪审团因服务目的有差异而被施以不同的对待,左右逢源的制度设计使得大陪审团角色多棱,难以捉摸。这种无法阐明的现象甚至迫使实践产生了跳出对抗制程序的理解,把大陪审团视为纠问机关⑩。然而这种认识已经完全背离了美国对抗制的司法体系。相较而言,大陪审团并不承担平等对待控辩双方的任务,其职责并非在于比较双方证据,从而查明事实真相,而是协助检察官把关案件,方便庭审。因此,更准确地说,大陪审团采取的以控诉为目的的审查程序与其说是纠问程序,毋宁说是对抗式庭审的准备程序。宪法第五修正案对联邦大陪审团的角色着墨不多,实践中只能通过一个个判例来不断修正大陪审团具体职能的履行及相关规则。然而,最高法院在大陪审团履行职能的性质认定上所采用的混合模式让大陪审团程序显得扑朔迷离⑪。
(三)角色定位:与职业司法分庭的民间力量
事实上,从组织隶属上看,如何安置大陪审团以使其与三权分立的国家结构相融合,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令美国政客头疼的话题⑫。有的视大陪审团为司法系统的一部分,有的视它为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受到检察官的控制。但在笔者看来,大陪审团角色定位为审查起诉阶段与职业司法分庭的独立民间力量为佳。在刑事起诉程序中注入民主的因素,以民间团体的身份对检察权形成制约,既非司法主体,亦非控诉主体,只是社会民主声音的一种表达。通过对预起诉案件进行证据审查,在确保起诉质量的同时,防止公民受到不当指控,发挥其利剑和盾牌作用。将大陪审团定位为独立的机构在最高法院的判例中也可以找到支撑⑬。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大陪审团扮演的角色,那么许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如在大陪审团与治安法官各自的职能问题上,二者其实并无重复之处。大陪审团通过普通民众的认知来制衡政府的行为;而预审程序则通过中立无偏的法官来评估控方证据的充分性。他们分别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保障指控的有效性。
三、独立性问题与大陪审团功能的发挥
(一)与国会的关系
历史上,大陪审团是普通法的产物。然而,作为立法机关的国会与大陪审团的渊源也由来已久。在19世纪,国会就已开始负担起规制大陪审团程序的任务,如,大陪审团的选举、任期,大陪审团会议的安排等。随后其规制的范围进一步拓展⑭。
《联邦刑事诉讼规则》中有关大陪审团程序的条文也是在国会的推动下得以被最高法院认可。从现行立法来看,法律已经改变了不少普通法时代有关大陪审团的一些规定。如,《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取消了大陪审团独立提出起诉报告书的规定,即大陪审团只能对检察官提交的案件进行证据审查,无权根据自身判断对发现的犯罪进行指控⑮。此外,大陪审团调查程序的秘密性原则近年也是国会立法改动的焦点。2001年国会通过的《爱国者法案》规定,检察官可以披露大陪审团证据审查中获悉的其他国家或情报机构进行的与美国联邦、州外交事务等有关的信息而不需要事先获得法院批准⑯。2004年制定的《情报改革和预防恐怖主义法》进一步规定,向有关机关公开大陪审团掌握的有关恐怖活动方面的信息不需要请示法院。国会通过的这些法案对大陪审团秘密审查原则形成了很大冲击。国会能在多大范围内对大陪审团进行规制不甚明了,到目前为止,国会还未曾挑战过大陪审团的其他基本特性。“宪法第五修正案只保留了普通法对大陪审团享有的实质性权力,即审查起诉的规定。”⑰一个不成文的共识是,只要保留此权力,国会便可对其他程序性问题适时做出修改。
(二)与法院的关系
大陪审团由当地法院负责召集,法院为大陪审团会议安排专门的场所。召集程序完成后,法院负责对陪审团成员进行任职前指导,法官宣读与大陪审团程序有关的法律条文,帮助陪审员了解职责,陪审团成员宣誓服从。根据《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的要求,在检察官及代表已在地区法院接受询问的被告人的律师以大陪审团未依法选任、抽签或召集为由,对陪审员名单提出异议时,法院有权决定是否更换陪审员。即使大陪审团起诉书已做出,辩方也可以陪审员名单或个别陪审员缺乏法定资格为由提出异议请求法院撤销该起诉书⑱。大陪审团对犯罪行为进行调查时使用的主要工具是传票,但大陪审团本身没有签发传票的权力。在传唤证人作证时,它需事先取得法院签发的传审令。对于在其面前作证的证人,证人保持沉默时不能直接被施以惩戒,除非得到法院的同意才可以强制证人作证⑲。另外,大陪审团不能挑战被告人的不能强迫自证其罪特权,也不能依据传票对证人及被告人住处等进行搜查、扣押相关文件等。
诚然,独立进行证据听审,独立地做出起诉与否的意见是法律规定大陪审团程序的应有之义,但是这种独立性却并不意味着大陪审团的完全自由、随心所欲。一旦大陪审团逾越了其法定职权的行使范围,法院将是受害主体寻求救济的正当途径。从以上分析来看,与其说法院对大陪审团职权行使的独立性产生着影响,不如说前者在为大陪审团独立行使职权提供程序保障与配合的同时,对其职权的不当行使又进行一定的制衡。这种恩威并施的制度设计,正是大陪审团独立且正当行使职权的重要保证。
(三)与检察院的关系
在与大陪审团关系密切的几个主体中,属大陪审团与检察官的关系受到非议最多。大陪审团设立的初衷是防止检察权滥用对公民权利造成威胁。然而,大陪审团对检察起诉发挥的制衡作用却遭到了质疑,质疑的原因有三:其一,由未经受法律训练的普通民众组成的大陪审团,组织本身羸弱;其二,大陪审团往往对案件了解得不透彻,在传唤证人问题上常常无所适从;其三,陪审员对刑事法律不甚熟悉,在适用法律规则上把握不够。不少论述在谈到大陪审团多大程度上对检察起诉形成影响时,一个常用的衡量指标是对于检察官提交起诉的案件大陪审团拒绝提交起诉书的概率有多大。据统计,在2007年度,大陪审团拒绝起诉的案件不超过24 例,同意起诉的超过63000 次,检察官获得大陪审团支持起诉成功率超过99.9%⑳。这些数字近乎说明了检察官在通过大陪审团审查关时的畅通无阻。高起诉率往往是学者抨击大陪审团形同虚设的靶子。然而另有一些学者认为数据的统计能说明一些问题,但其并不能充分反映事实的全貌。在大陪审团程序中,只要有“合理依据”认为嫌疑人从事了犯罪行为,就可以提交起诉书,该诉讼阶段的证明标准门槛极低,轻易便能达到,而且在证据审查时,控辩双方都不能提交有利于嫌疑人的证据,起诉书的做出又不需要全体陪审团成员一致表决通过,这就更增大了起诉的概率;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因大陪审团审查程序的存在,检察官清楚如果拟指控的案件没有合理的起诉事由必将遭到陪审团成员的反对,所以检察官在案件的筛选上已经事先进行过把关,由此大陪审团做出起诉决定也在情理之中,把高起诉率和大陪审团独立性丧失完全画等号似乎并不公允。
出现上文有关大陪审团独立性问题的质疑与争论,与大陪审团程序中检察官所承担的双重角色有莫大关联。检察官一方面是陪审员的法律顾问,一方面代表政府提出指控,是政府方的辩护人。作为前者,检察官既为大陪审团阐释证据调查中相关的程序及法律适用,同时在证据调查完毕大陪审团商议做决定前对实体法的适用进行指导;作为后者,检察官需提交控方证据,必要时对提交的案件及证据进行说明。“在充当法律顾问时,陪审团需审查哪些证据、传唤哪些证人都需检察官进行指导,所以这就不免会让人产生其有借法律指导之身份引导陪审团接触那些检察官想要陪审团知道的有利于获得大陪审团起诉书的信息之嫌。”㉑
事实上,在如何避免这一问题上司法实践中已有成熟的范例可资借鉴。在夏威夷州及军队适用大陪审团审理的案件中,设有专门的法律顾问为陪审团成员提供帮助。法律顾问的任期及薪酬都由当地及军事法律明确规定。专门法律顾问的职责在于对大陪审团提出的疑问如实进行回答,不偏不倚。然而,聘请专门的陪审法律顾问目前仍未成为联邦及州的通行做法。联邦系统给出的理由是大陪审团需获得法律帮助的事项极其有限,不存在足以设置专门陪审法律顾问的正当性。加之与陪审团成员接触频繁后,法律顾问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也会产生偏见㉒。
各方在检察官与大陪审团欲理还乱的关系中,各执一词,相持不下。到目前为止,在二者关系问题上立法并未出现大的改动。但在笔者看来,大陪审团引入的初衷是实现审查起诉阶段的民主,反映民意的声音。要想充分发挥民众的作用,防止程序虚置,专门法律顾问确是应时之需。实践中已有成熟做法,真正发挥大陪审团在起诉阶段的功能,保证其有能力独立行使职权至关重要。
四、大陪审团功能发挥的持续动力
(一)根深蒂固的司法传统
殖民时期,北美大陪审团就在对抗英国当局殖民压迫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殖民地人民心中留下了良好印象;在美国争取独立的运动中,大陪审团多次抵制了王权对公民权的侵犯;建国后,亲历王权压迫的建国者们深知专制独裁的恐怖,毅然在人权法案中保留了大陪审团制度。本着破除独裁、提倡民主的理念,美国采取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强调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既配合又制约,同时都要代表民意。作为正义最后堡垒的司法权尤其受到关注。为防止正义堡垒操控在一群职业司法人员手中,引入普通民众参与司法,发挥人民的监督作用,这是让美国人民心安的一项举措。
据研究显示,在刑事司法领域,公民判断程序公正与否的因素主要有四个:一是公民对程序的参与度,即使他的参与并不能左右程序的最终结果;二是决定做出者能否保持中立无偏;三是决定做出者是否可信;四是在程序进行中,公民能否受到有尊严的对待。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程序在公民眼中就是公正的㉒3。大陪审团来自于社区的民众,对社区其他成员间的违法行为进行审查,比起精英化、职业化的法官、检察官做出的裁决更容易让调查对象信服。另外,陪审团成员的遴选程序也是尽可能的公平,每个地区分成不同的区域,从每个区域中按比例选出一定的人数组成陪审团成员库。针对个案,从成员库中随机挑选陪审员。这种公平的选择程序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了所代表成员的广泛性,更增加了程序的公正性。
(二)张弛有度的审查环境
不像小陪审团,大陪审团成员工作中,没有法官在场,大陪审团主宰整个程序。他们调查案件不受米兰达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他证据规则的限制,有权传唤其想要询问的所有证人。大陪审团程序非对审程序,其只单方面接受控诉证据,不允许调查对象提交对其有利的证据。比起庄严的法庭氛围,由社区民众组成的大陪审团营造出平和的询问环境,易于拉近与被害人、证人间的距离,最大程度地获取有用信息。虽然在审查证据过程中受到检察官的法律指导,但在决议时除陪审员外,其他所有人都不允许在场。在互相发表对案件看法的基础上,本着良心给出起诉意见。整个过程在程序民主的前提下,更重视事实真相的发现。
(三)坚持审查的秘密性原则
大陪审团程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整个过程不对外公开。除必要的人员如检察官、接受询问的证人、记录人员、翻译人员在场外,审查程序谢绝旁听、观摩等。程序秘密性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防止被调查对象事先得知消息,隐匿、毁灭证据;防止出现在大陪审团程序中的证人在后续的诉讼程序中受到威胁、恐吓、人身攻击;避免给受大陪审团调查但最终被排除怀疑的无辜公民的名誉带来影响;保护大陪审团成员免受外界的不当干涉。当然,审查程序的秘密性并非绝对,存在例外情形,如大陪审团程序进行中的情况可以对履行职责需要的检察官及协助检察官履行联邦刑法赋予职责的政府工作人员公开。另外,当法院预先指示公开或司法程序要求时要公开,以及当大陪审团调查程序获悉的信息对州、地方司法工作人员出于侦查其他犯罪及执行刑法所需时,根据检察官的请求,法院可以批准公开。据前文所述,国会还另行通过法案对大陪审团秘密原则进行了限制。但因大陪审团具有独立侦查权,秘密审查程序中获悉的信息在侦破现代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犯罪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为服务于国家安全的需要,大陪审团在现代俨然成了情报机构和当局获取重大犯罪信息的得力助手,大陪审团程序已不再单独承载控诉职能,时代的需要已使它附带地担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能㉒4。
五、结语
美国大陪审团作为独立的团体,依靠法律赋予的实实在在的权力,在对政府权力进行制衡的同时服务于社区的民众,其在整个司法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容磨灭。我国为制约检察权而引入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㉒5,培育社会对公民参与司法理念的认同感,提高公民参与司法的积极性,赋予人民监督员必要的权力,是美国大陪审团运作机制呈现给我们的有益借鉴,也是今后发展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重点要做的工作。
注释:
①R.. H. Helmholzt.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Grand Jury and the Canon Law.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50,No.2,Fiftieth Anniversary Issue ,Spring,1983,p613.
②Ric Simmons. Re-Examining the Grand Jury:Is There Room For Democracy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82 B. U. L. Rev. 1,2002,p6,7.
③Ric Simmons,Re-Examining the Grand Jury:Is There Room For Democracy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Boston University Reviews,82 B.U.L.Rev.1(2002).
④贺红强:《诉讼角色视域下的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善意例外”》,《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6期。
⑤Susan M. Schiappa. Preserving the Autonomy and Function of the Grand Jury:United States V. Williams. 43 Cath. U. L. Rev,1993,p330.
⑥张鸿巍:《美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阶段之职权探析》,《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4期。
⑦[美]伟恩.R.拉费弗、杰罗德.H.伊斯雷尔、西南.J.金:《刑事诉讼法》,卞建林、沙丽金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10页。
⑧韩成军:《论法律监督与我国检察机关公诉权配置的改革》,《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⑨何家弘:《美国司法制度(九)——选择性起诉与辩诉交易》,《检察日报》2001年8月21日。
⑩⑪ Niki Kuckes. The Democratic Prosecutor:Explaining the Constitutional Function of the Federal Grand Jury. 94 Geo. L. J.1276,2006,p1276.
⑫路易斯·卡普农著,曹慧译:《美国传闻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12期。
⑬最高法院曾在United States v. Williams 案中明确指出,大陪审团既非行政分支,亦非司法分支,它不属于任何政府组织机构,而是宪法赋予的行使自有权力的独立机构。
⑭许乐:《论人民陪审机制的构建——以S 省F 县人民法院创设人民陪审团的探索为基础》,《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4期。
⑮ Susan W. Brenner and Lori E. Shaw,Federal Grand Jury:A Guide to Law and Practice Vol. 1(Second Edition),Thomson West(2006),P33.
⑯ Thaddeus Hoffmeister. The Grand Jury Legal Advisor:Resurrecting the Grand Jury's Shield. 98 J. Crim. L. & Criminology 1171,2008,p1193.
⑰杨旭:《美国司法社会工作的发展及借鉴》,《学术交流》2013年第3期。
⑱刘国庆:《论美国刑事证据法中的异议制度及启示》,《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1期。
⑲ Howard W. Goldstein. Grand Jury Practice. Law Journal Press,2008,p30.
⑳ Roger Anthony Fairfax. Jr。:Grand Jury 2.0——Modern Perspectives on the Grand Jury. Carolina Academic Press,2011,p196.
㉑李云飞:《中世纪英格兰巡回法庭的运作机制探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㉒ Susan W. Brenner,Lori E. Shaw. Federal Grand Jury:A Guide to Law and Practice Vol. 1(Second Edition),Thomson West,2006,p257.
㉓同⑳,p235。
㉒4张泽涛:《中西司法与民主关系之比较》,《河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㉒5魏建文:《检察权运行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构建》,《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