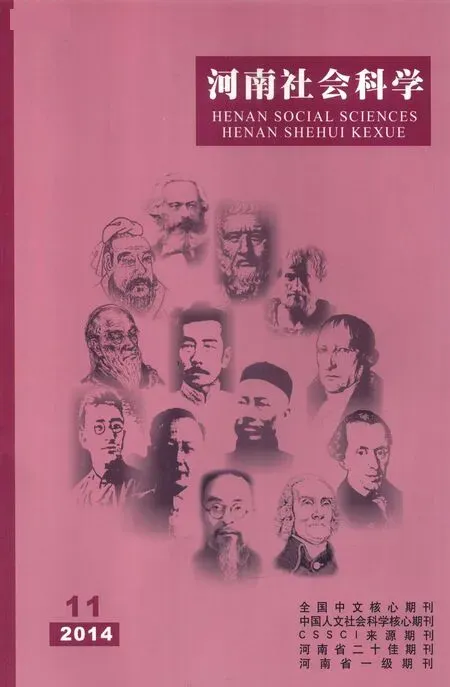重复:张爱玲的服饰叙事策略
贺玉庆
(怀化学院 中文系,湖南 怀化 418008)
一生痴迷服饰,甚至把生命比作“一袭华美的袍”的张爱玲,在生活中喜欢自己设计服装,常常“奇装炫人”。张爱玲的散文《更衣记》里那些关于服饰的精辟阐释折射出她深厚的服饰文化底蕴。她更是一位善写服饰的高手,她把自己对服饰的痴迷和内在体验移情到了她的小说创作中。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同样的服饰很多时候不是出现一次就结束,而是往往为了某种目的,有意让它在同一场景或不同场景中多次呈现,这种服饰重复的手法成了张爱玲小说叙事的重要策略。重复,最早是修辞学术语,指的是通过重复某词或某句来实现一种特定的修辞效果,后来发展为一种重要的叙事手段。米勒曾指出:“在一部小说中,两次或更多次提到的东西也许并不真实,但读者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假定它是有意义的。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或者是与其他重复形成链形联系的重复的复合组织。在各种情形下,都有这样一些重复。”[1]为此,笔者试图从张爱玲独特的服饰审美入手,重点探讨张氏小说中的服饰重复现象,尽可能充分地探索它包含的活动形式,并从这种非常有意味的形式中推衍其潜在的意义。
一、敏于服饰,眼光独特
张爱玲可以算作中国20 世纪服装历史上值得怀念的女人之一。她自小就表现出对服饰天生的眷恋,看到“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她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简直等不及长大,并发出小女孩的宏愿:“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甚至向往“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成年后的张爱玲更是把自己对服饰的狂热发挥到了极致,“不但在服装上出新、出奇、出古,在颜色的选配上也喜用一种鲜明而又参差对照的色彩”,“见过张爱玲第一面的人都会为她的衣着所惊叹。你很难用奇装异服的词句来形容她,但她的衣着款式、色彩的确与众不同”[2]。
张爱玲不仅在行动上以款式各异的服饰在不同的场合无言地张扬着她对服饰的偏好,而且还在很多作品里,表现出她对中国传统服饰的熟稔程度和独到见解。在《更衣记》里,张爱玲对传统服饰的变迁尤其是女性服饰的特点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她认为,“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在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张爱玲从古代公式化服饰中看到了儒家文化背景下封闭保守的服饰对女性人性的压抑,“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3]。她赞同张恨水的服饰思想,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这种审美思想在《红玫瑰与白玫瑰》女主人公的服饰上得到了充分显示。女主人公王娇蕊出场时穿的那件条纹布浴衣,“不曾系带,松松合在身上,从那淡墨条子上可以约略猜出身体的轮廓,一条一条,一寸一寸都是活的”。在作者眼里,宽松不严谨的家常浴衣,清清爽爽,没有束缚,没有点缀品,穿着舒适又带点诱惑性,能展示人的生命活力。
即使是《花凋》里郑川嫦穿的那件又旧又长又不合身的衣服,一般人会以为不够新潮、不够合体,但作者却以为“太大的衣服另有一种特殊的诱惑性,走起路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人的地方是人在颤抖,无人的地方是衣服在颤抖,虚虚实实,极其神秘”。对于当时流行的婚纱,张爱玲以为“不同的头脸笑嘻嘻由同一件出租的礼服里伸出来。朱红的小屋里有一种一视同仁的,无人性的喜气”(《鸿鸾禧》)。一味的雷同,缺乏个性,即使是漂亮的婚纱,她也不以为然。《年轻的时候》写到沁西亚的婚纱礼服也流露出与作者类似的看法,新娘在那件不知是租来还是借来的白缎子礼服中现出的是她那微茫苍白的笑,一样的没有活力、没有生气,更没有结婚的喜悦。
中国古代服饰讲究“错彩镂金、繁缉华赡”,服饰的精细和堆砌压倒了人自身,人成了服饰的奴隶和架子。具有现代意识的张爱玲以犀利的眼光看到了古时那种异常繁复的服饰形式背后的陈腐守旧和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她认为“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特别是满布着繁缛图案的绣花鞋很少有人前露脸的机会,实在没有必要。如果要有点缀品,她认为应该像现代西方的时装那样能“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也就是说,服饰的一切点缀要以能扬人体之长、避人体之短为宗旨,不能为点缀而点缀,一切应以实用为宗旨。
艺术活动的艺术意志主要取决于日常应世观物所形成的心理态度。可以说,张爱玲把自己对服饰的痴迷和内在体验移情到了她的艺术创作中,并且以一种不受遏止的方式充分地展开了。在她的小说世界,不管是哪个时代的人物,至少是她的女主角所穿的衣服,差不多每个人都经她详细描写。自从《红楼梦》以来,中国小说恐怕还没有一部对人物的服饰下过这样一番写实的功夫[4]。张爱玲以缤纷的服饰建构了一个斑斓的艺术世界,服饰重复的策略更成了她塑造人物、结构篇章、透视人性的有力武器。
二、服饰重复,缤纷多样
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多姿多彩,绣花鞋、戒指、手套、团扇、大衣、绒线衫等日常所见的服饰都被她信手拈来,并被不断重复。重复的表现形式变化多端,既有作品内部的重复,又有不同作品之间的重复。其表现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的重复贯穿全文始终,有的则处在小说中的某一场景。被不断重复的服饰都被作者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呈现出张爱玲观照生命、透视人物性格、心境的独特视角和手段。
同一作品内部服饰的重复在张爱玲小说中十分常见,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首先是某一场景的服饰重复。这种重复现象虽未贯穿文本始终,但它是张爱玲塑造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心境常用的“法宝”。如《十八春》重复五次的“红绒线手套”,它集中出现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先是写顾曼桢和叔惠一起照相时,“她一只手掩住了嘴,那红绒线手套衬在脸上”;接着写回来的路上曼桢忽然发现一只手套丢了,但因快到上班时间放弃回去寻找;第三次写世钧下班后冒雨到郊外找回手套;然后是世钧还手套;最后是曼桢看到叔惠进来,发现世钧的脸色仿佛不愿提起这件事似的,便把手套捏成一团塞进大衣袋里。小说就在这“红绒线手套”一丢一找一还一藏之间很好地传递了曼桢和世钧之间的爱慕心理,这比直接说出“我爱你”来得深沉含蓄,也凸显出他们内敛、腼腆的性格特征。
其次是贯穿小说始终的服饰重复。这种技法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也是屡见不鲜,如《十八春》里世钧送给曼桢的红宝石戒指、《鸿鸾禧》里娄太太为儿媳做的绣花鞋、《多少恨》里的家茵为小蛮织的柠檬色手套都在小说中若隐若现,直至故事结束。
下面来看看《多少恨》中的服饰重复现象,小蛮要的手套,在文本中虽然只出现了四次,但一直贯穿到小说的结尾。小说第一次提及手套是开篇不久,家茵来到小蛮家做家庭教师不几天,遇上小蛮过生日,家茵送了一盒糖作生日礼物,其父亲因小蛮刚掉了一颗牙齿不准她吃,从而引出手套这一服饰;第二次是在小蛮生病的时候,家茵买不到小蛮想要的颜色开始拆自己的围巾,准备给小蛮织一副手套,夏宗豫回家见了便主动帮拆绒线;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家茵选择离开上海,作者第三次写到她“从抽屉里翻东西出来,往箱子里搬,里面有一球绒线与未完工的手套,她一时忍不住,就把手套拿起来拆了,绒线纷纷地堆在地上”;第四次是在小说的结尾写宗豫来到家茵曾经住过的那间屋子,发现已人去楼空,曾经拿来织手套的柠檬黄绒线仍旧乱堆在桌上。这只被反复提及最后又被拆掉的手套曾经带给宗豫父女以希望和温暖,但好梦难圆,随着家茵父亲和宗豫太太的先后出现,他们的梦很快就破了。小蛮最终没有得到她想要的手套,夏宗豫也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婚姻。这双手套意蕴不是单一和确定的,它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家茵的心情就像最后留下的那样一堆乱绒线剪不断理还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家茵的独立自主,是她亲手拆掉了自己快织好的手套,就像她主动斩断和宗豫的感情,斩断她和小蛮的感情。这小小的手套一面连着宗豫父女对平凡、温馨家庭生活的向往,一面连着家茵对自己幸福未来的憧憬。它在小说叙事流程之外烘托出一种与人物的生存境遇相对应的文本氛围,暗示着规定情境中特有的情感和心理内涵。
同一服饰不仅在作品内部被不断重复,不同作品之间也存在着服饰重复的现象。像“绣花鞋”这一过去女性的日常服饰在张爱玲的多篇小说中被重复提及。如《多少恨》中的家茵在拖床底的箱子的时候,也顺带露出床底的一只天青平金绣花鞋的鞋尖;《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在遭到娘家人的排挤后是紧紧地把绣花鞋的鞋帮子按在心口上,戳在鞋上的一枚针扎了手也不觉得疼;《红玫瑰与白玫瑰》里振宝睡到半夜起来开灯,发现“地板正中躺着烟鹏的一双绣花鞋,微带八字式,一只前些,一只后些”;《小艾》里有席五太太那双似乎太小了点的玉色绣花鞋;《花凋》里有郑夫人为整年不下床早已病入膏肓的女儿川嫦置的两双绣花鞋。张爱玲作品中不断被提及的绣花鞋,以不同的方式重复着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这些与绣花鞋有关的太太、小姐们要么在婚姻中过着不幸福的生活,要么在自私的父母家里过着不堪的日子。一双双绣花鞋揭示出女主人公不堪的生存处境,蕴含了女人们无穷的辛酸和无奈。
每一种服饰都有着自己原有的属性,当它被张爱玲重复运用时,它不但携带了它原有的意义,同时又和文本中的人物、事件表述联系起来,强化人物某一方面的性格特征,或者是在特定条件下人物情绪的起落。而贯穿文章多个场景乃至始终的服饰,已经成为小说叙述故事、结构情节的介质。
三、服饰重复,伏脉结穴
张爱玲善于运用服饰重复的手法,将作品中的各色人物、对话以及其他事件组合在一起,将众多不可重现事件的前后发展顺序依照一定的程序组织得脉络清晰可辨。服饰意象作为叙事过程的关键点,往往出现在各种叙事线索的结合点上,道具虽小,却像一个个耀眼的金环串联于整部小说的经纬线中,具有疏通行文脉络、贯穿叙事结构的功能。这种技法是作者在创作中表现出的一种有意无意的结构照应,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可以通过某一服饰的多次再现而获得结构上的某种暗示。正如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时所总结的“草蛇灰线”叙事技巧,它“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兼动”。因为前后服饰之间所构成的“因果关系对于情节至关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将若干片段串连起来——这一点众所周知——还因为它将人物与行动、人物与其他人物串连起来”[5]。
如《色戒》,戒指这一饰品几乎成了小说的主角。戒指这一饰品第一次闪亮登场时,它不过是有钱人家太太们戴在手上的寻常之物。即使到第三次易先生提出为王佳芝买戒指时,一般也会被看作那不过是男人笼络女人的伎俩而已。直到第四次王佳芝准备以此为契机策划暗杀易先生的行动,戒指才开始作为一个醒目的意象凸显在读者面前,并意识到前面三次写戒指都是在为最后一次作铺垫的。读完小说才会惊喜地发现:戒指的每一次出现都是一个关节点、一个交叉点。如果没有牌桌上闪闪发光的钻石刺激,没有太太们牌桌上对粉红钻戒有价无市的议论,就没有王佳芝的自惭形秽和巨大心理落差,更没有她因为一枚小小的戒指就忘了身上肩负的使命和为此付出的一切;如果没有易先生在第一次单独见王佳芝时承诺给她买个戒指,就没有后面王佳芝想通过买戒指来实施暗杀计划。因为有了前面几次的蓄势和铺垫,王佳芝看到一枚六克拉的粉红钻戒突然改变初衷就显得合情合理、水到渠成。
虽然小说重复的戒指不是同一枚,但前几次提到的戒指都与最后的粉红钻戒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王佳芝他们本想通过美色诱杀易先生,眼看易先生也上钩了,但一枚小小的戒指成了温柔一刀,刺中了女人的软肋,完成了反诱杀。戒指的重复对人性潜在因素的发掘,特别是对女性自身弱点的严格审视在情节的发展变化中可谓是入木三分。
之后发表的《十八春》再一次运用戒指这一饰品来写男女之间的情事。沈世钧和顾曼桢定情的那枚红宝石戒指在文本中重复出现了五次。一开始是世钧赠送红宝石戒指给曼桢,他们彼此之间的爱情由朦胧走向明朗化。当世钧觉得自己送的戒指才六十块钱,是宝石粉做的,太廉价,比不上翠芝手上的订婚钻戒而感到抱歉时,曼桢笑说自己并不喜欢钻石之类的,反而“比较喜欢红宝石,尤其是宝石粉做的那一种”。他们关于这枚戒指成色和价值的议论,一般会以为是为了凸显曼桢的善解人意、不慕虚荣、看重真爱的性格特征,让人意外的是它为后来女佣阿宝选择上交戒指而不是私吞戒指埋下了伏笔。第二次是丢戒指,因姐姐曾经的舞女身份使爱情受挫,戒指被丢进垃圾桶又被奶奶捡到交还给曼桢,此时的戒指显示的是他们的爱情已出现阻力,裂痕开始产生。第三次是曼桢被姐姐关押时,她忍痛割爱把戒指送给姐姐的女佣阿宝,想以此换来世钧的营救。贪婪的女佣嫌戒指的物质价值太低,在权衡之下选择上交曼璐以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第四次是曼璐编造一段谎言把戒指退给世钧,这枚戒指在经历了坎坎坷坷后回到了恋人世钧的手上,但因其姐姐的话所产生的误会,戒指被扔在了野地里。因为有第二次丢戒指的行为,此时的世钧才会对曼璐编造的谎言信以为真。不然,他如果对自己的爱情多一点自信,进一步打听一下,谎言就会很容易被揭穿。第五次提到戒指是在沈世钧和顾曼桢十八年后的重逢中,虽然曾经的误解水落石出,但沧海桑田、人事已变,即使知道那时候彼此都是一心一意爱着对方的,而今也只能是“感到一种凄凉的满足”,彼此的人生悲剧已无法改写。
这枚红宝石戒指第一次出现时,我们一般只会把它看作普通男女恋爱时男方赠送给女方的定情之物,但随着曼桢摘戒——世钧丢戒——奶奶捡戒——曼桢贿戒指——阿宝交戒指——曼璐退戒指——世钧扔戒指等多次辗转,这枚红宝石戒指的不断重复使文本的情节转换自然而不露痕迹,又为故事的继续发展做好了铺垫。它的重复出现非但不显拖沓,反而处处留有玄机,造成一种层次感和紧凑感,构成了沈世钧和顾曼桢爱情通向悲剧的阶梯。红宝石戒指的多次重复强化了它在情节中的线索功能,使得小说情节跌宕起伏,行文奇巧不断。
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别具匠心地反复呈现在纷繁复杂的情节之间,一环扣一环,推动矛盾冲突的发展,它“作为叙事作品中闪光的质点,在文章机制中发挥着贯通、伏脉和结穴一类功能”[6]。
四、服饰重复,衍生象征
服饰是一种蕴藏着丰富文化密码的物品,张爱玲充分利用服饰的这一特性,灌注象征寓意。比起单纯的服饰物象,反复出现的服饰指涉更多层、更复杂,其意义更为开阔和深邃,它既有服饰本来意义的展示,又有意义与意义之间的包含和递进,更有作者主观附加意义的增添。因为服饰作为“一个‘意象’可以被一次转换成一个隐喻,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系统的一部分”[7]。而“人们阅读时常忽略这些重复现象,但许多文学作品的丰富意义,恰恰来自诸种重复现象的组合”[1]。譬如《鸿鸾禧》里娄太太为儿媳妇做的绣花鞋,它在文本中一共出现了五次。小说开篇不久就通过娄太太的女儿提到绣花鞋,当时新媳妇玉清正在祥云时装公司试穿结婚时的衣服,正愁行过礼之后穿的那件玫瑰红旗袍没有买到颜色相配的鞋子,四美告诉她说“不用买了,我妈正在给你做呢,听说你买不到”。第二次是正面写娄太太一团高兴为新媳妇做绣花鞋。第三次是她的丈夫娄嚣伯从银行回来靠在沙发上休息,一眼看见桌面的玻璃下压着一只玫瑰红鞋面,又看见另一只玫瑰红鞋面正在娄太太手里。第四次是写娘儿几个在布置新房、打发赏钱时,娄太太依然是“那只平金鞋面还舍不得撒手,吊着根线,一根针别在大襟上”。第五次是小说结尾处写婚宴后一家人坐在一起闲聊时,当娄太太为亲家太太伸手拿洋火时,只见“正午的太阳照到玻璃桌面上,玻璃底下压着的玫瑰红平金鞋面亮得耀眼”。作者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地写那双未完工的绣花鞋面,是重而不复。首先是写作的角度不一。第一次和第三次都是从家人的角度写绣花鞋;其余三次是从娄太太的角度来写绣花鞋。其次是家人对绣花鞋的态度也各异。娄太太本人虽然做鞋的时候是紧皱着眉毛,满脸的不得已,但因为“有机会躲到童年的回忆里去,是愉快的”。家人对她做鞋的行为却都颇有微词,女儿四美认为“妈就是这个脾气!放着多少要紧事急等着没人管,她却去做鞋”。女儿二乔也觉得难为情,认为“家里现放着个针线娘姨,叫她赶一双,也没有什么不行,妈就是这个脾气”,总使自己“在外人面前又还不能不替她辩护着”。作为未来儿媳的玉清听到婆婆为自己做鞋也吞吞吐吐地说“那真是……那真是……”这省略的话语,我们不妨推测一下,她是不是在心里说,谁要你做鞋子,真是多此一举!内心里可能还有埋怨和不满,只是不好对未来婆婆的行为指指点点,但其不愉快的心绪还是流露了出来。
本来,娄太太为买不到合适鞋子的儿媳做绣花鞋,传递的应该是婆婆对儿媳的亲密情意,结果因为在绣花鞋的重复之间穿插了儿子婚礼的筹备、女儿的不理解、儿媳的冷漠和丈夫的责备,从而使得文本中的绣花鞋衍生出许多新的内涵,成为一个可供人反复咀嚼的审美复合体。绣花鞋,作为客观物象,是指女性穿在脚上便于走路的东西,鞋面上有用彩线刺成的花纹图案等。最常见的图案就是鸳鸯戏水、龙凤呈祥、并蒂莲开。这些成双成对雌雄相配的具象,无不围绕着男欢女爱这一永恒的主题。到了张爱玲这篇小说里,意义已发生了变化,它一头连着娄太太愉快的童年生活和她现在的婚姻生活,一头连着家人的不解和责备,一头连着儿子大陆的婚礼。三者之间构成一种张力,多种意义在绣花鞋的凝聚下互相交织,又互相撞击。对娄太太来说,眼前一家大小“漂亮,要强,她心爱的人,她的丈夫,她的孩子,联了帮时时刻刻想尽办法试验她,一次一次重新发现她的不够”。做鞋的遭遇只是她三十年无数失败的一次,绣花鞋成了娄太太婚姻生活的一面镜子,它隐喻着娄太太对现有婚姻的厌倦和对童年生活的向往,更隐喻了作者对美满婚姻生活的怀疑甚至是否定,使人认识到婚姻悲剧的不可抗拒。正如文章结尾所写,娄太太由玻璃板下的绣花鞋面回忆起小时候看人家迎亲,旁观的时候一路是华美的摇摆,有着无边的喜庆,但当她结了婚,大儿子也结了婚,她终于“知道结婚并不是那回事”,华美繁盛的婚礼是做给别人看的,它吸引着其他人不断地走进去,一旦走进却都是孤凄、为难、麻烦无奈的人生。小说最后“娄太太只知道丈夫说了笑话,而没听清楚,因此笑得最响”这句话很好地诠释了小说潜藏的意义。在喜气洋洋操办儿子婚礼的背后,绣花鞋的重复出现给作品弹奏出不和谐之音,具有一种反讽的效果。本应热闹喜庆的婚礼在张爱玲的笔下有了浓浓的悲剧意味:夫妻恩爱是虚假的,婚姻的幸福是虚幻的。“从表面看,张爱玲对现实、对人生是很‘冷’的。但是我们细读她的作品,就不难发现,在她的‘冷’的后面有着一种非个人的深刻的悲哀,一种严肃的悲剧式的人生观。”[8]
“当一个字或一个意象所隐含的东西超过明显的和直接的意义时,就具有了象征性。”[9]可以说,张爱玲小说中的很多服饰一经重复就不再是普普通通的防寒保暖遮羞之物,也不仅仅是人物性格的表征,它往往超越了服饰原有的意义,开始走向虚拟化和抽象化,具有多重阐释的空间。余彬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张爱玲作品中的服饰“每一笔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写实,然而每一笔皆见出象征的空灵”[10]。这种写实与象征兼具的服饰成了人物情感命运、人生际遇的代言人,正像张爱玲在《童年无忌》所言:“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
我们知道“人活着,靠的是吃穿”。张爱玲从审视、欣赏服饰的角度来观察日常生活,来体验、感悟人生,来写人生的种种不如意绝对比透过嘴中的“思想”深刻得多。因为服饰本来就是人物思想、情感、身份等内在信息的表征,而一旦再加以重复,小说中的人物、事件、主题意蕴等都会变得开放、动态、异质和多声部。这种极有特色的服饰重复,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不是呆板机械的重复,而是重复中有变化,变化中又有个性,并且“在其反复出现之时,也于重复中反重复,力求展示新的意义层次,从而在同一意象的此层意义和彼层意义之间形成张力”[6]。正因为这样,她的服饰叙事才各自入妙,魅力无限,从而成为张爱玲小说有别于其他作家的神采之所在。
[1][美]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M].王宏图,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2]金宏达,于青.张爱玲传略[A].张爱玲文集(第四卷)[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3]金宏达,于青.更衣记[A].张爱玲文集(第四卷)[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4]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5][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M].王宇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6]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7][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8]饶芃子.心影[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5.
[9]荣格,等.人类及其象征[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10]余彬.张爱玲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