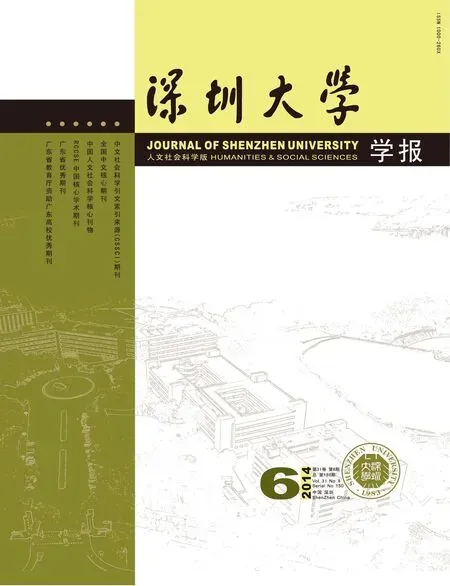先秦儒学与老年学
杨自平(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台湾 中坜)
先秦儒学与老年学
杨自平
(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台湾 中坜)
关于现今老年学,西方社会学已提出数家老年学理论,儒学领域则多从孝道及养老思想进行讨论,然皆有所限制,故拟将西方老年学理论与儒家观点进行对话,尝试建构一套儒家的老年学理论。先秦儒家的老年学,既能正视老年期的生理限制,又能安而不忧,致力道德实践。不仅为老年世代提供可行的安身立命法门,也为青、壮世代提出当下安立及面对老年的实践方向:一、自觉本心、好学修德,实现义命;二、孝亲敬老;三、面对未来衰老不忧不惧;四、将道德实践视为终身使命。透过建立正确观念及伦理道德实践来面对老年课题,乃先秦儒家对现今老年学发展的重要贡献。
先秦儒学;老年学;老年;高龄化;孔子
就现今世界而言,老年议题是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关于老年化问题,孙得雄指出:“人口老化是现代社会特征之一,也是人口增加型态转变的必然结果。”[1]以联合国所订下65岁以上为老年人口来看,据台湾内政部统计处对2014年6月底台湾人口结构分析显示,65岁以上者2748 989人占11.75%,扶老比15.9%,续呈平稳上升趋势。至于衡量人口老化程度之老化指数则为老化指数为83.14%,较上年同期增加5.03个百分点,呈现缓慢上升趋势①。据台湾内政部统计,2013年底的老化指数是80.51%,虽较全世界之30.77%及开发中国家之20.69%为高,但远较已开发国家之106.25%低。相较主要国家,远较日本192.31%、德国161.54%、加拿大93.75%、法国89.47%、英国 88.89%为低;但比澳洲及美国73.68%、新西兰70.00%、韩国68.75%、新加坡62.50%、中国大陆56.25%、马来西亚19.23%、菲律宾12.12%为高②。可见高龄化问题不仅是台湾迫切面临的问题,亦为世界各国必须正视的重要课题。
探讨老年化议题需留意老年族群的状况千差万别,不可笼统谈论。依台湾内政部的认定,将65岁以上者称为老年人,但老年族群的实际状况有所不同。依身心健康状况来看,以身心健全的老年族群来说,有尚在工作岗位,领取薪俸者;亦有退休后,请领退休金、年金,或由子女经济支持,而安享老年生活者;也有经济困乏,无依无靠者。就身心有病痛的老年族群,有虽有部分病痛,然仍能自主生活者;亦有身心有严重病症需特殊照顾者,此类亦有独居或与家人同居者等差异。
此外,探讨老年议题,亦须参考政府机构的相关数据统计,以及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如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以了解老年化议题有那些实际现象及问题。老年议题可从社会、家庭及个人不同面向来看。就社会面而言,不仅涉及庞大的老年族群,包括身心照顾、经济需求、经济消费、社会贡献等。同时亦影响青壮族群,如,青壮年提供健康照顾及经济资助等;就家庭面而言,包括由年长者代为照顾幼小子女、家中老年人的身心照顾等;就个人面而言,老年人如何面对自己的生活,而青壮年又如何安排自己未来的老年生涯等。
因此,欲深入探讨老年议题,必须留意上述问题,方能相应而深刻地探讨。学界针对老年议题发展出老年学(Gerontology),虽然老年议题的讨论在东西方极早便出现,但成为一门专业学问则是晚至20世纪③,“老年社会学”(Sociology of Aging)一词最早是由美国E.J.斯蒂格利茨所提出,并有几部影响现今老年学研究的要著问世④。
关于老年学的定义,《老年学理论与实践》一书指出:“老年学是对人们衰老的研究,这包括从各学科和实际工作领域对衰老过程,从生理、心理和社会方面进行研究。”[2]更具体来说,老年学的研究范围及特色,可由以下描述加以说明。
老年学以人类个体老龄化和人口老龄化为研究对象,这是一个没有其他科学研究的领域,使老年学能够成为一门独特或独立的科学;另一方面,由于既要研究个体又要研究群体,就不能不涉及人类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等,这就决定了老年学必须运用人类一切科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以获取新的规律知识,所以老年学必然是一门多学科共同研究同一个问题的学科,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3]
儒学是一门具极强时代性的学问,现今谈儒学亦不宜忽略老年议题。选定先秦儒学与老年学为题,便是尝试探讨儒学对该议题可能带出的省思。
目前学界以儒家观点讨论老年议题的研究论文不少,但主要切入向度有两方面:一是从孝道谈起,强调恢复孝道精神⑤;二是重视儒家所提出的养老思想,透过国家机制照顾社会上的老者⑥。这两方面都有一个共通点,即从群体的角度,由家庭、家族或社会谈老年照顾。然尚有一问题值得留意,即个人该如何面对自己的老年生涯。先秦儒家对此问题是有所关注的,而这些观点值得列入现今老年议题的探讨。
探讨老年学必须留意现有的理论,西方学界提出数派老年学理论,因内容繁多,故文中将简略介绍,以掌握整体发展。鉴于西方老年学理论虽有所见亦有其限制,而以儒学谈老年学多局限在孝道及养老思想的阐发,故尝试进行对话,一方面见出现今老年学理论的特色及限制,另方面尝试以儒家观点建构一套儒家的老年学理论,期能为老年学理论提出补充观点,亦能见出先秦儒学对老年议题的因应及贡献。
一、现今西方老年学理论回顾
宏观西方老年学理论,学者指出:“从目前来看,现有的老年学的主要理论和观点更多的是从社会学或心理学的某一个角度或者方面阐述个体老龄化进程的,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老年学理论体系。”[3](P30)
顾东辉据《老化与社会》指出老年社会学有五类重要理论:结构功能主义、冲突论、社会交换理论、脱离理论⑦(disengagementtheory)、活动理论[4],并就各理论分别解释。
关于结构功能主义 (structurefunctionalism)主张,顾东辉言道:“把整个社会视为一个有机组织体,该组织要透过不同架构间的相互依赖来维持平衡,……功能主义者强调社会秩序与稳定,认为社会需要重于个人需求。”“老人在社会体系中也有其价值。老年人累积长期经验,将文化传到下一代。老年社会不是隔离孤立的,老年问题可能不在老人本身而在社会结构。”[4](P255)
顾东辉认为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Dahrendorf)的冲突论(conflicttheory)主张:“人类社会基本上是一种不均衡权力分配的组合团体……只有如此,团体成员才会顺从与实行团体的行为模式,符合团体规则的要求。”因此,从冲突理论看,“老年问题之发生是因为在年龄阶层里,老年团体被分配的权力或资源不多也不均。他们属于弱势团体,为求生存,他们必须与非老年团体抗衡以改变地位和争取权益与福利。 ”[4](P255)
至于霍曼斯 (Homans)社会交换论(socialexchangetheory),顾东辉指出:“该理论相信,社会互动是人与人在交换过程中对利润和成本、取与给的计算,人们尽量寻求最大酬赏,同时避免得到惩罚。”[4](P255)根据交换理论,“老年问题产生源于他们缺乏交换价值,没有资源给予社会从而无法获取社会的尊崇。 ”[4](P256)
至于昆铭(Cumming)和亨利(Henry)1961年《年事日增》(Growing Old)提出的脱离理论(disengagementtheory),顾东辉指出:“他们认为,老年人有脱离社会的倾向,社会现有制度亦会让老年人自动从社会中脱离出来。”“脱离理论强调,当老人从社会逐步退出时,社会亦有意无意排挤他们参与社会事务。如:退休制度半强迫半期待地等老年人从岗位上撤退以利年轻人递补,这是一种双向撤离。”[4](P256)
至于罗伯特·哈维格斯特(R.J Havighurst)、阿尔布雷希特 (R Albrecht)合撰的巨著 《老年人》(Old People)提出活动理论(activitytheory),顾东辉指出该理论强调:“社会互动对每个人都有同等价值,正常的老化过程不能脱离社交活动。”“老年人要在精神和心理上与社会保持接触,要有活跃的社交生活,才能获得幸福晚年和维持开朗心境。”[4](P257)
邬沧萍、姜向群又补充另外四类理论:连续性理论、老年次文化群理论⑧、年龄分层理论、交换理论⑨、角色理论。
关于连续性理论,邬沧萍等认为:“连续性理论是对活动理论和脱离理论的挑战,其重点在于解释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差异性。”“人们中年期的生活方式会延续到老年期。……中年期开朗活跃者在进入老年期以后也会积极投入社会活动;中年期沉稳内向者在老年期一般不会热衷参与社会活动。”“连续性理论是以对个性的研究为基础的。”[3](P32)
至于罗斯(Rose)提出老年次文化群理论年龄分层理论,邬沧萍等指出:“该理论旨在揭示老年群体的共同特征,而老年亚文化群是老年人重新融入社会的最好方式。”“按照罗斯的观点,只要同一领域成员之间的交往超出和其他领域成员的交往,就会形成一个亚文化群。老年人口群体正是符合这个特征的一种亚文化群体。”“老年人通过在亚文化群中的成员身份来保持自我观念和社会身份;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其他人,其行为不能用一些综合的社会标准或规范来衡量,只有在群体成员期望背景下的行为才是得到认同的。”[3](P34)
至于M.W.莱利(Riley)和A.福纳(Foner)提出年龄分层理论,邬沧萍等指出:“该理论以社会学创立的角色、地位、规范和社会化概念为基础,分析了年龄群体的地位以及年龄在一个特定社会背景下的含义,形成一个理解老年人社会地位的框架和包括整个人生的老龄化概念。”“认为年龄不是一种个人特征,而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标准,是现代社会各方面的一个动态成分。”“认为同批人通过一个年龄层就被看作是进入到一个被期望并得到回报的逐级年龄系统。该理论承认一个阶层的成员和另一个阶层的成员不仅在生命周期上是不一样的,在所经历史时期上也是不同的。”[3](P34-35)
至于交换理论,邬沧萍等认为:“主要探讨环境、个体及其相互作用对老龄化的影响。该理论包括象征性相互作用理论、标志理论和社会损害理论等部分。”象征性相互作用理论认为:“在老龄化的过程中,环境、个体以及个体与环境结合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从象征性相互作用理论衍生出来的标志理论认为:“人们在与社会环境里的他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形成自我观念。……我们是根据他人如何评判自己来看待自己与他人的交往的。”[3](P36)社会损害理论和社会重建理论 “都是从标志理论派生而来的。社会损害综合征是指已有心理问题的个人所产生的消极反馈。……社会重建理论认为,通过向老年人提供机会,让他们生活在不受社会总价值观念影响和结构适当的环境中,增加其自信心和独立意识,可以干预这个恶性循环,中断进行性的损害。 ”[3](P37)
对于角色理论,邬沧萍等认为:“角色是个人与社会相互接纳的一种形式。社会通过角色赋予个人相应的权利、义务、责任和社会期望。这些角色给一个人确定和描绘了一种社会属性。”[3](P37)“这些角色通常连续性地排列着,每个角色都和一定的年龄或生命阶段相联系。在大多数社会中,日历年龄被用来当作进入各种位置的资格,用来评估不同角色的适应性以及不同社会环境下人们的期望。”[3](P37)“人适应衰老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这个人接受晚年角色变化的成功程度。老年人的角色变化与中年人不同,它不是角色的变换或连续,而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角色丧失或中断。因此,老年人不仅需要适应与老年相关的新角色,同时他们必须学会适应角色的丧失。”[3](P37-38)角色理论认为“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老年人适应衰老的途径之一是正确认识角色变换的客观必然性;二是积极参与社会,寻求新的次一级角色。 ”[3](P38)
综观结构功能主义、冲突论、社会交换理论、脱离理论、活动理论、连续性理论、老年次文化群理论、年龄分层理论、相互作用理论、角色理论这九类理论。脱离理论、活动理论、连续性理论、交换理论、角色可归为一大类,专门针对老年世代探讨其特性及生活方式;年龄分层理论、结构功能主义、冲突论、社会交换理论、老年次文化群理论则是从社会结构面,探讨老年世代与非老年世代间的区隔及彼此间的关联性。
考察这两大类理论,各类中各家说法皆有现实经验作为依据,然彼此却存在殊异性甚至对立性。如第一大类中的脱离理论、活动理论具对立性,而连续性理论又与二者对立;在第二大类亦有同样现象,如,结构功能主义、冲突论却处于对立立场。此意味着,老年问题有其多元性,无法简单规约成一统一理论。
至于先秦儒家⑩对这两大类议题的思考,以下将深入探究,并与现今老年学理论进行对话。
二、先秦儒学的年龄分层理论、角色理论及尊老思想
现今对老年的分期,六十五岁到七十四岁为初老期 (young-old)、七十五岁到八十四岁为中老期(old-old)、八十五岁以上为老老期(oldest-old),先秦儒学已有年龄分层理论,《礼记·曲礼》云:“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颐。”[5]
看似以七十岁称为老,然五十岁已属老年的开始,故“五十曰艾”,郑玄注:“艾,老也。”[5](卷1,P14b)《礼记·王制》亦云:“五十始衰”[5](卷13,P18a),“六十曰耆”,郑玄注:“耆,至老境也。”[5](卷1,P14b)可见,先秦儒学的年龄分层理论以五十岁为老年期的开端,五十岁为艾年、六十岁为耆年、七十岁为老年、八十与九十岁为耄年、百岁为期年。意即六十岁为初老期、七十岁为中老期、八十以上为老老期。
先秦儒学对老年期生理状况的转变亦有所描述。五十岁身体机能开始衰退,饮食需要与壮年不同;六十岁在饮食上需常补充肉食;七十岁需时时准备较好的饮食,且需穿着丝帛的衣物始觉温暖;八十岁依赖他人照料衣食,需随时准备珍馐及衣物;九十岁的老者,因饮食不时,故需随时提供食物,但此时即便旁人照顾周全,但因身体机能严重衰退,血气有所不足。《礼记·王制》言道:〈王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饱,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九十虽得人不暖矣。”[5](卷13,P18a)又云:“五十异粻,六十宿肉,七十贰膳,八十常珍,九十饮食不离寝。”[5](卷13,P18a)
此外,《礼记·曲礼》这段文字亦包含老年学的角色理论,五十岁尚未退休,仍可可担任卿大夫之要职[5](卷1,P16a) ,到六十岁,无论职场或家事可渐渐退居幕后,指导后进从事,故郑玄云:“六十不与服戎,不亲学。”孔疏云:“六十耳顺,不得执事,但指事使人也。”[5](卷1,P14b、P16a)到七十岁正式退休,家族、家庭的决策及执行,完全交付子孙,安心养老。故孔疏云:“六十至老境而未全老,七十其老已至,故言老也。既年已老则传徙家事,付委子孙,不复指使也。 ”[5](卷1,P16a)
至于八十岁以上称为耄,则指出此阶段老年人的身体及心理出现极大衰退现象,故郑注云:“耄,惛忘也。 ”[5](卷1,P15a)孔疏云:“惛忘即僻谬也。”[5](卷1,P17b)即出现昏昧胡涂、健忘的邪僻错误的状态或行为。至于百岁之人,身心状况更走下坡,整个感官能力尽失,需赖他人照顾,故郑注云:“期,犹要也。颐,养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尽养道而已。”[5](卷13,P18b)
对于老年期的角色,则依庶人及贵族身分分别说明。就庶人而言,五十岁不参与耕种、筑城等劳役工作;六十岁不参与军事活动;七十岁不处理接待宾
11客之事,与“七十曰老而传”相应;八十岁不参与丧、祭之事。〈王制〉云:“五十不从力政,六十不与服戎,七十不与宾客之事,八十齐丧之事弗及也。”[5](卷13,P18b)
对于贵族身分的卿士大夫,以一般状况,虽然五十始衰,然因其贤德,故仍可封爵任官,故云“五十而爵”[5](卷13,P18b),但到了七十岁则需退休,故云“七十致政”、“七十不俟朝”[5](卷13,P18b)。除非有特殊大事方可入朝上奏,〈祭义〉云:“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与之揖让,而后及爵者。”[5](卷48,P13b)至于八十、九十则不再上朝,君王若有事征询,则需亲自造访。〈祭义〉云:“八十不俟朝,君问则就之,而弟达乎朝廷矣。”[5](卷48,P9b)〈王制〉云:“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5](卷13,P18a)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儒学研究者在谈及老年议题多强调儒家独特的敬老、养老概念,并以此标榜为儒家的老年观的核心。殊不知这样的敬老概念,在西方早期社会亦存在过。美国著名心理分析学家艾瑞克·艾瑞克森(Erik H.Erikson)指出:
从过去的历史、从神话及传说、从人类学家及历史学家口中,我们知道以前的老者,在社会中大都是传统的传递者、祖先价值观的守卫者、传承的提供者,他们被尊称为贤人、族长、先知及高高在上的顾问。晚辈尊老者为顾问或先知并向其请益,因为他们可以根据长期来的经验、记忆、纪录预测事件的发生。[6]
综观上述,先秦儒学与现今西方老年学相较,相同的是皆有年龄分层理论,且对老年阶段亦有区分,亦提出老年角色观点。但不同处有两点:
其一,先秦儒学既正视老年期生理、心理的变化,提出士卿大夫七十致仕,但仍珍视老者的品德与学养,故七十岁遇特殊大事仍可上朝议事,八十以上,君王仍可亲自访视。足见贵族身分的老者并非完全与社会脱离,此与脱离理论看法略异。
其二,先秦儒学表现出明显的贵老、尊老意识,自天子至百姓皆如此,但与在西方早期敬老不同的是,先秦儒学所论除专业经验、人生经验外,更着重品德学养。
三、西方论老年期的睿智及美德表现
关于世俗对老年的理解,早在古罗马时期的哲学家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106BC-43BC)在84岁时[7]写成《论老年》(CatoMaior de Senectute)一文,便曾就当时对老年的四大误解指出:
老年之所以被认为不幸福有四个理由:第一是它使我们不能从事积极的工作,第二是它使身体衰弱,第三是它几乎剥夺了我们所有感官的快乐,第四是它的下一步就是死亡。[7](P10)西塞罗不赞同这四点看法,并分别提出回应,关于第一点老年人不能从事积极工作,他指出:
完成人生伟大的事业靠的并不是体力、活动,或身体的灵活性,而是深思熟虑、性格、意见的表达。关于这些质量和能力,老年人不但没有丧失,而且益发增强了。[7](P11)
针对第二点老年人身体衰弱这项,西塞罗回应道:“老年是缺乏体力的,……我们不但应当保重身体,而且更应当注意理智和心灵方面的健康。”[7](P18-19)至于第三点老年缺乏感官快乐,则指出:“一个人在经历了情欲、野心、竞争、仇恨以及一切激情的折腾之后,沉入筹思,享受超然的生活,这是何等幸福啊!”[7](P25)对于第四点死亡临近,他不否认这一点,并言道:“老年人去世就像一团火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的情况下渐渐烧尽而自然熄灭一样。……我乘坐的船就要在我的故乡港务局靠岸了。”但认为应该有一种积极正面的态度,言道:“老年没有固定的界限,只要你能担负起责任,将生死置之度外,你就是在非常恰当地利用老年。因此老年甚至比青年还自信,还勇敢。”[7](P34)
综观西塞罗对这四项看法的响应,可发现他对老年提出三点重要看法:一是承认老年确实有其限制,缺乏体力、缺乏感官热情、接近死亡;二是老年亦有其积极意义,老年人能深思熟虑,性格较成熟,能睿智地表达意见,且能不耽溺于感官欲望,而享受超然的精神生活;三是老年亦有其重要工作,注意身体及理智、心灵的健康,并且超脱生死,担负应负的责任。
对于整个人生历程,西塞罗认为:
生命的历程是固定不变的,“自然”只安排一条道路,而且每个人只能走一趟;我们生命中的每一阶段都各有特色,因此,童年的稚弱、青年的激情、中年的稳健、老年的睿智—都有某种自然优势,人们应当适合时宜地享用这种优势。[7](P18)
西塞罗将人生视为只能往前无法回头的发展过程,每个阶段各有特色及优势,人们需顺应且发挥这些优势,老年阶段亦是如此。
西塞罗正视老年的积极面并认为老年具有睿智的特色及优势的看法,亦表现于现代西方老年学学者所提出老年智慧的主张上。美国著名心理分析学者艾瑞克·艾瑞克森指出:“一生漫长的记忆及较宽广的视野,让紧急的事件都可以变成只是自然世界维持平衡的作用。”“老年人的智慧对于社会体系的运作将可以有重大贡献和影响。”[6](P385)意即老年人具有丰富的经验与视野。
美国心理医师马克·艾格洛宁 (Marc E.A-gronin)更进一步认为:
即使在年老而智力衰退或有其他损失的背景下,爱、创造和更新关系的能力反而增强,这是变老而得到的礼物。……威伦特的长期研究资料支持此一主张,透露出人到晚年,包含宽恕、感恩与慈悲在内的优点非常重要,是建立美好关系的基础。[8]
马克·艾格洛宁认为老年人最可贵的品德是具有爱、创造以及宽恕、感恩与慈悲。
关于睿智是如何出现,艾瑞克森注意到经验与视野的扩展所造成的影响,这理由相当合理。但对于爱与宽容等美德,艾格洛宁只针对执医经验提出现象观察,但如何出现,却未作说明。关于此,可回到西塞罗的看法找出解答。
前述西塞罗所提出的四点回应,已预设这样的前提,即他所针对的是年轻时已有良好品行的老年人。他指出:
我所赞美的只是那种年轻时代已经打好基础的老年。……无论是白发还是皱纹,都不可能使人突然失去威望,因为一个人最终享有威望乃是他早年品行高尚的结果。[7](P31)
西塞罗认为老年是否能受到敬重,倚赖年轻时所具备的高尚品行。此意味着,美好的品德在晚年不会自然出现,必须靠长期累积。至于如何于年轻时打好基础,这方面便是先秦儒家所关注的。
四、先秦儒学的工夫论与老年学
关于老年世代的安身,与西塞罗一样,在更早之前的孔子同样肯定需于年轻时打好品德基础,努力修德,否则到老年言行便无可称述者,无法获得该有的尊重或成为年轻人学习的榜样。孔子曾责备故旧原壤“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9]两人是故交关系,孔子秉持爱人以德之心,见原壤伸两足箕踞以待孔子的失礼仪态,方有这般深切的责备之语。而夫子之志在“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9](P82)此乃仁德君子自然产生的人格魅力。
此外,儒家重视孝道,孔子屡言孝的重要,并言行孝之法。孟子主张由善端存养扩充,肯定舜“大孝终身慕父母”[9](P303);荀子进路虽与孟子不同,但亦重孝,唯主张经由后天学习礼义而来。因此作为一位仁德君子必然具有孝心、孝行,不遇于时,则行孝于家;得行其道,则以身作责,并透过教化推广孝道。因此,儒家将孝视为君子必须力行之事,亦鼓励此良善的孝悌风气,这是儒家老年学与西方相较下的一大特色。
至于西塞罗所说打好品德基础,儒家有其具体的工夫实践。孔、孟认为人需正视存在的命限,并致力于实践道德义命。孟子的一段话,正可展现此观点。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9](P349)存养本心,推扩本心便是实践道德义命:对于上天对每个人寿命长短的安排,能坦然接受,即为安命;并透过修养以安顿身心,这便是立命。这便是儒家的人生态度。
在正视命限及安命上,除了接受上天对每个人寿命长短的安排外,包括贤·肖、人世际遇、贫富贵贱等命运,皆能坦然面对。《荀子·宥坐》载孔子语:“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10]孔子亦自道:“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9](P97)
此外,儒家亦指出人生有少、壮、老三大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生理特色,君子亦为以不同的工夫加以对治。孔子曾云:“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9](P172)此说法意味着,人生是由少壮到老的历程,生理特征亦会产生变化。对于老年,面对血气明显衰退,对于名利、欲求应该看淡。
对于老年期,除了接受血气衰退的事实,并淡泊名利外,对于道德理想的追求仍可继续坚持。故孔子尝云:“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9](P94)这也是儒家老年学的另项特色。
实践义命是儒家认为个人该努力从事的,在工夫上,除了对治血气外,对于时遇,亦应透过实践义命。《荀子·宥坐》则指出:“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以俟其时。”[10](P346)孔子自身便是终生致力于此,故自道其生命实践: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踰矩[9](P54)。亦即孔子的一生是自年少立志,不断实践的历程,方能到五十岁能充分体悟个人所受之天命,初老期能体悟深奥隐微之理,到中老期能从容中道。
观孔子一生,正是“博学深谋,修身端行”的最佳写照。关于孔子的好学,表现在他的勤学、乐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9](P98)然夫子之学并非博杂的摄取知识,而是在圣人之道的基础上谈博学。故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9](P93)又云:“予一以贯之。”[9](P161)正因以道为依归 ,方能通贯,源源不绝。
此外,除了学不厌外,孔子亦诲人不倦,曾自道:“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9](P93)“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9](P93)孔子好学、好讲学便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表现,既使自家身心得以安顿,实现义命,亦能协助他人达成这样的理想。
关于修身不辍,孔子与弟子曾参作了最好的示范。在孔子老年重病,弟子以为夫子将不久于人世之际,孔子仍坚守礼法,反对子路让门人作为自己的家臣 。而曾子在临终之际,不仅仍自省不辍 ,且仍认真回答孟敬子的提问15,无论自身或对社会的使命感,都坚持到最后一刻,真正实践了他的自我要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9](P104)
综观孟子论立命及孔子博学、修身之论,荀子重礼义之教,均可见出儒家认为君子在面对老年,应不忧不惧,坦然面对,此为安命;自少立志学圣人,好学乐道,终身修德,习礼不辍,此为立命;并能进一步爱人以德,诲人不倦,立人达人,帮助他人安立生命。
高龄化社会是现今世界的趋势,相较西方近年来针对老年议题发展出的老年学,台湾在这方面亦需有所开展。现代西方老年学理论多植基于实际现象的观察,无论脱离理论、连续理论、角色理论等皆如此。这些理论的特色在于实际依据老年人的现实状况提出思考,但限制是容易偏于现象的某些方面,或受限于研究的对象,如以健康的老人,或以失智的老人为研究对象;或受限取样多寡,或调查区域等等,所得出的结论是可能天差地别的。因此,如何综合各种现象的研究报告或理论,进而作全面性的思考,提出涵盖面更高的老年学理论,是值得努力从事的。
先秦儒家认为人生是由少及壮及老,往而不复的发展过程,到老年血气慢慢衰退,但君子面对此现象,既接受存在命限,故戒之在得,但却不放弃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努力不懈的学习及道德实践,方能在老年期展现睿智及过人的道德风范,而为年少者所敬仰,并乐于亲近学习。
至于社会方面则主张,上位者当提倡并实行敬老、养老的思想与具体制度,使老年人得到应有的尊重与生活照顾。
先秦儒家的老年学对现今老年学的启发,既能正视老年期在血气形躯上的限制,又能安而不忧,且仍能积极致力道德实践,让道德生命辉光日新。这样的观点不仅为老年世代提供可行的安身立命之法,也为未来会面临老年期的青、壮世代提出值得参考的方向。对青、壮年而言有四点启发:一是自觉本心,孝亲敬老;二是致力好学、修德,实现义命,发挥现阶段的生命意义;三是面对未来的衰老能不忧不惧,坦然面对;四是将道德实践视为终身使命,力行不辍。
对老年建立正确的观念及态度,并有积极的作为,应是先秦儒家对现今老年学发展的重要贡献。
注:
①参见2014年第30周台湾内政统计通报,“103年6月底人口结构分析”,2014年7月26日。台湾内政统计处网页http://www.moi.gov.tw/stat/news_content.aspx?sn=8057。
②参见2014年第3周内政统计通报,“102年底人口结构分析”,2014年1月18日。台湾内政统计处网页 http://www. moi.gov.tw/stat/news_content.aspx?sn=8057。
③ 袁缉辉指出:“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特大的经济危机之后,老年人失去工作,而储蓄又消耗殆尽,生活陷于贫困。老龄化过程和老年人诸多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对老年问题的关注,促进了老年学各学科的创建和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老年学的内容和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在英、法、丹麦和美国出现了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称为‘社会老年学’(Social Gerontology),它包括了老年社会学、老年经济学、老年人口学和老年政治学等方面,形成一个综合研究的系统。”袁缉辉:《当代老年社会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8页。
④ 袁缉辉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开展老年社会学研究较一早的国家之一。‘老年社会学’(Sociology of Aging)这一术语,是1943年首先由美国E.J.斯蒂格利茨所使用。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姆适研究委员会主席伯吉斯等,在罗斯福总统于1935年制定的社会安全法案影响下,首创了以社会学家为主的‘老年研究会’,被称为‘第一次对老年的社会学方面进行描述所作的有组织的尝试’。美国奥托·波拉克所著的《老年的社会调整》(1948年)是在老龄问题上的第一部社会学著作。另一项老年社会学成就,是1961年由罗斯和彼德森主编的《老年人和他们的社会领域》一书,它是美国中西部社会学会一系列会议的产物。”袁缉辉:《当代老年社会学》,第8-9页。
⑤ 与此议题有关之期刊论文不少,如,杨勇刚:〈儒家孝道观与老龄社会〉,《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3期,第94-99页。徐照伟:〈浅析《论语》中的‘孝’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 年1期,第138-139页。陈运春:〈传统儒家孝道与当代老龄化社会问题研究〉,《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 年5期,第16-18页。杨卫军:〈儒家孝道与中国老龄化问题〉,《船山学刊》,2010年3期,第204-206页。曹立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与养老思想探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 5期,第88-91页。张践:〈儒家孝道观的形成与演变〉,《中国哲学史》,2000年3期,第74-79页。丁原明:〈儒家‘孝’文化的现代诠释〉,《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3期,第7-11页。董江爱:〈论儒家孝道思想的现代价值〉,《山西高等学校 (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2期,第36-37页。
⑥ 这部分台湾与大陆学者均有所关注,相关期刊论文,如,胡发贵:〈儒家的养老与敬老思想〉,《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3年2期,第14-17页。谢楠:〈生命来源观:中国家庭养老内在机制新探讨〉,《中州学刊》,2011年1期,第125-129页。陈金锋:〈孟子的‘养老’观〉,《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6期,第80-82页。潘剑锋、刘峰:〈论先秦时期我国养老敬老体系的初步成型〉,《求索》,2010年5期,第232-235页。赵雪波:〈‘养老’、‘教养’、儒家 ‘教化’〉,《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4期,第42-47页。胡蔼若:〈我国固有的敬老养老思想〉,《实践博雅学报》第13期,2010年1月,第119-146页。杨三东:〈建立以家庭为重心的养老制度〉,《中山学报》第13期,1992年5月,第183-200页。陈宽政:〈建立一个以家庭为重心的养老制度〉,《今日财经》第291期,1986年2月,第18-19页。黎圣伦:〈我国历代敬老养老制度〉,《中山学术文化集刊》第2期,1968年11月,第347-363页。梁坚:〈中国古代的养老制度〉,《台湾省立博物馆科学年刊》第6期,1963年11月,第114-118页。杨绩荪:〈古代敬老养老的制度〉,《中国世纪》第64期,1963年2月,第5-6页。
⑦ 顾东辉将disengagementtheory译为撤离理论,叶肃科亦采此译法,参见叶肃科:〈社会老年学理论与福利政策应用〉,《东吴社会学报》第9期,2000年5月,第77-122页。邬沧萍、姜向群则译为脱离理论,然因disengagement多译为脱离,故采此译法。
⑧ 《老年学概论》一书采用的是“老年亚文化理论”,叶肃科译为“次文化理论”,参见叶肃科:〈社会老年学理论与福利政策应用〉,《东吴社会学报》第9期,2000年5月,第77-122页。文章采叶肃科的译法。
⑨ 邬沧萍、姜向群译为“相互作用理论”,叶肃科译为“交换理论”,参见叶肃科:〈社会老年学理论与福利政策应用〉,《东吴社会学报》第9期,2000年5月,第77-122页。此译法简单明了,故采此译法。
⑩ 此处所探讨的先秦儒学,相关经典有《论语》、《孟子》、《荀子》、《礼记》、《大戴礼记》。其中,《礼记》、《大戴礼记》虽为汉代戴德、戴圣所辑,然各篇内容却可上溯自先秦,故亦将这两部经典列入。
11孔疏云:“大夫得専事其官政,故曰‘服官政’也。”
12孔子尝曰:“志于道”,参见《论语·述而》。
13《论语·子罕》:“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闻,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14《论语·泰伯》:“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15《论语·泰伯》:“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笑;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1]孙得雄.一起面对高龄化的台湾[J].健康世界,2011,(431).
[2]梅陈玉婵等.老年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邬沧萍、姜向群主编.老年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顾东辉.社会工作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254.
[5]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
[6]艾瑞克·艾瑞克森(Erik H.Erikson),琼·艾瑞克森(Joan M. Erikson)等.Erikson老年研究报告—人生八大阶段[M].周怜利译.台北: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
[7]西塞罗.论老年、论友谊、论责任[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8]马克·艾格洛宁(Marc E.Agronin).生命永不落:一个心理医师追寻老化意义的旅程[M].陈秋萍译.台北:远流出版社,2012.
[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
[10]王先谦.荀子集解[M].台北:华正书局,1988.
【责任编辑:向博】
The Confucianism and Its Viewpoint on Senior Citizens
YANG Zi-p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The Central University of Tai Wan,Tai Wan,Zhongli)
Seeing that the western theories about senior citizens have their limitations and the Confucianism’s interpretation mainly focus on filial piety and provision for the old age,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to find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imitations of contemporary theories about senior citizens and to construct the viewpoint of senior citizens of Confucianism through dialogue so that some suggestions can be offered to the theories on senior citizens and how Confucianism deals with the issues of senior citizens may be highly focused.Confucianism’s viewpoint of senior citizens inspires us to truly realize the physical limitations of the elderly people,and to guide them to behave themselves in accordance with moral rules,showing the values of their lives.In addition,these viewpoints also point out some solutions to problems younger generation will possibly encounter in their old age. Such inspirations are as follows:First,be aware of your original self and respect your parents and other elderly people.Second,study harder and modify your behavior and mental status.Third,be brave enough and never be worried about the old age no matter how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feeble you will be in the future.Last but not least,one has to constantly live up to moral self-awareness and make it his/her lifelong mission.Proper understanding and positive ways of modifying one’s mental status and behavior toward one’s old age should be something that Confucianists have left for us to value modern-day theories on senior citizens.
Confucianism;Theory on Senior Citizens;Old Age;Being Aging Population;Confucius
B 22
A
1000-260X(2014)06-0046-08
2014-10-10
杨自平,中国文学博士,台湾中央大学教授,《当代儒学研究》杂志主编、《中央大学人文学报》杂志副主编,主要从事易学、中国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