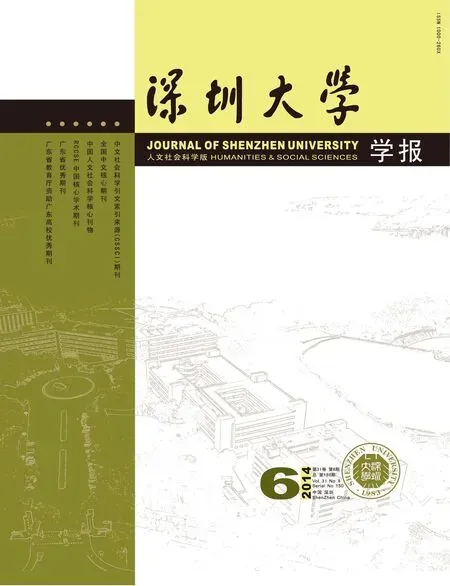比较康德的德福一致论与孔子的天命观
杨祖汉(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台湾 中坜)
当代儒学研究
比较康德的德福一致论与孔子的天命观
杨祖汉
(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台湾 中坜)
编者按:当代儒学研究正朝向“在地化”与“全球化”的两个维度不断延伸与拓展,引发出许许多多的值得关注与探讨的问题与丰富内容。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儒学”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全球的”。今天和未来,儒学将以和以往不同的方式与形式在国内与国际的学术、文化,乃至政治舞台上扮演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海峡两岸学界对此均高度重视。今年,中国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圆满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空前隆重的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的盛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开幕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举世瞩目,引起极大的热烈反响;而自2012-2014年三年以来,台湾中央大学儒学研究中心连续三届成功举办“当代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儒学之国际展望”国际学术会议,取得了重要的丰厚的学术成果。本刊此期“当代儒学研究”以及“特稿”专栏,分别刊发戴琏璋先生、杨祖汉先生和杨自平先生于今年召开的“第三届当代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儒学之国际展望”上发表的三篇颇具特色与价值的论文,同时刊出韩敬先生在耄耋之年关注“儒学热”,有感而发,并赐稿本刊的大作,以飨读者。
敬请垂注!
对于孔子所说的“五十而知天命”的诠释,两千年来没有确解。朱子对孔子“四十”与“五十”生命境界的所以不同的批注,说明了朱子之说是要从道德的当然之理进至所以当然的存有论之理。此即要从道德实践所理解的道德原则来说明存在界,这便关涉到个人的道德实践是否得到合理的回应之问题。借着康德所说的“德福一致”是实践理性的必然对象或目的,而此虽然也可以作为行动的意志的根据,但与道德法则作为实践行动的意志的决定根据,意义有所不同之论,可以比较出孔子与康德对于行义是否必然有合理的结果,此一问题上见解的同异。从孔子的自信“天生德于予”之说,可证践德者会有自己的实践行动必能带出合理的结果的肯定,但此一必然的肯定是属于宗教性的信仰上的必然,不同于以道德法则决定意志之为必然。这两个层次的必然性,是可以区分的,从孔子对于道之将行将废都视之为命,而在明知道不能行,仍要以出仕为义,而不可违反,可说明此意。
孔子;朱子;康德;德福一致;知天命
一、引 言
孔子对天命有甚深的体会与敬畏,言“畏天命”,而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之自述语,一般都认为是孔子德性生命或智慧的生命的发展的重要关键。对于何谓“知天命”,是历代儒者都苦心研究的问题,也未有一个大家皆同意的定论①。我在“当代儒学对孔子天论的诠释”②文中,对当代钱穆、徐复观、劳思光及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的讲法有一些讨论,最近为学生导读康德《实践理性批判》,觉得康德在讨论德福一致是实践理性的必然对象,但又不能作为行动的格准之义,可借以解释孔子知天命的一些涵义。即康德认为有德者必有福,是合理的想法,但人的实践道德,并不能以追求德福一致作为目的,因为实践道德是行所当行的事情,不能有所为而为。虽然吾人不能为了实现德福一致而实践道德,但在从事德性实践,即在按无条件的律令而行时,又必以德福一致为必须实现的理想,此中的分析十分细微,康德此一区分似可以表达孔子在行道时,相信天命在我,上天一定借着孔子而行道,即是说孔子对于他的行道是有信心的。但虽如此,他对于道的终究能行或不能行于天下,都能够接受,而认为不论成败,都是天命所在。孔子在这里也表达了相信道一定能大行,个人的德福也一定相应,但人不能以道一定能行或德福一致作为道德行为的根据或目的,故行道的结果如何人都可以接受。本文希望借康德之说对孔子的天命观做一探索,并比较二者的异同。
二、朱子论孔子四十与五十生命境界之不同及其涵义
朱子在批注“吾十有五志于学”章中的“四十而不惑”句处,曰:
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则知之明而无所事守矣。[1]
朱子之意认为孔子四十岁时,对于事物的当然之理,即道德之理,都能无所疑惑,故道德实践已达仁精义熟的地步,不需勉强持守。在“五十而知天命”处,朱子注曰: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是物所以当然之故也。知此则知极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1]
这是说孔子在五十岁时,对于当然之理的“所以然”,能够深切了解。朱子此注语意涵知天命,是知达到“极其精”的地步,由此极精之知,而起真实行。依朱子所谓“所以当然之故”,是“天道流行而赋于万物者”,即是说人间伦常事物所表现的道德当然之理,是天道流行,使万物如此的,即万事万物所以都表现出道德之理,是因为天道、天命使之如此,这是对道德之理给出了存有论的说明,认为人生伦常所依据或人生所以能成为合理的存在,是由于道德之理。而这道德之理不只是人伦或人事之理,而又是天理,即此道德之理是天地间的恒常之理,是“存在之理”。朱子所谓的“所以然”是道德当然之理之所从出,他认为道德之理出于天道、天命,当然这样说,便涵道德之理即是存在之理之意,故吾人可以做上述的诠释。当然此说也涵因为道德之理是上天赋予于一切人物的,所以人需要实践道德之理,但此意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以存有之理,来说明道德之理,所谓“形而上学的道德学”或“宇宙论中心哲学”,若如此便是他律的伦理学。从朱子注孔子“四十”与“五十”的不同,是明白当然之理与所以当然之理的不同,可知依朱子,对于天道、天命这“所以然”的了解,是从道德的当然之理推上去来说的。这是从道德的实践来推形而上的天道,而不是由上而下,从天道来规定道德的当然之理。此当然之理,是人本知的,而且在伦常日用中常表现出来。而所以要从“当然”推到“所以当然”,是为了说明何以人间要表现或依循道德之理。人都感受到道德之理是人都应该遵守的,没有人可以例外,而为什么人会对道德之理有这种人人都必须如此遵守的感受呢?朱子从“当然”推至“所以当然”,便是要说明此一问题。他从人人都有必须遵循道德之理的感受或理解,而推至“这理便是天道之所在”。因此“当然而不容已”之道德之理,是有“所以然而不可易”③的天理作为根据的,道德之理也就是天理之所在,而由于有这一步的肯定,人就更能坚决的依循此理、按照此理而实践,而毫不摇动。
本来四十而不惑时已经可以按照道德之理来实践而不疑惑,而进至了解到此道德之理不只是人世间之理,又是天理之所在,是一切存在之所以能存在的根据,了解至此,则循此理而实践,便更不会有疑惑了。而此所谓“更不会有疑惑”之疑惑,不同于在人伦关系中,是否应实践道德之疑惑。此后一疑惑,在“四十而不惑”时就解决了。如果还有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则“五十而知天命”时,通过知天命而解决的疑难或问题,便不是四十时所面对的问题。我认为孔子四十而不惑已经完全了解人间伦常所要表现的道德实践,即对于人生伦常之理已经透彻了解,但作为一个圣哲的生命,他的智慧并不能只考虑人间伦常的事情,而必涉及天地万物、往古来今的存在。即孔子的生命智慧一定要从人间的道德领域进至涵盖一切存在的存有论的思考,而知天命就是从现实人生的伦常的存在或有限的存在,进至包含一切存在的存有论的思考,亦可说是站在包含往古来今一切存在的角度下来思考人间的道德实践,站在此角度来思考道德实践,便会有人间的道德实践是否也符合使一切存在成其为存在的存在之理的问题。即站在天地的立场来看,人间的自觉实现道德、表现德性的价值是否有其绝对普遍性?是否具有无限的价值?如果可以这样理解知天命的意义,则孔子的五十知天命是表征他从有限的人生界跨出去,而体会超越的、无限的领域与意义的一大步。故如果说四十而不惑还不是究竟的人生境界,必须继续往前发展,则五十所要克服或消解的疑惑,应是应然的道德之理是否符合一切存在所以能存在的存在之理。这即是问一切存在、一切人、一切事,是否真的依循道德法则而存在?按朱子之意,通过格物穷理的工夫,是可以从人世间的道德之理推到太极之理的,太极含种种人伦道德之理,所谓太极含万理。又既然说是太极之理,则太极之理当然就是使天地万物能够存在,或使一切存在维持生生不已地存在的根据,如果能够从当然之理推至太极之理,明白到当然之理就是所以然的天理,则人的按照自己理性给出的道德法则而实践的事情,就会有充分的、不会动摇的信心;因为假如吾人所据以实践的道德之理,虽然是人所知的伦常之理,但又不只是人之理,而为天地之理,则人在伦常生活中是实践使一切存在能成其为存在,又维持天地生化,使一切存在能生生不已地继续存在之理,则人在实践道德时,不管发生怎样的情况、后果,都不足以动摇人践德的决心。我认为这就是程伊川与朱子提倡格物穷理,以此为内圣学的关键工夫的理由所在。此中“所以然”是以“所当然而不容已”为根据而推上去的,故此从“然”推“所以然”,并非从泛说的事物之然处来推,而是从伦常日用中、人所共知的孝悌慈处推其所以然④。故此从然推所以然是有对道德之理的一般理解来作根据的,是从常知推至真知。如程伊川谈虎色变的例子所表达之意,亦即朱子注语“知此是知极其精”之意。而此从常知到真知,从所当然到所以当然的发展,对于人的道德实践是必要的工夫⑤。
以上藉朱子对孔子四十与五十人生境界的不同之诠释,来说明孔子五十知天命时,所解决的问题,是人生必须依据的伦常道德之理,是否就是使一切存在得以存在的天理。而如果了解了道德之理就是天理的话,则人就更能遵循道德之理而不会有疑惑。此一说法函蕴了人的按照应然的道德之理而实践,是否在现实的世界能有相应合理的结果产生的问题。而此一问题应该是每一个要求自己依理而行,从事无条件地实践的人一定会产生的问题。此一问题是如此:人当然是要按照道德而实践的,如为父当慈、为子当孝,而且人的实践这些道德行为并不因为这些行为可以使吾人能得到现实上的好处,所以要去行,而是只因为这样去行,是吾人认为我应该行之故而行,而且吾人认为这些行为是人人都当行的行为,人只能因为道德行为是人所当行、谁也不能例外的缘故而行,除此缘故外,不能为了其他。这是康德所谓的道德行为是按照无条件地律令而行的行为,而且道德行为不只是行为的外表符合义务,而是为了义务而行的行为之意,此一对道德行为的规定或了解,人只要稍一反省自己行为的存心,就可以知道,此所谓常知。对道德的常知人人都有,谁都不能说自己对道德行为是什么一无所知,人也不能够说只有他真正懂得什么是道德行为,如康德所说,在道德此一事情上,人不能提出什么新的东西来⑥,但此一为人人所共知的道德行为的意义,并不保证人可以真正实践出道德行为。由于人有感性的欲求,往往会在要做出道德行为时,迁就感性欲望的要求,而希望借着善行来得点好处,此希望得点好处便是顺从感性欲望的要求,而使得无条件地实践成为有条件的行为,即成为为了达到另一目的而做出道德行为。这种存心的滑转,好比是朱子所说的人心与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2]由于这种天人交战,是人在要求自己做真正的道德实践时都会产生的,故人要贯彻落实道德行为,便必须要克服这种普遍的生命问题。上述朱子与伊川要从“常知”进到“真知”,从“当然而不容已”之理,进至此理为“所以然而不可易”,应可以从克服此生命问题而给出的工夫来了解。这是将理从道德之理了解为天地之理,以克服人对依此理而实践时,所产生的何以一方面实践道德,另一方面又借此实践而要得到感性上的满足的要求之问题。人如果知道这种无条件的实践正是天理之所在,便不会有借此理而得满足感性的要求之想法,因为此理就是天理,本身就具有无可比拟的绝对的价值。若想借此实践行为而获得其他的好处,就会使此行为本有的绝对价值降而为相对的价值,这是得不偿失的。故越明此义,便越不会受到感性欲望(人心)的要求而造成行为的动机(存心)的滑转。
另一方面,如果坚信道德之理就是存在之理,则人虽然不是按照现实存在的实然情况去从事行动,但由于实践道德是按照理所当然而实践,而此理所当然是人人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于是此一存心所遵守的,如同康德所说的,是普遍的、形式的法则,是不能有任何个别、特殊的内容在其中的。比如说:人的言而有信,只因为守信是人人都应该行的,不能因为任何各别的理由而守信,故人的实践道德,必须一空依傍,把一切个别的、有内容的想法都抽掉,不能为任何别的理由,只能为如此做是人人都该做的,即只能依照依形式的普遍性,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故按理而行之理必须是普遍之理之形式,不能有任何材质在其中。若有任何材质在其中,便不能具有普遍性。人的行动之存心,假如只因为此形式的普遍性而行,才可以说是道德的行为,则道德的行为必须是在行为的存心只受形式的普遍性所决定时,才算是道德的行为,而人的行动的存心竟然可以只受形式的、可普遍的法则所决定,这是相当难以理解的,在此形式的普遍性,或形式的普遍的法则的决定下,可以使人给出行动,这是难以解释的。人一般的行动都是有所为而为的,而此无条件的律令以形式的普遍性来对人的存心做出决定,要人只能因为要作出的行动是人人都该行的,只因此之故而行动,道德法则只以理的缘故而给出决定,它不需要对人的感性欲求给出任何承诺,也不须答应人以求幸福为目的之任何想法,而若一旦有其他的承诺,则此行动的动力就不是因为理的缘故,即并不是出于义务,不是为了义务而行,那就不算是道德行为。此抽掉一切各别的想法或内容,只剩下空洞的、形式的普遍性之理,似乎是不能引发人去行动的,但如果道德行为的动力不是只因为此理是当然的、人人都该行的、形式的、普遍的理所引发,就不算是真正的道德行为的动力,故如果世间真有道德行为,则纯理或纯形式的道德之理本身就足以给出道德行动的动力。如果纯理不能给出动力,则世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行为产生。如果一旦了解道德之理之为无条件的律令,且是形式的、无内容之理,只因理本身,不需其他作用支持,便足以决定人之意志,而给出行动,而此时吾人的意志就表现为纯粹的善的意志、自由意志,愈了解此义,便愈有实践的力量产生,若果是如此,则知理或“真知理”便可引发行动实践之动力,而此理的是否能活动并不是问题所在。此一义一定要成立,这是从道德行为的本质定义就可以推出的义理,当然何以纯理或抽掉一切其他动机的理所当然,会引发如此纯粹的道德实践的动力呢?这也是难以说明的,虽难以说明,但乃是理当如此的。
上说之意或可如此解说:当人在深知道德行动所根据的道德之理是当然的、普遍地为人所遵守的,即乃是一“理所当然”时,便会愿意朝着此当然之理而遵行之,当人发现此是一当然之理时,不能不有愿意循之而行的要求,如果没有这个要求,便是反对或忽略此当然之理,反对当然之理就等于是反对自己的理性,因为理所当然就是理性所肯定必须如此的,反对之就等于反对理性自己,如是人便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这应该是上文所说的,越了解道德之理,越会引发实践的动力的缘故。依康德,这是法则与自由之互相涵蕴(见康德《实践理性底批判》第一章定理三、问题二之注说)。即从对于道德之行动必须是无条件的实践之事,由此了解,便会肯定人必须有完全为道德法则所决定之意志之存在,方可有真正之道德实践,于是纯善的意志,即只依理性给出的无条件地该行而行之法则而行的自由意志,便一定要为吾人所有,故对道德的理解便涵对人有自由意志之肯定,而此肯定亦必涵人自己必须依理而行,必须呈现其自由意志之要求,如是便往使自己之意志成为纯善的自由意志处努力,如是便会给出依道德法则而行的动力。可以说,这是由对法则之了解而产生实践的动力。
上文是说真正的道德实践不会考虑到任何现实上的利害,践德之人的存心只因为理所当然之故而实践,不会有其他想法,如此才能说他的存心是被形式的、普遍的法则所决定。如果他的行动的存心有一丝为了其他的目的而行的想法,他的行为就不能够有道德价值,这个道理人稍加反省也都可以知道,并不难解。但也由此而会产生极大的困惑。道德实践不是为了行为的结果的有利而决定去行。但在给出真正的道德实践时,也必会预期有合理的结果,即相应于道德实践而来的结果产生。虽然践德者不会考虑行动的结果是否有利,但由于道德实践是按照一形式的普遍的法则而行,据上文的分析,此按照普遍的形式的法则而行,是行人人都当行的事情,而此一行动实践,是理性认为最合理的,而此种最为合理的行动,当该产生合理的结果,如果人从事理性认为最为合理的行动,而结果却产生不合理的情况,那就很不可理解了,对于此人是不能接受的。故在人按照无条件律令而行,为义务而实践义务时,虽完全不考虑行为的结果,但也一定预期或相信在这种行动实践下,一定会有合理的后果产生,这便产生了道德实践的一大困惑。因为按照当然之理而实践的人,虽不会以行动的结果之预估来决定行动的存心,即不会考虑现实上的情况是否会因着行所当然的行为而产生合理的改变,才去行动,但他又预期现实的世界会因为自己的实践行动而有合理的结果,而且道德行动所依据的是人的理性所给出的道德法则,此法则是以自由为特性的,并不按照经验自然的情况而给出决定。此以自由为特性的按法则而来的行动,应该与现实的经验的自然的存在情况不能一致,因为现实的经验的自然之存在情况,所依据的是自然的法则,或机械性的法则,并不是由人的理性所自发的、自由的原则,如果人的道德实践与现实的经验自然的情况有自由与自然的不同,则如何可说,人从事道德实践时,现实的经验情况会相应产生合理的后果呢?但据上文所说,人在从事道德实践而完全给形式的法则所决定,只问行为是否为行所当行,不会有其他想法时,却预期现实的世界会产生相应合理的后果,这便是人的理性从事实践时,会产生的不可解的困惑。当然从事道德实践时也需要经验知识,但经验知识是为了如何把道德行为具体实现出来,而并非由经验知识来决定人的行动实践的存心或意志,人的道德行动的存心必须由自发而无条件的行所当行的理性判断所决定。故道德行动虽然需要经验知识的辅助,但并不以此就可说道德行动会使现实的经验界产生符合道德实践要求的后果。又人的践德只受理性所给出的、人当该做人人都需做的行动之命令来决定,不能借此行动来满足他的感官的需要,如果是如此,则现实世界的存在,便不会按照我们的道德行动而产和适合我们感官的情况。因为如上文所说,现实世界的存在所以依循的是自然的、经验的法则,用宋儒的话此是气化之事,而道德行为所依据的并非气化的原理。如果是这样,则由应然之理给出的道德行动,是不能与根据实然的气化的原则而活动变化者相应的,若是如此,如何能说明当然之理就是所以然之理呢?故程朱提倡格物穷理,希望从事物的存在之然处,了解到都是当然之理的呈现,或证明吾人内心不容已要实践的孝悌慈的道理,也就是天地万物所以能存在的道理,这种说明或证悟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应然者是否为实然者的问题。
如何冲破这应然与实然的鸿沟,是一重大问题。此问题除了是应然与实然的区别外,还有一更深微的心理疑问需要解决,此一疑问可借用钱穆先生的话来说:“何以当然者而竟不可通?何以不可通而仍属当然?其义难知。”[3]钱先生这一诘问很有深意。一般认为当然者,一定有此当然者必能实现的想法,如果不能实现的,就不能叫做当然。道德上的当然的行为如上文所说是按照人人都当如此行,即按照一普遍的形式之理而行动,而不能有别的动机,当人如此的行动时,很自然会认为自己所做的是理当如此的行动,而理当如此的行动当然一定是现实上人人都会如此做的行动,我只是做人人都会如此做的行动而已,既然所做的是人人都该如此做的行动,则此行动又怎么会不能产生符合道德实践的要求之现实情况呢?或可说此一行动怎么会不为多数人所接受呢?此一感受或要求,是从道德行动所具有的普遍性而逼出来的要求,而此普遍性不靠从现实上要求每一个人同意而给出,乃是人从反省自己、慎独,要求自己存天理而去人欲,遵从无条件的律令而行动,而产生出来的普遍性要求。这也是儒学以“为己之学”,或“反己之学”为特性之缘故,越能反求诸己,越能体会到人本有的本性、本心是可以给出普遍的决定的,而此本性本心既然能如此的给出普遍的决定,那一定也就是天理所在。故人若如孔子般诚心诚意的修己以安人,求行道于天下,怎么可能会有道不能行的现实情况呢?但事实上确常有道不能行的情况。这便造成了践德者心中的大困惑。此困惑便是人在行所当行时,一定会肯定此时所行的,就是普天下最合理的事情,故行道者一定会有道借着我的努力而大行的信心,如果没有这种信心,可以说就不算是行道。在按照普遍的法则去行道时,等于是按照普遍的意志去行动,既然行动是按照普遍的意志而行,则必定有此行动是一切人都会接受的信念,但现实上往往事与愿违,何以故会如此呢?在现实上,行道居然会事与愿违时,这是践德之人一定会产生的困惑的。进一步说,虽然了解行道而不一定能通,但自己仍然要去行道,这也是践德者会有的感受与决心,用孔子的言论来说,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或云:“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⑦这种明知道不能行而仍然要尽当行之义,正是真正的行道者所该有的态度,但这种行道的人该有的态度或想法,又如何可能,如何才能清楚解释呢?据上文所说,从事道德实践是做自己认为所有人都该做的事情,于是此时一定会有我的道德行为必有合理的结果产生的预期或信念,但当面临现实的情况,居然与上述的预期不符甚至相反的时候,何以自己不会产生沮丧、绝望的心理,反而仍然无条件的实践下去?这需要做进一步的探索。
对于道的能大行,或不能大行的现实,人是可以接受的。虽然人可以接受道之有不能行的可能,但仍然无条件的去行道,而且是带着道一定能行的信心去行道,这是孔子所说的知天命,或“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之意,这种错综复杂的感受,我想用康德所说的德福一致论中德与福的关系给出一些说明。康德认为德福一致是理性的实践的使用时所要求实现的理想,即是说当人从事无条件的,按义务而行的行为时,会有有德者必有福气的想法,人的道德实践虽然是无条件的,但也因为能按照无条件的律令而行动的人,就是最值得有幸福的人,故有德者必须有福,如果有德者无福,这个世界的存在就很不合理了,上帝为何要造这个不合理的世界呢?又为何要让这个世界继续存在呢?是故德福一致必须实现。依康德,为了达成有德者必有福的实践理性的必然要求,必须肯定上帝的存在。虽然人的践德不考虑现实世间是如何,不会按照何种行动会产生于己有利来给出行动,但正因为人能有无条件的实践而纯粹的存心,他就值得有福,上帝会按照他的存心,而给出他应得的幸福。这种说法虽然吊诡,但也是合理的。于是越不为了现实的幸福去行,越值得有福。当然,虽然值得有福,但完全不能为了最终是会有福,而去践德,如果有此存心就不值得有福了。虽然不能有此存心,即不能为了有福而去践德,践德之时必须只因为人人该如此行而行,即只能为普遍的形式的法则所决定。但此时人又可以有能无条件的实践者值得有福的期望,此德福一致的理想不能是道德行动的存心,但可以是人在践德时的期盼。此中甚有玄义可说。
三、康德的德福一致说之涵义
康德认为德福一致是实践理性的必然要求实践的对象(康德《实践理性底批判》卷二,〈纯粹实践理性底辩证〉),一个公正的人必希望有德者得到幸福,即幸福是有德者该得的,虽然有德者并不以幸福的得到作为行德的条件,有德者主观上不求幸福,但在客观上有德者值得有幸福,如果值得有幸福者却得不到幸福,这样子的存在的世界,乃是不合理的,是故,德福一致是实践理性必然要求的理想。由于德福一致是实践理性一定要求实现的理想或必然的对象,要达致这一定要实现的理想之要求,便非要有上帝的存在不可,因为现实世界或经验世界服从的是自然的原则,而有德者按照无条件律性而行,所服从的是自由的原则,有德者的道德行动不能受任何现实的情况影响,不能因为他的实然的生命的欲求而去服膺义务,如果是这种情况,他所做的义务性的行为,并非道德行为,他必须是为了义务而行,而不受任何其他现实、感性欲望的影响而行动,才是道德行为,是故有德者的生命活动,如上文所述是服从自由的原则,而自由的原则与自然的原则是截然不同的,那么由服从自由的原则,自由自决的行动的人,他给出来的行为,应该与服从自然原则的现实世界的变化不同,他不会为了达成他的个人幸福而去行动,他只能为了应该行而行,若是这样,这两套以不同的原则作为根据的情况,怎么能合在一起呢?如果没有第三者把服从自由自决的有德者的心意与服从自然原则的现实气化的世界的情况关联在一起,而使彼此相应,使越有德的人他的现实遭遇越能顺遂,那么德福一致就不可能产生了,故由此康德便论证上帝存在非肯定不可。
本文不讨论上帝存在是否有必要,而是要说明,从康德上面的论证中可以体会到德福一致是人在实践道德实践时,一定会产生的理想。本文所注重的是此一义理。我认为孔子在努力行道时,他也一定会有道必定能行,而他这个行道者一定会有合理的遭遇产生的认定,故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又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在这些情况下,孔子肯定了自己作为一个有德者,一定会有合理的情况从内心的纯德带出来,是故,他个人的遭遇一定不会太不合理;人可质疑孔子在这种危险、随时都可能死于非命的情况下,他的信心是没有根据的;但我认为这是至德或纯德者一定会从内心流露出来的一种肯定,在此感受下,孔子也未尝没有与超越者相感通之意,而此超越者亦未尝不可以人格神以表示之,如牟先生所云之超越的遥契。[4]孔子这种肯定是很有根据的,这是纯德者对于有德必有福的当下肯定,也就是对于存在的世界是一个合理的世界的肯定。这种肯定如同康德所说的德福一致是理性的实践的必然的对象。进一步,虽然人在纯德的境界下,对于德福一致的实现有直接的肯定与相信,但并不以此一理想的实现作为行动的条件,即是说,这一理想虽然是践德的人必然会产生的相信或信念,但人的实践道德或义务,并不以为了实现此理想为行动的条件,道德的行动应该还是无条件的,虽然是那么正大的德福一致的理想,也不能作为道德行动的决定根据。关于此义,可引康德一段话来说明:
道德法则是一纯粹意志底唯一决定原则。但是因为道德法则只是形式的(即由于只规定格言之形式为普遍地立法的而为形式的),所以它作为一决定原则须抽掉一切材料,即是说,抽掉作意底每一对象。因此,虽然最高善可以是一纯粹实践理性底全部对象,即是说,是一纯粹意志底全部对象,但是它却并不因此之故而即可被看成是意志底决定原则;单只是道德法则才必须被看成是原则,基于此原则,最高善以及最高善之实现或促进才是所属望或所意在者。……这一解说(或提醒)是重要的,即在如“道德原则底规定”这样一种精致微妙之情形中而为重要的,在道德原则底规定处,些微的误解即足以颠倒了人的心灵。因为从分析部所说,我们已知:如果我们在善之名下,认定任何对象为意志底决定原则以先于道德法则,并因此,从这对象中而推演出最高的实践原则,则这必总是引出他律,而毁灭了道德原则。[5]
康德此段说明最高善(德福一致)虽然是实践理性的必然对象,但并不是决定意志的原则,因为如果行动是道德的行动,则决定此行动的意志的原则只能是纯粹的道德法则,而道德法则是没有材质内容的,只有要求行动的格准能同时是一普遍的法则,即只要求行动的主观原则,可以普遍化。此外别无其他。于是人要做的是把个人的特殊的想法抽掉,只因为人人都该如此行而行动。这一作法如果依宋儒的观念来说,就是“存天理,去人欲”。故决定道德行动的意志只能是天理,而在天理中,只有普遍性的形式,而没有任何内容。德福一致虽然涵有道德法则在其中,但由于有幸福作为其内容,故并非纯粹的普遍的形式之理,于是德福一致虽然是人在从事无条件实践时,会产生的理想,但并不能以实现此理想为目的,去从事道德实践。康德在此处的区分十分精微,他说如果在此处有稍微的误解,便会产生他律的行为,即是说,如果我们为了实现德福一致而去从事道德行为,就是他律的行为。虽然德福一致是我们的理性所肯定合理的、应该实现的事情,但我们也不能把德福一致作为行动的目的,为了实现此目的,而去从事道德行为。康德此一区分,正好说明了孔子不许可子贡以“博施济众”为仁之故,“博施济众”是仁者所一定要求实现的理想,但你不能说我为了实现“博施济众”而去行仁,行仁义是出于无条件为善的存心,并非先有一个既定的目标(如至善),而照着这个目标如何能实现来去作为,依此义,道德行为是行所当行,可说是当下即是的,行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以此行为来达到某一伟大的成效或目的,道德的行为不需要因为达到何种的有价值的成效才能是道德行为。
当然,德福一致虽然不能是决定我们道德行为的原则,但乃是我们按照无条件律令而给出道德行为时,一定会产生的合理的期待,甚至是必然的期待。固然道德行为不因为有任何实质上的目的可被达到而为,但践德之时就必然会产生这种德福一致的期待,幸福与道德法则的结合是有必然性的[5] (P407),这种必然性应该是实践的必然性,此二概念并非是分析的,而是综合的,但康德认为有德者必有福,是实践理性的必然对象,由此而言二者有必然的关联性。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人真正从事无条件的实践时,内心自然会产生践德一定有合理的结果的想法,所以会如此想,因为在践德时会认为存在界是以道德原则来作根据的,此如上文朱子所认为的,从当然之不容已推上去,便会了解所以当然,而此便是天命的意义。即是说,若是真正有践德的体验,便自然会肯定道德的原理就是存在的原理,存在界是由道德之理所决定的。既然存在之理即是道德之理,则吾人按照纯粹的道德法则而行动时,一定会有合理的遭遇产生,故就个人来说,就会有德福一致的期待。这也是上文所说,孔子所以会有“天生德于予”、“天之未丧斯文也”的感受之故。孔子这些话,既肯定了道德的法则就是存在的法则,也有我既践德则上天一定不会给我不合理的遭遇的信念与期盼,这里践德与合理的遭遇,在实践道德的要求下或感受下,是有必然的关联性的,此所谓实践的必然性⑧,此中虽然要清楚辨明道德行动不能以带有实质目的的理想为决定意志的原则,但人一旦为无条件的道德法则所决定而去行动时,也一定会产生最高善(德福一致)这种理想一定要实现的想法,康德续云:
但是,如果最高善之概念包含道德法则之概念以为其最高的条件,则最高善必不只是一个对象,而它底概念以及它存在底观念,由于因着我们自己的实践理性而为可能者,必同样亦是意志底决定原则,这一义亦是显明的。因为在那种情形中,意志,如自律原则所要求者,事实上实为那“早已含于这概念(最高善之概念)中”的道德法则所决定,而并不是为任何其他对象所决定。“意志底决定”底概念底这种次序决不可忽略,因为若非然者,则我们将误解我们自己,而且以为我们已陷于一种矛盾中,当每一东西实处于圆满谐和中时。[5](P401)
康德此段说虽然德福一致不等于道德法则,因为其中含有幸福,但由于德福一致中有道德法则,而且幸福是由决定意志的道德法则所带出的,于是德福一致也有其必然性,他认为如果事物是存在圆满谐和中时,则实践道德一定会有德福一致的后果,由于是如此,德福一致这最高善,亦同样是决定意志的原则,按康德此说与上文不一致⑨。虽然康德在此段中仍强调决定意志者是道德法则,但既说最高善是决定意志的原则,便不同于只以道德法则为决定意志的原则。康德在后文便说:“如果最高善不是因着实践规律而为可能的,则 ‘命令着我们去促进最高善’的那道德法则必亦被引致徒然无益的空想的目的,因而结果亦必须是假的。”[5](P408)按康德这个说法,亦似乎太强,好像跟前面所说的决定道德行动的原则,只能是普遍的、形式的道德原则之义不同,此处好像说德福一致一定要从道德行动中带出来,如果德福一致不能实现,则吾人依理性而给出来决定意志的道德法则,便是虚假的,于是道德法则之真实性,需要德福一致的实现来证实,而如果德福一致不能实现,人对于道德法则就可以有它不是真实的,可能只是我们的想象的怀疑。
康德此处所说,应比不上孔子的说法来得合理。按照孔子知天命之说,固然孔子有个人的遭遇一定不会不合理的自信,但孔子并没有道一定大行才是合理的或才是天命的想法。孔子当然希望道能大行,也相信自己的道德实践的行为,不会有不合理的结果,但不会因为他的行动是合理的行动,便认为道一定大行。故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对于道的将行将废,孔子都可以接受,这就不像康德所说的德福一致既为实践理性的必然对象,也就可以作为意志的决定原理。孔子不会以道之必行来决定他的行动的意志。孔子在行道、践仁时,确有受命于天,天命我行道的自信,如同上文康德所说的,最高善是实践理性的必然对象,但在现实世界中,是否可以因着孔子的努力,而一定实现此理想呢?在孔子则不管理想的是否能实现,都可以接受,这种态度比康德的想法松动一些,我认为这可能是更为合理的想法。在康德由于认为德福一致如果不能实现,则由于德福一致之福是与道德法则有必然的关联性的,则德福一致若不能实现,便会产生道德法则为假的后果,而在孔子虽有行道践仁而来的天命必在我的信心,但并不认为,他的行道一定会产生道必大行或他一定当王的后果(虽然后来《中庸》有“大德者必受命”之说,但孔子本人不一定有这种想法),孔子之所以既肯定天命在他,但又不必期盼道之大行,而以道之行与废皆是命,我们可以用最高善虽然是实践理性所必然要求、必然要实践的对象,但并非是决定我们从事道德行为时意志的原则之义来说明,即德福一致虽然是践德者必然的期盼,但践德者并不是为了此一目的才去从事道德实践。故对于康德从德福一致之为实践理性的必然对象,而说最高善也是决定意志的原则,最高善如果不能实现,则道德法则为假,则是吾人所不能同意的。
此中,相信天命在我或天生德于予,由此而肯定个人的遭遇一定平顺(德福一致)或相信道一定能大行,这是由实践而来的肯定,此肯定虽然有必然性,但并非对于实践的意志有必然的决定性,有践德的要求的人当然会认为道德实践有其必然性,人当该只以道德法则来决定行动的存心。道德法则决定人的意志是无例外地必然的,而德福一致虽然也因为有道德法则所带出来的必然要求,而有其必然性,但德福一致并非人在实践道德实的决定根据。如上文所述,如果人是为了实现德福一致之故而去实践道德,那这种为善便是他律的行为,而没有道德价值。故期望大行其道或德福一致,虽然是具有必然性的,但只是必然的期待,此期望的能否实现,并不影响按照无条件的律令而来的道德实践。于是这一种一定有福随同实践道德而来的必然的信念与期待,只是宗教性的事实,并非道德实践层次之事。从康德所说的德福一致并非道德实践的根据,可以划分道德实践上的必然与宗教信仰上的必然。由此可以理解孔子何以一方面肯定天命在我,一方面又可以接受道的行与废,认为这两种不同情况都可以视同天命而接受,甚至虽明知“道之不行”仍要尽君臣之义。孔子这一态度表示了无论如何,人都有其当行之义,此义务的服膺,并不受道之能行不能行之事实所影响。由此可证,将道德与宗教两个领域划分开来,而将知天命在我、道必通过孔子而大行的必然肯定视为信仰上的必然,而与道德义务的服膺之为被道德法则所必然决定的情况,做出区分,应该是合理的。在道德实践上,人的意志必须受无条件的律令所决定,在此层次上,不容许有例外,若有例外就不是道德行为的。而在践仁而达到知天的地步时,也必有天命在我、道由于我而大行的必然肯定,但这种由实践而来的宗教性的必然肯定,是可以容许有例外的。即使道不因此而大行也不会对天命产生怀疑,这应该便是孟子所说的“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之义。即既知天命在我,但又不以为天命所决定的合理的现实一定在我的行为遭遇上实现,或不因为行道而得不到合理的结果而怨天尤人。通过道德的实践,而有合理的现实会产生的期待,这期待的是否实现并不能影响道德的实践,而对于这种宗教层次上的期待,也只能在不断地道德实践的努力下来维持。
四、结 语
以上所说,我认为就是孔子所谓“知天命”的涵意,其中的义理条列如下:
(一)从道德实践而体会到人所依从的道德法则是无条件的,而此无条件的道德法则是没有任何个人特殊的想法在其内的。即人是依循普遍的形式之理而去行动,在此时人会感受到他决定去实践的意志是普遍的、人人都会决定如此去行的意志。由于在此时表现了行所当行的无条件的普遍意志,则人会认为此决定吾人去行动的道德之理就是使一切存在能成其为存在的存在之理。即是说人在真正实践道德或服膺义务时,会有当然之理就是所以然之理的肯定。
(二)由对道德之理就是存在之理的肯定,从事德性实践的人会产生自己的遭遇会与道德的行动相应的信心。如同康德所说的德福一致(最高善),幸福一定会随着践德而产生,能实践道德,则相应于道德而该有的幸福必然随德性而来。此中德福有必然的关联性,而这种德福一致的信念,也是践德者必然有的信念。这种德与福的必然联系与德福一致必然能实现的必然性,是从实践道德就可以分析出来的。当然这种必然是属于实践上的必然。
(三)践德者虽然对德福有必然的联系,德福一致必然实现是有信心的,这可以说是必然有的自信,对德福一致必然能实现的肯定,但这终究是一种实践而来的自信,这是属于宗教信仰的层次上的必然自信,与在道德实践上所肯定的无条件的律令一定要是意志的决定原则,这种必然性,是不同的。在道德实践上不能容许有不依道德法则的决定,如果有不依道德法则的决定而产生的行为,最多只有合法性,而绝没有道德性。故践德不能违反法则对意志的必然决定,但在德福一致的必求实现来说,这种实现的必然性由于是属于宗教信仰的层次,虽也有其必然性,但不同于道德实践上的必然性般不容许有违反,故虽然有德福一致必求实现的肯定或信念,而仍然可以接受德福不一致,或道不能大行的现实情况,不会因为德福一致不能实现,而怀疑道德义务是人所必须服膺的。孟子所说的“夭寿不贰”就是不因为个人遭遇的不合理,而对天命起怀疑之意。
(四)于是德福一致虽然是实践理性所必然要求实现的对象,但由于德福一致一时不能实现并不影响道德实践之事之为必然,故此二者虽然都有其必然性,但分属两个层次,不会产生冲突,即不会因为德福不一致而造成对道德法则起怀疑的结果。如果此说可通,则是否对德福一致如何可能,非要说明不可呢?是否可以让德福一致维持其作为一宗教信仰上的肯定,而不因为德福一致之不能有充分的说明,而影响到道德实践。于是不必因为德福一致的难以说明,便非要去给出一圆满的说明不可。幸福本来是有关于感性的事情,对于感性而言,那些遭遇或感受是幸福的,那些是不幸福的,是有一定的分别的。幸福固然不只是感性的事,而与人的知性、想象有关,但并不能完全脱离感性,而感性的苦乐感受,是有其定性的,不能有太大的、截然的不同。故幸福不能不包含由感性而来的愉悦、满足。如果为了说明德福一致之可能,而泯除了福与非福的分界,恐怕是有问题的。牟宗三先生思考圆善问题的解决之道,用天台圆教来说明圆善,即由于三千法都可以是佛法,于是不论圣、佛遭遇到的存在情况是那一种情况,都可以成为表现无限的意义之圣人境界或佛法身,这可以说任何法都是佛法,保住了人间一切差别法都可以成为圣、佛境界的说法。但一切遭遇可以是德的呈现,并不等于是福,因为福是有关存在的事,对此牟先生用王龙溪“四无说”所涵的心意知物浑然是一之义,来说明一切存在,在圣、佛的境界中,是随心而转的。既然一切法可以随心而转,则在圣、佛的境界中,他们所处的存在界,与他们内心无限之德,是浑然是一者,于是德之所在就是福之所在,故牟先生说:“德福一致浑圆事,何劳上帝作主张?”[6]牟先生的说法当然是十分精深玄奥的,但如上述幸福虽然不只是感性之事,但总有关于感性,既有关于感性,便不能以圣、佛的无限意义的境界来涵盖,感性上对于幸福与不幸福的情况,是有一定区别的,这种分别,恐怕不能由于达到圣、佛的境界而泯除。如果说由于达到了圣、佛的境界,于是圣、佛的感性都被转化了,在此时他所感受到的任何情况都是赏心乐事,都感到满足,这样说恐怕太神秘。故吾人主张,虽然德福一致(最高善或圆善)是实践理性的必然对象,即一定要实现的理想,但此必然要实现是在宗教信仰的层次上说的,既然是在信仰的层次上说,则不必在哲学思辨上一定要要求一个理性的说明或圆满的解答。
注:
① 徐复观先生认为对此问题,是“二千年无确解”,见徐复观:〈有关中国思想史中一个基题的考察〉,《新版学术与政治之间》(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页439。最近余英时教授在《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台北:联经出版社,2014年4月初版三刷)对孔子的知天命从“轴心突破”的观念来做诠释,引史证义,认为孔子对于“天”和“天命”抱着深挚的信仰,但却不把“天”当作人格神来看待。(页54)。其论与当代新儒家所强调的孔子的仁教的特殊意义(如牟宗三先生所说的“践仁以知天”)大略相似。
② 收入拙著:《当代儒学思辨录》(台北:鹅湖出版社,1998.11)。
③ 朱子《大学或问》:“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宋〕赵顺孙纂疏,黄坤整理:《大学纂疏中庸纂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页66。
④ 此意见朱子《中庸或问》。
⑤唐君毅先生认为朱子从当然之理来了契入天命,是很恰当的。但朱子对天命只理解为当然之理的本源,以此讲孔子之知天命,则只知得此所以然而已,外此则别无工夫可用。(《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一,1973年5月,新亚研究所,页115)唐先生认为在知天命后更有尽性的工夫可讲,故知天命并不只是知道当然之理出于天命而已。唐先生此义当然有深刻的哲学涵义,但我认为朱子此一对孔子知天命的诠释,是有从常知进至真知的发展者,此知当然之理乃是出于天,而且此理是使一切存在成其为存在之理之“真知”,使人能更无怀疑地从事道德实践,是非常重要的工夫。
⑥ 康德说:“有谁想去引出一新的道德原则,使其自己好像是此道德原则底第一发现者。”见康德《实践理性底批判?序言》,译文引用牟宗三先生译注:《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5册(台北:联经出版社,2003年,页145)。基督教的思想家鲁益士(C.S.Lewis)在其《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余也鲁译,香港海天书楼,1998年)书中也表示了对于道德律的存在,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他对道德律的理解也
B 22
A
1000-260X(2014)06-0036-10
2014-10-10
杨祖汉,著名学者,台湾中央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主要从事儒学和中国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