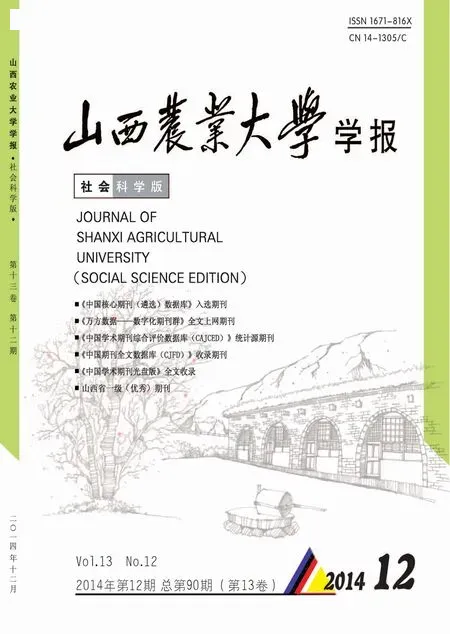译者中心论视角下的《活着》英译版对比研究
韩思宇
(北京邮电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876)
译者中心论视角下的《活着》英译版对比研究
韩思宇
(北京邮电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876)
在生态翻译理论中,以译者中心论为方法论去研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价值和作用。译者中心强调作为唯一主管因素的译者在适应与选择中的核心地位,以白睿文翻译的《活着》为例,在原文写作风格方面,他选择了尽可能继承余华先生的独特风格,多采用直译的方式处理特有名词的翻译,并且多使用简单词汇来保留余华先生朴实的叙述风格,而在中英文时态冲突的问题上,他抛弃了英文时态的丰富变化,用一种时态规避了与中文时态的不同步。然而,在专有名词和中国式叙述方面依然反映出白睿文先生明显的关于中国文化知识的不足。
生态翻译学;适应与选择;译者中心;语言冲突
生态翻译学是一种跨门类的交叉学科,它使用生态学的理论来研究翻译活动,以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为指导,重新解释了翻译活动。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1]其核心理论为“翻译适应选择论”,而译者作为整个翻译活动中唯一的主观因素,自然成为了翻译活动的核心,从而形成“译者中心论”。译者在理解和表达的过程中,其主体性得到了最大的发挥,他可以重新选择和表达的原著的文化立场、选择文本的意义、对原文的模糊信息进行定位创造。[2]这是译者的权力,也是对译者需要规范的地方。作为一种针对翻译过程的研究范式,生态翻译学将翻译活动视为一个完整的翻译生态环境,着重关注译者同翻译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这里所说的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3]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翻译作品也需要遵循“汰弱留强”“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只有适应整个环境的作品才能够长久留存,否则将会被淘汰。也就是说,整个翻译活动是以译者为中心的前提下,不断地适应与选择的过程。
中国当代小说具有比较鲜明的特色,放弃宏大叙事,注重从围观视角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并且在国外也有相当不错的口碑。余华先生的《活着》讲述了主人公福贵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一生,时间跨度非常大,作者通过讲述福贵一生的遭遇,反映了新旧社会交替的巨大变革,而且无论在人物刻画还是叙事上都达到了中国当代小说的高峰。《活着》的英译本是由美籍学者白睿文所译,它在美国出版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目前学界对于中国当代小说的译本的研究以及翻译方法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只能从个别案例中总结一些规律。因此我们把白睿文先生对《活着》的翻译放置在整个翻译生态环境中,用适应选择理论去解读他的翻译思路,这也是从这一个案中总结一些经验和不足,从而为中国当代小说的翻译工作体用一些素材。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就翻译主体而言,白睿文作为翻译过程中唯一的主观因素,总是在不断地寻求平衡点,他是翻译的中心和主体,他自身的文化、翻译水平决定着译本的生存能力。在后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白睿文个人独特的翻译方法以及他的局限性,而就翻译过程而言,鉴于中文和英文语言、文化的差距,也可以从白睿文翻译思路的角度逐个分析语言差异的多种处理方式,这也便于我们分析中国小说文化是如何与西方理念融合的。
一、运用短句、简单词汇继承原文朴实风格
翻译的成功与否,标准不仅仅在于是否讲清楚了故事,还包括有没有还原原文的特色和底蕴。一部能够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作品一定要能够尽可能完整的保留原文的特色和原作者的写作风格,否则就只能是用英文讲一个发生在中国的故事。白睿文先生在翻译《活着》的过程中,确实也在追求对原文风格继承的最大化。
(一)语言通俗简明
在《活着》中,白睿文准确地抓住了余华严谨又独具民族特色的写作风格,尽可能地重现了原文的独特魅力。以下是几段福贵和他父亲的对话。通过对中英文译本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白睿文对于余华原作风格的适应性。
ST1: 我爹三根指头执着一盏煤油灯从房里出来,灯光在他脸上一闪一闪,那张脸半明半暗,他弓着背咳嗽连连。爹坐下后问我:“债还清了?”
我低着头说:“还清了。”
我爹说:“这就好,这就好。”[4]
TT1: Holding the kerosene lamp with three fingers, Dad emerged from his room. The glow from the lamp danced upon his face, leaving it half illuminated and half cloaked in darkness. His back slumped over as he coughed incessantly. After sitting down he asked me, "Did you settle the debt?"
"It's settled."[5]
这部分主要讲述了福贵的父亲在听说福贵赌博输掉所有家产后的表现。在第一句话中,灯光效应非常重要,灯光很好地展现出当时昏暗又压抑的氛围。在白睿文的译本中,他使用了"dance"这个词,与原文中“一闪一闪”相呼应,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原文语调的适应。“还清了,就好,破了”这三个词在中文中本就非常通俗口语化,所以白睿文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也使用了一些简单词汇,如"settle, good, raw"来适应原文。余华在对话中喜欢用短句和平调来表达出福贵和他父亲沉重的心情。白睿文也试图通过短句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余华被许多文学批评家称作“中国的海明威”,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作品代表了当代中国的一大文学高峰,更由于其简明的写作风格,以至于“小学生都可以读懂”。
(二)句子细腻简短
余华擅长使用短句进行细节描写来表达人物的感情和性格,他很少使用形容词或副词,而是尽可能得将人物白描出来,而福贵是一个非常平凡,无需雕饰的老农形象,无论是他的语言还是动作,一定是朴实的,一定是没什么修饰的,这是余华风格与福贵特质的契合点,《活着》因此相得益彰。白睿文看到了这种相得益彰,他希望融入到这种和谐中,因此他试图用同样的方法来翻译,以保持原文的特色。如:
ST2: 我的腿马上就软了,站在那里哆嗦起来,我说:
“我只有一个儿子,求你行行好,救活他吧。”
医生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可他又说:
“你为什么只生一个儿子?”
这叫我怎么回答呢?我急了,问他:
“我儿子还活着吗?”
他摇摇头说:“死了。”
我一下子就看不见医生了,脑袋里黑乎乎一片,只有眼泪哗哗地掉出来……[4]
TT2: Immediately my legs went soft. Standing there trembling, I said, "I only have one son. I beg you, please, save my son."
The doctor nodded his head to let me know that he understood, but then he asked, "How come you only had one son?"
How was I supposed to answer this? I got anxious and asked him, "Is my son still alive?"
He shook his head and said, "He's dead."
Suddenly I could no longer see the doctor-my mind went blank and my head began to spin. All I felt were the tears pouring down my face.[5]
中国的小说家更喜欢通过对人物语言、动作的描述来暗示人物身份、性格以及心理活动,而不同于西方小说经常出现大段大段的心里描写,那种类似于上帝视角的呈现方式。因此中国小说的语言,尤其是描写动作、语言、神态的句子所表达的情感更为细腻和微妙。
一如前文所说,余华先生擅长这样的手法。就在前文截取的这个片段中,他使用了很多中文中口语化的,简单直白的词汇。如“活着,才,软了,哆嗦,行行好,知道了,急了,死了,黑乎乎”等。这种白描式的手法,非常细腻而真实地传达了福贵绝望、焦急和害怕的情绪。白睿文为最求同样的效果,彻底在译文中表达出这种情感,也用了一些很口语化的词汇,如"alive, before, soft, trembling, please, understood, anxious, dead, stiff"等。译文因此带有了浓厚的中国式乡土气息,一个活灵活现的几近绝望的中国老农形象跃然纸上。
二、遵循中文规则调和中英文冲突
生态翻译学认为在翻译过程中存在三个维度的适应选择,其中所谓交际维层面的选择适应就是原文要表达的目的在译文中得以实现。[1]中文与英文分属于不同的语系,无论在句法、时态、表达方式上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中文表达的目的要在英文中实现需要译者在句法、时态、表达方式的选择上找到平衡点。从英文版《活着》中我们可以看出,白睿文先生选择了遵循中文规则来调和中英文的冲突。
(一)寻找最恰当的方式表达“活着”原意
一般而言,中文语境中带有“着”字的词汇一般是表现正在进行的状态,“活着”可理解为“活”这种状态正在进行。但是当“活着”作为这部小说的题目时,则不能如此简单的理解其词义。余光中在谈翻译时,曾把翻译活动比作婚姻,它是一种两相妥协的艺术,面对翻译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译者不能做“忠实的仆人”,而应主动协调各种因素,化解矛盾。[6]
在《活着》英文版的序言中,余华曾说过,活着,是一个简单的短语,却包含着强大的力量。活着的力量来自忍耐。我们要忍耐生活给予我们的责任,忍耐快乐、悲伤、无聊和平庸。[5]原文中想要传达的哲学是生活中没有绝望。生命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活着”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状态描述,而是表达了一种态度,一种要活下去的态度,一种对生命的追求和不放弃。
与余华的生活哲学相对应,白睿文将标题《活着》翻译成"To Live"。白睿文说在他曾经想把小说的名字译为"Lifetime"。但事实上,"To Live"要比"Lifetimes"更加符合这部小说所要传达的哲学,因为"to live"是为了生存,挣扎求生的含义,他不是一种正在进行的状态,而是一种追求生命的态度。lifetimes则仅仅表示一生,甚至连状态的感觉都没能体现,而更没有生存艰难的含义。余华相信人们应该更多的关注生命的过程,以及最求生命,永不绝望的精神,因此英文小说的标题也最好刻意强调生命的不同寻常。"To Live"就非常恰当地传达出了这种精神。
(二)统一英文时态规避中英文时态冲突
白睿文认为,翻译过程中,最大的问题,莫过于中文的时态问题。在拉丁语系中,语言分为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这个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是中文中并非如此,中文是借助语境和功能性词汇来变现时态的。面对这一问题,白睿文在认真分析原文后,决定用固定时态,而不是完全遵照原文的经常变换的时态,以减轻读者的阅读障碍。试举一例:
ST3: 凤霞说起来又聋又哑,她也是女人,不会不知道男婚女嫁的事。村里每年都有嫁出去娶进来的,敲锣打鼓热闹一阵,到那时候凤霞握着锄头总要看得发呆。[4]
TT3: Fengxia may have been a deaf-mute, but she was still a woman, and she had to have known that it was only natural for men and women to get married eventually. Every year there were village women marrying out and other new brides who married in. During the excitement of the drums and gongs, Fengxia would always stand there holding on to her hoe as if in a trance.[5]
有庆死后,福贵和家珍决定为凤霞找个丈夫,替他们来照顾她。在第一句话中,余华的原文是用一般现在时,平和地叙述了凤霞的现状,但随着“到那时候”的出现,时态开始转换,从现在时转化到了过去时。但是在白睿文的译本中,我们可以发现整段的时态都是过去时,忽略了时态的转化。这是白睿文处理中英文时态冲突的方式,即统一时态,淡化时态转化。这实际上对原文的意思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反而通过这种方法使英文读者更易于理解,可读性大大加强,也就是说更适应了译文所处的生态环境。
(三)遵循中文的意合原则保留小说原味
中文和英文分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一个是汉藏语系而另外一个是印欧语系,其语法差异甚大。而中文和英文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句子的形合和意合。英语更加注重形合,它会使用适当的连接词,如介词、副词、连词和关系代词来连接不同的意群或句子成分,来达成一种相对严谨的句子结构。但中文却更加看重意合,中文不追求词句形式上的完整,而更注重语句之间内涵的衔接。相比较而言,意合的好处就是能够让读者更容易领会原文的意境。白睿文小心处理这种冲突,尽可能在词汇上保留原文内涵。
ST4: 仆人说着转身走去,这时候连长从腰里抽出手枪来,把胳膊端平了,闭上一只眼睛向走去的仆人瞄准。[4]
TT4: As the servant finished he turned around and left. The commander took his pistol from his holster, and, straightening his arm and closing one eye, took aim at the servant.[5]
原文中,仆人仅仅“转身走去”,并未使用任何的连接词汇,但是翻译成英文后,白睿文使用了两个连接词"as"和"and",这样会使阅读更加顺畅。
ST5: 以前我是过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整天有气无力,每天早晨醒来犯愁的就是这一天该怎么打发。[4]
TT5: I was like a monk caught up in his daily routine of ringing the bell, completely listless.[5]
在原文中,第一句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很明显这句话没有任何连接词,但是,译文中则不然,白睿文使用了"of"来连接"daily routine"和"ring the bell"。在这里,白睿文首先将中文意译成英文,在根据英文句法加入连词,以此解决中英文句法的冲突。
三、缺乏中国常识导致原文本义丧失
熟谙英汉两种文化,尤其是他们的差异能有效消除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避免带来不必要的冲突与误解,[7]这是对译者的要求。译者如果不熟悉两种文化,或对于特有词汇的涵义不去深究,往往会出现大的误解而影响翻译质量。《活着》是白睿文翻译的第一本小说,当时,他仅仅学习了中文四年,还有许多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常识没有了解和掌握。这种局限性是非常关键的,因为白睿文是翻译活动的核心,这种局限性将直接影响他对原文的理解和表达。从下面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式语言习惯掌握的不到位以及对中英文词义差异理解的不准确。
ST6: “福贵,我还能养活自己吗?”[4]
TT6: "Fugui, will you still be able to take care of yourself?"[5]
原文是福贵的妻子家珍在得了软骨病之后说对福贵说的话,她是在询问福贵她自己还能否养活自己 。但是,白睿文在翻译时把“我”翻成了"you",意思就变为“你(福贵)是否能养活你自己?”这是白睿文对原文意思的误解,他没能理清楚人称的指代,而这种误解大概也是由于中英文表达方式的不同造成的。
ST7: “毛主席万岁。”
几个戴红袖章的人冲上去对春生又打又踢,骂道:
“这是你喊的吗,他娘的走资派。”[4]
TT7: "Long live Chairman Mao!"
A couple of kids wearing red armbands rushed over to him. Kicking and hitting him, they cursed, "Was that you who yelled? You fucking capitalist roader!"[5]
第一句话是春生高喊出来的,他当时正被红卫兵批判。在中文中,“万岁”不仅仅有长寿的意思,同时也专用于中国古代的皇帝。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就是中国人民心中的皇帝,故称毛泽东“万岁”。而除“万岁”外,还会用“千岁”向诸侯表达长寿祝福。因此,用"long live"并不能等同于“万岁”。这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的,在西方世界没有“万岁”与“千岁”的区分,因此统一称"long live",而在中国却不能一概而论。可见,白睿文还没有完全适应原文所处的文化环境。
ST8: 我重新站起来,像只瘟鸡似的走出了青楼。[4]
TT8: I stood back up and,like a diseased chicken,walked out of the House of Qing.[5]
在这个例子中,“青楼”在中文中有特殊含义,专指古代的妓院。但是白睿文仅仅把它翻译成"the House of Qing",显然他不知道“青楼”的含义,这不得不说是一处失误。
事实上,国外的译者在翻译中文小说时,大多数都会遇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文化误解和冲突。尤其对于一些专用的词汇或习惯性的表达,国外的译者往往是直译过来的,因为他们不懂这些词汇的真正含义,其结果只能与原作者的本义相差甚远。正如我们在翻译"bad apple"时,应翻译成“没有道德的人”而不能是“坏苹果”。
四、结语
《活着》作为一部后现代主义风格浓厚的作品,没有宏大叙述,没有对广阔时代背景的描述,而是以一种小人物的第一人称视角,将那个时代的变迁娓娓道来。叙事风格朴实、灵活,在诸多简单词汇的排列中渗透出浓厚的乡土气息。白睿文先生的翻译工作继承了这一风格,整部译文以简单词汇、简单句式为主,多采用直译的方式翻译词句,可以说除了句法冲突时,不得已遵从英文句法外,他几乎是一字一句地翻译原文,这包括对原文所用的修辞方式和对中国式叙述方式的全面保留。当白睿文先生面对中英文表达方式和时态差异时,几乎全面遵循了中文的表达方式和原则,并抛弃了英文的时态变化,统一用一种时态来迎合中文的时间表达习惯。
由此可看出,在《活着》的翻译中,处处体现着白睿文先生作为翻译主体的核心作用,他选择直译余华的简单词汇和句子,来保留中国小说通过描写人物细节来展现人物性格、心理的特色,这种特色因此能够通过英文被西方读者认识和分析。他也选择抛弃英文的时态变化,规避中英文时态冲突,大大降低了翻译难度和英文的理解难度,使西方读者看到一种不同于通过词汇、句法展现的时间表达方式。他还选择遵循中文的意合原则,尽可能的保留小说原味,让读者更接近余华所要表达的真意和细腻的表达方式。谢天振先生认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8]确实,白睿文先生做出的这些选择是为了适应原文也是为了通过他的传递,将余华先生的世界展现给英文读者,也许最终的译文对于英文读者来说不是特别容易体会,但确实打开了一扇窗,让英文读者离原作者更接近一些。
最后,不能忽视的是,有一些原文的文化内涵并没有能够很好转化过来。过多的直译可能导致英文读者读得懂语言却读不懂内涵。针对这一问题,一方面,有些中国特色的内涵(例如:对“福贵”的翻译)还需要在正文以外加以注释和解读;另一方面,类似于“青楼”翻译的问题还应该通过多了解中国文化来避免。
[1]胡庚申. 翻译选择适应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16-176.
[2]陈友勋. 翻译中处理意义的研究方法探析[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6.
[3]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 中国翻译, 2011(2):5-9.
[4]余华. 活着[M].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9-153.
[5]余华著. Michael Berry译. To Live[M].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3:5-197.
[6]余光中. 余光中谈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25.
[7]霍兴.基于适应选择论的译者中心与译者素质的提高[J].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2):73-75.
[8]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137.
TheEnglishTranslationofToLiveunderthePerspectiveofEco-translatology
HAN Si-yu
(SchoolofHumanities,BeijingUniversityofPostsandTelecommunications,Beijing100876,China)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theories included in the eco-translatology: translator-centeredness and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s. The translator-centeredness mainly stresses the core status of translators, who act as the only active factor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ake Michael Berry's translationToLiveas an example, he chose to follow Yu Hua's special writing style to keep the original taste most of time, and literal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is mainly adopted in the English version. As for the conflicts of tens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Michael Berry chose to use one fixed tense to avoid the reading obstacles, but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could be discovered in the translations of proper nouns and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Eco-translatology; Selection and adaptation; Translator-centeredness; Language conflicts
2014-06-06
韩思宇(1990-),女(汉),山西太谷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翻译方向)方面的研究。
I046
A
1671-816X(2014)12-1270-05
(编辑:佘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