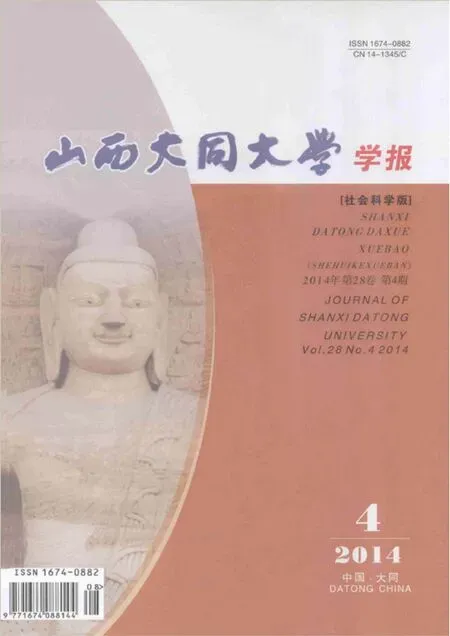前喻文化遭遇并喻文化所引发的冲突与融合
——以《喜福会》为例
赵慧敏
(山西大同大学外语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前喻文化遭遇并喻文化所引发的冲突与融合
——以《喜福会》为例
赵慧敏
(山西大同大学外语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喜福会》以独特的视角讲述了有着不同文化背景与成长经历的母女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与谅解。从代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母女之间的误解、矛盾以及达成的和解,可以发现在异质文明交汇的移民家庭中并喻文化与前喻文化之间存在断裂与融合。
喜福会;代际冲突;前喻文化;并喻文化
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喜福会》[1](The Joy Luck Club)发表于1989年,是当年美国四大畅销书之一。谭恩美也因此被《华盛顿邮报》称为“讲故事的高手”。小说以其独特的叙述方式关注中西文化冲突下两代女性移民的生存状态,对母女两代代际关系冲突与和解的描写打动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成为读者不断探究小说文本的独特魅力之源。
在知网上检索到研究《喜福会》的论文452篇,按论文所依理论可将其分为八类:翻译与语言研究(47篇);后殖民主义研究 (69篇);接受批评研究(4篇);生态主义批评研究 (4篇);心理分析研究(38篇,包括代际关系研究1篇);性别研究(64篇);叙事学研究(64篇);东西文化冲突研究(151篇)以及综述性质研究(10篇)。各类论文在论及文章审美意蕴的过程中,质量良莠不齐。但关于《喜福会》中的代际关系研究视角却十分引人注目。该视角不仅涉及独特的移民环境,而且试图为当今世界普遍的代沟冲突做出人类学的解答及预测。因此与《喜福会》跨文化背景下母女关系的冲突与和解十分契合。本文拟从代际关系的角度探究文本中母女关系演变的实质,分析小说在纷乱的表象下试图展示的意义维度。
一、前喻文化(Postfigurative)中的移民母亲们
《喜福会》中一共出现了四位母亲:吴素云(Suyuan Woo),许安梅 (An-mei Hsu),龚琳达(Lindo Jong)与映映·圣克莱尔(Ying-ying St.Clair)。她们都是从旧中国到美国新大陆的第一代移民,处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新文化的夹缝中,带着不同程度的创伤记忆,她们在旧文化与新地域的磨合中将自己对环境的适应力发挥到了极致。
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千里鸿毛一片心”(Feathers From a Thounsand Li way)里,四位母亲(吴素云以吴精美回忆中的形象出现)分别以叙述者的身份讲述了自己早年在中国的经历。这些经历不仅深入骨髓地影响了母亲们,更反映在母亲们与新大陆出生的女儿们之间的冲突中。女儿们一次次以疏离抗拒的方式提醒着母亲们的异质性,反对着母亲们融化在骨子里、奉为天经地义的生活经验。而母亲们与自己的母亲之间却一改这类剑拔弩张的关系,更多体现出的是生死相依般的温情脉脉。迥然不同的两种母女关系不仅揭示了异质文化交汇时可能出现的冲突,更多反映的则是两种不同文化进程之间的断裂与不稳定。
玛格丽特·米德将“未来重复过去”这一文化类型定义为“前喻文化”。[2](P22)它是指“年轻一代的全部社会化都是在老一代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并且完全沿袭着长辈的生活道路”[2](P8),具有“对变化缺少认识,每一代儿童都能不走样地复制文化形式”的特点,并且“代代相传”,“成年人能够理解养育他们的父母”,正如“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养育自己的子女那样”。[2](P23)而这一封闭的类型正是四位母亲扎根的深层文化土壤。
在以宗法制为基本社会关系的旧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安梅一直被女孩儿不听话的悲惨下场吓唬着,而龚琳达从小就被母亲以外人的身份定义着,映映则被保姆一再告诫要安静顺从,不能多嘴。“这种惩罚和被彻底抛弃的威胁所训练出来的文化特性很有持久性”,即使母亲们置身于美国这个新环境中,在地域上完全脱离了原有文化的禁锢并且成功涵化了一部分美国文化的民主与自由思想,可是她们仍然“带有原有文化的自认感,在新的文化中,期望着能够像在原有的文化中那样获得自认”。[2](P23)因此她们的行为和想法只会给“大口吞咽可乐”的女儿们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和难堪,而在与自己母亲的相处之中则显出一往情深的尊重与怀念。
米德认为前喻文化能够得以保持的两个基本条件是:缺乏疑问和缺乏自我意识。[2](P8)因此,许安梅能够对婆婆与母亲的诋毁采取默认态度,龚琳达则为“履行父母的诺言”而牺牲了自己的一生。映映则始终“牢牢管住自己的嘴巴”,“不会让一丁点个人的想法和见解从中泄露出来”。生活在这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文化中,年青一代在成长过程中就能够毫无疑问地接受父辈和祖辈视之为毫无疑问的一切。这种文化的传递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排除了变革的可能,当然也就排除了年轻一代对老一代的生活予以反叛的可能,排除了代沟产生的可能。[2](P8)因此生活在前喻文化中的母亲们与自己的母亲之间才会更多地展示出母女之间理想的和谐与爱,尽管这爱带有畸形的色彩,同时也会与自己的亲生女儿出现诸多误解和冲突,尽管这也是爱的一种表现。
而当母亲们移民到美国之后,新的图景展现在她们眼前,新的文化传统也让她们措手不及。当她们为女儿的未来“选择了新型的教育体制和新的职业目标以后,孩子们便由于教育和双亲体系发生了最初的决裂”。[2](P58)而这一决裂在异质文化的冲突中便不断地开始扩大到让人倍感孤立无援的境地。
二、并喻文化(Co-figuration)中的女儿们
与四位母亲相对应的女儿们分别是:吴精美(Jing-mei“June”Woo),许露丝(Rose Hsu Jordan),薇弗莱·龚(Waverly Jong)以及丽娜·圣克莱尔(Lena St.Clair)。她们都是移民美国的第一代孩子,是完全意义上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先前文化的中断”使她们“丧失了现成的行为楷模”,而盼望着“子女能受到更好的教育,比他们自己更成功”的母亲们在与变迁中的种种困难进行斗争时,女儿们在学校中所习得的“标准的美国行为的解释”又让她们拥有了“能够与上一代相抗衡”的“巨大权威”以及“行为风范”。[2](P8、63、69)正是在女儿们这种新文化方式形成的过程中,酿就了最初的代际冲突。因此吴精美在母亲想尽办法的天才改造计划中愤怒地为自己下定义:“我本来就不是神童,我永远也成为不了天才”;许露丝面对母亲则是哭笑不得、啼笑皆非;薇弗莱质问母亲“为什么你非要拿我出风头”;丽娜则因母亲说话做事的方式而羞愧难当。
米德将此种文化类型冠之以“并喻文化”,她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这只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肇始于前喻文化的崩溃之际”,并且此种文化“只能维持十分短暂的时期”。在新的环境中,“年老的一代首先必须面临先前的行为方式的丧失。这种丧失是痛苦的,因为这意味着将要对先前的生活的否定,简言之,意味着对自身的否定”,[3](P8、9、69)这就使老一代在面对下一代的时候内心失去了可以怙恃的传统,失去了底气,只能依靠父母所代表的权威身份,愤怒地镇压着他们已经理解不了的孩子们。而孩子们则生活在“年轻移民的行为方式与他们的祖先要有明显的不同”的美国,“美国儿童的经验代表了新时代的新文化”,他们恳求父母“不要在公共场合讲外国话”,“不要穿他们的外国味十足的衣服”以及“看不惯父母说话和做事的方式”。[3](P45、81)
因此吴精美会对“喜福会”作为一个团体“感到脸红”,并且认为母亲们的装扮“样子十分好笑”并且“显得古怪”。而许露丝则因为母亲为着寻找年幼失足堕海的弟弟“竟愚蠢到妄图用信仰去改变命运”而感到十分愤怒。薇弗莱·龚袒露心声道“我要躲避的,就是妈妈的闲言碎语,妈对我的不足之处的寻觅和挑剔”,这些“时时搅得我心烦意乱”。而丽娜则能轻易地分辨出母亲的胡编乱造,并且自己也学会编造“中国人不能在这里买东西”一类避免让自己在他人面前尴尬的谎言。
对第一代移民的孩子们来说,米德预言道,“不管这种迁移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祖辈人毕竟是代表着已被抛弃在身后的过去”,因此他们常常“拒绝学习祖辈的语言”,“只学说美国英语”。[2](P45、123)而文中的四位女儿无一例外地应验了预言,她们对中文的掌握程度都很低,根本丧失了与母亲们深层交流的能力。她们不会懂得母亲们渴望使她们变成白天鹅的梦想,也不会理解母亲们“貌似张牙舞爪”,实则“耐心等待着自己的女儿”进入她们生活的卑微愿望。
三、前喻文化遭遇并喻文化
米德认为代沟是指“年轻一代与年老一代在行为方式,生活态度,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对立、冲突”。[2](P1)而冲突的原因在于抚育后代的新的方法无法适应孩子们的成长过程,而这些新的方法恰恰是第一代人,即那些新生活的开拓者们希望自己的后代所遵循的。[2](P55)
在《喜福会》开篇,母亲们的集合象征便表明了自己移民美国的梦想只是在美国生下一个长得像自己的女儿,但是“她不用看着丈夫的眼色低眉顺眼地过日子”,“她讲一口流利漂亮的美式英语,不会遭人白眼看不起。她将事事顺心、应有尽有”。母亲们想要把女儿“它打磨成一只真正的天鹅”。这样的信念使移民母亲们奋斗不已,并且愿意“遵守当地的规矩”并“琢磨其中的奥秘”,可惜的是女儿们对这样无私的牺牲与奉献却并不买账。
在“慈母心”(Two kinds)一章中,吴素云会“用中国话高声”说道:“在我家里,只允许听话的女儿住进来”。甚至在气急时厉声叱责“还不都是为你好啊!”“没有良心!”。而女儿的回应如同双刃剑一般划过了她们彼此心中最柔弱的地方,她哭着咆哮道:“那么我希望不做你的女儿,你也不是我的母亲!”。
孙隆基认为中国人的个体“基本上没有合法性,它必须由外力加以制约,才能下定义。因此,不论是上一代还是下一代,都必须把‘自我’抹杀掉,而摆出处处以向自己下定义的对方为重的姿势”。[4](P198)吴素云在这里便是如此,她以固有的文化定向思维将自己设计的未来强加在了已经具有独立意识的女儿身上,并且宣称为了不懂事的孩子吃了多少苦,费了多少心。可惜这样苦口婆心的说辞根本打动不了接受美国开放式自由民主教育的女儿。
除去上述的直接冲突,误会还发生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在新年饭上,薇弗莱与吴精美就广告书发生了争执,在母亲“自我压缩的人格”影响之下,她解决冲突的基本方法就是“让外按内”[4](P239),不问是否公平,也不关心问题实质。
而在龚琳达过往的讲述中,她被当做了“生育的工具”,[4](P227)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未替她和她的丈夫考虑过两性之间真正的愉悦,在平常的虐待之外,她还“被圈禁在床上不准起身”,尽管“保证她儿子的种子不致流失”这一原因是如此的荒谬。龚琳达早期在中国的两性生活被简化到生育目的论上,全程被长辈仆人等监控,虽然在想尽办法逃离掉这样的大环境之后,深植在潜意识中的集权式思想仍旧激发着龚琳达的控制欲,她的“私人空间”、“私人时间”、“私人生活领域”被剥夺以后,潜意识中也认为自己有权利剥夺女儿的“私人状态”[4](P238)。她将女儿作为自己的财产以及人生成功的证明。可惜的是女儿的性格中缺乏顺从的因子,这伤害了母亲的自尊,也掐灭了女儿天才的发展可能性。
在许安梅讲述的部分中则着重描绘了自己的母亲。还在儿时,许安梅就一直被告诫着要听话,而母亲在外婆病重的时候回来割肉熬药更是给她上了关于“孝顺”的生动一课。安梅的母亲在遭遇飞来横祸之后,以受害者的身份承担着始作俑者应该受到的责难和谴责,没有得到家人的任何同情,反而被武断地冠以各种下流的罪名。她没有能力反抗命运的不公,只能独自承受着自己的愤怒与悲伤。
孙隆基认为中国人所谓的“孝”之道要求“下一代完全向上一代投降”,并且认为必须要“做到完全认同的地步”。[4](P197)这在许安梅母亲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面对充满苦难的坎坷一生,许安梅母亲以绝对服从的“孝”作为活下去的支柱,而婆婆的死让母亲的世界迅速坍塌了,最后只能用死亡为许安梅争取到了一条出路。许安梅是深爱着自己母亲的,因此她学会了“大声反抗”,可是在来到新的文化环境中,她重蹈覆辙地表现出“没有主见”的性格缺陷。尽管她努力以相反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女儿,但女儿还是走上了优柔寡断的老路。
映映·圣克莱尔讲述的故事里有更多疯狂的成份存在。她因前任丈夫的不忠亲手掐死了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儿子,从此陷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在旧中国的婚姻中,映映为了取悦花心的丈夫,逐步抹掉了“自我”,甚至在最终报复的过程中“达到了完全不顾自己权利的地步”[4](P243)。她让年幼的女儿一并体会到了创伤带来的恐惧无力与绝望,将情绪问题化为昏昏沉沉的卧床不起。这直接造成女儿对爱情、婚姻采取的逆来顺受的态度。
母亲们的表现向来在国内“被认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扭曲与亵渎,是作者为了迎合西方主流文化的品味而故意对东方文明的践踏与侮辱”,[5](P51)但生活在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的夹缝中的“第一代归化儿童”无疑在这样真实的描写中得到了释放和解脱。
然而作为“第一代的归化儿童”,在“确立的生活方式中也许会永远保存着旧文化的淡淡的影子”。因此精美的生活中充斥着五行说,薇弗莱也学会了母亲的似风般的精明与不动声色,许露丝则在预兆中明白了“所谓命运,它的一半出自我们的期望,一半,又是出自我们的疏忽”,丽娜则始终关注着风水对运势的影响。而且如前所述,并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类型只能存在较短时期。因此,处在异质文化中的移民母亲与女儿在文化断裂的夹缝里最终有了理论上可以和解的可能。
小结
米德在进行人类学的研究中发现大部分有关代沟的讨论,往往强调了年轻人的被疏远却忽视了老年人,正如薇弗莱意识到的那样,母亲其实一直在等待着女儿进入她的生活中,“一直等成了一个脾气暴躁的老太太”。
实际上,正是以女儿们为代表的并喻文化类型在以矫枉过正的方式推开了父母,用不耐烦与冷漠将代沟变成了看似无法跨越的鸿沟。而“真正的交流是一种对话”,它要求“让每一个人都听到,同时也要听每一个人在说什么”,[3](P152)这无疑也是母亲们讲述故事的初衷,她们想用倾诉一生的方式与女儿们和解,让她们知道代沟是隔不开血浓于水、休戚与共的亲情的。
尽管她们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成长经历,可是这并非放弃爱的理由。虽然对话的母女双方缺乏共同的语言,但是在尊重彼此的前提下,她们通过双方的努力去理解文化类型的多样性,最终达成了谅解,母亲与女儿都放下了戒备,如出生婴儿般重新学着去爱也学着去感受爱。虽然代沟在这样的和解中并未消失,固有的文化冲突也并未清除,然而真诚地去听,并且努力地试着听明白,“这就是我们这个充满危险的,但有潜在自愈力的世界的希望”,[3](P153)而理论上可以被沟通的前喻文化与并喻文化于此也就在生活中得到了践行。
而这希望不仅给予了《喜福会》中的母亲与女儿们,同时也昭示着我们在面对代沟时这一解决方法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如此,《喜福会》不仅揭示了人类诸多困境中的代沟问题,更以作家独特的敏锐预言着代沟最终被沟通的可能性。
[1](美)谭恩美著,程乃珊等译.喜福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2](美)玛格丽特·米德著,周晓虹,周怡译.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3](美)玛格丽特·米德著,曾胡译.代沟[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4](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姜 苓.从《喜福会》看中国式的慈与孝[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49-51.
The Cultural Conflict and Fusion Appeared When Post-figurative Encounters Co-figurative——A Case Study of Joy Luck Club
ZHAO Hui-m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xi Datong University,Datong Shanxi,037009)
The Chinese-American writer Amy Tan’s Joy Luck club tells a story about the conflicts and understandings between mothers and daughters who have their own growing experience in the different culture background.From the angle of generation gap,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misunderstanding,conflicts and reconciliation between mothers and daughters,and concludes that there are the fracture and fusion in immigrant families when post-figurative encounters co-figurative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Joy Luck Club;generation gap;post-figurative;co-figurative
I207.42
A
1674-0882(2014)04-0060-04
2014-04-05
赵慧敏(1979-),女,山西长子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大学英语教学。
〔责任编辑 郭剑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