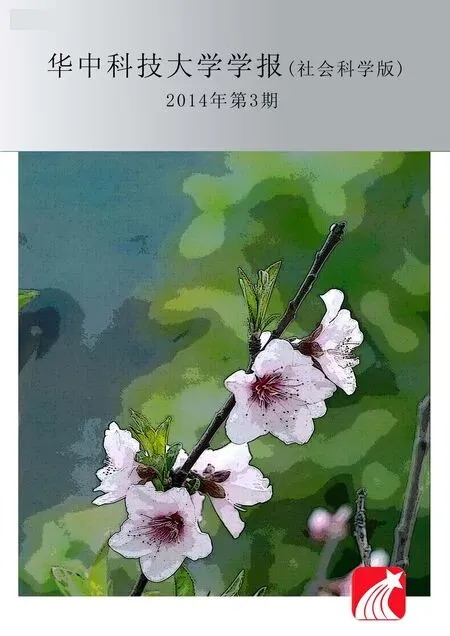“厚概念”与“薄概念”:威廉斯对道德客观性的勘定
潘红霞,
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4
李燕,
军事经济学院 政治理论与人文社科系, 湖北 武汉 320035
伯纳德·威廉斯是20世纪最重要的道德哲学家之一,其理论极富开拓性与原创性,但概念复杂、领域宽泛而晦涩艰深,道德客观性是理解威廉斯道德哲学的钥匙与关键。本文通过对威廉斯道德客观性思想的解读,试图以此说明为何威廉斯的道德哲学能成为当代道德哲学的转折与起点。
一、道德客观性:为何如此重要
道德是否具备客观性?围绕着这一议题展开的讨论主要集中于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客观主义两种观点。前者从道德多元论出发,认为道德受限于时代、地域和文化等因素而具有特殊性和不确定性,在此意义上是主观的和相对的,并且也符合人们日常的生活经验和感性认知。后者则认为道德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有一个普适的道德标准衡量行动的正当与错误,总会有一个终极的道德原则可以跨越文化差异、不同的社会共同体乃至不同的历史阶段来对人性做出道德判断,道德可以是客观的*徐向东认为,主流观点至少承认道德在两方面是客观的:一是道德规范产生或出现的方式不依赖于任何特定个体的意志;二是道德规范产生的条件不是由任何特定个体的心灵决定。徐向东著:《道德哲学与实践理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37页。。包括休谟在内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哲学家否认在伦理学中存在客观真理,道德命题之所以为真是因为它们代表着构成世界组成部分的道德实体或结构,即道德现实与人类存在一定的因果必然关系,道德主体利也是利用科学知识来观察物理对象。威廉斯虽然赞同这一立场并怀疑伦理学中的客观性,但他认为休谟等人的简单类比未能触及伦理学的本质所在。
在威廉斯看来,道德判断不是致力于去表征外在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关于人们应该做什么和他们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如果在道德判断中存在任何客观性,它必定是通过一个与科学客观性不同的类推方式寻求而来。伦理学中的客观真理必定不是由伦理实体或者是添加到外在世界的伦理属性组成,而是由支撑某种实践的、非描述性推理的客观正确性组成,这些推理是关于人们应该怎么做和他们应该如何生活的判断。与科学客观性相类比,它将存在于获得客观性、普遍性与真理性的方式的事实中,而这必须得到进一步检测和修正,因为偏见和曲解将通过个人的意外事件或狭隘视角被引入个人的实践判断。一个人能修正的曲解越多,就越能接近想要得到的真理。当可以存在伦理真理时,它一定是局部的和历史性的偶然事件,并且基于来自人们实际的动机与实践的理由。因此,威廉斯的结论就是,道德判断不能应用于偏离时代太久远的文化以及在那种文化中产生的品格。在实践领域中,超越个人自己观点的雄心是非常荒谬的,类似于一个人试图消除属于他自己的事实的所有痕迹。同样,物理科学可以追求一种客观性与普遍性,而人文科学这样做则没有意义。因此威廉斯挑战了伦理学中致力于普遍性与客观性的雄心,而这主要体现在他对道德客观性的质疑与探究之中。
威廉斯在区分科学与伦理学的基础上接受了科学实在论而质疑道德实在论,想要表明道德不可能以科学所具有客观性的方式而具备客观性,甚至说道德根本就没有客观性可言。但是,当威廉斯认为我们必须放弃道德客观性的观念时,他并不认为我们必须舍弃(至少不是完全地)道德知识和道德真理的概念。更准确地说,他认为我们应该把道德概念作为我们建构道德现实的载体,有了这一现实基础,那么我们就可以要求拥有相关知识。在其看来,科学致力于表征外在世界事物的实际存在,追求的是对物理世界获得独立于个人主观性的客观化概念,通过对各个观点收敛的方式来获得客观性。道德判断直面人们应该做什么以及应该如何生活,它远没有科学所具有的认识论与形而上学基础,根本不可能取得科学模式的客观性。即便是致力于在实践中探寻与收敛各个观点的伦理学,也与科学具有完全不同的明晰性与普遍性。具体而言,威廉斯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道德客观性概念:第一种是如果道德信念能像科学的模式探寻伦理现实(例如科学信念追随经验世界),那么道德主张可能具有客观性。第二种是指如果人性的知识(基本需求或动机)能表明自身是对人类幸福的决定性论述,道德亦是客观的。但显然伦理学不像科学那样能给予科学信念实质性的内容,而且科学能对各个不同的观点进行收敛,而伦理学则不具备收敛性,这即意味着道德无法具有客观性。同样,关于人性知识的论述,特别是关于幸福的论述,也只是代表某种人类可能性的特殊化,就正确的概念而言,很难成其为一种客观性与普遍性。在双重意义上,威廉斯都认为道德不具有客观性。
二、“厚伦理概念”与“薄伦理概念”
就理解威廉斯道德客观性而言,只有伦理的“厚概念(thick concept)”才是关键。威廉斯认为伦理概念有“厚”与“薄”之分并有显著区别,并给出了厚概念的具体例子:背叛、许诺、勇气、撒谎和感激等*最知名的威廉斯研究专家与传记(《伯内德·威廉斯》)作者马克P.詹金斯(Mark P. Jenkins)概括了威廉斯的厚概念与绝对概念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代表着由威廉斯出于自己目的而修正的在先的(pre-existing)概念。Mark Jenkins,Bernard Williams,Acumen Publishing Ltd, 2006, p.133.。伦理的“厚概念”是一种比喻,如怯懦和贞洁这样的厚概念是与正当和恶这样的“薄概念”(thin concepts)相比较的。就其内容而言,薄伦理概念的内容显得含糊不清,而厚的伦理概念是“更实质性的概念,如果我们使用相同的这些概念时,则有更大的希望获得一致认同。”[1]32“厚”概念与“薄”概念之间并无截然对立的区别,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得到诸如正义一类要薄得多的厚概念,这依赖于概念中包含多少经验性的内容。事实上威廉斯是在程度上将概念区分为“厚”与“薄”,而非严格的类型学划分。
厚概念的典型特征是导向性,即“世界导向的(world-guided)”(被世界是怎样的引导)与“行动指导的(action-guiding)” (它们指导着人们的行动)[2]140-141。一方面,厚概念的世界导向性确保了世界的客观性并决定着它们的应用;另一方面,厚概念的行动指导性保证了其应用为行动提供了主要理由。与这些厚概念对比的是“善”、“正当”与“应当”等薄概念。薄伦理概念由于普遍性和抽象性而缺乏世界指导性,但这类词语已经构成了目前至高无上的道德体系主要部分。
如何区分厚概念的世界导向性与行动指导性呢?厚概念的应用被世界导向,是指这类概念可以被正确或错误地应用,并且获得这些概念的人会同意它可以或者不能应用于某种新的情形中。在许多情形中,这种共识是自发的,而在另外的情形中则存有判断与比较的空间。在伦理的情形中也一样,首先在那些实质性的或厚的伦理概念中可以看到,如怯懦、勇敢等典型地与行动理由有关。这一类概念应用时通常给某人提供了一个行动的理由,尽管那个理由不一定是决定性的而且可能被其他更重要的理由超过,但它与行动的一般联系还足够清楚,这些概念可以归纳为“行动指导的”(action-guiding)。
最初威廉斯以厚概念的特殊性与薄概念相区别,他以残忍和勇敢为例说明了二者的不同:厚概念的意义只能在一个有限范围和人类生活的特定领域应用于行动和对象上,它有描述的内容且与人类的经验相关,通过传递关于行动者的信息、意图、欲望和动机而具有描述意义。薄概念是以那些一般化的词语如“善”、“正当”与“应当”来表达的概念,是道德论述中最普遍的概念,但并非最经常使用的道德概念,而是在多变的情境中使用它们并以此来评价所有类型的人、事态和行动,这一普遍性特征使薄概念几乎不包含描述性内容。例如,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勇敢”的用法:勇敢不单指在危险情境中值得赞扬的一个道德行动,也是行动者知道有危险但愿意服从于更大的价值目标,从而自愿面对危险采取的行动。因此厚概念的描述性内容可以作为一个评价理由,这些专门的伦理概念既有描述性又有评价性的意义。
威廉斯认为厚伦理概念在许多规则中起着重要作用,表达了事实与价值的联合,但我们显然对这些概念如何起作用还缺乏理解。例如,在他看来以黑尔为代表的学者对道德论述进行了错误的语言学分析应用。虽然他们在“是”与“应当”之间用法的区别捍卫了事实与价值的区别,却掩盖了我们伦理论述的真正性质,这些论述并不主要依赖于这些一般化的词语:“他们发现的是许多那些我已提到的‘更厚的’或更特殊的伦理概念……例如背叛、许诺、残忍和勇敢,这些词语看来表达了事实与价值的一种结合”[2]129。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事实与价值的要素相结合,来调和当代道德哲学对事实与价值区别的过于简单化而造成的困扰,而厚伦理概念共享一个评价性观点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展示厚伦理的概念内涵而实现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和解。除了厚与薄这一比喻性的区别之外,厚伦理概念既描述了世界是怎样的,同时又能给人们一个理由那样做或者不去行动,要求它们的使用者必须共享一个评价性的观点,以便能从这样一个概念的一种应用继续到另一种应用,尽可能多地分享厚伦理概念中所包含的重要的评价性观点。这也就是它们同时既是“世界导向的”的又是“行动指导的”含义所在。
无疑,厚伦理概念能帮助我们在事实与价值的论争中辨别世界的真正特征并为我们提供行动的理由,还能指导人们的行动,以此表达一种对人类利益的积极理解。
三、科学与伦理:客观性之争
道德是否具有类似于科学的客观性?除了从伦理的厚薄概念区分之外,威廉斯必须对科学与伦理本身进行深度区别。为此他提出了“绝对概念”(absolute conception),并将其解释为“在最大程度上独立于我们的观点和它的特质”的概念[2]139。威廉斯认为绝对概念包含着一种独立于我们的经验来反思那个一直存在的世界的思考方式,它描述了关于现实的知识。就知识论本身而言,科学知识是以绝对概念为中心获得的,它包含着对我们如何获得知识来源和材料的解释,提供的这些解释表明我们相信这些为真的科学命题。世界的绝对概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真理的信念,同样地它还调节着理性的反思与追问。因此绝对概念能使科学到达知识的领域,而伦理学则不能。与科学知识不同,伦理知识体现在使用厚伦理概念的命题中,它存在决定于伦理中的厚概念。厚伦理概念的应用既是世界导向的,又是行动指导的:一方面它们的应用标准基于知觉的研究建立而无论这一标准是否被满足;另一方面它们被用来赞扬行动、人或者为他们提供行动理由,所以它们也能指导行动。在通常的应用中,许多概念既是伦理的又是厚的,并且在大量情形中被广泛使用,因此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之中将会有大量的伦理知识。
具体而言,以客观性为区分,科学与伦理至少存在如下三个区别。
首先,在伦理学中获得共识的希望不如在科学中大。伦理争议中的分类比科学中更直接。例如,与科学的概念类比,正义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们同意一系列无争议的情形和一系列认为与这一词的应用有关的考虑;但关于这一词应如何应用以及标准应如何制定和修正亦不清楚。饱受争议的对立者之间的相互竞争会带来一个胜负的结局,寻求共识与客观普遍性的科学能较容易地接受失败的结果,但缺乏客观性的伦理学却难以接受这一知识挫败。在科学中通过实际观察能获得一个非强制性的共识,其标志是拥有一个客观的真理价值,加之科学理论无法解决的争议还可以通过理性的手段解决。而伦理争议允许的范围则更广泛:尽管对一个行动是否残酷或仁慈,或者一个人是报复性的或宽宏大量的争议较之以前要少些,但价值观多元化会导致差异巨大而难以达成共识。因此,我们在科学研究中寻求以事实为解释前提的共识,科学寻求自身与现实构成的协调一致,而我们对伦理事务的推理并不是以这一方式进行的。
其次,科学反思可以增加科学知识,而“在伦理学中反思可以破坏知识。”[2]148在科学研究中,理论的思考与方法论的反思可以产生对客观知识的积累,而伦理研究只能减少我们的知识。威廉斯认为逻辑性的反思或者系统化的哲学并不一定能对生活或有争议的伦理问题带来满意的解答,反思破坏了只有人类才能具有的真正的道德知识或文化。在知识共同体中科学与伦理学具有不同的作用:科学研究中共同体的成员对知识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在伦理学研究中它是某种有助于修正我们伦理反应的事物。对伦理问题的反思仅仅只是在应对实践中非常紧迫的伦理问题时才变得很重要,且对可接受伦理问题难以达成共识。反思的层面不是一个给予我们以前没有的知识的地方,而至少是破坏了一些伦理知识。实际上,它不是为了重建的目的而去破坏:我们不能通过更深入的反思,获得新的伦理知识来代替我们已经失去的。当反思成为哲学研究内容的时候,它反映的是它不能为伦理学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但必须注意,虽然伦理研究并没有要求我们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认可为最好的,也不能始终都能成功地处理面临的道德挑战,但伦理反思足以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伦理思考仍然具有力量,如果没有它,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糟。
最后,科学与伦理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各个观点收敛(convergence)的可能性。科学研究与伦理反思都希望能获得被其他人的独立发现认可的观点。威廉斯用对观点的收敛(凝聚性)这一观念作为科学研究产物与伦理信念之间根本区别的一个标志,他认为在科学中存在对各个观点的收敛,而在伦理学研究中显然缺乏收敛的条件。科学概念在理论上与观察上一样是“世界导向”的,即当它们应用于对结果判断的可靠性时,可以依据它们与相关事态的偶然联系得到解释。科学信念能为世界的绝对概念提供一个基础。现代科学的重要特征是:“它可以用来解释伴随我们的起源和独特性的生物怎样能理解同样由科学赋予特性的那个世界。”[2]140在科学中我们对每个问题的追问都可能产生对回答的一种收敛,但在伦理学中也没有与我们知觉的科学解释相关的东西,即便最一般的概念也不是世界导向的,至少在一个高度普遍化的层面上难以获得合乎逻辑的收敛。
四、道德的非客观主义
道德客观性的失败会影响我们理解道德实践,为了做出正确的理解与再次修正,威廉斯提出了关于道德的“非客观主义”概念。威廉斯认为伦理知识可以在传统社会中存在,因此他想象出一个“高度传统的”(hypertraditional)社会来构建这一概念。这是一个更强调具体伦理表达形式的社会,其社会成员使用厚概念,而非薄概念做出判断。创建这样的社会有两种方式,其一是依据一种“客观主义”模式构想它们的活动:把社会成员视为含蓄地“努力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发现价值的真理,这是一种我们和其他人,也许还包括不属于人类的生物全都在参与的活动。”[2]147在此客观主义模式之中,社会各成员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概念表达所在世界的知识。例如我们知道真理包括颜色的概念,即使这样的知识按威廉斯的用词也是“透视性的(perspectival)”。高度传统社会中存在伦理知识,但关于伦理的真理还是比关于颜色的真理更具“地方性”和“透视性”。不同于科学的解释,伦理的解释唤起的解释“不仅仅存在于伦理所在物理世界中,也存在于我们周围的社会世界里”[2]150,因此根本性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实践与反思之间的关系。现在与这一社会有关的问题是:社会成员做出的有些判断实际上包含了在一个更一般和理论的层面上他们从没考虑过的含义,但是如果我们让他们做出那些判断并且表达那些观点,他们的陈述将更具普遍性内涵。
其二是依据一种“非客观主义”模式构想他们的活动,即把他们的伦理判断视为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以及已经形成的一种文化的产物(尽管他们没有有意识地创造它)。依据这一模式来理解伦理概念比其他的理解方式更能经得起检验。例如,薄的伦理概念是那些最一般的高度抽象的概念——如正当、善或应当;厚的伦理概念是更特别的能具体决定伦理存在而且更清晰的概念——诸如残忍、勇敢和慷慨等。关键是厚概念比薄概念包含有更多经验性内容,因此它的应用标准更清晰且不那么具有争议性。实际生活中,人们对一个行动是否正当的困惑更甚于一个行动是否平均或慷慨。因此厚的伦理概念可以并且是“世界导向”的。
在使用一些厚概念而不是其他概念时展示出的可以说不可能是这个世界给出的知识,这也是威廉斯已经发现的伴随着薄概念的一个问题。这些概念是做出更多普遍道德判断的典型载体,因此对行动正确性的理解不像厚的伦理概念,它应该具有一种更普遍和更广泛地共享的意义。一方面,我们认为其他文化会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正当这一概念,但另一方面在普遍化层面上,谁的答案是正确的却没有定论,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把本土社会认为是“尽力以它们自己的方式来发现关于价值的真理”[2]147。由此而来,伴随着薄的伦理概念的问题是:在渴望超越我们具体的且是决定性的伦理存在时,薄的伦理概念已经超越了伦理知识的束缚。
虽然厚概念是能起作用的知识的概念,但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享有相同的厚概念,并且厚概念的词汇在一个多元社会里含义各尽不同。厚伦理概念给出了关于行动方案的方案,因此在能被薄伦理概念表达的实践理由的层面上我们就得到了公认的不一致。在面临关于如何做决定的实际生活问题上,我们得到了一些像“正确”与“错误”之类的词语,但是最终那些薄的伦理概念还是会被公认的。那种公认的不一致是一个重要的异议,虽然一个重要的异议并不能代表异议的所有基础,而且这存在于两种不同的伦理语言或者世界的两种不同结构中,但这理所当然就是一个异议。因此威廉斯把问题总结如下:“我们知道当人们说他们想要真正的伦理真理时,首先当他们说想要伦理中的客观性时,他们想要的不仅仅是厚概念中的本土语言,和相关的最少的真理。他们希望它能跨越文化和我们文化中产生的异议(跨越多元主义)而在概念上是同质的。”[3]32
论述至此可以发现,威廉斯对道德客观性采用的论证模式,一直以来都备受争议,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与批评,威廉斯也给出了相应回应。诚然,这一论证模式是否成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成功的,的确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威廉斯就客观性问题所提出的科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对比过于夸大。事实上笔者认为,在伦理学与在科学中一样,我们的伦理追问与反思也会达到客观性的标准,也会产生类似于科学的客观性知识,因此道德与科学都可能具备客观性。此外,威廉斯论证的“反思可以破坏知识”非常深刻,但问题在于,没有知识我们如何能有信心。假如所有的伦理知识真的被破坏了,那么也许就是在这里能有一个空间让信心来代替。如果威廉斯的怀疑主义是正确的,它们注定是要失败的,那么作为一个知识失败的候选人的我们就产生不了信心。“没有知识,没有一种伦理理论可以产生信心。”[4]165因此,笔者认为,虽然反思已经对伦理知识有所破坏,但是我们还必须依赖正确的反思,因为我们可能非常难以达成一种普遍性和客观化的伦理知识,但是我们还要对伦理抱有充分信心,只有这样才能在对伦理经验的反思之际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生活的本真需求,这也是任何道德哲学的旨趣所在。
[1]Bernard Williams.Morality:AnIntroductiontoEth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2]Bernard Williams.EthicsandtheLimitsofPhilosophy,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3]Bernard Williams.TruthinEthicsinTruthinEthics, eds. by Brad Hooker,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4]J. E. J. Altham. “Reflection and confidence”, inWorld,Mind,andEthics:EssaysontheEthicalPhilosophyofBernardWilliams, (eds.) by J. E. J. Altham and Ross Harris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