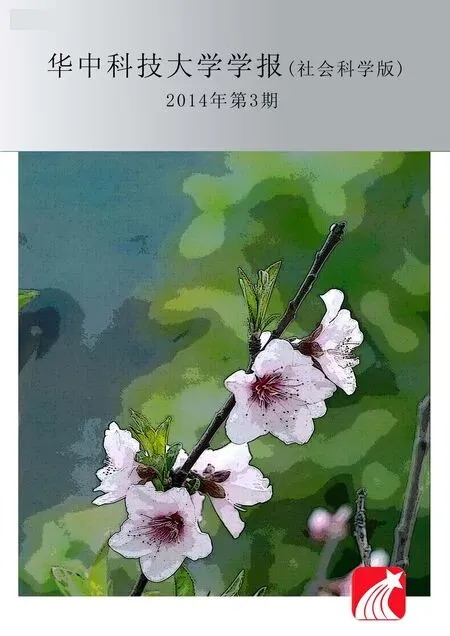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选择的若干思考
唐皇凤,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一、问题提出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的治理体系逐步转型为现代治理体系、稳步推进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过程。要准确把握和理性反思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路径,第一个需要思考的基本理论问题是:面对各种特殊历史境遇的不同国家,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的异同,是探索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选择的理论起点。
一方面,就治理的本质而言,中西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要实现的核心目标是相同的,即从一种消极被动的防御型治理转变为积极主动的干预型治理,从一种局部性和象征性的传统治理转变为一种整体性和实质性的现代治理,进而实现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政治整合和动态监控,汲取和集中社会资源以确保现代化事业的顺利推进。
另一方面,中西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历史情境、根本问题和主体力量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两者在国家治理现代转型的具体路径方面迥然有异。以英、法、美等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具有悠久的法治传统,在文化权力转型为制度权力的过程中,基本遵循从司法权主导向立法权和行政权主导的方向位移。而中国传统上就是一个理性早熟的国家,在秦汉时期就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一直有较为强大的国家能力,而作为现代政治秩序的另外两大要素——法治和负责任的政府则是长期缺失的。因此,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在一个行政权主导的社会中逐步发育立法权和彰显司法权,最终形成行政权和立法权、司法权之间互补均衡的现代治理结构,而推进法治建设(显然是发育和成长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战略抉择)。
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特征
厘清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明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区别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思考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选择的逻辑起点。而要清晰把握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特征,首先要明确治理相对于传统的统治和管理所具有的特殊属性。整体而言,治理集中关注国家功能实现方式的问题,强调以共识愿景、认同信任、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平等协商、多元共治的方式来制定和执行政策,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和优质的公共产品,在各种主要的治理主体之间达成合作性的行动是其聚焦的核心问题。
在治理理论的视野下,构建一个成熟的现代治理体系,核心是理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四大关系,而合理的价值排序与价值均衡、科学的制度与公共政策安排、强而有力的组织支撑以及有效的体制机制创新是理顺这四大关系的基本路径。
综合学界的各种观点,我们认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一般包括四大核心构成要素:(1)具有民主品格、公共精神、权利与义务对等的现代公民;(2)一个能够有效抗衡和制约专断性的国家权力和资本权力,高度组织化与制度化的现代社会;(3)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在竞争性的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4)一个廉洁高效、兼具可问责性和回应性的法治型、服务型的现代政府。其中,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模式是决定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基本特征的轴心力量,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独特的典型特征,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兼具有效性与合法性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2)开放性、包容性与可问责性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外在表征;(3)回应性和调适性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国家治理现代化涉及正确地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三者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撑的合作治理框架。明晰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职责权限分工,建立纵向和横向的政府间合作关系,在提升政府治理整体效能的基础上,形成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网络治理模式。具体而言,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标准包括:一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符合时代潮流;二是国家治理的组织架构符合现代理念,且能够及时解决特定社会经济发展历史阶段所面临的诸种治理难题;三是国家治理的成本相对较低,而效能相对较高。
我们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涵集中体现在以下六个层面:(1)治理主体的多层化和多元化,各种各样的治理主体都能够发挥他们整体的效用,多元的治理主体能够参与国家治理活动;(2)治理结构的分权化和网络化;(3)治理制度的理性化;(4)治理方式的民主化与法治化;(5)治理手段的文明化,因为在现代中国的具体治理实践中,不文明的暴力化倾向依然存在;(6)治理技术的现代化。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一个非匀质性社会、发展中社会与断裂社会从事大国治理,其制度转型与国家建设存在巨大的内生性风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预防风险、纾解危机和走出困境的重要战略抉择。在当下的中国,以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的网络化为基础,渐进实现治理制度的理性化、治理手段的文明化以及治理技术的现代化,最终达成民主、法治而有效的国家治理,是未来十年中国国家治理与政治发展的蓝图与愿景。
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主题是现有的国家治理体系如何应对快速社会变迁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和制度,寻求有效的资源积累结构,确保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与制度转型的平稳进行,以达成民主而有效的国家治理。
具体来说,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举措主要有以下几点:(1)创新国家治理理念,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塑造改革共识;(2)增强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自我完善能力,大力加强现代国家制度建设;(3)构建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网络化治理模式,实现国家治理结构的现代化。
笔者认为,除了探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特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路径之外,就国家治理问题的学术研究而言,下面几个问题的延伸思考更具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第一,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国家治理行动的效度和限度何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很多年,最终能否形成发展的增量结构与新的制度要素,能否突破传统治理结构的约束,避免国家治理长期陷入内卷化的困境,这是需要时间去验证的。
第二,在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特别强调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役使变量,它具有时滞与堕距效应。正因为文化在现代治理中有非常重要的决定意义,那么如何在现代治理理念的牵引下,通过现代国家制度建设,激发基层官员的公共服务动机,在公民教育、激活公民参与和发育公民治理模式的过程中,培育具有民主品格的现代公民,这是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成长的关键问题。
第三,现在中央政府具有非常明显的现代性取向,但是地方和基层政府还处于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当中。地方治理的现代化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洼地,是现代政府建构中的短板。中国的地方官员充满了“发展焦虑症”,官员理性与社会公共理性存在相当程度的背离。我们需要从“内部人的视角”,分析地方官员到底是怎样看待“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的,因为如果地方官员缺乏现代治理理念,那么要顺利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就十分困难。我们也需要理解地方官员的制度激励结构,在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层面分析研究中国地方官员的行动逻辑。因此,在国家治理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关注行政文化、地方官员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层面的东西,这些都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思考的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问题。
第四,如何构建有效的公民需求的显示机制,以及多元社会主体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重构国家-社会的制度化联系机制,这个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既需要一个能够有效驾驭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变革浪潮、兼具回应性与调适性的现代执政党,一个强有力的守法政府,也需要一个健康而有活力的社会,更需要无数享有自由与尊严的公民。在中国特定的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的历史场景中,国家治理体系现代转型的关键在于重构自由与秩序、效率与公正、权力与权利、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构建国家
市场 社会之间有效互动与相互制衡的网络化治理结构,积极而稳妥地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当下的中国社会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需要明智的决断,而且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巨大的政治勇气,尤其是丰富的政治想象力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