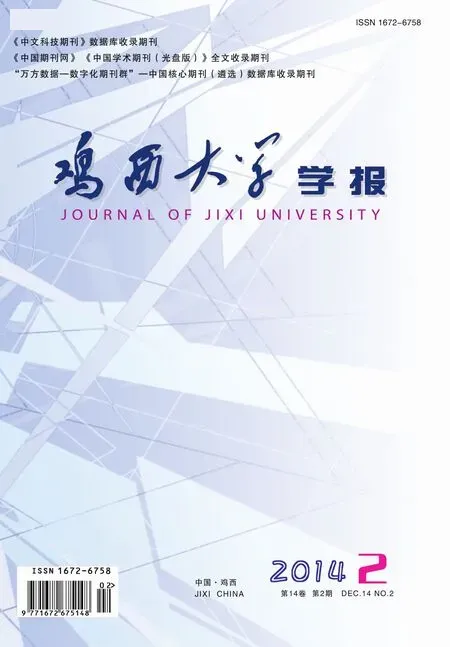解读布鲁克斯诗歌《萨丁- 勒格日·史密斯的星期天》中的反英雄人物形象及主题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一 简介
1.布鲁克斯在文学界的地位及作品风格。
格温多琳·布鲁克斯是美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诺贝尔文学奖黑人女性得主。作为一位非常独立的作家,她的诗歌创作融合了欧洲和非裔美国文学的双重传统,使得她在美国文学界有独树一帜的特色。她的作品不论是诗歌、小说、自传和小散文都散发着浓厚的非裔美国人的意识、黑人女性的角度与角色和黑人创作技巧。George E. Kent曾说:“布鲁克斯的作品在美国文坛占有独一无二的位子。不仅仅是因为她很智慧的融合了自身的种族意识与西方诗歌技巧,更因为她成功地弥补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学术型诗人到60年代黑人年轻激进派作家的间隙空白了。”[1]美国艺术运动的核心人物Haki R. Madhubuti曾在1972年说:“格温多琳·布鲁克斯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她是用英语语言作为行动道具的一阵暴风如同在非洲大陆上行走的一头狮子。”[2]
2.诗歌《萨丁- 勒格日·史密斯的星期天》简介。
该诗收录于布鲁克斯1945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布朗泽维尔的一条街》,全诗159行,为诗集中最长的一首诗。诗歌主角史密斯是一位居住在芝加哥南区的黑人聚集区的普通黑人男性,全诗通过对其星期天起居活动的描写塑造了一位看似极具享乐主义思想的花花公子形象,而掩盖在肤浅华丽外表下的真实状态恰是作家对黑人所处的复杂社会的强烈抗议,展露了其对黑人悲伤生活环境的诉求。按照描述场景牵引为标准全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1-42行)用“慢镜头特写”的方式描述了史密斯星期天早上从醒来、到起床、再到梳洗更衣的全过程;第二部分(43-74行)由叙述者和读者共同诠释进入史密斯的衣橱之旅的所闻所见。第三部分(75-159行)由叙述者以抽离的方式来揭示史密斯对街头音乐、先祖历史事件和性关系的选择态度。
3.反英雄的定义及主要特点。
反英雄(anti-hero)顾名思义是与“英雄”相对立的一个概念,是电影、戏剧或小说中的一种角色类型,在文学创作中体现了作者对“英雄”概念的分解与拆卸。[3]就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社会背景而言,战争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冲击了传统的道德准则。这也促成了美国作家的现代英雄观更趋于现代非理性主义与人性化,即人在处理和他人、和传统的关系中表现出了特有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这种新的价值取向与态度也标志着美国文学发展进入了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新阶段——现世的、普通民众的生活成为了关注的聚焦点。在布鲁克斯的诗歌中,其关注的都是黑人区的普通男性和妇女形象,聚焦其生活中琐碎的日常活动,他们看似与文学中塑造的经典英雄毫无关联,但与背后却同样蕴含着极具“野心”的大主题。
二 《萨丁-勒格日·史密斯的星期天》中的“反英雄”形象:史密斯
作为该诗的主角,史密斯没有皇家贵族的优越家庭背景,他仅仅是一位长期生活于黑人聚集区的黑人男性。在该诗中布鲁克斯采用第三人称的视角来描写这个小人物在星期天的起居生活,作为一种文学叙事手法的第三人称视角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途径进入史密斯的周末生活世界,并试图从超然的角度对整个人物提供一种全面信息的叙述。 诗中出现的意象:破旧的睡衣、白菜、上衣的肩垫出卖了其如贵族般醒来时的幻觉,显示出其物质条件的贫困;楼下的垃圾桶、小巷内小硬币叮叮当当的贸易嘈杂声、街道上“吐痰的路人、粗鲁的街贩、用破旧丝带打扮的小女孩、街边的妓女”都表明史密斯所生活的社区环境的脏乱;与妓女发生性关系也透露出史密斯对性的欲望及随意。其整天的关注点集中于服装、食物、妇女和性,这些都表明史密斯给读者的印象是所受教育极其有限、个人没有崇高的奋斗欲望与理想、缺少对未来生活的不断努力拼搏,这些特征都使得史密斯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反英雄”形象。
三 “反英雄”形象史密斯的性格分析
1.唯我独尊的自负史密斯。
史密斯的星期天从清晨起床开始,他的许多行动都表明他基本上是自我迷恋的。早上当史密斯醒来的时候,他不是简单地从床上爬起来,而是“展开精心缓慢舍不得皇家般的”“等待了片刻他设计他的统治”这种壮观的方式来唤醒和迎接美好的清晨。当他“移驾”到镜子时,他驻足良久地欣赏镜子中的自己呈现出陶醉的神态,赞美自己面色姣好、五官端正、棱角分明,这些都表现出史密斯的自恋和“爱自己”。这些壮观景象很明显带有讽刺的语调,却是对史密斯的自负性格一种真实和犀利的诠释:史密斯是高贵的,史密斯是萨丁- 勒格日(英文satin有绸缎的意思)·史密斯,周日的史密斯才是真正的史密斯。
2.对凄凉现实否认与抽离的史密斯。
虽然史密斯表现出了自我相当傲慢自负的性格,但面对凄凉的现实情况时他似乎时常意识到自己能做的就是迅速否认和驳回。例如,第一部分中他沐浴时散发的甜美芬香讽刺性地让史密斯有身在皇族家室的幻觉,而他的真实环境却是“但你忘了还是你永远不知道他的遗产白菜和辫子熟悉的旧巷垃圾桶伸向南方(但总是美好的)深红的甜木兰把香奈儿的耻辱。”这一现实与幻觉的鲜明对比也表明了史密斯的真实生活幻觉的凄凉、贫困、潦倒与混乱。第二部分中,当史密斯提及对自己身份的认知时,想到了先祖的过去:“祖先的历史……挖出自己的身份……数以百计的饥渴与他自己的打成一片……”,史密斯停止继续挖掘先祖的苦难史, 他“迅速做出自己的考虑和反应即用最有力量的方式独自走开”,他的结论是“一切都很简单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从史密斯用最有力的方式独自走开的行动中,清晰地表明了其不愿直面自己的黑人身份,对“根”选择逃避,对现实中身为黑人的种种困难选择抽离与否认。当然,史密斯什么也不能改变。他唯有一厢情愿的告知自己这些都是他人的过去,与己无关。
四 史密斯的生活目标与梦想
起床后精心打扮的史密斯并未去参加重大的排队或集会,而是走到所住社区的街面看电影、与“涂着指甲、抹了三层唇膏、头戴大帽、身着蕾丝袜、脚踏高跟鞋”的情人一起进餐、吃饱喝足后再离开餐厅,并在夜幕来临时回家获得性欲望的满足。这些对于史密斯才是真正关心的事情,他虽毫不关心满足欲望的手段,却格外关心最终的结果。事实也证明他是知道她们的,这些事情已经成为他的常规,过去的每一个星期天甚至将来的每一个星期天例行般的享乐生活是史密斯的生活目标与梦想。
五 突显“白人审美观和价值观融合”大主题的小人物史密斯
布鲁克斯的诗歌总在不断探索在美国话语中被降格和边缘化的黑人的地位和出路问题,本诗也不例外地提出黑人如何在白人主流话语中奋力争取从边缘到中心,从无声到有声,赢得和白人平等的对话关系。第三人称叙述者在描述史密斯衣橱构造时,写道“让我们一起检查……这个衣柜的内脏谁的荣耀不是钻石、珍珠”,显然在史密斯的价值观看来,一个像模像样的衣橱内必须有拥有钻石来提升档次,这些价值观是崇拜物质主义的白人的价值观,史密斯受到其物质观同化。当黑人物质条件无法满足用钻石去争取与白人的平等时,史密斯也尽其所能在衣帽的颜色选择方面做了调整。他拥有“黄色、酒红色、夸张绿、深蓝色条纹”多件西装、窄脚裤、绅士帽、鲜艳的伞具、领带等,尽力用绚丽的颜色吸引白人的关注,成为白人眼中的潮流达人。史密斯甚至为自己的西装垫上肩垫条,努力使其在白人中看上去更加服装合身、打扮得体。在叙述史密斯的艺术审美观时写到:“这里是他的雕塑和他的艺术他所有的建筑设计你可能钟爱颇具价值的大理石巴洛克的恐怖洛可可你忘了你忘了。” 巴洛克和洛可可是代表欧洲文化的典型的艺术风格,其出现在史密斯的房间内,再次说明史密斯逐渐改变自我民族内的艺术审美观,向白人的艺术审美靠近。所有这些生活的细节都渗透着在美国种族歧视的现实下,弱势的黑人对黑白种族平等的无限渴望,他们虽生活在社会底层,物质贫乏,饱受歧视,但依然对生活充满了乐观和良好的心态。
六 小人物史密斯对黑白种族问题的解决之道
本诗作为一首自由诗,采用了白人诗歌形式和较正式的语言,同时大量引入美国口语和黑人口语,有着黑人音乐明快、简洁的节奏以及浅显直白的语言,是传统格律与现代语言相结合的产物。在塑造史密斯形象时,作家巧妙地将日常口语、黑人英语和布鲁斯音乐同直白的叙述方式结合起来使诗歌凸显出鲜明的黑人民族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在表现黑人史密斯与白人的不平等地位时,作家采用了强烈对比的手法,使种族歧视的黑暗现实得到更加鲜明的彰显。在描写黑人史密斯的混乱现实生活状态与星期天潜意识的皇家幻觉时,既揭示出黑人的痛苦和无助,也展现了其乐观的生活态度和一种不断上升的黑人愿望,所以,和传统的黑人诗歌不同,本诗反映了美国黑、白两种文化冲突及两种文化的有机结合,具有“反英雄式的”人物特征的史密斯代表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黑人的普遍心理和性格特征,具有典型性意义。在种族问题上,史密斯选择做一个温和派,建议用融合和抗争两种方式来解决美国的种族问题,提倡通过种族融合来消解白人中心主义,种族融合恰好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解决种族问题的一种主导办法。而作家也用了“黑人主题、白人风格”来支持史密斯的选择。
[1]Brooks, Gwendolyn. A Street of Bronzeville[M].New York: Harper, 1954.
[2]Kent, E. George. A Life of Gwendolyn Brooks[M].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90.
[3]Madhubuti, Haki R. “Gwendolyn Brooks: Beyond the Wordmaker— The Making of African Poet.” [M] Report from part One. Gwendolyn Brooks. Detroit: broadside Press, 1972. 11-30.
[4]Karen Jackson Ford. The Sonnets of Satin-Legs Brooks[M].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7. 345-373.
[5]王岚.反英雄[J]. 外国文学,200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