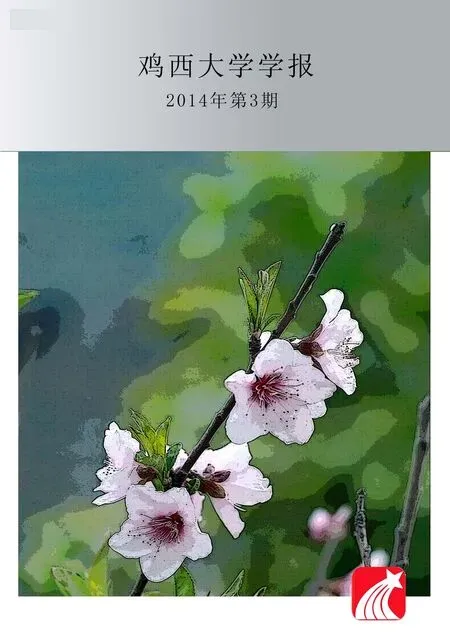浅析《归雁》中的女性悲剧观
邢向楠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作为文学研究会成立时期唯一的女性作者,庐隐是以一系列反映社会现实的问题小说登上文坛的。《灵魂可以卖吗》《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等作品深切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用工制度、军阀混战等问题。在问题小说风潮过去之后,庐隐着手开创自己的文学世界,她笔下的人生始终是悲苦的,疾病、死亡、飘零是她笔下的主人公的生命主题。从《海滨故人》《或人的悲哀》到《归雁》《女人的心》,她用这些自叙传性质的故事来表现女性在追寻独立人格和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伤痕累累而又不甘沉沦的抗争姿态,带有浓重的感伤色彩。
庐隐作品中的感伤一方面来自于她悲观主义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也与她凄苦的身世有关。庐隐的一生充满坎坷,自幼便不为生母所喜,幼年丧父,成年之后又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接连亡母、丧夫、痛失知己石评梅和疼爱自己的哥哥。她的中篇书信体小说《归雁》记录了她在丧夫、亡母、痛失知己等一连串的打击之后的心路历程,真切动人地为我们展示了她的心灵创伤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她倔强的个性,感受到她的人格魅力。
庐隐的感伤抒情风格,曾经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力倡导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情况下,庐隐的悲情被当做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持这种观点的有茅盾、阿英等批评家。茅盾在《庐隐论》中曾批评她“庐隐的停滞”。阿英在他的《黄庐隐》中,将庐隐的的悲观主义归结为“厌世主义”,并且认为她应该按照科学所指示的方向,摆脱这种厌世主义。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女性文学批评兴起的情况下,庐隐和她的作品浮出地表,有人将她笔下女主人公的痛苦,归因于社会解放运动的不彻底,以及男权主导下的社会结构中妇女解放运动的艰难,这样一来她笔下的哀伤成了女性群体的叹息。还有人从现代性的角度,将庐隐笔下的悲情归为颓废主义,认为她是个用颓废、痛苦来反对工具理性,追求审美现代化的作家。
在《庐隐自传》中庐隐对自己的悲观主义世界观做了如下剖白:“为了人生不免要死,盛会不免要散,好花不免要残,圆月不免要缺,——这些无计奈何的自然现象的缺陷,于是我便以悲哀空虚,低估了人间。同时,又因为我正在读叔本华的哲学,对于他的‘人世一苦海也’这句话服膺甚深,所以这时候悲哀变成了我思想的骨子,无论什么东西,到了我这灰色的眼睛里,便都要染上悲哀的色调了。”[1]从庐隐的文学观念上来说,与功利主义者不同,她追求的是对内心情感的表达,“至于说悲观有何用——根本上我就没希望它有用,——不过是情激于中,自然的流露于外。”[2]坦率而真诚地暴露复杂隐秘的心理创伤,始终执着地表现人生的悲哀,用自叙传的形式,充满激情地将知识青年在追求个人的自由意志、独立人格和人生价值的道路上磕磕绊绊的曲折经历表现出来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除了郁达夫,恐怕就是庐隐了。
《归雁》中的感伤浓得化不开。它记录了女主人公纫菁在夫死母亡之后回到北京的一段生活,主要围绕着她和青年剑尘之间的爱情风波展开。庐隐用哀婉抒情的笔调,将她在亡夫之后飘零天涯的孤苦无依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文中大量的对纫菁自杀倾向的描写,对人世险恶的感慨,对女性悲剧性命运的哀叹,都让人为之叹息。茅盾批评这部作品,“大约十年以后庐隐她写《归雁》和《女人的心》这两个中篇,她并没给我们什么新的,她这两个中篇依然是《海滨故人》的‘继续’。”[3]而庐隐自认为她在这部作品中暗藏了变革性因素,她在自传中写到“到了我作《归雁》的时候,我的思想已在转变中,我深深的感到,我不能再服服帖帖的被困于悲哀中。虽然世界是有缺陷,我要把这些缺陷,用人力填起来。……最后我是被旧势力所战胜,那一只受了伤的归雁,依然负着更深的悲哀从新去漂泊了。”[4]《归雁》在表现了女主人公纫菁对礼教压迫个体的控诉,流露出来的她对于命运的控诉,对于妥协软弱的自我的不满,对于打破命运的枷锁的执着,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坚韧、更加成熟的庐隐。
《归雁》充分展示了女主人公纫菁痛苦矛盾的内心,也让我们深入了解到“五四运动”后的转型社会中,在旧礼教的藩篱下,觉醒了的女性追求个性自由的诉求,以及在反抗社会的过程中所要面临的社会压力和自我怀疑的痛苦,揭示了作者庐隐作为独立个体的女性为了坚持自我的伟大和尊严所付出的代价。
社会大环境对丧偶女性的压迫、纫菁本身的善良和对独立个性的坚持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纫菁和剑尘的爱情悲剧。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社会风气虽然开化了很多,但是礼教的藩篱并没有被完全打破。社会中存在的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依然无处不在。纫菁作为丧夫的女子,与年轻又富有才华的剑尘交往,受到了很多人的非议,这在作品中由纫菁好友星辰道出。舆论上的压力让纫菁和剑尘的爱情注定无法得到世人的祝福。当我们联系庐隐后来的《女人的心》等作品,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礼教、传统道德、舆论的惊人压力,因为人永远都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的社会属性,所以人永远不可能对来自社会环境的压力免疫。知识女性勇敢追求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等与传统礼教相冲突的行为依然要面临社会大环境的压迫。同时,出于人道主义情怀,善良的纫菁不愿成为剑尘的地狱,她不愿让剑尘感染自己的深入骨髓的绝望,更不愿意让他因为与自己的爱情而陷入舆论的漩涡。纫菁本来在北京过着消极颓废的生活,随着与剑尘的相遇相知,纫菁发现自己的生命因为有了剑尘而变得热闹了起来,剑尘写信鼓励她走出自己的小世界并且接受他的感情,这种追求虽然与纫菁本来的人生轨迹相左,但是大大缓解了她的寂寞。剑尘却在与纫菁交往的过程中,受到她的悲伤情绪的感染,对人生、对社会的美好未来产生了怀疑的态度。而纫菁对他的坚决拒绝,也让剑尘感觉到不解和消沉。纫菁多次使用自私来形容自己对剑尘的依恋,因为她要的是一段没有归宿的纯精神恋爱,而剑尘需要的是稳定的婚姻和家庭,终于纫菁在跟剑尘的母亲交流之后,在感受到这位老夫人对儿子与她交往的忧虑之后,决定彻底地拒绝剑尘。纫菁对剑尘的拒绝,实质上是出于对剑尘的爱护,是为了让剑尘免于受到社会的谴责和嘲讽,能够继续在原本的人生道路上前行。无论是社会的压力,还是来自对恋人的爱护,都决定了纫菁只能辜负一段普通世俗意义上的爱情,成为无家可归的孤雁。纫菁的悲剧根本上来源于她充分尊重自己的个体价值,充分尊重自己的个性,倔强不屈地向命运抗争的人生哲学。正如纫菁在文中所说的,“与其说是受外面冷刻的讽刺的打击,不如说是我先天的根性如此,……我的灵魂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捉摸的东西,剑尘固定的‘爱’怎能永远维系得住我?”[5]在同一时期的《云鸥情书集》,庐隐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她不需要一个类似于婚姻这样的形式固定的东西,她需要的是随自己不同阶段的心理需求和感情需求而变化的收放自如的纯精神恋爱。追求自己理想的恋爱形式,不屈服于社会,甚至是自己的恋人,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努力实现自我的伟大和尊严。无论是文中的纫菁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庐隐,都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出于倔强的本性,出于对自我个体价值的绝对尊重,她不愿意向自我妥协,也就更不愿意向压迫女性和自然人性的礼教屈服,所以她选择了不断地漂泊,像一个过客那样根据自己的本心不断地行走。
《归雁》中纫菁的精神魅力在于她倔强的个性,在于她用最颓废也是最决绝的方式向社会反抗的决心和勇气。庐隐作品中大量关于社会环境的描写和女性所处地位的感慨,被很多女权主义批评家援引,作为证明庐隐的作品控诉了传统的礼教和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的观点的依据。而庐隐本人,在激烈地控诉社会地同时,也将矛头指向自身,虽然社会压力巨大,虽然命运不公,女性经过抗争也是可以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是那个不愿接受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的自我,不断地追求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自我,造成自己漂泊天涯的孤苦命运。《归雁》中纫菁提到的亡夫元涵,实际上是庐隐现实中的爱人郭孟良的化身,庐隐顶着郭孟良在老家已经有妻子的压力,毅然嫁给了他,从这个意义上说,庐隐是追求婚恋自由的胜利者,是对社会进行反抗的胜利者。可是婚后的生活的琐碎磨灭了她玫瑰色的梦。经济上的压力,再加上郭孟良的疾病和突然离世,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都让庐隐体验到婚姻的荒诞和残忍。婚姻是个茧,一个禁锢女人的茧,同时也是可以给女人归属和依靠的茧。虽然与郭孟良生活在一起的庐隐,也会写信向朋友抱怨生活中的琐碎和不如意,但是失去了元涵的纫菁认为自己就像无主的梨花,只能独自在人海漂泊。纫菁最终选择了拒绝婚姻,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她认识到,婚姻与爱情不同,爱情中尚且能够保留自己的独立人格,但是婚姻是社会学上的意义,选择婚姻必然要面临社会,要失去自我。无家可归的孤雁诚然悲苦,确实保留个人自我的最好选择。是庐隐宁愿选择孤独一生,也不愿向社会妥协的魄力,成就了纫菁们的精神魅力。
《归雁》体现了庐隐对于女性悲剧的独特思考,她认为女性最大的敌人,不是传统礼教,不是社会舆论,而是那个不愿屈服的自我。庐隐对于女性命运悲剧的认识,是基于自己和同伴们勇敢地打破礼教的藩篱、不断追求自我的亲身经历得出的结论。当庐隐总结和反思自己和同伴们的生活,这些经历过“五四运动”的精神洗礼的觉醒了的知识女性,在与家庭抗争、与社会抗争成功,终于追求到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之后,却依然无法摆脱悲惨而平庸的命运。这让她不得不正视社会变革的艰巨性,并且怀疑社会解放之于女性解放的意义所在。是追求个性向命运抗争和追求完美的世俗生活向变革中的礼教妥协,这一被五四运动提倡的新文化新道德激化了的人性当中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的矛盾造就了一代知识女性的心灵创伤和漂泊命运。女性要摆脱做他人的努力和工具的命运,保持独立的人格,向整个社会宣战,向命运挑战,只能不断地反思自我,挑战自我。
《归雁》是庐隐企图着手处理自己文学世界中的无解的哀愁、为悲观的女性寻求一条出路的作品。她通过对纫菁在坚守自我过程中所经受的来自社会和自身双重压力的刻画,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和人性本身的矛盾性和软弱性。表达了作者要始终保持个人的尊严,就只能像过客那样,成为四处飘零的孤雁,不断行走,不断追求,不断地与社会抗衡、向自己挑战,与命运搏斗的人生感悟。
[1]庐隐.庐隐自传[A].林贤治,肖建国.海滨故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205.
[2]庐隐.庐隐自传[A],林贤治,肖建国.海滨故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226.
[3]茅盾.庐隐论[A].林贤治,肖建国.海滨故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310.
[4]庐隐.归雁[A].林贤治,肖建国.海滨故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206-207.
[5]庐隐.归雁[A].林贤治,肖建国.海滨故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113.
[6]乔以钢.“五四”时代的“伤痕文学”——论女作家庐隐的创作[J].天津师大学报,1993,6:63-67.
[7]肖淑芬.庐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女权主义作家[J].扬州大学学报,2011,6:21-26.
[8]毕新伟.颓废的现代性及其流变——重读庐隐[J].中州学刊,2012,2:234-240.
[9]郭群.庐隐的自我意识[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5,5:91-101.
[10]阎振宇.郁达夫与庐隐[J].石油大学学报,1994,2:6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