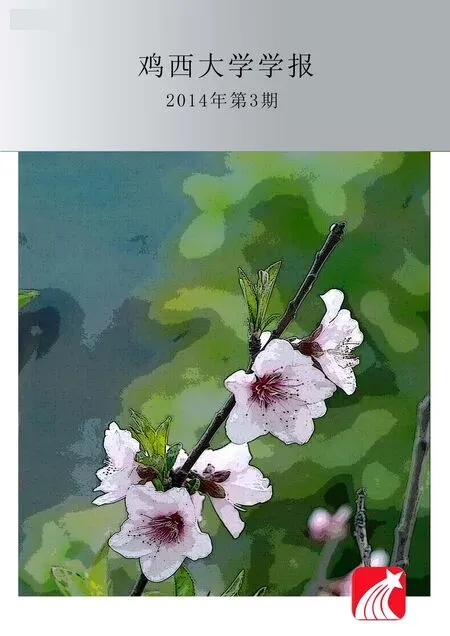沈辽与陶渊明归隐思想异同论
林阳华
(三明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沈辽(1032—1085),字睿达,号云巢,钱塘人。与沈括、沈遘合称“钱塘三沈”。据《沈睿达墓志铭》《宋史·沈辽传》《云巢诗并序》等所载,可知沈辽具有较为复杂的出世思想。他幼年即不喜仕进,因此在为官之前,即与方外人士有频繁的接触,并受到他们的佛、道思想的陶冶。即使因其兄沈遘之故,出任寿州酒税之后的仕宦生涯,他亦没有停止与佛、道人士的参禅论道。在贬谪永州、隐居池州阶段,特别是归隐池州的生活,他更加坚定了与仕途断绝的决心,佛、道思想成为了其在隐居道路中获得适意的重要源泉。沈辽的出世思想多样,由儒、释、道三教构成。本文拟探讨他与陶渊明归隐思想的异同,以此窥探他出世思想中的道家、道教思想。
一 沈辽与陶渊明归因思想的相同之处
中国古代的隐士层出不穷,他们归隐的形态种种。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大隐、小隐、中隐。其中小隐的典型代表是陶渊明。到了宋代,宋人对陶渊明的接受贡献巨大,陶渊明受到了比以往任何朝代更大的关注。其中一点在于对陶渊明的归隐给予了新的阐释。
如果将陶渊明作为一种“原型”的话,那么宋人显然对其有所取舍和运用。“人的原型有许多类型,每一类都含有独特的意义。以封建文人而论,仅从仕与隐的角度看,就有功名型、隐士型、先官后隐型、亦官亦隐型,等等。每一类原型的代表人物都是多重历史文化含义的价值集合体。”[1]陶渊明作为“千古隐逸之宗”,并不是指他为第一个隐者,而是说他的隐逸本身即有“原型”意义,且这种意义是拥有“多重历史文化含义的价值集合体”。具体到宋代时,“宋人对陶渊明诗文精神的把握也远远超出了前人。前人论渊明或赞其‘真率’,或赞其‘任真自得’,或赞其退守、‘耻事二姓’的高风亮节,或非议其消极退隐。而宋人却从另外的角度对之评述,不大论其退隐的社会价值所在,而是转向对陶个人性情与其人生态度之间关系的处理上,把个人的本真置于首位,所以大多数宋人把陶的归隐归结为他‘不与物竞,不强所不能,自然守节’、‘知其不可而不为’的自然本性,是一种缘于对自我身心自由追求的结果。宋人认为陶的退守不仅体现了陶的高洁人格,更重要的是,陶退守后能在生活中寻找到一种‘悠然自得之趣’。并发明出陶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便在于他‘此心淡无著,与物常欣然’。陶的‘心淡’,宋人认为是一种‘不为物累,不为情牵’、‘不以物喜,不以物怨’的对外在名利的超然,是有志于‘道’的表现。”[2]时人之所以赞赏陶渊明的隐逸是“一种‘不为物累,不为情牵’、‘不以物喜,不以物怨’的对外在名利的超然,是有志于‘道’的表现”,是同宋人的人生观、仕隐观紧密联系的。在他们看来,陶渊明的归隐重要的不是他是否是“耻事二姓”、是否是消极退隐,而是他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处世的良好典型借鉴方式,以使他们能够超越名利的束缚,而追求本真、自然。于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宋人如此欣赏陶渊明的归隐态度。
沈辽对陶渊明也较为推崇,在他的诗歌中,他或以陶渊明自比,如《答金山禅师》云:“远公手札远相招,陶令怀归正郁陶。遥想宴堂长夏静,坐临江水看风涛。”或以陶渊明他比,如《春晚偶题》云:“幸有陶公五株柳,不恋河阳千树花。数日东风吹欲尽,小轩寂寂日西。”或直接流露出对他的追随,如《杂感》说道:“咄咄待秋至,秋至安足惊。年华去如扫,正如宠与荣。区区白驹隙,君子慎所行。不如陶渊明,超然自归耕。”《西斋》亦云:“东斋清旷西斋静,上下往来唯一径。幸有方床不得眠,行休已有陶潜兴。”
除了陶渊明之外,对其他隐士,沈辽亦对他们推崇不已。如对严君平的不慕仕宦,而以算命维持生活、闭门读书的高尚行为给予了赞赏。这批隐士,与那些推行大隐和中隐的隐士不同,他们不为五斗米而折腰,也不为了高官厚禄而违背自己的人格。他们的身上保持着一种纯真、悠然自得的品格,他们知足常乐,以道家“无为”的态度泰然处世。《杂诗六首》其六云:“达人体无为,泛泛若野马。胡为狂夫志,愕然小天下。知足自有余,多谋始恨寡。可否必系己,出处焉用假。大块劳群物,吾生信容冶。死生会如一,高情乃能舍。”他们能不苟求,能态度容冶地对待人生,这也是沈辽歆慕他们的原因。当然在沈辽推崇的隐士之中,陶渊明是居于首位的,因为他们的归隐有诸多相似之处。
关于陶渊明的思想宗儒宗道孰重孰轻的问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有研究者对此给予了较为通融的解答:“总的来说,渊明一生执着于自然,同时也是执着于名教。如果把他一生分为三期的话,他早期‘游好在六经’,学的是忠孝信义,不曾废弃儒学,是执着于名教;后期坚持隐居,安贫乐道,也是执着于名教;中期时仕时隐,在官场‘外坦荡而内淳至’,行不苟合,反对矫伪,是执着于自然,同时也是执着于名教,这就有力地说明渊明无论仕隐,他自始自终都是名教自然合一的信奉者,然又与假名教假自然派迥别。”[3]此种论说对解决陶渊明的思想纠纷,确实有重要的意义,值得重视。陶渊明一生确是自然和名教合一的信奉者,而且不管是以上所划分三期中的哪一期,即使是第一和第三期,他其实都是既执着于名教,又坚守自然的,这样解说当会更加合理有力。对陶渊明思想的这种说法,同样也适用于沈辽,但后者更为复杂。
沈辽的一生大致亦可以划分为三期,而且他最终像陶渊明一样走上了归隐的道路。
第一期是他为官之前。当时他“幼挺拔不群,长而好学尚友,傲睨一世。读《左氏》、《班固》书,小摹仿之,辄近似,乃鉏植纵舍,自成一家。”[4]与陶渊明一样学习儒家经典,执着于名教。但已无心仕进,不愿意违背自己的本真,这与陶渊明有所不同,他此时的归隐当为“市隐”,为隐于城市的非官吏。这样的身份使他相对自由,故有很多与佛道徒亲密交往的机会,并较早就有出世思想。沈辽服完母丧至开封时,王安石父子称颂其似陶渊明,可以看出在此之间,沈辽即已推崇陶渊明,并与之有几分相似。
第二期是他的为官时期。他虽然欲为民解决困难,但心有余悸,而且对官场黑暗现实的深入认识,使他常常有归隐之念。《走笔奉酬正夫即次元韵》云:“壮心欲驰步辄跚,试出锋颖官已瘝。中心忽忽倦且烦,不如归去江海闲。要悬大刀数抚镮,何陋九夷与八蛮。自顾鄙性疏且顽,谁能随时事黠奸。从来多病筋力孱,正当落魄卧深山。”疾病缠身,精力不济,也为他性情耿介,不善于为政,欲归隐找到了借口。同时,他与陶渊明一样,虽贫但反对矫伪,行亦不苟合。《次韵和李正甫》说道:“故国重寻梅柳春,自怜头上二毛新。已知悯默安无位,宁免低昂为有身。前日少年都自梦,比来贱仕始忧贫。多惭幕府文章客,都为风光作主人。”尽管悯默无位,“贱仕始忧贫”,然而不会为了名利富贵而随人低昂,因为这样就不能随心自适,这与陶渊明也相像。但陶渊明五仕五隐,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徘徊与挣扎,而沈辽则没有这样做。且他在此期仍然与佛、道人士谈佛论道,佛、道思想有了新的发展。
第三期是他被流放永州与归隐池州时期。虽然沈辽在永州时,由于遭受贬谪,行动有所不便,但是彼时他已类似隐者。而至池州时,他游览于九华、秋浦,筑室于云巢,已是对官场完全失望的隐士。由于不再牵涉仕途,《送曾处善赴宝应尉》云:“我初隐身治蓬藟,余生不复人间世”,故能洁身自好,坚守隐德。他隐居齐山时,与陶渊明呈现出更多的相似之处。如以下两首诗所说,其中《次韵伯成见赠》云:“水上浮云断不还,松间幽石自斑斑。柴门不接红尘路,满座长将白日闲。往解谁能寻赤轴,无情还自爱青山。清泠台下无多路,断葛枯藤不足扳。”《开北山望白石烂》亦云:“欲寻白石烂,故开北山路。所向虽似殊,吾真得孤屿。容与水上云,娑罗月中树。胜意已自适,何必方舟渡。”诗中所体现出的如水上云一般容与、同月中树一样婆娑的自适状态,以及不用为世事忙碌而丧失本性的闲适心境,是他与陶渊明共同的道家委运任化思想的体现。
且此种“悠然自得之趣”“此心淡无著,与物常欣然”的精神风貌,正是宋人欣赏陶渊明归隐境界的某一方面,亦是沈辽与陶渊明的共同之处。另一方面,沈辽与宋人对陶渊明归隐境界的实践途径又有所不同。宋人普遍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再加上儒、释、道三教的融合等原因,他们不会像陶渊明一样走上真正的归隐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归隐”更多的是如同以苏轼为代表的“吏隐”。他们虽学陶渊明,但并刻意在形迹上仿效之,这正是宋人之所以学习陶渊明,而不尽像陶渊明的重要原因。而沈辽则既在形迹上仿效陶渊明,又在精神上与之契合。所以沈辽对陶渊明的“原型”意义的认识和改造,是与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人有所不同的。
另外,尽管沈辽在精神和形迹上皆仿效陶渊明,然而他们的最终归隐又有些不同。陶渊明在归居园田之后,并未忘记仕途,他常常回忆少年时的兼济之志,因此呈现出心理上的矛盾,但是他最终运用道家思想将其较好的融合,化解了困惑。而沈辽则不同,他不再关心仕途,对待仕隐的态度已没有像陶渊明那样的挣扎,因此对道家的去伪存真思想有更加纯粹的接受。沈辽《谕客辞》认为被人质疑与非难的隐士,是一个能离世而葆真者,他委形于山林,凌风驾云。由于不以杜几惊俗,不仿效屈原以宣泄悲愤,亦无暇和同于群物,因此能看到他的坚贞。但是那些惶惶于世俗之人,对此却大为困惑。沈辽对他们的行径表示了不满,在他看来,这样的隐士才是较为理想的,所以他在归隐池州时,不以归隐为忧,能够“离世而葆真”。事实上,从他作于隐居池州的诗文来看,确实是如此的,诗文风格并没有牢骚不满之意,虽多与友人交往,有部分唱和之作,但涉及的多为谈文论艺内容,以及游山玩水的适意之情。
二 沈辽与陶渊明归隐思想的不同之处
沈辽的归隐思想与陶渊明的不同之处,还表现在:它还与道教有关。“正因为陶潜是主张形尽神灭的,所以他并不相信鬼神和因果报应等一套。”[5]陶渊明所处的晋宋时代,虽然佛道教、玄学兴盛,他也与慧远等方外人士有所交往,但他坚持的是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与无神论,沈辽处于宋代,科学较之更为发达,但他却相信道教。
道教的长生不老之术,为中国古代广大文人所信仰,沈辽亦然。他原本是以儒士的身份同道士交往,且交往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向他们学习长生不老之术。其诗文中阐述与道士往来,且追求长生不老方法的信息不占少数,如《赠有道者》说道:“昔吾知养生,始自皇人经。其说乃浩博,隐奥通神灵。锦囊固申行,梦寐嗟沉冥。十年不一开,未甘遂遗形。矫矫高平生,真诀炳丹青。要妙不在多,一言如发硎。使人久滞念,霍如病已醒。岂徒固衰朽,且将延百龄。”《寄赠舒州徐处士》亦云:“昔爱灊川游,青林覆幽石。道人携手行,萧然名山客。谁知堕世路,譬如羁飞翮。林皋未脱去,纷纷头欲白。轻负皇人经,犹怀稚川策。幸已弃韦带,远谢功名迹。聊希闭关士,正苦身为役。别来二千日,还丹应有获。毋忘锋囊赠,使我升仙籍。将酬金镮脆,青绫三万尺。”由此可见,沈辽很早即与道士有密切的交流,而其谈论的话题正如上所说,是探讨求道成仙之路。而且亦不难看到,沈辽虽然依照他们的指导方案实施,但其间有所间隔,他也领悟到亦达到此目的,需要付出较大的努力,所以说:“幸已弃韦带,远谢功名迹。”这一种观念在他的其它诗文中,亦有所体现。如《寄赠伊先生》云:“在昔齐光禄,招余访仙宫。崇岩九叠峻,行望庵前松是时先生种松自虚仙观,此关连至庵下。下马过星坛,超然挹孤风。华冠映绀发,谈笑想鸿濛。饮之青菁饭,喻以朝元功。顾余方羁束,焉能谢人中。闇黮七八岁,日月何匆匆。吾非久寐客,不烦一言攻。己知弃宠辱,安能为世庸。还丹何时就,白云弄秋空。相望江湖上,杳杳复蒙蒙。”对于沈辽来说,欲长生不老不仅需要“己知弃宠辱,安能为世庸”,而且他对此也深有领会,“吾非久寐客,不烦一言攻”。由于需要以上的这些条件,方可以更好地不延迟进程,因此选择不涉人世的纷扰,选择归隐就成了其实现这一目标的良好途径。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沈辽在诗文中流露出急于归隐的情愫。
沈辽所学习的《皇人经》等秘笈,为其加深对求道成仙之术的认识当有较大的帮助,其中之一即是以上诗中所说的“且将延百龄”。且这种欲望,从其早期一直延续到即将死亡之时。以上所举数例可作为其早期求仙学道的明证,而至贬谪零陵阶段,亦没因为流放的身份而停止过。《云巢编》附录《沈睿达墓志铭》云:“君(沈辽)昔在沅、湘间,闻有道士善捕逐鬼魅,役使丁甲,人甚神之。过南岳闻其适至,亟召之。已去矣,常恨失之。”在零陵时,沈辽曾与王道士和博古、太古等隐士、道士交往。王道人曾请人画沈辽像,沈辽为此作有《题画像》,已见上文。他又写有《次韵博古赠王道人》,其云:“调笑同方朔,机微似幸灵。囊中万金药,机上九仙经。虚静孤猿噪,支离病鹤形。子云称隐德,于此识沉冥。”在《题画像》中,沈辽称王道人为“卧鹤山人”,所谓“支离病鹤形”,即是对他具有仙风道骨的形容。他的囊中有万金药,机上有九仙经,俨然就是一个仙界人物。
等到沈辽归隐池州时,作有《奉送太古归旧隐》:“人生富贵无金丹,须臾白骨凋朱颜。何为愁苦强作乐,逍遥不去烟霞间。吾昔东游岂无意,腰下铜章初不关。至今山水尚可想,断梦时向荆溪还。安得此身如白鹤,飞与道人天外闲。路逢仙友若相问,为道绿发今斓斑。”沈辽与太古此时均为隐士,且他们皆求仙学道,人生“须臾白骨凋朱颜”道出了其学道的主要原因。往昔苦苦探究,而今已大有所获。这正是他信奉道教长生不老之术,以及选择最终归隐的结果。换句话说,是道教的长生不老的“车轮”载着他踏上了归隐的道路,而归隐反过来也推进了他更加相信长生不老“神话”的存在。
直到沈辽即将亡故之时,仍然追求着长生不老。《沈睿达墓志铭》云:“一日,在齐山,道士者忽来。欣然迎见,(沈辽)从容问曰:‘富贵非吾愿,所欲知者寿耳,为我视之。’道士许诺,归夜作法,入冥穷观。明旦,谓君天上构楼已就,可趣治装矣。道士去无几何而卒。”在沈辽看来,求仙学道的目的并不在于取得富贵,而是为了长寿。因此他与当时那些倚靠求仙学道以获得名利、富贵的高官显宦不同,而是以隐士的身份来实现延年益寿目标的,显示出较大的虔诚性与较长的持续性。
综上所述,沈辽在踏入仕途之前,已具有强烈的出世思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对官场的黑暗已有所认识,再加上仕宦经历的坎坷,不善于为吏等原因,促使他常常有归隐之心,并最终归隐齐山云巢,坚守道义和固穷守节。他早期即与佛、道人士交往,佛、道所倡导的出世思想,特别是道教、道家的离世保持本真,追求自然的理念,使得沈辽对他们的行为大加赞赏,其中的代表是陶渊明,因此沈辽与陶渊明的归隐思想有较大的相似性。而道教的长生不老思想,同样推动了沈辽隐逸欲望的加强,这与陶渊明坚持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与无神论是不同的,因此也成为了两者归隐思想的差异。
[1]张海鸥.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54.
[2]何海燕.宋代文人对陶渊明的接受[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104.
[3]李华.陶渊明新论[M].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212.
[4](元)脱脱.宋史[M].中华书局,1977:10652.
[5]李锦全.陶潜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112-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