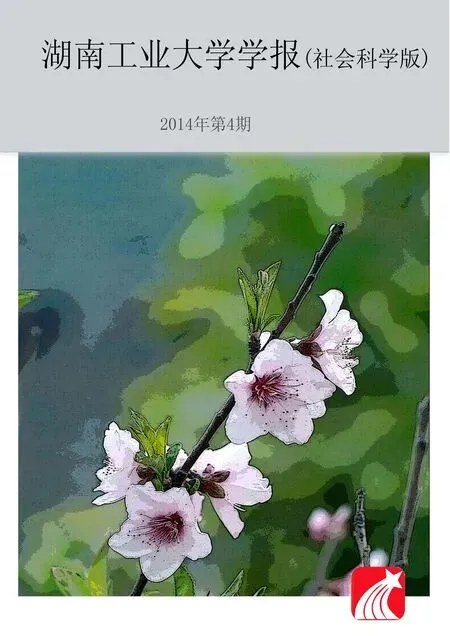论《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真与善*——兼论一种本体论的伦理学
杜海涛
(西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真与善的关系的问题是贯穿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开始就把伦理学的性质定位为不同于像数学和自然科学等追求绝对精确性的学科,因为伦理学关涉的更多的是具体生活中的践行,而非一种关涉知识性的真理。所以他说:“从如此不确定的前提出发来讨论它们时,只能大致的、粗略的说明真。”[1]7这也是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驳斥过苏格拉底“德性即知识”的学说的理由。从思想背景来看,亚里士多德也在企图解决荷马史诗和智者派遗留的德性相对主义问题,这迫使他像柏拉图一样追求一个实践推理的“第一因”。但这个第一因虽是起源于经验归纳,但却具有深刻的形而上学意义,体现出一种绝对真理的意味。这和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始时对伦理学性质的定位明显不一致。
亚里士多德强调德性更重要的在于习惯的养成和具体的践行,那么实践上的“善”是否真的对应一个他所谓的具有真理性的“善本身”呢?在探索这个问题的方式上,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批判苏格拉底式的“logos 庇护”,即在言辞和逻各斯的辩证之中来把握“善”,但同时也承认了“只有哲学才能发现人类卓越性的真理”。他所谓的合于中庸的勇敢、节制、公义等德性,其实也是哲学的勇敢、哲学的节制、哲学的公正。那么这些涉及到“善本身”或“德性本身”的探讨,不论把它当做知识性的,还是实践性的,其实都面临着真与善在伦理学中难以统一的困境。
一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高尚的不确定性”和本体之真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继承了古希腊本体论传统,认为处于流变中的事物表象是不具有本体意义的,因此是相对的,不具有真理性。按他的学科划分,伦理学并不是一种关涉形而上学的学科,不像数学和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绝对必然的意义。他说:“今天有人因为富有而毁灭,或由于勇敢而丧失性命。”[1]7特西托勒说:“的确,由权威观点上升到真正的知识,刻画了哲学生活的本质活动。但亚里士多德选择由反思、并在某种程度上由保留高尚的不确定性来开始研究,正派的学生而不必然是哲学学生,就其有这种不精确性之特质。”[2]所以伦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生活中的事件,而且这些事件在不同的场合境域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原则,由此,伦理学毋宁说是一种合情性的学问。赵汀阳说:“合情性稍微接近于sensibleness,它意味着理性理由之外、但与理性理由同样有力的感性理由……于是它和理性理由是同水平上的无可置疑的人性理由。”[3]但亚里士多德认为,恰恰是因为这种“高尚的不确定性”人才可以考虑和选择。因为人“不会思考永恒的东西,如去考虑宇宙,或正方形的对角线和边的不等关系……我们能够考虑和决定的使我们可以努力获得的东西……考虑是和多半如此、会发生什么又不确定,其中相关的东西又没有弄清楚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1]67所以不确定性才使人的自由得以可能,人之所以能够自由考虑和选择,是因为在伦理领域人们所面临的境遇,并不像数学或形而上学领域一样具有必然性和永恒性,而是不可预言的,它需要人类的实践去证明和完善。人类在不确定性的具体操作中运用理性,寻求合乎中道、代表人类行为特殊性的准则,并为了高尚之故。所以特西托勒才称之为“高尚的不确定性”。
特西托勒所说的不确定性,是相对于中庸而言的。亚里士多德说:“对适当的人、以适当的程度、在适当的时间、出于适当的理由、以适当的方式做这些事。”[1]55因此面对不同的境遇,合宜的行为就是德性的行为,所以才有了勇敢、节制、正义等诸德性。这些德性分别代表着两种过恶的中道,如勇敢是鲁莽和怯懦的中道。过和不及的道路有很多,但通往中庸之道却是唯一的,因此亚里士多德是在诸多不确定性之中寻求那个“所以然”的东西。这也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真理知识的契端。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在当时社会面临着两个背景:一是智者派出售辩术导致的德性相对主义传统,二是柏拉图的理念论的哲学体系。前者为达到特定目的,以辩术为工具,诠释德性,导致了德性的相对性;而后者一生致力于寻求一种绝对的善,为世间的善恶究其根源。
亚里士多德企图建立一种具有绝对意义的伦理学,去打消智者派的相对主义流弊,但同时他又不同意柏拉图的善理念学说,因为他认为柏拉图不能说明善的使用的多样化。而且柏拉图用来解释善的理念的那些语言,事实上不能算作解释。谈论善“本身”显然并没有给“善”增添什么,理念是永存的是会将人引入歧途的,某物永远存在并没有使它在任何一点上好一些。所以他没有像柏拉图一样寄托于一种善的理念,而是以一种“人的功能性”的本体论预设为整个伦理体系的始基。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本体论具有真理性、超越性的意义。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将存在(being)作为本体,其代表了最为本质、最为基质的东西,也是其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普特南在其《无本体论的伦理学》中认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人的功能性”的论证模式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使用。由此“功能性”也成了伦理学众多不确定性中最“真”的东西,这也是本文关于“真”的论述真正的所指。
麦金泰尔说:“亚里士多德传统内的道德论证至少包含一个核心的功能性概念,即,被理解为一种本质的本性和本质的目的或功能的人的概念。”[4]74“本质”或“本性”其实已经有了一种形而上学本体论上的意义,是一种具有真理性质的预设,具有绝对性和普遍性。亚里士多德说:“正如眼、手、足和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有一种活动一样,人也有一种不同于这些特殊活动的活动,那么这种活动究竟是什么?生命活动也为植物所有,而我们所探究的是人的特殊活动。所以我们必须把生命的营养和生长活动放在一边。下一个是感觉的生命的活动。但这似乎也为马牛和一般动物所有。剩下的是那个有逻各斯的实践的生命。”[1]19在这里人的功能代表着人之为人所具有的特征,其有两层含义:(1)人的功能性异于其他物种,为人之独有。(2)使整体变好的品质。亚里士多德把人的功能性定义为逻各斯或理性,其实就是说理性或逻各斯是人人所固有的特性,人类的行为也应该是一种符合逻各斯的行为,人拥有理性会更好的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这种定义其实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预设,因为说人的本质是理性,既是一种极度普遍的概括,而且无法被经验所证明。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在现当代伦理学界被称为美德伦理学。美德伦理学不同于一般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伦理学的地方在于,它认为人类德性的践行的动机不是具体现实的目的,而是人的人格性的完善。这是一种“实现”模式,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中提出一种从潜在到现实的实现模式,在伦理学中他依然在运用此模式。麦金泰尔把这种实现模式概括为一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构架,即“偶然所是的人性(human nature as it happens tobe)(处于未受教化状态的人性)最初与伦理学的训诫相左,从而需要通过实践理性和经验的指导转变为实现其目的而可能所是的人性(human nature as it could be if it realize its toles)。”[4]67道德之动机最终落实到“实现其可能所是的人性”这一目的(toles)。这样就不同于所有以快乐和功利为动机的伦理学,因为人的功能性已是最大的事实,道德活动的本质在于人格的完满,在于人的理性本质在行为中的体现,所有德性的践行都是为高尚(noble)之故,因此学界也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为美德伦理学。
二 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伦理学”可能面临的逻辑困难
亚里士多德把属人之善定义为“灵魂符合逻各斯的实现活动”,这个结论的得出是从人的功能性预设开始论证的,可是从一个关于人性的事实性的陈述,怎么能够得出属人之价值?亚里士多德企图用功能性的本体概述,来创立一种超越功利的伦理学,他的一系列关于德性和幸福的学说也以此为始点,那么其中很自然的面临着“是”与“应该”的自然主义困境。
不仅是亚里士多德,从西方伦理学史来看,自柏拉图以降,西方哲学家大多有本体论伦理学的倾向。如基督教伦理学的道德训诫就不仅是一种神定法的表达,而且也是一种本体目的论。原罪的概念和上帝的意志作为必然的人性和行为的终极目的,其实也是本体论的一种表达。康德直接将其伦理学定义为道德形而上学,企图建立一种像数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必然性的伦理学。但休谟对“是”与“应该”的关系的怀疑,从逻辑上质疑了这种本体形态的伦理学。他的这一问题引发了伦理学对伦理的逻辑和语言的研究。及至近代,本体论与伦理学的关系出现了三种不同观点:“一是试图彻底将伦理学与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分离开来,主张‘无本体论的伦理学’,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哲学家罗蒂和普特南;二是彻底颠倒近代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关系,不是形而上学为伦理学奠定基础,而是伦理学替代并完成第一哲学的使命,将伦理学本身视为‘第一哲学’,其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三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摇摆派,一方面拒斥形而上学,另一方面却又将‘本体论’(Ontologie)阐释为‘实存论’,从而以‘实存哲学’取代伦理学,其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5]
不论是本体论的伦理学还是后来的情感主义或实用主义,其实都是为人类的道德寻求一个根据,为善探求一个根源。情感主义或实用主义把这种动机诉诸于效率或个人的情感体验,充满相对性和不确定性。而本体论伦理学的方法是将这种根据寄托于一种人性的基础,德性践行的过程,同时也是人格实现的过程。但是这种伦理学构架本身面临着事实和价值无法统一的困境。人性是一种事实,而德性是一种应然性的践行,以“事实”之属性来言说人何以“应该”做某事,始终存在逻辑困难。黑尔说:“如果一组前提中不包含至少一个祈使句,则我们不能从这组前提中有效的引出任何祈使句结论”。[6]任何道德命令从动机到结论,在推理过程中必须有一个祈使句作为前提,如:
大前提:把全部箱子搬到车站去。
小前提:这是其中一个箱子。
结论:把这只箱子搬到车站去。
也就是说在大前提和小前提中,必须有一个是表达命令式的祈使句,如果两个前提都是陈述句,无法形成道德命令。如:
大前提:人的功能性是logos
小前提:我是人
结论:我应该做符合逻各斯的事
下面这组前提和结果之间明显存在着间然性,这意味着以事实性的人的功能性直接作为人的道德动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将面临着摩尔所谓的“自然主义谬误”(摩尔在其《伦理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自然主义谬误”这一观点,其实是休谟关于“是”和“应该”难题的另一种表述)。但麦金泰尔说:“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最初论证,预设了G.E 摩尔所谓的‘自然主义谬误’根本不是什么谬误,而且,关于什么是善的陈述恰恰是一个事实陈述。”[4]187麦金泰尔所说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最初论证,其实就是关于“善”的论证,那么善究竟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体系中占居什么位置,和真又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有了这个论证就可以忽略了摩尔的诘难呢?
三“善”的事实性意义和价值性意义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善,善首先是一种欲求的目的,对于人而言,可被欲求的就是善的,可是每个人的欲求都不一样,所以善也便是相对的了。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善本身”的说法,善本身就是指最高的善,它的基础是欲求的层次划分,低一级的欲求是实现高一级的欲求的手段,由此形成了欲求之链,欲求之链的顶端是终极的善,它只作为目的,不再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善是善本身。善本身意味着一种真正的善,不再是相对的善,其便有了一种本质的意义,因而,在这种意义上,善不仅是一种人们对于幸福的价值评价,同时也代表着一种事实或真理。这种善本身便是幸福。
既然善是一种目的和欲求,那么真正的善就是真正值得欲求的东西。那么什么才是真正值得欲求的东西呢?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善的论证,亚里士多德依然寄托于人的功能性。伯格说:“当在追求或回避中所显示出来的欲望的正确性与在肯定或否定中所显示出来的思想的真理符合一致的时候,行为的始因就是真的。因此,选择作为行为的来源显得像是与它自己的双重来源,即欲望和为了某物的logos 的杂交产物。但是如果logos 自身就是导向一个目的的,那么,他就不再与欲望并立为二,因此,它就可以不再被局限为一种工具性的考虑,臣服一种由欲望的独立功能所给定的非理性目标。”[7]人类的选择和行为体现着人之为人的卓越,人类的卓越在于合乎理性的行动。那么人类应该选择一种合乎理性或逻各斯的行动,这也是人的理性和功能性在行为中的表达,它支配着人趋向于某种善。
麦金泰尔说善是一种事实性陈述,是因为善作为目的(toles),所指的同时也都是可欲的事件,所以我们表达一种善其实也就是指向作为目的的对象。但在另一方面,善(good)包含着评价的意义。黑尔认为事实陈述本身就包含着一种评价,因为如果陈述的事实具有“合目的性”,那么它肯定意味着一种善的评价。如我们说“这个表走得很准时”,这句事实陈述其实包含着“这是一块好表”的价值评价。但在日常应用中人们往往忽略善的事实性意义,只看到其作为评价的应然性,所以导致一种真与善、事实和价值的分离。
一门伦理学只要试图探究“什么使人生值得赞美和有意义”,或试图告诉人们如何认识自己生活的目的并为实现一种好生活的内在目的而培植自己的内在品格和美德,仅靠“经验”是不够的。因为人的有限性的事实决定了我们在伦理学中需要一种形而上学的方式。所以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功能性的本体论预设是其论证的核心,以此保证了其逻辑体系的完整性,并切实开辟了一种伦理学模式,为人的道德实践给出了一个逻辑上具有绝对意义的依据。
在近代的伦理学中,之所以倾向这种本体论的伦理学,其实跟理性本身的发展有很大关系。理性在中世纪神学中与信仰始终保持着对立的姿态,在哲学和神学的调和中,最终沦为神学的婢女。在启蒙运动以后,启蒙主义者大力倡导理性,但其实并没有把理性恢复到中世纪以前的高度。休谟一方面强调经验在认识中的绝对作用,同时发展了加尔文主义的理性观。他说:“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8]可见在休谟看来理性仅是算计目的的工具。正是这种理性的狭隘性,它的功能仅存在于事实层面的利用和计算,其本身无法顾及到价值领域。因为目的的设定是激情的作用,与理性无关。这就造成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所以休谟才能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著名的“是”和“应该”的难题。
在伦理学中,面对事实和价值的分离,更应该考虑的是认识事实的理性在本质上是否具有价值意义。从韦伯或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定义来看,休谟对人类理性能力的规定可以算作工具理性的先驱。康德虽然把人的实践能力的必然依据归之于人的理性本性的尊严,可在他的认识论中排斥了理性有认识物自体的能力。人的理性本身无法把“理性”当做本体来认识,因此理性尊严不能实现在本体论上的应用,它本质上也不具有价值意义。20 世纪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认为现代性所谓的理性,实质上是一种非理性。霍克海默说:“在它实现的时刻,理性变得非理性而愚蠢。”[9]因为这种理性无关人生的意义,只关心以合适的手段达到一定的目的,这种理性也被称为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工具理性除了自我保存之外没有别的目标,像宗教和艺术一样,它把情感从自身中排除出去。
哲学需要一种本体论的理性观,这也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功能性没有沦落为工具理性的原因。作为人的本体,理性本质上代表了一种价值,亚里士多德通过人的道德实践对人的功能性的实现的论证,将人的最大善、最大幸福定义为理性的沉思的生活。既然是被实现的,其本身肯定就意味着目的,这是不同于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的地方。再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善本身也兼含着事实和价值两层意义,所以后来的基于事实和价值的批判也不适用他的伦理学。
[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特西托勒.德性、修辞与政治哲学——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解读[M].黄瑞成,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3.
[3]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
[4]麦金泰尔.追寻美德[M].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5]邓安庆.“无形而上学的伦理学”之意义和限度——以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三种论证为例[J].哲学动态.2011(1):48-52.
[6]黑尔.道德语言[M].万俊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0.
[7]伯格.尼各马可伦理学义疏——亚里士多德与苏格拉底的对话[M].柯小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180.
[8]休谟.人性论:下册[M].郑之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453.
[9]麦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李小兵,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