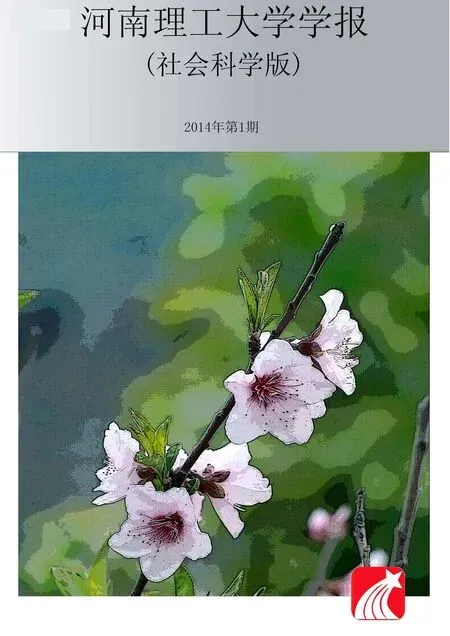论《金瓶梅》的“伦理—道德”形态
孙全胜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南京 211189)
论《金瓶梅》的“伦理—道德”形态
孙全胜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南京 211189)
《金瓶梅》的道德形态和伦理形态以同质异构的方式显示。道德形态指向个人的主观世界,伦理形态面向外在的客观世界,二者契合于实现德性生活。因此,《金瓶梅》的“伦理-道德”形态建构,不仅面向个体德性的塑造,也寄希望于群体伦理纲常的完备,并以主客结合的模式建构趋向真善美的道德规范。
《金瓶梅》;伦理形态;道德形态
《金瓶梅》的现实主义性质与理想主义追求,使它不仅具有道德形态,也有着伦理形态。其道德形态直指人性阴暗之处,呼吁个人恪守内心、远离“酒色财气”、节制欲望;其伦理形态痛斥社会环境和等级秩序,期望建构完备的群体伦理,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在获得基本需求后,生活得更好就成了人的进一步希望。建立真善美的道德规范,正是《金瓶梅》“伦理—道德”形态的宗旨。道德哲学只是对人生存状况的关怀,并没有超人类的权威立于后。《金瓶梅》揭示荒诞的人生境遇,不仅是为了从“伦理—道德”形态层面宣扬“因果报应”,而且是为了在批判世人假恶丑的表演中,发掘出真善美的道德规范。
一、《金瓶梅》的道德形态:节制个人欲望
《金瓶梅》的道德形态彰显在对节制个人欲望的倡导。它揭示了情爱的荒诞:热闹背后的肃杀,充实过后的空虚。情爱之所以荒诞,是因为它源自偶然的冲动。情爱是强大的进化法则,《金瓶梅》在一开头就指出了情爱的虚无本质及害处:杀人利器。情爱始于冲动,一开始就带有盲目的色彩。“那西门庆见妇人来了,如天上落下来一般,两个并肩叠股而坐。”[1]34他们的相遇始终充满功利,西门庆看到的只是潘金莲“白生生的腿,肉奶奶的胸”,而潘金莲看到的则是西门庆的财富。这样一个感官的世界,他们为了欲望,把自己逼上了绝路,“良久,王婆在茶局里冷眼张着,他在门前踅过东,看一看,又转西去,又复一复,一连走了七八遍”[1]21。西门庆和潘金莲早就暗通情意,他们苟合在一起,只是时间问题。曾经年少爱追梦,他们一腔热血,以为情爱生活多么美好,而最后空留叹息,像是做了一场梦,始终醒不了。恨自己,恨社会,他们陷入了自卑、痛苦、自责的深渊。朦胧中,他们是在等待,等待一场如雨的爱情,可她们又不能等待,因为绝美的爱情,只是梦幻。和所爱的人在一起,当然会有种很美好的感觉,可这种美好感觉既不是来源于所爱之人的美好,也不是来源于恋爱生活的美好,而是来源于意识欺骗和本能冲动。爱情需要男人的无耻,女人的可爱。恋爱的男女双方其实是正在谈判的对手,男人考虑的是如何使用最小的投入(投入包括时间、精力、情感、资本等),以换取最大的收益;女人运筹的是如何彻底识破男人的真实目的,万不得已,决不能突破最后一道防线。“大官人你在房里,便着几句甜话儿说入去,却不可燥暴,便去动手动脚打搅了事,那时我不管你。你先把袖子向桌子上拂落一双箸下去,只推拾箸,将手去他脚上捏一捏。”[1]25爱情始于偶然的冲动,而归于必然的虚无。
情爱之所以荒诞,是因为它与占有欲紧密相连。潘金莲和西门庆本没有交合的机会,是一阵风让拿着叉竿的潘金莲正好打中刚出殡回来的西门庆,他们的情爱一开始就与死亡相关,妾的死亡丝毫不能阻止西门庆的继续寻欢,“一日,三月春光明媚时分,金莲打扮光鲜,单等武大出门,就在门前帘下站立。约莫将及他归来时分,便下了帘子,自去房内坐的。一日也是合当有事,却有一个人从帘子下走过来。自古没巧不成话,姻缘合当凑着。妇人正手里拿着叉竿放帘子,忽被一阵风将叉竿刮倒,妇人手擎不牢,不端不正却打在那人头上”[1]17。西门庆见了美人潘金莲,心早跳作一团,只是想尽快占有那白嫩的肉体;而潘金莲见了浪子西门庆,也早已是春心萌动,留恋万分。当西门庆听说,潘金莲这个美人竟然配与武大时,更激起了他的强烈使命感,决心让潘金莲享受该得的幸福。人在脆弱之时,经不住温柔。转眼之间,他们就急不可耐地宽衣解带了。在这场肉体碰撞中,西门庆得到了欲望释放,久受压抑的潘金莲也获得了肉体的满足,而王婆不仅得了送老衣服,还得了银子。真是一举三得的好事。可怕的不是环境,而是人心。情爱之本质是欲望,满足一个欲望,必定带来更多欲望。情爱最常见的形式就是两性之间的捕捉与追逐。情爱体现着弱肉强食的法则,它是通过伴侣间的接吻、拥抱、爱抚以及性行为等法则表现出来的。女人为了爱情,彼此仇视和愤恨。情爱体现的不是良善,而是占有欲。没几日,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偷情就被无聊而世故的街坊们谈开了,人人都冷漠而津津有味地窥视他人,任凭弱肉强食、卑鄙横行。郓哥怂恿武大抓奸,并不是出于正义感和同情,而是因为分不到油水眼红。即使偷情的信息,也需要请客吃饭才能交换得来。武大即便老实,也不是傻瓜,他早疑心金莲了,只是没发作出来。精心策划的抓奸行动终于开始了,西门庆先是吓得钻到了床底,继而在潘金莲的怂恿下,把武大打了个半死,而围观的人群冷漠地看这一场好戏。假如以前西门庆和潘金莲偷情还需要遮掩,被发现后,他们反而有恃无恐了,正大光明地幽会了。走投无路的武大与金莲谈判,他现在什么也不顾了,只想继续活着。他提出,只有金莲能给他看病,他就不对武松说。这真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他的话在金莲听来,就是威胁。为了清除最后的阻碍,潘金莲决定毒杀他。可悲的是,即使杀人,人也要假惺惺地用谎言做遮掩,“那妇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来。武大哎了一声,说道:‘大嫂,吃下这药去,肚里倒疼起来。苦呀,苦呀!倒当不得了。’这妇人便去脚后扯过两床被来,没头没脸只顾盖。武大叫道:‘我也气闷!’那妇人道:‘太医吩咐,教我与你发些汗,便好的快’”[1]42。为了获取幸福,清除一切障碍,人的生命根本不值一提,他们的死亡丝毫不能触动人心,这是一个麻木冷漠的社会。只要活着,就要不断放纵,这就是人的宿命,“到六月初二日,西门庆一顶大轿,四对红纱灯笼,他小叔杨宗保头上扎着髻儿,穿着青纱衣,撒骑在马上,送他嫂子成亲”[1]56。
情爱之所以荒诞,还因为它始终与物质利益纠缠不清。爱情本是两个人的事情,一旦掺入第三者,就会引起无限的纠葛和冲突。这只是因为人性自私,容不得别人染指自己的东西。爱情本是精神的交流,一旦掺入物质,就必然走向死亡。西门庆和潘金莲之间根本没有疼惜和怜悯,只有变相地利用和虐待。男女之情爱在《金瓶梅》中,最主要表现就是私通。男女个个是奸夫淫妇。男人无耻野蛮、朝三暮四,女人水性杨花、丑陋闷骚。他们相互之间私通,完全不顾及内心的真实感受。“事实上,凡是把婚姻中把爱情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的人,在感情问题上往往比较敏感,既容易相互挑剔,也容易动情别恋。”[2]潘金莲自私淫荡、阴狠毒辣、刻薄势利,她在内心还是渴望与心爱的男生厮守一生的,如果单纯为了满足性欲,她完全可以直接去做风月女子。而西门庆始终不甘心呵护一个女人,他要占有更多女性的身体。正是看破了男女的淫荡本质,才使西门庆极得女人的欢心。相濡以沫往往不敌狐媚之术。男人想得到最好的,而女人想要“一切”。作为个人,潘金莲是值得同情的。母亲卖了她,张大户奸污了她,武松羞辱了她,这个社会一直不把她当作人看待,她又怎么能平和地面对人生。潘金莲也应受到谴责,因为她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她不能因为自己受了委屈,就欺负比她更弱的弱者;她不能为了和西门庆长相厮守,就毒杀“丈夫”;她不能因为嫉妒,就用阴毒的方法害死李瓶儿和她儿子。性爱本没有过错,但为着性爱谋财害命就不应该了;偷情也可原谅,但如果为偷情而不择手段,那就应该受到谴责。《金瓶梅》没有一丝暖人的情感,只有冷漠和敌视。因为情爱欲望,潘金莲或直接或间接先后害死了4个男人:先是张大户不顾身体、年龄,强行和潘金莲交合,致使百病缠身,不久病死;为了和西门庆偷情,直接毒死武大;为了满足爱欲,让重病中的西门庆吃春药,导致脱阳,射血而死;最后又与女婿陈经济私通,致使陈经济被赶走,乞讨街头。
情爱之所以荒诞,还因为它始终是一种矛盾的存在。《金瓶梅》的笔法嘈杂,其性爱描写时而热闹无比,时而阴森无比,在热闹中透着死亡气息。这同样是男人对待性爱的矛盾心理。一切海誓山盟,都是谎言。一切你侬我侬,都是占有。爱情给了我们幻想,可我们走进爱情,才发现梦碎了。原来,未来并不像我们规划得那么好,我们究竟还是无法忍受幻想破灭的过程。嫉妒是人类的普遍心理。情爱就是一场意淫,人们就是喜欢把情爱和生活绞在一起,结果导致了异化。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牢固地潜藏在每个人的心理深处。女性之间的明争暗斗在性爱中表现得最突出。个人欲望极强的潘金莲在嫉妒的驱使下,到处煽风点火,由最初的谩骂升级为血腥谋杀。潘金莲先是借机吓死了官哥儿,又辱骂死了李瓶儿,从而获得了更多的性权利和家庭话语权。可见,男女之情爱是世间最自私的情感,绝不容许第三者加入。嫉妒让人变得阴暗,让人心理扭曲,甚至丧失基本的人性。一次次被卖,潘金莲只是想卖个好价钱。女人把嫁人当作一生最大的赌注,可潘金莲一次次都赌输了。她只是想要奢靡的生活,被人宠爱,可是好男人太少,有钱有权的男人也太少。情爱始终体现着宰制权力关系。他们的性爱游戏就是角色扮演。爱情是刚开始,但愿永不结束;是已出发,归宿尚待寻求。他们只是裸命的存在,一切尊严、荣誉都一文不值。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成不了你的梦。自己风流快活就行,而别人稍有出轨,就暴跳如雷。男女无论在生活中,还是性爱中,都处于极端的敌对状态。为了实现偷情的目的,丈夫就成了阻碍,潘金莲必须清除武大。所以,武大之死,她满是高兴,“怎肯带孝”[1]47!旧人已去,潘金莲日夜盼望早日过门,“这婆娘过来和西门庆说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不到后来网巾圈儿打靠后’”[1]42。潘金莲简直急不可耐,西门庆几日不来,她就烦躁不安,“因见西门庆两日不来,就骂:‘负心的贼,如何撇闪了奴,又往那家另续上心甜的了?把奴冷丢,不来揪采’”[1]47。潘金莲为了肉欲,简直来之不拒。《金瓶梅》的情爱呈现买卖化,男女集体淫乱,让整个社会成为荒诞的存在。因此,《金瓶梅》的道德形态,直指情爱的荒诞本质,要求个人少私寡欲,节制内心冲动。
二、《金瓶梅》伦理形态:恪守群体纲常
《金瓶梅》的伦理形态通过倡导恪守群体纲常展现出来,它批判了世人动物般的生活。群体的失德状态首先表现在人人都利益熏心。社会环境是人人都钻营世故、追名逐利。西门庆作为一个势利小市民,根本不懂爱情。两性之间,女性作为弱者,本能地追求宠爱。男性面向事业,而女性面向家庭。繁衍后代的重任让女性更加重视现实利益。因为孩子的抚育是需要物质基础的,而不是靠理想就能实现的。梦想当然能够指引人类向前,但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满足不了,何谈理想?尤其是古代妇女不事劳动,整天闲在家里,过无聊的日子,怎么能不空虚寂寞,怎么能不思念情爱。在那个时代,潘金莲的爱情根本不可能实现。潘金莲作为欲望放纵的极端典型,呈现了人被欲望控制的悲惨景象。可悲的是,没有这种欲望,人类就不能繁衍。“妇人的一切是个迷,同时妇人的一切只有一个答语:这答语便是生育。”[3]女性更受生殖意志的支配,所以女性性意识一旦爆发,对性爱的追求要比男性急切和久远。男性感恩的不是迎合他的性爱,而是母性的温柔,所以当温柔的李瓶儿死去后,西门庆仍念念不忘她的母性。
群体的失德状态还表现在人人都将道德变成获利的工具。《金瓶梅》呈现了传统伦理道德在新兴资本主义萌芽下的颓败趋势。不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而是人性能够比以前获得更透明的呈现。现实的残酷都是人积极营造的。无处可逃,只能一路走下去,直至死亡。不是潘金莲无耻,而是整个社会淫荡。世人的丑陋表演不仅无耻,而且可笑。他们自始至终都用一种冷漠而又不屑一顾的表情面对一切。他们对生命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嗤之以鼻。生活没有明天,看不到希望,证明自己的唯一方式,就是一种很惨烈的运动——情爱。为了金钱利益,每个人都恬不知耻。他们都努力希望成为弱肉强食社会中的强者,他们审时度势,适应能力强,绝不牺牲自己的利益以挑战不可战胜的规则,而是聪明地利用规则,增强自己。整个社会妓院化,每个人都利欲熏心,凭什么要求一个弱女子守节?何况,如果不淫荡,就不能生存。女人在选择丈夫时,总希望对方是个白马王子,可世界上,哪有什么王子?何况女人自身又不是白雪公主。于是,她们挑三拣四。等不及了,终于嫁了,又把愿望寄托在子女身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与其说是欲望使潘金莲走上了绝路,还不如说是吃人的道德使她只能走那条路。她只是不想坐以待毙,是严苛的道德,使人变得虚伪。严苛的道德对偷情的不宽容,使人人都想偷窥他人的阴私,竭力想抓住他人的把柄,用道德的利器害人。如果社会能对偷情持宽容态度,潘金莲也就不用百般遮掩,甚至不惜杀人灭口。社会越低端,道德越严酷;道德越严苛,人心越冷酷。世人都是值得宽恕的。他们只是为了生存,而生存游戏就是弱肉强食。在死亡威胁渐渐降临,而生之希望又未完全破灭之时,杀己比杀人更需要勇气。真的很难去相信一个人。人心防备重重,利益重重纠葛。潘金莲为了得到家庭话语权,处处挑拔离间,“性极多疑,专一听篱察壁”[1]80。与西门庆前几个妻妾不同,潘金莲既没有给西门庆带来丰厚的嫁妆,也没有给西门庆带来广博的人脉关系,她只有赤膊上阵,凭借自己的肉体争取权利和利益。她疯狂地和西门庆纵欲,并不完全是为了满足欲望,而是想为西门庆生下男孩,以提高自己的地位。《金瓶梅》首先讲述的是金钱,性爱只不过是获取利益的手段。人与人处于敌对冷漠的状态,一切关心和同情,只不过是实现自己利益的手段。
群体的失德状态还表现在人人都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情爱看似为了满足本能欲望,实则始终有利益驱动。“人需要现实的约束,如果没有约束,就沦为放纵;可如果一味顺从现实的暴虐,就失去生活的价值。”[4]潘金莲和青楼的妓女没有根本的区别,他们都试图用自己的青春貌美换取更好的物质财富。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武大,其他几个男人都是罪有应得。所以,潘金莲真正对不起的男人只有武大。而对不起潘金莲的人却很多,先是她的母亲,生下她,却因为忍不住寂寞,改嫁他人,并把女儿卖给王招宣;王招宣死后,又被卖给张大户;张大户奸污了她,后来又把她送给武大。潘金莲始终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她本是天真无邪的孩童,只是被社会环境熏染得心思阴毒。“他父亲死了,做娘的度日不过,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闲常又教他读书写字。”[1]7《金瓶梅》中的女性不是觉醒,而是为了生存而扭曲了人格。她们非但没有获得解放,而是在男权社会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资源就那么多,而人的欲壑难填。因此,人与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反目成仇、原形毕露和自相残杀处处映照在现实中。潘金莲是典型地为了自己不顾他人的人。与其说她冷血,不如说她更早的明白了这个社会的残忍。当相师断言她将克夫时,她竟从容地说,早就克过了。在她心中,根本没有贞节观念。因此,张大户死后,她跟着武大;毒杀武大后,她又从容地跟着西门庆。《金瓶梅》展示的欲望世界只是男人眼中的世界,是男人的执迷和梦想。人成为商品,也以商品买卖的视域看待他人。其实,市场经济原则要比农业经济原则强很多,起码在商人西门庆眼中,已经不太关注贞节,已经抛弃陈腐的伦理纲常。对商人西门庆来说,需要的不是复归伦理纲常,而是健全符合商品经济的道德。经济水平低,再多的道德约束只是对人性的压制。嫁给西门庆后,潘金莲仍然觉得压抑,于是与琴童私通,“单表金莲归到房中,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时如半夏。知道西门庆不来家,把两个丫头打发睡了,推往花园中游玩,将琴童叫进房与他酒吃”[1]91。他们的情爱就不断地在虐与被虐的转换中进行。在残酷的人情世态下,西门庆的一切财富都是自己辛辛苦苦打拼来的,他少不得在社会上打点。而在家中,他企图利用性虐待控制妻妾。当西门庆发现潘金莲又偷情后,简直要发疯了,他把琴童打得鲜血淋淋,“当下把琴童绷子绷着,打了三十大棍,打得皮开肉绽,鲜血顺腿淋漓”[1]92。可当潘金莲梨花带雨、撒娇哀求后,他的怒气立马全消,并立即和潘金莲交合在一起。
群体的失德状态还表现在人人都失去羞耻之心。世人很少不贪财好色的,西门庆一生穷尽心力都在追求金钱和女人。而要获取财色,就要用奸骗的手段。他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霸占别人的妻子。人与人之间没有真正的关切和同情,只有利用和排斥。看似脉脉含情,实则明争暗斗;貌似关心他人,实则相互算计;嘴上仁义道德,实则内心阴暗卑鄙。风光时,人群簇拥;一旦倒台,便作鸟兽散。西门庆一死,便遭到了众叛亲离的结果。先前的好朋友应伯爵、谢希大、韩道国等人不但翻脸无情,而且直接拆西门庆的台。接着便是妻妾的背叛,李娇儿改嫁新贵,潘金莲与女婿偷环,孙雪娥与情人私奔,孟玉楼又喜欢上了李衙内。男女孤独地行走世上,相遇了,正如干柴遇烈火,不肉体碰撞,还能干什么?可他们总把自己当天使,可正是他们的贪心和无知,才使人类被赶出了伊甸园。可没有欲望,人类又怎么繁衍?女人们忙着结婚,忙着找个男人做依靠。“大部分女人今日仍然是已婚的、结过婚的、准备结婚或者因为没有结婚而苦恼。”[5]人情冷漠、世态炎凉,生存是一场不停淘汰的游戏。人性的卑鄙与丑陋之所以能潜藏起来,是因为还没有找到滋润它的土壤。所有的人都是为了生存而已。所谓的信任、善良、正义、美好,只是一击即破的幻象罢了。西门庆生前的满满自信是建立在丰裕的金钱财富之上的,“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1]521。而要吸引女性,也必须靠金钱权利,西门庆就曾经夸口,“实不瞒你说,这五件事我都有。第一件,我的貌虽比不得潘安,也充得过;第二件,我小时在三街两巷游串,也曾养得好大龟;第三,我家里也有几贯钱财,虽不及邓通,也颇得过日子;第四,我最忍耐;他便打我四百顿,休想我回他一拳;第五,我最有闲工夫,不然如何来得恁勤”[1]23。但再多的财富也换不来健康,在放纵了几年后,西门庆就气断身亡。在本该欢乐的过年时节,西门庆的生命惨淡收场。
三、《金瓶梅》的“伦理—道德”形态:建构趋向真善美的道德规范
《金瓶梅》的“伦理—道德”形态就是建构趋向真善美的道德规范。建构合理的道德规范,首先要发现人性和社会的病变之处。兰陵笑笑生从来就不是个冷酷的“刽子手”,他更像一个高明的医生,他要发现人性的病变之处,然后穷追猛断,“直捣黄龙”。他手持利刃,为我们解开了人性的一些难题和迷惑之处。他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怀着好奇心,于细微处发现现实的荒谬之处,然后畅快淋漓地解剖一番。《金瓶梅》的“伦理—道德”形态体现的是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反思和超越,其深刻性与局限性是并存的。它以佛家因果的应然追求消解了生命的本然存在,其对人类生存的展望必然是悲观和绝望的。一夫多妻制度不合爱情的本意。因此,潘金莲和其他妻妾爆发了尖锐的矛盾斗争。为了独占西门庆,她用尽心机。她明知纵欲会让西门庆虚脱,但他仍不放过西门庆,并拼命吸取着摩擦的快感。因为西门庆不是她一个人的,她甚至盼着西门庆死,以间接打击和她争宠的女人。因此,男女之情爱,不是相互吸引,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爱情也不是生活的希望,而是人生的泥潭。现实中从来就没有纯粹的爱情。潘金莲带着对男人的仇恨,潜意识里想用性杀死西门庆,她的目的实现了,长期的纵欲引发了西门庆身体机能的退化,“那管中之精猛然一股冒将出来,犹水银之淀筒中相似,忙用口接咽不及,只顾流将出来”[1]818。男性对情爱既怀着无比艳羡的心情,又怀着无比恐惧的心理,这让男性既痛苦不堪,又欲罢不能。西门庆自知命不久矣,虽然内心恐惧,但仍不信任他人,“西门庆自觉身体沉重,要便发昏过去,眼前看见花子虚、武大在他跟前站立,问他讨债,又不肯告人说,只教人厮守着他”[1]825。长期的纵欲,让西门庆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但临近死亡,他仍心存侥幸,“只望一两日好些出来,谁知过了一夜,到次日,内边虚阳肿胀,不便处发出红瘰来,连肾囊都肿得明滴溜如茄子大”[1]821。看尽世态炎凉的西门庆,自然料到了妻妾在他死后定然另攀高枝,所以他苦苦哀求她们,“拉着潘金莲,心中舍他不的,满眼落泪,说道:‘我的冤家,我死后,你姐妹们好好守着我的灵,休要失散了’”[1]826。
实现真善美的伦理追求,要参透万物本空的实相。《金瓶梅》写尽人性之丑态,旨在打破世人对贪嗔痴的执迷不悟,参透万物本空的实相,点燃内心的纯洁与悲悯。人生痛苦,幸福虚幻。人生是条不归路,走上它就意味着孤独。世人一直孤独,原本没有价值的东西,却让人们无限付出。为了功名,宁让青春荒芜;为了权势,宁让良心放逐。最美的星星,其生命往往很短暂,达到辉煌的顶点即走向灭亡。宗教对人性的改善并没有多大作用,它只能安抚人恐惧的内心。“真正的自由不是连续不断地进行征服活动,而恰恰是在明确地认识和满足了存在的时候制止这种征服活动。”[6]西门庆的性欲望膨胀,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几乎一天也离不开女人。既是西门庆也需要长期依赖春药,才能满足女性,暴露了男人的普遍无能。男女天然的生理结构,让男人处于主导地位,却处于弱势。过度的放纵,就会快速地走向死亡。爱情只是人走向死亡旅程的回光返照。“寂寞使他们恋爱,而恋爱使他们更加寂寞。寂寞是每个人的宿命。这也可以看出,爱情或许只是冲动与偏执的结合体。”[7]人类就在集体的谎言中繁衍下去。性爱对于人真是两难的问题,性爱的低级丑陋让人难于启齿,于是只能造出性爱能带来欢愉的谎言自欺欺人。男女之情爱还表现在女性妓女化和男性的同性爱。“当每个参与者得到别人给予的价值,同时也给予他人以价值时,就存在着爱的这种相互关系。”[8]男女之情爱,始终体现着经济利益,穿插着金钱关系。这只是因为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太低,人们的一切言行,都是为了求得生存。而女性的经济地位尤其低下,她们必须凭借性爱换取物质利益。只要活着,就不能摆脱物质利益的纠缠,因此,西门庆临死前仍惦记着家产如何分配,“又分付:‘我死后,段子铺里五万银子本钱,有你乔亲家爹那边,多少本利都找与他。教傅伙计把贷卖一宗交一宗,休要开了’”[1]826。因为财色嫁给西门庆的女人,也必定因为西门庆之死选择更好的依靠。因此,西门庆刚死,她的女人们纷纷改换门庭。道德伦理是情爱的反常呈现。道德伦理终究无法压制人的本能欲望,宗教终究无法拯救世人的沉沦。谈道德,表征了人的内心恐惧和虚伪。人类要获得救赎,必须依靠他者的力量,而这个他者,至今还没有出现。“自从类人猿能够直立行走并显露了性器官时,性欲就变成恒常而不仅仅是周期性的冲动。”[9]
要实现真善美的道德理想,就要提高个人素质。西门庆死后,潘金莲继续从容地与陈经济私通,“原来潘金莲那边三间楼上,中间供养佛像,两边稍间堆放生药香料。两个自此以后,情沾肺腑,意密如漆,无日不相会做一处”[1]78。人生没有意义,但只要活着,就要有寄托。在一个失去神明的所在,众人在欲望的泥潭中沉沦。潘金莲总要生存,而作为一个女子,她只能依靠男人,于是西门庆死后,她只能依赖别的男人,凭借自己尚存的姿色换取生存所需的物质利益,“潘金莲在房中,听见打了陈敬济,赶离出门去了,越发忧上加忧,闷上添闷”[1]780。与女婿偷情的潘金莲,最终被发现而被赶出家门,沦为被卖的角色。在下层民众“易子而食”的现实下,西门庆的放纵真不算罪过。执迷不悟的潘金莲,既甘心被有权有钱的男人利用,也甘心被情欲所利用,于是当武松哄骗要娶她时,她高兴的不能自抑,“他若不嫁人便罢,若是嫁人,如是迎儿大了,娶得嫂子家去”[1]888。正处于困境的潘金莲,看到一丝希望,怎能不不紧紧地抓住,她兴冲冲地跟武松回家,结果却丢了性命。她以为天下的男子都是被性欲控制的,她过高估计了自己对男人的影响力。倒是吃斋念佛的月娘对武松的为人看得透彻,“月娘听了,暗中跌脚,常言‘仇人见仇人,分外眼睛明’,与孟玉楼说:‘往后死在他小叔子手里罢了。那汉子杀人不斩眼,岂肯干休’”[1]889!潘金莲之死让人们感到的不是快意,而是悲悯。如此娇弱的女性却被残忍的武松开膛破肚。潘金莲毒杀武大时,好歹还是又哄又骗又胆怯,而武松杀潘金莲却一点也不掩饰,一点也不胆怯。这失去了基本的人性。如果连胆怯也没有,那还是人吗?我们看到的只是武松的仇恨和愤怒,而不是正义和良善。与一般男性不同的是,西门庆不追求白嫩的小女孩,而是专门挑选性经验丰富的妇人,这显然有悖男性常态。“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10]《金瓶梅》通篇描绘性爱带给男女的快感,似乎忽视了性爱给人带来的虚无和空洞。这也背离了性爱的实质。因为性爱除了给人快感和欢愉之外,更多的是空虚。这份空虚是人人都能感到的。但由于生殖需要,整个社会都竭力否定性爱带来的痛苦。由此,整个社会在性爱问题上形成了集体无意识,集体说谎。这才是最可怕的。情爱以欲代情,不仅混乱了伦理道德,而且成了敛财的工具。兰陵笑笑生对于人的生存方式的病症所开出的药方以自我修养为基础。“个人的道德修养从来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要,我们能心存感恩,少一丝功利,就能逐步做到无愧于心。”[11]由此,人们应当追寻善良的足迹,因为善良可以化云成雨,洗涤人的灵魂。“学术研究要有计划,这要比散兵游勇更具有学术影响力。”[12]研究《金瓶梅》,不仅是为了正视那个浮华的世界,更是为了从中获取伦理道德意蕴,以指导现实。
概而言之,《金瓶梅》彰显了对理想“伦理—道德”形态的追求。它既是鲜活的鬼蜮世界,又是练达的世情批判史诗;既是伦理之种的播散,又是善良之芽的培育。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不是空洞的道德宣讲,而是饱含真情的谆谆劝告。兰陵笑笑生凭借批判人性的阴暗与社会的冷漠无情,证实“伦理-道德”应当内化为人的自觉律令。因此,我们只要在“伦理-道德”规范的约束下,识破“酒色财气”的虚无本质,让善良常驻灵魂,就能在浮华的世界上依道而行。
[1]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 周国平.爱情的容量[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191.
[3] [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巫静,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90.
[4] 孙全胜.现实断裂处的爱情呈现——论《伤逝》的伦理形态[J].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51-55.
[5]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99.
[6]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82.
[7] 荀泉.绝望中的希望之“虹”——论《伤逝》悲剧意识的“三位一体”[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61-64.
[8] [美]欧文·辛格.爱的本性——从柏拉图到路德:第1卷[M].高光杰,杨久清,王义奎,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4.
[9] [美]艾布拉姆森.弗洛伊德的爱欲论——自由及其限度[M].陆杰荣,顾春明,都本伟,等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110.
[10]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57.
[11] 萧荪.忠恕之道,推己及人——浅谈儒家“君子”人格的三维目标及其二重意蕴[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70-273.
[12] 高淮生.考辨张竹坡家世生平撰述《金瓶梅》研究长编——吴敢金学研究综论[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329-340.
[责任编辑 杨玉东]
On the Ethical and Moral Form of The Golden Lotus
SUN Quan-sh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Jiangsu, China)
The moral form and ethical form are isomers in the novelTheGoldenLotus.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subjective world of individuals, while the latter refers to the external objective world, but both fits into the realization of a moral life.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and moral form inTheGoldenLotusis not only oriented to shaping an individual’s virtue, and perfecting ethic codes of the society as well, which incorporates subject and object and comes close to the sublime ethics.
TheGoldenLotus; ethical form; moral form
2014-01-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ZX07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JA720004)
孙全胜(1985—),男,山东临沂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伦理学等研究。
E-mail:sunquansheng1116@126.com
I207.4
:A
:1673-9779(2014)01-008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