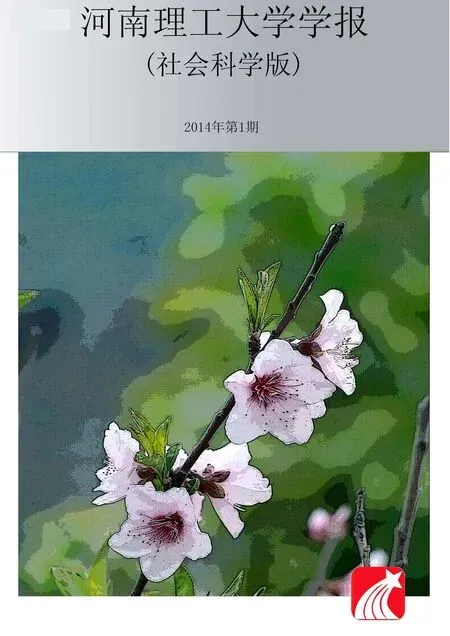“影响的焦虑”和 “创造性误读”
——简析哈罗德·布鲁姆的诗歌理论
张宏涛
(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南焦作454000)
哈罗德·布鲁姆于1930年出生于纽约的一个犹太家庭,在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并在该校任教,其文学批评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60年代美国大学校园里学生们反传统文化运动促使布鲁姆重新评价文学传统特别是对于浪漫主义进行重新认识。布鲁姆在这期间的主要著作有:《雪莱的神话创造》(Shelley’s Mythmaking,1959),《幻想的伴侣: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导读》(The Visionary Company:A Reading of English Romantic Poetry,1961)和 《布莱克的启示:诗歌讨论研究》(Blake’s Apocalypse:A Study in Poetic Argument,1963)。他早期的著作主要是通过细读一些诗人的作品来阐释他们的思想,同时把浪漫主义思想置于后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的中心位置。当布鲁姆的具有革命性的浪漫思想于70年代逐渐成为学界正统时,他也步入自己的理论发展的最重要阶段,这个阶段是以其影响深远的四部曲为中心展开的: 《影响的焦虑》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1973),《误读图示》(A Map of Misreading,1975), 《卡巴拉和批评》 (Kabbalah and Criticism,1975;又译作《希伯来神秘教义和批评》),《诗歌和压抑》(Poetry and Repression,1976)。这些著作将那个时期的浪漫主义想象的全景集中外化总结为一种概括的诗歌理论和批评理论。从对修辞和精神分析入手,布鲁姆提出后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创作是一种新诗人奋力去克服前辈诗人影响的过程,是一种获得性的焦虑表现。批评家的任务即去发现这种压抑机制如何通过不同的“误读”策略表现出来。在其文学批评的第三个阶段布鲁姆把自己的宗教体验引入自己的思想体系,表现出对于人精神方面的强调和重视,代表作有:《对抗:走向一种修正理论》 (Agon:Towards a Theory of Revisionism,1982)。
一、哈罗德·布鲁姆的诗歌理论
布鲁姆的诗歌理论所具有的浪漫个人英雄主义与他所处的怀疑主义、反人本主义的解构时代格格不入。有学者将布鲁姆归入心理分析学派,也有人因为他是耶鲁“解构四人帮”而把他划入解构阵营,还有人因为他的“误读”理论而认为他赞成“读者反映论”。而他自己却说:“我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我属于我自己。你应该知道我和保罗·德·曼之间的分歧,他和其他解构主义者强调语言意义的不稳定性,而我认为作家的想象力应该独立于语言之外……我的‘误读论’并非指读者和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价值,而是一种更为对抗性的批评,一种诗人与诗人之间相互对抗的批评。我的理论受到尼采和弗洛伊德的影响,我吸收尼采的对抗论和弗洛伊德的防御论,但不能说是心理分析批评。”[1]他的理论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他反对解构批评所崇拜的语言虚无主义,即对于确定意义进行无求无尽的拆解;他极力恢复浪漫主义的诗人、意图以及想象的力量,把诗歌历史解读为强力诗人之间的某种英雄主义心理戏剧,依靠自我独创而进行斗争的强力诗人们的“表达意志”。
在他的文章《破除形式》 (The Breaking of Form)中,他把他的诗歌理论区别于诗学。 “By‘theory of poetry’I mean the concept of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poet and of poetry,in distinction from poetics,which has to do with the technique of poetical composition.”[2]2(说到 “诗歌理论”,我指的是诗人和诗歌的性质和功用,和强调诗歌创作技巧的诗学截然不同。——作者译)他所强调的是诗人、诗歌的性质和功能而不是诗歌创作的技巧。作为文学评判家,布鲁姆因为“影响的焦虑”和“创造性误读”理论而广泛为人所知,他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揭示了浪漫主义诗歌历史变化的内在机制和规律。
他的著作《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The Anxiety of Influence:A Theory of Poetry)开启了他的理论探索。结合弗洛伊德的“家庭罗曼史”,尼采的“强力意志”和德·曼的“误读”,布鲁姆指出所有晚辈“强力诗人”,为了建立自己诗人地位,在面对前辈诗人时必须有意或无意地采取一种“误读”的策略或方式。
在这本书的开始部分,布鲁姆说到, “Poetic influence,or as I shall more frequently term it,poetic misprision,is necessarily the study of the life-cycle of the poet-as-poet.”[3]7(诗学影响,或者我应更频繁地去界定的概念:诗学误读,必须是对于诗人作为诗人之生命轮回的研究考察。——作者译)他认为所谓的影响就是“误读”,就是“the poet in a poet.”[3]11(诗人心中的诗人。——作者译)一般来说,后辈诗人很难抗拒前辈诗人的影响,只有那些“强力诗人”可以做到。
布鲁姆认为新的文学经典出现的前提是必须要有一个对应的文学前辈的影响,这种影响其实是包含一个让人费劲心思学习传统的过程。这样后辈诗人在创作上由于这种影响而被限制,内心就会充满焦虑。这里经典和传统就意味着“影响的焦虑”的存在。“The young citizen of poetry,or ephebe as Athens would have called him,is already the anti-natural or antithetical man,and from his start as a poet he quests for an impossible object,as his precursor quested before him.”[3]10(诗歌世界里年青的公民,雅典人称他为ephebe,作为反自然和传统的人,从一开始作为诗人,就像他的前辈一样,在追求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作者译)这种后辈诗人的焦虑可以和弗洛伊德的家庭罗曼史做比较。后辈诗人面对着由前辈诗人、经典作品和文学传统所表征着的“父亲”,一个给他营养和保护的同时又威胁、压制他内心反抗欲望的“父亲”,表现出一种爱恨交加的情感。无疑这个“父亲”所代表的传统东西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会无形中压制后辈诗人的创新。但是压制可能会造成反抗,焦虑可能会带来创造热情。后辈诗人中之强力者可能会由于这种“影响的焦虑”而变得更加有创造力。
“影响的焦虑”实际上是一种互文活动:“强力诗人”生存于前辈诗人的阴影下,他们必须战胜这种阴影从而超越前辈。在面对焦虑时,后辈诗人可能只是把自己遗失在前辈作品的文本中,而忽略思考作品的美学特征和原创性。在诗歌创作上,平凡的诗人和有创造力的诗人的根本区别在于谁能够克服前辈诗人所留下的条条框框的影响,建立自己的风格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新的经典。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少数“强力诗人”能够敢于否定并且克服“影响的焦虑”,通过创造力和美学概念创新解放他们自己。这些“强力诗人”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去挑战经典和传统并不断地修改,否定自己以前的作品。他们总是处于一种生成个性化的过程之中,所以布鲁姆声称这些“强力诗人”最终的对手是“时间”,而且是他们有权利去宣称“过去”的“过去性”。
“影响的焦虑”所带来的问题是传统与创造性的关系问题,即传统的传承与艺术创造力之间的矛盾:“强力诗人”依靠什么对抗传统?和T·S·艾略特不同,布鲁姆强调的是“强力诗人”的个人才能。对于“强力诗人”来说,为了对抗诗歌传统的压制,他们的武器就是他们自由独立的观点和态度,他们的个人化的意志。“强力诗人”的确可以从过去的文本中去发现些许灵感,但更多的是他们以陌生化的再现或呈现方式去发现新的题材。
“Influence,in the deep sense,is a never ending process.”[4]145(影响,就其深层意义,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过程。——作者译)这种没有尽头的焦虑所带来的“强力诗人”的创造性给诗歌历史以持续的活力。就此,布鲁姆给出了他的两个结论:第一个就是他关于现代诗歌历史的性质揭示。“Poetic influence-when it involves two strong,authentic poetsalways proceeds by a misreading of the prior poet,an act of creative correction that is actually and necessarily a misinterpretation.The history of fruitful poetic influence,which is to say the main tradition of Western poetry since the Renaissance,is a history of anxiety and self-saving caricature,of distortion,of perverse,willful revisionism without which modern poetry as such could not exist.”[3]30(诗学影响——当两个真正的强力诗人卷入其中时,总是伴随着一个诗人对前辈诗人的误读。误读这种创造性的纠错行为实际上必须表现为误解。这个成果丰硕的诗学影响的历史,也就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这种诗学影响的历史充斥着焦虑、自我救赎、歪曲以及任性、主观的修正,而所有这些却是现代诗歌之所以成为其自身的原因。——作者译)他认为诗歌的影响总是表现为伴随着一个后辈诗人对前辈诗人的“误读”,这种“误读”必然是一种创造性地纠偏,一种事实上的同时也是必要的“误解”,而自文艺复兴以来主要的西方诗歌传统都饱含着焦虑、自我拯救、意义的歪曲、非理性以及强烈的修正主义。要成为“强力诗人”,后辈诗人必须具有对抗前辈诗人或传统的不可征服的意志,布鲁姆的观点是前辈诗人或传统是由文字表面意思的胜利所代表,而后辈诗人所要做的是必须借助于意象、修辞等途径来反抗文字表面意义,来表现其意志。“The center of my theory is that there are crucial patterns of interplay between literal and figurative meanings,these patterns are quite definite and even overdetermined.What determines them is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because it is the war against belatedness that results in certain patterns of analogous images,tropes,psychic defenses,and revisionary ratios.I do not say that these patterns produce meaning,because I do not believe that meaning is produced in and by poems,but only between poems.”[5]88(我的理论的中心即存在于字面意义和修辞意义之间的十分关键的互动类型,这些类型是十分确定甚至是过分确定的。而决定这些类型的就是影响的焦虑,正是由于对抗迟到的战争才导致了某些确定类型的类比形象、比喻、心理防御和修正比。我不能讲这些类型能够产生意义,是因为我不相信意义是在诗里或是由诗所产生的。意义仅在诗与诗之间产生。——作者译)布鲁姆诗歌理论的中心要点就是文本的表面意义与修辞意义之间存在不同类型的、关键性的相互作用,这些类型的相互作用是确定存在并且他们的生成是多因素决定的。“影响的焦虑”决定这些不同类型相互作用的产生,因为抗争“迟到”的战争导致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相似意象、修辞、心理防御以及“修正比”。布鲁姆没有说这些不同类型的相互作用会产生意义,因为他不相信意义会出现于诗歌本身,他认为意义只出现于不同的诗歌之间。这种诗歌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后辈诗人对于前辈诗人的具有对抗性质的“创造性误读”之上。为了解释这种“创造性误读”,布鲁姆特别给出6种“修正比”即6种对抗形式:“克里纳门” (clinamen),即转向或反语;“苔瑟拉” (tessera),即续完或提喻;“克诺西斯”(kenosis),即清除或转喻;“妖魔化”(daemonization),即移置或夸张; “阿斯克西斯”(askesis),即缩减或暗喻;“阿波弗瑞底斯”(apophrades),或死者的回归。“布鲁姆的六种修正比就是六种比喻,也就是六种阐释方式……让意思在比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清晰。”[6]
布鲁姆认为后辈诗人对于经典的阅读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后辈诗人把他们通过时空不断变换的美感体验以及他们的想象力转换成具有创造力的东西。这种创造的成果就是属于他自己的诗歌,一个借助于“误读”的“谎言”。“The poem is a lie about itself,but it only gets to itself,by lying against time,and its only way of lying against time is to lie about previous poems,and it can lie about them only by misreading them.”[5]112(诗就是一个关于自身的谎言,通过对抗时间的谎言而实现自身。这种对抗时间的谎言进行的唯一方式即是关于先前诗歌的谎言,是通过对前辈诗歌的误读实现的。——作者译)
前辈诗人的影响注定会表现在后辈诗人的身上,但另一方面这种诗歌的影响在渗透的过程中反向地也给人们带来对前辈诗人认识上的变化。按布鲁姆的解释,“创造性误读”也可以称作“对抗式批评”。通过“对抗式批评”,人们也认识到后辈诗人也会在其前辈诗人那里留下自己的痕迹。由于所有诗人的贡献,“一首宏大的诗”就此形成。
二、哈罗德·布鲁姆的诗歌理论中的关键概念
布鲁姆作品中的启示录语气以及大量充满神秘色彩的字眼,会时时令读者感到困惑,似乎其批评本身也是诉诸其个人的想象力。这让人们认为布鲁姆作为批评家,也像浪漫主义诗人一样,具有英雄主义的“权力意志”和“信仰意志”。对此,伊格尔顿曾给出评论:“批评本身对于布鲁姆来说其实只是某种形式的诗,就像诗乃是对于其它的诗的隐含的文学批评一样,于是一个批评阅读的成功与否到头来就不在于其真理价值,而在于批评家自己的修辞力量。”[7]185布鲁姆诗歌理论的独特性和他所运用的一些基本概念息息相关,这些概念很好地阐释了他对于诗歌创作和发展的理解。下面就其诗歌理论中出现的关键概念进行解释。
(一)传统
对传统的理解T·S·艾略特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传统代表着文化意识和文学经典,同时传统也是使一部作品流芳百世的根本。布鲁姆首先承认传统是充满力量并且给人施加影响的存在,它充满丰富意义,给人以有用教化,充当着无形的教育工具的角色。但针对诗歌,他重新定义了传统的性质和功能。“It is now valuable precisely because it partly blocks,because it stifles the weak,because it represses even the strong.”[4]29(它现在有价值,恰是由于它部分的阻碍,由于它压制弱者,甚至是由于它对于强者的抑制。——作者译)传统在这里不是后辈诗人获得力量的所在,而是一种起着负面作用的但同样是富有价值的存在。弗洛伊德对传统的解释是传统就是被压抑在个体意识当中的文化积淀。从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得到启示,布鲁姆认为在诗歌传统方面具有神秘的、不能被指涉的被妖魔化的特征,这和T·S·艾略特所认同的正统的传统概念不同。 “There is then something uncanny about tradition,and tradition,used by Eliot,say,as a hedge against the daemonic,is itself,however orthodox or societal,deeply contaminated by the daemonic.…Tradition is itself then without a referential aspect,like the Romantic Imagination or like God.Tradition is a daemonic term.”[5]98(传统本身是神秘的、难以解释的,艾略特正是把传统当做对抗神秘的手段,而传统本身不管多么正统或社会化,总是会受到神秘物的浸染。传统本身并不存在指涉物,就像浪漫主义或上帝,传统其实就是一个神秘的术语。——作者译)
(二)影响
布鲁姆从词源的角度对“影响”的解释是“影响”最初意味着“inflow”,即向某个方向的流动。对于诗歌方面的影响,他认为和原初意义有一定的区别。“by‘poetic influence’I do not mean the transmission of ideas and images from earlier to later poets.”[3]71(我认为 “诗学影响”不是把观点和形象从前辈诗人那里传到后辈诗人。——作者译)他把诗歌上的“影响”解释为一种以互文性表现出来的文本之间的关系,他对于“影响”这个概念的使用是为了达到一种修辞效果。“What I mean by‘influence’is the whole range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one poem and another,which means that my use of‘influence’is itself a highly conscious trope”.[4]70(我这里所说的“影响”即一首诗和其他诗之间各个层面的关系,这意味着我对“影响”这个词的使用本身即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比喻。——作者译)
(三)焦虑
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布鲁姆认为焦虑这种痛苦的情感体验就是一个心理战场,“强力诗人”就是要在这个战场取得胜利从而摆脱被遗忘的命运。在他对于诗歌的解释当中也给焦虑这个概念做了注解,一首诗不是对焦虑的克服而是焦虑本身。“Every poem is a misinterpretation of a parent poem.A poem is not an overcoming of anxiety,but is that anxiety.”[3]95(每首诗都是对某首前辈诗的误读,每首诗都不是对焦虑的克服,而是焦虑本身。——作者译)
(四)误读
通常情况下,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分为正读和误读,前者指对作者的创作动机、作品的意蕴以及作品的艺术价值的理解与作者的创作本意相符,反之称为误读。但保罗·德·曼认为由于文本的修辞性,阅读总是伴随着对文本意义的忽略、偏离或歪曲,这样阅读的历史也就是误读的历史。可能是受保罗·德·曼的影响,布鲁姆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文本并不是意义的容器,而是误读发生的场所。他承认对于诗歌的正确阅读是非常困难的,这种正确的阅读对于布鲁姆来说就是以修辞方式表现出来的“误读”。“I do not agree wholly with de Man that reading is impossible,but I acknowledge how very difficult it is to read a poem properly,which is what I meant by my much attacked critical trope of‘misreading’or‘misprision’.”[2]16(我不完全同意德.曼所说的“阅读是不可能的”,但我承认要正确地读一首诗有多困难。这就是因为有“误读”的存在。这里,“误读”作为一种关键的比喻,常使我受到别人的批评攻击。——作者译)他认为诗歌就是一种焦虑,一种误读,就是暗含意象和对抗的修辞,而阅读诗歌就是一个心理防御过程。“强力诗歌”会产生强烈的心理防御过程,这种“强力诗歌”产生的“误读”越是强烈,由此“误读”产生的其他“误读”越多,它就越是容易被人们接受为经典。“A strong poem,which alone can become canonical for more than a single generation,can be defined as a text that must engender strong misreadings,both as other poems and as literary criticism.When a strong misreading has demonstrated its fecundity by producing other strong misreadings across several generations,then we can and must accept its canonical status.”[8](一首强力诗歌成为经典,经历过一个时代,那它即可被定义为一个可以产生强烈误读的文本,不管这种误读的形式是其他的诗歌或是文学评论。当一种误读通过产生其它跨越几代的强力误读证明了它的深厚生命,那么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接受它的经典地位。——作者译)
三、结 语
布鲁姆的诗歌理论内容充满了“强力诗人”面对传统因素所带来的“影响的焦虑”时所表现出的不可征服的强力意志,这种意志使他们在“迟到”中通过“误读”创造经典。例如,他认为华兹华斯的《永生颂》是对弥尔顿《利希达斯》
的误读,雪莱的《西风颂》是对华兹华斯诗歌的误读,而济慈的《心灵颂》是对弥尔顿和华兹华斯诗歌的误读。“布鲁姆的文学理论代表着一种充满激情而且富于挑战精神的回归,即回归那个从斯宾塞和弥尔顿到布莱克、雪莱和叶芝的新教浪漫主义‘传统’,一个被艾略特、利维斯及其追随者们所勾勒出来的保守的英国国教派谱系 (邓恩、赫伯特、蒲伯、约翰逊、霍普金斯)排挤掉了的传统。”[7]184因此,他的理论被一些批评家认为是20世纪70年代最大胆、最有创见的文学理论。
[1] 张龙海.哈罗德·布鲁姆教授访谈录 [J].外国文学,2004(4):103-106.
[2] BLOOM,HAROLD,PAUL DE MAN,etl.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M].Great Britain:Routledge&Kegan Paul Ltd,1979.
[3] BLOOM,HAROLD.The Anxiety of Influence:A Theory of Poetr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1973.
[4] BLOOM,HAROLD.A Map of Misreading[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1975.
[5] BLOOM,HAROLD.Kabbalah and Criticism [M].New York:Seabury Press,1975.
[6] 张龙海.哈罗德·布鲁姆论“误读”[J].当代外国文学,2010(2):57-67.
[7] [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 BLOOM,HAROLD.Agon:Towards a Theory of Revisionism [M].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1982,P285.
[9] BLOOM,HAROLD.Poetry and Repression:Revisionism from Blake to Stevens[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