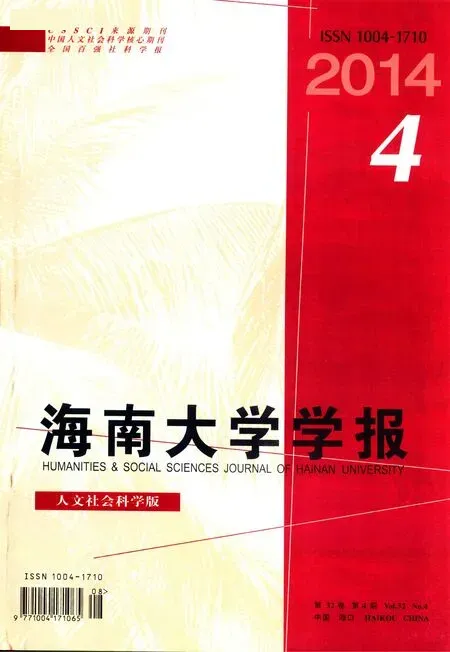《阿史那》:莎士比亚悲剧的互文性中国化书写
李伟民
(四川外国语大学莎士比亚研究所,重庆400031)
1947年,由李健吾根据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翻译、改编成民国时期的中国化莎剧《阿史那》,该剧剧本发表在《文学杂志》1947年第2卷第1至3期上。这是中国莎学史上值得注意的一次早期本土化的翻译、改编。据李健吾说,《阿史那》的“材料的库藏是唐书和新唐书。阿史那真有一位定襄县主下嫁阿史那……他觉得远非形骸上的接触所能比拟……东拼西凑出来的形骸,不会就止于形骸吗?莎士比亚会因他的冒昧在中国活过来吗?”[1]李健吾的《阿史那》为了获得历史感和语境的认同感,寻求的是,阿史那以中国历史上的真实人物[2]566为基础,故此该剧形成了以初唐历史、文化、现实、人物为背景,以《奥赛罗》的情节、主题为线索和主旨,具有互文性特色的中国化莎剧。为此,本文将从《阿史那》与《奥赛罗》两个文本之间的交融,以“翻译加改编”形成的互文性对话为理论平台,通过《阿史那》的互文性,关照这样一类莎剧在中国莎学史上的意义。
一、翻译改编中的互文性之彰显
诞生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化莎剧翻译、改编乃至演出,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采用中国戏曲改编莎剧的中国化改编、演出;民国时期的中国化莎剧改编多以中国历史为背景,以话剧的形式搬演莎剧。这一改编方式,到21世纪更以电影的方式在《夜宴》和《喜玛拉雅王子》中得到了延续。李健吾将莎剧翻译、改编为中国化的莎剧《阿史那》,既有很强烈的对现实政治、社会、人性的思考,又有对艺术、审美的追求,但由于改编得较为匆忙,而且以“翻译加改编”形式呈现,故此,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与中国莎剧改编史上并非是一部有影响力的莎剧,也正由于这个原因,多年来对《阿史那》的研究稀疏,造成在李健吾研究中忽略莎剧改编研究,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不但在李健吾研究中有重要意义,在中国莎学研究史、现代文学史和外国文学传播史研究上,更能达到补苴不详、深入探讨之目的。
当时的戏剧界已经意识到,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观众与外国戏剧之间存在着鸿沟,而李健吾把外国戏剧改头换面以中国剧情加以译著,是文学的、“爱美的”[3]48戏剧的一条出路。那么李健吾是如何落实自己的改编意图呢?即如何体现出《阿史那》的互文性呢?莎士比亚戏剧是文学的戏剧,作为文人的李健吾在“翻译加改编”中,当然会按照文学性的要求重造《奥赛罗》中的人物,但故事还是那个故事,情节还是那个情节,主题还是那个主题,只不过将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对英国社会的思考,移植到初唐,以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莎剧形成对邪恶人性的批判,来警示现代社会罢了。这种翻译加改编中形成的不可避免的互文性,也就自然构成了其莎剧改编的特色,即使是不成功的特色。
与话剧登上中国舞台的初衷相一致,政治宣传和对“社会问题”的探讨是改编者考虑的首选,面对民族危机,李健吾改编动机与当时中国的内忧外患关系密切,即“针对即将覆灭的‘大东亚共荣圈’和南京伪政府”[4]386,借莎氏酒杯浇中国的块垒,以文艺复兴指涉中国社会现实,创作出具有“准政治隐喻剧”特点的中国式莎剧。李健吾的《阿史那》与中国话剧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同步,原创剧本不够,求助于翻译改编也是为了“‘孤岛’、‘沦陷’时期“苦干剧团”将外国剧本改头换面,变成中国剧情上演[3]48-49的重要原因”。以李健吾、顾仲彝为代表移植经典莎剧的改编,成为抗战时期“孤岛”、“沦陷”地区戏剧家对侵略者及其附逆,隐晦而又有所指向的曲折反抗和批判,是对民族压迫、社会黑暗的强烈反应。对于此种翻译、改编的莎剧,在中国莎剧传播的早期,借鉴外来话剧莎剧形式,隐喻中国现实,对莎剧在中国的传播是一种贡献,正如李健吾自己在《以身作则·后记》中所坦承的:“我梦想去抓住属于中国的一切,完美无间地放进一个舶来的造型的形体”中去,在“中国的一切”中,政治的批判意识要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莎剧也就自然成为了其选择改编的剧目之一,是他借用外来形式的话剧阐释批判、暴露人性弱点的生动注脚[5]。李健吾翻译、改编《阿史那》就是利用莎剧这种外来形式,在获得艺术享受的同时,有意使观众通过对社会与邪恶人性的批判,从而与现实政治发生联系,使翻译、改编中的互文性更加彰显。
二、契合中的建构与置换中的解构
从艺术角度来看,《阿史那》的指涉在互文性中已经改变了原作,改编也不再仅仅是“元文本的译制”[6]54,更不能“将读者带回到书面现实中的元语言”[6]56中去。这就表明,《阿史那》这种“带回”(改编)已经在背景、人物、情节以及改编者所要影射的对象、表达的主题等方面发生了彻底改变,即除了部分重返《奥赛罗》的元语言与语境之外,其互文性已经使《阿史那》成为中国版的《奥赛罗》了,并得以呈现为一个翻译与改编相结合,改编与指涉呈现位移,具有社会与伦理道德批判,结合中国社会现实的《奥赛罗》。反映在两个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建构了“嫉妒—野心—阴谋”呈现出的心理发展曲线,人性的善良、丑恶,性格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渗透于其中的中西文化的交融。如果抛开李健吾的主观政治意图,以互文性在文本内的体现顺藤摸瓜,就会发现,在人物心理的表现上,阿史那在令狐建的挑唆、污蔑下,在是否要杀李燕真的激烈思想斗争中,以及什么时机杀害李燕真,有矛盾的思想斗争和心理发展过程,这一点可以说与原作《奥赛罗》如出一辙:
难道你以为我是那种无聊东西,一天到晚往醋缸里头泡……我女人出身高贵,天生貌美……她一定善守妇道,不辜负我一片净爱她的心情。我虽然自惭形秽,不过,县主那方面,我不觉得她有一点点厌弃我的意思。所以,令狐,光只怀疑没有用,我要亲眼看见……[7]
但是“闻三人成虎,十夫揉推,众口所移,无翼而飞”,致使阿史那的心理发生了急遽的变化:
就是全营的人马,伙夫马夫算在里面,尝过她的甜头儿,只要我不知道,我也快活,现在,永远完了!永别了,心平气和!永别了,知足常乐!永别了,冲锋陷阵,千军万马!永别了,血染征袍,功名万代!永别了,胡笳羌笛!永别了,战鼓,快马!全永别了,耀武,扬威,贺兰山,朔方大军!完了!我阿史那这一辈子算是完了![7]
再看《奥赛罗》:
你以为我会在嫉妒里消磨我的一生,随着每一次月亮的变化,发生一次新的猜疑吗?不,我有一天感到怀疑,就要它立刻解决……谁说我的妻子貌美多姿,爱好交际,口才敏慧,能歌善舞,弹得一手好琴……我也绝不因为我自己的缺点而担心她会背叛我……当我感到怀疑的时候,我就要把它证实;果然有了确实的证据,我就一了百了,让爱情和嫉妒同时毁灭。[8]337
要是全营的将士,从最低微的工兵起,都曾领略过她的肉体的美趣,只要我一无所知,我还是快乐的。啊!从今以后,永别了,宁静的心绪!永别了,平和的幸福!永别了,威武的大军、激发壮志的战争!啊,永别了!永别了长嘶的骏马、锐厉的号角、惊魂的鼙鼓、刺耳的横笛、庄严的大旗和一切战阵上的威仪!还有你,杀人的巨炮啊,你的残暴的喉管里模仿着天神乔武的怒吼,永别了!奥瑟罗的事业已经完了……[8]343
这里“嫉妒”变成了“醋缸”,“肉体”变成了“甜头”,“妇道”、“胡笳羌笛”、“贺兰山”等也成为中国事物的明显标志,尽管如此,仍然不难看清其中的翻译痕迹及其相似性。阿史那挚爱自己的妻子,令狐建却是危险的野心家和十足小人,当天真(甚至是头脑简单)[9]的君子与奸佞的小人相遇后,往往是小人得逞于一时。小人的一时胜利会使悲剧的凝重覆盖读者和观众的心灵,为阿史那由英雄演变为杀人犯和代表纯真、柔弱、美的李燕真的死而扼腕叹息。与奥赛罗一样,阿史那实在不忍美和爱在自己手中就此消失,可当他一旦陷入猜疑后,自卑感以及怕人格受到侮辱的心理就得到了空前的强化,他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了。阿史那所显示出的这些人性中的弱点,可以说是中西皆然,古今相通。在这里,李健吾仍然是沿着莎士比亚构筑的人物的心理特点:顾虑的缘由,强化疑心,酿成罪过的情节发展过程,使人们看到两个文本中人物心理变化之间的某种契合,毫无疑问,这种契合造成了《阿史那》在潜移默化中映现出《奥赛罗》的影子,毫无疑问,这种映现是互文性的绝佳证明。如果再深入一步看,这种属于人物性格层面的互文,把接受者带入了普遍人性范畴的语境中,中西两个文本中的人物性格形成了某种文化交流。如此一来,在互文性的作用下,就会使改编的《阿史那》借助《奥赛罗》产生基本一致的认同感和相同的道德批判指向。所以“从其产生的年代以及分析的年代”[10]观照《阿史那》,笔者发现,其在揭露社会丑恶、批判罪恶行经、揭示阴暗心理方面,通过互文性的自然转换,《阿史那》与《奥赛罗》之间就在表现人和人性上,自然形成了某种共识,并在共识的作用下把《奥赛罗》中国化了。从心理曲线的变化,到人性展示的契合,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阿史那》与《奥赛罗》之间的互文性主要表现在对人与人性的剖析、主题沿用、内心矛盾、心理发展变化、故事发展主要线索、揭露与批判精神的再造以及伦理道德的评判上,二者都以指涉人性中的“嫉妒、野心、爱欲、阴谋”作为推动人格裂变的原因。不同的是,《阿史那》由此衍生出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批判”与“揭露”的伦理道德指向。而在此基础上,再造的中国版《奥赛罗》也就跨越了莎氏时代的时间和空间,成为与中国文化、语境对接的莎剧。
《阿史那》的翻译加改编更多地融入了创作的理念,按照李健吾的话来说:“是字句,是结构,是技巧,也是血肉”[1],所以在《阿史那》中包含有大量来自汉语语境,富含中国文化信息的成语、俗语、历史典故,通过中国化的建构塑造出一个悲剧英雄——阿史那,以及制造悲剧的小人、野心家——令狐建,李健吾在解构英国文艺复兴时代精神的同时,以数量颇丰的蕴含汉文化信息的言语,拉近了读者和莎氏的距离,也容易使观众和舞台演出产生共鸣,如:“宁使我负天下人,勿使天下人负我”[1],“舍生入死,聊报万一”[1],“边荒兴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人生几何时”[1],“匹夫之勇”[1],“深谋远虑”[1],“花容月貌,国色天香,温柔敦厚,活泼轻盈”[1],“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1],“智者所不取,仁者所不为……名与身孰亲,名节、名节……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1],“知足者常乐,人一知足,虽贫犹富”[7],“我独伊何,来往变常……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9]等,其中既有化用《诗经》中的诗句,也有南北朝诗歌的直接运用,成语、俗语比比皆是。所以,笔者可以据此认为,此时的作者是无意于翻译,而是执着于创作的,故此在这一层面上的解构,更多地表现为是一种创作。
在此意义上的互文性说明,《阿史那》以报本反始“移花接木”[11]11的互文性,演绎出原作英雄美人气质,波谲云诡的剧情,卤莽英雄的偏听偏信,小人的阴鸷狠毒,杀人后的痛悔,使《奥赛罗》激荡人心向善,痛惜毁灭美的情感张力依然留在了《阿史那》中[11]11。尽管李健吾赋予了《阿史那》丰富的中国文化色彩,人们仍然可以从中找出原作的影子,这显然是莎剧中国化后的一种特殊创作方式。李健吾改编的指导思想是,莎剧改编应该“百分之百是中国的”[1],中国人改编莎剧“只借重原著的骨骼,完全以中国的风土,创造出崭新的人物、气氛和意境,那是化异国神情为中国本色的神奇。”[12]李健吾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认为:“学莎士比亚还是为了自己”[13],为了自己的文化,甚至是为了政治隐喻的需要。其实,《阿史那》的改编仍然遵循了“改编的灵魂要与莎翁原作共鸣”的指导思想,李健吾强调,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历史里体现他的高贵,语言里提炼他的诗意”[1],否则,他也不会说《阿史那》来自于《奥赛罗》了。
与《奥赛罗》相契合,《阿史那》的互文性呈现出的是“嫉妒、爱欲、权力、阴谋、野心之间的纠葛”,但从“令狐建”形象的塑造上,折射出的是李健吾对人性认知的深度,使读者和观众从互文性中悟到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相同或不同人物之间的某种若隐若现的关系,以此警惕策划阴谋,觊觎权力,野心膨胀之辈等,这都是不同文化语境中人性的翻版与再现。《阿史那》在20世纪40年代有意识借用伊阿古之流阴险、卑鄙具有时代环境特点的反面人物,如:充满野心的军人、阴险的小人,使人们既可以通过原典看到人性中的阴暗面,权力斗争的血雨腥风,又曲折地反映了腐朽世界已经为野心膨胀者和奸佞小人令狐建、鱼小恩之流的生存提供了适宜的温床,也便于人们通过“改编者和演出人员运用曲笔抨击当时黑暗的现实和社会邪恶势力”[14],从中认清改编的意图,从而在舞台演出中显示出深刻的批判意识,并在演出中获得观众的理解与共鸣。令狐建的形象隐喻了战乱中产生出的各类野心家、阴谋家,为此类人物在权力角逐场上的表演,增添一个形象而生动的注脚。正如令狐建所说:
世上的人不见得个个儿全有做主子的命,做主子的也不见得个个儿全叫人忠心到底……我表面伺候阿史那,其实我伺候的是令狐建……你可以说我是过河拆桥……[1]
我不喜欢搬弄是非,不过,你一定要我说,我只好说了。也就是前两天吧,我在行营和白元光一个炕上睡,我因为牙疼,一直睡不着觉。我就听见白元光糊里糊涂在喊:“好燕真,我们得当心,别叫人看穿了”!他捏住我的手,直嚷:“我的小心肝儿!我的好人儿!”过些时候,把脚搁到我的大腿上,直咂嘴,还直叹气,后来就捶着炕嚷嚷:“老天不长眼,会把你嫁给阿史那那黑小子!”[7]
《阿史那》和《奥赛罗》中主人公的人格均经受了很大的煎熬与考验、拷问和鞭笞,私欲膨胀到了极点,野心发展到了极致,手段极其卑劣,善良的人性被吞噬了,正常的人性也最终泯灭。在这一点上,令狐建与伊阿古毫无二致,性格特征极为相似。这两个形象都成为文本中被谴责、批判的“欲望再生产”[15]式的对象。例如,令狐建觉得:
……我像苍蝇一样叮他,我像孙子一样孝顺他,我里里外外两个人,一个做给别人看,一个留给自己用,你可以说我心口不应,你可以说我过河拆桥,只有我本人,清楚我是什么样一个坏蛋。[1]
李健吾强调:“莎士比亚可以说是善于处理空白的剧作家。”[16]11所以令狐建的内心独白使人物性格具有油画般逼真的效果,增加了观众和读者的想像空间。因此,作为互文性明显的《阿史那》也以舞台上的大段独白,反映主人公的内心,以此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对两个文本进行观照,就会清晰看到“堕落者”、“阴谋家”、“野心家”的心理基础以及权力诱惑、野心膨胀、灵魂堕落的性格特征。
《阿史那》与《奥赛罗》的互文性,还表现在营造戏剧性上。奥赛罗杀人以后,环境氛围使剧中人物的情感与内心反映融合在一起,制造出强烈的悲剧效果,阿史那也反复掂量,“我不敢往那上头想……我不弄死她,我就算不了好汉,我一世的英名就坏在这小贱人身上……我弄灭了你,只要我后悔,我就可以重新点亮你熊熊的火光……天下会有人狠得下心来不要你活!让我再香香你,再弄死你,我再爱你。”[9]《奥赛罗》的文本为李健吾提供了营造强烈心理效果,以达到戏剧性的基础,所以李健吾也沿着莎士比亚所构筑的戏剧性,将阿史那杀人中的矛盾心理、内心恐惧、爱恨交加成倍外化、放大,这对于准确描绘人物内心起到了“举一纲而张万目”的作用。《阿史那》与《奥赛罗》的互文性,在外在形式的表现上也都是以诗化剧词、冗长的独白的手段来达到塑造人物性格之目的。
以外国优良剧本的风格写中国戏,也可以说是把外国戏剧中国化,是李健吾等一批留学西方的学者为实现“话剧民族化”[2]388进行的艰难探索。从互文性的角度来看,此时《阿史那》中的人物已经不只是作为莎士比亚的创造物出现的,他(她)已经在“他”民族的文化环境中演变为经过互文性改造的再创造,由此,重新建构的中国莎剧叙事取代了原作的叙述内容,并在戏仿中取得了与本文结构的“多重复合统一”[17]。相对于原作来说,《阿史那》在人物塑造、人性挖掘上,建构了从英国文艺复兴时代进入初唐的中国化的叙述模式,再通过初唐时期的隐喻,过渡到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批判。《阿史那》以普遍的道德评判原则以及对善恶、美丑、真诚与虚伪的隐喻,宣示了对野心、阴谋和小人的鄙视与批判,表明对社会普遍遵守的道德底线一再被破坏的谴责,并通过其悲剧的震撼感,让人们的心灵为之震颤。所以,大家看到二者之间虽然没有,甚至不必在相同的叙述层面上实现复合统一,但在对假恶丑的批判层面,尤其是在戏剧所体现出来的道德标准判断上,则在殊途同归中实现了互文性。《阿史那》的改编证明,互文性是“从本文之网中抽出的语义成分总是超越此本文而指向其他先前文本,这些文本把现在话语置入与它自身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更大的社会文本中。”[18]40这就是说,《阿史那》在互文性中繁育出中国化的“伦理视点”,是按照人类社会、文化和习俗所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对现实中扭曲的人性给予中国化、民族化的再建构,使欲望、想象、正义的伦理愿望和悲剧的震撼力,在“悲剧艺术效果”[16]226的交织中,以“出于性格的自然与必然的推测”[19]得到被转换和替代的审美呈现。在《阿史那》中,程芸看清了自己的丈夫令狐建“原来是一个险恶的小人,一个恩将仇报的无耻东西!”[9]在关键时刻她敢于大义灭亲,而李燕真始终秉持着“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我嫁了阿史那,我爱我的阿史那。他就是骂,他就是打,他就是固执到底,我心里头也就是他这么一个人[9]。此种“伦理视点”通过《阿史那》对《奥赛罗》的解构和映射明确告诉观众,如“好人不得好报,这世上就是这么一个世上。”[1]这样的改编形成了《奥赛罗》中的“一个(或多个)信号系统”[20]5被挪移至《阿史那》的叙事系统中。尽管,《阿史那》所依傍的文化语境与《奥赛罗》的区别明显,但在人性、人物矛盾冲突与解决等基本关系和故事情节的铺展上,与原作可谓异曲同工,改变的仅仅是外在的东西。因为,无论是《奥赛罗》还是《阿史那》中所展现的社会、历史,并不是外在于文本的孤立社会现象、社会关系、人物性格的简单叠加,决不会超然于人性之外。因为,无论是《阿史那》还是《奥赛罗》都分别与它们所产生的社会形成了难以分割的必然联系。这是一种更为复杂、更多方向的互文性关系,笔者称之为深层互文性或第二互文性也未尝不可。
三、对换与对话:美学意义与认知价值
如今看来,这部翻译、改编的《阿史那》在促使李健吾对主题意蕴深入开掘的同时,也通过强化的意象——手绢的丢失、去不掉的黝黑肤色——“黑不溜秋的骚鞑子”[7]和内心深处的“他者”心理,从内外两个层次表现出英雄作为“人”的内心的极度恐惧与矛盾。奥赛罗始终是作为一个“他者”而存在的,为了彰显“他者”的心理,戏剧中一再出现手绢的情节,“金枝玉叶又怎么样?你是我的女人,你不拿我当丈夫看,我就有资格处置你。你的堂房天子哥哥也成全不了你这小淫妇妹妹……你栓得住她娇滴滴的人,你可栓得住她热烘烘的心?……我宁可做一个癞蛤蟆,在烂泥坑里面吸臭气,也不要把我心爱的东西摊开了,奉送给别人受用”[7],丢掉的“绣着一大朵牡丹花的花手绢”[7]等与原作若即若离的对白,体现出李健吾对原作创造性的改写。李健吾与莎氏一样,目的都是要营造一种以猜忌、嫉妒心理变化为特征的氛围,使《阿史那》在与《奥赛罗》的互动中始终围绕着“肤色”、“手绢”作为隐喻的“嫉妒”、“堕落”的互文性展开。这是李健吾与莎士比亚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超越时间和空间,是中西文化、民族之间的对话,是人类弱点之间的对话,更是人性的对话,按照巴赫金的理论,互文性的特征之一是对话和交流,“任何一个表述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对话(交际和斗争)中的一个对话。言语本质上具有对话性。”[21]即良心与野心、美善与丑恶、真诚与虚伪、执著与堕落、挚爱与嫉妒、猜忌与坚信之间的中西文化对话。《阿史那》在这种对话和交流中,构建起互文性书写方式,以爱和美的最终毁灭作为代价,并在悲剧性的结局中建立了互文性的对话机制。
这正好说明,《阿史那》在“‘李健吾式’翻译”[22]中呈现的是文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改编关系。因为“任何文本都是引语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23]翻译、改编的《阿史那》由于其先天具有的互文性特点,使其获得了经典文学作品的某些品质,《阿史那》沿用《奥赛罗》中矛盾冲突紧张、激烈的情节,人物性格发展充满矛盾,个性鲜明,情感充沛,大起大落,弥补了李健吾戏剧创作中轻视故事,缺乏强有力对手戏的不足之处○131949年以后,随着时过境迁李健吾翻译改编的戏剧就没有再演出过。田本相认为孤岛时期,李健吾这类“改编非常成功,因为人们感受到作者对现实的悲愤情感和抗战必胜的信念”,参见田本相:《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660—662页。张殷认为,李健吾在创作过程中,过分轻视“故事的力量”,也缺少“多侧面的个性”展示,这是李健吾的戏剧不为后来的舞台演出者青睐的原因之一,参见张殷:《对李健吾中期剧目界定及文本探究》,《戏剧》2003年第4期,第113页。邹元江认为,李健吾的戏剧够不上艺术,李健吾的剧作从来不能上演。参见邹元江:《戏剧“怎是”讲演录》,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73、287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李健吾的戏剧主要目的不是“艺术化的呈现”。。由此看到,在经过一再忧郁之后,阿史那终于向李燕真举起了屠刀:
我要是弄灭了你,我的好女人,我到什么地方去找那一把天火,再把你点亮了?[9]
阿史那用情不明,却也用情太痴;不大容易妒忌,可是妒忌起来,就糊涂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信手抛掉他的价值连城的夜明珠。[9]
据此可以得出,《阿史那》与《奥赛罗》的互文性,在没有脱离莎氏原文本的基础上,通过多方位的吸纳与被吸纳,在发生互动关系的文本之间呈现出盘根错节之关系,显示出《阿史那》在文本语境、悲剧精神和文化代码在互文性的作用下已经发生了改变,使莎氏的《奥赛罗》已经变异为中国的《阿史那》,而且经过变异的文本也不再是以单一自然语言为载体的原作,但其批判精神仍然没有失落。在不同文化背景得到了经过变形的再一次延伸和转换,并由此产生出中国化、民族化新的美学认知价值。
放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大背景下观察,《阿史那》对《奥赛罗》的“建构”与“解构”,既是在原作与译作,也是在历史与文化、民族与时代、戏剧观念与舞台建构之间确立他们之间互文性关系的。它们之间的互文性已经蕴涵在《奥赛罗》主旨语篇的主题、内容之中,并由此在不同体裁、语境或风格特征中形成了一个混合交融的共同体,也由于《阿史那》对《奥赛罗》的互文性书写,使其在中国语境中形成了新的意义潜势,使来自于他体裁的文本获得了另外一种生命意义。在这种“翻译”以及主观化的改编中的解构已经变换了主体的位置,演变为中国化、民族化的另一位置,使原有文本的潜势在所形成的新的潜势里,其互文性得到了确认和光大。所以,文本比较,可以使处于另一语境里的互文性阅读与互文性观赏得以实现。
毫无疑问《阿史那》是在对《奥赛罗》的建构与解构之中完成的。这种对《奥赛罗》中国式、民族化的重读,是在原作与创作、偏离与更新、删节与浓缩、挪移与翻译、建构与解构中建立起了两者之间的互文性关系的,《阿史那》的价值很大一部分也恰恰是建立在与《奥赛罗》的互文性之上和延伸出来的中国化、民族性,李健吾“要《阿史那》百分之百是中国的,他希冀莎士比亚也在这里拥有同等的分量”[1],同时也使互文性的《阿史那》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并在对中国社会发生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对经典的“以前的文本的遗迹或记忆形成”[18]40的追寻与沿用,是重读基础上的有意误读的中国化再阐释。
四、结语
《阿史那》与《奥赛罗》之间的互文性使其在中国莎学史上形成了特有的美学意义和认识价值,成为通过这种“文学的书写伴随着对它自己现今和以往的回忆,追寻自己情感的依附物。”[20]35《阿史那》以一系列的翻译与复述、追忆和重写超越了时空。李健吾认为:“艺术是真理的工具”[24],从《阿史那》的改编中可以看到,李健吾的策略是,采用莎剧的故事内容、情节、人物、伦理道德评判标准及其悲剧精神;而社会背景、故事情节、人物已经置换为中国人所熟悉的。这种互文性的置换使人们在接受经典的过程中减少因文化、民族和时代所带来的生疏与隔膜,为更好理解莎氏悲剧精神,为作家建构中重置的主观意蕴,也为接受者跨越文化之间的差异,同时也再次为“文本地位提升”[25]与对经典的深入认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1]莎士比亚.阿史那[J].李健吾,译著.文学杂志,1947,2(1):63-102.
[2]李健吾.后记[M]∥李健吾.李健吾剧作选.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
[3]姜涛.“佐临的风格”与梦想[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
[4]白文.佐临氏在“苦干”时期的艺术活动[G]∥上海艺术研究所话剧室.佐临研究.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
[5]宁殿弼.李健吾悲剧创作的艺术特色[J].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1):52.
[6]弗兰克·埃尔拉夫.杂闻与文学[M].谈佳,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7]莎士比亚.阿史那[J].李健吾,译著.文学杂志,1947,2(2):87-131.
[8]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9[M].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9]李健吾.前言.莎士比亚.阿史那[J].文学杂志,1947,2(3):68-102.
[10]罗伯特·考克尔.电影的形式与文化[M].郭青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1.
[11]柯灵.序言[M]∥李健吾剧作选.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
[12]孟宪强.中国莎学简史[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48.
[13]李健吾.咀华与杂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242.
[14]曹树钧.莎士比亚在中国舞台上[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89:107.
[15]刘建辉.挂在墙上的摩登——展现欲望都市的又一表象[M]∥孙康宜,孟华.比较视野中的传统与现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02.
[16]李健吾.戏剧新天[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17]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1117.
[18]王瑾.互文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9]李健吾.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61.
[20]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邵伟,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21]巴赫金.对话、文本与人文[M].向春仁,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94.
[22]姜洪伟.试论改编剧《阿史那》与原作《奥瑟罗》的关系[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1):86.
[23]Juliu Kristeva.Word,Dialogue and Novel[M].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 Ltd.,1986:36.
[24]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56.
[25]维克多·泰勒,查尔斯·温奎斯特.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M].章燕,李自修,译.刘象愚,校.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5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