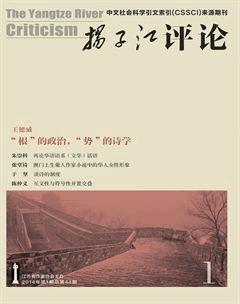“根”的政治,“势”的诗学
一、前言
华语语系研究是新世纪以来最受注目的论述力量之一。这一论述始于陈鹏翔教授在上个世纪末对传统华文文学的批判。①但华语语系研究能够形成具有思辩向度的议题,则必须归功史书美教授。她的专书《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2007)论证丰富、立场鲜明,因此出版后引发此起彼落的对话。我们也许未必同意她的立场,但却必须尊敬她的论述能量以及政治憧憬。②
如果以《视觉与认同》为坐标点,我们大致可以勾勒一个当代华语语系的论述谱系。这个谱系至少包括如杜维明教授的“文化中国”、王赓武教授的“地方/实践的中国性”、李欧梵教授的“游走的中国性”、王灵智教授的“中国/异国双重统合性”等立论;以及如周蕾教授的“反血缘中国性”、洪美恩(Ien Ang)教授的“不能言说中文的(反)中国性”、哈金教授的“流亡到英语”等反思。③这些学者各据海外一方,也各有立论的动机。大抵而言,前一组学者虽承认华人离散的境况,却力求从中找出不绝如缕的文明线索,想象“花果飘零,灵根自植”的可能性。后一组学者则质疑任何“承认”的政治;他们解构“中国”(血缘、语言、书写,主权)作为实践或想象共同体的合理合法性,甚至不无连根拔起的尝试。
史书美教授深化这一谱系的辩证性。她强调清帝国以来中国(面对藏、蒙、新疆及其他少数族裔)的“内陆殖民性”;中国海外移民在移居地充满掠夺性的准殖民行径;以及落地应该生根的“反离散”论,在在引起议论。④方法学上,她呼应了北美后殖民主义以及少数族裔研究理论,力图带入华裔立场。与此同时,张锦忠教授凭借马华旅台学者观点,指出不同华语地区的文化发展盘根错节,难以归纳成一二理论。⑤石静远教授(Jing Tsu)则发挥英美实证主义特色,仔细爬梳华语语境内种种文学合纵连横(literary governance)的样貌。⑥
短短几年内,华语语系研究发展如此蓬勃,当然显示此一议题的潜力。但无可讳言,目前所见的讨论仍然存有许多——包括来自我个人的——盲点与疏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类讨论尽管壁垒分明,却不脱对一种我所谓“根”的空间政治的执着。本文试图回答华语语系研究若干疑义,也希望对目前以后殖民主义或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根”的空间论述,提出建言。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尝试响应香港黄维梁教授对“华语语系”命名问题的批评;第二部分对我个人所曾着墨的后遗民论述再作检讨;第三部分提出“势”的诗学,作为“根”的政治的对应。
二、必也正名乎?
2013年8月,香港《文学评论》刊出黄维梁教授的长文《学科正名论:“华语语系文学”与“汉语新文学”》,文中针对2006年刊于《明报月刊》的拙文《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提出质疑。黄教授的论点可以综述如下:一,“华语语系文学”作为Sinophone Literature的中文对应词,适宜性应该商榷。一般而言,语系指称语言家族,如汉藏语系、印欧语系、高加索语系等,每一家族都含数十甚至数百分支语种,形成庞大体系。相形之下,华语,或黄教授定义为汉语的统称,只是汉藏语系中的一支;如果以“语系”名之,容易造成不懂汉语(粗糙地说,则为中文、华文、华语)的人的误会,以为“汉语”是个“巴别塔(Tower of Babel)般的语言大家庭,其中有许多语言”。⑦
其次,黄教授认为,Sinophone一词在英语词汇里与Anglophone、Francophone、Hispanicphone等词颇有定义混淆之处。后面三者都指涉欧陆国家在境外对所传布的语言共同体,如英国之于印度,法国之于西非,西班牙之于拉丁美洲。年久日深,这些外来强势语言已经潜移默化成在地语言基础。但不论如何,这样的现象只是一种语言内部的变化,与“语系”无关。
除了“华语语系”的翻译、解释问题外,黄教授指出目前已经有各种描述中国大陆以外的汉语/华语文学现象的名词,如华文文学、大陆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等。要之均代表中国文学界对“界外”文学的尊重与包容;刻意使用“华语语系文学”因此有画蛇添足之嫌。更有甚者,黄教授暗示提倡“华语语系文学”如我等,往往使用如版图、策略、对抗、收编等挑衅性字眼,有违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的“王道”。
最后,黄教授以澳门大学朱寿桐教授的《汉语新文学》为例,作为大陆学界跨越制式文学史的最新尝试。该作企图超克“国家板块,政治地域”制约,以“汉语审美表达的规律性”出发,探讨大陆中国与华人世界的文学表现。金庸、白先勇、余光中等因此进入正典,展现汉语文学兼容并蓄的特征。据此,黄教授的结论是Sinophone Literaure的正名应该是“汉语文学”。
黄教授是学界前辈,对“华语语系”一词有以教我,应该衷心感谢。但他的质问触及华语语系论述易生混淆之处,持类似疑问者恐怕不在少数,因此有加以厘清的必要。华语“语系”一词,诚如黄教授所言,似有名实不符之嫌。但我在《明报月刊》拙文刊出后下一期复读者来书已说明,使用“语系”一词,有其不得不然的“策略”考虑。这就回到史书美教授对Sinophone的定义问题。事实上,黄教授提问的对象应该是史教授才是。
史教授对Sinophone的定义和黄教授恰恰相反,她的专书开宗明义点出使用Sinophone的意图,正是要提醒我们汉藏语言家族的复杂性,而汉语只是其中一种。史教授所关注的范畴恰是汉语的驳杂性,以及中州正韵(普通话?)以外,华夏文明中其他声音表述。她的着眼点在于大陆境外的汉语圈或境内境外少数民族的语言传播现象。以“华语语系”来诠释她的Sinophone视野,因此良有以也。梅维恒(Victor Mair)教授认为我们统称的汉语从来不是一统的语种,而各地所谓的汉语方言如此繁杂分歧,已经可以区域语言(toplect)来对待。⑧延续梅教授的看法,我们可以说汉语就是个“巴别塔”。史、梅二位教授的观点意外得到了中国官方的佐证,2013年9月5日新华社发布中国教育部的说法:“中国目前仍有四亿多的人口不能使用普通话交流。”这些人恐怕多数竟是汉语的使用者。“发展普通话,共筑中国梦”成为年度大计。⑨
史书美对Sinophone的定义有其特定政治思考方式,下文将再讨论。但她所设想的华语语系观念跳脱了黄、朱两位教授的汉语框架,值得深思。中华文明的流传过程里,书写表意方式无可讳言的以汉语为大宗。然而“书同文”的现象并不能排除种种地域、阶层、族群、文化里的形声、会意的可能表现。⑩强调华语语系研究,而非华文或汉语研究,正是因为理解(并且提示我们留意)正宗汉语书写表意系统以外,以内,以下,种种自成一格的言说位置、发声方式、表述行为。
从语言到文字再到文学当然是极复杂的问题,此处暂时存而不论。我所要强调的是,尽管我们承认汉语书写的重要性,却不必如黄维梁教授所建议,视其为唯一的“审美判准”。一个时代或地域有一个时代或地域的文学,已经是老生常谈。在不以文字见长的地域或阶层,“文学”又是如何定义?唯有在这样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格局下,黄教授念兹在兹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才不致沦为官方或主流意识的说法。
即使我对Sinophone/华语语系的用法自有理论的脉络,我仍然必须承认“语系”一词并不适用Anglophone、Franchophone、Hispanicophone的历史与言说情境,因此黄教授的指教,促使我思考,此前我刻意在Sinophnoe和其他语种离散传播现象上作出对等翻译,反而模糊了问题的焦点。
与此同时,我对黄教授提议以“汉语文学”作为Sinophone的对等翻译,却又必须表示异议。原因无它,众所周知,Anglophone、Franchophone、Hispanicophone文学带有强烈的殖民和后殖民辩证色彩,都反映了十九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占据某一海外地区后,所形成的语言霸权及后果。因为外来势力的强力介入,在地的文化必然产生绝大变动,而语言,以及语言的精萃表现——文学——的高下异位,往往是最明白的表征。多少年后,即使殖民势力撤退,这些地区所承受的宗主国语言影响已经根深柢固,由此产生的文学成为帝国文化的遗蜕。11这一文学可以铭刻在地作家失语的创伤,但也同时也可以成为一种另类创造。异地的、似是而非的母语书写、异化的后殖民创作主体是如此驳杂含混,以致成为对原宗主国文学的嘲仿颠覆。上国精纯的语言必须遭到分化,再正宗的文学传统也有了鬼魅的海外回声。
恰恰是在这里,我们看出史书美教授与黄维梁教授的绝对距离。史教授承袭后殖民主义和少数族裔文学说法,将中国——从清帝国到民国到共和国——也看作是广义的帝国殖民主义的延伸,如此,她定义的Sinophone就与Anglophone、Francophone、Hispanicphone等境外文学产生互相呼应。她同情僻处中国国境边缘的弱小民族,遥居海外的离散子民。她的华语语系带有强烈反霸权色彩;对她而言,人民共和国对境内少数民族以及海外华语社会的文化政策,不啻就是一种变相的殖民手段。黄维梁教授恰与史教授针锋相对。在他看来,以往的海外文学、华侨文学往往被视为祖国文学的延伸或附庸,时至今日则代之以世界华文文学等名称,适足以表现尊重个别地区的创作自主性。他将所推动的“汉语新文学”去政治化,将来自“中国”的汉语文学视为万流归宗的隐喻。
我以为史、黄二人的理论各有过犹不及之处。史书美教授将清代以来中国的境况都依殖民、被殖民的角度解释,难免以偏概全。清朝是否为“帝国”?近年引起众多论辩;历代在综理汉满文化、调节其他族裔的关系上多管齐下,极难简化为欧美定义下的殖民政策。12清朝原是一个由满洲人建立的皇朝,却脱胡入汉,统领中原,岂不是史教授定义下的一个从边缘打入中心的Sinophone政权?她对清帝国的批判其实反证了自己的观点。“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复杂多义的政教传统。另一方面,史教授强调移民者对在地原住民的经济文化及政治势力的掠夺,形成“移民者的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与帝国殖民主义形成五十步笑百步的关系。
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外患频仍,但并未出现传统定义的完全被殖民现象——除非我们将后殖民理论无限上纲,视任何“外来政权”的统治都是殖民统治。香港、台湾、满洲国、上海等殖民或半殖民地区里,中文仍是日常生活的大宗,文学创作即使受到压抑扭曲,也依然不绝如缕,甚至有特殊的表现。13这促使我们思考殖民论述之外,这些地区华人延续他们的文化语言传统的动机。另一方面,由于政治或经济因素使然,百年来大量华人移民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他们建立各种社群,形成自觉的语言文化氛围。尽管家国离乱,分合不定,各个华族区域的子民总以中文书写作为族裔文化——而未必是政权——传承的标记。
黄维梁教授藉“汉语新文学”发挥的Sinophone观点,同样引起我的疑义。他在努力推动汉语文学大团圆之余,有意无意忽略了同文同种的范畴内,主与从、内与外的分野从来存在,更何况在国家主义的大纛下,同声一气的愿景每每遮蔽了历史经验中断裂游移、众声喧哗的事实。他强调他的汉语文学大同世界里,金庸、白先勇与传统共和国文学史的大师平起平坐,这真是个文学的“和谐社会”。果如此,中国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美国哈金的《自由生活》、法国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香港陈冠中的《盛世》、台湾舞鹤的《乱迷》,何以就被“和谐”掉了呢?
黄教授指责海外汉学学者刻意使用挑衅字眼,与祖国为敌。他越是希望将文学“去政治化”,却越显出“中国”“汉语文学”定义的复杂性。尊重汉语为中国文学的最大宗是我们的共识,但这并不代表汉语圈以内和以外的文学政治必得用“一床锦被遮盖”。欲洁何曾洁,这是我对黄教授“正名说”的保留。我们必须正视中国/汉语文学众声喧“华”的辩证意义。与汉语对比,华语有相对较大的地域、文化、族群、语言/语音的驳杂性和包容性。这也正是史书美教授强调“华语”作为Sinophone 的翻译的初衷。
三、当后遗民遇见原住民
针对以上所介绍的两种解释Sinophone——后殖民主义vs.国族主义——的立场,我曾经提出“后遗民写作”的看法。我的论点来自我所谓的华语语系的“三民主义”现象:“移民”、“夷民”、“遗民”。14华人投身海外,基本上身份是离境的、漂泊的“移民”。时过境迁,一代又一代移民的子女融入了地区国家的文化,形成我所谓的“夷民”——也就是从这一点来看,史书美教授认为华语语系终究是过渡现象。但仍然有一种海外华语发声姿态,那就是拒绝融入移居的文化,在非常的情况下坚持故国黍离之思,是为遗民。这三者都各有时地的制约及因果,互为定义的例子也所在多有。但我认为如果仔细思考上述海外华语语系的现况,华语“移民”、“夷民”、“遗民”文学之外,我们应该正视“后遗民”的观点。
“后遗民”原是我针对台湾当代文学政治所发明的词汇,出于我对“后学”,尤其是“后殖民”、“后现代”理论不无调侃意味的回应。“遗民”的本义,原来就暗示了一个与时间脱节的政治主体。遗民意识因此是种事过景迁、悼亡伤逝的政治、文化立场;它的意义恰巧建立在其合法性及主体性已经消失的边缘上。宋元、明清鼎革之际,都有宗室后裔、志士仁人不愿舍弃前朝正朔,或遥奉故主、或徐图大举,形成“遗民”现象。
“后遗民”把这样的遗民观念解构了——或不可思议地,招魂般地召唤回来了。到了二十世纪,民主、共和、革命思想当道,强调忠君保国的遗民意识理应随着“现代”的脚步逐渐消失:过了这个村,没有那个店。然而事实并不如此,从大清到民国,从民国到共和国,从社会主义到后社会主义,每一次的政治裂变,反而更延续并复杂化遗民的身分以及诠释方式——遗民写作也因此历经了现代化,甚至后现代化的洗礼。晚清遗老文化后续有了国民党到台湾的遗老文化;更不可思议的是,当代大陆新左派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盛世”,俨然也有着遥思“先帝”,不胜唏嘘的姿态了。
我所谓的“后”,不仅可暗示一个世代的完了,也可暗示一个世代的完而不了,甚至为了未来而“先行后设”的过去/历史。而“遗”,可以指的是遗“失”,是“残”遗,也可以指的是遗“留”——赠与与保存。失去、残存、留传三者之间形成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如果遗民已经指向一种时空错置的征兆,“后”遗民是此一错置的解散,或甚至再错置。两者都成为对任何新兴的“想象的本邦”最激烈的嘲弄。由此产生的焦虑和欲望,发明和遗忘,妥协和抗争,成为当代华语语系论述的焦点。
《后遗民写作》曾经遭到不少质疑。最直接的挑战是,这就是“遗民”意识的借尸还魂;“后”遗民就是遗民的后之来者。这样的说法有望文生义之虞,忽略了“后”所承袭的“后学”——从后现代到后历史、后殖民——的理论资源。德西达(Jacques Derrida)“魂在论”(hauntology)对我的影响尤其明显。我所借的尸、所还的魂,必须在这一语境里思考。15但我更希望强调的是,“遗民”说是出自中国传统的独特论述,因此用以讨论华语语系的记忆政治学,兼亦反省阴魂不散的中国意识,尤多一层历史关联性。
“遗民”意识的产生除了国朝鼎革,也可能来自地域、文化甚至“天下”的兴替。无论如何,遗民在时空的皱褶里,在正统的边缘上,苦思解脱之道。而我的看法是,如果“遗民”总已暗示时空的消逝错置,正统的替换递嬗,“后遗民”则更错置那已错置的时空,更追思那从来未必端正的正统。这样的姿态可以是颓废的、耽溺的,但我更期望指出其中批判和解脱的契机。
我以为“后遗民”心态弥漫在华语语系的世界里,成为海外华人拒斥或拥抱(已经失去的,从未存在的)“正统”中国的最大动力。论者亦有谓后遗民理论刻意贬低新兴民族主义以及后殖民论述,为现有或已逝政权的合法性找寻借口。恰恰相反,我以为“后遗民”是具有强烈批判——以及自我批判——意识的论述。我甚至要说,越是激烈的民族主义者与后殖民主义者,越应该反省他们/她们思路中阴魂不散的遗民情怀。君不见,在“江山鼎立开新国”的时代,首要之务就是打造一个其来有自,但“总已经”失去的国家或地方根源?为了未来而发现(发明)历史,当后设变为先验,后遗民的双面幽灵已经出动。
换句话说,“后遗民”并不只是“遗民”的延伸,而有了物种突变的意涵。后遗民论述让我们在海外面对中国性或是华语所谓的正统性和遗产继承权的问题,带来了复杂的选择。海外华语语系的子民在世代传衍之后,当然可能如史书美教授所预测,逐渐忘记、抛弃父祖辈的中国情结——黄宗羲早就有言,“遗民不世袭”。也可能如石静远教授所言,基于各种(政治、商贸、文化、宗族)沟通的动机,自觉地和中国(假故国之名?)相互协商,建立网络。更激进的可能却是:有没有那(中原的或宝岛的或“南洋人民共和国”的)正朔/霸权是一回事,何以华语语系的子民在离散以后,明明知道“我们回不去了”,而仍然塑造、拆卸、增益、变通、嘲仿他们对家国和故土的效忠或背弃?
“中国”的幽灵必须严肃对待。除魅还是招魂?作为一种“法事”,后殖民论述不能完满的解释二十世纪华语语系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只有当我们正视后遗民思维的不绝如缕,我们才能理解这是华语语系文学与Anglophone、Francophone等境外文学最大的不同之处。
以上的讨论也许可以作为对刘智浚教授《当王德威遇上原住民:论王德威的后遗民论述》一文的回应。16刘教授对后遗民论述的关注让我感动;他在文中所显示的焦虑和误读却也足以说明拙作《后遗民写作》论述的不足。无可讳言,《后》书的出现有特定历史时间因素,也显示我个人从事此一论述的挣扎和反省。但我已一再指出“后遗民”一词的有效性不在于为哪个政权护航,而在于提出一个批判界面,让我们理解号称“民主”与“现代”的政治意识里视而不见的盲点,也让我们发现史料/始料未及的创造性。刘教授将我对“民国遗民”的嘲讽看作成一种自怜,我无言以对。他的台湾文学史观不能容忍朱天心、舞鹤、李永平、骆以军等我所谓具有后遗民意识的作家,则令人不解。李、朱、骆三人分属外省第一代(?)和第二代作家,也许血统不够纯正,但舞鹤不是“正港”台湾人么?
刘教授的批评尤其集中于舞鹤书写雾社事件的小说《余生》以及我的评论上。有关此作的讨论不胜枚举,此处略过不表。刘教授的批评主要针对舞鹤对这一起泰雅族抗日事件没有作正面叙述,非但有愧于泰雅英烈,甚至对整个族群不敬。更何况舞鹤对于泰雅族后裔的颓败生存境况的描写,侮辱了当代台湾原住民的主体性。而台南人舞鹤写起泰雅族故事,根本就是越俎代庖。
刘教授的出发点来自于坚定的(原住民)民族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四百年来,台湾原住民受到从荷兰人到国民党的压迫,他们徒劳的抗争,他们悲凉的存在,无不激发有识之士的“始原的激情”(primitive passion)。但在各个外来政权席卷宝岛之前或同时,是否各时期移民来台的汉人出于各种自发动机对原住民的巧取豪夺,也应该受到批判?史书美教授所谓“移民者的殖民行径”早有一针见血的观察。最不可思议的是,刘教授对泰雅族的“烈士”精神、抗暴壮举,从修辞到逻辑,竟然充满了前面所论的(而且相当国民党式的)遗民意识:雾社事件是台湾史的重要一刻;英烈千秋,忠勇足式,作为后之来者,我们决不可唐突于万一。
舞鹤的《余生》之所以重要,正因为他将莫那鲁道从忠烈祠请了出来。他告诉我们雾社勇士抗日是事实,但除了反帝反殖民外,也可能也是部落“出草逻辑”使然。而中国论述所忽略的第二次雾社事件恰是日本人挑拨下,泰雅族部落之间的战争。比起同行(尤其是泰雅族作家),舞鹤写出这个故事的资格并不更多或更少。要紧的是,他呈现了一个外来的汉人重新“遇见”——而不是重新“预见”——雾社事件的震撼、尴尬与反思。他有藉此一浇自己块垒的动机,他不能原汁原味的用泰雅语言表述,他不在现场。但他从来没有讳言这些局限,也不想将他的故事划归任何反殖民或(沈葆桢式的)“遗民世界”。更极端的说,台湾的原住民族原来就不是汉民族,没有必要为汉人沾沾自喜的遗民意识装点门面。在这个意义上,舞鹤是后遗民作家,因为他舍弃以血缘、族裔、宗法、语言为基础的遗民叙事逻辑,重新思考雾社事件的残片,及其所遗留/赠与台湾后世的意义。
捍卫台湾本土立场的学者企图建立岛上原生性(indigeniety)理想,当然值得尊重。但在强烈的寻根焦虑下,他们不知不觉形成原乡、原道、原住民、原教旨的连锁。一方面将原住民化为正本清源的岛屿象征,另一方面又亟亟还原原住民的绝对本体性。前者将原住民寓言化17,后者将原住民始原/绝缘化,两者诚意十足,却都忽略原住民在地的、历史的处境与时俱变。与此同时,对晚近从东南亚或其他地区迁入的新住民(移民而来的夷民?),我们是否也给予关切?
我们必须让问题化简为繁。方法之一,不妨就让“后遗民遇上原住民”,新加坡作家谢裕民的《重构南洋图像》18里的中篇《安汶假期》或可为例。在那个故事里,一位新加坡青年与父亲到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首府安汶寻根。偶然间得知他们原籍安徽凤阳朱姓。1662年,明亡以后十八年,十世祖欲赴台湾投靠郑成功,却为台风吹到安汶。十九世纪中,偶有粤人阙名来到岛上,遇见土著,却“声类京腔”,“口音非闽非粤”,竟是朱氏后人。阙受托携其子回到中国,即为新加坡青年的曾祖。曾祖日后自中国移民印度尼西亚,1960年代又因印度尼西亚排华回到中国,却将一个儿子托在新加坡,即是青年的父亲。故事高潮,父子两人在安汶似乎找到家族后人,但他们看来就(像)是土著……
《安汶假期》的情节尚不止此,还包括了一个荷兰女子来到前殖民地的怀旧冒险,以及主人公后现代式的恋爱游戏。但对我们而言,明代遗民如何辗转成为印度尼西亚土著,经历殖民经验与中国的召唤,成为新兴国家新加坡公民,俨然就是一则后遗民谱系的寓言。当新加坡父子似乎与亲人重逢,问题来了,“我们的血统到底要追溯到哪里?三代前有印度尼西亚土著血统,再往前原来还是明朝的贵族。谁知道再往前追溯,会不会不是汉人?”在摩天大楼里工作的青年回想家族身世,曲折得像一场诱惑,却又如此破绽重重。的确,当后遗民和原住民开始接触,记忆重组,身份变换,华语语系的历史与虚构变得无比繁复,“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终至不能闻问。
四、“根”的政治,“势”的诗学
华语语系论述与中国文学论述在分殊彼此的过程里,目前所依赖的理论资源基本不脱“空间/位置的政治”(spatial and positional politics)。提到现当代中国文学,论者立刻想到中国大陆所生产的文学,而且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叙事”作出或正或反的连接。相对的,提到华语语系文学,海外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联想浮上台面。在这个二分基础上,我们有了内与外(interiority vs. exteriority)、包括与排除(inclusion vs. exclusion)、定居与离散(settlement vs. diaspora)等等划分畛域、区别立场的论述。由此产生的伦理问题,如敌或友(hostility vs. hospitality)、整合与抗争(governance vs. resistance),尤其耐人寻味。
“国家”与“文学”原本就是二十世纪以来由西方引进的政治、审美建构。谈“中国”文学的国家定位,因此无可厚非。但作为文学史的观察者,我们总必须将研究对象再历史化;我们毋须把中国当作铁板一块,逢“中”必反。而应先询问所谓“中国”,是主权实体、是知识体系、是文明传承还是民族想象?或甚至是欲望爱憎的对象?19我们也不必将“文学”化约为简单的西方文类表现;“文”的思维与表征在中国文明里有复杂的传承,不宜轻轻带过。20同样的,华语语系文学虽然是最近的发明,也一样需要被历史化。Sinophone论述的出现,呼应了华语区域的学者近年对身份的焦虑,一方面固然受到后殖民、后遗民等论述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中国崛起”的联动产物。
不论如何,两造的论述都是以特定地理或者心理坐标为起点。这一坐标,我以“根”的隐喻名之。中国论述面对海外离散境况,每每比拟祖国的历史文明仿佛大树一般,根深柢固,华裔子民就算在海外开枝散叶,毕竟像“失根的兰花”,难免寻根的冲动。离散者最后心愿无他,就是叶落归根。华语语系文学与以往海外华侨文学、华文文学最不同之处,就在于反对寻根、归根这样的单向运动轨道。即便如此,论者的修辞策略却似乎仍围绕着“根”的隐喻:中国文化、政治的影响如此深远,必须连根拔起,才好另谋发展。相对于叶落归根的呼吁,只有在移居地落地生根之后,才能成就华语语系的主体性——不论是这一主体性的塑造还是舍弃。
在此之上,我们同时可以回顾两种较为细腻的响应。1961年唐君毅先生(1909~1978)发表《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慷慨陈述华族文化的分崩离析,和坚守道德价值的必要。三年后又发表《花果飘零和灵根自植》,期勉海外流亡人士自信自守、别开新局。这两篇文章对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境外的离散论述有深远影响。让唐有感而发的自然是1949中国政治的大变动,知识分子流亡海角天涯,只有尽一己之心力,挽狂澜于既倒。但唐的号召之所以动人,应不仅在为一个时代或一个政权的倾覆哀悼而已。清末民初以来,他所信赖的儒家道统不早在现代狂飙下,陷入花果飘零的困境?往前推去,当龚自珍一辈学者在十九世纪中发出“衰世”之叹,以“忧患”一辞注历史,21或当明清之际的王夫之(1619~1692)不感叹一家一姓的兴废,而感叹文化传统的存续,已经为现代中国“感时忧国”的叙事预作说明。22
上个世纪还有另外一种关于“根”的论述,恰恰与唐君毅所代表的新儒家传统背道而驰。那就是鲁迅的《野草》(1926)。试看《野草》的题词: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23
鲁迅对中国主体的思考一样及于文明以及其本体的存亡上。中华文化花果飘零以后,世纪的罡风与狂飙如此残酷,灵根怎能自植?在没有灵根的荒原里,只有野草“坦然”、“欣然”的“自生自灭;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唐君毅和鲁迅的时代和理论立场极其不同。但他们都跳脱简化的国族主义立场,思考更广义的中国文化与现代性交会以后所面临的危机。唐君毅从儒家资源找寻救赎之道,鲁迅反其道而行,坚持希望与绝望同为虚妄,必须置之死地以后,才能谈起死回生的辩证性。
如果转向西方当代理论,德勒兹(Gilles Deleuze [1925-1995])与瓜达利(Felix Guattari[1930-1992])所提出的“根茎论”(theory of rhizome)也许可以作为另一个批评的界面。德、瓜两人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操作下的知识体系及主体建构过分依赖主与从,中心与边缘的二分法;这些体系和建构基本不脱有根有柢,开花结果的“树状(arborescence)思维。”“我们厌倦这些树什么的,也不再相信根什么的……从生物学到语言学,我们受够了所有和树[的象征]有关的论述。只有地下茎的,气根的,偶生的,根茎的才是真正美丽的,可爱的,政治的。”24根茎意味抽长的纤维、延伸的茎脉各行其是,甚至“穿透树体,展现新奇怪的,新颖的用处”25。
德勒兹与瓜达利的理论根源颇为复杂,包括了莱布尼兹(Leibniz)的原子论到世纪之交的无政府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此处从略。但正如他们理论所强调的根茎想象的无孔不入,盘根错节,我们可以据此嫁接到中文/华语语境,从而正视中国国境以内到以外,语言、文化、政治根的接触从来难以厘清,而形成蔓延交错,无孔不入的现象。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承认这一“根茎”论充满解放/解构式的狂欢气氛,虽然口气热烈,难免显得一厢情愿。
灵根、野草、根茎的说法,都对我们所熟悉的“根”的论述有所修正。除此,后殖民主义大师豪尔(Stuart Hall) 的“根/径”(roots and routes)论也可作为参考。26但既然引用“根”的隐喻,这些说法也依然在界限或极限的认证,空间或位置的定义上,作文章。它们各有政治意图,却也为内蕴的象征所限。27我们的挑战是,在这些有“根”——也有立场/位置甚至路径——的论述之外,是否仍有其它理论突破的可能?
法国汉学家余莲(Fran
类似余莲的观察在西方汉学界其实不乏前者,30但他出入中西哲学的方式仍然值得注意。余莲强调中国体系的空间观不以本质化的“差异”(difference)观点,而强调“间距”(écart)观。间距不产生“非此即彼”的差异,而有“往复来回”、“不即不离”的动线。用林志明教授的话来说,“那是突破自己的局限(和自身的思想产生一个间距),同时也是给予思想一个新的可能(和他人的思想产生间距)。”31更有意义的是,他强调时间观中的要素之一,“不再是以行动来作为考虑观点,而是以(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变动来作考虑观点。”32如果西方的时机观(kairos)所属的时间出自偶然,无法降服,我们的因应之道或可能是掌握有利关键,防患于未然,或可能是英雄式的自我发明或超越。中国传统的时机则是在对付“偶然”之外,一种“势态中的潜力”、一种因势利导或顺势介入的方法。
这里的关键词是“势”。“势”有位置、情势、权力和活力的涵义;也每与权力、军事的布署相关。余莲认为“势”在印欧语系中没有相应字眼,他问道,如何经由现实本身的局势来思考它们的活动力?或者说,每一种情况如何能同时被感知为是现实发展过程(comme coursdes choses)?33他将“势”译为“事情发展的自然趋势才是决定现实的最佳方式”。34近年对“势”重新诠释而受瞩目者另有汪晖。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里取径柳宗元,强调“势”作为一种历史动能,和“理”相互作用、消长的关系。35汪晖以此说明宋代以后的思想的蜕变,时间可测与不可测的能量释出,促使以往著毋庸议的天理由量变产生质变。余莲的灵感则来自王夫之。后者的诗学观使他得以跨出历史、思想的范畴,思考“势”作为审美效应的可能:一种厚积薄发的准备,一种随机应变的兴发。
早在《文心雕龙·定势》里,“势”已经被引入为文论的要项。唐代王昌龄、皎然等文论中,“势”被引用为诗文的“句法”问题或策略部署。36如余莲所谓,是在王夫之的论述里,“势”被细腻处理,成为读史观诗的指标。他指出因为“势”,中国审美概念才显示了与西方“仿真”说(mimesis)截然不同的概念基础,将艺术活动视为一种实现(actualization),而非模拟、再现(representation),的过程。37新加坡学者萧驰更据此继续发挥,指出王夫之诗论从“取势”到“待势”,从“养势”到“留势”,无不触及诗人运筹帷幄,静中有动的涵养。38文学艺术的表现里,从诗歌到书法,“势”的变化过程乍看似乎无可捉摸,但又有迹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