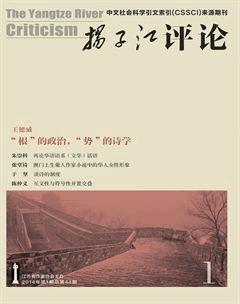澳门土生葡人作家小说中的华人女性形象
张堂锜
一、 基督城的克里奥尔人:澳门土生葡人的文化特征
澳门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中一道独特秀异的风景线,而土生葡人文学则是澳门文学风景线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设若没有土生葡人的创作,澳门文学依然可以其东西历史文化特殊交会下的丰富性与多元性自成一个丰饶的存在,但却会因此使其亮眼的文学成就减去几分光芒,同时令其极具特色的文化风貌失去几分动人的魅力。在台湾、香港等同属殖民背景的区域中,只有澳门形成了“土生”这样特殊、复杂与耐人寻味的族裔。不夸张地说,因为土生葡人的文学创作,造就了澳门文学在其他地区华文文学都无法取代与模拟的地位。
在澳门的土生葡人,俗称“土生”,葡文为Macaense或Filhos da Terra,泛指在澳门出生的欧亚混血儿。这里的“欧”主要是指16世纪中叶以来入据澳门、并于1887年与清政府签订《和好通商条约》后,展开对澳门一百多年实质殖民管治的葡萄牙;至于“亚”则涵盖了日本、印度、马六甲和华人。有关“土生”的定义、起源与族群属性是一个在人类生物学上至今仍存在一定争议、模糊的问题。例如阿尔瓦罗·德梅洛·马沙多(Alvaro de Melo Machado)在1913年出版的著作《澳门记事》中主张土生是“同日本女人、马六甲女人,乃至近期同中国女人通婚的产物”;卡洛斯·埃斯托尼奥(Carlos Augusto Estorninho)则在发表于1962年的论文《澳门及澳门土生人》中认为,由于“中国闭关锁国及严重排外的特点”,因此葡人与华人没有发生过通婚现象;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神父则在1965年出版的《澳门土生葡人——澳门》一书中主张澳门土生是“葡萄牙男人同中国女人通婚的产物”。这些分歧的见解说明了澳门土生定义的复杂及不确定性①,并长期困扰着中、葡学术界对澳门土生的研究。
大陆学者李长森于2007年对澳门土生深入且完整的研究成果,笔者看来正好解决了此一棘手的争议。根据李长森的考证,“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是不同时段有不同的混血成分,分阶段累积和混血的多元化构成了澳门土生族群”,他的分析结论是:“澳门开埠前主要是‘葡、印、马混血,16世纪中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为‘葡、日混血。‘葡、华混血虽然在澳门开埠后即已出现,但真正成为一种时尚,则是在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末。到19世纪后还有新的纯欧洲人与澳门土生人的混血,甚至出现完全的华人血统融入澳门土生族群中的‘另类土生现象。”②换言之,许多争议其实是来自于对整个四百多年澳门土生族群发展变迁未加以分阶段考察所形成的误解。
当然,对于澳门土生族群在人类生物学、历史人类学或种族志方面的探讨不是本文的重心。本文讨论的澳门土生葡人作家,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典型的土生人”,亦即在澳门出生、具有葡国血统的混血儿,其中大部分是中葡混血儿。③这个说法是对土生葡人具有代表性与普遍性的描述,在学界大抵已成共识。由澳门基金会出版的《澳门百科全书》上的介绍就持这样的观点:“土生葡人主要是指在澳门出生、具有葡萄牙血统的澳门葡籍居民,包括葡萄牙人与中国人或者其他种族人士结合所生的混血儿,以及长期或几代在澳门定居的葡萄牙人及其后代。”④对这群目前占澳门总人口不到2%的土生葡人,《澳门百科全书》也简要叙述了他们在生活、文化上的特性:“他们都懂葡文,一般能够讲流利的广州话,但只有少数能阅读中文。他们认同葡萄牙为自己的祖居国,长期接受葡国教育和文化,信奉天主教,保留许多欧洲的生活方式;同时又世代居澳,视澳门为故乡,受华人社会风俗习惯深刻影响。”⑤可以说,在西方欧洲人外貌底下,他们是有着“东方血缘”和“华夏血统”的一个特殊群体。华洋杂处、中西交会的特点在他们身上留下最深刻也最生动的印记。
但也正因为土生身上流着两种(或以上)的血液,使他们面临了双重身份认同的边缘化地位。在澳门华人眼中,土生是葡人、西洋人,然而在葡国本土,“那里的一些葡萄牙人认为土生葡人是澳门人或东方葡萄牙人,甚至认为他们是中国人。”在文化特征上,“他们既认同葡国文化,但又不大能融入欧洲葡萄牙人的社会;既生活在华人为主体的澳门社会里,但又与华人社会相疏离。”⑥在澳门被殖民的时代,他们有着殖民者的优越感,但面对来自欧洲的葡人又有失落感,这种矛盾心理,使论者认为他们具有“克里奥耳”(creole)特征。艾勒克·博埃默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一书中提出creole一词,此词在语言学上是指“一种因文化交汇而形成的混杂性的语言”,如在上海曾流行一时的“洋泾滨”(pidgin)。这种混杂的性质使艾勒克·博埃默用来指“殖民者的后裔,但他又属于殖民地本土”⑦。包括程祥徽、郭济修等澳门的研究者就以“克里奥耳人”来形容土生葡人的特殊性质:“土生葡人在文化层面上就是一种克里奥尔现象。无论从语言的视角还是心理的视角、性格的视角乃至从他们在澳门社会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看,土生葡人族群都具有克里奥尔性质。”⑧
这种又中又西的文化混合,导致土生族群自豪与自卑共存的复杂心理,在面对欧洲葡人时感到血统不纯的种族差异,在面对华人时又流露出殖民者的种族优越感,这使土生族群拥有自我属性的独特文化特征与视角。举例来说,土生葡人将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基督城”、“洋人区”,而中国人居住的地方为“中国城”、“华人区”,但这并不是简单的区域划分,而是两种不同的生活圈和文化诠释,这种划分同时表现出基督城的人要比中国城的人优越、高尚,基督城的事物也比中国城来得文明、美好。对土生而言,基督城是他们的文化归属。这种源于种族与文化的区分,在土生文学中经常被提起,本文所要讨论的小说及主题和这个在澳门因长期殖民而存在的文化现象息息相关。
二、“跨文化场域”中的土生文学表现及其特色
认识了土生族群特殊的历史背景及其文化特质后,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明澳门土生的文学表现及其特色。
由于土生葡人仅占澳门人口的2%,约二至三万人,其中只有一万人居住在澳门及香港,其余的分布在葡萄牙、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及巴西。1999年澳门主权回归之后,许多土生返回葡国定居或移居他国,居住在澳门的土生人数已逐渐减少。⑨本文所讨论的就是这群为数不多却极具特色的典型土生葡人群体,在他们之中,出现过一些以葡文写作的作家,他们作品的语言、题材及创作风格,都有鲜明的个性,在澳门这个独特的“跨文化场域”中充分显现出他们土生葡人特殊的身份特点与文化背景。诚如澳门学者汪春所分析,这批土生作家,“尽管在创作中使用的语言是葡语,但他们表现出来的思想情感、思维方式、心态特征、价值取向、审美情趣都带着他们的特殊身份,特殊生存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表现出与本地华人或大西洋彼岸的葡国人明显不同的特点,是独具一帜的作家群。”⑩
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早在19世纪初即有用古老的“澳门土语”所写成的土生歌谣出现,但要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才开始出现一批土生作家在澳门的葡文报刊如《澳门之声》、《南湾》等园地发表新诗、小说、戏剧等作品,由于用葡语写作,一般读者难以阅读,故未引起本地读者的重视。这些作品的陆续出版,使澳门土生的心理、文化、情感与思想有了真实的呈现,透过翻译,这些作品成了澳门文学中极具魅力的一环。它和土生的身份认同一样,既不是真正的葡萄牙文学,也不是澳门的华人文学,而是专属于澳门一地的土生文学,其中有澳门华人生活、自然地景、风俗民情的反映与描绘,也有土生与华人互动甚至产生爱情的刻画等等,毫无疑问,它是澳门文学历史上特殊而美丽的一章。
这些被翻译结集出版的土生文学作品约30部左右,小说数量不多,仅有飞历奇(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1929-2010)的短篇《南湾》(1978)、长篇《爱情与小脚趾》(1986)、《大辫子的诱惑》(1994);江道莲(Deolinds Salvado da Conceicao,1914-1957)的短篇《长衫》(1956)。11本文即试图从飞历奇、江道莲这两位具有“典型土生人”身份、同时又具代表性的澳门土生葡人作家的小说作品中,探讨在他(她)们眼中的“双重他者”——“华人”“女性”的形象,包括大家闺秀、担水妹、奴婢、女工、蛋家女等等,她们的身份、地位、思想与情感。
探讨华人女性形象是研究土生文学必然要触及的议题,因为之所以有土生族群的产生,和华人女性脱离不了关系。以长篇小说《移民》(1928)、《原始森林》(1930)知名的葡萄牙作家菲利喇·狄·卡斯特罗(Ferreira de Castro,1898-1974),曾经于1939年与其妻子结伴环游世界时,途中经过中国,并顺道造访澳门,最终写下了长篇游记《环游世界》,其中有关澳门部分,他特别写到了土生葡人:“现时有二十四万中国人居住在澳门,其中很多是为了逃避战乱而来的。葡国人大约有四千五百人,其中二、三百人在葡萄牙出生;其余的都是土生葡人。土生葡人是白种人和黄种人的混血儿,这是葡人被穿长裤和衬衫,前额长着浏海儿的中国女孩子的魅力吸引的结果……。”12这是全书唯一写到澳门土生的文字,他强调的是“中国女孩子的魅力”,而魅力的由来是外貌与穿着。有趣的是,飞历奇小说《大辫子的诱惑》,强调的是华人女性油亮美丽的长辫子;江道莲的《长衫》也提到了华人女性衣饰的象征“长衫”(即旗袍)13。辫子与长衫成了澳门土生小说中对华人女性外在形象的典型描写,同时也以此来喻指所有的华人女性。这些小说不约而同地将故事核心聚焦于华人女性,使我们得以一窥在澳门特殊的殖民社会底下华人女性的处境与心理。
同时,探讨华人女性形象又是理解这群被称为“澳门之子”的重要切入点──他们的婚姻观、文化观、价值观与种族观等,在这些小说中也有着真实且生动的表现。透过华人女性形象的刻画与呈现,充分反映出在澳门这个特殊历史、社会与文化交流下的殖民地区,葡人、土生葡人与华人群体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从而让我们认识土生葡人这个特殊族裔的复杂心理,以及在葡萄牙与中华传统文化双重影响下,他们对两性关系独特的观察视角。
三、褪色的长衫:江道莲小说中的华人女性形象
在土生小说中,以华人女性为主要题材,故事发生的背景都在中国与澳门,江道莲的《长衫》应该是第一部,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她也因此被称为“澳门孕育的唯一的女作家”14。
江道莲出生于澳门,父亲是葡萄牙人,母亲是澳门人,典型中葡混血的土生。她从小接受葡萄牙式的教育,澳门利宵中学毕业后,到香港学习英语,并担任家庭教师。二次大战前,她在港澳两地教葡语。二战期间,她到香港并担任“香港难民葡文学校”校长,同时为当地的葡文报纸《澳门之声》翻译BBC电台的电讯稿。由于局势动荡,她又到上海生活了一段时间,并与第一任丈夫育有二子。返回澳门后,在一家葡文报纸《澳门新闻》长期担任记者,并编辑妇女副刊。1948年与报社同事开始第二段婚姻,并育有一子江连浩。除了大量的新闻报导文字,她还写了小说、散文及文学批评、艺术批评文章。1956年,她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弗朗哥书店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著作——短篇小说集《长衫》,立刻获得好评。可惜就在才华开始展现之际,却不幸因癌症病逝于香港医院,令人不胜唏嘘。她的才华与遭遇,和中国知名的女作家萧红有相似之处。
在以男性为主的保守年代15,江道莲身为女性土生葡人,因为在工作上表现出坚强的意志,思想上具有卓然独立的正直品格,以及创作上拥有过人的才情而在1940年代的土生社会为人所知。她是澳门有史以来第一位葡文报刊的女编辑、记者,她的两段婚姻,独立抚养两个孩子的责任感,以及在战乱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与冷静,都相当受到瞩目。她的《长衫》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土生女性如何看待、描写、观察中国社会和女性。她以“西方人”的视角看待华人女性,虽然有时不自觉地流露出“俯视”的心态,但并无殖民者习见的傲慢与偏见;她以女性的立场刻画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诸多女性的灾难与不幸,显现出她充满爱与正义的宽广心胸。
《长衫》收录了反映1930至1950年代澳门生活的短篇27篇。作者以代表华人女性服饰的长衫为名写了一个短篇,同时又以此短篇为书名,说明了《长衫》是一部关于华人女性的小说,透过这些小说,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华人女性的形象。小说内容可分为两类:一是描写中葡恋情的悲欢离合,不同种族通婚家庭中的文化冲突,在令人反思中有着对华人女性遭遇的不平与同情;二是描写抗战期间中国内地的烽火灾难、民不聊生,妇女受到的痛苦,以及澳门在社会动荡中对难民的收容。全书弥漫着阴冷、哀伤与控诉、悲凉的基调,美丽青春的长衫在时代战火、种族成见的摧残下,褪色而破碎,读来令人心酸不忍。
第一类作品塑造出了一种鲜明的华人女性形象,那就是中葡爱情下的牺牲者与失落者,代表作品有《林凤的苦难》、《怀恋之隅》、《施舍》等。《林凤的苦难》中包炮仗的女工林凤,与一位葡国军人恋爱,“一直想把她搞到手的工头阿雀”因此恼羞成怒,经常“用下流的脏话羞辱她”,说她“轻信那个欧洲鬼会娶她,娶她一个目不识丁的女工,一个只有青春韶华和在长衫下隐约可见的优美身段这唯一诱人之处!”这令她深受刺伤。但林凤相信“他”,因为“他向她讲述他的故乡,谈起他的母亲,许诺有一天带她去看麦浪滚滚的田野和白雪盖顶的山脉”。虽然他从未向她提过婚事,但林凤认为外国人的习惯可能如此,“许诺带她到那遥远的西洋去这无异于成亲的计划”。不久,她怀孕了,就在她沉浸于爱情的喜悦时,“一天晚上,他来告诉她说,他要走了,预先根本不知道,他是被迫同其他士兵一起返回那遥远的故乡,但他许下诺言一定要回来把她带走。”林凤强忍着哀伤去看他随部队登船离去,“从那天起,林凤一直背着这沉重的十字架,盼望着他从西洋回来聆听他和她的孩子的第一声啼哭。这一切换来的只是转瞬即逝的幸福时光,和被人发觉有身孕后的恐惧及其后果。”16这是典型的中葡异族恋曲悲歌,一个卑微的华人女性,在时代与战争的操弄下,已然注定了其命运的苦难坎坷。
《怀恋之隅》也是一个中葡间的爱情悲剧。一个刚从欧洲学成回来的年轻葡国建筑师爱上了一位中国姑娘,她是一豪门大户的千金。情窦初开的姑娘也爱上了那建筑师,“为他那西方人身上所特有的魅力而倾倒”。虽然姑娘受过欧洲式的教育,但家族是传统专制的旧家庭,对父母尽孝是姑娘必须遵守的家规。后来,姑娘被男方的父母接受了,但姑娘的父母却坚决反对,尽管建筑师为了表示爱意甚至连未来的家园都亲手打造好,但最终她仍选择了自杀来表达对父母的反抗和对心上人的承诺,故事末尾写道:“从那时起,那所宅第的大门永远敞开,只有一个仆人照料,但总有一种有人居住的外观。据说,那年轻姑娘的幽灵每天在那里徘徊。一个年轻的中国姑娘为了爱一个西方人竟然要离开这尘世。”17凄美的爱情背后是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冲突。
更令人同情的是《施舍》中的母亲,儿子即将搭船前往葡萄牙“去完成学业,去结识父亲的家族”,但身为土生,儿子的成长有着难言的苦楚,原因是:“母亲是那位贫穷的华人妇女,愚昧无知,赤足行走,未受过任何教育。有一天父亲把他带到了家中,现在仍不明不白地呆在那里。不知道是算女仆呢,还是没有婚姻保障的妻子,但他知道她是他的母亲,他内心深爱的母亲,在社会上引以为耻的母亲……”母亲与父亲之间因为语言隔阂,几乎无话可说,“从他懂事以来,只见父亲发号施令,母亲唯命是从。在餐桌上,母亲用筷子吃米饭而他和父亲则使用刀叉。”如今他要远渡重洋,离开澳门及这个令他困惑与痛苦的家庭,在去码头前,他“伤心地告别了母亲,因为他知道,他再也见不到她了”。母亲用长衫的袖子擦拭泪水,“他要母亲不要到码头上送他”,但这位卑微的母亲还是在码头出现了:“突然他如中了雷击一般,楞在了那里。近处,一位华人妇女嚎啕大哭,企图冲开一条路,走到他的面前。”披头散发、呼天抢地的母亲让儿子感到不安,急忙转身要登船,为了不让别人起疑他和妇女的关系,他“取出了一枚硬币,把它扔到那双如同做虔诚的祷告一般高举在他面前的手中。然后,他颤抖、紧张、飞快地躲开了,急忙登上通向轮船的栈桥”。于是,我们看到这位可怜的母亲“圆睁双眼,呼天抢地地失声痛哭,不断地说:──我孕育了他的生命,可他只给了我一点施舍,一点施舍啊!”18土生家庭中华人妇女的低贱、无助、心碎的形象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第二类作品在书中的数量更多,江道莲写作的背景在二战期间的中国,战乱与饥饿塑造了在生活中挣扎的痛苦者与不幸者,这些华人女性在战火蹂躏下有时表现出坚强不屈的性格,令人感动,但更多的是在现实巨大力量的打击下如草芥般的浮沉生灭,令人感伤。这类作品有《长衫》、《那位妇女》、《疯女》、《米饭与泪水》、《新生命的降生》、《饥饿》等。以《长衫》为例,阿忠与珍女奉父母之命在三年后成亲,但珍女在去美国读了两年书回来后,思想与谈吐有了很大的改变:“姑娘临别时腼腆,踟蹰,回来时已变成了一个丰满匀称,挺秀优雅的女子。谈吐流畅,神态坚毅,信心十足”,但珍女仍和阿忠完成喜事,并“努力使自己适应丈夫的脾性”,五年后,她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原本幸福的生活在日本人的侵略战争发动后开始转变,逃难、饥饿及丈夫失去工作的懦弱无能,使珍女决定挺身而出,“她发誓为了让孩子们不再挨饿,她要同命运,战争和这地狱般苦难的生活抗争。”她让阿忠照顾孩子,自己到城中的舞厅工作,由于她年轻、舞跳得好,加上婚宴时穿过的黑色长衫,很多寻欢的阔佬围着她,陪舞收入使他们一家很快得以度过难关,但她和阿忠之间的矛盾渐深,烦躁不安的阿忠,有时会“把筷子扔到了地上,气得不愿吃那用男人和丈夫尊严的昂贵代价换来的米饭”。最后,一次激烈的争吵,阿忠用刀杀死了珍女,他被逮捕入狱,孩子则被送进孤儿院。被戴上手铐、步出小屋时,“杀人犯环视了一下四周,看见了那件挂在门后的黑色缎长衫在随风飘荡,似乎在刺激他,在讽刺他,在折磨他那颗已痛不欲生的心灵。”19这褪色、沾血的长衫,已然成为战争时代华人女性命运的一个隐喻。
《那位妇女》则写出了一个鲁迅笔下“祥林嫂”式的华人女性。原本“身穿一件合体的蓝色长衫”的妇女,在丈夫被捕入狱后不得不离乡背井,带着三个孩子流落街头,而叙事者“我”总会在他们经过时“按习惯给了她些食物”,“母亲面有羞色,伸手怯生生地感谢人们给他们的面包。”在销声匿迹一段时间后,再见到那可怜的妇女,令“我”感到吃惊,“只见她眼睛红肿,萎靡不振,披头散发,如疯子般踟蹰街头”,询问之下,才知道妇人的女儿竟活活饿死!“我”给了那妇人和她两个儿子食物,只见妇人“把要来的饭均分成两份给孩子们吃,自己从来不留任何东西。”又过了一段时间,在路上遇见“身上的长衫脏破不堪”的妇人,却已不见两个小孩,这让“我”感到害怕,唯恐听到不幸的消息,还好妇人解释说,已将他们送给“家产巨万,无子嗣的收养人”,“现在他们有床睡觉,可以坐到桌子上吃上热饭。他们没有死,只是不再是我的孩子,因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我留下来等他们的父亲。如果等不来他的话,那我就去找我的女儿。”从此,再也没有见到那妇人了,这让“我”不禁要感叹:“人们就是这样发动战争,可受害者却是妇孺。”20反战的思想建立在作者对许多不幸悲剧的目睹与同情上,这位妇女为孩子的付出与身心的煎熬不过是那战争时代众多不幸中的一个缩影罢了。《饥饿》中那位从内地逃难到澳门的妇女也是在丈夫、孩子相继离开人世后,受不了战争的折磨而“跌跌撞撞地爬了起来,继续往前走。但这次的目的地是死亡。”作者写下这个故事,因为“她那凄惨、饱经痛苦折磨的身影永远铭刻在了我们的脑海中。她是这个多苦多难的可怜中国所遭受苦难的象征”21。
江道莲身为记者,生活在97%以上是华人的澳门社会,这些抗战时期发生在澳门及中国的故事,许多是她亲见耳闻,她以记者锐利的目光捕捉生活现实,以女性的角度关注女性的遭遇,再以作家的细腻文笔刻画这些惨不忍睹的“故事”,留下了一个个生动的女性形象,说《长衫》是澳门1930至1950年代华人女性真实的历史画卷应不为过。葡萄牙学者林宝娜(Ana Paula Laborinho)为《长衫》写的评介文章中就提到:“我们注意到江道莲是通过旗袍来象征中国的女性世界。她深入到这一世界的深层,触摸中国妇女多层面的心脉律动,叙说她们的眼泪和微笑,赞扬他们虽受磨难而不屈服的坚强性格。”22也就是说,在叙述这些东方女性苦难故事的时候,江道莲不是只有怜悯与同情,她还有一份来自女性的理解,一份对华人女性勇于反抗现实、坚毅情操的肯定与尊敬。这是江道莲小说另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她身为土生妇女,带有殖民者的特殊身份与较高的地位,但她没有以主权者的姿态来看待华人女性,这和她认同自己身为“他者”的身份有关23。身为土生,在葡国人眼中是非正统、非主导的“他者”;身为妇女,在土生社会里仍然是附属、被动的“他者”。然而,相对殖民的土生,澳门的华人是“他者”,而华人女性在华人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又是“他者”。可以说,这是一个“他者”在叙述“双重他者”的故事结构,江道莲同情这群被父权社会不公平支配下的中国女性,其实寄寓了自身在同样困境下的生存感受。作为一位“注视者”,在塑造华人女性形象的同时,也投射了自身的欲望与恐惧,困惑与梦想。正如澳门学者谭美玲的分析指出:“《旗袍》并不是一本主张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的小说,而是一种女性书写,写出她们在男权主导的传统下,长期的、普遍的生活模式”,“这实是‘人类的遭遇,也是作者的遭遇,既对于自己的认同,也对他人作设身处地的认同。”所以江道莲“选择写这些女性故事、中国人的故事,不是要看扁她们/他们,而是要把一些存在的事实表现出来”。24
可以说,《长衫》是一位澳门土生妇女对华人女性命运的感同身受,也是对战争残害生命与人性的有力控诉。尽管美丽的长衫已经褪色,但《长衫》中的种族议题、生命思索与女性形象将会被后人不断阅读与认识。
四、 油亮的辫子:飞历奇小说中的华人女性形象
和江道莲一样同为澳门土生小说家的飞历奇,是澳门读者最熟悉的葡语作家。他也是出生于典型的土生葡人家族,但不同于江道莲在生活上的独立自持,他是有葡国伯爵头衔的贵族后裔。在澳门读完利宵中学后,优渥的家境使他于1946年前往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就读法律系,1954年毕业后返回澳门,开始长达四十多年的律师生涯。执业之余,他坚持写作,陆续出版了《南湾》、《爱情与小脚趾》、《大辫子的诱惑》等小说集,其中《爱情与小脚趾》曾于1992年拍制成葡萄牙电影《澳门爱情故事》,而《大辫子的诱惑》则于1995年由澳门的电影公司拍制成电影,在葡萄牙、澳门上映,这也是他为何在澳门社会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原因。热爱写作的他,即使是七十高龄,依然着手写作小说《望厦》,但2010年过世,不知书稿是否完成?澳门文化局计划为他出版全集,作为土生葡人创作的代表,但碍于家属意见,目前仍在洽谈中。可以说,飞历奇是在澳门社会、文坛最具代表性、也最受肯定的土生作家。
当然,他和江道莲也有一些不同之处。首先,他的代表作是长篇,而江道莲是短篇。其次,江道莲的小说集中描写了二战期间的故事,虽然有少部分涉及中葡恋情与婚姻,但还是以华人题材为主;而飞历奇则是以土生题材为主,他所描绘的土生青年与华人女性的爱情,虽然背景是20世纪初期,但从某个意义上说,他写出的是四百年来一直存在的土生男性与华人女性间爱情与婚姻的现象,他所引起的思考显然要比江道莲的作品更深刻、丰富。再次,飞历奇是土生男性——这个性别的差异,不论是对他在土生社会的地位还是创作题材的思考与选择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土生社会存在着女弱男强的性别阶级意识,而且土生族群一直有女多男少的失衡现象,所以澳门土生男性比起女性享有更多更高的地位与权势25。飞历奇除了性别的优势,他还是贵族后裔,对土生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知之甚详,所以他的两部代表长篇小说都以土生上流社会的男性为主要人物——《爱情与小脚趾》的西科·弗隆达利亚是一个土生显赫家族的纨绔子弟,《大辫子的诱惑》的阿多森杜也是出身富家的土生青年。以上这些差异,使飞历奇的小说比起江道莲有着更鲜明的澳门土生文学特色。
由于《爱情与小脚趾》的男女主角都是土生葡人,尽管故事中安排了被逐出基督城的土生富有青年西科,沦落到最低层的华人区,与一个中国的卖菜寡妇阿太同居,过着潦倒不堪的生活,但粗鲁的阿太在故事里扮演的是对比土生少女维克多利娜善良有情的女性形象,并非作者笔下的主要人物,加上故事主要围绕着两位土生青年的恋情,所以本文主要的讨论对象将置于《大辫子的诱惑》。
《大辫子的诱惑》里的男主角阿多森杜,是个风度翩翩、玩世不恭的土生青年,家境富裕,被称为风流场上的征服者。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一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吸引、“诱惑”,从此坠入情网。拥有这条乌黑辫子的是中国城最贫穷的雀仔园的“担水妹”阿玲,她虽然目不识丁,但能干又漂亮。阿多起初是被她迷人的外貌吸引,但后来逐渐了解她内在的美好品行而真心爱上她;阿玲起初认为阿多态度轻佻,加上两种不同文化出身,几次拒绝,后来也是感受到他真挚的爱而不顾众人反对和他相恋并结婚。在基督城/中国城截然迥异的文化风俗与族群特性压力下,阿多被指责玷污家族声誉而被逐出家门,连昔日好友也不肯伸出援手,至于阿玲也为了这桩爱情成了雀仔园的叛逆者,房子被查封,同样被逐出了家园。两人只能搬到另一个华人区居住,过着孤立且艰苦的生活。经过几番磨练,阿多找到了船运公司的工作,改掉昔日花花公子的习气,终于和阿玲克服文化上的阻碍,过着美满温暖的生活。最终,原本反对这桩婚姻的阿多的父亲有所悔悟,找到了阿多和他的媳妇、孙子,在阿玲“公公”的一声叫唤下,原有的阶级藩篱被亲情拆除了,阿多重新被父母和周围的土生葡人接纳,而阿玲也和雀仔园的人们和好如初。
这个大团圆的结局,象征了两个族群的大和解,也说明了基督城与中国城的矛盾对立有着松动与融合的可能。小说为我们保留了1930年代澳门华人与葡人两个社会因为文化差异所形成的偏见、传统,也预示了未来这样的隔绝、排斥与冲突将渐渐失去意义。尽管如此,飞历奇的土生男性立场,还是使这个爱情故事在种族优越的基础上推展。阿多被逐出基督城,在华人区历尽艰辛,但他一直设法要和土生交往,最后也是在被土生朋友认同、妻子与儿女被父亲“认”了之后,他在心理上才真正重返基督城。相对于基督城的高贵、富裕、整洁有文化,阿玲所居住的雀仔园,则是藏污纳垢的贫民区,连住在里面的中国人也多蛮横粗野,小说里这样写道:“雀仔园自从作为住宅区开始存在的时候起,它的名声就不怎么好。那里肮脏不堪、疾病蔓延,也是流氓、恶棍这些人类渣滓的避风港。即使在它变成城区以后,它的坏名声也没有能随之消失。……居住在雀仔园这块小天地里的只有几千人,且都是穷人。……女人则大部分当佣人、织布女、扫地工、梳头妇、洗衣女、担水妹等。”26在他笔下,华人女性从事的多是“低贱的职业”,唯一能让这些女性体现出她们高雅的只有“那条垂挂在后背上的长长的黑辫子。这是中国下层人家的姑娘们的统一发束。”就像担水妹阿玲,即使“腋下和后背都浸透了汗水,裤腿边上和光脚板上沾满了泥土”,仍充满自信地认为:“唯一干净和好看的东西,就是那条黑亮亮的辫子,那是她的不容置疑的骄傲。”
小说里的阿多,先是被阿玲的辫子吸引,后是被她的身子诱惑,辫子与身子,飞历奇对华人女性不能说没有“物化”之嫌。而且,在脏乱、落后、贫穷的中国城里,“经常在雀仔园井边打水的担水妹”中,飞历奇写道:“阿玲最显特出”,“具有公主的地位”,将阿玲的形象刻画得明显高于其他担水妹,其实是为了与优越的阿多相匹配,华人公主与土生公子,飞历奇基于土生葡人的种族优越感还是多少流露出来。这也许是他的阶级局限,也可能是他的写作策略。然而,不管如何,他依然透过这个中葡爱情故事塑造了“阿玲”这个独特的华人女性形象,而且这个女性形象改变了阿多及其家族的命运,贯穿整个故事,散发出动人的魅力──从这个角度看,他对华人社会的文化理解、情感认同又是不能否定的。
小说中的阿玲,除了外在的“体态健壮”,“长得最苗条、秀气”,以及拥有“那条又粗又黑的长辫子”,她还具备了华人传统女性吃苦耐劳的坚毅精神,面对挑战挫折不服输的韧性,以及以和为贵、以德报怨的胸襟气度。毫无疑问,飞历奇将他对华人女性的认知与想象都投射在阿玲身上,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东方女性特质的典型形象。
小说中写到两人被迫沦落到没有人认识的华人区,阿多纨绔子弟的习惯使他找不到适合工作,自怨自艾,想不出办法,这时阿玲挺身而出,决定要去同情她的女友阿瑞的店里干活,她对阿多说:“我从来都是光着脚走路,也从来没有为此感到羞耻。我不能没有必要地穿破我那双唯一的木拖板。对于一个从来都是一无所有的人来说,这没有什么不光彩的。”面对不解(应该说无能)的阿多,阿玲冷冷地说:“我失去了一切。而且,作为一个女人,我比你失去的还要多。”于是,她毅然离开了两人暂时栖身的家。她心里想着:“如果阿多森杜还像从前那样喜欢她,就一定会来找她。”阿玲的离开,警醒了阿多的沮丧与绝望,他有了新的体认:“上帝决定的事情只有上帝知道。我们选择的道路,我们就应该走下去。”为了生活,阿玲差一点把辫子剪了卖掉,但在最后一刻,阿玲决定保留这珍贵的辫子,尽管它可以卖得极好价钱。终于,阿多找到工作,两人重归于好,有了孩子,也有了自己的房子。可以说,是阿玲这个担水妹,解救了阿多这位富家子弟。小说中还有个细节很有意思,当阿多去找阿玲约会时,雀仔园四个高大粗壮的恶棍,决定要修理阿多这个外来的“鬼佬”,不料阿玲跳出来保护阿多:“阿玲举着扁担跳到街心,横眉怒目,一副以死相拼的样子。她毫不示弱地宣战了。只见她熟练地挥动扁担,使劲朝站在面前的一个家伙的双腿扫去,像稻草人似地把他撂倒在地。……愤怒的阿玲转过身,犹如一位身经百战的巾帼英雄,用奇特的技术挥动着她的扁担。两个被打倒在地的人一边呻吟着,一边躲着姑娘的扁担。”她像个胜利者,大声地说:“谁也别想碰一下我的男人!”以一击四,这不是“英雄救美”的传统模式,而是“美救英雄”的新女性了。阿玲过人的勇气、坚定,颠覆了弱不禁风的东方女性形象,赋予了华人女性新的生命力。
阿玲不仅在关键时刻扮演护卫男人的角色,平时在家相夫教子也显现出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智慧:“他开始为改变自己下降了的生活而奋斗。聪明的阿玲接受了男人的一些习惯,因为他总是自己的丈夫。但她也没有放弃让男人接受她的一些中国习惯。他们互相谦让,互相适应,逐渐产生了他们独特的和谐的生活方式。”两种差异的文化在女性的温柔进退中被融合得自然而有尊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但这位出身贫寒的担水妹做到了。在生活的历练中,阿玲有着明显的蜕变:“当然她也知道,如果让她现在像从前那样在大街上光脚走路,她会感到极不自在。她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从前的女友们也已经不像原来那样对待她了。过去的担水妹已经不存在了。她只属于雀仔园的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一位为自己的爱情而抡起扁担击败了四个蛮汉的姑娘。”这不应该被视为强势的土生文化的洗礼,而是两种文化的彼此交流影响,也是阿玲女性本质、华人传统特性的成长与升华。研究飞历奇小说的澳门学者就指出:“我认为,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打破了过去对华人女子的偏见及对跨族繁殖婚姻的偏见,对年轻一代的土生葡人通过自主的婚姻来选择自己的身份方面做了肯定。”27
光脚的担水妹阿玲,可以说是土生葡人小说中对华人女性最血肉饱满、正面刻画的人物形象。虽然在这场动人的爱情故事中,阿玲比较被动,而且阿玲必须和阿多到天主教堂结婚,依附葡萄牙的文化传统与婚姻规范,还有华人居住的雀仔园被描述得脏乱落后,以和基督城的高贵形成强烈对比,但细看全书,飞历奇始终是以饱含情感、欣赏的心态来塑造阿玲的形象,宛如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也像一个纯洁的天使。尤其是在小说结尾,阿多的父亲放下土生富有人家的身段,愿意接纳被逐出家门的阿多及阿玲时,阿玲开门迎接这位老人,对他激动但温柔地说道:“爹,进来呀。这是你的家。”一个典型温婉贤慧的华人传统女性形象鲜明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她背后那条又黑又粗的长辫子,仿佛也正散发着油亮温暖的人性辉光。
五、 南湾畔逐渐远去的低吟
飞历奇除了两部长篇,还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南湾》,收有6篇小说,其中涉及华人女性的有3篇:《蛋家女阿珍》、《樱花浴》、《华商情仇》。江道莲的短篇多为二千余字,最长的《长衫》不过七千字,但飞历奇的短篇至少一万字,《华商情仇》更长达五万多字,可见飞历奇比较喜欢和擅长处理复杂的情节。这三篇中可以和《大辫子的诱惑》相提并论的是《蛋家女阿珍》,这不仅是因为这篇作品写于他在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就读期间,并在1950年获颁菲阿幼德·阿尔梅达文学奖,更重要的是,小说描写在水上生活的蛋家女阿珍和葡国水手曼努埃尔相遇相恋但最终不得不黯然分手的凄婉故事,其中触及了中葡之恋,并塑造了一个不同于阿玲的华人女性形象。
蛋家女阿珍出身贫苦,没有文化,相貌也不出众,但她温柔善良,逆来顺受,具有传统东方女性的特质。她爱上了一个经常搭她船的葡国水手,两人相恋并生了一个女儿“美丽”。那是对日抗战期间,尽管战火并未直接波及澳门,但水手是因为战争才来到这个东方小城。水手思念远方的故土,阿珍的出现抚平了他冰冷的心。阿珍很清楚地知道,“他一定还有其他相好的女人。男人们都是如此,更不用说一个浪迹天涯的水手了。”但是,“她没有一点儿嫉妒心,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男人可以任意娶妻纳妾。她认为这很自然,毫不奇怪。”28虽然阿珍谦卑的神情“像个顺从的女婢”,但在水手眼中,他看到“她身上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温柔,令人心驰神往。”“她那渴求爱情,心甘情愿委身于他的举动深深打动了他。这种无言的顺从使他得到满足。”然而,几星期以后,水手因为被盗匪枪击受伤,在医院住了几个月,不知消息的阿珍虽然伤心气恼,但也不敢在外人面前流露。她甚至以为,水手肯定又迷上了其他女人。等到出院后,两人重逢,水手发现船上多了一个小生命,女儿的降临给他们带来了短暂的幸福。直到日本投降,“澳门全城燃放鞭炮,欢庆胜利”,水手却奉命搭船返回葡萄牙。为了女儿的前途,阿珍决定忍受巨大的悲痛让水手把女儿从身边带走。离别前夕,“蛋家女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她失声痛哭,哽咽声断断续续,撕心裂肺,令人断肠。曼努埃尔想劝他别哭了,可他的声音也哽咽了。他感到将要失去的是无价之宝,是任何东西所不能代替的。”从一开始,水手将阿珍视为“一个在他满足肉欲后可以扬长而去的玩偶”,到认为她是“无价之宝”,水手的转变将这段异国恋情超脱了原始的肉欲而上升到爱情的层次,主要原因还在于阿珍自始至终愿意牺牲、不争不吵、全心付出的真情打动了他,尤其是结尾,当启航的汽笛声响起,“曼努埃尔张开双臂紧紧地将柔情似水的蛋家女拥在怀里。阿珍一往情深地注视了他片刻,然后顺从地把女儿交给了他,低声作最后的道别:‘你要保重!多保重啊!……”将这位东方女子顺从、无奈的形象做了最大张力的描绘,充满哀伤与遗憾,但另一方面,作者又对这位生活在社会底层、具有美好品行的华人女性寄予了强烈的同情与赞美。
在飞历奇这样的“西方人”眼中,阿珍的表现与心理,无疑符合了他对一个典型东方女子的想象,这种想象带有男性对女性、殖民者对被殖民者、强权对弱势的性别/阶级/族群意识。担水妹阿玲与蛋家女阿珍的命运都被主导的葡国男性支配,飞历奇身为土生葡人男性的立场,在这些带有东方情调的故事中昭然若揭。毕竟,飞历奇虽然在澳门出生,但一直接受葡萄牙文化教育,他的思维很难跳脱出欧洲——葡萄牙殖民主义的认知体系。然而,他笔下的华人女性,在某个意义上,却都比男性要来得坚强、勇敢、识大体,从这一点看,他又没有如一般殖民者所不自觉流露出强势文化凝视下的刻板心态。他成功塑造了阿玲、阿珍这样具有美好精神质量与顽强生命意志的华人女性,在审美功能和人性价值上带给人们一种反思的力量。
江道莲和飞历奇,将他们眼中的“他者”——华人女性的地位、生活、命运作了生动的呈现,同时在注视“他者”形象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身为土生,处在葡人与华人的文化夹缝中,在殖民时期,他们对身份的建构固然有所困惑与思考29,但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太大的困扰与失落,直到1999年的主权回归,葡澳政府结束,大批葡国人及葡国土生主动或被动地纷纷返回欧洲,留下来的则面临了工作、生活上的改变与不安。他们被迫出走的落寞身影,不禁让人联想到华人女性当年在战火中牺牲、逃难的惊恐眼神。“自我”与“他者”,澳门土生的身份转变就和中葡四百年来的历史纠缠一样复杂。
澳门土生文学是中葡文化四百多年来在澳门相遇、交会的产物,是华人社会所孕育出来的一份珍贵文学遗产,具备了跨种族、跨国界、跨文化的特性,因而显示了更为多元丰富的阐释空间。华人女性形象的讨论不过是澳门土生文学/文化研究中的一环而已。飞历奇《南湾》所描写的南湾,原是一弯美丽的海滩,后来成为澳门行政与社会生活的中心,特别是葡人、土生聚居之处,也就是小说中所提到的基督城。如今,基督城不再,南湾畔的克里奥尔人日渐离散,他们曾有的悲欢话语已经化为风中远去的低吟,甚至成为人们记忆中的绝响。对这个逐渐消失的族群,特别是他们的文学已然成为澳门文学的必要组成,而澳门文学又是世界华文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版图,学术界的冷漠以对是自身文学完备发展的一大损失,在学术层面上对土生文学予以更多的关注实在是刻不容缓。
【注释】
①以上几人对澳门土生的看法可参阅安娜.玛里亚.阿马罗(Dra.Ana Maria Amaro)著、金国平译:《大地之子——澳门土生葡人研究》(澳门文化司署,1993),页10;李长森:《明清时期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发展与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14-15。
②此一归纳见于汤开建为李长森《明清时期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发展与变迁》一书所写的序言,见该书页3。
③按照澳门立法议员、土生律师欧安利的说法,除了典型的土生人外,还有一些在习惯上也会被放进土生之内的有:澳门出生的纯葡裔居民;在澳门以外出生但迁澳居住并接受当地文化的葡国人;从小受葡国文化教育、讲葡语、融入葡人社会的华人。参见汪春:《澳门的土生文学》,收入刘登翰主编:《澳门文学概观》(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页334。
④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修订版(澳门基金会,2005),页25。
⑤同上注。
⑥参见郭济修:《飞历奇小说研究及其他》(澳门文化广场,2002),页5。
⑦[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页10。
⑧见程祥徽:《序》,收入郭济修《飞历奇小说研究及其他》,页vii。程祥徽的说法,主要参考郭济修在63页对飞历奇小说的分析时提到土生文化具有“克里奥尔”性质,而飞历奇在某种程度上是“克里奥尔人”的见解,但程祥徽在文字上稍有发挥。
⑨根据澳门统计及普查局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30日,澳门的居住人口估计约为591900人,其中华人占97%,葡萄牙人(包括土生葡人)和其他外国人占3%。所谓其他外国人包括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另外,根据澳门土生律师飞文基的说法,现在整个澳门特区约有一万人左右的土生葡人,见新华社澳门记者张家伟、郭丽琨:《澳门土生葡人回归十年生活:文化交融,多元共存》,2009年12月9日。另,根据曾任澳门文化司司长,现为澳门建筑师、作家的土生葡人马若龙的说法,回归后的土生人数约剩七千人左右,见《回归后的澳门政局及未来发展路向》(未署作者),台北:《中国评论》第36期,2000年1月,页28。
⑩汪春:《澳门的土生文学》,收入刘登翰主编:《澳门文学概观》,页337。
11在目前翻译出版的土生文学作品中,爱蒂斯·乔治·德·玛尔丁妮于1993年在美国纽约Wantage出版社出版的《废墟中的风——回忆澳门的童年》,是一部具文学手法与艺术感染力的回忆录,对在澳门的土生家庭、生活、历史,以及澳门的土地、人民都有充满深情的叙述与回忆,从内容来看是一部抒情与叙事兼备的散文。但在汪春所撰的《澳门的土生文学》中却将它归入“澳门土生文学的小说”来将以介绍,并不妥当,因此本文未将这部作品纳入讨论。汪春一文参见饶芃子、莫嘉丽等著《边缘的解读——澳门文学论稿》,页214-215。此外,玛里亚·翁迪娜·布拉加的短篇小说集《神州在望》,由金国平译,于1991年由澳门文化司署出版,这部小说的题材多取自澳门,描写了在澳门的土生和华人的许多故事,特别是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苦难,是了解当时中国处境很好的窗口,但因为作者是葡国人,于1961年起来澳门任教了几年,并非土生,所以本文也无法纳入讨论。
12菲利喇·狄·卡斯特罗的《环游世界》,写他游历过的希腊、土耳其、伊拉克、印度、缅甸、马六甲、中国、日本、檀香山、美国等地,其中有关中国的一章(包括澳门、香港及广州)后来独立成书,以《澳门与中国》为名并用葡文及中文两种语言出版,于1998年由澳门的海岛市市政厅印行。本文所引出自该书第32页。
13江道莲小说目前有二种中译本,一是由姚京明译、1996年由澳门文化司署与花山文艺出版社印行的《旗袍》,列入“葡语作家丛书”;二是由金国平译、1999年由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印行的《长衫》,列入“澳门文学丛书”。本文采金国平的译本,因为这部小说的原书名是Cheong-Sam,其音为长衫,而且港澳粤语中多将旗袍称为长衫,所以译为长衫较为贴切。
14见江道莲的儿子江连浩在《长衫》的导言中所言。江连浩是澳门著名的设计师。这里指的应该是第一位土生女作家。
15在土生葡人的社会里,女性是受到轻视的。根据安娜.玛里亚.阿马罗的研究,土生在澳门登记世系,男女有别,男人要说明姓名、世系,女性则不管其血统,只记载婚姻状况,用已婚、未婚或“无主”来登记,全无世系可言;此外,澳门的土生葡人妇女在16至18世纪时,如果找不到丈夫或做人家的姨太太,就可能会被葡国人送到外地或修道院去当女奴或关起来。这种对土生葡人妇女的行为,一直正式及非正式地维持到20世纪的60年代。由此可见,在土生社会里,男尊女卑,男主女从,女性一直是被动的弱者。以上参阅安娜·玛里亚·阿马罗:《不为人知的澳门土生妇女》,《文化杂志》中文版第24期,1995年秋季,澳门文化司署出版,页101-103。
16以上引文出自江道莲:《林凤的苦难》,《长衫》(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页12-15。
17以上引文出自江道莲:《怀恋之隅》,《长衫》,页38、39。
18以上引文出自江道莲:《施舍》,《长衫》,页16-19。
19以上引文出自江道莲:《长衫》,《长衫》,页4-11。
20以上引文出自江道莲:《那位妇女》,《长衫》,页4-11。
21以上引文出自江道莲:《饥饿》,《长衫》,页91、92。
22林宝娜:《评介:作家及作品》,《旗袍》(姚京明译,澳门文化司署、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页4。
23“他者”一词为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在《第二性》中所提出,意指在父权社会中,男人以其优越等级及结盟而得到种种好处,居于主导地位,而女人则是被动、被剥夺的一群,相对于主体男性来说扮演着“他者”的角色,这也使得男女两性的主从关系,如同主仆。参见《第二性》(邱瑞銮译,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00)序言,页1-7。
24谭美玲:《〈旗袍〉中的两性关系》,收入廖子馨编:《千禧澳门文学研讨集》(澳门日报出版社,2002),页208、209。
25安娜·玛里亚·阿马罗:“在澳门女人从来多过男人”,见《大地之子——澳门土生葡人研究》,页31。
26飞历奇:《大辫子的诱惑》(澳门文化司署、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页3。以下有关这部小说的讨论均以这个版本为准,引文部分则直接将页码标明于后,不再另行加注。
27郭济修:《飞历奇小说研究及其他》,页49。
28飞历奇:《南湾》(李长森、崔维孝译,澳门土生教育协进会,2003),页16。以下引文直接将页码标明于后,不再另行加注。
29土生文学中有关身份思考的作品以诗歌表现较多,例如若瑟·多斯·圣托斯·费雷拉的《未来》:“澳门的未来……将会怎样?/中国人的未来?/葡国人的未来?/那些生长在澳门/葡萄牙的儿子们的未来?”;李安乐的《澳门之子》:“永远深色的头发,/中国人的眼睛,亚利安人的鼻梁,/东方的脊背,葡国人的胸膛,……心是中国心,魂是葡国魂。”还有《知道我是谁》:“我的父亲来自葡国后山省,/我的母亲是中国道家的后人,/我这儿呢,嗨,欧亚混血,/百分之百的澳门人!”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土生对自己的身份有着不安的困惑,也有自我解释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