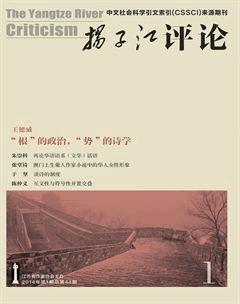当代文学中的“土改”主题写作论纲
本文站在“文学史”和“当下”的高度,论述与评判当代文学中的“土改”主题写作,依次讨论如下四个问题:追述“土改”的当代写作史、阐明“土改”写作的界限与范畴、文学与历史的离合、跨界的拓展。这是历来“土改”主题写作研究中,较有代表性与争议性,或深具开拓意义的问题。在探研、反思创作与研究现状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对“土改”主题写作的研究前景与潜在研究路向,做出建设性的预判。
新世纪以来,知识界对于“土改”运动的关注、写作与研究,持续取得进展。在“正统”和“非正统”两种传统土改小说写作模式之外,出现了“第三种模式”,也即老年“记忆写作”,这一种立足于个人性与民间性的老年记忆写作,对以“虚构”为主的土改小说写作模式,起着“补阙”与“纠正”之作用,丰富着包括“土改”在内的当代历史主题写作。对于土改这种“当代历史”主题写作,我们在进行解读时,往往不局限于文学的藩篱,借助于当代历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知识,以作深入的对照研究。
一、“土改”的当代写作史
“讲史”向来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主流,现当代文学也不例外,从鲁迅的《故事新编》到施蛰存的《石秀》,从姚雪垠的《李自成》到莫言的《檀香刑》,众多现当代作家以文字的形式进行“穿越”,来表达自己对于历史与当下的见解。
土改作为中国农村当代变革的起点,是书写和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无法绕过的全方位运动。作为一种“当代历史”题材,土改的写作意义主要有三:首先,土改是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历史运动,相类的有“朝鲜战争”、“大跃进”、“文革”、“上山下乡”等运动。其次,存在明显的争议或禁忌,如“土改”运动的过火与扩大化、暴力与酷刑,这些争议程度不同地体现在土改主题写作里。第三,“创伤性”:从个体创伤到民族集体创伤,具体表现为对待运动对象的“过度惩罚”、参与者的精神创伤和民族道德文化的创伤。
“土改”也因此成为吸引众多写作者的“历史”题材:其写作几乎与现实进行的土改运动同步,早在国共内战时就有作品产生,并且造成空前的社会现实效应。赵树理、丁玲、孙犁和周立波等解放区文坛泰斗,纷纷参加土改并用文字写作,讴歌运动的伟大和必要,其土改主题写作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殊荣并顺理成章成为1949年后“十七年”文学的最初典范。1950年代新解放区的土改高潮结束后,移居香港的张爱玲拿出针对大陆红色政权的《赤地之恋》和《秧歌》,以土改为小说叙事的开端与核心进行“反共”叙事。反观同时期国内缺少有影响的作品,陈思和认为首先源于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客观形势:“中国社会发展变化太快,1950年代初,土改以后的农民还没有充分享受获得土地的欢乐,农村就开始了合作化运动,一场新的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政治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以至于继续躺在土改胜利果实上的思想行为转而成为落后,可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绊脚石。”在这个要求农民重新交出土地归集体所有的时刻,“文艺创作如再渲染土改后农民获得土地的欢乐,显然是不合时宜的。”①不管怎样,土改主题写作由此沉寂多年确是不争事实。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尤其进入1990年代以后,“新历史小说”浪潮中才涌现出不少写“土改”的作品:张炜《古船》(1986)溯及洼狸镇“当代”的历史恩怨,就是从土改开始的。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1993)讲二十世纪中国马村村史,前半叶是孙、李两大户争雄,而从土改开始才彻底变成了赵刺猬、赖和尚的无产阶级联合统治。莫言《生死疲劳》(2006)将土改置于“六道轮回”的第一道,显然不是无意的。
从“写作模式”上看,“土改”写作大致上分为两种对立与分裂的叙事模式,一种是官方主流的模式,或称“正统土改小说”,强调作为阶级斗争的土改运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另一种反其道而行的“非正统土改小说”②出现得较晚,更多站在受害者一方,来颠覆正统写作模式。从“文学史”的角度上讲:1940年代的主流/正统土改写作,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模式的最初典范,对1950年代农村阶级斗争题材小说创作影响巨大。1980年代后的土改主题写作,基本属于“新历史小说”的范畴。而主要出现在21世纪初的第三种土改写作,这里称之为“记忆写作”模式。
其代表者,如沈博爱《蹉跎坡旧事》、姜淑梅《乱时候,穷时候》③等。写作者多为1920-1930年代生人,亲身经历过土改运动。对于亲历者来说,土改“这种完全以非常性的革命理念和斗争方式导致的农村千古奇变,对于身处其境、投身其中的农村大众来说,留下的是永远也挥之不去的记忆。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是怎么记忆那段历史的?他们又是如何评说的?”④尽管绝大多数亲历者不曾进行文学创作,但“记忆”终究难以磨灭。于是,他们在老之将至之时,以“非虚构”的形式,将土改“少年记忆”用“文字”叙述出来并公开出版,形成社会影响,完成了记忆的文学化与社会化。这些建构在“记忆”基础之上的文字,表现出了不同于“虚构”小说的特点:怀旧、创伤、个人体验性与民间性等。可以说,他们给土改主题写作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二、 历史写作的界限与范畴
以往学界在梳理和研究“土改”题材写作时,一般多聚焦于直接写“土改”运动的“小说”文体,对于其他文体写作,以及写土改前、后的小说甚少触及。我以为,应当把表述土改的叙事散文、自传、回忆录、传记等文类,涵盖到评论和研究的范畴中来。尤其是近年有一定社会影响和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自传性记忆写作,如沈博爱的《蹉跎坡旧事》、姜淑梅的《乱时候,穷时候》等⑤。此外,张爱玲的《秧歌》、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刘庆邦的《遍地月光》等小说,或以追述的形式,或间接写土改,或全面写土改运动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剧变,也即土改的后果和影响。甚至还可以囊括沈从文等土改亲历者和写作者的书信、日记里的土改见闻和评价等。
那么,接下来就必然涉及到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从“文体”的角度看“当代历史”题材的“写作”,“历史写作”能否涵盖非专业作家的自传、回忆录、传记、日记、档案材料等所谓“非虚构”的“文体”?如果可以的话,那么第二个问题是:该如何衡量?以什么标准?以文学审美还是其他标准?
在第一个问题里,土改写作中的“记忆写作”一类,在以往研究中并不被重视。其实这些涉及到普通个人在重要历史事件中个体体验的记忆文字,其独特写法与意义不应低估,终将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点。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具有新的文学审美意蕴的写作类型。其对人生早年经历的时间顺序的推重,有别于零散的叙事散文集(如鲁迅《朝花夕拾》)。其对“讲什么”和“怎么讲”关系的平衡与兼顾,使其有别于强调内容而不注重形式的传统自传与回忆录。在语言叙述上,这种记忆写作在文笔的优美和叙事的流畅上,广被称道,具有高度的文学审美价值和意义。其对“历史”的认知与评判,源于“亲历”及岁月的沉淀,直观而冷峻——与非亲历性、虚构的“新历史小说”写作大异其趣。
记忆写作与小说的关系,又可称“非虚构”与“虚构”写作的分野。以梁鸿《中国在梁庄》为代表的“非虚构”写作,一定程度上冲击并更新了我们在“文体”上的观念。而如果将其纳入文学研究的话,当代文学的价值就不仅仅体现在文学审美的领域,也能够体现在社会历史研究的领域。
从近年国际传记理论和潮流来看,相当数量的回忆录、自传、传记乃至档案都可纳入“文学”范畴。面对着充满创伤性的二十世纪中国,不管是亲历者还是非亲历者,在现在的传记或是回忆录的理论当中,已经把这类基于记忆事实的题材写作,都视为可虚构、可进行文学想象和文学创作的。尽管它有一个界线,但这个界线本身也是含糊不定或者充满争议的。
而从实际操作来说,有人认为在文学研究中,可以对此做“技术”上的处理:首先是筛选与认证。如对于文学对象的选择上,要经过一种基于文学或美学普遍标准的评判分析,只有在标准之上的文字我们才认可与接纳。其次,对于标准之下的文学性、艺术性不高的文字,因为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那么可以采用“另设专章”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像日记、档案等。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相关写作较为零散。
当然并非所有的上述文体写作均可纳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衡量“标准”的问题。那么,语言/文笔、人物形象塑造、情感表达、“真实性”、叙事手法及效果等等,均可作为衡量的标准。在尚无定论的情况下,“标准”是一个可以暂时搁置的问题,它可以在研究过程中,在学术讨论和争议中逐渐生成并被广泛接纳。
三、 文学与历史的离合
在历史主题写作上,文学应否根基于历史?我以为,一方面,历史是文学的基础,就“土改”而言,倘若不是运动的重大政治、历史意义及其引起的观念巨变与人事震荡,就不会吸引我们的写作者和研究者持续关切与写作。另一方面,由于文学想象不同于历史想象,文学艺术有着自己的表现形式、规律和法则,因此土改文学和土改历史(研究)的差别显而易见。陈思和如是描绘土改写作中文学与历史的差别:“‘文革后出现的土改书写,文学与历史的意义已经截然分开。历史学者推断土改运动的是非功过,而文学创作则直逼人性,这就是艺术真实比历史真实更加长久的道理。”⑥以“文学”的形式来再现“历史”的过程,必然产生“真实性”的争议。
历史地看,“土改”是一项持续长时间,开展有先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广义上的土地改革,从1920年代苏区的土地革命算起,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初的西藏农奴制改革。其中,1940年代中后期的“老根据地”和1950年代初期“新解放区”的土改最为集中和典型,也是土改写作者及研究者重点关注和描述的阶段。
主要缘于政治形势和地方差异所导致的土改政策的波动性,造成了土改运动在时间和空间上表现出的复杂性,也造成了我们在所谓“真实”问题评判上的困惑和争议。就已有的“土改”写作而言,存在官方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正统土改小说、海外反共背景下的张爱玲小说和1980年代以来新历史小说里的非正统土改,以及时人的私人记录、近年的记忆写作等不同写作模式。围绕着这些面目迥异的文学面目,有关“真实”之争无从避免、难有定论。
关于“真实性”的论争,我们可先从“亲历者”身份的周立波、丁玲等“党作家”和张爱玲等写作者出发。比如对《赤地之恋》和《秧歌》的评判,学界长期以来纠结于张爱玲是否参加过土改的问题上,1984年以柯灵的《遥寄张爱玲》⑦一文作为代表。这个问题颇类似于鲁迅是否真的看过中国间谍被杀的幻灯片的争议。它促使许多人执着于寻找所谓的“证据”。在许多地方,土改运动是一场残酷的乃至血腥的道德伦理、人际关系的革命与斗争,伴随着革命与群众的暴力,因此对于土改暴力的呈现方式,也长期成为“真实性”争议的核心。《赤地之恋》及《古船》在暴力氛围的营造以及暴力酷刑与杀戮的刻画上,让人怵目惊心,其程度完爆《暴风骤雨》。陈思和认为张炜的深刻性表现为对这国家暴力与民众暴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描绘,而且这种场景描绘“完全符合后来历史学家关于土改的研究成果。”⑧近年的历史研究表明:“暴力土改的问题不仅确实存在,比较普遍,而且许多地方还相当严重,伤害的人群也是非常大的。”历史学家还提醒我们注意:土改并非一定伴随着过度暴力,其发生多是在特定时间段、基于特定原因和条件。“这也是今天围绕着土改运动暴力与否,会出现那么多歧见的一个原因所在。”⑨
于是一系列追问出现:“真实性”是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有没有讨论的必要?讨论有没有结果?能否就事论事?能否有所超脱?怎样超脱?我们还可以追问:对“文学真实”的要求,是以“历史研究”为主要参照,还是其他?“真实”应否分类?怎样分类?从宏观还是微观出发?整体抑或局部?
我曾经针对“真实性”的问题,从“宏观真实”与“具体真实”两个方面来进行讨论。“若仅以土改的具体性而言,我们可以说正统叙事和张氏小说所叙述都是曾经存在、发生过的,因此都具有某种真实性。但仅仅从具体材料的表现上,恐怕也不能‘客观地断定谁更真实。”《暴风骤雨》等正统土改小说“所致力呈现的,是运动与斗争的历史合理性与必然性,是历史前进的宏观方向,而并非简单地反映具体的生活场景”。所谓“生活的表面真实”从来就不是它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类写作,通过弥合“党的政策”与土改运动的裂缝,将其构筑成一个整体观念与话语模式,以此来推动“国家”的权力延伸与渗透,最终为推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摇旗呐喊。也就是说,在“宏观真实”的层面,正统土改写作“更为贴切地展现了意识形态对社会改造的结果”。就此而论,即便非正统土改小说具有更多“具体真实”的成分,恐怕也未必能简单判定高下。作为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极其复杂的历史运动,我们的历史题材写作,或许根本不存在纯粹的客观真实反映,也不可能得出一个普遍适用的“真实”评定⑩。
作为“当代历史”主题写作,在意识形态的强烈干预下,周立波与张爱玲们极大地限制了自己的创作基点与文学想象,扬意识形态而抑、弃艺术规律,先后采取了近乎相反、简单对立的写作模式。后辈作家张炜、尤凤伟、刘震云、莫言等“非亲历者”以几乎相反的写作模式,也没有完成对意识形态干预局限的本质性超越,结果是两种写作模式对土改历史的文学表现都不无偏颇,都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四、 跨界的拓展
本文的剩余篇章,我们试图从跨学科视野来进入历史主题写作的研究,同时又尽量规避因历史语境变换带来的立场和视角变化,学科和语境的转换,是研究的双刃剑。此外,还将初步探讨从土改的史料、影像与绘画领域来切入研究的可能性。
1. “法学”的视野与历史语境
前文从“文学与历史”、“文学与记忆”等关系进行探讨,我们还可以从“文学与法学”的角度来讨论历史主题写作,尤其是针对争议性、创伤性的历史记忆写作之时。以土改为例,本质上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伴随着惩罚、暴力与生命伤害。如果从现代法律观念与司法规则——如公开公正的法庭审判和司法程序、“罪刑罚相适应”、“罪刑法定”原则——来衡量的话,那么运动中发生的许多行为是野蛮、粗暴、不合“法”的,尤其是失控的群众暴力。从以上角度入手,往往会有新的发见。
但是,我们在将“法学”引入文学评论与研究的时候,必须注意一个“实际适用”的问题。调用“法学”角度的时候,必须充分注意到文本所描述的时代、作者创作/写作时代以及我们“当下”时代三者之间的历史语境和价值观上的变换与差别。不同历史语境下的人考虑问题差别可能很大。这与价值观的改变息息相关。革命年代的杀戮与死亡,对于参与者来说可谓司空见惯的事情,“法律”和司法程序的有与无,哪些人该杀该留,杀多少留多少,由谁来判定裁决,对革命者来说大多够不上原则问题。我们经常论争的土改过度暴力等“真实性”的问题,更多地指向这种“价值观”的分歧,“史实”的层面反倒变得不那么重要:“我们没有办法简单地拿这样的标准,去要求,包括去批评过去的人。历史就是这么发生的,我们无法要求那个时候的人像我们今天这样思考,自然也无法简单地斥责当年那个时候的人如何漠视人权、轻视生命,滥施暴力”。11
此外,还应该把战争环境跟非战争环境下的土改区别开来。处在战争环境里的土改,一切都要从战争胜利出发,在“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等逻辑前提下难免出现流血和暴力。战争环境下的“土改”或其他运动过程中,几乎没有“法”的存在,或者“法”(政策文件)是根据斗争形势随时变动的,都由“政策”说了算,或者当权者来裁量把握,这种情况下就很不一定符合我们现在所讲的司法公平公正预想。正如杨奎松所言:“你又没有法律的规定和标准,又没有相应的司法程序,全看群众对斗争对象的仇恨程度,而仇恨这种东西又全无限度。”12
我们现在谈“司法公正”观念下的程序和原则,是1980年代以后法制相对健全以后才有的观念。在“土改”或者“反右”发生的历史时期,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司法公正的概念或规则。当代的“成文法”及其观念,是不存在或者影响极小的,往往是“习惯法”或者道德伦理在起实际作用。也就是说,民主自由、人权人性或司法公正等概念,都是“后来”的概念与标准。我们今天看历史问题及评论研究的时候,必须谨慎处理,充分考虑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
2. “文字”之外
除了文字,与“土改”相关的还有史料、影像、绘画等资料或艺术表现形式,如是种种对我们的讨论不无裨益。
在土改史料领域,主要有蔚为大观的各地土改档案(如文件、表格、材料)13,各地在土改前后印发的土改手册14,历史存留下来有代表性的土改实物等。尽管这些更多地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一般来说对于文学研究缺乏直接的意义和作用,但起码对文学研究,也是一种参照,它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包括土改在内的历史与记忆应该以何种形式保存下来,是以历史档案的形式收藏于博物馆,还是以文学性的加工变成一种叙事题材广泛传播?
而在影像、绘画等视觉艺术领域,以土改为主要表现内容的作品并不多见。其中,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是个特例,从1940年代的小说到1950年代的电影,再到21世纪在“元茂屯”所拍的纪录片、专题片,六十多年间持续得到关注。2005年,导演蒋樾、段锦川回到《暴风骤雨》故事发生地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镇,“把整个对该村农民、地主和当年工作队员的采访,比较如实地记录下来,剪出了一部不对外公映的纪录片。”15研究者张均曾分析纪录电影的不足及对小说的解构:“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不同视点讲述了尚志市元宝镇的同一土改事件。小说从革命立场出发,将地主叙述为集剥削者与道德恶棍于一体的负面形象,藉以确证土改的合理性与解放的正义。纪录电影则重返当年土改发生地,以大量当事人口述,展示了小说有意删除和遗忘的另一面,有力地解构了小说的‘正典叙述。然而纪录电影本身也存在难以为人注意的对于权势者罪恶与底层不幸的大面积‘遮蔽。”16
2012年12月10-14日,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节目做了一辑名为《暴风骤雨:土改纪事》的五集专题片,回访了四位解放区作家丁玲、周立波、赵树理、孙犁写作土改作品的原型地,按照该节目的惯例,以人物讲述记忆作为叙事的推进。这一辑节目,既不谈作品,也不谈作品与记忆的关系,也没有展示更多的资料(而且在五集里重复使用),远远没有挖掘小说与人物记忆背后更多的隐藏信息。采访对象和评价方式比较老套和单一,分别采访了几个当年积极分子、地主的后代。在材料剪裁上比较片面,只谈当时农民苦状,然后在共产党工作队领导下,斗倒地主分田地浮财,最后翻身分地分浮财的喜悦和运动之后的积极性。节目既不追问合理性,也避免谈及数年后“土地归公”和翻身的短暂与虚幻。加上不时穿插无关紧要的国内战争形势,来为阶级斗争做注,而本该最为核心的“作家作品”则惨遭无视,与土改运动无关紧要。既乏创新,深度也欠奉,是一辑低于“凤凰大视野”平均水准的专题。
文学与美术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常被运用于古代文学、古代历史的研究中,尤以美术中的“图像”运用最广泛。新世纪以来,文学与美术的关系问题开始在我国学界受到重视,由于研究显示了一种有价值的学术转向,有人将这一关系研究称为新世纪的“新学问”。其意义,大而言之,除了它对同一对象研究的多学科视角,更在于它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发现了新问题——文学与美术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勾连或通约?作为文学载体的语言和美术两种符号及其互文,对于当代文艺创作领域中的文学史、美术史乃至当代历史的重构有何意义?小而言之,我们可以明晰土改作为“主题创作”的概念与范畴,在文学和美术领域的影响和衍变过程。并且进一步追问:作为历史运动和创作主题的“土改”,何以成为主题创作,何以转瞬即逝,何以再度繁荣?17
土改绘画上承解放区文学与解放区木刻,下启“文革”文学与美术,其美术史地位自不待言。古元、力群、江丰等知名创作者先后涌现。绘画不同于文学对于运动“全方位”的“再现”,集中表现运动中最具典型的场景,如批斗会、烧地契、分田地等。
革命年代里的土改文学与绘画,有高度的相似性。当代政治文化生态是其共同的产生和“繁荣”的基础,在“形式”上,同为革命文艺的艺术化,目标和任务主要是为阶级对立的建构与形象化表达,同为响应、遵循和践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约的创作方向与任务,体现“毛泽东时代”文艺特色的重要艺术种类,均为政治所驱驰前进的艺术。二者有诸多内在共通性,但主要地由于表达方式上的差别,因此有明显不同的发展轨迹。
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如陈思和、贺仲明、唐小兵等人对于土改小说,从写作类别、模式到语言暴力,从局部到整体时有推进。近现代史学界对土改运动的研究,代表者从杜润生、董志凯到黄宗智、张鸣,再到杨奎松、李里峰、李良玉等,极大推进了土改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现代美术史界关于土改题材绘画作品的研究同样精彩:由王璜生、邹跃进、李公明等人发起并践行的“毛泽东时代美术(1942-1976)”的提法与研究上的成熟,一批新中国美术画册及研究成果应运而生,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邹跃进、陈履生、王明贤等人在新中国美术史领域,产生了《新中国美术史》18等著作,李公明、杨小彦、冯原、胡斌等学者对土改图像与阶级观念和意识形态建构关系进行了富于艺术与历史深度的探研,如李公明《“阶级”与“怨恨”的图像学分析》19、胡斌《解放区土改斗争会图像的文化语境与意识形态建构》20、帅好《政治运动中的美术》21等。
近年来,袁行霈聚焦在陶渊明的文学史与绘画史交叉研究、陈平原在晚清图像与文化、姚玳玫在现代文学/美术的个案解读上,尝试将文学/文化与美术做交叉对比研究,开拓出新的学术领地。但是尽管当代文学研究和美术研究各自繁荣,但基本“老死不相往来”,甚少学科交叉研究。相对于当代文学与电影、戏剧相对较多的联系与论述,而政治色彩更为鲜明突出、组织意味更加浓厚的当代文学与当代美术的比较研究,至今人迹罕至,这一缺失将影响我们对当代历史的多面认识。
对“土改”的写作和研究,我们说,一方面可谓蔚为大观,但另一方面,在深度、广度和表现形式的丰富性上,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仍有大量可开掘的空间。我们不仅重视原有的宝贵研究经验,还要拓宽视野,借助于多学科交叉和多种表现形式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推进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且本文所涉论题和方法,可拓展至“集体化”、“大跃进”、“文革”等当代历史题材写作的评论和研究。
【注释】
①陈思和:《土改中的小说与小说中的土改》,《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②早在2002年,我在写作《土改的两张面孔——〈暴风骤雨〉、〈故乡天下黄花〉叙事比较》一文时,就对土改写作的两种模式进行了这一区分与命名,该文章后来发表于《小说评论》2006年第2期。学者贺仲明也采取了类似的划分,在《重与轻:历史的两面——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土改题材小说》(《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一文中,从“创作者”的代际差别出发,将“中国当代土改题材小说”分为“土改运动的亲历者”,及“80年代后的年轻作家”两类创作。
③沈博爱:《蹉跎坡旧事》,语文出版社2013年版,姜淑梅:《乱时候,穷时候》,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沈、姜两位作者分别生于1936年和1937年。
④张学强:《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页。
⑤这些人生回忆录中,土改只是其中的一段,但是作为历史的转折,对记忆主体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⑥陈思和:《土改中的小说与小说中的土改》,《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⑦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4年第4期。
⑧陈思和:《土改中的小说与小说中的土改》,《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⑨杨奎松:《中共土改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谈往阅今:中国党史访谈录》,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页。
⑩本段主要观点及引文,见黄勇《真实的书写?——张爱玲土改小说论》,《二十一世纪》(香港),二零零四年三月号(网络版),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401052.htm
11杨奎松:《中共土改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谈往阅今:中国党史访谈录》,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73页。
12杨奎松:《中共土改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谈往阅今:中国党史访谈录》,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页。
13如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
14如湖南省文联筹委会编:《文艺工作者怎样参加土改》,新华书店湖南省分店1950年版。
15杨奎松:《中共土改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谈往阅今:中国党史访谈录》,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页。
16张均:《革命、叙事与当代文艺的内在问题——小说〈暴风骤雨〉和纪录电影〈暴风骤雨〉对读札记》,《学术研究》2012年第6期。
17再度繁荣仅限于文学,美术界对于历史运动的创作,除了弘扬主旋律,甚少“回顾”的创作,如对反右、大跃进、大饥荒等题材的反映,其关注焦点和表现范围相比文学要狭窄得多。
18代表性的“新中国美术史”及相关研究著作如邹跃进:《新中国美术史(1949-2000)》,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陈履生:《新中国美术图史(1949-1966)》;王明贤、严善錞:《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陈履生:《革命的时代:延安以来的主题创作研究(1942-2009)》,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19李公明:《“阶级”与“怨恨”的图像学分析——以毛泽东时代美术中的地主-农民题材为中心》,收入作者文集《在风中流亡的诗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0胡斌:《解放区土改斗争会图像的文化语境与意识形态建构》,《文艺研究》2009年第7期。
21帅好:《政治运动中的美术——以谢志高、程十发、李可染、刘曦林为例》,刊于《领导者(2013年特刊·历史报告)》,也可见“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30311787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