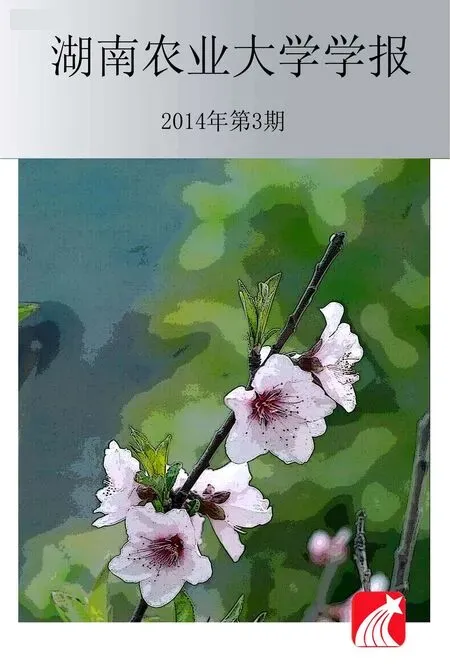苏联集体农庄与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差异分析
易棉阳,曾鹃
(1.湖南工业大学商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8;2.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苏联集体农庄与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差异分析
易棉阳1,曾鹃2
(1.湖南工业大学商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8;2.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虽然以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为师,但两者也存在明显差异。在发展路径上,苏联集体农庄的发展完全取决于政府意志;中国农业合作化过程是政府主导和民间需求相结合,更加符合农村实际和农民意愿。在所有制上,苏联集体农庄的土地和大型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且程度越来越高;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则根据不同时期生产实际及时调整,并在公有化程度上逐步退却。在富农政策上,苏联主要通过暴力镇压方式消灭富农,并剥夺其全部财产;中国主要采取行政强制,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其留下了出路。在单干户政策上,苏联强迫单干户加入集体农庄;中国则是引导方法单干户入社。在生产管理上,苏联主要实行集体承包制;中国则采取包产到队的生产责任管理模式。
苏联;集体农庄;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差异
20世纪20~30年代和50年代, 苏共和中共分别在农村掀起声势浩大的农业集体化(合作化)运动。学术界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有的认为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翻版[1]。有的认为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部分借鉴了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经验,但自身特色亦较为鲜明[2]。还有学者认为,两场运动在目标、内容和基本形式上确有相同或类似之处,但两者也存在较大差异[3]。集体农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和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组织载体,虽然在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制度、剥夺农户独立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实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诸方面有相似之处,但这两种组织同样具有各自特点,相异之处亦相当明显,体现了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对苏联集体农庄的继承与创造。鉴于现有研究对两者之间差异比较迄今并无专题研究成果,笔者拟利用近年公布的相关资料对两者的相异性进行比较分析。
一、发展路径的差异
苏共农业集体化政策变化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1917—1918年)为重点发展农业公社,其最大特征是实行全盘公有化,“加入公社的人应放弃其个人的一切财产,在入社时应将一切家什和一切财产(动产、不动产和现金)交给公社,成为公共财产”,在分配上,“公社的基本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消费上,“为了爱惜劳动、产品和燃料,公社应该设立公共食堂”[4]23。与重点发展公有化程度高的农业公社相反,对于公有化程度低的劳动组合和共耕社两种集体农庄,则不但不扶持而且还进行阻扰[5]86。1918年组建的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是农业公社,没有劳动组合和共耕社。农业公社效率非常低,托洛茨基曾指出,农业公社“在某些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甚至还很低”,原因是公社“缺少对个人利益的直接关心”,结果是“工作非常勤勉的人毫无奖励,工作草率或工作得很少的人也并不因此而有所失。”[6]139因此,苏共不得不进行政策调整,农业集体化进入劳动组合、共耕社、农业公社并行发展的第二阶段(1919—1929年)。共耕社中的农民把自己的土地交由集体联合耕种,农具和耕畜等生产资料仍归农民私有,土地、生产资料、劳动力三者都参与分配,依靠公共积累添置生产工具。在劳动组合中,生产资料归公所有,但允许农户私人拥有部分小型农具和少量耕畜,允许耕种小块的宅旁园地,分配上取消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报酬,实行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7]1-2。共耕社类似于中国初级社,劳动组合相当于高级社。在第二阶段,公有化程度高的劳动组合占据主导地位,公有化程度较低的共耕社得到较快发展[6]90。1929年,斯大林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苏联农业集体化进入第三阶段。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还没有公有化的共耕社是集体农庄运动中已经过时的阶段”,而“不仅生产公有化而且分配也公有化的农业公社”,在苏联“条件还没有成熟”,所以,“现在应当抓住的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形式,就是农业劳动组合”[8]241-242。此后,劳动组合成为苏联唯一的集体农庄组织模式,共耕社和农业公社不复存在。综上,苏联集体农庄最初选择一步到位的发展路径,失败以后转而采取三种集体经济组织并行发展,最后只允许发展公有化程度居中的劳动组合。
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过程,以公有化程度的高低为标准逐步过渡发展。第一阶段(1950—1953年)重点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简单低级的劳动互助,它是按农民固有互助习惯组织起来的一种临时性和季节性组织;二是常年的互助组,它有简单的生产计划,有些还积累了牲畜、农具等公共财产;三是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土地合作社,它有一定程度的生产计划和技术分工,有一定公共财产积累,“是在较好的互助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农业生产互助运动在现在的高级形式”。[9]511-5121953年“一五计划”实施,粮食的需求量激增,粮食供应顿显紧张。为提高粮食产量,中共决定在全国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重点发展初级社的第二阶段(1954—1955年)。初级社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它的显著特征是有“一部分公有的生产资料”,实行按土地分红和按劳取酬的分配方式[10]359。在政府推动下,农民入社热情高涨,1955年底到1956年春,全国出现农业合作化高潮,初级社迅速上升为高级社,有的甚至直接从单干户和互助组升级为高级社,高级社数量不顾发展规律急剧增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总体进入第三阶段,即高级社阶段(1956—1958年)。高级社的土地、主要生产资料全部归集体所有,社员集体劳动,分配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不分男女老少,同工同酬[11]404。
苏联集体农庄发展路径之所以异于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路径,主要因为两国制度变迁模式的差异。苏联农业集体化主要是通过政府主导型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发展何种形式的集体农庄完全取决于政府意志,苏联农民毫无话语权。而在中国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政府则充分吸取苏联教训,更加符合农村实际与农民意愿,其制度变迁模式是政府主导与民间需求相结合。虽然在第三阶段实践有所偏差,但前两个阶段都是先由农民自己组织互助组和初级社,政府再予以规范推广,基本保证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步过渡的发展路径。
二、所有制的差异
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后,劳动组合作为集体农庄的唯一形式,成为集体农庄的代名词。薄一波曾指出,“我国高级社类似苏联的集体农庄”[12]360。人民公社由高级社合并而成,其经济功能与高级社相似。苏联农业劳动组合与中国人民公社(高级社)之间的所有制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土地所有制差异。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合作社不仅是对传统小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效组织,而且是通往共产主义的过渡形式[13-14]。正因为合作社具有共产主义性质,所以马克思主张合作社实行土地公有制,他说“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13]634。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规定:立刻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交给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在此基础上组织农民发展集体农庄。苏联宪法也明确规定集体农庄“占用的土地是国家的全民财产,根据工农国家的法律拨给劳动组合无限期即永久使用,但劳动组合不得买卖,不得出租”[15]575。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农民拥有对土地的完整产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和让渡权)。在互助组和初级社阶段,土地依然归农民私有。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土地则实行集体所有制,《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入社农民必须把私有的土地”转化为“合作社集体所有”,社员私有土地上“附属的私有的塘、井等水利设施,随着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11]407-408。人民公社时期,实行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管理架构。由于生产队是人民公社最基本的核算单位,因此“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16]625。生产大队和公社,对小部分土地主要是林场、茶场等拥有所有权。
二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差异。苏联集体农庄的大型农具和耕畜等基本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包括“全部役畜,农具(犁、播种机、耙、脱粒机、收割机),种子,饲养公有牲畜所需要的饲料,经营劳动组合所需要的经营建筑物以及所有农产品加工企业”。1932年苏共通过《关于保护国营企业、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财产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所有制法》,规定“公共财产是苏联制度的基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集体农庄和合作社的财产,如田野里的庄稼、集体储备粮、牲畜和合作社商店里的货品等均为国家财产”[17]85。1935年颁布《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规定农户私人可以占有小型农具等小部分生产资料,也允许私人饲养牲畜,并根据谷物和经济作物产区与畜牧业发达的种植区的实际规定饲养的具体数量[18]336。与苏联集体农庄类似,中国高级社也主要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入社农民必须把“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零星的树木、家禽、小农具、经营家庭副业所需要的工具,仍属社员私有,都不入社”[11]407。“大跃进”时期,曾一度消灭农村私有制,把社员的自留地、房屋、家禽、小农具等私有财产全部无偿收归人民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经营、统一核算。不过,这种状况迅速得到纠正。高级社和人民公社都允许私人饲养一定数量的家禽,且没有对社员私养的家畜数量作出明确限定。因分配给每个社员的自留地“一般不能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5%”,中国每个社员自留地数量远低于苏联每个社员可拥有自留地的数量,严重制约了农户家禽养殖能力,导致家庭副业远远落后于苏联农户。
三是所有制演化的差异。苏共历届领导人都追求集体农庄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1937年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结束时,共有集体农庄24.37万个,每个集体农庄平均13.7户。1953年全苏集体农庄减少为9.3万个,平均每个集体农庄达到211户。1976年苏联集体农庄减少到2.77万个。同时苏联还把大量集体农庄改组为国营农场,以提高国有化程度。据统计,1954—1970年,全苏有2.4万个农庄被改组为国营农场,由1936年的4 137个上升为1976年的19 600个。国营农场占全国耕地面积的比重,由1936年的0.6%上升为1979年的53%,而集体农庄耕地占比由 1937年的 99.1%下降为1979年的42%[19]45。正因为苏联集体农庄向着“一大二公”方向发展,公有化水平越来越高,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越来越严重,生产效率始终没有得到提高。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也曾一度追求“一大二公”,1955年初级社平均不到31户,1956年成立的高级社平均达238户[20]11-12。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成立的人民公社平均 1 000户以上,如辽宁平均每社2 000户,河南平均每社4 000户,北京平均每社1 600户[21]730。合作社规模扩大的同时,所有制也在不断升级,1958年北戴河会议提出要变高级社的小集体所有制为公社的大集体所有制,并逐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实践证明,公有化程度高的大社不但没有产生规模经济反而导致管理成本高、生产秩序混乱,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1959年中共中央采取措施坚决纠偏,把公社一级所有制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承认公社、生产大队(相当于高级社)、生产队(相当于初级社)三级所有制,实行三级核算,并以生产队的核算为基础。这是人民公社所有制公有化程度的退却,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相反,苏联集体农庄公有化程度却越来越高,也越来越脱离实际。
三、生产管理的差异
苏联集体农庄和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属于欧文式的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类似于初级农产品生产企业,在生产上面临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难题:无法精确划分生产流程、无法精细地进行劳动分工、无法准确地界定生产责任、无法准确地鉴定劳动质量、无法准确地进行绩效考核。针对这些难题,苏联和中国都结合本国情况在实际中对生产管理进行了一些探索。
从 1939年开始,苏联的一些集体农庄实行集体承包制尝试,即把集体农庄田间作业队划成若干作业小组实行包产包工,对于超产的作业组额外加算劳动日。这种集体承包制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大平均主义,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至 1940年,全苏约有18%的农庄实行这种办法[22]141。经过不断探索,1947年苏共决定实行生产队独立核算,要求集体农庄在收入分配时,应把各个生产队的收成情况纳入考察,收成高的生产队应得到更多收入,其庄员也获得较高报酬。1948年苏联部长会议要求集体农庄实行计件包工制。不过,这些集体承包制的尝试因斯大林反对在 1950年初被迫终止。赫鲁晓夫上台后,集体承包制再度施行,并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得到大力推广。集体承包制的优点在于能消除土地无人负责的现象,提高庄员的生产责任心,从而提高生产效率。科斯特罗马区推行集体承包制之后,1972年的劳动生产率比1968年提高65%,每公担谷物的劳动日消耗量降低了 58%[23]188。到1982年,苏联实行集体承包制的作业队约3.2万个,人数占全国农业总劳动人数的 9%,某些加盟共和国达到25%。1983年全苏农业会议上,苏共要求在全国农村普遍推行集体承包制,在 1985年前把这一先进制度在所有农村牢固地建立起来[24]。
中国农业生产合作进入高级社阶段之后,积极创新生产管理方式,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探索实施“工包到组”和“田间管理包到户”。“工包到组”就是生产队把一定地块的主要农活向生产组实行常年包工或季节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就是将零星的田间管理杂活责任到户。“工包到组”和“田间管理包到户”相结合是集体和个体劳动相结合的一种有益探索。有些地方在“工包到组”的基础上实行“包工包产到组”,个别地方在“包工包产到组”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实行“包产到户”,如江津区江津县龙门区刁家乡的六村二社和十村一社、二社,把合作社的土地按照各户的劳力、人口情况分到户,肥料、种子也分到户,耕牛由各户按人口多少轮流喂养和使用,生产和收获都由各户负责,各家收各家得,只根据生产计划规定产量,按比例缴纳公粮、统购粮食和一部分公积金。二是推行“以产定工”,即根据每个生产队创造的净价值来确定其应得工分,以避免增产亏本现象出现。具体做法是:合作社根据每种作物的计划指标的纯收入和用工数量,分别规定每个生产劳动日应该达到的产量,来确定每个劳动日的计酬标准;分配时生产队在每种作物上实际完成多少工作日的产量,就给生产队记上几个劳动日[25]343。在生产队层次上进一步明确生产责任制,如河北省保定专区7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小组固定地块常年包工或季节性包工,有的甚至包产,还有的把部分农活包到了户[26]。这些探索在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曾一度被废止,但 1959年又迅速恢复并向前发展,各地按照年初郑州会议精神建立“三定一奖”、“四定一奖”的生产责任制,即公社对生产大队实行“四定一奖”(定生产指标、定投资、定上交任务、定增产措施,实行超产奖励),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实行“三定一奖”(定生产指标、定投资、定增产措施,实行超产奖励)。1962年中共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明确规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实行自主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这种制度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16]625包工、包产到队的生产责任制在全国农村最终得以确立。
由于苏联集体农庄在所有制上长期追求高的公有化程度,作为经营制度的集体承包制实际上与所有制相矛盾,导致直至苏联解体之前几年,集体承包制仍尚未在全苏集体农庄大面积确立。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在所有制上也曾一度追求更高层次的公有制,但中共迅速意识到高公有化不能带来高生产效率,果断放弃了高公有化的追求并退却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层次,这种退却为集体承包制的产生和确立扫清了制度障碍。
四、富农政策的差异
中苏都把发展合作组织作为消灭农村剥削、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在剥夺了地主土地之后,农村中的剥削阶层主要就是富农阶层。在如何消灭富农阶层上,中苏有着政策上的明显差异。
1929年全盘集体化以前,苏联实行限制富农的政策:实行土地国有使富农不能兼并土地;向富农征收高额税收;限制富农雇佣劳动力数量从而限制富农经济规模;强制富农按规定价格将粮食出售给国家。在政府限制下,部分富农陷于破产境地,至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前夕,苏联富农占总农户的比重约为4%~5%[27]93。1927—1928年,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认为其产生的首要原因在于“富农进攻”和“小农经济的分散落后”[17]45,要求“立刻动员党内所有优秀力量”,对富农和投机分子采取“特别的镇压措施”[17]47。1929年斯大林提出不能允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之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的死敌”,要“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表明苏联的富农政策由过去的限制转变为消灭。斯大林还认为消灭富农要依靠集体农庄,“具有反富农性质的汹涌澎湃的集体农庄运动,正在自己的道路上扫除富农的反抗”[28]126。消灭富农从两方面展开,一是物质上的剥夺,即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包括牲畜、生产用建筑物、住宅、农产品加工企业、饲料和种子;二是肉体上的打击,即流放驱逐富农,1930通过的《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的措施》把富农分为三类并分别进行处置:第一类富农(即反革命活动和暴乱组织的组织者),立刻逮捕并关进集中营,第二类富农(即大富农和半地主),流放到西伯利亚、乌拉尔等人迹罕至的边远地区,其余均为第三类富农(占富农总人数的75%),驱逐到本地区在集体农庄地域外专为他们划定的边缘地段[29]296-297。在1929—1932年的消灭富农运动中,共有120万户约600万富农被消灭,大部分是按1930年新标准划定的新富农,“准确地说,消灭富农实际上是消灭农民,因为被消灭者中绝大多数是中农和贫农”[17]98。被流放的富农被称之为特殊移民,其所居住的所谓特居区条件极为恶劣,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有的特殊移民“饿得像狼一样”,有的“像牲畜一样赶进教堂”,还有的孕妇不得不在棚子里生孩子[17]100。为了生存,他们有的杀人、放火、毒死牲畜、捣毁机器;有的千方百计逃离特居区;还有的铤而走险,揭竿起义。面对特殊移民的激烈反抗,1933—1935年,苏共一度采取怀柔政策,缓和了矛盾。1937年,斯大林又指示开展一场“富农战役”,要求各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各级机关,统计已经回到家乡的富农和刑事犯人数,立刻逮捕其中的“最危险分子”,枪毙罪大恶极者,其余人员被关进集中营。富农战役到 1938年结束,总镇压人数为81.9~83.4万人之间,枪毙人数为43.7~44.6万人之间[17]19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的富农政策经历了一个从保存到限制到消灭的过程。土改时期,为孤立地主,中共采取保存富农的政策。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已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30]。1953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全面展开以后,中共的富农政策调整为限制富农。中宣部印发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出,“在目前时期,党在农村对富农的政策还是限制富农”[31]715-716。主要采取经济手段,包括通过统购统销限制富农的经商活动,发放国家农贷限制富农的借贷活动,调剂合作社里面的劳动力、农具限制富农的剥削行为等方式[32]。1954年中共把富农同地主、反革命分子一并列为敌对阶级,发动贫雇农对富农进行斗争,富农政策演变为消灭富农。不过,在加入合作社方面,中共还是对富农网开一面。《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规定,在合作社成立之初的几年内,不接受富农入社,但在合作社巩固之后,“已经多年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经过社员大会审查通过、县级人民委员会审查批准,个别地接受他们入社”,但“在入社以后的一定时期内,不许担任社内任何重要的职务”[10]363-364。《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留给富农的余地更大,“已经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合作社根据他们的表现和参加劳动生产的情况,并且经过乡人民委员会的审查批准,可以分别地吸收他们入社做社员或候补社员”,对于不够条件的富农分子,“经过乡人民委员会的批准,合作社可以吸收他们参加社内的劳动,使他们获得改造成为新人。对于这些人,合作社应该同对待社员一样地按照他们的劳动付给报酬,……这些如果表现良好,经过乡人民委员会审查批准,可以做候补社员”,“在入社以后的一定时期内,没有被选举权,不能担任社内任何重要职务;做候补社员的,并且没有表决权和选举权”[11]405-406。
中国消灭富农与苏联消灭富农有显著差异:第一,苏联采取暴力镇压的极端措施消灭富农,中国主要采取行政强制如召开斗争大会来消灭富农,没有关押、流放富农。第二,苏联在消灭富农后,剥夺了其全部财产,集体农庄没有给富农留下出路;而中国允许富农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只剥夺其多于入社股份基金的那部分财产[11]168-211。苏联采取暴力方式消灭富农,加剧了社会矛盾,引起了社会动荡;中国采取较为温和的方式消灭富农,有效控制了社会矛盾,还充分利用富农在发展农业生产上的优势,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苏联消灭富农运动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很多中农和贫农也受牵连;中国在消灭富农过程中,仅极少数的中农和贫农受到牵连。
五、单干户政策的差异
没有加入集体农庄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被称之为单干户(苏联也称之为个体户,而且是一个蔑称)。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和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都不允许单干户的大量存在,但两国的单干户政策有着明显差异。总体而言,苏联主要采取强制办法来迫使单干户加入集体农庄,而且还采取了经济和肉体打击的残酷手段。中国则主要采取以引导为主、强迫为辅的办法来使单干户加入合作社。
1929年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之前,苏联集体农庄发展非常缓慢。据有关资料,1918年苏联集体农庄1 600个,集体化农户比例为0.1%,1928年集体农庄33 300个,集体化农户占比也仅为1.7%。1929年入庄农户的比例亦不过3.9%,从1930年起迅速上升,1936年达到90.5%[5]。在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过程中,农民不是一批一批地,而是整村、整乡、整区地加入集体农庄。尽管斯大林在《大转变的一年》中宣布集体农庄是农村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但当时苏联绝大多数单干户并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所以,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初,单干户主动加入集体农庄的积极性很低。在此背景下,苏联于 1929年派出“两万五千人大队”来到地方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使用制裁、逮捕、没收财产、剥夺选举权等各种手段强迫单干户加入集体农庄。如在中央黑土区的乌斯曼区和阿年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搜查,所有不愿意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都被逮捕,十天之内该区集体化比例由26%提高到82.4%[17]71。政府的强制措施遭到农民强烈反抗,据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报告,1930年1月1日到4月 15日的四个多月时间里,全苏发生农民起义27次,参加人数达2.5万人。面对农民的反抗,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镇压中不仅使用刺刀、手枪、步枪和机关枪等武器,还出动了红军,动用了装甲车、大炮和飞机。政府的残酷镇压带来了集体化的“卓著成效”,至1936年全苏基本实现农业集体化,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达90.5%。或许是感于残酷镇压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或许是不足10%的单干户已不足为虑,1936年起,斯大林决定不再采取“逮捕和枪毙”的消灭手段,他还认为把单干户“直接抓起来掐死的做法太愚蠢了”,而应“通过经济措施和财政措施教育个体户”,“让他们啥也剩不下”,不得不加入集体农庄[17]159。1936年之后,单干农民所承担的税收比集体农庄庄员至少高出25%,900多万单干农民经济状况迅速恶化,不堪重税的单干农民不得不加入集体农庄。
中国实现合作化的时间短于苏联实现集体化的时间。1954年3月底,加入初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比重为1.5%,到1955年3月底达到88.9%,基本实现初级农业合作化[33]131-132。1955年12月底,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比重仅为 4%,到1956年12月底,达到87.8%,基本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34]428-430。中国反复强调发展合作社要坚持农民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反对强迫命令。1951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明确提出,“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在农业的互助合作运动上,强迫命令的领导方法是错误的”[9]516。《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也规定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决不能用强迫的方法,应该用劝说的方法,并且做出榜样,使没有入社的农民认识到入社的好处,不会吃亏,因而自愿地入社”[10]358。虽然一些地方确实出现了强制单干户入社的现象,甚至还采取吊打等暴力手段,如浙江仙居在合作化高潮中,251个乡干部有74个打过人,该县埠头乡自1956年11月到1957年4月被干部吊打的农民有25人,大路乡被吊打的农民有17人[30]178,但这种情况出现后,中央立即予以坚决纠正。1956年秋和 1957年春,一些群众要求退社单干,出现退社风潮,有些地方群众聚众闹事,如浙江仙居2.18万人参加退社闹事,持续2个月,107名干部挨打,430户社干被抄家,有的农民甚至携带土枪、土炮上山,扬言要攻打乡政府[34]361。面对群众的过激行为,中共中央要求做好工作,尽量争取社员不退社。对一些富裕中农和原来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如果仍然坚持要退社,“可以允许他们退出,而不必把他们勉强留在社内”[35]648。政府的怀柔政策迅速平息了群众情绪,退社风潮在 1957年夏天消退。退社风潮后,1957年下半年各地方纷纷出台措施限制单干户,如陕西省委农村工作部于1957年制订10条措施,对单干户实施严格管理[36]611。1957年底国务院发出《关于正确对待个体农户的指示》,规定合作社对单干户具有行政管理权,可以监督其“生产活动、播种计划、纳税和农产品交售”,督促其“照数补交和出售”统销物质,制止其“在自由市场上买卖国家统一收购和禁止自由买卖的农产品”,可以向其“摊派义务工”和公益事业“所需的人工和款项”[35]747-748。
毋庸讳言,无论是苏联集体农庄还是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都不但没有发展农业生产力而且还制约了农业生产力的进步。个中原委,值得玩味。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无论中苏,政府主导建立起来的生产合作社,体现的是政府的意志,违背甚至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被强制加入合作社的农民,合而不作,消极怠工。不过,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以苏联集体农庄为师并进行了诸多创造,不仅对原制度进行创新,而且为后来的制度创新准备了前提,因而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比苏联集体农庄具有更大的制度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了改革,在坚持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允许家庭分散经营,从而形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新型农业经营制度,迅速发展了中国农业生产力。当前,中国农业现代化需要大力发展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必须体现农民的意图而非政府意图、归农民所有而非政府所有、一切由农民自己作主而非政府作主,否则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就难逃历史覆辙。
[1] 王前.关于合作化理论的沉思[J].中共党史研究,1989(1):47-55,1.
[2] 赵金鹏.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不是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翻版——与王前商榷[J].中共党史研究,1990(6):76-79.
[3] 郑明.中国与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兼与王前、赵金鹏商榷[J].中共党史研究,1991(5):75-78.
[4]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苏联农业公社资料:上[G].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印,1959.
[5] 杜吟棠.合作社:农业中的现代企业制度[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6]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苏联农业公社资料:下[G].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印,1959.
[7] 伊林.农业劳动组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8]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 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0] 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1] 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1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15]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研究室.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解决问题决议汇编(1929—1940年):第二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6] 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7] 吕卉.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0.
[18] 金挥,陆南泉.战后苏联经济[M].北京:时事出版社.[19] 国家计委办公厅翻译处.苏维埃政权二十年(统计资料汇编)[G].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1954.
[20] 国家统计局农业统计司.农业合作化与1955年农业生产合作社收益分配的统计资料[G].北京:统计出版社,1957.
[2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22] 苏联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五卷[M].上海:三联书店,1984.
[23] 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苏联经济研究组.二十年来的苏联经济:1954—1973[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24] 谢建明.试论苏联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的历史演变[J].湘潭大学学报,1985年校庆特刊:79-83.
[25]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农业合作化[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26] 保定地委农村工作部.关于1957年整顿农业合作社的总结报告[G].河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879-1-275.[27] 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苏联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G].北京:统计出版社,1956.
[28] 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9] 周尚文.新编苏联史:1917-1985[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N].人民日报,1950-06-30(2).
[31] 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4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2] 苏少之.新中国关于新富农政策演变的历史考察[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7(1):114-121.
[33] 莫曰达.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发展[M].北京:统计出版社,1957:131-132.
[34] 高化民.农业合作化始末[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35] 国家农委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36] 陕西省农业合作史研究室.陕西省农业合作重要文献选编:下[G].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曾凡盛
Diversity comparison in Soviet Union collective farms and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operatives
YI Mian-yang1, ZENG Juan2
(1.Business Colleg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8, China; 2.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operative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Soviet collective farm,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Soviet decide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collective farm;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operatives was decided by government and peasant .On the ownership, Soviet collective farm practiced state ownership,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operative practiced collective ownership. On the rich-farmer-policy, Soviet eliminated the well-off farmers; Chinese retained the well-off farmers; On the one-man policy, Soviet forced the one-man to join it’s collective farm; Chinese led the one-man to join it’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operative. On the production management, Soviet practiced collective contract system, Chinese practiced the production team responsibility system.
the Soviet Union; collective farms; China;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operatives; diversity
F321
A
1009-2013(2014)03-0075-08
10.13331/j.cnki.jhau(ss).2014.03.013
2014-05-0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1YJC790246);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2012M521520)
易棉阳(1977—),男,湖南涟源人,经济学博士,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合作经济理论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