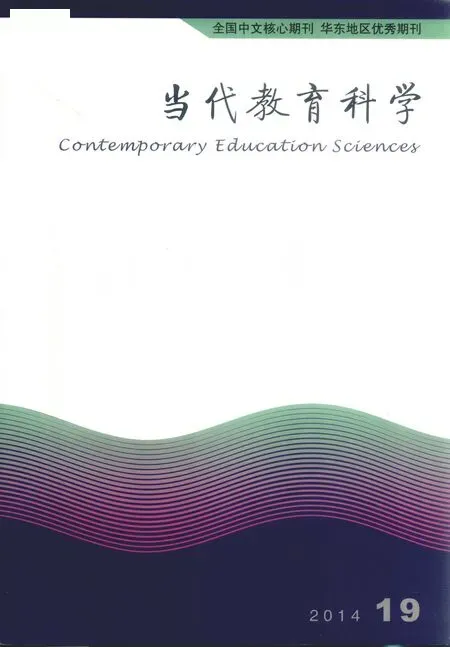论教育幸福及其双重结构*
●韩登亮
论教育幸福及其双重结构*
●韩登亮
各种关于教育幸福的陈述都是需要价值判断的命题,在教育承诺中获得意义,并通过现代教育的承诺对个体价值予以承认,并赋予个体幸福以合法性。这种个体幸福的价值赋予在教育实践中必然地具有双重结构,既在消极的意义上消除个体教育幸福之间的冲突,也在积极的意义上通过教育扩展个体的幸福可能。
教育幸福;教育口号;消极幸福;积极幸福
“幸福”这一概念已经成为教育中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词汇。教育能否给个体带来幸福、教育过程是否能让人体验到幸福、幸福是否是教育的最高价值判断等等疑问也成为教育不断自我省思的问题。但是,当我们反问“教育中的幸福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幸福一词似乎又变得深不可测,令人难以捉摸。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百个教育研究者就会有一百个关于教育幸福的定义。康德曾说:“幸福的概念是如此模糊,以致虽然人人都在想得到它,但是,却谁也不能对自己所决意追求或选择的东西,说得清楚明白、条理一贯。”[1]对幸福一词的“真实含义”的追寻也许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即便如此,人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追求幸福的脚步,这似乎也在昭示人们,教育中的幸福一词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术语,而只是一个教育口号。
一、作为教育口号的教育幸福
不同的学科领域因为研究立场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对于教育幸福的研究也就有了不同的学科视角和价值取向。那什么是教育中的幸福?美国分析教育哲学家谢弗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研究思路。他认为,要理解教育幸福一词的各种用法和阐述的多样性、分歧性,可以从教育口号的角度进行研究。在谢弗勒看来,相对于教育术语和教育隐喻而言,教育口号是一种非系统化的,表述不严谨,但通俗易懂,常被人们接受和传诵的教育语言,它的兴趣既不是为了促进对话,也不是为了解释术语的意义,而是为了从心理上激发听众。教育口号现象十分普遍,比如杜威提出的“以儿童为中心”的口号,就曾经影响了整整半个世纪的教育实践,至今余音未绝。教育口号有其来龙去脉,有其变化的语境,“这些不同的上下文背景主要包括了口号的文字表述、给予口号以生命力的实践活动以及形成口号的陈述母体。三方面的标准是相互独立的,当口号之间在文字上相互冲突、产生矛盾时,并不等于它们代表了不可调和的冲突的实践建议”。[2]从教育口号的角度来看,对“幸福”一词抽象含义的研究也只有抽象的意义,在实际的实践活动中过分执着于概念反而会损害实践活动,培根称这种语言的误用为“市场假象”,[3]概念之争不能解决问题,仅仅着眼于语言的辨析和概念的澄清反而容易诱导人们的理智去关注于抽象的理论而非真实的实践。所以有效的方法应当是首先分析教育中关于幸福的各种表述的性质。
幸福在教育中的使用有多种表述方式,但是教育中引入幸福概念的各种表述方式无一例外都是一种命题。不论我们说“幸福是教育的终极目的”还是“让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感到幸福”,都蕴含着“教育能够带来幸福”以及“教育过程是幸福的”这样的一个可以作出是或者否的回答的命题。当然,在作出是或者否这样的命题过程中首先还需要我们进行相关价值的判断。哈迪曾经指出,我们理解概念时的解释往往就是一种价值判断的过程,“价值判断有两种功能,一是‘表达’,一是‘劝说’。可见,理论家们所使用的语言是情感语言,这些情感语言提供的不是信息,而是试图激发听者的情感态度,从情感上影响和劝说他们”。[4]
当幸福作为一种口号或者口号的组成部分被人们陈述的时候,陈述者不论是出于怎样的动机,都定然是受某一先在的价值观的影响进而对某一命题进行判断。而在教育之中,这一价值观念就是某一时期教育研究者们共有的对教育价值的共同判定,来自于各个时代教育的“价值承诺”成为教育为自己赋予的应然使命。而社会历史实践的变迁使得教育这一“能指”在何种“所指”意义上存在成为一个变动的过程,教育承诺也经历着不断的变化。教育承诺的核心是最终价值承受者是谁的问题,而作为参与教育逻辑命题出现的幸福其核心也是解决“教育幸福到底是谁的幸福”的问题,后者必须在前者得到确证的条件下才能提出。如果教育承诺不承认某一主体是价值的承受者,那么讨论这一主体在教育中的幸福就是不合理的、非法的。只有当教育承诺允诺了某一主体的教育价值承受者的地位,幸福问题才能够随之被人们进行讨论。
在教育领域中,教育的价值承诺对于这一主体的划定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纵观整个人类的发展史,在人类文明早期,教育的价值承诺是氏族、部落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保证,个人是作为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得到定义的,这个时候的幸福问题只对共同体有意义,对个人是没有意义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了阶级划分,这个时期教育的价值承诺主要变成了阶级社会再生产的保证。对统治者来说,其统治得以延续是至关重要的,统治阶级中个人的幸福在不损及统治的前提下也得到了认可,而对被统治者来说幸福则是没有意义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不幸地活着或者接受统治阶级灌输的虚假的幸福观念是被统治者可能的两种生存方式。到了近现代以后,个人权利的确证才得以成为一种可能,并强烈地要求教育做出发展、解放每一个人的价值承诺,个体的幸福问题才真正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命题。因此,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被承认,也就历史性地划定了教育中幸福问题的主体,受教育者的幸福问题也才成为教育活动中的核心问题,幸福与否也就必须相对于受教育者个体而做出最终评判。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不能将幸福问题与幸福感问题混同起来,因为幸福感问题首先是一个私人问题,不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标准来界定幸福,有效的幸福问题似乎只能是“我是否幸福”的个体幸福感判断。如果只限于承认这一点,那么教育就不能再对幸福说些什么了,因为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他人的幸福,因此也就无法真正地进行一种幸福的教育。如果真是如此,那也就从根本上否认了教育的合法性。进一步说,如果教育不能给予幸福,那教育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因此,作为一种教育口号的幸福概念,其问题不是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的角度来讨论具体的教育幸福,而是在更为基础的层面上对教育幸福的结构进行阐明,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讨论教育是否以及如何能够保证个体的幸福。基于此我们将教育幸福区分为消极幸福与积极幸福。
二、消极幸福:个体教育幸福的冲突及其解决
贡斯当在阐述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自由的概念时曾指出,现代自由首先是免于被他人剥夺自由权的自由,也就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自由。[5]因此我们在讨论群体幸福的时候不能再以群体发展的名义压制个体的幸福诉求,因为个体相对于群体具有逻辑上的在先性,那么也就意味着在教育幸福的问题上,首要的问题不是如何使个体幸福不断获得的问题,而是如何使每个个体避免不幸的问题,这就必然得出一个消极性的标准:任何人幸福的获得都不得损害他人的幸福。教育存在的理由也可以由此辩护:虽然教育不必然地能够给人事实上的幸福,但是不经过教育个人就无法在社会中有效地进行实践活动,最终个人就会成为他人的负担和不幸。因此教育存在的首要价值不是造就幸福而是预防不幸。
同样的逻辑可以推广到教育个体之间的幸福冲突中去。对于每个人来说,教育幸福总意味着拥有某些东西,每个人的幸福感构成都包含着一定的要素,但却不可能被普遍地满足。“每个人在事实上总会有着某种程度的生活欠缺,不论我们在主观上是否感觉到这一欠缺,幸福在客观上总是多多益善的。”[6]这些幸福索求之间必然地有所冲突,从而幸福必然是一种结构性的匮乏。教育中通常的方法是进行所谓的幸福观教育,用“较好的”幸福观取代“不正确的”幸福观,但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个体幸福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矛盾。幸福观教育不能消解教育幸福的结构性冲突问题。而且这些幸福观教育常常有以更高的幸福代替低级幸福的思想倾向,希望通过鼓励追求更高幸福来规避当下幸福追求受挫带来的不幸体验。但是当受教育者追问“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一套幸福观念”时,教育者总是无法给出逻辑上有效的理由。培根对这样的教条式的方法有过尖锐的批判:“还有一类假象是从哲学的各种各样的教条以及一些错误的论证法则移植到人们心中的。我称这些为剧场的假象;因为在我看来,一切公认的学说体系只不过是许多舞台戏剧,表现着人们自己依照虚构的布景的式样而创造出来的一些世界。”[7]在教育实践中,必须在实践中有效地回应这种结构性冲突,否则教育幸福就是结构上不可能的东西了。对单个人来说,绝对的幸福是不被允许的,这会必然地导致他人幸福的损害。因此,幸福问题就必然从“不损及他人幸福”的反方向进行考察。这种反向的考察实质就是将他人的幸福考虑进去,这可以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金律的讨论进行说明,因为这一规则将自己所不欲的确定为不能给别人的,所以当规则成立的时候,你所给别人的东西也就是别人可以随时回敬你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不会给你造成麻烦。这也与康德的“律令普遍化”的处理相似:我们必须衡量我们的规范能否适用于包括自己的所有人,最起码能被别人反过来用于自己身上。正如当人们在生活中追逐利益时,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合法的,但是其前提条件是不损及他人的利益,否则他人也就可以损及你的利益,最终变成弱肉强食的状态。同样,在教育中,个体追求幸福的最大化必须有一前提制约,这一前提就是不损及他人的幸福,否则也会形成教育的弱肉强食。
人首要的“不欲”不是所欲的东西得不到,而是理该由自己获得的东西被他人得到,因此教育幸福问题在逻辑上首先是教育的公平问题。教育公平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各种显性教育资源的分配,也包括课堂中的教师关心、帮助、人格尊重等隐性教育资源的分配。这一原则也可以从反面进一步阐述为一个受教育者在遭遇种种教育不公平之后,即使他最后获得了幸福感,他的幸福也不能够成为这种不公平的合法证明。公平性的幸福是消极意义上的幸福,但也是绝对意义上不可被损害、牺牲、替换的幸福。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消极意义上的教育幸福是一种对公平的确认,是教育幸福能够成立的结构性要求。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一层结构虽然可以为教育提供存在的意义和预防个体的不幸,但是这一层结构只是说明了个体幸福并存时的社会性问题,而非解决个体幸福的私人性问题。而在确保消极意义上的教育幸福基础上,我们还需要教育能够提供一种积极的幸福。
三、积极幸福:作为扩展个人幸福可能的教育
如前所述,不造成他人的不幸和不被他人损害我的幸福都不是幸福问题的全部。幸福问题既是一个公共问题也是一个私人问题,作为前者,必须保证一种教育的公平性,而作为后者,则要确保一种个体幸福的能力。
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我们只能有效地进行“我是否幸福”这样的判断,而无法进行“他是否幸福”的判断。虽然你可以说“他很幸福”,其含义也不过是一个感慨而非逻辑的有效判断,表达的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自己的幸福观念在他人身上的投影,是否幸福的命题只能由提出命题的个体自己给出解答。但是,幸福作为一种教育口号绝不会仅仅满足于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消极意义上的教育幸福即使有价值,也不能成为教育所追求的理想状态,教育总需要在不损及别人幸福这一规则之上给自己更多的价值负载。而同时个人在不损及他人的前提下也需要最大限度地完成自己存在的意义与幸福。但是如前所述,我们不能从具体的个体幸福来阐述教育幸福,而教育幸福必须是基于一个普遍结构性的阐释,笔者认为这一阐释只能是来自于教育能够为受教育者扩展幸福的可能这一事实。
教育中的人是未完成的人,“在夸美纽斯的伟大而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已把人理解为‘可教育的动物’,‘实际上,人不受教育就不能成为一个人’。康德所讲授的教育学,其论点也是‘人是唯一必须受教育的造物’”。[8]任何教育的前提都必须承认人的可教育性的假定,而可教育性也能置换成关于幸福的教育陈述:教育能够形成人本身,这种改变可以成为现在和未来的一种幸福。杜威在论述“教育即生长”的观点时也曾经说过,“生长的首要条件是未成熟状态。……我们说未成熟状态就是有生长的可能性。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指现在没有能力,到了后来才会有;我们表示现在就有一种确实存在的势力——即发展的能力”。[9]发展的问题同样也是幸福的问题,教育能够承诺多大程度的幸福就在于它能够为个人幸福扩展多大的领域,并在何种程度上形成一个能够获得幸福的人。
因此,教育幸福的积极方面的含义就是:个人幸福可能的扩展。这也是幸福问题在教育领域与其他生活领域的重要差异。在其他的领域,幸福问题是一个面对过去的问题,幸福判断主要是作为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过去生活的综合判断,而在教育领域,幸福问题则主要是在一个从现在延伸出去的未来如何展开的问题。前者更为重视一种实然性,后者则更重视一种可能性。从这一角度来说,幸福一词作为一种教育口号,就不能够仅仅着眼于受教育个体的幸福感问题,而更为重要的是考察教育实践在为个人提供幸福可能的过程中对于扩展个体的幸福可能具有怎样的意义。
“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生活动力,这是一个明显的真理。如果不去或不能追求幸福,生活就毫无意义。”[10]不去追求幸福和不能追求幸福的性质不同,前者是一种行为的选择,自愿放弃了对幸福的追求,而后者则或是由于不幸而丧失了追求幸福的可能,抑或是不具备幸福的能力。如前所述,不幸是教育必须消除的东西,不能够成为通向幸福的障碍,而幸福的能力则是教育必须积极促成的东西,没有它则幸福不可企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现代社会由于分工的深入,也由于人的生活各个领域的不断扩展,每个人能够实现自己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可能选择也就扩大了起来。虽然马克思批判了日益严重的分工带来的异化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分工与新的生活方式的扩展创造出了人们新的生活领域和生活方式,对人的潜能来说则意味着有了更多的幸福选择。
正因为教育对于获得幸福意义重大,幸福的口号在教育领域获得了极大的认同,虽然对于幸福究竟是何涵义难以获得一致的看法,但并不妨碍这一口号的使用。而在使用中,不论幸福是何具体含义,也总要含有“接受教育比不接受教育的更接近幸福”的意思,否则如果承认了不接受教育可能比受了教育更容易获得幸福,那么这一口号就失去了作为口号的实践基础和存在意义。而“接受教育比不接受教育的更易获得幸福”能够被大家自然接受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育扩展了个体进行生活的空间和多样性,套用赵汀阳先生的表述就是为受教育者指出更多的“可能生活”,为受教育者开辟出更多的获得幸福的路径。因此,作为扩展个人幸福可能的教育,其能够顺利地实现其价值承诺就成为判断教育是否导向幸福的重要尺度。同样的,将教育的幸福问题在积极的意义上表述为扩展受教育者的幸福可能,也能够对当下过分关注当下教育过程幸福感的一些教育口号的缺陷进行有效的分析。教育幸福面对的是学生的幸福可能,因而在本质上是走向未来的,关注于教育的当下幸福虽然合理但不充分,“当下生活既不是丢掉过去也不是遗失未来。假如过去和未来没有加强现在的话,那么就毁灭了现在。”[11]如果将眼光仅仅放在当下的幸福问题上,就损害了受教育者的未来幸福。教育面对的是未完成的人,当下的幸福如果不能为未来幸福开拓疆界,那么所谓的当下幸福也就不过是成为了一种快乐或者快感而已。当下的幸福是重要的,但不是教育的最重要问题,教育对于幸福的价值不能够在当下的教育生活中得到充分的表达,但却真实地塑造着学生的未来生活。只有理解和践行这种现实教育的未来性维度及其意义,未来的教育幸福也才真正有可能成为现实。
[1]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66.
[2][4]唐莹.元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135,125.
[3][7][英]培根.新工具[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第一卷41节,44节.
[5][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M].阎克文、刘满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4-46.
[6][10]赵汀阳.论可能生活[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151,143.
[8][德]博尔诺夫.教育人类学[M].李其龙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35.
[9][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9.
[11][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41.
(责任编辑:刘丙元)
韩登亮/聊城大学教科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复杂中的适应:基础教育学校变革研究”(编号:12YJA880039)、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教师职业道德的制度规约与自主责任感的培养”(编号:2010GZ072)、聊城大学博士基金项目“山东省农村教师专业发展与服务支持体系研究”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