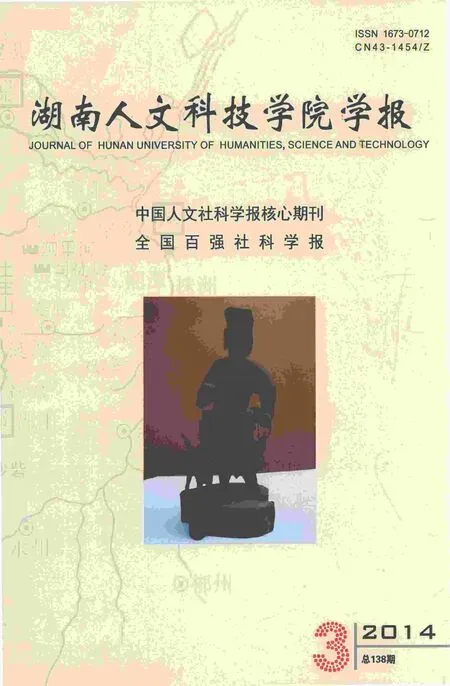“数+量+动”结构的名词性及其生成机制
闫亚平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对于“数词”、“量词”、“动词”三者之间搭配问题的研究,人们更多地关注“动+数+量”,如“看一遍”、“来一趟”、“打一枪”、“踢一脚”等,而很少注意到“数+量+动”。其实,在语言实践中,除了“动+数+量”结构,还存在着“数+量+动”组合。比如:
例1 养鸭是一种游离,一种放逐,一种流浪。(汪曾祺《鸡鸭名家》)
例2 咱们应该牢记一点:报纸的目的,一般来说并不是想探讨事情的真相和原因,而是想炮制一种观点,制造出一场轰动来。(北大语料库)
例3 台下一片哄笑。(北大语料库)
例4 窗户一阵震颤,接着是此起彼伏的汽车警笛声。(北大语料库)
例5 一种分析认为,这支多国部队主要起“威慑力量”作用,人数可减为1.6万到2万人,其中美军4 000人到5 000人。(北大语料库)
例6 该飞机起飞后只好使用其他发动机飞行,并于9时11分被迫返回羽田机场紧急着陆。一场虚惊才告了结。(北大语料库)
例1中“一种游离”、“一种放逐”、“一种流浪”为“数+名量+动”做宾语;例2中“一场轰动”为“数+动量+动”做宾语;例3中“一片哄笑”为“数+名量+动”做谓语;例4中“一阵震颤”为“数+动量+动”做谓语;例5中“一种分析”为“数+名量+动”做主语;例6中“一场虚惊”为“数+动量+动”做主语。可见,我们所分析的“数+量+动”结构实质上是“数+量”作定语直接修饰“动词”,且能单独充当句法成分,而像“一脚猛踢”、“一把抓住”、“一口吃完”等则不属于我们所要探讨的范围。
一“数+量+动”结构的句法功能
据我们对北京大学CCL语料库(网络版)中“数+量+动”结构的统计,发现现代汉语中“数+量+动”结构主要充当3种句法成分。
(一)宾语
“数+量+动”结构充当宾语的居多。比如:
例7 默默无语里,胡兰成重重握了她的手,像是感谢,像是知恩,亦像是一种倾诉。(北大语料库)
例8 果然,海瑞这道奏章在朝廷引起了一场轰动。(北大语料库)
例9 于是我们落泪了,为了一种付出,一种坚强,一种升华,还有我们格外渴望也不愿失落的那种爱!(北大语料库)
例10 在一阵骚动之后,忽然全部匆匆撤退走了。(北大语料库)
例7中“一种倾诉”为“数+名量+动”结构,作动词“是”的宾语;例8中“一场轰动”为“数+动量+动”结构,作动词“引起”的宾语;例9中“一种付出”、“一种升华”为“数+名量+动”结构,作了介词“为了”的宾语;例10中“一阵骚动”为“数+动量+动”结构,作了介词“在”的宾语。
(二)主语
“数+量+动”结构也可以充当主语。比如:
例11 两种分析都成立。(北大语料库)
例12 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西安事变”前的两场虚惊,差点破坏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计划。(北大语料库)
例11中“两种分析”为“数+名量+动”结构。例12中“两场虚惊”为“数+动量+动”结构,分别作了全句的主语。
(三)谓语
“数+量+动”结构还可以充当谓语。比如:
例13 台上台下一片唏嘘。(北大语料库)
例14 刘勋苍朝着杨子荣一摆手,大家一阵哄笑。(北大语料库)
例13中的“一片唏嘘”为“数+名量+动”结构作谓语;例14中的“一阵哄笑”为“数+动量+动”结构作谓语。
二 “数+量+动”中“动”及整个结构的名词性
田文玉指出:“一量加VP”结构,当“中心语是动词,其本身具有动词性,表动作、行为或心理活动,在句中充当主、宾语时,具有了名词性,表示一种被述说或关涉的事物”[1]134。的确,在“数+量+动”结构中,“动词”不再表示具体的动作、行为,而被看成一种抽象的实体,成为“数+量”计量的对象,具有了一种名词性,整个短语也表现出明显的名词性。这一点在“数+量+动”结构作主语和宾语时,表现得更加明显。比如:
例15 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北大语料库)
例16 当他打开饭厅的大门时,一阵哄笑冲他而来,这是他万万意料不到的。(北大语料库)
例17 我深知过重的精神负荷在一个封闭的心灵里会有崩溃的危机,写作是一种释放,在一个社会生活发生空前巨变的时代写诗,我们这一代诗人承受着更为多变的压力。(北大语料库)
例18 所以15个小项目的比赛中均成绩平平亦在人们意料之中,也可以说,这次比赛只是对参赛者的一次锻炼。(北大语料库)
例15中的动词“表达”原本指的是将思维所得的成果用语言、表情、行为等方式反映出来的一种行为。如在“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这句话中动词“表达”表示主语“他”所发出的一种行为。而在例15并没有突出它的动作义,而是被看成一种抽象的实体,成为“一种”计量的对象,具有了名词性。整个短语充当被陈述的对象,带有明显的名词性。例16中的“哄笑”原本也是表示一种动作行为,如在“记者当场哄笑”这句话中就表示主语“记者”发出的一种动作行为。而在例16并不表示具体的动作行为,而是被看成一种实体,受“一阵”的计量,具有了名词性。整个短语充当被陈述的对象,带有明显的名词性。例17中的“释放”原本也是表动作、行为的,如在“他们释放了一种有毒气体”这句话中动词“释放”就表示把有毒气体放出来。而在例17里动词“释放”成了计量的对象,意义上被看成一种抽象的实体,具有了名词性。整个短语成为动词“是”关涉的对象,具有明显的名词性;相应地,例18中“锻炼”这个动词也表示一种动作行为,如在“他锻炼身体”这句话中就表示主语“他”所发出的动作。而在例18里却不突显这种动作义,而是被当成一种实体,具有了名词性。整个短语作为动词“是”关涉的对象,也表现出明显的名词性。
其实,这种情况在“数+量+动”结构作谓语时,也有所表现。比如:
例19 伦敦一片轰动,人人在猜测匿名的作者是谁。(北大语料库)
例20 八大金刚一阵狂笑。(北大语料库)
虽然,在例 19、例 20中“数 +量 +动”结构——“一片轰动”、“一阵狂笑”分别作了谓语,由于受更大构式的影响、制约,动词“轰动”、“狂笑”表现出了一定的陈述性,但也与相应动词直接作谓语有着一定的差异。试把例19、例20与下面两例做一比较:
例21 这件事轰动了当时的科学界。
例22 鬼子们得意地狂笑。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动词直接作谓语,如例21、例22,整个句子是叙述性的,叙述与主语有关的动作行为。而一旦形成“数+量+动”结构作谓语,如例19、例20,整个句子就变成描写性的了。因为形成“数+量+动”这样的组合作谓语后,其中的“动”和整个短语还带有一定的名词性。因此,看到例19、例20,我们第一时间想起的应是类似如下这样的例句。
例23 屋外一片月光。
例24 脸上一副苦相。
我们把例19、20和例23、24作一对比,发现它们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意义上都比较接近,即都是通过形成“一+量+名/动”结构充当谓语,整个句子是描写性的,而不是叙述性的。
三 “数+量+动”中“动”及整个结构名词性的由来
(一)“数+量+动”的由来:构式的继承与引申
构式语法认为,构式是语言和语言研究的基本单位。其特点为形式和意义的对应体,而且其意义不能完全从其组成成分或其他构式中推导出来。一个新构式,或者确切地说一个非典型构式,并不会凭空产生,而是人们根据典型构式创新而来。那么,“数+量+动”作为一种超常搭配,作为
一种非典型构式,其相应的典型构式是什么呢?
其相应的典型构式为“数+量+名”。正如盛林所说:“在计量事物时,量词与数词、名词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没有数词,仅单位无从表量,没有名词,则没有计量对象。所以,数·量·名的结合就成为汉语中一种最典型的表量结构。这种表量结构在汉语中非常活跃和常见,以至于人们在判断量词的时候,也习惯于用这一结构作为标准。”[2]同时,大部分《现代汉语》教材都把“能受数量短语修饰”作为判断名词的一个标准,也有力说明了“数+量+名”这一构式的典型性。
由于构式具有动态性和能产性,所以,为了描述在客观世界的经验,为了满足表达的需求,人们在典型构式“数+量+名”的影响下,又造出了非典型构式“数+量+动”。
构式的意义不可能凭空产生。那么,其意义是怎样产生的呢?构式语法认为,构式的形成是心理固化过程和联想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对语言实际使用的抽象概括。Glodberg等发现论元结构的意义起源于该论元结构中出现频率高、儿童较早习得的某些特定动词。儿童基于这些特定动词对该论元结构的意义进行概括,逐渐把概括出来的抽象意义赋予这种论元结构,并用于理解其他同样结构的句子[3]。也就是认为构式义的形成基于其中的典型构式及典型构式中的某些典型成分。而一旦在典型构式的基础上形成整个构式的构式义,人们就会用它来理解其他同样的结构,比如说非典型构式。
因此,人们在某些特定名词的基础上对典型构式“数+量+名”的意义进行抽象概括,并逐渐把概括出来的抽象意义赋予“数+量+X”结构,用于理解其他非典型构式,如“数+量+动”,从而形成包括“数 +量 +名”、“数 +量 +动”等在内的“数+量+X”的构式义,即:1.“数+量”对“X”进行计量;2.构式整体上是名词性的,且这种名词性不随其内部成分的变化而变化;3.X位置上的词语在该构式的层面上表现为名词性,而在语义层面上这个位置上的词语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形容词等。
可见,“数+量+动”中“动词”及整个结构的名词性是构式赋予的,是构式压制的结果。
(二)“数+量+动”成立的机制:构式压制
为了提高自身的解释力,获得对语言现象的统一阐释,构式语法理论非常关注那些被传统语法称为“特殊现象”、“边缘现象”或“偶发现象”的例证,并进一步提出了“构式压制”概念。Goldberg主要从“构式”可对“动词”产生压制的角度指出,构式通过对词项施压可使其产生跟系统相关联的新的意义[4]。Michaelis认为压制是当构式框架和填充词汇发生冲突时,人们通过语义转换等认知方式进行协调而满足该构式的句法规约[5]。王寅指出:“压制主要指当词汇义与结构义发生‘语义冲突’或两者‘误配’或‘不兼容’时,此时潜在性句法环境就会产生一个‘压制因子’,它会对词汇义产生强制性影响,即当两者产生冲突时,解释者常须根据构式义对词语义做出‘另样解释’或‘不同解释’,以能使两者相互适应或协同,从而就可获得对词组和分句的合理解读”[6]。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施春宏强调指出“构式压制”当理解为:“在词项进入构式的过程中,如果词项的功能及意义跟构式的原型功能及意义不相吻合,那么构式就会通过调整词项所能凸显的侧面来使构式和词项两相契合”[7]。也就是说经过构式压制,使得非典型构式中相关成分在词类和意义上的矛盾和冲突得到消解。正如袁野所指出的:“压制现象正是解决构式和词汇间矛盾的结果,比如主动词通常具有的价数与其所在的句法结构具有的论元数不等的现象:The boss barked the workers to work,即一价动词bark用在了二价的致使结构中,从而产生了构式图式对动词的压制”[8]。被Goldberg频繁引用并广为人知的例证是:
例25 Pat sneezed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
“sneeze”原本是不及物动词,在例25中却带上了宾语,并产生了“致使X移向Y”这样的意义。Goldberg认为这种功能和意义并不是“sneeze”本身具备的,而是由这个构式赋予它的,是构式压制的结果。因为此构式的原型为致使结构,其本身就具有致使—移动义。
那么,由于非典型构式“数+量+动”中的“动词”与“数+量+X”整体上的名词性相冲突,该构式义通过构式压制促使其中的“动词”产生名词性的意义,从而消解了构式义和词项的矛盾。
“动词”为什么能被压制出名词性的意义来呢?认知语法认为一个表达式的意义是由概念内容和对概念内容的识解共同构成的。同样的概念内容由于识解方式的不同而会产生不同的意义。Langacker把人类的识解方式分为整体扫描和顺序扫描[9]。牛然明、高德文进一步阐释为:“前者指一系列成分状态在表征时间内持续的变化过程,后一成分状态的形成预示着前一个成分状态的消失,其结果是凸显一个过程;而后者是一种积累式的扫描,各个成分状态因被同时激活而共存,形成一个完型,即一个抽象的实体。例如:动词“enter”凸显一个射体从一个空间外到该空间内的一个过程,其中包括无数个成分状态,属于顺序扫描,而名词“entrance”则同时激活了“进入”这个过程的所有的成分状态并使它们共同存在,从而构成了一个抽象的实体”[10]。在概念内容上,Langacker认为名词性成分在图式层面上凸显某个认知域中的一个区域,它由一组相互联系的实体构成;动词性成分凸显一个过程,由一组互联的关系或成分动作构成[11]。可见,通常情况下,名词是以整体扫描的方式,形成一个整体性的格式塔/完型,即一个抽象的实体;动词通过顺序扫描而凸显过程。
但在“数+量+动”结构中,其中的“动词”由于受整个构式名词性的制约,其识解方式为整体扫描而不再是通常情况下的顺序扫描。在整体扫描的认知方式下,随着时间延续的具有过程性的动作被识解为一个整体,在人的大脑中形成一个完型,即一个抽象的实体,具有了物性。也就是说一个过程进入了一次认知过程的注意中心,被认知者当作一个存在物(事物)来对待。这样其中的“动词”就临时具有了名词性的意义。可见,一个表达式的语法范畴并不完全取决于其所映射的概念内容,而是由概念内容和施加于概念内容之上的具体的识解方式共同决定。
当然,不同的动词能被压制出名词性意义的程度是不同的。相比较而言,双音节动词优先于单音节动词。通过我们对北京大学CCL语料库(网络版)中“数+量+动”结构的统计,发现能进入“数+量+动”结构的无一例为单音节动词。可见,单双音节动词的名词性程度是有差别的。
四 结语
综上所述,在典型构式“数+量+名”的基础上形成汉语中“数+量+X”构式的构式义,即:1.“数+量”对“X”进行计量;2.构式整体上是名词性的,且这种名词性不随其内部成分的变化而变化;3.X位置上的词语在该构式的层面上表现为名词性,而在语义层面上这个位置上的词语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形容词等。因此,“数+量+动”作为非典型构式,是典型构式“数+量+名”的继承和引申,其“动词”及整个结构的名词性是“数+量+X”这一构式赋予的,是构式压制的结果。而“动词”之所以能压制出名词性的意义来,与其识解方式的转变有很大关系。
汉语动词“名词化”、“名物化”问题一直是语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12]。对此问题的论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构式语法的出现无疑给我们提供了观察问题的新的视角。虽然它还处于发展过程中,但在相关问题的阐释上还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1]田文玉.略谈“一量定语”的两个问题[J].华中师院学报,1983(5):131-136.
[2]盛林.从单纯表量到多远化表意:试论汉语历时发展中的“数量名”结构[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94-98.
[3]ADELE E G,DEVIN M C,NITYA S.Learning argument structure generalizations[J].Cognitive Linguistics,2001,15(3):286-316.
[4]ADELE E G.构式: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M].吴海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MICHAELIS L A.Type shifting in construction grammar: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a spectual coercion [J].Cognitive Linguistics,2004(15):1 -67.
[6]王寅.构式压制、词汇压制和惯性压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9(12):5 -9.
[7]施春宏.从构式压制看语法和修辞的互动关系[J].当代修辞学,2012(1):1-17.
[8]袁野.构式语法、语言压制现象及转喻修辞[J].当代修辞学,2011(3):40-48.
[9]LANGACKER R W.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volumeⅠ[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10]牛然明,高德文.汉语“NP的VP”构式的构式语法新探[J].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5):10-28.
[11]LANGACKER R W.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practical applications volumeⅡ[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12]胡裕树,范晓.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和“名词化”[J].中国语文,1994(2):81 -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