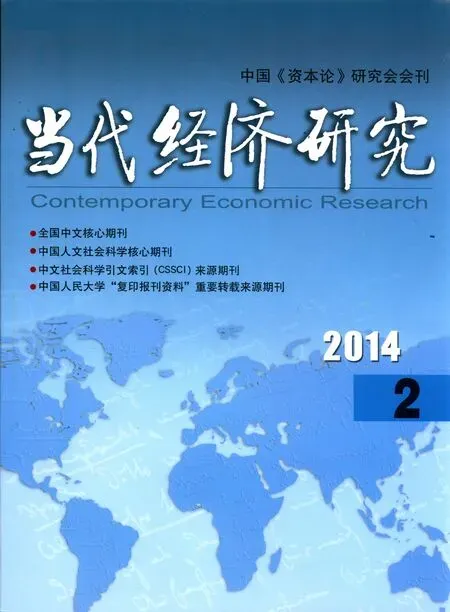美国学界关于社会不平等的争论
于海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美国学界关于社会不平等的争论
于海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收入与财富不平等成为美国首要的社会问题,并引发学界的反思与争论。作为当代美国主流思想左、右翼的理论代表,自由派与保守派学者在与社会不平等相关的诸多问题上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种认识上的冲突和对立,是当前美国社会矛盾激化的集中体现,也深刻反映了两派学者的思想理念之争。其中,自由派的观点更多地维护了中下层劳动阶级的利益,具有进步意义,但由于缺乏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入认识和批判,不可能对社会不平等问题提出具有实质意义的解决方案。
美国;保守派;自由派;不平等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伴随西方经济形势持续恶化以及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凸显,不平等问题重新回归美国社会的视野。近一年多来,“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爆发与蔓延、各大机构一系列最新研究数据的相继公布,以及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大选年围绕向富人增税的“巴菲特规则”的激烈论争,更是将收入不平等话题推向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也引发西方学界的深刻反思。在美国,关注政治和社会平等、主张机会均等、捍卫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自由派学者,与倾向个人自由、维护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制度、倡导新自由主义的保守派学者,甚至展开了一场大论战。他们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阐发自己对不平等问题的认识,围绕当代美国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问题进行思想论辩和交锋。
一、美国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到底有多大
自由派和保守派学者都承认,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各阶级,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与极少数上层阶级,在收入和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差距扩大了。但是,二者间到底存在多大程度的差距,不同立场的学者看法不一。
自由派学者强调,战后长期以来生产率增长与工资增长间的联系,已经被打破了。在过去30年间,剥削率大大上升,美国社会从中受益的人群只有1%。2000年以来,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①等关于顶层收入者的相关研究,为自由派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他们通过对美国国税局历年发布的统计数据的分析发现,1980年代中期后,美国顶层家庭收入所占份额急剧扩大。到2007年,顶层1%家庭占有的收入份额约达到24%,为1928年即大萧条开始前一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从未超过10%,一直徘徊在7.7% ~9.8%之间。[1]
早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保守派经济学家就一直在驳斥赛斯的数据,批评其采用的是税前收入,因而没有表明联邦政府以累进税、社会保险和所得税抵免等支付形式进行的货币再分配对富人的影响。[2]康奈尔大学教授理查德·伯克豪瑟(Richard Burkhauser)等指出,如果采用税后的收入,并将政府的货币转移也包括在内,差距并没有那么大。如1979~2007年间,美国收入分布顶层20%人群的收入增加了49%,而中间20%家庭的收入也几乎增加了30%。[3]
2011年以来,一些无派别倾向的组织机构相继发布一批最新统计数据,与保守派的统计结果针锋相对。如2011年10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 Budget Office)公布的数据表明:“1979~2007年间,1%最高收入者的平均税后家庭实际收入攀升了275%,而中间3/5的人口只增长了不到40%”;“顶层20%人口的税后实际收入增长了10个百分点,其中绝大部分又流向了1%的最高收入人群,其他各部分人群所占收入份额则下降了2~3个百分点”。[4]美国人口普查局(U.S.Census Bureau)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在2010年的家庭总收入中,20%最富有的家庭占50.2%,20%最贫困的家庭只占3.3%。而1980年,即所谓“里根革命”开始之初,二者所占份额分别是44.1%和4.2%。也就是说,在这30年间,最贫困家庭的收入减少了21.4%,最富裕的家庭收入增加了13.8%。而其他各20%的家庭所占收入份额,都有不同程度减少。美国人口普查局还对顶层5%家庭进行统计,其所占收入份额,从1980年的16.5%增加到2010年的21.3%,即增长率达到29.1%。到2010年时,顶层5%家庭所占收入份额要大于底层50%的家庭总和。[5]
这些新数据被自由派学者广泛引用,用以批评和指责当代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和收入不平等,而保守派则继续撰文质疑和攻击这些数字的准确性。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罗恩·哈斯金斯(Ron Haskins)认为,关于收入不平等急剧增长的指控,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或具有误导性,美国贫富差距并不如想象般巨大。他的依据除了前文所说税收等对富人收入的影响没有计算在内之外,还强调,作为中低阶层美国人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非现金津贴,如食物券、收入税抵免以及为儿童提供早期教育的“启蒙计划”(Head Start)和帮助低收入家庭子女上大学的“佩尔助学金计划”(Pell Grants),都没有纳入统计之中,这些津贴实际上每年需花费9000亿美元。[6]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的戴安娜·弗奇戈特·罗思(D.Furchtgott-Roth)认为,收入差距扩大的误导因素还包括高收入双职工家庭和低收入单身家庭的增加,以及1986年美国税改以来,税法变化带来的以企业标准收税转向以个人标准收税造成的影响。[7]
二、不平等是“好事”还是“坏事”
保守派学者认为,不平等反映的主要是人们在努力程度和天生才能等方面的差异,因此收入不平等是件好事。它能够促使人们努力地改变现状,而如果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收入、地位、声望和其他报酬,多数人将很难产生奋发向上的动力。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米歇尔·坦纳(Michael Tanner)这样比喻说,经济决非一块具有固定尺寸的蛋糕,不是一个人分的蛋糕越大,其他人得到的就越少。这块蛋糕的尺寸是无限的。但为了让蛋糕变大,需要让人们成为有雄心、有技能的风险承担者,需要人们为更大的分享而努力奋斗。这意味着他们必然因其努力、技能、雄心以及承担的风险,而得到回报,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大的不平等。他引用哈耶克的话总结道:“我们期望实现的经济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不平等的结果”。我们寻求的是一种更少贫困的繁荣和不断增长的经济,其中每个人都能因其才华和本能而实现自身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谁还需要平等呢?[8]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丹尼尔·黑尔(Daniel Heil)也表达了同样观点。他指出,如果不平等的发生是受更专业化的经济驱动,人们因为自己的生产而赚了大钱,并且能够像“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之类的企业家一样,为人们创造有价值的产品和就业,那么不平等就是一件好事,人们应为此欢欣鼓舞。[9]
显然,在保守派那里,“机会平等”远比“结果平等”重要。美国企业研究所总裁亚瑟·布鲁克斯(Arthur Brooks)这样说,我们支持平等,但这是支持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如果你是占70%的多数人,你应当相信每个人都有机会成功。占30%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则更不喜欢因无视个人努力程度和个人才能,而最终实现经济地位的大致平等。公正不是他们的王牌,而是其阿喀琉斯之踵。收入平等不是公正,而明显是不公正。[10]一些保守派也倾向于此,认为只要人们在整个一生中能够有机会增加收入,能够比父辈生活得更好,这个体系就是有效的。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近年出版的著作,通过分析美国社会较高的社会流动性,证明现行体系运行的有效性。他发现,多数美国人最后达到的薪资水平,往往会高于其最初阶段,“在1975年收入排在全国最后20%的人当中,有四分之三的人的收入在16年后上升到了全国的40%。”[11]136
自由派学者反对以个人能力和努力来界定不平等,认为天生的不平等制约着机会平等的实现。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美国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他认为,美国社会的突出特点,表现为出身至关重要,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几乎没有机会爬到社会中层,更不用说社会顶层。以来自社会底层的孩子为例,他们即便与那些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相比,具有相同或者更高的天资,并且通过努力上了好的大学,但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因而更加容易辍学。因此,在美国现实社会中,小霍雷肖·阿尔杰式的穷人孩子,最后成功的故事远没有传奇中那么普遍。[12]2012年1月,在政府智囊机构“美国进步中心”发表的演讲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在分析美国的阶级不平等状况后认为,美国社会的高度不平等使代际流动水平较低,从而形成了一个“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Great Gatsby Curve)。即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将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他预测,到2035年,美国的代际流动甚至会比现在还少,那时个人出生时的阶级地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未来的经济前景。[13]
与保守派相比,自由派学者更加关注和重视分配,强调如果把经济比作一块大蛋糕,富人分享的越多,其他人分享的就越少。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于政策的钟摆越来越偏向富人一边,富人获得的蛋糕越来越大,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中产阶级”不断萎缩,作为当代美国政治标签的“美国梦”已经破灭。在上文提及的演讲中,克鲁格高调指出由收入分配的“两极化”造成的中产阶级萎缩的问题。他以家庭收入达到中等收入作为中产阶级的统计标准,指出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数量从20世纪70年代的50.3%,下降到2000年的44.2%,而2010年只有42.2%。[13]加利福尼亚大学劳动经济学家西尔维亚·艾勒格里托(Sylvia Allegretto)也认为,在战后30年间,中产阶级的工资增长一直与生产力增长保持一致,但此后中产阶级的收入已经大大滞后于生产力增长的水平。其标志性指标是CEO的工资。20世纪70年代,它们只是普通工人工资的24倍,而今天已经达到300倍。[14]
三、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根源何在
关于造成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原因,美国学界长期存在争论,三种观点一直占据主导。
(一)全球化论
这种观点认为,全球化造成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究其原因,一是非技术移民直接参与工作竞争,而远在其他国家的非技术工人也通过贸易间接地参与到竞争之中,两者共同压低了美国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尤其因为这些非技术移民基本上位于收入分布的底部,从而使得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更加严重。[15]43二是全球化直接经由贸易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离岸业务等渠道,对美国的收入分配造成显著影响。[16]
(二)技术进步论
这种观点强调,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扩大源于经济结构变化,主要是新科技革命的兴起,提高了对高技术工人的需求量,造成“知识工人阶级”收入激增,拉大了与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差距。但也有学者认为,技术变革实际上很难与全球化模式分割开来,因为全球化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技术的重要性。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B.Freeman)指出,技术进步隐藏在分散的经济活动以及离岸生产背后,“离岸生产与数字化共生共存”。[17]
作为技术进步论的延伸,近些年美国保守派中逐渐流行起一种说法,认为教育在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哈佛大学高级专家史蒂文·施特劳斯(Steven Strauss)甚至认为,受教育水平影响将美国分割成了两个经济上迥然相异的国家。他对不同职业人群的收入进行对比后发现,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就越高。如拥有专业学位的人,收入能够达到非高中毕业生的6倍,2009年二者的收入分别是12.8万美元和2万美元。而且,受教育水平也与失业率直接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失业率越低。过去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非高中毕业生的失业率在7%~15%间浮动。而那些拥有大学文凭的人,在当前经济危机下的失业率为4.5%,只是美国整体失业水平的一半。这样,美国经济创造了两个分裂的社会:一是受教育水平较低者,工作缺乏稳定性,不断经历着衰退和萧条;二是受教育水平较高者,拥有的财富在不断增加,工作受经济衰退的影响很小,个人发展前景良好。这种趋势反过来又对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2000年美国大学入学率只有63%,2009年这一数字约为70%。[18]
自由派学者反对教育决定论。他们虽然承认更好的教育终将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但强调教育并不具有决定意义,教育既不能解决失业问题,也不能缩小收入差距。劳伦斯·米歇尔(Lawrence Mishel)运用大量数据分析美国失业问题,得出一个大胆而极富说服力的结论——美国的失业并非结构性失业,而是周期性失业。周期性失业意味着今天的失业者,最终能够依靠其掌握的技能在各自的产业部门找到工作,意味着教育对于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没有大的帮助。同时,大量数据也表明,教育与收入不平等问题无关。即使拥有大学甚至更高学历,也不能保证在前10%收入者中获得一席之地。在过去15年间,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但无论大学毕业生还是高中毕业生,他们的单位时间工资补偿都没有任何实质性增加。[19]克鲁格曼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如果把所有问题归结为教育,那么不平等就成为一种供需关系的结果。这样,解决不平等的方式就成了改善教育体制,没有人会因为日益扩大的不平等而受到指责。[20]
(三)制度政策说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呢?自由派学者主张制度政策说,这也是美国学界关于收入不平等原因的第三种具有影响力的观点。在自由派学者看来,政策选择、规则和制度的作用非常关键,它们既能塑造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能通过产品市场的解除管制,以及社会支付、工资设置机制或工人协商权的变化,对收入分配产生直接影响。耶鲁大学教授雅各布·汉克(Jacob Hacker)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指出,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根源主要在于“政治”,是政治决策在塑造市场时偏向特权阶层、牺牲公众利益的结果。
他们认为,有三个“政治”层面共同推动了这种政治决策的形成。一是政策安排(policy-setting),这一点最重要。其中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各种影响人们生活的政策决策都是由政府制定的。二是“制度”(institution)。通过“否决点”的塑造,制度规则让行为者有机会通过其希望通过的政策,阻止其不希望实施的政策。三是“组织”(organization)。组织在促进政策变化中具有关键作用,而当前美国的组织环境极具偏向性。许多代表商业和富人利益的组织异常强大,并且因其拥有的各种资源而受到政治家的关注和青睐;而工会的持续性衰落,致使代表穷人和中产阶级的那些组织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弱小。这三个政治层面,共同促成了导致更大不平等的体制性政治偏向。总之,各种不同形式的组织及其围绕政策安排和选举进行的斗争,构建起美国的政治冲突,而美国的政治制度,则有利于那些代表富人利益的组织及其联盟推行捍卫自身利益的新政策并重塑市场。[21]
与这种政治结构决定论的视角不同,同为自由派学者的克鲁格曼,更加强调新自由主义政策选择的作用和影响。他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鼓励或允许”高度不平等的保守主义运动,才是美国不平等增长的真正原因。在他看来,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决非偶然,正是二战期间政府采取的政策,如战时工资管制带来的收入“大压缩”,以及其后长期奉行的社会制度和规范,促使美国社会实现了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镀金年代”的极端不平等,向战后相对平等的转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主张自由市场的“华盛顿共识”取代了推动底层阶级收入增长超过了上层阶级的《底特律条约》(the Treaty of Detroit),②一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出现了:绝大多数工人不再能够分享生产力增长的收益,而“富人们变得心满意足”。社会不平等越来越大,贫富分化也越来越严重。[22]
四、如何解决当前美国社会的不平等问题
围绕不平等问题解决方案,美国保守派与自由派学者的争论焦点,集中在是否应该对富人增税上。一直以来,保守派针对该问题的观点是建立在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所谓“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基础上的,即对富人减税将有利于创造更多的投资,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最终使所有人都能受益。然而,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以及长期持续的高失业率,证明这一说法难以成立。《财富》、《赫芬顿邮报》等刊物的撰稿人桑杰·桑胡(Sanjay Sanghoee)认为,涓滴思想背后隐藏的议题是不平等的合理化。它把美国工人的福利与富人的“丰裕”直接挂钩,既能保障企业和富人的利益,同时也不必担心来自穷人的过激反应。而实际上,美国经济是建立在不平等金字塔范式基础上的“上滴式”(trickle up)经济,它确保了财富的向上流动而非向下垂滴。他以美国相对高收入的投资银行为例,分析了其内部极端悬殊的收入分布,指出在类似的等级制组织中,财富主要在金字塔顶部集中,位于金字塔底且承担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的人们,只得到极少量财富。虽然与其他行业相比,投资银行从业者总体的收入相对较高,但其内部高低层按比例的差异补偿机制造成了巨大的收入差距。这种差距以指数关系使财富迅速地积累于少数人手中,进一步扩大了财富差距。因此在美国,财富不是垂滴式的而是上滴式的。[23]
前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加利佛尼亚大学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B.莱克(Robert B.Reich)提出了对富人增税的三个理由。一是基于以下需要:缩减长期预算赤字;维持主要公共服务;捍卫社会保障和医疗;增加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不对中产阶级增税。二是当前富人的税率处于历史低点。20世纪40年代至1980年,最高收入者的税率至少是70%,50年代时曾经达到91%,而现在只有35%,即使将税收扣除和信贷因素考虑在内,也比二战后任何时期的收入税率低得多。三是收入的高度集中,也使得富人完全有能力支付增加的税收。他认为,过去几十年的经历表明,对富人减税并没有带来工作岗位的增加,更多的工作机会是中产阶级创造的。“涓滴经济学”完全是一派“胡言”。对富人增税不是保守派所言的“阶级战争”,而是一个人们已经达成的共识。[24]
在这场论战中,“涓滴论”因为在实践中的“失效”,已经很少为保守派所提及。他们更倾向于从教育、文化视角解析社会分裂的根源,强调下层阶级更大的经济流动与对富人的增税并无关系,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收入差距而是文化差距。查尔斯·默雷(Charles Murray)的新著《分裂:美国白人的现状(1960-2010)》,代表了保守派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看法。默雷认为,美国产生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不是收入,而是受教育的上层阶级或“认知精英”(cognitive elite)和下层阶级间的行为差异非常大。他以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居住的两个典型社区Belmont和Fishtown为例,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四种重要社会倾向“婚姻、勤奋、犯罪和虔诚”在两个社区的发展变化进行比较,指出虽然前者在上述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后者面临的冲击显然大得多。如Fishtown有更多的成年人离婚、从未结婚或成为“未婚母亲”。他据此认为,美国下层阶级传统的市民社会纽带已经完全退化了,他们越来越缺乏友善、信任、政治意识和市民参与精神。基于这一认识,他反对自由派学者提出的增加福利支出以及对富人增税等解决不平等的方案,强调20世纪60年代“伟大社会”时代(Great Society)的社会福利计划,正是美国工人阶级社会秩序崩溃的根源。因此,他为改善社会不平等开列的处方,也完全迥异于自由派,主张摒弃“新政”和“伟大社会”,而代之以一个能够保证基本收入的体制;同时,尤其要坚守美国生活方式的四个传统支柱“家庭、使命、社区和忠诚”。在他看来,这是自华盛顿以来美国社会规划的真正基石。[25]
除对富人增税外,自由派学者还提出了其它一些具体解决方案。2012年,《新共和》杂志高级编辑蒂莫西·诺亚(Timothy Noah)在《大分裂:美国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危机及其应对》一书中,总结了应对不平等的八项政策方案,主要包括向富人征收重税、削减政府开支、引入更多的技术工人、普及学前教育、对大学收费进行控制、重新监管华尔街、选举民主党总统以及复兴劳工权利等。其中,“强工会”是自由派学者大都赞同的不平等解决之道。[26]克鲁格曼早在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著作中就已指出,工会的衰落与收入不平等存在密切联系。工会不仅给工人带来高工资,也能够鼓励没有工会的那些企业提供良好的工资和福利,因为后者需要与前者争夺优秀的员工。随着工会自里根政府以来的衰落,中产阶级的工资增长也陷入停滞。因此,解决美国的不平等问题,需要重新复兴工会的影响力。[22]
左翼倾向的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新近发布了关于工会衰落与不平等程度扩大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给自由派的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持。该研究认为,1973~2011年间,工会成员从占劳动人口的26.7%下降到13.1%。工会的衰落尤其对男性中等收入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是1978~2011年间约3/4的白领、蓝领男性工资差距扩大的原因,也是超过1/5的高中毕业和大学毕业男性工资差距扩大的原因。工会的衰落削弱了工人在工资、福利和劳动条件上的议价权,限制了无工会公司提高工资和福利,以与有工会公司在竞争员工方面的“溢出效应”。同时,“去工会化”也与全球化、解除管制以及更低的最低工资标准等一道,共同强化了雇主的权力,削弱了中低收入者获得好工作和经济保障的能力。[27]
五、几点看法
首先,美国学界围绕不平等问题的论战,是当前美国社会矛盾冲突激化的集中反映。
自二战后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连续扩张了近30年。在这期间,美国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出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经济的高速发展,改善了大众的生活条件。在1945~1975年间,美国的小时工资迅速增加了250%,加之养老、保险和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物质生活的丰裕以及社会各阶级、阶层在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和差距的缩小,导致整个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呈现缓和趋势。即使60年代后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和学生运动极具社会影响力,但也未能对现实资本主义形成具有威胁的挑战。长期的繁荣似乎已经将人们的不满和愤怒销蚀殆尽,资本主义似乎迎来了“繁花似锦”、“一片光明”的发展前景。
与之呼应,关于“左、右翼论战已经丧失意义”的“共识政治论”、“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已经终结”等理论主张,也一度备受推崇。但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后,伴随着凯恩斯经济学的退潮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兴起,大政府、福利国家等支撑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政策框架被彻底打碎。尤其是21世纪以来,在信息网络泡沫和金融泡沫的破裂导致20世纪90年代美国高速发展的“新经济”终结之后,隐藏在富庶的“中产阶级”社会之下的各种社会矛盾,如失业、贫困、社会失衡等日益凸显出来。在实践中,一种对现实社会境况不满的沮丧、愤怒情绪,在各劳动阶层悄然蔓延。在金融危机爆发且绵延不愈的背景下,这种消极的愤怒最终转向积极的抵抗。始于美国其后遍及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占领”运动,正是人们这种不满和愤怒情绪的表达与宣泄。
理论是对现实的抽象和理性认识。近几十年来,围绕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及其社会后果,美国学界的左、右两翼学者一直争论不休。保守派捍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效性,主张新自由主义缩减了社会不平等的绝对程度,宣称相对不平等的存在促进了向上的社会流动。自由派则大多是凯恩斯主义的支持者,强调新自由主义盛行以来社会相对不平等急剧增加,认为新自由主义“对不平等视若无睹或者实际上助长了不平等的发展”。[28]金融危机发生后,劳动阶层生存状况的恶化,激化了社会矛盾,并直接导致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最终演变为围绕收入不平等而展开的激烈论战。鉴于西方经济难以很快走出危机,作为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不平等将是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学界持续关注和争论的重要问题。
其次,这场论战也是美国两大主流思想理论流派的政治理念之争,其围绕不平等的争论和分歧,体现了二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作为美国政治上的左翼,自由派的思想理念某种程度上蕴含着集体主义的意味。尽管他们也坚持个人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但关注更多的是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把机会均等视为保障自由的基本条件。他们强调,只有为个人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才能保证每个人都有一个机会均等的开端。同时,自由派也相信和重视政府在维护正义和保证机会均等中的积极作用。因而,他们倡导一种积极的政治,主张较大的政府和较强的政府干预,通过征收累进税、增加政府开支和制定有限的政府计划等措施,医治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弊病。
自由的价值观则是保守派的政治标签。他们坚持个人自由高于平等,认为经济和社会平等远不如自由重要,不平等反而是一种积极的、不可或缺的社会价值。保守派因而竭力维护私有财产权和自由企业制度,反对除必要外以任何形式对公司进行规制,支持激励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支持由市场而非通过政府计划分配产品的要求。与这种认识一脉相承,尽管他们承认现代社会中政府存在的必要性,但主张应该建立一个有限的小政府,以减少政府规制。
从思想理念上看,虽然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价值观相冲突和对立,但实际上二者却是一种互动和互补的关系。现实的美国政治就一直是在这两种价值之间,维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在一段时间内,自由派的价值观占上风,如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的“罗斯福新政”时期,对平等的诉求成为社会优先考虑的目标;而在另外一段时间,如70年代经济危机后的西方经济滞涨时期,保守派的价值观则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摆脱政府控制的自由”被置于优先地位。
当前,在新自由主义显现疲态、资本主义经济再次面临危机,以及社会公正平等的吁求愈显强烈的时刻,自由派的思想理念有无可能替代新自由主义,重新回归统治地位?虽然从危机来的实践看,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范式转型的迹象,但为了缓和激化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如2010年的“医改法案”(PPACA)、2013年初通过的解决“财政悬崖”法案中的相关增税措施,已经开始更多地倾向自由派的理念。克鲁格曼认为,民主党的这些政策已经对再分配产生一定影响。他支持无党派研究机构“税收政策中心”的统计结果:医疗改革法案实际上使最高1%收入者的税后收入减少了1.8%,最顶级的0.1%人群的税后收入减少了2.5%;财政悬崖协议更使最高1%收入者的税后收入减少了4.5%,最顶级0.1%人群的税后收入减少了6.2%。因此综合来看,最高1%美国人的实际收入减少了约6%,最精英的那一部分人收入下降了约9%。他指出,尽管相比1980年后这部分收入群体获得的巨大收益,这仅仅是部分的清退,但也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
最后,从阶级政治的角度看,保守派和自由派围绕不平等的论战,仍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的争论。争论的最终目的是在体制范围内,寻找一个医治资本主义弊病以及平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良方。虽然就基本观点而言,具有左翼色彩的自由派的观点,更多地体现和维护了中下层劳动阶级的利益,相关学者对社会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现象,以及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破坏性后果的深刻揭露,对于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具有启发意义。但在根本上,这些分析和批判都没有触及不平等问题的实质。囿于作为西方经济学家的局限,他们不可能深入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寻找问题的根源,只是强调这是美国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后果,而没有认识到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阶级对抗性的必然结果。同时,作为凯恩斯主义的捍卫者,他们虽然熟知新自由主义的错误,但并不能深刻透视自己所秉持理论的局限。尽管新自由主义政策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但简单地回归凯恩斯主义,充其量只能暂时缓解不平等状况,而决不可能根治不平等;只能够推迟不平等引发的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而决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从这个层面看,他们的不平等分析尽管具有进步意义,但其提出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诊疗方案,决不可能产生实质性效果,从而极大降低了理论批判的力度。
注 释
①Emmanuel Saez,因为在不平等研究上的重要贡献,2009年曾获得被誉为经济学界“小诺贝尔奖”的克拉克奖。
②1950年,通用汽车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签署了《底特律条约》(the Treaty of Detroit),根据该合同,通用将以收益确定型(DB)模式为员工提供企业年金福利,换取工人不罢工,并允诺会随着经济发展调整工资,创立了现代的企业养老金制度。大批公司还同时开始提供了医疗保险等福利。
[1]Saez Emmanuel.Striking It Richer:The Evolution of Top Income in the United States[EB/OL].http://elsa.berkeley.edu/~saez/saez-UStopincomes-2007.pdf[2009].
[2]Alan Reynolds.The Top 1%… of What? [EB/OL].http://marginalrevolution.com/marginalrevolution/2006/12/an_excerpt_from.html[December 14,2006].
[3]Burkhauser Richard V.,Jeff Larrimore,Kosali I,Simon A,Second Opinion'on the Economic Health of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B/OL].http://ideas.repec.org/s/nbr/nberwo.html[2011].
[4]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Trend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between 1979 and 2007[EB/OL].http://cbo.gov/ftpdocs/124xx/doc12485/10-25-HouseholdIncome.pdf[2011].
[5]U.S.Bureau of the Census.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s to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EB/OL].http://www.census.gov/hhes/www/poverty/publications/pubs-cps.html[2012].
[6]Haskins Ron.The Myth of Disappearing Middle Class[N].Washington Post,March 29,2012,
[7]Furchtgott-Roth D.The Myth of Increasing Income Inequality[EB/OL].www.manhattan-institute.org/pdf/ir_2.pdf[2012].
[8]Tanner Michael.The Income-Inequality Myth[EB/OL].http://www.nationalreview.com/articles/287643/income-inequality-myth-michael-tanner[January 10,2012].
[9]The Experts Weigh in on the State of the U.S.Middle Class[N].Pittsburgh Post-Gazette,November 14,2011.
[10]Brooks Arthur C.American Fairness Means Equality of Opportunity,Not Income[EB/OL].http://www.aei.org/article/society-and-culture/free-enterprise/american-fairness-means-equality-of-opportunity-not-income/[July 13,2010].
[11][美]托马斯·索维尔.被掩盖的经济真相[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12]Krugman Paul.America's Unlevel Field [N].New York Times,Jan.8,2012.
[13]Krueger Alan.The Rise and Consequences of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EB/OL].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krueger_cap_speech_final_remarks.pdf[January 12,2012].
[14]Allegretto Sylvia.The Few,the Proud,the Very Rich[EB/OL].http://blogs.berkeley.edu/2011/12/05/the-few-theproud-the-very-rich/[December 5,2011].
[15][美]拉古拉迈·拉詹.断层线[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16]Scheve K.F.,M.J.Slaughter A New Deal for Globalization[J].Foreign Affairs,2007,(4):34-47.
[17]Freeman Richard.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C].W.Salverda,B.Nolan,T.Smeeding,eds.,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Inequal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579.
[18]Strauss Steven.The Connection between Education,Income Inequality,and Unemployment[EB/OL].http://www.huffingtonpost.com/steven-strauss/the-connection-between-ed_b_1066401.html[November 2,2011].
[19]Mishel Lawrence.Education Is not the Cure for High Unemployment or for Income Inequality[EB/OL].http://www.epi.org/publication/education_is_not_the_cure_for_high_unemployment_or_for_income_inequality/[January 12,2011].
[20]Krugman Paul.Graduates versus Oligarches[EB/OL].http://krugman.blogs.nytimes.com/2011/11/01/graduates-versusoligarchs/[November 1,2011].
[21]Pierson Paul,Jacob S.Hacker Winner-Take-All-Politics: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M].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0.
[22]Krugman Paul.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M].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7.
[23]Sanghoee Sanjay.America's Trickle 'Up'Economy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Inequality[EB/OL].http://www.huffingtonpost.com/sanjay-sanghoee/americas-trickle-up-economy_b_2258110.html[December 7,2012].
[24]Reich Robert B.Why We must Raise Taxes on the Rich[EB/OL].http://robertreich.org/post/4344201496[April 4,2011];and Harry Bradford Robert Reich Defends Raising Taxes on The Rich in under 3 Minutes[EB/OL].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2/06/13/robert-reich-defends-rais_n_1593427.html[June 13,2012].
[25]Murray Charles.Coming Apart: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1960-2010,[M].Crown Forum,2012.
[26]Noah Timothy.Great Divergence:America's Growing Inequality Crisi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M].Broomsbury Publishing,2012.
[27]Mishel Lawence Union.Inequality,and Faltering Middle-class Wages[EB/OL].http://www.epi.org/publication/ib342-unions-inequality-faltering-middle-class/[August 29,2012].
[28]Coburn David.Beyond the Income Inequality Hypothesis:Class,Neo-Liberalism,and Health Inequalities[J].Social Science &Medicine,2004,(1)41-56.
F062.6
A
1005-2674(2014)02-060-08
2013-12-11
2013-12-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2BKS06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9CLS018)
于海青(1975-),女,山东青岛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国外左翼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张 旭
——从乔治·罗奇伯格的《和谐弦乐四重奏》研读他的《生存美学》
——桑塔格的“新感悟”美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