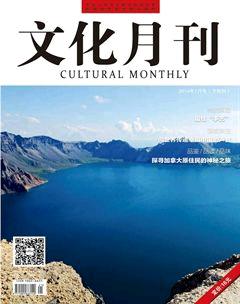“保守派”辜鸿铭,果真“顽固保守”吗?
王京涛
提到“辜鸿铭”的大名,相信很多人不会感到陌生,虽然未必了解其人,但起码大概听过他的名字。尤其是近年来,这位曾经享誉海外的晚清思想家,越来越多地以滑稽、怪异的姿态走进了《走向共和》、《建党伟业》、《湘江北去》等影视中。这说明,即使是在大众文化中,这位独树一帜、桀骜不驯的思想家,也开始占有一席之地了。尤其是近年来,研究他的著作,以及他本人的著作文集越来越多地出现,公众对这位人物的兴趣在明显增加。
谈到这个人,大家的印象,可能最典型的就是他近乎可笑的“顽固、保守”了,其次就是“英文好”,包括一些研究学者,同样对他持此印象。他英文好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他果真“顽固、保守”吗?在我看来,并非如此。若从2005年算起,我关注此人至今有8年时间了。在这期间,我几乎读了我所搜集到的有关此人的所有材料,包括他的著作、对他的学术研究,以及演绎他人生经历的故事等等。他给我留下的整体印象不仅不是“顽固、保守”的,反而是极开放的、求进步的。当然,只有了解了他的思想,才能体会到这种开放与进步。
人们为何普遍认为他“顽固、保守”呢?我想,主要是因为两点:一是他拖长辫、穿长袍的外表;一是他逆潮流而动、在“新文化”与“革命”大行其道的特殊时代倡导儒家文明——他不仅在国内倡导,更主要的是在国际上倡导,主张西方应引进儒家文明以自救,被西方视为“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英国作家毛姆语)。所以,人们认为,他不是一般的顽固、保守,而是“极端”顽固、保守。
但我认为,若以这两点而认定他“顽固、保守”,实则是对此人的不了解。先说第一点,他在人们纷纷剪辫、换装的民国初期,刻意保留清代装束,这算不算保守?我说,不尽然。他其实在著作中谈过装束问题。比如,在他的中文著作《张文襄幕府纪文》中写有《在徳不在辫》一篇,文中说:“今人以除辫变服为当今救国急务者,余谓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辫之除与不除,原无大出入焉。独是将来外务部衮衮诸公及外省交涉使,除辫后窄袖短衣,耸领高帽,其步履瞻视,不知能使外人生畏敬心乎,抑生狎侮心乎?”意思是,人们认为“除辫变服”能救国,但中国的存亡并不在于装束,而在于自身的能力,改了装束,剪了辫子,外国人就会敬畏你吗?
在辜鸿铭看来,改革的要务,并不在装束外表。因此,他其实很轻视这种变革。此外,他也曾对自己的装束做过解释,他晚年在日本讲学时曾说了一句:“我留了这样的辫子,不是出于个人的喜好,而是出于对满洲朝廷的忠节而保留的。”(《辜鸿铭论集·东西文化异同论》)那么,又该如何理解他对清朝的“忠节”呢?答案又在他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又名《清流传》)一书中。这是他出版于1910年的英文著作,虽然不及他的《中国人的精神》有名,但对于理解这个人物却非常关键。他在该书第二版中收录了他发表于《北华捷报》上的一篇文章《雅各宾派的中国》,他在文中自我解释说:“许多外国朋友取笑我,认为我的做法是对大清王朝死心塌地的愚忠。但我的忠诚不仅是对我的先辈们曾获得其恩典的皇室的忠诚,我在这件事上表现的忠诚,也是对中国的宗教信仰的忠诚,是对中国人的文明事业的忠诚。”
也就是说,辜鸿铭之所以拖着长辫、穿着长袍马褂,一个原因是他认为装束的改不改,对于改革来讲并无大的意义;另一个原因,是对中国文明的忠诚。
那么,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他忠于儒家文明、倡导儒家文明,这又应怎么理解呢?是一味的保守吗?我说,也不尽然。这一点,同样可以在他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中找到答案。我之所以说这本书非常关键,其实是集中体现了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即“兼容并蓄”,或者说“扩展”思想。这一思想,我在2013年7月于北京大学举办的首届国际中西文化比较研讨会上做过发言,当时,有参会的学者朋友对我说,听了我的发言之后,改变了他对辜鸿铭的看法。
他的这一思想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的“序言”中明确提出,“中国和欧洲文明都不是绝对完美的文明。”他还批评传统的“中国文人”说,“中国文人的确对他们自己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一无所知。”因此,中国文人不懂得“兼容并蓄”或“扩展”思想,而“中国文明之所以软弱无力,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一点”。
所以,我们看到,他虽然“忠于”中国文明,但并不是一种顽固的“愚忠”,而是有很大的理性。那么,问题就在于,他所说的“兼容并蓄”或“扩展”的思想,到底指的是什么?其实他在著作的很多地方都提到了,这也是在他著作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他说:“真正意义上的兼容并蓄,即灵魂的兼容并蓄。……它能使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对完满的状态的一孔之见远远不是具有永恒意义的、绝对的完满状态。”他进而指出:“为实现这种真正的兼容并蓄,所必需的东西,用个政界的术语说,就是‘开放原则。这里所说的开放并不是指贸易和铁路的开放,而是指思想和精神的开放。”
也就是说,他认为,任何一种文明本身并非完美的,因此,不能固守于一个文明,那么就需要这种兼容并蓄。通俗地讲,其实就是指不同文化的融合。事实上,他在《东西文化异同论》的演讲中说得已经很明白:“我深信,东西方的差别必定会消失并走向融合的,……所有有教养的人,都应为此而努力,为此而做出贡献。……因为常常批评西洋文明,所以有人说我是个攘夷论者,其实,我既不是攘夷论者,也不是那种排外思想家。我是希望东西方的长处结合在一起,从而消除东西界限,并以此作为今后最大奋斗目标的人。”
到这里,您还认为他是一味顽固、保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