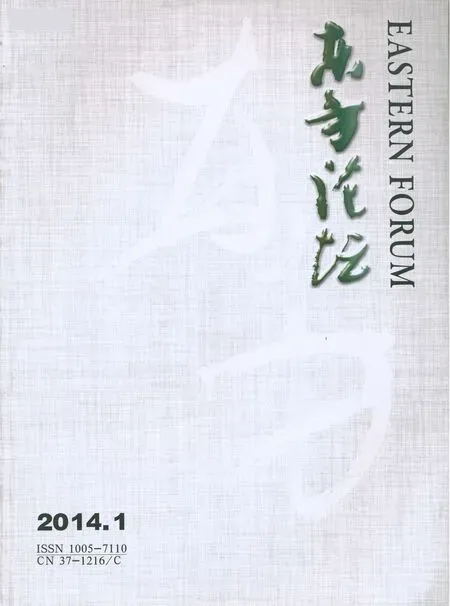大屠杀·政治·性别
——西方20世纪中后期《麦克白》批评研究
殷 振 文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大屠杀·政治·性别
——西方20世纪中后期《麦克白》批评研究
殷 振 文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莎士比亚戏剧经典批评俨然是20世纪众多理论流派的“展示舞台”。作为莎士比亚的悲剧经典《麦克白》也不断被再诠释和重新理解,并激发出新的哲学意义和思想论争。20世纪中后期的《麦克白》批评研究围绕“大屠杀”、“政治”和“性别”三大主题,简要呈现经典意义重构和再诠释的多重路径,并阐明当代的哲学批评、政治批评、性别批评对当代世界和人类命运的人文关切和现实批判。
《麦克白》;大屠杀;政治批评;性别批评
20世纪后半叶充分显示了 “批评的世纪”的含义。从存在主义退潮﹑到结构主义的兴起﹑以及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流行,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的更新,再有后殖民理论,新历史主义﹑以及政治批评和伦理批评兴起等。20世纪中后期文学理论批评流派众多,并催生各种新的文学经典诠释范式和批评方法。“20世纪的西方莎评可以说是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一张缩影”。[1](P1)莎剧经典批评也几乎成为各种批评理论的行动场地。不论是德里达的“幽灵”,还是格林布拉特的“驱魔人”,在某种意义上,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言:在上帝以后,世界完全由莎士比亚决定。关于《麦克白》在20世纪后半期的批评和研究史,本文将集中围绕 “大屠杀”﹑“政治”和“性别”三个关键词作为研究基点,通过对扬·柯特(Jan Kott)﹑艾伦·辛尼菲尔德(Alan Sinifield)﹑玛丽莲·弗伦奇(Marilyn French)及珍妮特·阿德尔曼(Janet Adelman)等学者在20世纪中后期《麦克白》的文本批评及研究进行梳理和阐述,试图阐明在20世纪西方学界该戏剧经典的文本意义被重新诠释的线索历程,以及该戏剧作为经典被重新塑造的过程。
一、《麦克白》的“大屠杀”批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发生了无数的大屠杀,包括犹太人等数亿人的死亡。无论在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文学批评领域,大屠杀都是一个从未间断的话题。在此选取波兰批评家柯特(Jan Kott)作为分析个案。他的著作“似乎预告莎士比亚研究的勇敢新世界的来临”。[2](P279)波兰处在战争﹑恐怖﹑危险,专制的时代(二战或者冷战中期),当时波兰的政治氛围很接近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历史氛围。历史是在时间之流中被建构和叙述,通过弥合时间间隔的叙述,通过讲述过去,柯特重新描述和反思自己所处时代的人类命运和生存处境。“柯特是和伊丽莎白一世同时代的人,就像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的人”,同时“莎士比亚是当代的柯特,而柯特则是莎士比亚的同代。”[2](PⅩ)柯特在《莎士比亚,我们的同代人》(Shakespeare ourContemporary)书中发掘了莎剧所具有的荒诞派戏剧特征。他带着20世纪存在主义的哲学体验去诠释和解读莎士比亚戏剧,且融入了他本人作为犹太人的人生体验和经历。“他的目标就是突显莎氏悲剧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关联。”[2](P68)柯特把莎士比亚悲剧与20世纪的“历史恶梦”联系在一起, 甚至戈达尔(Jean-Luc Godard)和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各自导演的电影《李尔王》和波兰斯基(R Polandski)的电影《麦克白》的拍摄制作均受到柯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批评的影响。
《麦克白》的情节几乎完全符合历史剧中若干情节。“《理查三世》的重要情节与过程都出现在《麦克白》中,而且更加残忍。”[2](P68)柯特看来,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与悲剧(特别是最黑暗的《麦克白》)还是有差别的,历史在《麦克白》中不像是在历史剧中那么作为宏大规律,而是作为恶梦去表现的。所谓的宏大原理与噩梦,只是描述同样的权力和王位斗争的不同比喻或描述,但这两种比喻是两种不同的途径或历史哲学。如果世界被视为机械性的原理或规律体现,而历史的神秘之处在于它的恐怖和不可避免,这在莎氏的历史剧中充分展现。
《麦克白》 始于屠杀,也终于屠杀。“麦克白(自己)谋杀了邓肯。”[2](P68)历史是一种决断,如同犯罪使个体不得不承担责任,并且不得不通过个体之手去执行。麦克白在被班柯的鬼魂折磨时说:“我已两足深陷于血泊之中,要是再不涉血前进,那么回头的路也是同样使人厌倦的。”(三幕四场,依据朱生豪译文)这一场甚至在全剧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就是“流血”!鲜血在悲剧中不是一个抽象的比喻,而是被谋杀的人们的鲜血在流淌。这鲜血沾染在屠杀者的手上和脸上,匕首和刀枪上,无法被洗刷干净。在《麦克白》剧中,不断的杀戮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死于非命,鲜血覆盖全剧,所有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因为所有人都在血泊中前行。在剧中,死亡和罪恶都是具体真实的,在悲剧中表现的历史在柯特看来,也是残酷的,和令人窒息的。
柯特认为,《麦克白》的主题不是政治的野心或犯罪的恐怖,而是人类的大屠杀。在戏剧中,历史已经退化到最原始简单的形式, 杀戮和被杀。“野心只是杀戮中的意图和策划。恐怖则是杀人犯的记忆,新的谋杀的不可避免。”当然在莎氏的历史剧中也是谋杀不断,新国王就是谋杀老国王的罪犯。这仿佛就是历史的规律。但在《麦克白》中,这种原理和规律却像一个不断加剧恐怖气氛的噩梦,《麦克白》整部戏大部分发生在夜间:傍晚﹑午夜或黎明前:“使人盲目的黑夜,遮住可怜的白昼的温柔的眼睛……黑夜的罪恶的使者却在准备攫取他们的猎物”。(三幕二场)麦克白问:“夜过去了多少了” ?麦克白夫人答:“差不多到了黑夜和白昼的交界,但却分不出是昼还是夜”。(三幕四场)
柯特提示人们,没有一部戏像《麦克白》这样重视和纠结于人们的睡眠。因为女巫的诱惑和预言,班柯竟无法入睡:“催人入睡的疲倦,像沉重的铅块一样压在我身上,可是我却一点不想睡。慈悲的神明! 抑制那些罪恶的思想,不要让它们潜入我的睡梦之中。”(二幕一场)。而后,谋生者麦克白彻底“谋杀”了自己的睡眠而再无法入睡。“整个苏格兰,没有人能安然入睡。除了噩梦,再没有安然的梦与睡眠。”在悲剧中,所有人都带着苦痛﹑心存恐惧,“每一分钟都产生新的祸难”,而且谋杀随时都可能发生,“流血是免不了的”,而且“流血必须引起流血”(三幕四场)。在戏中,人们除了漫漫黑夜中的黑暗,不仅看不见光明和希望,也寻不到丝毫友谊或怜爱,甚至连欲望都被谋杀的鲜血沾染。谋杀使得一个人变成噩梦的玩物,并从生活的世界坠入无边的虚无和恐惧。
柯特认为,麦克白很清醒地意识到并绝望地陷入大屠杀的恐怖逻辑是:以罪恶开始的事业亦将以罪恶巩固之;想要通过谋杀去阻止谋杀的发生,似乎谋杀的罪恶才得以洗刷,噩梦才能得以解脱!《麦克白》揭示了人类无法摆脱大屠杀的噩梦的真实处境,不论在人类制定法律以前,或者人类社会有了法律以后,谋杀和屠杀事件都不可避免,并且随时都在发生。麦克白谋杀国王,却又不肯接受自己是杀人犯的事实。想通过谋杀去阻止谋杀的发生,而且只有谋杀才是得以解脱的途径,这似乎就是屠杀的可怕之处!麦克白杀死国王,因为他不肯接受他惧怕杀死国王的事实,谋杀国王以后的麦克白,却又不接受自己是杀人犯的事实。“麦克白谋杀因为他想摆脱噩梦,但谋杀本身却是噩梦的必然。 噩梦令人恐怖就在于它没有结尾。”[2](P74)麦克白陷入虚无越来越深,他每次选择都令他发现自己更加可怕和陌生,“他自己的灵魂都在谴责它本身的存在。”柯特将麦克白的绝望处境存在主义化,“存在对于麦克白变得意义含糊或至少是两重的,我们无法接受我们自己,因为接受意味承认大屠杀记忆和噩梦作为现实。
麦克白梦想一个再没有屠杀的世界,所有的谋杀都会被人遗忘,所有死去的人就这么被埋葬,新的开始继续。“在陷入噩梦越来越深的时候,麦克白希望噩梦的结束;他渴望一个没有罪恶的世界,却是在他越来越深地陷入罪恶。麦克白最后的希望是希望死去的不要再起来。”麦克白幻想有一次谋杀可以让所有的谋杀终结,但在戏中,班柯的鬼魂对麦克白可见,因为死者还会归来。“麦克白不想接受现实和噩梦的不可回避,同时不能面对自己,协调自己,他将自己的罪行视为他人。”[2](P76)但最终麦克白知道,他逃不出噩梦,因为这是人类的真实处境。“他们已经缚住了我的手脚,我不能逃走,可是我必须像熊一样挣扎到底。”“我简直已经忘记了恐惧的滋味。……我的习惯于杀戮的思想,再也没有什么悲惨的事情可以使它惊悚了。”麦克白最终发现一切的行为和选择都是荒诞,或者说根本没有选择:“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第五幕﹑第五场)在这段绝望的独白之前,已经有一段类似的话:“从这一刻起,人生已经失去它的严肃的意义,一切都不过是儿戏;荣名和美德已经死了,生命的美酒已经喝完,剩下来的只是一些无味的渣滓”。(二幕二场)在柯特看来,《麦克白》从始至终表现出完全消极的哲学观,人类改变不了生存毫无意义的绝对性;在柯特看来,麦克白已经接近人类体验的极端,麦克白最后已经彻底陷入虚无,这部戏完全陷入彻底的虚无主义,它不再相信所谓人类的尊严,并且再没有反抗的必要,“不论是善的﹑恶的,迫害者﹑受害者都毫无区别地同归于尽”,[3](P189)这是人处在荒诞世界的最后结果。这也是生存的无意义和存在的荒诞性的哲学主题的戏剧性表达。
柯特认为,《麦克白》的主题是大屠杀,它在讲述人类的真实境地。当考虑到柯特的犹太血统,以及他经历的犹太大屠杀的历史背景,这不难令柯特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其他批评家的诠释角度。并在莎氏戏剧和当代荒诞派戏剧之间勾画了新的联系。20世纪发生了太多的大屠杀,《麦克白》被不断重新阅读或者也是因为人类的命运依然像麦克白及其同代人一样。
二、《麦克白》的政治批评
特雷·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认为文学理论和批评乃是时代政治﹑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政治的这个词所指的仅仅是我们把自己的社会生活组织在一起的方式,及其所涉及的种种权力关系”。[4](P196)政治批评的主要特点是将《麦克白》和莎士比亚时期的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一般的政治批评认为,《麦克白》参与到詹姆斯一世的一项政治计划:努力提出一套系统而有说服力的绝对王权国家(Absolutist State)的意识形态,这部悲剧是特别献给詹姆斯一世的,戏剧试图证明了绝对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整部戏带着意识形态色彩不遗余力地将麦克白不合法,而将他的反对者合法化。”[5](P125)
艾伦·辛尼菲尔德认为这种解读是“詹姆士式的意识形态(Jamesian ideology)”:以国君的绝对权威身份书写戏剧。封建制时代,国王权力往往比名义上要微弱,他不得不与教会﹑贵族和封建领主分享权威。而在16世纪步入绝对君主制的历史进程当中,权力逐渐集中在国王身上,君王是绝对的合法性根源。绝对的君主集权必须通过垄断暴力合法性来源和依据才能实现封建制向君主制的转化进程。这种意识形态先要区分“正当暴力”和“不正当暴力”。当暴力服务于普遍权威时,它是正当;反之则非正当。在戏剧开端,麦克白在镇压叛乱时,他在邓肯的许可下使用暴力是被赞誉和鼓励的壮举;但当谋杀邓肯时,麦克白则是一个可怕的罪恶的杀人犯和篡位者。按照“詹姆士式的意识形态”方法解读,《麦克白》戏剧本身参与了詹姆斯一世的政治权威建构,莎士比亚创作此剧恰好迎合绝对君主制的需求。所以暴力的合法性被成功地垄断在绝对的君主那里,现代政府就开始使人民接受合法的暴力,或者服务于君主或国家的暴力行为本身不会被视为暴力行为。“《麦克白》恰好赶在它(绝对君主制)确立暴力合法性垄断地位的历史关头。”[5](P122)
詹姆士式解读的第二特点是明确区分“合法君主”和“不合法的僭主”。合法的君王相信自己是人民承认和接受的,因为他的权柄来自于上帝,他必须对上帝负责。而不合法的僭主则刚刚相反,他以非法和暴力手段取得王位,他无法得到人民认可,反而是他认可和任命人民,他放纵自己的欲望和激情不受约束和限制,他以追逐最高权利和最大利益为核心。很明显,詹姆士一世努力避免绝对王权与麦克白有任何相似之处。他认为合法继承的君王不可能成为僭主。麦克白是一个彻底的僭主,因为他顺从自己的欲望和野心,谋杀合法的君王取而代之,并为确保自己权力的稳固对自己的部下臣民任意杀戮,从而落得众叛亲离,死于非命。按照上述解读,麦克白死于非命表达了一个主题:正义和邪恶较量而最终以正义得胜。而且麦克白从来没有争取到自己权力和国王位置的合法性,从剧中他一次又一次展开杀戮可以看出。“在戏剧结尾,麦克白最终被灭掉,似乎他从来都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国王。”[5](P126)麦克白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僭主,他通过谋杀合法国王的方式取得王位;而同时麦克白被反对者杀死时,他的反对者依然没有被看作一个合法君王。
为了推翻上述政治解读和诠释,辛尼菲尔德揭示了另外一种叫“布坎南干扰(Buchanan Disturbance)”的解读方式以取代詹姆士式解读。“布坎南理论是詹姆斯解读法的实质性的对立,它后来被用于辩护革除詹姆斯的儿子查理,……对于布坎南来说,君主权来自于人民并且保持于人民;行使权力违背人民意愿的君主就是僭主,并且应该被革除或推翻。”[5](P127)合法的君主也可能成为僭主,因而被人民推翻也是合法的。按照布坎南理论,合法君王和僭主的二分法没有依据。辛尼菲尔德认为根据布坎南理论,《麦克白》是为了辩护1567年推翻詹姆士的母亲玛丽女王(苏格兰的玛丽) 行为之合法性。“玛丽女王既是合法的君主,但却同时是僭主,推翻她的行为是合法的。玛丽女王与麦克白十分相像:她厌恶臣属的正直,听信女巫预言,任用外来的图谋不轨者,在政治对手的家里安插密探,并威胁他们的生命。”[5](P127)玛丽女王的下场跟麦克白也很相似!“布坎南干扰”理论打破詹姆士式解读的僭主与合法君主的二分观念,这不但揭示詹姆士的绝对王权的内在矛盾,同时也颠覆了以往对麦克白的政治解释和批评。
和布坎南理论相比,詹姆士式的解读破绽百出。辛尼菲尔德努力将戏剧解读为推翻僭主的合法性。同样,在悲剧结尾,麦克德夫杀死麦克白,拥戴马尔康为王;这一点与戏剧开端麦克白的角色和处境何其相似,麦克德夫成为一个制造国王的机器,这些都令合法君王的权威仍然处于不明确中,马尔康的权威依然可能受到挑战。辛尼费尔德还设想麦克德夫与女巫再次相遇,这些都在说明在向绝对王权的转型中,权力关系的不稳定性是罪恶发生的条件和因素。
辛尼菲尔德很重视麦克德夫和马尔康的对话。这段对话抹去了合法君王和僭主之间的区别。马尔康说:“要是我有一天能够把暴君(僭主)的头颅放在足下践踏,或者把它悬挂在我的剑上,我的可怜的祖国却要在一个新的暴君(僭主)的统治之下,孳生更多的罪恶,忍受更大的苦痛,造成更分歧的局面。”马尔康说的新的僭主就是他自己。而麦克德夫回答:“人性中无限制的纵欲是一种虐政(僭政),它曾经颠覆了不少王位,推翻了无数君主……谁也不能禁止您满足您的分内的欲望。您可以一方面尽情欢乐,一方面在外表上装出庄重的神气,世人的耳目是很容易遮掩过去的。”(四幕三场)这一幕对话抹除了区分僭主和合法君王的企图。“麦克德夫让我们看到,詹姆斯试图描绘的绝对王权下的君主的美德只是意识形态的操作,这种假象足够保持他的制度得以维持下去。”[5](P129)这段对话阐明了什么才是僭主,同时提醒了人们:在合法君王和僭主的品行之间存在着诸多模糊不清的重合。作为两种不同的政治批评案例:“詹姆斯式意识形态”和“布坎南干扰”理论竟在同一部经典中揭示出截然相反的政治意味和功能。前者强调该剧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而辛尼菲尔德所青睐的后者则揭示该剧颠覆性的政治功用。但无论是服务还是颠覆,戏剧都和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三、《麦克白》的性别批评
性别批评也同样揭示《麦克白》的政治内涵和意义,性别批评学者认为莎剧中的性别问题归根结底总是政治问题,“相信性别与性在文学和其他各种话语中都是中心性的主题,而任何压制掩盖这些问题的批评解释都是有严重缺陷的”。[4](P211)玛丽莲·弗伦奇认为莎士比亚的悲剧多表展现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之间的冲突。如果爱和生育等同于女性原则,杀戮和死亡则代表着男性原则。《麦克白》的主题应是女性原则被压抑的危险后果以及男性原则霸权的危险性。“这部戏剧不是关于野心本身的,而是关于为了一部分原则放弃另一部分,为满足野心去牺牲所谓不必要的原则与价值。”[6](P241)
玛丽莲·弗兰奇认为男性主义的原则与英勇﹑占有和勇气﹑权威﹑独立﹑正确﹑权利﹑合法等联系在一起,男性中心主义通过权力去维持秩序。女性的原则是服从和适应权威和秩序。如果爱和生育代表女性,那么杀戮和死亡代表男性。因为世界永远处在暴力和攻击的威胁之中,所以男性原则就占据优势。莎士比亚清醒地看到社会中男性原则主导一切的危险性,他反思了让暴力,权威去跨越压倒其他价值(女性原则)的代价。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多具男性主义色彩,因为从亨利六世和理查三世的四部曲,到理查二世与亨利五世的四部曲,多属于权力角逐和阴谋杀戮的世界;他的悲剧也多展现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之间的冲突,以及后者被前者压制和贬斥。整部戏是对男性原则主宰的世界贬低抹杀女性原则和男女性别原则不和谐与失衡的后果的想象。
我们毫不怀疑麦克白是“屠夫”。在戏剧中,男性身份被等同于去杀戮的能力,在此文化中,权力即等于战事上的英勇。法兰西认为麦克白夫人及其令人憎恶不仅因为她的残暴,而是她违背了男女性别原则之和谐,违背了自己作为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她没有阻止丈夫谋杀国王(父亲﹑客人),反而诱惑和纵容麦克白的野心去谋杀邓肯。她放弃自己的女性特质,去追求男性原则:“来!注视着人类恶念的魔鬼们,解除我的女性的柔弱,用最凶恶的残忍自顶至踵贯注在我的全身;……进入我的妇人的胸中,把我的乳水当作胆汁吧!”(一幕五场)她认为自己的丈夫身上充满过多男性温柔的乳臭。弗兰奇根据史实推测,当时的苏格兰女人喜欢“戴上”胡须,表现男性的勇猛;麦克白夫人应该认同苏格兰当时文化的男性观,男人即杀戮。
在谋杀邓肯的前一刻,麦克白处在犹豫之中,麦克白夫人讥讽丈夫的犹豫和软弱是“畏首畏尾的猫儿”和懦夫。麦克白反驳到:“只要是男子汉做的事,我都敢做;没有人比我有更大的胆量。”麦克白夫人继续以同样的逻辑刺激麦克白,“是男子汉就应当敢作敢当;要是你敢做比你更伟大的人物,那才更是一个男子汉。”麦克白夫人彻底放弃了自己抚育和怜悯的女性特质:“我曾经哺乳过婴孩,知道一个母亲是怎么恋爱那吮吸她乳汁的子女;可是我会在他看着我的脸微笑的时候,从他的柔软的嫩嘴里摘下我的乳头,把他的脑袋砸碎”。(一幕七场)麦克白无法反驳夫人在于他们都认同:男性气概是行动的最高准则。
另外一个“男性原则”霸权的细节表现在:在谋杀班柯以后,麦克白看见鬼魂,导致自己暂时精神错乱,麦克白夫人当时问“你是一个男子吗?”以及“你的男子气都失掉了吗?”麦克白回答:“我是一个堂堂男子。”(三幕四场)当鬼魂消失,麦克白最终变得镇定,他说:I am a man again.(朱译“我的勇气又恢复了”)男性原则的文化霸权与主导地位是谋杀的根源。弗伦奇认为,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冲突的另一个高峰就是麦克德夫夫人和孩子被杀戮,女性代表的爱和抚育原则荡然无存。整个世界由此变成谋杀的地狱。弗兰奇认为但男性原则造成的结果只是徒有其表的胜利,因为说所有人都是这种原则的牺牲品。接二连三的谋杀不断发生,当那个完全靠个人自我约束的圈套被暴力打破后,男女两性原则失去平衡,整个世界完全变成了地狱,充满谋杀和暴力。苏格兰也不再被称为母亲,而是坟墓。
另一位女性学者珍妮特·阿德尔曼在《受扼制的母亲》(Suffocating Mother)书中揭示,女巫和麦克白夫人代表的母性力量(Maternal power)是一种毁灭性力量。女巫的母性权力威胁了男性权威和秩序,麦克白和其他男性试图着摆脱这种力量。所以《麦克白》的主题应该是男性身份建构中的认同危机和焦虑。[7](P133)这种焦虑在《李尔王》中也有表现,例如在暴风雨当中李尔呐喊“别让妇人所恃为武器的泪点玷污我的男子汉的面颊”。(二幕四场)对母性力量的恐惧和排斥可以表现在对女巫形象的刻画上,她们被视为危险和邪恶的源泉。同样,阿德尔曼强调这种恐惧与排斥贯穿《麦克白》全剧。作者认为母性力量贯穿《麦克白》全剧,女巫和“魔鬼一样的”麦克白夫人激发起母性力量。悲剧通过再现麦克白与她们的关系,展现了男性自我身份的建立和追求,与来自女性力量能够支配控制男性行为思想威胁的内在矛盾。通过父亲缺失,母性力量对男性的威胁在剧中表现出来;邓肯是权威的中心,尊严和血统的渊源,但“在邓肯被谋杀之前,父性与母性的平衡已经被打乱。”[7](P131)邓肯在政治上软弱无力,象征着父亲权威不断被侵蚀。在邓肯的国家,女巫的母性权力已经吞噬了男性权威和蛊惑败坏了秩序。
阿德尔曼认为,当父亲权威缺失,母性力量就操纵了麦克白的行动与思想。最恶毒和有力的女性是麦克白夫人,她的可怕不是试图消除女性特征,而在于女性力量本身。和弗兰奇一样,阿德尔曼也分析“你们这些杀人的助手……把我的乳水当作胆汁吧(to take my milk for gall)”的含义。阿德尔曼却认为“to take my milk for gall”的意思不是拿乳水去换胆汁,而最合适的理解应是麦克白夫人要魔鬼吸取自己的乳汁,并将其作为毒液供养男人。“乳水本身就是胆汁,转换根本不需要。这些话很明显地传达了一种性别恐惧:母性哺育可能传递各种疾病和病毒,这种恐惧在《麦克白》剧中得到生动表现。母性力量还体现在她对丈夫的男性身份构成威胁。她曾哺育过婴孩,但她却能无情地砸碎婴孩的脑袋,因为婴孩面对母性力量是完全软弱和无抵抗力的;“如果麦克白不按照夫人的男人标准去做事,他也会变成像婴孩一样的人。”[7](P140)为了摆脱女性权力对麦克白男性身份的侵犯,避免自己成为夫人眼中软弱无能的人,麦克白决心谋杀邓肯。“愿你所生育的全是男孩子,因为你的无畏的精神,只应该铸造一些刚强的男性。”(二幕七场)麦克白通过幻想麦克白夫人成为刚强男性的母亲,使自己摆脱了男性的软弱缺点。另外一处摆脱女性权力的剧情表现在,麦克白轻信或误解了女巫似是而非的预言,麦克白不会被女性所生的人伤害。但反讽的境况是:杀死麦克白的麦克德夫不是从母腹中产下的,而是被“剖腹产”的,但他依旧是来自母性。麦克白最终的失败其实暗示着幻想逃离女性权力的完全失败。
同时,戏剧情节也暗示母性权力的衰弱与男性身份的艰难重建;女巫在第四幕以后再没有出现或被提及,而麦克白夫人最终走向毁灭。男性身份的重建就是要尽量远离女性或削弱女性的影响。阿德尔曼认为麦克德夫的经历也恰好体现了这一观点,麦克德夫抛妻弃子,家庭的毁灭和妻儿的死亡竟使他成为一个无畏的男人;而且他告诉麦克白他是被剖腹从母亲的子宫内取出的,这竟然成为他战胜麦克白的利器,或者是麦克白最终丧失依靠的关键因素。最后麦克德夫与麦克白的战斗与第一幕麦克白与麦克德夫的战斗处于类似境地:为摆脱女性权力而战,或为确立男性身份的确立而战, 战斗的结果是被从母性体内“切割”出来和没有家庭的麦克德夫战胜依赖女性权力的麦克白。
阿德尔曼还提醒人们注意:《麦克白》暗示了一个独立于母性力量的国度:英格兰。最终马尔尔康和麦克德夫在英格兰的帮助下,打败依靠女巫力量的麦克白;在剧中,苏格兰是一个女巫很有势力的国度,并且女性的权威对男性的行为影响之大可以体现在麦克白与夫人的关系中。英格兰作为一个和蔼的父亲形象,帮助“没有亲近过女色”(四幕三场)的马尔康去战胜麦克白,最终建立一个没有母性力量参与的男性社会。
[1] 杨周翰选.莎士比亚评论汇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2] Kott,Jan.Shakespeare our Contemporary,Methuen,1965.
[3] 孙家琇.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
[4]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 Sinifield,Alan.Macbeth. Macmillan,1992.
[6] French,Marilyn. Shakespeare's Division of Experience.Jonathan Cape Ltd,1982.
[7] Adelman,Janet.Suffocating Mothers:Fantasies of Maternal Origin in Shakespeare's Plays,Hamlet to the Tempest.Routledge,1992.
责任编辑:冯济平
Massacre,Politics and Gender: A Concise Review of Critics of Macbeth in the Middle and Late 20th Century
YIN Zhen-wen
( School of Humanit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
In the 20th century, Shakespeare's works still remain the stage for different schools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Shakespeare's Macbeth was so repeatedly re-interpreted by the critics that new philosophical meaning and academic discussions have been generated. A concise review on Macbeth in the middle and late 20th century focuses on three key subjects: massacre, politics, and gender. This review will present multiple methods of literature canons'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Meanwhile, it will show the humanistic care and realistic criticism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political and gender criticism.
Macbeth; massacre; political criticism; gender criticism
I106
A
1005-7110(2014)01-0120-06
2013-10-07
殷振文(1984-),男,河南郸城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西方文艺理论和外国文学研究。
——他者形象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