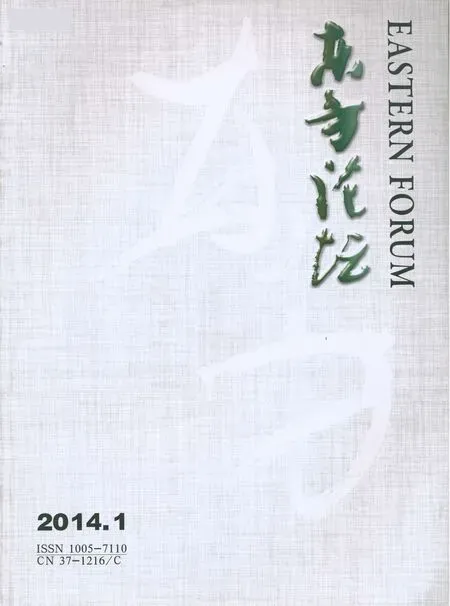现代社会思潮与基督教信仰
吕 绍 勋
(青岛市社会科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现代社会思潮与基督教信仰
吕 绍 勋
(青岛市社会科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西方传统的基督教信仰秩序被破坏后,人们寻求非宗教的世界解释方式。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浪漫主义,都要求将超验者从人类的知识结构和道德地形图中驱逐出去,而将知识的基础和道德的根源设定在人类的理性或本性之内。现代世俗思潮对基督教信仰的冲击,使得人们重新重视自然神学的重要性。而从自然神学衍生出来的自然神论,则是传统基督教信仰与现代人本主义之间的过渡。追问世界与上帝同一性的泛神论,和自然神论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无神论。在当今这个多元化时代,面对众多世俗思潮的冲击,基督教信仰应当如何自处,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难题。
现代思潮;多元化;基督教信仰
现代社会的基督教信仰处于极其复杂的境况之下。就西方社会而言,一方面,随着基督教神圣秩序的破坏,新的象征体系和世俗秩序纷纷建立,人们希望通过非宗教的方式来解释世界。这些非宗教的方式,无论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还是浪漫主义(Romanticism),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将宗教信仰中的超验者从人类的知识结构或道德地形图中驱逐出去,而将知识的基础或道德的根源设定在人类的理性(Reason)或本性(Nature)之内。现代世俗思潮,尤其是理性主义对基督教信仰的冲击,使得人们重新重视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的重要性和解释力,成为了与启示神学(Revealed Theology)并驾齐驱的一条神学进路。而自然神学所衍生出来的自然神论(Deism),则是传统基督教信仰与现代人本主义之间的过渡。自然神论反映了近代人类对上帝和世界是不是一回事的追问。对于这一追问给出肯定答案的,还有泛神论(Pantheism)。自然神论和泛神论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无神论(Atheism)。
另一方面,非宗教的解释方式也暴露出自身的不足,人们会时不时遭遇到宗教解释的必要。例如在葬礼上,当面对死者亲属的时候,人们离开宗教的言说方式几乎无法开口。我们或者说他的灵魂已经得救了,或者说他已经得到安息了,再或者说他在天之灵也不愿意看到你这么伤心。我们唯一不可能说人死如灯灭,他已经完完全全消失了。如今全球范围内各种传统宗教的复兴﹑新兴宗教的崛起,也都暗示着宗教的理解方式在人类社会中的必不可少。
当今的基督教信仰即处在这种多元化的思想背景之中。“多元化”(Pluralism)最初指美国的一种情形。在那里不同的宗教都可以得到国家的宽容(而不是限制),都可以进行自由的竞争。各种宗教就像商贸活动中的卖家一样,都极力推销自家的产品,以便争取更多人的信奉。这种竞争不仅发生在不同的宗教传统之间,而且也发生在同一传统中的不同宗派之间。这种状况可以称之为“宗教内部的多元化”,它与“宗教外部的多元化”一起,影响着现代人的信仰选择。在这种多元化的精神图景中,尤其是在世俗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基督教信仰何以自处,是每一个基督徒和宗教学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现代思潮之一:分解式理性
在对传统基督教神圣秩序的反叛过程中,分解式理性(disengaged reason)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所谓“分解”,开始是指人类从原来宗教信仰所建立的神圣秩序中脱离出来,转而依据理性的能力和限度来理解世界。分解式理性的始作俑者是笛卡尔。“勒内·笛卡尔事实上是近代哲学真正的创始人,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的。独立的思维在这里与进行哲学论证的神学分开了,把它放在另外的一边去了。思维是一个新的基础。”[1](P63)笛卡尔真正地使哲学与神学相分离了,而且将哲学完全建立在了思维(理性)的基础之上。笛卡尔虽然也讨论上帝,但这里有一个根本的﹑极具现代性的转变,即在他那里上帝及其创造的秩序,不是外在于我们的,而是我们合理性建构的内在秩序的一部分。在这个内在秩序中,理性占据着霸权地位。理性统治下的秩序之所以是善的,不再是因为这个秩序与上帝的秩序相配合,而是因为理性对激情的有效控制。笛卡尔所寻求的理性,乃是本身既“确定”又“真实”的东西。“这种东西与信仰的对象不同,并不是仅仅真实而无从认识的东西,同时也不是仅仅具有感性的﹑可疑的确定性而无真实性可言的东西。”[1](P69)这种理性不仅要从信仰和世界中脱离出来,而且更进一步地,因为它要对激情进行控制,也使得它从肉体中脱离出来。查尔斯·泰勒称这种理性为“分解式理性”。
后来,洛克将这种分解式理性推倒了极致,使得自我意识成为了一种“点状自我”(punctual self),即没有任何广延﹑不具有任何实体性的(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自我意识。就像几何学中的点一样,它可以不与任何肉体相关,也可以寓居于任何肉体之中。这是一种更加激进的分解态度。点状自我对对象具有构建能力,但它自己却远离任何一种特殊性,它以简单观念为材料构筑复杂观念,或者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或使之并列,或把它们分割开来。在这种无广延﹑无实体的自我理解中,根本没有为上帝及其创造的秩序留下任何空间。
启蒙运动继承了这种分解式理性,对一切非理性的﹑超验的解释世界的法则全面排斥。具体到社会实践活动,就是反对教会,反对传统的权威,反对一切以现成的方式被给予的知识;新的知识的建立需要一个坚实的基础。这里所谓“坚实的”是指符合逻辑的与可经验的。康德曾说过,所谓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2](P23)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说:“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中,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代替幻想。”[3](P1)如何理解被彻底启蒙的世界笼罩在一片灾难之中?按照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解释,启蒙在祛除了一切神话和神秘的原则之后,人们在通往现代科学的道路上,错误地放弃了对意义的追求,认为一切不符合算计与实用原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认为所谓的超验者,无非是主体对外界的折射,是人类非理性的建构;一切“不能被还原为数字的,或最终不能被还原为太一(Eine)的,都是幻想”。[3](P5)
这种试图仅仅依赖思维的方法,却时不时遭遇思维之外的世界。对思维来讲,世界是一种巨大的抽象和无知的混乱,让本来企图寻求平静和统一的现代自我感到恐惧和无所适从。世界在祛魅之后,重新又获得了一种神秘色彩。这就是沃格林所说的,“新的象征又会从世俗的科学语言中发展起来并取而代之”。[4](P212)例如在工业社会,“人造环境”(尤其是商品和货币)便获得了这种神秘性,成为了新的世界象征;现代人正被更多的超出自身之外的东西所控制,人与世界,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遭受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异化。
现代思潮之二:浪漫主义
休谟对两个命题的怀疑动摇了理性主义的基础:其一,因果关系并不是我们直接感知到的,或者说我们并不能确确实实地知道它是存在着的。其二,我们无法用逻辑的方法证明世界的存在,而只能作为信念接收下来。因为我们无法将所有的事实都还原到数学的层面。[5](P38-39)另外一个动摇理性主义的普遍性理想的,是孟德斯鸠的相对主义,他指出普天之下并非处处皆同,尤其是关于幸福的问题。然而真正对启蒙理性形成致命冲击的,是源于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相对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确立。如果说理性主义还有意于建立一个世界秩序的话,浪漫主义则无意于此。这两种思潮的对立与碰撞,是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对于现今基督教信仰困境的理解,也将依赖于此。
这里所讨论的“浪漫主义”,不是艺术(尤其是文学)领域中的创作派别或创作方法。艺术中的浪漫主义是对新古典规范结构的反叛,“与古典主义强调理性主义﹑传统和形式上的和谐不同,浪漫主义更推崇个人﹑想象和情感的权利。”[6](P568)虽然这种创作态度多少反映了我们所讨论的浪漫主义的精神特质,但我们所讨论的是浪漫主义的哲学本质,它将自然作为道德本体,将本性及其表达作为人的本质。它被卢梭﹑赫尔德等所阐发,后来也被歌德和黑格尔所接受。
另外需要澄清的是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区别。自然主义抹煞道德本体,认为一切都是欲望,甚至都是肉体的欲望。而浪漫主义则不然,它承认道德本体,这个道德本体就是“自然”。这个“自然”不是茫茫无际的以物理原则组织在一起的机械宇宙,而是有灵性的生命体。自然根本上是善的,我们之所以不善,乃是因为与自然的疏离,如理性的使用将自然变成了外在对象。通过理性的控制以求达到善,是理性主义的主要成果之一。但浪漫主义者认为,理性的使用伴随着的是道德的衰落,因为理性对人类本性的控制并不是一件好事,人类要达到善,应该顺应本性。
认为自然根本上是善的,这与自然神论极其相似,但我们必须指出两者之间细微的区别。浪漫主义显然是受惠于自然神论的,但自然神论在谈论自然本身是善的之前,还要回答这个问题,即“自然为何是善的?”答案是自然作为上帝的创造物,所以是善的。浪漫主义则从来不问自然为何是善的,“自然是善的”就是第一前提。这种“在不提上帝的情况下就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则尽量不提上帝”的原则,显然是一种现代思维。
浪漫主义虽然认为善的根源是自然,但同时也强调自然的善只有通过内在于我的本性才被发现。我的本性即是自然(在英文中它们是同一个词:nature)。本性与自然的和谐,不是个体对外在秩序的服从,而是这两者本来就是一个东西。使人为善的不是命令,而是冲动。这是一种更为主观的态度。对内在之声来说,需要做的乃在于摆脱其外在羁绊,宣布自己拥有全部道德的资格。
浪漫主义认为我们的最终幸福,就是与这种内在之声和谐相处,也就是说完全成为我们自己,而不是成为其他的什么样子。成为自己本来的样子,与基督教的“成圣之路”,即放弃自己本来有罪的样子,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圣洁的样子,是大相径庭的。也就是说,在浪漫主义者那里没有原罪的概念。但有趣的是,某些浪漫主义者,如卢梭,却固执地认为人性之恶不是知识或教化可以抵消的。堕落在卢梭的道德观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浪漫主义者对人性,起码在日常状态下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人性,有着深深的不信任,所以才提倡要发现一个深藏着的本来的样子,要作回真实的自己。这其实是一段艰难的路程,因为人们往往搞不清楚什么才是本来的样子,误认为按本性行事就是按欲望行事。这就是为什么自称是浪漫主义者的人,有时是卓然不群的,有时是放荡不羁的,但有时也是纵欲的。
在浪漫主义者那里,原本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找到的同一和完整性的根源,如今却发现存在于自我之中。查尔斯·泰勒指出,“卢梭是大量当代文化和自我探索哲学的起点,也是使自律的自由成为德行的关键这一信条的起点。他是现代文化转向更深刻的内在深度性和激进自律的出发点。”[6](P559)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分解式理性与浪漫主义的一个共同点,也是它们作为现代思维的共同点,就是这种内在性和自我的同一性(自律)。自我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不需要参与到一个外在的结构中去;相反,一切外在的因素都可以构建为内在体系的组成部分。
对自律的理解,康德追随卢梭,谴责对欲望的服从,也谴责分解式理性对世界的控制。他将这些原则都称之为他律,即认为欲望和工具性的需求,都不是人类的本性。人类的本性乃是遵照普遍律令的最终目标行事,它不是以行为的后果,而是以行为的动机为根据的,它体现出来的不是对某物的服从,乃是人类的自由与尊严。与卢梭不同的是,自律遵从的本性不是人类的冲动,而是理性。当然不是工具理性和理论理性,而是实践理性。“康德明确主张,道德不可能在自然或任何外在于人类理性意志的地方发现。这是对所有古代道德观的彻底摒弃。”[6](P561)可以说康德的理论是现代立场最直接和最不妥协的阐述,而康德则是一个真正高尚的现代人的代表。
在康德主义看来,浪漫主义把自然当作道德根源,并将善理解为人的本性与自然的统一,是对人的自主性的限制。自然依然是一种他律。但在浪漫主义者看来,康德的理性自律割裂了人的内在本性与外在自然的统一,使得自由与自然成了相对立的概念。但两者也有共同之处,他们对分解式理性与自然主义持批评态度,并且更重要的,二者都是内在化的结果,二者都试图置知识或道德的根源于内部。
浪漫主义确实也存在着一个大大的困境。传统哲学的善,是由上帝﹑理念等超验的道德根源所规定的;而浪漫主义的道德根源是内在的人类本性。那么什么是善的,则由人类本性决定。人类本性所表达的,是对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日常欲望的满足,以及对于我们置身其中的宏大自然秩序的情感。情感上的愉悦与伦理上的善之间往往会划上等号,伦理学与美学之间的界限不再那么清晰了。
在浪漫主义中,表达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没有表达就无所谓浪漫主义。“假如我们是通过内在的声音或冲动接近本性,那么我们只有通过表达我们在自身发现了什么才能充分了解这种本性。”[6](P578)这种表达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它是对“我们自身”的表达,是一种由内向外的显现;其二,通过表达而显现的东西,不意味着是预先已经得到充分说明的,它有可能在表达的过程中才建立起来;其三,表达需要一定的媒介;其四,当原有的媒介不足以表达一个慢慢建立起来的东西时,我们便会使用新的媒介来表达这个新的东西,这时我们称之为“创造”。第四个特征在艺术创作中是常常遇到的情形,也是浪漫主义哲学最能体现出它的主体性的地方。所以,浪漫主义同时也是一种“表现主义”(expressivism),它不仅是对现成事物的呈现,更主要的是对本性的创造性表达。因为“生命冲动的这种方向不能也不可能在这种显现之前就是清晰的。要实现我的本性,我必须通过对它的阐明去定义它;但是还有一种更强意义上的定义:我实现着这种阐述,因而赋予我的生命以确定的形态。”[6](P579)在使本性得以显现,使生命得以塑造的意义上,表达的媒介,如语言,在此获得了空前重要的地位。
表现性个体是我们现代文化的一个基石,它对我们是如此重要,以至我们很难意识到它是人类历史近代才出现的观念。我们都认为这种“自然而然”的方式,乃是人类亘古以来的思维方式。对这种创造性的表达方式,所感受到的出离自身的敬畏感和神圣感,接近了某种神圣的宗教情感,所以这也是审美与宗教体验的相近之处,是中国近代提出“美育代宗教”的理由所在。
现代思潮之三:自然神学
基督教信仰受到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等现代思维的冲击,开始从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领域撤离,有神论视界的原初完整性已经破碎,这意味着宗教领域之外全面世俗化时代的来临。同时基督教内部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叫做“基督教的理性化”。基督教的理性化与世俗化不同,世俗化要求抛弃上帝,理性化则不要求抛弃上帝,它主要表现为用理性来融合信仰,采取一种从下到上,从人到上帝的建筑术。理性与信仰的融合并不是一件新事物,它长久地存在于基督教传统之中。之所以说近代以来基督教内部的这种变化也是一种现代思维,乃是因为与信仰所融合的理性,更根本地讲是现代的分解式理性。自然神学在现代社会占有一席之地,主要乃在于理性的现代理解赋予了它一种新的生命力。
卡斯培在描述现代思潮对传统基督教信仰的影响时说:“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已经失去了信仰的维度,就是奥秘的维度。因此,从神学上而言,我们又被迫倒退到理解的开端;我们的经验能力已多半局限于五官所能把握的东西,局限于能够被计算﹑被生产的东西。结果,在我们这个世俗化的社会里,教义神学比以往更须关心其本身的理解预设。这种对理解信仰之理解预设的反思,称为‘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7](P109-110)在现代语境下,传统基督教通过启示和教义所传达的关于上帝的信息,已经变得没有说服力了,成为了一种无法被现代人所掌握的外国语。如今,信仰的理解预设必须被重新界定,必须限定在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所能把握的范围之内。
卡斯培认为,在《圣经》中没有明确反思过信仰的自然预设,即《圣经》里并没有自然神学。但另一方面,《圣经》却又实践着自然神学,“因为《圣经》就活在一个完全由宗教决定的环境中;《圣经》因而可能已经以一种完全自明的方式不仅求助于宗教观念和经验,而且还求助于普通人的日常经验,由此得出可供宗教陈述利用的种种形象。”[7](P110)即《圣经》所揭示的神学主题,乃是从当时的生活经验出发的,无需论证。在这种未经反思却广泛运用的神学背景下,存在着一种根本的信念,那就是:创造的秩序与拯救的秩序是相互一致的。
早期教会的教父们曾以双重的方式提到通过认识自然而达到对于上帝的认识的可能性,即上帝既可以通过可见的自然之物被人所知,也可以通过人类灵魂的自然本性而被人所知。教父们对自然知识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做彻底的思考,是被古代诺斯替主义逼出来的。诺斯替主义强调上帝与世界﹑精神与物质之间的二元划分,认为救赎不是世界本身得到救赎,而是从世界中救赎出来。经院哲学主要遵循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第一部第二题第二条中所提出的公理,来表达创造与救赎的同一性,这个公理是“恩典预设自然”(gratia supponit naturam)或“信仰预设理性”(fides supponit rationem)。“这一公理的真正意思应是上帝启示必须预设一个能够倾听﹑理解并自由作出决定的主体。因此,上帝只能向具有理智和自由意志的人发出信仰的召唤,而不能向诸如无生命的对象或没有灵魂的生物发出这种召唤。”[7](P114)
到了近代,传统信仰的自然预设遭到了人们的怀疑和否定。这种怀疑和否定以双重的方式出现:“由于过高地评价理智(理性主义),从而导致一种见解,错误地认为人类和世界是绝对自主的;与这种过高的评价相反的是,通过贬低理性,从而主张,唯有在信仰之中,人类才能接近上帝(唯信主义),只有通过宗教传统,才能接近上帝(传统主义)。”[7](P114)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1869-1870)和第二届大公会议(1962-1965)批判了这两种偏激的现代方式,即理性主义与唯信主义,而试图调解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关系。但问题是,同时肯定自然秩序和超自然秩序,其实等于承认了两种神学的可能性。这两种神学是很难调和为一的,因为它们是两个根源生出的两棵大树。于是现代天主教就有了两种神学松散地叠合在一起的双层图式。
以上对《圣经》﹑早期教会和现代教会的陈述,反应了自然神学的第一种考虑,即:人类对信仰的接受,绝对不是在一种化学处理过的“纯粹”状态中,而必然是基于人类的日常生存状态的;信仰必然是以人类所能理解的方式接受的,这里主要是指理性。从而,信仰与理性从来就是相一致的。
自然神学还有第二种考虑,即:不以信仰见证者为起点,而以听众为起点。即信仰见证的目的,不在于表达个人的宗教经验,基督徒在对自己的良心负责的同时,还必须向所有的人解释他们的盼望。所以,基督教信仰不可能不涉及人类所共有的东西,这种共有的东西将各种差异的人作为普遍的人联系起来,这个共有的东西就是理性。自然神学认为基督教不可能退到个人经验中去,而必须走向人类共有的理性理解。
自然神学中的“自然”概念,不是哲学上的自然,它不是与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如文化﹑历史等)相对立的﹑未曾修饰过的现实。自然神学中的“自然”,乃是与“恩典”相对立的一个概念。起先,自然由于是上帝创造的自然,是服从于恩典并被恩典所成就的。后来,随着自然独立地位的获得,以自然为基础,以理性为手段所建立起来的自然神学,获得了与启示神学相对立的地位。这是近代基督教内部所不断探讨的难题。而在基督教之外,自然早就独立了出来,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整套非神学的知识体系,这就是现代完全世俗性的知识体系。
现代自然神学与自然知识体系如今也都面临着一种所谓历史主义的挑战。历史主义提倡一种相对性的知识观,人们发现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文化背景,就会为知识和信仰提供不同的预设前提。赤裸裸的自然是不存在的,自然必然是披着各种观念的自然。所以自然神学也好,自然知识也好,都要与具体的历史条件相关联。这一方面否定了启蒙思潮中那种抽象的﹑非历史性的自然和理性知识,另一方面也否定了自然神学的可能性。历史主义者坚称,人类的信仰和知识的理解预设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化的。那种寻求知识和信仰的不变的先天预设的崇高理想,在历史主义中失落了。信仰和知识的合理性证明,要以信仰和知识所发生的历史视域为预设,而不是永恒不变的。
现代思潮之四:自然神论、泛神论与无神论
自然神学的基础是自然,强调的是信仰与理性的融合,以及敬拜上帝与人类日常生存的融合。自然神学在现时代的精神图景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后来衍生出来的自然神论(Deism),查尔斯·泰勒称之为传统基督教信仰和现代人本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8](P221)自然神论可以说是自然神学的特殊形态,它作为一种思潮,发生于启蒙运动时期,并一直影响着现代人的宗教观念。
卡斯培曾指出,“启蒙运动时期有代表性的宗教哲学,不是泛神论,而是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发端于17至18世纪间的英国(赫伯特勋爵[Lord Herbert of Cherbury]﹑霍布斯[T. Hobbes]﹑托兰[J.Toland]﹑洛克[J.Locke]﹑廷德尔[M.Tindal]﹑科林斯[A.Collins]等),以后成为法国启蒙主义者(如培尔[P.Bayle]﹑伏尔泰[Voltaire]﹑狄德罗[D.Diderot]等)所效忠的宗教哲学,最后进入了德国(如赖马鲁斯[H.S.Reimarus]等)。”[7](P37)自然神论是一种信奉自然的宗教,它追求的乃是每一个人在不依赖于超自然之物的情况下,可以获得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宗教真理。在启蒙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宗教形态被发现,基督教信仰变得相对化了,成了众多宗教形态中的一种。于是,人们开始寻找一种可以概括所有宗教形态的普遍的宗教知识。这种宗教知识的基石乃是自然,所依赖的乃是理性,所建立的神学体系乃是自然神论。在自然神论中,上帝变得多余了。因为上帝在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就像机械师制造了钟表一样,让世界按照其自身的规律运转了,上帝退到了世界的背后。人们要认识上帝,最好的办法就是认识世界的秩序,因为它就是上帝意志的体现。这种观念一方面是受了当时自然科学的影响,尤其是受了牛顿的影响;自牛顿开始,就混淆了“获得自然知识的方式”与“自然本身的方式”,把两者相互等同,并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变成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另一方面,自然神论也确实有着基督教传统的根据。“世界是上帝的意志”是一个传统的基督教观念,我们通过认识被造物的秩序,可以发现善——即上帝的意志,这种观点在基督教传统中是十分常见的。但在基督教传统中,这种善不仅仅局限于人类的现世利益,而是有着更加神圣的目的。但是到了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的自然神论,对于善和世界目的的理解,日益变得人类中心主义了。
泰勒认为,洛克对自然神论负有主要的责任。按照洛克的理解,通过理性对自然法则的研究,我们就可以认识上帝的目的。上帝的诫命与人的理性,被自然法这颗结实的螺丝帽拧为一体了。而在洛克看来,自然法的首要原则是自保。“因为上帝设计的存在具有自我保存的强烈欲念,我们能推断,我们的自保就是他的意图。”[6](P358)所以,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维护,都是符合上帝意图的。同样,他人的自保也是符合上帝意图的,每个人也都需要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洛克在《政府论》第86段中说道:“因为上帝既然已亲自把保存自己生命和存在的欲望(强烈的欲望),作为一种行动的原则,扎根于人的身上,‘作为人类心中的上帝之声的理性’就不能不教导他并且使他相信,按照他所具有的自我保存的自然趋向行事,就是服从他的创造主的旨意。”[9](P74-75)
自保成了上帝意旨的中心点,获得生存资料的能力被赋予中心的重要性和尊严。基督教如若接纳这一中心点,则彻彻底底地成为了人间宗教,即以人类自保为中心教义,以上帝意志为扩展性论证的世俗化宗教。在清教职业观中,世俗的工作还有一个超验的目的,这个超验的目的始终占据着中心位置。而在自保的教义中,世俗生活占有中心位置,超验性的目的被消解在世俗目的之内。因为每个人都有自保的倾向,所以,我们应当为了公共的善——每个人的自保——而工作。这个公共的善,不是来自于上帝诫命之一的“你们要彼此相爱”,而是来自于自然法的“你们要彼此自保”。上帝诫命的第一条“你们要爱上帝”,在公共的善中是找不到立脚点的。
在自然神论看来,要了解上帝的目的,最正确的方法,同时也是最高尚的和最可靠的方法,就是运用理性。我们通过理性认识自然法,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理性实践是参与到上帝计划中去的路径。从人到达上帝的理性,比从上帝到达人的启示更加可靠,更能为人类所掌握,原来虔诚地为了上帝而生活的问题,现在则变成了有理性地生活的问题。理性在自然神论中,占有着比以往在任何宗教中都重要的位置,它就是道路。
基督教信仰与理性的现代联姻,使得天意变得越来越易于理解,神恩的地位也越来越趋于消失。以自然为神学的出发点,以理性为建构神学体系的工具的作法,必然不是真正的“关于神的诫命的学问”,而是人间的世俗化的变种。在人类因懒惰﹑贪婪﹑激情﹑野心等而偏离自然法的正路时,上帝才作为候补队员,进入人们的视野。 “人类有潜在的理性,但同时对非理性和罪恶有内在的喜好,注定由于他们自身的缘由使他们自己最好的潜能受挫,那么人们就能明白他们的状况呼求能把他们拯救出来的上帝。”[6](P364)上帝在极其危机的时候才被呼求,并作为神话般的力量,在人们实在想不通的地方,挥动魔术棒。即神恩只在两个地方补充性地出现:其一,在人类本性之善因罪的限制而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其二,在自然法之外的问题域中,如关于拯救的问题。
自然神论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本质,必然要消解超验维度。这种消解包含着四个方面,第一,高远目标(further purpose)的消失。人们认为,从根本上讲,我们之所以向上帝负责,仅仅是我们要实现自己的好处。第二,恩典的消失。上帝的意志就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这个意志是可以通过人类的理性和适当的教育发现的。上帝虽然还被认为是存在的,但他创造了世界,并给予了我们理性的能力之后,就躲到世界的后面去了。第三,神秘感的隐退。如果上帝的目的乃是为着人类自身的好处,并且这个目的可以在我们的理性中发现,那么,更多的神秘因素就不再必要了。在一个理性可以把握的宇宙中,神迹是多余的。第四,原来认为上帝在人类中有着计划,要使人类超越当前状况的信念崩溃了。基督教传统中,人类作为上帝计划的参与者,有一个从凡夫俗子到“成圣”的过程。现在,世俗生活成了人类生存的目的,甚至上帝也要服务于此目的。
自然神论其实反映了近代人类的一个努力,那就是追问上帝与世界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对这个问题给出肯定答案的,不但有自然神论,而且还有泛神论(Pantheism)。这两者都有一个危险的倾向,那就是无神论(Atheism)。
“泛神论指的是,就其存在与本质说,上帝与现实的整体(pan)是同一的。”[7](P35)虽然在各种宗教文化中都可以找到泛神论的因素,但泛神论这个概念及其体系的建立,却仅仅产生于近代。卡斯培认为,在近代泛神论的思想家中,居首位的乃是布鲁诺。对他的泛神论思想形成决定性影响的,乃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新世界观和人生观。布鲁诺的自然科学研究,使得他被世界本身的美与和谐所倾倒,这种新的世界图景,是与传统教会所设定的老图景相冲突的。布鲁诺在世界中看到的是无限——这个本来属于上帝的特质,从而他把上帝和世界视为同一,世界是上帝的必然展开。后来,斯宾诺莎发展了最为连贯的泛神论体系,他吸收了新柏拉图主义和犹太教中的神秘观念,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新的世界观念。根据他的观点,世界不具有实体性,它仅仅是神性实体(上帝)的属性得以展现出来的有限模式;只有上帝是绝对无限的实体,并通过一系列因果关系在世界中展现出来。“这种泛神论的基本原则可化为这个公式:上帝或自然(Deus sive natura)。但是这个公式并没有断言一种彻底的﹑无差别的统一;上帝和自然仍然存在,被区分为创造自然的自然(natura naturans,或译‘主动的自然’)和被自然创造的自然(natura naturata,或译‘被动的自然’)。”[7](P36)在这个公式中,虽然上帝和自然仍然被区分开来,但上帝已经被定义为一种自然,即主动的自然。这种学说对后世影响极大,一度成为了莱辛和歌德时代看待世界的标志性宗教态度,并影响了荷尔德林﹑谢林﹑黑格尔﹑施莱尔马赫等人。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当代,人们宁愿设想一个决定世界规律的上帝,而不是一个决定人类命运的上帝,尤其不是一个决定人类善的动机和知识范式的上帝。
自然神论与泛神论的区别是微小的,但它们确实是不同的思想体系,并有自己的发展理路。如果说它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就是自然神论还设想一个超验的上帝,他是世界的创造者,而泛神论则将上帝等同为自然,是内在于世界的。按照泛神论的理路发展下去,必然的结果就是无神论。因为当上帝等同为世界之后,再保留一个超验的上帝实在是多余了。如果这个上帝不能被认识,那他对我们就毫无意义,如果通过世界能认识他,那他就没有必要站在外面。
对无神论有决定性影响的,是18﹑19世纪的自然科学中的经验主义﹑感觉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念。在这些自然观念的逼迫之下,上帝撤退了,他退出了科学﹑哲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的诸领域,成了落后分子﹑宗教人士谋生的饭碗。当然,现代的自然科学日益认识到了自身的局限,并常常在两个方面遭遇上帝,“一是当它探讨其自身的最终的预设时,这些预设本身已不再属于科学;二是当它探讨科学家面对其研究带来的后果时的伦理责任,尤其是在核子科学和遗传学领域。”[7](P41)
同时在宗教领域内,教会也在协调科学和信仰的关系,努力把科学变成可以用来护教的东西。科学无神论和教会的这种作法,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试图把上帝和世界置于同一个层面上,上帝变成了世界的竞争者。这既误解了上帝的绝对性,又误解了人的自由。归于上帝的任何属性都不能归入世界,只有上帝被严肃地看作是上帝时,上帝才将世界解放为世界。这是卡尔·巴特等保守派神学家不断强调的。将上帝等同为世界,不仅上帝死了,而且人也失去了自由,人不再是世界的参照点,而成了世界及其物质的一种功能。或者干脆成了各种物质中的一种,是一种精密的物理机器。作为自然科学的现代心理学,就犯了这个错误,它试图在大脑的某个神经中枢中,寻找人类高兴﹑愤怒或嫉妒等情感的发源地;并通过一组组的实验数据来提供证明。也许有一天,现代心理学可以在大脑中的某个神经中枢中,发现人类良知的发源地;当然,最好是发现上帝。
回答这个问题:多元化时代基督教信仰何以自处?
贝格尔曾经努力为基督教信仰探索一条现代出路,即从日常生活的经验中,找到一条通往超验范围的信仰之路。他既不赞同自由主义神学从人到上帝的人类学的道路,因为自由主义神学的乐观在社会现实面前充分显露了它的乌托邦性质;他也不欣赏以卡尔·巴特为代表的新正统主义只强调上帝的恩典与启示的反人类学的道路。虽然后来有些新正统主义者,如布鲁内尔(E. Brunner),对此有所修正,但新正统主义整体上依然倾向于强调人类的“失落”﹑“不幸”﹑“绝望”等,似乎新正统主义是一种“绝望神学”。贝格尔指出,存在主义人类学的阴暗性似乎十分合乎新正统主义的这种口味,两者的结合便可以产生一种新式的存在主义神学。考克斯的《世俗之城》(The Secular City)再次转向了对人类学的愉快的接纳,人际交往的世界又一次被视为有目的的人类改善活动的场所,而不是无益的泥沼。在这个场所中,道德的基调虽不再倾向于先前的悲观,但却过于承认人间的享乐,结果达到了一种对世俗化的赞扬。贝格尔似乎更愿意回到以人类学为出发点的神学,但不是一种短暂的﹑情绪性的乐观,也不是一种对世俗化的激进肯定,而是要扎根于人间的基本体验,指出一条不受文化情绪影响的天堂之路。“我认为,神学思想应从经验角度给予的人类环境内,寻求可以被称为超验之表征(signals of transcendence) 的东西。……我所说的超验之表征,意指能在我们的‘自然’实在范围内发现,而看来却指向实在之外的现象。”[10](P63)或者说,贝格尔相信,上帝在人间留下了一些记号(singals),这些记号构成了人类的本性,通过考察人类的本性,一旦认出这些记号,就可以知道上帝的存在了。
贝格尔称他自己这种从人类经验出发到达关于上帝的命题的方法,为“归纳信仰”(inductive faith)。贝格尔说:“我用归纳一词来指任何一种以经验为出发点的思想过程。演绎是相反的过程,它以先于经验的观念为开端。因此,我所说的‘归纳信仰’意指一种宗教性的思想过程,它以人类经验的事实为开端。而‘演绎信仰’却正相反,它以某种假设为开端(尤其是关于神圣启示的假设),这些假设不能通过经验来检验。简言之,归纳信仰是从人的经验出发到关于上帝的命题,演绎信仰则从关于上帝的命题出发来解释人的经验。”[10](P69)贝格尔自己承认说,他的这个方法天然地接近神学自由主义,但已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种盲目乐观的自由主义神学了,而是采取了更为审慎的态度。他似乎试图调解保守神学与自由神学之间的冲突,认为他们都有偏颇之处,同时也都误解了对方的用心。他在使用归纳信仰的方法的同时,也强调了要面对传统。一方面,因为在思考一些神学基本问题时,传统有着巨大的借鉴力量,出于谨慎和谦虚,我们也应该正视传统。另一方面,因为从历史上的一切人类经验中,都有可能发现通往上帝之道的“超验之表征”。也可以说,人类传统中的一切秩序,都是一种“超验之表征”。所以贝格尔主张“神学思考必须在普世主义意识中进行,在我们目前的多元化环境中,在宗教方面只停留在自己人之间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10](P97)
1996年1月,查尔斯·泰勒荣获天主教圣母会奖(Marianist Award),并在戴顿大学(the University of Dayton)的颁奖仪式上发表了题为《天主教的现代性?》 (A Catholic Modernity?) 的演讲,第一次公开宣布自己天主教徒的身份,并试图探讨天主教信仰与现代性问题。泰勒的用意,乃在于调和天主教神学与现代多元文化,尤其是与世俗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泰勒认为,天主教应该去接触各种民族的文化,天主教徒应该有全球性的宽广视野,并使得各种文化与天主教信仰相适应。这并不违背天主教的原意,因为天主教(catholic)的希腊文是katholou,它的意思是“全宇宙的”和“普遍的”,泰勒在两种相互关联的意义上来分析这个词,即它“同时包含有普遍性(universality)和整全性(wholeness)两个含义,或者可以说,它是通过整全性实现的普遍性。”[11](P14)泰勒认为,救赎的发生是通过道成肉身,即上帝的生命进入到了人类的生活。但是,人类的生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复杂的,是不可彼此替代的。那么道成肉身的救赎,就提供了一种和解的方式,一种合一的途径。通过这种途径,多元化的存在者意识到他们通过自身不能达到整全性,彼此的互补是必要的,而那种认为自己无需改变的态度是不可取的。“或者我们可以指出:彼此的补充和完成的同一都是我们最终达到整全者的一部分。”[11](P14)这不同于历史主义的态度,历史主义往往忽略了互补性,而直接走向单一性(sameness)。这种单一性不是整全性,往往使得人们走向一种失败的天主教,而不是一种“好的天主教”(good Catholics),因为单一性使得上帝所创造的人类的多样性被压制了。
泰勒认为天主教应该是“跨越差异的整体”(unity-across-difference),而不应该是“同一性的整体”(unity-through-identity)。天主教应该面对各种人类的多样性,上帝不仅体现为三位一体的显现,也体现在人间生活的多样性上面。在泰勒看来,天主教的一项原则是信仰的拓宽,这种拓宽不仅仅是奉献形式﹑精神形式﹑敬拜仪式和对道成肉身的反应形式的增加,而是信仰在多种文化形态中的对话﹑融合和显现。泰勒于是举出了现时代初期在中国和印度传播信仰的耶稣会士,如四百年前来到中国的利玛窦(Matteo Ricci),先后学习了佛教和儒家经典,并且与中国的高僧鸿儒积极往来,在赢得明朝士大夫信任的同时,将基督教信仰通过一种新的途径彰显出来。
对于现代人来说,我们生活在众多的基督教生活形式的复兴中,这些精神领域可以补足我们自身的狭隘,提醒我们自身的偏颇,以便走在通往整全性的道路上。这就是泰勒所指出的“现代天主教”的可能性。这是一种面向所有的人类文明的开放态度。
但是这里有一个困难,那就是开放的现代天主教,是泰勒向天主教开列的药方,这个药方或许会激励着天主教徒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对待多元文化;但对于天主教之外的现代人,尤其是无宗教信仰的世俗中人,这套方案是没有任何效力的。所以,或许哈贝马斯等人所主张的,在哲学和公共理性的基础上建立诸文化之间的对话,才是更加现实的。
也许泰勒一度认识到了这个困境,所以在后来的著作中,他不再在多元对话中为基督教谋得一席之地,而是更加侧重于分析现代精神图景的危机,并不失时机地指出基督教信仰在多元化时代守护人类精神家园的价值所在。
[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C].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3]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 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M].张新樟﹑刘景联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 以赛亚·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源[M].吕梁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6]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7] 卡斯培.现代语境中的上帝观念[M].罗选民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8] Charles Taylor:A secular Age [M].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9] 洛克.政府论:上篇[M].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0] 彼得·贝格尔.天使的传言:现代社会与超自然再发现[M].高师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1] Charles Taylor:A Catholic Modernity?[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责任编辑:侯德彤
Christian Faith and Pluralistic Thoughts in Modern Society
LU Shao-xun
( Qingdao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China )
People have been trying to explain the world in secular ways since Christian order was destroyed in the Western society. Both rationalism and romanticism put the basis of knowledge and the source of morality within human reason or nature. The challenge coming from modern secular thoughts makes natural theology important again. Deism which evolved from natural theology is a bridge between traditional Christian faith and modern humanism. Both deism and pantheism exploring the unity between God and the world have one same trend, namely atheism. How Christian faith maintains itself in this pluralistic age is a question to be answered.
modern schools of thought; pluralism; Christian faith
B913
A
1005-7110(2014)01-0027-09
2013-09-28
吕绍勋(1981-),男,山东菏泽人,青岛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哲学与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