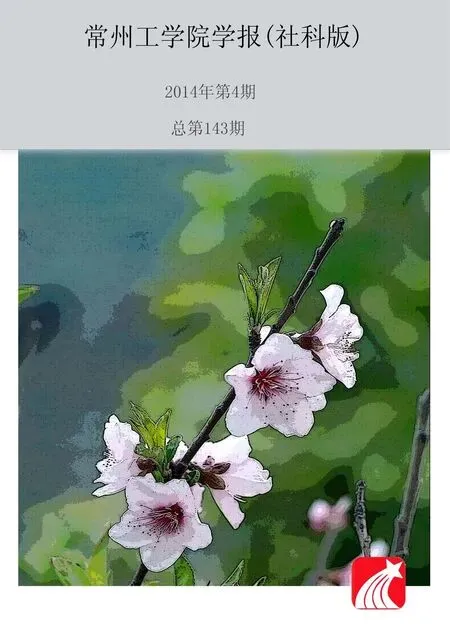论张翎新移民小说叙事的意象营构
高侠
论张翎新移民小说叙事的意象营构
高侠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无锡214122)
北美华人作家张翎的创作风格传统,其新移民题材小说叙事擅长意象营构,精心挑选有寓意的物象结构情节,转承起合情韵生动;巧妙运用组合叠加意象刻画人物,借助梦境、画境和诗境凸显主人公的心理曲回;更着意架构地理标识鲜明的南方、北方时空体意象,以哲理意蕴深远的象征渲染、升华人性探察的主题。
张翎;小说叙事;新移民;意象营构
提及小说的叙事风格,写下大量新移民故事的北美华人作家张翎自谓“很老派”,称自己并不太关注叙述方式的新奇,而是格外注重借助枝干清晰的情节、花叶丰满的细节讲好故事,颇得中国传统文学意象化叙事的神韵。意象,乃寓意之象,“是以象征、隐喻、神话启喻为基本活动方式来承载或破译精神内涵或文化密码,使简约的语言获得有效的信息增值,因而极具美的魅力的艺术形象”①。杨义认为,意象是“中国文学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神采之所在”②。张翎显然深谙此理,其小说叙事中那些扎实细腻、匠心独运的意象营构,在烘托诗意氛围、增添浓郁情味的同时,也推动情节发展,凸显人物心性,升华主题蕴涵。
一、物象:金针巧织度
明清小说评点常以“金针”这一喻象来赞誉作者细节处理的精巧,张翎小说在结构情节时常设置一些有寓意的物象,恰如“金针”,“在暗示和联想中把意义蕴含其间”,“发挥着贯通、伏脉和结穴一类的功能”③。《雁过藻溪》中,末雁多年难以走出亲情阴影,中年又离婚失意,心头压着两块石头的她返乡归葬母亲,在颓败祖宅紫东园母亲房中意外捡拾起一方旧手帕,“边角上绣了一朵花,像是莲花的样子——颜色当然早已褪尽了”④。时光交错的恍惚间,莲花在末雁掌心发出细小而清晰的声音“开吗?开吗?”。这细小的声音子弹般刹那间洞穿末雁的心,牵扯出她身世的隐秘——五十年前,出身不好的母亲以失身的代价逃离家乡,而末雁正是那场狂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结下的苦果。伴随身世秘密的层层剥离,情节铺展的关键处,挣扎回旋于情感漩涡的末雁耳畔不时响起莲花细小声音,“开吗?开吗?”声中,“五十年后的眼泪和五十年前的眼泪带着不同的缘由在这块失却了劲道的旧布上相聚”⑤,横亘的情感隔膜得以化解,寡淡的婚姻生活得以清理,压抑已久的渴望得以释放,末雁终于挪开心头的重压,有勇气如莲花般去寻求新生的绽放。《花事了》中,温州城里两大商行文氏与花氏联姻,文家二公子文喧恋上花家痴迷绍戏的二小姐吟云,定亲时特意费尽周折、花高价购得一把琵琶相赠,吟云对诸般聘礼不闻不看,独对此琴爱不释手,心中了然文喧知音之意。带着这把琵琶,留下请文喧等两年的字条,吟云离家学戏,情急之下,花家让姐姐吟月替嫁,吟云归来震惊之余毅然离家。外出经商的文喧偶遇随小戏班漂泊的吟云,重逢时刻百感交集,吟云怀抱琵琶借戏文诉说委屈,伤心处琴弦砰然断裂。解放前夕,文家迁居香港,即将临盆的吟月随记挂吟云的家人留了下来,从此与丈夫隔岸相望。时代风云的激荡变幻中,演员吟云勉力撑持着花家,出于感恩续弦嫁给文化局领导,后却陷入与丈夫前妻之子争夺房产的尴尬中。36年后,另组家庭的知名台商文喧回乡探亲,清晨的花宅,激荡幽婉的琵琶声再度响起,“起先声气很是急促嘹亮,如同无风天里下的暴雨,噼噼啪啪地敲打在窗台上。一阵急雨过去之后,琴声便渐渐低缓下来,化成细细一缕雨丝,若有若无似绝非绝地飘在院中——却听不出调子”⑥。文喧离去,房产官司落定,吟云再度失踪,一起不见的还是那把琵琶。琵琶与吟云如影随形,出现在她人生的每一道关口转折处,或拨弹有声,或暗哑沉默,曲尽主人情路坎坷,人生幽怨。类似绣有莲花的手帕、爱情信物琵琶这样的器物意象在其他作品中还可举出多例,它们使张翎小说的情节安排错落有致,叙述串接珠圆玉润。
张翎还着意于以喻意丰富的物象刻画人物,她笔下新移民故事的女主人公多有一个能映射自身性格命运的物象化名字,这些喻意鲜明的物象名字也堪为“金针”,穿连点缀着人物心性的非凡之处。《雁过藻溪》中生于1952年“土改”运动中的末雁原由母亲取名小改,少时的她尚不明了这名字暗藏的身世隐痛,只觉得与母亲之间隔着一堵无形的墙,母爱被坚冰封固。上大学后,她自作主张更名为末雁,动机显然源自缺少亲情所带来的失群落单之感。从初中毕业主动报名插队逃离家庭,到恋爱、高考、留学、定居,生存打拼之路上的末雁,苦苦寻求感情依托却又总难以如愿,如离群的孤雁迁徙漂泊渴望归巢。《空巢》中那个性格倔强的保姆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春枝,年轻时倾尽全力帮参军服役的丈夫撑持家庭,中年时却遭遇退伍后经商发达丈夫的背叛,为争女儿的抚养权不惜净身出户,辛苦做保姆为女儿筹谋一份良好的教育前景。春枝坎坷后的倔强自立,正如春天里枯树干上发出的嫩绿新枝,历经严寒摧残却并不折服,看似柔弱却自有一股韧劲和活力。这份苦寒逼出的生命势能不仅拯救了颓废萎靡的何教授,也令情路上顾虑重重的何田田深受启发,感悟了爱之真义。《余震》女主人公小灯原名小登,大地震中与双胞胎弟弟被压在一块楼板两头,救一个就必须牺牲另一个,痛彻心扉的抉择后母亲放弃了她。劫后余生的小灯丢失了记忆,然而当养父母为其取新名时,她却坚持以“灯”字为名,下意识间追逐着脑海深处细若游丝的亲人称唤,期盼点亮剧痛之后陷入黯淡混沌的心灵。此后的生活中,心灵的余震化作莫名的头痛、焦虑失眠死死缠绕着她。与家人关系紧张,事业落入困境,内心陷入黑暗,几番濒临绝境的小灯在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下,蛰伏多年的童年记忆渐渐苏醒,她踏上了归乡之路,回到久违的旧宅,听到母亲“纪登”“念登”的呼唤,终于推开了心底那扇关闭已久的窗户,重新点亮了心灵之灯。末雁、春枝、小灯,这些精心撷取的物象化的名字可谓人物形象塑造的点睛之笔,张翎笔下的女主人公们因之形神俱出,情韵生动。
二、心象:情思显曲回
以“跨界书写”著称海外华文文坛的张翎,其新移民故事并不刻意展现文化的冲突、融合,而更着迷于东西方共通人性的探察与开掘。她尤其擅长将笔下人物推入某种极致的生存境遇中来接受残酷的人性拷打,因为“伤痛给了我们活着的感觉,所以伤痛是人性最基本的特质之一”⑦。杨义认为:“当叙事作品需要更深地透视人类生存境遇的时候,就有必要动用意象组合的另一种方式,即添加组合。”⑧在运用添加组合意象摹写人物复杂的情感世界、心理曲回方面,近作《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堪称典型。创作渐入佳境却遭人恶意诽谤的女作家沁园失魂落魄地踏上了东欧浪漫之旅,当被问及旅行感受时不禁一怔,恍觉自己的心不在脚上,也不在眼上,甚至没在心里,“原先藏着心的地方,仿佛被一只老茧丛生指甲尖利的手掏过,掏得很猛很急,掏出了一个边缘毛糙的大洞”。“没有心的眼睛是缝隙巨大的竹篮,存住的只是渣滓。”⑨一路行来,沁园的眼中尽是“灰涩与幽暗”。袁姓中年男导游认出并察觉到沁园的伤痛,不时以意味深长的讲解点拨着沁园。旅程尾声的一个风雨之夜,袁导提议每人讲一个“一生中最黑暗的夜晚”的故事,并带头讲起1956年11月3日那个寒冷的冬夜。可怖的隆隆声中,苏军的坦克碾碎了首都布达佩斯的宁静,无线电波中,总理纳吉和著名作家哈伊的呼救声“把黑暗撕扯出了破绽,可是黑暗太稠太浓,他们的声音,还是丢失在了黑暗的缝隙里”,“对纳吉来说,这个他一生中最黑暗的夜晚,永远没有能够走向白天”⑩。对于曾是当年社科院最年轻历史学教授的袁导,为妻子放弃专业出国,不得不以带旅游团谋生,然而还是遭遇了家庭的解体。离婚出户的那个夜晚,女儿凄厉的哭喊飘荡在寒风中,撕碎了他的心,“这是巴黎最冷的一个夜了,漆黑”⑪。而对于留苏出身、经历政治运动浩劫的徐老师来说,奔赴青海找寻挖掘爱人骨殖的“那个夜,实在太黑太长了”,“她想一直搂着他,坐过无数个黑夜,一直坐到天塌地陷,地老天荒”⑫。沁园终于醒悟,其实每个人都需要熬过自己“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熬过内心的阴霾,那本是人生历练的应有之意。夜晚与黑暗两个意象的组合,空洞、寒冷、浓稠等意象的叠加,再辅以程度副词“最”的修饰,顿时洞穿了人们遭遇不测、陷入绝望的心理境遇。重击之下的人性挣扎,是如此惊心动魄,刹那间点燃了整个叙事。
梦境、画境、诗境也是张翎谋求以组合叠加意象探幽人性奥秘的常用途径。《尘世》中,在异域辛苦经营咖啡馆的刘颉明,一份情感在内地女子江涓涓与女招待混血儿塔米之间游移。正当他准备迎娶涓涓时,一场大火将咖啡馆烧成灰烬。昏昏沉沉的梦境中,刘颉明来到一片海滩,浪花惊起了群鸥,沙滩上只剩下孤零零的两只,“一只受了伤,低垂羽翼,步履蹒跚,一步一呻吟。另一只远远驻足,频频回首观望。‘等我……’,伤鸟无望的低语在尚未抵达它的同伴时便已迷失在浪和礁石的杂响里”⑬。回国相亲时,刘颉明曾无端梦到火灾,梦中的场景是涓涓二婆家的老屋,救起的却是塔米,而现实中的火灾,却是塔米忙前忙后帮他善后,救他于困境。两场梦境中的意象组合乃刘颉明矛盾心理的对应呈现,淡雅沉静的江涓涓是他对故土亲情难以割舍的牵挂,而热情奔放的塔米则是他生存打拼中温暖的依傍,难以取舍。《望月》中,张翎直接将女主人公的身份设计为有追求的画家,以其不同时期的作品意境呈现其精神状态。成名作《畲寨风情》组画,神态活泼的少男少女,凤尾竹摇曳的吊脚楼,棕黄桔红的色调,透着一股活泼泼的热力。孪生妹妹的死,热衷赚钱的俗气丈夫,让知音难觅的望月一度陷入迷惘,笔下“竟全是荒原墓地”,笼罩在“月光下”“落日里”,“孤鸟”栖息在“断枝”头,“落叶”“残花”卷裹在风雾雪霜里,一派清冷肃杀的意境中透露着画家的落寞伤感。在同道画家、乐观积极的宋世昌鼓励下,望月搬离喧嚣的都市,栖身远郊小屋,“看着屋外的红红绿绿,屋里的坛坛罐罐,倒真有了几分竹篱茅舍的农家心境”,画中同样的景物,“少了些寒色,多了些暖色;少了些肃杀之气,多了些温馨悠闲”⑭。不同色调、境界的画面景物清晰显露了女主人公内心的波澜起伏。对于望月这样的新一代移民而言,丰裕的物质生活显然已并非首要目标,生活空间的迁移,觅求的是放飞理想,精神疆域的拓展,这注定了她必要跋涉过一段自我确证的坎坷心路,领略另一番形而上生命移植的甜酸苦辣。新作《何处藏诗》中,何跃进随手写在废纸片上那些诗,字里行间散落的意象,勾连着他与青梅竹马的女友端端一段痛彻心扉的恋情:“你可以把心紧紧锁上/可是把钥匙交给我吧/我请求你/我承认,我不是最好的管家/但是我会把它埋进湖心/让它在淤泥中间/开成一株荷花/岁岁年年,洁白无暇”⑮……即使陪伴左右,何跃进竭尽所有也未能保护好纯洁柔弱的端端,眼睁睁地看着出身不好的她被时代狂流裹挟着,身不由己地一步步落入阴冷、黑暗的命运泥沼,隐忍、挣扎,最终却还是为污泥浊流所吞没。作品全文共穿插了13首长短不一的诗,诗境与情节及人物深藏不露而伤痕累累的内心紧密契合,纷繁的意象迭映折射出人性的幽深细密。有心的梅龄处处留意收起那些纸片,渐渐读懂了这个孤独男人心底的款曲,终将一段以虚假婚姻换取移民资格的交易演绎成了深挚温暖的真情。
三、境象:光影共徘徊
单个或组合叠加的器物、景物意象,无论是结构情节,还是映衬人物,对叙事所产生的修辞效果还主要停留在语符的喻意能指层面,当笔端触及迁徙、漂泊、归宿等移民文学绕不开去的核心主题时,张翎小说的意象营构便跃进到高一级层面——境象象征。这里的境象,乃巴赫金所谓的叙事文学作品中的时空体:“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力,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中。”⑯相对于物象,人物故事发生、运动其中的时空意象显然更为宏阔,其语符能指更多维度、寓意也更深远。地理标识鲜明的境象,其基础的构筑素材通常来自作家生活经验中累积的心理表象,张翎小说中“天光云影共徘徊”的境象可划分为以故园、乡土为核心的南方与以高原、极地为核心的北方。
从浙江温州苍南县藻溪镇走出去的张翎,家乡小城的山水人文景观无疑是心头最熟稔亲切的记忆。她的新移民故事中,南方小镇的故园、乡土既是女主人公们异域漂泊、奋斗的出发地,也常常是她们受挫后回归疗伤、安顿灵魂之所。《望月》中,孙家姐妹的母亲沁儿乃旧上海赫赫有名的三圆金笔厂老板的独养千金,深得宠爱,十岁时得的生日礼物竟是一座花园大宅——沁园。“沁园的一颦一笑,界定了市井之辈的层次”,“从从容容地与时代脱着节,无视着外边时尚的千变万化”⑰。沁园中的女人也如那满园经年盛放的白玉兰,斑驳的红木窗架,即使落入尘俗也竭力保持着清高孤傲的心劲。这股心劲逼赶着孙家母女历经着各自的磨难,却也护佑着她们度过命运劫波的冲刷和击打。《雁过藻溪》中,当末雁跨过祖宅紫东院的门槛,“便猝不及防地一脚跌进了历史”。枝条稀疏的老树,树干上鼓爆着的歪歪扭扭的疤痕,依稀可辨“日月水火……天地……玄黄”的字迹,废弃多年的水井,“井沿和石板上都长了厚厚一层青苔”,末雁终在这里完成了与母亲穿越时空的灵魂相遇,弥合了心头郁积已久的痂痕。静静伫立在历史尘烟中的故园之外,藻溪小镇的清丽山水、温馨人家是张翎作品中出现最多的南方境象。《尘世》里,男女主人公带着过往的感情创痛开始交往,第二次约会,江涓涓特意邀请刘颉明随她返回藻溪故里。行路疲倦时,刘的“眼前陡然一亮。原来是一汪溪水,悄无声息地环绕过来,将路堵得很是窄小起来。水虽然不宽,却还算干净,清清的略带了一缕蓝。水边有几块大石头,黑黑厚厚地长了些青苔。溪边有一棵老树,满身疤痕,一半在岸上,一半在水上。低矮处的枝干遭清风一吹,几乎就探进了水里。隔着树荫隐隐看见一座老屋,油漆斑驳,露出木头的底色来,很是古旧落魄的样子”⑱。清溪、老屋,痴情仁义的二婆,归家的感觉让相识不久的二人心灵迅速走近,生出了亲人般的牵念。《空巢》的结尾,女儿田田也是在保姆春枝家乡那条叫藻溪的水边找到了离家出走的父亲,“藻溪是条小溪,线似地在山石中流过。石头很乱,从那岸歪歪扭扭地铺过这岸,就成了涉水的丁步”。父亲带了春枝的女儿在溪边钓鱼,“父亲甩竿的动作很是落力,仿佛在上演一出细节到位的戏文,……全出戏文只有一个观众,就是春枝”⑲。澄净的溪水边柳枝爆出嫩绿的新芽,初春的阳光里,自己也在感情中挣扎过一番的女儿终于放下了对父亲黄昏恋情的介怀,获得了心的释然。
南方境象温润而精致,显然适于抚慰生命移植的疲惫创痛,但其关涉移民者生存状态的象征意蕴则总有些绵柔有余而张力不足。越往人性探察的深处走,张翎越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于是,追随自己一路向北的生活轨迹,她逐渐将眼光投向朔风横扫、冰天雪地的高原极地,投向那片时空下粗粝却率真放达的生命形态,刻意营造了更为辽远而宏阔的北方境象。《向北方》中,少年陈中越“小心翼翼行走在精致而错综复杂的街景习俗人情中”,总觉得“江南的城郭像一件小号的金缕绣衣,他轻轻一动,就能挣破那些精致的针脚”⑳,渴望北方的“大”而“宽阔”“简单明了”“漫不经心”“无所畏惧”。结婚生女,留学移民,人到中年,生活事业上一路领跑的妻子与他渐行渐远。烦闷冲动之下,陈中越终于迈出了“向北方”的步伐,来到北纬52度、靠近北极圈的苏屋瞭望台。在这个印第安土著的聚居区,他遇到了九岁失聪的男孩尼尔和他的妈妈。自不足一斤半的尼尔早产那一刻起,母亲达娃就西西弗斯般,背负多舛命运的重厄,竭力扶助羸弱的儿子攀爬生命之山,直至付出生命。达娃坚忍承受境遇的苦寒,与厄运搏挣的勇毅深深震撼了陈中越,收养孤儿尼尔的决定意味着他拔出了自我心灵的沼泽。《雁过藻溪》中,与陈中越有着同样感受的藻溪青年黄百川,怀揣灵魂自由舒展的渴望,远赴青海支教。从飞机上俯视下去,青灰色的山脉,大片大片边角分明的绿和黄,一带蓝色蜿蜒而去,“那山那水那地,竟然是一种他远未曾想象过的葱茏”㉑。在这片神奇的高原,“每一个毛孔里都恣意地流淌着阳光”,飞鸟般不羁的藏族女子唤醒了百川的激情;手浸冰水、忍着刺骨寒冷静息凝神捏塑酥油花佛像的塔尔寺老艺僧涤荡了百川的灵魂,引领他步入生命的另一重境界。也是在酷寒的北极,一次极昼、极夜交界时刻惊心动魄的日落,不禁令末雁身心战栗:“从橙过渡到紫,从紫过渡到青,再从青过渡到灰。每一层的过渡仿佛都是一种撕扯和挣扎,是天地相拥翻滚过程中溅出的叹息。突然间,天滚到了地的身下,世界坠入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惊悸中,她向搭档汉斯袒露了深藏内心的孤独苦痛,得到了汉斯的理解宽慰。意外重获爱情的末雁“没有想到,属于她的光和暖,竟会从那个蕴藏了最浓重的黑暗和寒冷的极地生出的”㉒。显然,生存环境严酷的北方境象已成为张翎笔下除南方故乡之外,又一人物灵魂获取救赎、新生之地,辽远开阔,劲风横吹的冰天雪地,含蕴着人之精神能量的极致绽放,象征着自由高远的人生境界。
南方与北方两个系列的时空意象,既与张翎个人生活经历直接对应,也清晰标识出她新移民叙事主题的精神向度:“我一直在写、或者说要写的是一种状态,即‘寻找’。我的场景有时在藻溪,有时在温州,有时在多伦多,有时在加州,就是说一个人的精神永远‘在路上’,是寻找一种理想的精神家园的状况。”㉓作为一种象征蕴涵厚重的境象,南方与北方,从早期的对峙到晚近的融通,也表征着张翎小说人性探察的不断深入。
注释:
①孙春旻:《表象·语象·意象——论文学形象的呈现机制》,《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3期,第115-117页。
②③⑧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7页,第276页,第283页。
④⑤⑨⑩⑪⑫⑲㉑㉒张翎:《张翎小说自选集·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42页,第143页,第14页,第36页,第40页,第48页,第98页,第170页,第137-138页。
⑥⑬⑱张翎:《尘世》,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页,第42页,第92页。
⑦万沐:《开花结果在彼岸——〈北美时报〉记者对加拿大华裔女作家张翎的采访》,《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年第2期,第70-73页。
⑭⑰张翎:《望月》,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297页,第89页。
⑮张翎:《无处藏诗》,《收获》,2012年4期,第20-54页。
⑯巴赫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74页。
⑳张翎:《雁过藻溪》,时代出版社,2006年,第3页。
㉓南航:《十年累积的喷发——张翎访谈录》,《文化交流》,2007年第4期,第18-21页。
责任编辑:庄亚华
I106
A
1673-0887(2014)04-0014-05
10. 3969 /j. issn. 1673 - 0887. 2014. 04. 004
2014-05-23
高侠(1969—),女,副教授。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2012SJD75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