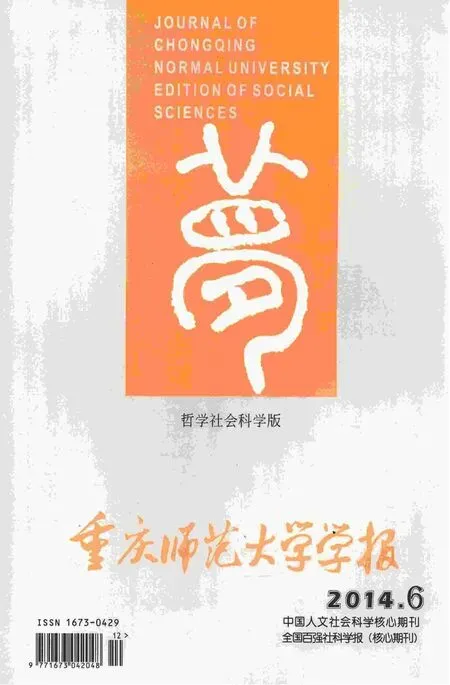雅化:钱穆关于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总体观察
严金东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文学具有“独立自主”的品格,这是现代学科制文学研究中一个被普遍承认的信条,这个信条很明显地落实于对文学作品的“审美独立”的解读上。流风所及,文学史的研究中也不乏呼吁对文学史“自身内在规律”的把握,例如就常常有人批评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太依附于朝代变迁。文学作品的解读且不论,就追求一种体现文学史“自身内在规律”的文学史叙述而言,似乎到目前为止,还未有哪部文学史著作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许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是一个例外,该书导论中明确宣称“文学发展过程实在是与人性发展的过程同步的”[1]。以此为纲,该书的不少论述确给人以很新鲜的感受。当然,章、骆之作也引起了不少争议,这里不关注这一点,我们想说的只是,“文学与人性同步发展”的设定固然有合理的地方,但毕竟没有针对“中国文学”,以此为纲的中国文学史编写当然还不能满足我们对中国文学史“自身内在规律”独特性的认识要求.
在一定程度上,能更好地满足这个要求的是文史大家钱穆先生关于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一个总体观察:“雅化”。此观点是钱穆先生20世纪60年代在海外发表的。早在1987年,大陆的巴蜀书社即重印了集中表达此观点的海外版《中国文学讲演集》一书。2002年,三联书店再次重印《中国文学讲演集》的扩充本《中国文学论丛》的海外版。应该说,以上两本著作在大陆出版已颇有一段时间了,但论其效应,恐怕不能不承认,钱穆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国内文学研究者的太多回应。是钱穆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认知价值?笔者认为不是这样的,故下文不揣浅陋,试图剖析一下钱穆“雅化”的文学史发生发展观,期望能展示这样两层意思:一、“雅化”概念新颖而贴切地描述了中国传统文学特别是唐以前文学发生发展的大势,具有直接的认知意义;二、“雅化”在“重写文学史”、“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等论题的探讨中,直接相关于当代的文学史、文学理论的研究。并且,“雅化”说法源于一种历史情境中的文学史观察,这对于我们当下文学研究也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
一、“雅化”概念内涵
所谓“雅化”,指一种不断冲破特定时空范围的广大化、持久化的演进趋势。钱穆以为,这样的“雅化”构成了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旋律。之所以取“雅化”这样一个说法,正源于中国传统文学的雅俗之论。“雅本为西周时代西方之土音,因西周人统一了当时的中国,于是西方之雅,遂获得其普遍性。文学之特富于普遍性者遂称为雅。俗则指其限于地域性而言。又自此引申,凡文学之特富传统性者亦称雅。俗则指其限于时间性而言。孰不期望其文学作品之流传之广与持续之久,故中国文学尚雅一观念,实乃绝无可以非难。”[2]31-32钱穆认定中国文学“尚雅”,持论看似寻常,但其新鲜深刻之处在于:他改变了雅、俗仅仅指人们的某种感觉、品味的通常看法,赋予其时、空两方面的客观内容。当然,钱穆并非在任意地改变雅、俗两字的通常意义,他实际上是指出了支撑两字通常意义背后的不为一般人所知的客观内容。的确,通常所谓鄙俗,客观而言即指那种只能在狭小时空范围内流行的东西,所谓高雅,则指向那种在更广大时空中流行的东西。或许有人说,“曲高和寡”,高雅的东西怎么是更流行的?此疑问还是只看一时一地,试想一下千年万年的流行,试想一下经典的永恒。
但人们可能还会有疑问:“孰不期望其文学作品之流传之广与持续之久”,此种“雅化”追求,固属作者之常情,但它能用来解释上千年的中国文学之发展吗?钱穆的“雅化”说法是不是简单了一些?通观钱穆的论述,笔者以为,“雅化”一词固然简单,但它对于中国文学史演进的解释,确有提纲挈领之效果。以下请展示钱穆“雅化”的文学史现象描述。
二、“雅化”的文学史现象及其原因
钱穆从《诗经》开始,首先指出中国文学史源头的“雅化”。“十五国风所载各诗,凡以登之庙堂,被之管弦,则殆已经王朝及各国士大夫之增润修饰,非复原制。……风格意境,相差不太远,则早已收化一风同之效矣。……当时声诗一贯,所谓十五国风,乃与雅颂同一雅言,同一雅乐,固已经一番统一之陶铸。……循此以往,中国文学之风土情味日以消失,而大通之气度,日以长成。”[2]10以上所涉及的《诗经》事实乃文学史常识,但钱穆对此常识的“雅化”理解却独出心裁。《诗经》所载之作品,时间跨度数百年,地域跨度上千里,但音韵统一、风格统一、意境统一。我们知道这些事实,由此我们争论的是“孔子删诗”的问题、十五国风还算不算民歌的问题等等,但从没想到中国文学史的这个“光辉起点”——其光辉在于“风土情味日以消失,而大通之气度,日以长成”。钱穆的解释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无疑,他的解释更有历史的深厚眼光,能让我们更富意味地理解中国文学的开端。
进而钱穆又论及楚辞、汉赋、汉乐府,“所谓楚辞吴歌,此乃十五国风所未收,而战国以下崛起称盛。然骚赋之与雅诗,早自汇通而趋于一流。故楚辞以地方性始,而不以地方性终,乃以新的地方风味与地方色彩融入传统文学之全体而益增其美富。……所谓汉乐府,亦即古者十五国风之遗意,亦自不脱其乡土之情味与色调。然当时文学大流,则不在风诗而在骚赋。魏晋以下诗人模拟乐府旧题者绵辍不绝,此如汉人之效为楚辞,前此地方性之风味,早已融解于共通之文学大流。”[2]10-11“楚辞以地方性始,而不以地方性终”,汉乐府同样“以地方性始,而不以地方性终”,终“融解于共通之文学大流”。钱穆此论,再次从人所共知的事实中,有力地揭示了中国文学史“雅化”的演进趋势,“(楚辞、汉乐府)实不在其能代表地方性,而尤在其能代表共通性,此即所谓雅化也。”[2]11
从《诗经》到楚辞、汉乐府再到唐诗、宋词,应该说,钱穆揭示的中国文学史的“雅化”演进是不争之论,那么唐宋以后呢?小说的兴起或许依然有“雅化”的一面(如谓其完全“雅化”,则令人感到不安),那么戏曲呢?特别是面对各个地方戏曲的繁盛,如昆曲等,又该如何判定?实际上,我们知道,小说、戏曲在文学领域内的崇高地位,是现代的文学理论带来的认识结果。就中国固有的文学传统而言,小说、戏曲终不能登大雅之堂。因此,钱穆用以揭示中国文学“大统”的“雅化”一词,并不能直接地用在小说、戏曲的兴起与演变上。但这样一来,问题也出现了——是否可以说,“雅化”的文学史进程只到唐宋为止?钱穆没有这样说。针对小说、戏曲的兴起,他只是强调文学“大统”的重要,“自唐之中晚期,迄于现代,中国文学中,小说戏曲等,开始占有重要地位。此下此一趋势当望其逐步加强,此亦可谓是中国文学园地上一可欢迎之新客莅止。然我们实不当认此才始是文学,更不当一笔抹煞了中国以往文学大统。”[2]47钱穆的意思很明显,他认为中晚唐以前,中国文学的“大统”已经形成,他所讲的“雅化”是针对中国文学的“大统”而言。但我们还是要问,能不能把“雅化”的观点贯彻到底,进一步用其去解释唐宋以后文学传统的演进?钱穆没有这样做。但笔者以为,这并非不可能。从原则上说,第一,中国文学的大传统,亦即经典传统,或曰诗文传统,从先秦到清末从未中断;第二,唐宋以后戏曲、小说的勃兴并没有改变诗文为正统、为主流的文学局面;第三,戏曲、小说固然明显有“俗”的一面,但它们既然是在中国文学大传统中兴起与演变,就不能不受“雅化”趋势的影响。以上三原则告诉我们,以钱穆的“雅化”观去看唐宋以后文学史的发展,不是不可以,只不过需要更全面、更辩证罢了。
中国文学何以从一开始就奠定了“雅化”的趋势?钱穆主要将其归因于大一统的社会政治格局的早早形成。钱穆从中西古代文学代表体裁的不同说起:“西方古代如希腊有史诗与剧曲,此为西方文学两大宗,而在中土则两者皆不盛。此何故?曰,此无难知,盖即随俗与雅化两型演进之不同所致也。荷马略当耶稣纪元前9世纪,适值中国西周历宣之际。其时希腊尚无书籍,无学校,无戏院,亦尚无国家,无市府。……中国当大一统王朝中兴之烈,其文学为上行。希腊在支离破碎,漫无统纪之时,其文学为下行。故中国古诗亦可以征史,而史与诗已分途。希腊则仅以在野诗人演述民间传说神话而代官史之职。……正以中国早成大国,早有正确之记载,故如神话剧曲一类民间传说,所谓齐东野人之语,不以登大雅之堂也。其后中国大一统局面愈益焕炳,文化传统愈益光辉,学者顺流争相雅化。”[2]12-13史诗的存在,对世界各民族的早期文学发展而言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为什么中国(汉民族)古代文学早期的发展中没有宏大的史诗?许多人谈论过此问题,但眼光如钱穆者似还未有。作为史学家的钱穆的回答清晰而客观、简洁而深刻:“正以中国早成大国,早有正确之记载,故如神话剧曲一类民间传说,所谓齐东野人之语,不以登大雅之堂也。”一句话,中国(汉民族)没有史诗,那是因为没有这个需要,大一统政治的早早形成,正规史书的早早出现,文学与史学的早早分途,使得中国(汉民族)早已不需要宏大的史诗了。钱穆的回答可能不是中国(汉民族)没有史诗的唯一原因,但肯定是解释此文学现象的一个深刻而客观的原因。
一般意义上的史诗的缺失以外,中国戏曲艺术的发达很迟、成熟很晚也是一个较为引人注目的文学史现象。钱穆顺大一统的政治原因出发,进一步解释了这个问题。“春秋时未尝无优伶,优孟衣冠,惟妙惟肖,亦足感悟于楚王,而有其所建白,然志在行道天下者,则于此有所不暇、不屑……具体乃剧曲所贵,故亚里斯多芬之喜剧,乃即以同时人苏格拉底为题材,若在中国,则临淄剧情不习熟于咸阳,鄢郢衣冠不见赏于邯郸。局于偏方,格于大通,诚使中国有伊士奇、斯多芬,斯亦一乡里艺人而已。”[2]14钱穆的意思很明白,他认为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政治规模培养了士人胸怀“天下”的眼光气度,而戏曲艺术贵于表现具体人物的言行举止、衣帽容饰等,限于当时的条件,这样的戏曲艺术必然是局限于小地方的表演,所以“志在行道天下者,则于此有所不暇、不屑……文人之兴感群怨,自不甘自限于此稀薄疏落之一隅……故中国民族文学之才思,乃不于戏剧见之也”[2]10-14。也许有人会说:戏曲艺术也可以小中见大,俗中见雅,由地方而观天下等等,钱穆的判断是否有点武断了?对此疑问,我们想回答的是:第一,“随俗”应该是戏曲艺术的一个基本取向,至于“俗中见雅”则非待优秀的戏曲不可,并且还离不开观众高水平的鉴赏,故钱穆以“局于偏方,格于大通”去总体上观评戏曲,未为不可。第二,同对史诗现象的解释一样,我们同样认为钱穆对中国文学中戏曲现象的解释不是唯一的答案,但肯定也是必须重视不能绕过的一个回答。
三、“雅化”观的当代启示
以上主要是对钱穆观点的评述,我们更关心的是,“雅化”观是否有助于我们当代的学术思考?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就钱穆“雅化”观的具体内容而言,它至少在两个议题上直接对我们当代的中国文学研究有启示意义。其一,对“重写文学史”的启示,其二,对“区域文学”探讨的启示。此外,作为一种历史情境中的文学史观察,“雅化”观对于我们当下的文学研究也有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
针对具体议题,其一,我们完全可以说,钱穆的“雅化”文学演进观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重新书写开启了一条极富启发意味的思路。学界“重写文学史”话题,最早由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的几位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提出,后很快波及到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直到今天,依然不断有人撰文探讨文学史的重新写作问题。就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重新写作而言,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努力方向:微观和宏观。微观方面,如《诗经》成书过程、五言诗如何兴起、词的源头等等,宏观方面,则指两三千年的文学史叙述框架问题、内在发展逻辑问题。一本真正有创见的“重新写作”的文学史著作,一定会在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视野,但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以高标准去衡量,说这样“重新写作”的文学史还未出现,也是可以的。检讨新时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的论著,一方面,在局部、微观方面有重要突破之作不是没有,也在相当范围内赢得了学界的激赏,如木斋的词史研究、古诗十九首研究等。[3]另一方面,虽有几部新的文学史受到好评,如前文所述的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及当前流行的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但总体上,还未有一部学界公认的能在整体上有本质性突破的文学史著作出现。这里所谓“在整体上有本质性突破”的说法,其实有点笼统,我们更可以追问:到底是在哪一个方向、哪一个层面上才有望达成“在整体上有本质性突破”?笔者以为,立足于中国文学固有的价值观,揭示中国文学史固有的发展规律,而不是被“审美”、“人性”等西方概念牵着鼻子走,这是“重写文学史”必须要考虑的一个突破方向。这也是说,制约“重写文学史”的关键还是先在的文学史观的问题,是一个能否真正摆脱百年来西方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带来的文学史观的问题。钱穆不是文学史专家,他的著作对于具体的微观层面的文学史研究帮助不是很大,但钱穆是一个能真正同情地阐说民族历史的文化大师,他的“雅化”的文学史演进观不是对西方文论、西方美学的注解,而是真正以中国为本位的文学史言说。通过前文的介绍,我们已看出,“雅化”作为一种宏观的文学史观,它的确带来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理解中国文学史自身内在演进趋势的新视野。我们相信,在这种新视野的观照下,再投入具体的微观层面的文学史研究,“重写中国文学史”就现实地具有了一条可行的道路了。
再论其二。近年来,对“区域文学”的探讨渐成热点,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学”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恰成对比的是,钱穆的“雅化”说则强调对地方性的突破。很显然,钱论原则上不关心“区域文学”,但是,两者不正有一种反向的相关关系吗?“雅化”说能提出,那是因为它看到了地方性,“区域文学”在当今被重视,那是因为它不满足于某种大一统的文学叙述,两者在同时看到文学发展的整体和局部的两端上是相通的。就此而言,当今“区域文学”的热烈探讨,可以表现对传统的某种大一统文学叙事的不满足,但它绝不能无视文学发展的大一统性质的存在。关键在于,什么样的大一统认识?这样的大一统认识是否真正契合了文学史的发展?我们认为,钱穆的“雅化”说是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大一统性质的一个深刻识见,它对于“区域文学”的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启示与指导意义。试举一例。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考·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骄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此说诚为卓识,但它可能也带来了某种文学史认识的误导。如几十年来通行的文学史写作,差不多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王国维之说来确定各朝代文学叙述的重点与篇幅的。但真实的文学史发展一定是这样的吗?当今的地域文学研究中,明清文学占了最大比例,研究者们从“岭南文学”“湖南文学”“徽州文学”“陕西文学”“黑龙江文学”等等地域文学中,大量发掘到的作品是诗文,而不是通行文学史中着重叙述的戏曲、小说。这个现象说明什么?人们很自然地想到:这是诗文传统的强大。我们则要进一步说:这是正统文学的强大,是中国文学史大一统演进趋势的强大。而这个演进趋势就是“雅化”。而当我们区域文学的研究者注意到钱穆的“雅化”观——一方面关注不同水土产生不同的区域文化,不同区域文化中又产生不同的区域文学,另一方面又注意到区域文学本身的冲破地域限制的“雅化”,则对区域文学的认识难道不是更合理、更客观吗?
以上两点启示意义,只是就钱穆“雅化”观的具体内容,直接针对当今学界较受关注的相关议题而言,实际上在我们看来,钱穆的“雅化”观更有一种方法论上的启示。我们可以问:钱穆何以能得出此观点?这个提问并非没有意义,因为,第一,“雅化”论确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觉,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看法。第二,钱穆似乎只是在一种常识的基础上很轻易、很自然地得出了此看法。于是就不得不问:为什么别人就看不见这个“雅化”?我们的回答是:因为钱穆真能回归于一种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观察文学史演变,而他人则不能或做得很不够。所谓“历史情境中的观察”,其内涵并无高深之处,无非是说处身于一种具体、活泼、活生生的历史发生中去观察。但显然,道理上明白它是一回事,真能做好它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也许在其最高境界上,非大家不能为。钱穆“雅化”的中国文学史演进观察,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证。
钱穆首先是史学大家,他能从一种宏阔的历史视角去观察文学,这丝毫不令人奇怪。难能可贵的是,视角虽然宏阔,论述却不笼统,尤其是在篇幅简短的前提下(《中国文学论丛》是一部演讲论文集,该书直接谈论“雅化”的不过其中两三篇),钱穆却能从细节去论述,这不能不说体现了作者的洞察力。如前文举过的例子,“故亚里斯多芬之喜剧,乃即以同时人苏格拉底为题材,若在中国,则临淄剧情不习熟于咸阳,鄢郢衣冠不见赏于邯郸”云云,就很生动地说明,在各城邦独立成国的古希腊,各国文人剧作家等必然首先为本地人服务,于是以方言土语,以本地人喜闻乐见之题材、形式构成的戏剧说唱等艺术也就自然而然地发达了。相较而言,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早早形成,在此客观情势感召下,文人学士的追求绝不会限于一国一地。以司马相如为例,钱穆说:“下逮汉初,蜀中文化亦辟。今观《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所载,其风土神话,亦殊玮瑰绝丽。然以司马相如不世卓荦之才,终亦不甘自限于乡土,未尝秉笔述此以媚俗。必远游梁国……卓然成汉赋大国手。”[2]13蜀国的司马相如如此,古代中国任何地方的一流文人同样如此,肯定不会甘心于“只为本地人服务”,其创作必寄情“雅化”,以求通达天下。这样就可以想像,由于欠缺一流文人的支持,偏重于地方文化的(至少在早期可以这样说)戏剧说唱等艺术形式,在中国文学史上成熟很晚也就不难理解了。细细体会钱穆此处的论说方式,在中希(古希腊)比较的大视野下,在揭示中国文学发展的总体特征这个大目标下,作者谈论的是以苏格拉底为题材的喜剧,谈的是“临淄剧情不习熟于咸阳,鄢郢衣冠不见赏于邯郸”,谈的是临邛人司马相如不甘心做一个临邛成都间人,这使我们一下子就回到了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了,并且在中希具体的历史情境比较中一下子就感受到了何谓“随俗”,何谓“雅化”。这正是前文所谓“历史情境中的观察”。更重要的是,在钱穆的《中国文学论丛》中,这种“历史情境中的观察”比比皆是,并且总能使得各种各样的常识性的知识、材料立刻焕发出非同一般的意味。限于篇幅,此处不能多举,读者可自行检阅。
当然,钱穆如此举重若轻的“历史情境中的观察”,绝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它首先表征了一位史学大家的史识境界,这不是他人能够直接学来的东西。但除此以外,对于我们现代的文学研究者来说,它依然可以有方法论层面上的启示:文学史或者说文学现象本身永远是鲜活的,只有不被一些先在的大概念如“文学”、“审美”、“抒情”、“叙事”等等束缚住,从活生生的文学现象出发,才可能得出有价值的洞见。这是一个大话题,不是本文要展开的内容。想暗示的只是,站在方法论角度,或许我们可以说,钱穆对中国文学史“雅化”的观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当代现象学所要求的“回到事情本身”的认识原则。
[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2]钱 穆.中国文学论丛[M].北京:三联书店,2002.
[3]傅璇宗.引言:关于重写文学史之我见[J].社会科学研究,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