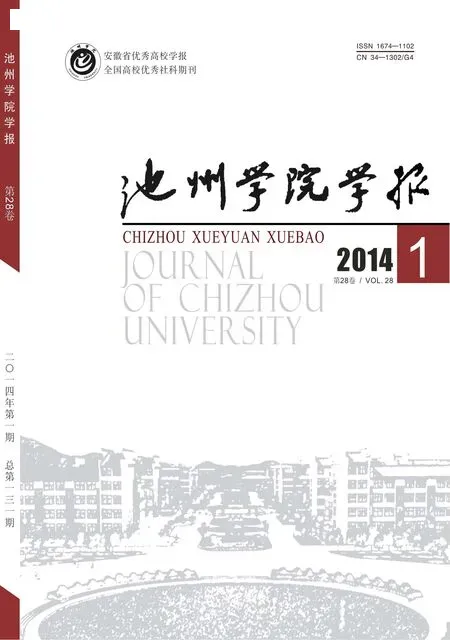历史与文化认同:明清徽州家谱中的中原认同现象考察
徐 彬,祝 虻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
历史与文化认同:明清徽州家谱中的中原认同现象考察
徐 彬,祝 虻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演进史上,中原作为一个极为特殊的文化地理单元与中华文明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联,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表现出了强大的辐射力,这种辐射力的现实载体就是由中原迁出的一批批移民。这些移民在繁衍生息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强烈的中原认同现象,其实质是认同产生于中原地域上的悠久传统和先进文化。由于迁徙至徽州的宗族族群亦不例外,反映在明清徽州家谱中的这种认同现象就尤其明显。通过考察这种认同现象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契合与反差,能够管窥这些迁徙者们与原住地之间的文化传承等联系,进而在更为原始的层面上了解徽文化的形成。
徽州;家谱;中原认同
明清时期徽州社会居民主要来源于北方中原地区,迁入徽州的“中原衣冠”子孙繁衍,聚族而居,逐渐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宗族区域社会。为维持宗族社会的稳定与延续,提升自身文化内涵,获取更多的现实利益,各宗族除了构建起各自基础性的血脉认同外,还逐步形成了更为广泛的文化认同。在中国古代一直存在将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的传统,对中原的文化认同自然能够标示家族优势文化与悠远历史。同时,历史上又确有大部分中原世家大族迁入徽州并繁衍生息,当这些宗族在追溯自身与中原的联系时,这种历史事实与家族内部有意识形成的文化认同便自然交织在一起。
1 徽州宗族迁徙的历史事实
徽州宗族的形成是中原大族南迁的结果,其构成的主要部分便是由北方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世家大族,尤其是在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与唐末农民大起义时期,大量封建士大夫与仕宦定居徽州,逐渐发展成各自的家族。这些属于士族阶层的封建社会精英分子,或逃避战乱,或向往徽州山水,或宦游徽州,或隐居徽州,均在迁徙至徽州后便定居繁衍[1]。徽州宗族出于溯本清源的目的,往往在家谱中对于这段迁徙事实进行详细的记载,从而保存了家族迁徙的历史史实。
在东汉之前已有中原士族迁居徽州,其中方氏最为典型,其家族世望河南,“汉哀帝时,曰纮,拜丹阳令,后因王莽篡乱,累征不起,遂家于歙之东乡”[2]。方氏后裔逐渐散居徽州各地,成为本地著姓。到西晋“永嘉之乱”时,以王氏、谢氏为代表的中原士族大量南迁,并散居江南各地。这些世家大族的后裔虽迁居江南各地,但多奉此时的南渡士大夫为自身先祖,如徽州谢氏就以谢安为自身先祖,“谢出晋太傅文靖公安之十三世孙曰杰,仕隋,为歙州教授,由会稽始家歙之中鹄乡”[3]。徽州王氏亦不例外,其支脉就有以王导之后自居,“晋丞相导,由琅琊迁江左;至唐,曰璧,字大献,由江左迁新安”[3]。除永嘉南渡士族后裔迁居徽州外,还有一些是直接迁居徽州的,如徽州俞氏,“俞待制献可,字昌言,歙县人,其先居河间,晋永嘉之乱徙新安”[3]。唐末,为逃避黄巢大起义的打击,封建士大夫纷纷避祸江南,大量直接迁居徽州。《新安名族志》记载,唐末,河内(今河南沁阳市)查氏族人便为了逃避黄巢起义迁居徽州,“世居河内县,传至唐河湖参议之裔曰师诣,从九江匡山药炉源徙宣城,转徙黄墩,官至游击将军、折冲都尉。”其后裔便是南唐枢密使、谏议大夫的休宁查文徽。另有徽州王氏王仲舒一脉亦是如此,“五世孙仲舒……游宦江南,家于宣城之连塘。生子七人,长曰初,进士及第;初生希羽,避黄巢乱于歙之黄墩,广明元年巢渡淮,复迁泽富,今谓王村一世祖也”[3]。史书记载王仲舒为河南太原人,其后裔王希羽则已为歙州人,“天复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等及第。希羽,歙州人也,辞艺优博”[7]。这种大规模的士人迁入对徽州地区人口结构和地方风俗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罗愿《新安志》卷一《风俗》中的记载:“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4]。北宋末年,女真贵族征服中原,宋王朝偏安江南,又有大批士大夫和仕宦跟随南渡,避地徽州。此次人口南迁,作为其中主体的赵氏亦有迁居徽州,“出僖祖文献朓之后,迄太祖造宋禅于太宗,太宗长子汉恭宪王元佐生懿恭王允升,……士禬三子:秉义郎不仞、朝散郎不彼、正义大夫不俄,俱扈从高宗南渡,遂居歙之岩镇”[3]。除皇室外,还有一些北宋仕宦也迁居徽州,徽州宋氏先祖即是此时迁居徽州的,“其先开封人……子贶,字益谦,补将仕郎,为新安尉,因乐山水之胜,遂家焉”[3]。宋贶其祖曾随周公望出使金朝,“建炎三年周公望奉使金,即行辟惠直随使节,……子贶,字益谦……晚徙居于歙,累以恩赠父,官至少师”[6]。史书其人则长期定居徽州,并认同其为歙县人,“贶,歙县人”[7]。
徽州宗族处于现实情况考虑尤其重视对于家族先祖迁徙情况的阐述,在修纂家谱时,多会单独辟出《源流序》等予以介绍。其中一些具有历史意识的文人所修之家谱,更是重视从历史事实的角度出发解读家族迁徙史,明代史学家程敏政就在其修纂的《新安程氏统宗世谱》中以《谱辨》为平台,通过列举前人的历史撰述来考证本族迁徙情形。以这些徽州家谱为底本所纂修成的《新安名族志》中所记载的徽州宗族迁徙史料虽然有人为臆断因素,但其中不乏历史事实的存在。尤其到了清代,考证之风的盛行也影响到了徽州文人对于自身先祖迁徙史的阐述,更加偏重于从历史事实出发。戴震在阐述其戴氏家族迁徙情况时所利用的资料为《礼记·大传》这类当时流传极为广泛的图书,甚至得出“盖谱牒所记,戴公以下,护公以上,不审信也”[9]。这一明确否定之说,表明家谱中的记载有与历史事实不符的情况。但是历史事实缺乏并未影响徽州家谱世系构建的活动,家谱中同时体现了从文化认同出发所形成的徽州家族迁徙史。
2 徽州宗族文化认同的表现
徽州宗族社会的重要构成主体即是中原移民,对于迁入者来说,一个明确的家族共同体认同才能保证家族的存在与延续。而仅凭血脉延续所形成的天然家族认同并不能保证裂变后的家族共同体还能一直保持团结。这样一来,就要求各个徽州宗族形成自身独特的家族文化认同。同时,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之间的界限区分已渐趋明朗,宗族社会已呈稳定之态,只有成为世家大族,保证自身的文化优势,才能更多的占有资源与权利。同样形成后的世家大族重要维系纽带便是自身独特的文化认同。文化传统的形成需要宗族在时间上的积累,而徽州宗族就是通过姓氏起源、始祖追溯和世望记载三种方式来完成的自身积累。在这种积累过程中,徽州宗族自然就建立了与中原的紧密联系,从而形成了广泛的中原认同,这种地域认同正是对于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家族独特文化认同的直接表现形式。
2.1 姓氏起源方式
明清徽州族谱中普遍存在有阐述自身姓氏的内容,姓氏起源几乎都能追溯至周代以前甚至于神话故事,在地域则集中于以河南为代表的中原地区。究其原因主要是家族借此来强调自己家族渊源之悠久,并非是后期由于政治等原因改变而来。其姓氏起源的历史已无确切的历史依据,其中的相关内容更多的是家族文化认同的一部分。
在徽州族谱中对于姓氏源流的阐述,更多地体现了文化认同而非历史事实的考证,以具有传奇起源故事为载体的文化认同代替了家族真实历史起源的记载,如徽州著姓汪氏家族内就有关于姓氏起源的传说故事,“汪始于颍川侯,鲁成公黑肱次子,夫人姒氏生侯,有文在手曰‘汪’,遂以名之,后有功于鲁,食采颍川,号汪侯,子孙因以为氏”[3]。这种故事在时间上几乎都在秦朝之前,有的甚至直接将本族姓氏起源安于被视为中华共祖的黄帝轩辕氏。同样以徽州汪氏为例,其家谱中就有这种追溯,“溯始于黄帝以及周公旦,至成公黑肱之支子,蔓延海内”[91]。在记载起源人物的同时,徽州家族族谱中还详细阐述姓氏起源的地点,并将其具体情形以图象的方式确定下来,如徽州汪氏族谱中就有《颍川辨》和《颍川受氏祖宗木本水源地图》[10]。这种几乎以故事为参考依据的记载极为普遍,一些传统史书编纂者甚至历史学家所修族谱亦相信此即其家族姓氏的历史来源。明代著名史学家程敏政所修《程氏统宗世谱》中就相关阐述,“程以国氏始于休父,世望安定;而婴公事赵家邯郸,再望广平,此固程之所自出者也”[11]。而在金门诏所撰《休宁金氏族谱》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金门诏曾编纂过《明史》,又参加过《古今图书集成》的修纂,理应受乾嘉学派影响而极重考证,却在阐释金氏由来时,全无论证。此族视西汉时期金日磾为始祖,并点明其是赐姓为金,但却又将自身姓氏来源安置于传说中的金天氏,继而推至黄帝轩辕氏,“溯而上之则为金天氏,谓其以金德王天下,故金宗之也,又上之为黄帝轩辕氏,谓其为庶姓之始祖也”[12]。这种缺乏历史事实的叙述可从徽州宗族内部对中原文化认同中得到合理解释。
2.2 始祖追溯方式
明清徽州社会普遍认为家谱即是为本族敬宗收族所用,为达到这一目的,徽州宗族纷纷构造出属于自身的显赫先祖。按其中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徽州宗族多以两种方法确定自身先祖:一是将正史中同姓的将相名人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贯成世系,再取离自己始祖最近的一位作为直系祖先;二是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找到同姓的一族,将其中最后的传人与自己的始祖衔接[13]。通过这两种方案加上对原有系谱的继承,徽州各族已然确立了本族先祖,其存在时间大部分都是宋代以前,并且可以将之归为高官重臣、官宦世家或文化名人三类,如徽州曹氏视晚唐重臣曹全晸为自身先祖,徽州毕氏以累世簪缨的毕憬后裔自居,徽州陈氏则视东汉著名儒士陈实为其脉之祖。通过这种选择方式,徽州宗族往往能够和之前的士族联系到一起,如徽州徐氏家族就以晚唐宰相徐商、徐彦若为自身先祖,而将始祖追溯至属于南朝士族的徐摛。
由于在宋代以前中原地区一直属于中央政权的核心统治区域,正史中出现了大量出身中原的将相名人。以河南为例,根据丁文江对二十四史中辟有列传的5769个历史人物的地理分布所进行的研究,在明代以前河南地区一直稳居全国各地区的前三甲,尤其是在宋代以前,一直居于首位[14]。同时仅在隋唐两朝,籍贯能够确定为河南的宰相就有69人,约占总数的20%[15]。这种巨大数量的人才聚集使得通过上述两种方式加之继承之前的记载所产出的徽州宗族始祖自然有相当一部分的籍贯为河南。这种看似自然的结果实际上正是在徽州宗族按上述选择方式有意识而为的。据《新安名族志》所载93个姓氏中,大部分都明确将自身始祖籍贯定于中原地区。这种始祖创造方法是以正史记载为出发点,符合一定的历史事实,进而产生的中原认同往往也令族中后裔信服。这种认同感在由后裔撰写的族谱谱序中就被明确表达出来,如明朝正德年间毕氏后人所撰《毕氏谱序》中就有“吾毕氏自少卿憬公以硕胄始望河南”[16]的记载。在此之外由于政权变动的因素,统治中心移至河南后,往往世家大族中的族人亦会随之迁徙至河南。这种情况在一些徽州家族追溯始祖时也会有所反应,其表现就在对于徽州宗族先世迁徙情形的构建。典型的代表就是休宁金氏家族,在其族谱中就有随刘秀建立东汉政权而迁居南阳的记载,“珍公因光武都洛阳,遂迁南阳……九世同居,旌为义门,复望于南阳……汉代世家与国同朽者,唯金氏而已”[12]。这种记载在正史中只能找到零星的个别记载,但通过建立起与河南的此种联系产生了族人对河南南阳的地域认同,也提高了休宁金氏的历史地位。甚至还有部分徽州家族的中原认同则是直接由家族自身创造的,这一情形主要是由于家族始祖在正史上未有明确籍贯记载。徽州曹氏的情况就是如此,始祖曹全晸虽是唐王朝镇压黄巢起义的重要领军人物之一,但在正史之中对其家族却记载寥寥,仅模糊记载有一子名为曹存实。然而在明代万历年间修成的《曹氏统宗世谱》中不仅详细记载了曹全晸家族情形,还明确点出曹全晸为“河南汴梁祥符县忠良乡”[17]人,同时又记载家族在迁居黄墩之前就居住于河南汴梁忠良乡,“唐昭宗起自汴梁忠良乡”[17]。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其家族是认同河南为先祖居住地的。无论是以正史记载的始祖籍贯还是以其他方式建立起来的徽州宗族与河南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旦被记载入宗族家谱,其意义即从历史事实上的过去变为了文化认同上的过去,产生出来的河南认同便成了这种文化认同的最佳外延形式之一了。
2.3 世望记载方式
在历史上,望、世望往往直接代替籍贯的存在,其内在的原因就是世望代表着高门大姓,是家族影响力在地方的体现。其中的典型就是郡望,追溯郡望的源流,可以看出其是以世家大族传统居住地为载体,以家族传统为标志。这种家族传统虽直接源自于家族先祖的累世为官,但更多地确是体现在先祖的高尚德行和家族的深厚文化积淀上。郡望产生之后,具体的功能与内涵不断演变,随着隋唐时期选官制度的变革,士族随之丧失了由门第带来的政治特权,郡望逐渐也随之变为传统士族社会地位的传统象征符号[18]。自唐以后,标示世望的历史现象虽然在史册中逐渐湮没,但在家谱中却依然广泛存在,并一直延续至今。在现存徽州家谱中,对于家族世望的记载已是普遍现象,其中一些人口众多的大家巨族甚至会有辨析本族世望所在地的记载。这些记载以唐代《氏族志》等史料为基础,结合自身对于始祖的追溯,最终确定本族郡望,其中大部分的地理位置都位于河南。
中原本身就是士族聚居之地,世望的数量十分之多,仅以河南汝南一地为郡望的姓氏就有:周、昌、袁、殷、齐、和、蓝、危、梅、盛、应、鞠、仰、咸、廖、沙、盖、麹(麦)、糜等19个之多[19]。对于这些姓氏的世望之地,大部分徽州家族选择了直接继承,如徽州周氏,“秦并其地,遂为汝南著姓”[20]。并对世望所在进行辨析,如徽州叶氏就在家谱中利用《南阳辨》对自身世望南阳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今为南阳府,其属有南阳县,在中州之南,故以南阳称之,而叶氏有自叶迁居其县之南顿乡高贵里者,氏族蕃盛。至唐搜集天下望姓,遂以南阳为望族至今,称叶姓属之南阳”[21]。有的则专辟一章阐述本族世望,如徽州方氏:“相传方自雷祖四十六世孙显,虞舜时封河南万户侯,子孙袭封爵,世居其地,此河南郡望所由始也”[22]。有些徽州家族甚至在纂修自身族谱时就以世望所在为谱名,如清代徽州项氏修谱时就以《汝南项氏续修宗谱》为名,徽州吕氏亦有名为《河南新安吕氏宗谱》的家谱。还有些家族还通过书写出世望之地作为全谱正文开篇,以宣扬自身世望,如徽州郑氏族谱中就有王安石所书“荥阳世家”,徽州方氏族谱中则有“河南嫡派”。通过以不同的方式在家族族谱中记载、强调本族世望所在地,徽州家族实现了世望认同,也自然形成了这一形式的中原认同。
3 历史与文化认同的交融与演化
家谱是记载一家一姓世系和人物事迹的文献,可以被视为是一家一姓之历史。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就曾说过,“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碟,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23]。同时家谱之中存在的妄相假托,牵强附会,对此传统社会士大夫亦有清醒的认识,唐代学者颜师古就曾有言,“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宁足据乎”[24]?实际上,这种矛盾的认识正是家族历史事实与文化认同交织表现出的普遍形态。而这种交织的不断演化,特别是其中的家族文化认同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徽州宗族文化中的重要一部分。
3.1 历史事实与文化认同的交融
通过构建出徽州家族的中原认同,家族自身的文化认同自然表现出来。在这种构建过程中,徽州宗族迁徙的历史事实自然与家族文化认同交织在一起。实际上,明清徽州家谱的编纂者始终具有较强的历史意识,即是在家谱中蕴含有“以稽先世,以贻将来”的历史传承思想[25]。如明永乐七年(1409),赵文就在在所作的《环溪朱氏谱序》中说:“甚矣,谱之不可不作也,谱不作则支派无自而明,孝敬无自而崇,族无自而睦,谱其可以无作乎?古之君子所以甚重也,若宋欧阳公、苏老泉咸作谱以稽先世,以贻将来,良可尚也”[26]。同样的论述,在徽州家族族人中亦能找到,明崇祯年间吴文班:“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史纪世代兴亡承祚继统褒贬抑扬以昭来世,谱系姓氏源流序次昭穆聚宗收族以贻后昆。史非玉堂硕彦弗克纂修,谱非博学隆望不能编辑。故国史则推班马,家史则称欧苏,应斯任者必待其人”[27]。清朝徽州学者程拔先也有类似论述:“家有谱犹国有史也,国有史而后是非明,得失定。家有谱而后支系叙,昭穆分,若四肢之联而不乱,气脉之贯而相能也”[28]。甚至在明确要求修谱人据实记载,“家之有谱,家之史也,修之云者据事实而纂修之”[29]。
从上面这些论断显然可以看出明清徽州家谱编纂者的历史意识并不纯粹,对于历史事实的要求更多地表现在对于现在血脉延续的记载上,而对于家族先祖的历史事实,在认识上就已经与文化认同相互交融。这种交融集中体现在始祖崇拜上,在元代,徽州学者已经认识到徽州宗族以本地历史人物为先祖的始祖崇拜现象,郑千龄说:“尝见郡中大家,程必祖忠壮,汪必祖越国,方必祖鉴湖,吴必祖少微”[30]。而当编纂者试图在家族先祖存在与迁徙等情况上,力图求真时,就会对于这种有意识的交融发出挑战,进而直接威胁家族的文化认同。在这一情况下,族内士大夫往往会出于家族稳定团结的需要而选择家族文化认同,否定可能更为贴近历史现实的考证结果。在明代史学家程敏政于成化年间所修统宗谱刊梓后,徽州程氏内部立刻出现了不少的攻击声音,认为其“冒祖附族”。不仅出现了《新安程氏世谱正宗迁徙注脚纂》这类直接力图推翻其说的著作,民间还出现了大量非理性的声音,直至清代,临溪派榆村人程易还说程敏政“自讳其昧所自出”,“识者谓其家世才名照耀千古,而后嗣终于斩然者,未必非谱之为咎也”[28]这种攻击的产生与延续本身就证明了,相较于历史事实,徽州宗族族人更加在意家族自身的文化认同。虽然明清徽州家族对于自身历史事实有着一定的认识,甚至会有破除盲信的尝试,但在家族发展的现实下,族中更多地会以夸耀自身先祖为出发点修纂家谱,进而在历史事实与文化认同上以后者为先。
3.2 历史与文化认同的演化
家族历史与文化认同的演变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就是成为家族文化的基础,其二则是促进徽州区域文化出现转变。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出现显著变化,同时程朱理学盛行,使得敬祖收族观念在徽州士大夫群体中深深扎根。正是在这种社会现实的影响下,徽州宗族文化才得以最终形成。这种宗族文化是以家族谱系为核心,以族规家法为外延,通过具体的祭祀等实践活动表现出来的。徽州宗族文化是在继承中原宗族文化的基础上,用理学加以阐释、改造后最终形成的。其中的内涵就是尊祖、敬宗、收族,而稳固的基石就是强烈的宗族认同,同时家族早期历史的模糊也为这种文化认同的形成提供充足的空间。在徽州家族确立始祖崇拜之后,又将自身先祖推上了神坛,如休宁陈村陈氏始祖陈禧即为一位地方神灵“土人神而祠之”,胡姓太常卿明星公亦是一样,“民德之,立祠于冈上”[3]。而在明清徽州家谱的修纂上,更是要求详细记载先祖事迹以保证这种文化认同,如《檀岭王氏宗谱》中《凡例》条下就有:“世系宜明也,我王氏遥遥世胄,太子晋以上俱著于天家,似非草莽之臣,所宜殚述”[30];同时这种记载往往是不经历史考证,直接继承旧谱而来,“谱自一世颍川侯,各显祖图像、履历、实迹,咸遵通谱与纂要”[31]。这种方式所形成的家族先祖形象已难与历史事实保持一致,近乎完全属于家族内部的主观创造,而家谱编纂者又将如此记载模式扩展至对于家族先人的记录上,“谱书纪善而不纪恶,为亲者讳也”[32]。如此一来,整个家谱编纂在其历史求真性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但却能令族人产生强烈的宗族认同感,对以尊祖、敬宗、收族特征的徽州宗族文化形成更为有利。
正如《新安名族志》中所反映的迁徙情况看,中原认同在徽州宗族中表现地极为普遍,所形成的中原文化认同,在改变徽州本地风俗的同时,也改变了徽州宗族的文化品格,为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文化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在中原移民迁入之前,山越文化是徽州地区文化的主流。其最大的特点便是民风彪悍,“好为叛乱,难安易动”[33]。直到隋唐时期,山越才被彻底征服,文化特质亦发生改变,渐趋“文雅”。这种转变从宋代开始,至明清时期形成,在方式上就是向中原文化的迅速靠拢,其结果之一是独特宗族文化的形成。对于这种变化,清代《橙阳散志》有着恰如其分的描述:“武劲之风,盛于梁陈隋间,如程忠壮、汪越国,皆以捍卫乡里显。若文艺则振兴于唐宋,如吴少微舒雅诸前哲,悉著望一时,而元明以来,英贤辈出,则彬彬然称东南邹鲁矣”[34],尤其是在宋元时期,以朱熹及其弟子开创的新安理学,对徽州地区影响深远。为了确保徽州地区理学的统治地位,朱熹之后的徽州学者除了确立朱熹为徽州文化象征外,还在理学发源上寻找支撑点。便构建出洛阳程颢、程颐与徽州程氏的血脉联系,最终在明清时期,将徽州冠以“程朱阙里”的称号,“程夫子生洛,朱夫子居闽,人知三夫子洛闽相去之遥,不知两姓之祖同出歙,又同出黄墩之撮土也”[35]。实际上,这一文化地理单位在是历史事实上并不能成立,但在文化认同上却能得以长期延续,其本质上就是徽州宗族中原文化认同的一种外延。
纵观明清徽州家谱,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原认同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认同现象虽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本质上是对于中原文化的服膺,这种文化认同与家族自身历史事实互相交融。这种交融在构成了家族文化基础的同时,也深深影响到了整个徽州文化的形成。对于这种地域认同现象的考察能够更好地阐释徽州宗族文化的深刻内涵,为进一步从徽州家谱出发解读徽州文化提供参考。同时也可以作为从历史学角度对徽州家谱研究的补充。
[1]赵华富.徽州宗族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
[2][清]汤球,黄爽.众家编年体晋史[M].乔治忠,点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
[3][明]戴廷明.程尚宽.新安名族志[M].朱万曙,等,点校,余国庆,审订.合肥:黄山书社,2004.
[4][唐]王定保.唐摭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5][宋]罗愿.新安志[O].文渊阁四库全书485册.
[6][明]林钺,邹壁.太平府.[M].赵子文,点校,赵宏,等,审订.合肥:黄山书社,2009.
[7][宋]刘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9.
[8][清]戴震.戴震全书(六)[M].合肥:黄山书社,1995.
[9]南源汪氏支谱[O].道光二十九年南源敬敷堂刻本.
[10]汪氏宗谱[O].清光绪二年叙伦堂刻本.
[11]程敏政.程氏统宗世谱[O].明成化十八年刻本.
[12]金门诏.休宁金氏族谱[O].清乾隆十三年刻本.
[13]冯剑辉.徽州宗族历史的建构与冲突——以黄墩叙事为中心[J].安徽史学,2007(4):104-112.
[14]张卫东.略论唐五代河南人才的地理分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7):93-97.
[15]余意峰.中国历代宰相籍贯分布的时空变迁规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3):107-110.
[16]毕济川,毕鬰.新安毕氏族谱[O].明正德四年刻本.
[17]曹氏统宗世谱[O].明万历四十三年刻本.
[18]顾向明.3-9世纪崇重“旧望”的价值观及其对社会风俗的影响[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218-313.
[19]李爱军.牛君仪.王宝红.汝南姓氏源流及郡望堂号文化初探[J].天中学刊,2011(8):100-103.
[20]周思栗.笄山周氏洮回派宗谱[O].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21]叶有广.黟县南屏叶氏族谱[O].清嘉庆十七年木活字本.
[22]方善祖.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O].清乾隆十八年刻本.
[23][清]章学诚.文史通义[M].吕思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4][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M].陈文和,等,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00.
[25]徐彬.历史意识与历史编撰理论对明清徽州家谱的影响[J].安徽史学,2010(3):68-72.
[26]汪菊如.义成朱氏宗谱[O].清宣统二年存仁堂木刻活字印本.
[27]吴元孝.临溪吴氏族谱[O].明崇祯十四年刻本.
[28]程士培.新安程氏统宗补正图纂[O].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29]程大鹏.安徽休子阳程氏支谱[O].清光绪元年刻本.
[30]王承波.檀岭王氏宗谱[O].清光绪十四年刻本.
[31]不详.南源汪氏支谱[O].清道光二十九年南源敬敷堂刻本.
[32]汪炳章,等.磻溪汪氏家谱[O].清同治三年刻本.
[33]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4]江绍莲.橙阳散志[O].清嘉庆十二年刻本.
[35]高攀龙.高子遗书[O].文渊阁四库全书.
[责任编辑:余义兵]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y:An Investigation of Central China Identity Phenomenon in Huizhou Genealog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Xu Bin,Zhu M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Anhui 241000)
During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Central China,as an extremely unique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unit,is directly related with Chinese civilization.It has great influence,whose carriers are its emigrants.Central China identity phenomenon is gradually formed where the emigrants lived and procreate,whose essence is identified with long history and advanced culture in Central China.Without exception of the emigrants to Huizhou,the identity is obviously reflected in Huizhou genealogy. The investigation of coincidence and contrast between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facts finds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the emigrants’original places,which helps interpret the formation of Huizhou culture from the primitive perspective.
Huizhou;Genealogy;Central China Identity
K207
A
1674-1104(2014)01-0001-06
10.13420/j.cnki.jczu.2014.01.001
2013-08-17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1&ZD094);国家社科基金(11BZS035)。
徐彬(1971-),男,安徽广德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博导,池州学院皖南民俗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徽学;祝虻(1989-),男,安徽东至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