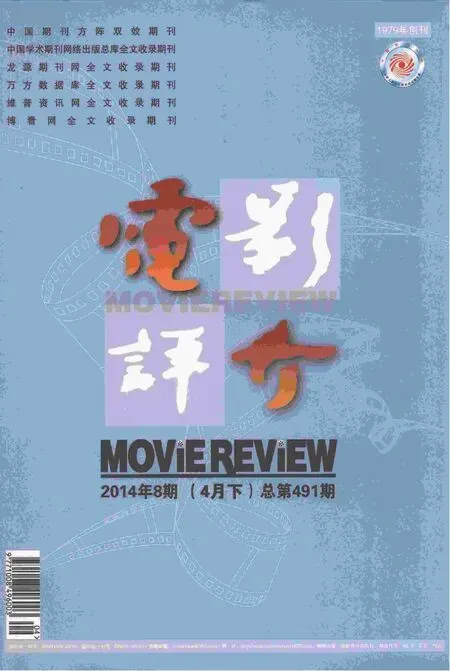贾樟柯《天注定》:在信仰缺失的年代,重寻人与世界的连结
□文/尤宇翔,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生

电影《天注定》剧照
电影必须拍摄的并非世界,而是对世界的信仰,即我们与世界仅存的连结。让我们重新信仰世界,此即现代电影的艺术力量。在这个精神分裂的世界里,我们亟需相信这个世界的理由。
——吉尔·德勒兹
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尚未完成现代化整体建构的疾行过程之中,生活于这个国度里的普通个体被一股巨浪所裹挟,难以找到一块憩息的岩石借之停下疲惫的脚步。作为当代中国最具思想深度的电影作者之一,贾樟柯一直密切关注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努力用镜头去捕捉社会急剧转型中的现实,给我们呈现了“另一个版本的中国故事”。影片《天注定》是贾樟柯导演聚焦当下中国现实的又一部力作,该片继续关注普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切身的生命体验。本文试图择取四个方面对该部影片进行初步探讨:首先,探讨影片所呈现的一种“静态暴力”影像与救赎之路径;其次,关注影片所致力于探索的一种“会面艺术”与共时影像;再次,探讨影片怎样通过虚假力量完成一种个体叙事;最后,探寻在信仰缺失的年代,怎样重寻人与世界的仅存连结。
一、“静态暴力”与救赎之途
《天注定》在海外公映以来获得国际媒体的广泛好评,英国《卫报》盛赞其“带有昆汀·塔伦蒂诺的特质,是贾樟柯版的《低俗小说》”,并称“这部电影是当代中国愤怒、痛苦而讥讽的俯瞰。”影片向我们呈现了四幅“真实”的暴力图景,让我们直面社会现实中赤裸裸的暴力。贾樟柯影片中所呈现的暴力与通常我们在传统武侠、动作类影片中的暴力有何不同?贾樟柯影片所呈现的暴力,我们可暂且称之为一种“静态暴力”影像。在这种影像中,出现的是极其特别的暴力,这种暴力“先行于所有情节刻画着片中的人物,并赋予这些人物角色以生命。这种暴力跟写实主义的暴力反其道而行,在还未构成动作之前‘正值行动’的暴力。”[1]正是这种处于进行中的“静态暴力”突破了我们的底线,达到一种极限情境。
影片中所呈现的“静态暴力”皆发生在弱势群体当中,且其自身必然会承受着不可挽回的代价。这种暴力“总是正值行动中,可是对动作来说这暴力过于激烈……人物因为经受着自身的冲动暴力不寒而栗,也因此作为猎物,成为他自身冲动的牺牲者。”[2]当《天注定》中的大海、三儿、小玉、小辉无法控制自己而激起瞬间即逝的暴力时,这种用表面上的粗野来弥补自身的脆弱,反而将他们的懦弱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论片中的四位主人公的性情如何,这种冲动就本质上来说已经是片中人物角色无法承受的。这种暴力就存在于自身之中,必然地摧毁片中人物或使他沦入损耗或死亡的流变里,这样的暴力才会甦醒。
但贾樟柯终归还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影片没有仅仅止步于暴力的呈现,没有停留于彻底的绝望,而是在试图探寻拯救这种暴力的途径。贾樟柯说:“但光有新闻的解读描绘是不够的,我希望从艺术角度将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而事实上,只有展现了暴力残酷的一面,才能让人们从情感上反感暴力,消除暴力产生的根源。”[3]怎样才能消弭这种“静态暴力”的突然爆发?又如何拯救深陷这种暴力的人物?贾樟柯的影像提出了种种疑问与猜想,然而没有明确的答案,但似乎也给出了一丝希望的微光。
二、“会面艺术”与共时影像
有评论者质疑《天注定》的真实性,这种直接取材于微博上的真实案件,是不是仅仅是一个个案,能否反映当下中国的真实现况?《天注定》中,贾樟柯所呈现或“再现”的不是一个已成的现实,而是一个尚待解读的现实,用巴赞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写实形式,一种离散、省略、游走或散漫的形式,一种将浮动的事件与微弱的连带关系凝成聚块的形式;真实不再是再现,而是被‘对准’;并非再现一个已然被解读的真实,而是对准一个模糊、尚待解读的真实。”[4]这是一种所谓的“会面”的艺术,影片透过一连串出于平常无奇、日常情境的毫无所指,一种纯视效情境骤然浮现,而面对如此情境的影片主人公无法给出任何答案或回应,只能深陷于迷惑之中。《天注定》正是聚焦极其复杂的“日常的庸俗性”,对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日常生活变得如此重要,是因为“最为庸俗或日常的情境亦释放出相当于极限情境的‘静谧力量’”[5],它们使得影像变得无法忍受,并赋予它梦幻般或恶梦似的步调。贾樟柯《天注定》给我们呈现的正是这种日常情境,所有瞬间的暴力皆产生于普通的日常生活情境之中。
贾樟柯的影像呈现的是一种“共时影像”,是过去当刻、当刻的当刻与未来当刻的同步性,它使得时间变得异常可怕而无法解释,三种隐含当刻总会重生、拆解、消失、替代、再造与回返。贾樟柯影像赋予叙事一种新价值,因为它将叙事抽象化为一连串的动作。这种叙事不再是一个人物演出不同的角色,而是两个人物,多个人物诠释同一人物。一种不同世界的当刻同步性。这不再属于处于同一世界的主观观点,而是同一事件发生于不同的客观世界,这个世界皆隐含在该事件中,而事件就如同无法解释的世界。这就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当下中国的复杂现实,这种不断变化,不断分化,无法解释,难以决断的现实。贾樟柯导演的影片正是努力聚焦这种复杂纠缠的当刻现实,瞄准一个尚待解读的现实。换言之,只能用影像聚焦当刻,对准一个模糊、尚待解读的当下中国的复杂现实,而无法做出任何的价值判断。
三、“虚假力量”与个体叙事
《天注定》几乎集聚了贾樟柯的影像人物序列,从早期的《小武》到晚近的《海上传奇》基本上所有的人物都在《天注定》中出场。“影片集合了《世界》拾荒者离场的背影,《三峡好人》呆照般的群像,《无用》开场的平移镜头,《站台》的群众场面。”[6]从《三峡好人》到《天注定》,从好人韩三明到举起枪的大海、三儿,贾樟柯影片中的主人公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嬗变。三峡那里的好人们或重拾旧好,或作别往昔,时过境迁,故事的主人公终于蜕变为《天注定》中的“英雄侠客”,贾樟柯用影像向我们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中国故事。然而问题也与此同时产生,贾樟柯的影像世界是否能与中国现实等同?通过这样的影像序列,能否探索到当代中国的真相?或换言之,有没有这种所谓当代中国的真相?
贾樟柯的影像序列是虚构的,为了获取艺术生命与批判现实的力量,更深刻的电影力量,而选择了一种“伪造叙事”。贾樟柯一直致力于打破剧情片与记录片的界限,记录与虚构相结合,努力探索生命背后的真相,这也正是帕索里尼所谓的“诗化电影”。贾樟柯导演之所以选择这种叙事方式,是因为不存在生命的高低价值之分,生命无需评断,无需辩解,它是无辜的,拥有一种“流变的天真”,外在于善恶。这种叙事可以普通中国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7]《天注定》中的大海、三儿、小玉、小辉都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缺乏关注也无心关注的一群人,然而他们都有各自迥异的卑微生活。影片通过四个虚构故事的呈现,重拾了他们几乎被抹去的自我,我们无法对四位主人公及其生命抉择做出评断,只能体味这些卑微人物的现实遭际。
四、信仰缺失与重寻连结
在《三峡好人》中,有一个镜头是韩三明与几位奉节船工透过人民币图案交流各自的家乡夔门与黄河壶口瀑布风景之美的场景,“他们素朴而沉实的生存行为在实际地和充满感情地读解和欣赏着人民币的符号之美,由此书写着一种家乡美景与金钱实用价值以及人际亲情等多元融汇的货币符号学美学。”[8]这里,人民币在社会底层还尚能充当人与人之间润滑剂的作用。然而在《天注定》中,金钱虽不能说是万恶之源,却也处处充当了人与人之间连结的障碍物所呈现的金钱充满了罪恶,作为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无疑是消极暴戾的。金钱无法充当人与人的连结,那信仰呢?贾樟柯影片中首次出现了一系列的信仰符号:乌金山的毛泽东雕像,三轮车载着的圣母子像,站立于乡间路上的两位圣女,三儿年三十不祭神而拜鬼,“夜归人”夜总会门旁的“命运天注定,灵蛇知祸福”,在东莞雨中车头前的菩萨像。这样的影像序列,反映了当前的中国处于灵魂信仰的真空状态,人与这个世界的仅存的连结断裂了。
什么才是微妙的出路,即“信仰”,但并非信仰另一个世界,而是人与世界的连结,信仰爱或生命。罗西尼西导演如此说:“由于世界因人而变,它越没有人性,就越属于那些或使人相信人与世界仍存在关联的艺术家。”[9]而现代的事实是我们不再相信这个世界,甚至不再相信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件,像爱、死亡等,好像他们仅仅片面相关。人们失落的反应只有信仰可以拯救,唯有对世界的信仰能够将人们重新连结。因此,“电影必须拍摄的并非世界,而是对世界的信仰,即我们与世界仅存的连结。让我们重新信仰这个世界,此即现代电影的本质力量所在。在这个精神分裂的世界里,我们需要相信这个世界的理由。”[10]
“‘青青翠竹,无非般若;郁郁黄华,总是法身’,这就要求人在洞穿世界的虚无本相之后,对生机盎然、鸢飞鱼跃的具象世界重新唤起欣赏和投入的热情。”[11]在此可以确定的是不再信仰另一个世界,也不再是另一个转化过的世界,而是单纯的仅仅信仰身体,信仰这个世界正常的体温,信赖贾樟柯影片序列中的“韩三明”。诚如著名影评人毛尖在评述《天注定》文章中所言:“我热爱‘韩三明’,他在贾樟柯的电影中出没,让人觉得这个世界不会马上沉沦,他是一种保障,仿佛世界尽头的烛光。对于中国人来说,他悄无声息的存在,比上帝带给我们更大的安全感,因为他是这个时代的正常体温和默默心跳,有时候足以弥合岁月的巨大裂痕。”[12]在这样一个信仰缺失的年代,我们需要重寻人与世界的连结,重新信仰身体,信仰这个世界正常的体温,如贾樟柯在《三峡好人》导演手记中所说:“即使在如此绝望的地方,生命本身都会绽放灿烂的颜色。”[13]从上述意义而言,贾樟柯导演的《天注定》给予当下中国一种难得的安全感,成为这个日趋沉沦世界尽头的一盏烛光。
[1][2]吉尔·德勒兹.电影1:运动——影像[M].黄建,译.台北:远流出版社,2003:236,238.
[3]李婷.《天注定》:以感受残酷来消除暴力[N].文汇报,2013-05-23(001).
[4][5][9][10]吉尔·德勒兹.电影 2:时间——影像[M].黄建宏,译.台北:远流出版社,2003:371;378;601;603.
[6]杨俊蕾.《有种》:第六代电影的洄游与谢幕异[J].电影艺术,2014(1):57.
[7]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123.
[8]王一川.异趣沟通与臻没心灵——从影片《三峡好人》到美学[J].文艺争鸣,2007(9):135.
[11]刘成纪.青山道场——庄禅与中国诗学精神[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344.
[12]豆瓣网.毛尖.被撞倒的人[EB/OL].(2014-03-16)[2014-04 -30]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0232092/.
[13]贾樟柯.贾想(1996—2008贾樟柯创作手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