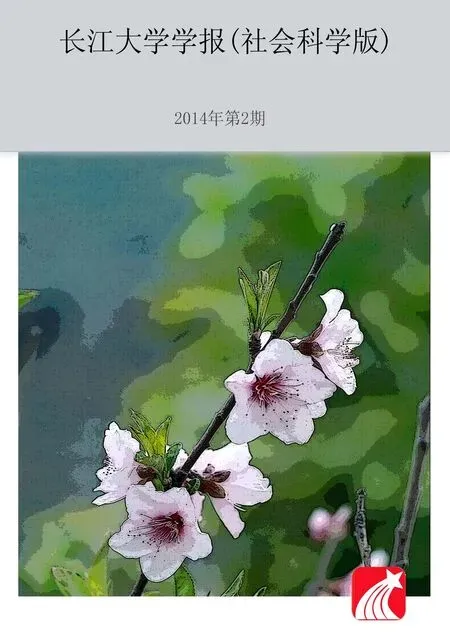福柯“全景敞视主义”的权力分析
王小溪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福柯在其著作《规训与惩罚》中对“全景敞视主义”这一视觉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向人们展示了一种独特的规训手段。如今,全景敞视主义经历了发展演化,渗透到当今人们的生活中,并一直被人们无意识地接受和实践。而这一现象背后,权力一直在无声息地运作着。
一、权力运作的独立性
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是一种非直接肉体惩罚的规训手段,这一规训手段旨在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秩序。全景敞视主义理论的理想形式是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段照到另一端。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囚室里关进一个疯人或一个病人、一个罪犯、一个工人、一个学生。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瞭望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1]“每个人都被牢靠地关在一间囚室里,监督者可以从前面看到他。而两面的墙壁则使他不能与其他人接触。他能被观看,但他不能观看。他是被探查的对象,而绝不是一个进行交流的主体。他的房间被安排成正对着中心瞭望塔,这就使他有一种向心的可见性。但是环形建筑被分割的囚室,则意味着一种横向的不可见性。正是这种不可见性成为一种秩序的保证。”[1]而全景敞视建筑的主要后果就是:“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1]
如今,使用全景敞视建筑来监督和规训公民显然难以被人接受,然而,全景敞视主义已经以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形式渗入人们的生活——实际上,我们生活的社会本身就是全景敞视建筑的变形形式。城市被规划成不同的功能分区,如医院、学校、工厂、政府等。这些不同的功能分区就犹如全景敞视建筑中被分隔的囚室。各个功能分区里聚集着性质相同的人。表面看来,人们没有被强制隔离或封闭,似乎是自由的。然而,在每个功能分区中,为了维持秩序,都有具体且严格的规则和纪律。虽然作为少数人的管理者难以持续不断地监视作为大多数人的被管理者,但是被管理者还是会自觉遵守各自所在的分区的规章制度。因为制约人们的不仅仅是监督者这一具体的人或角色,而是边沁所谓的“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1]权力自身。违反规则的人既可能被监督者发现,也可能不被发现。监督者只是权力运行的可见符号,但这一符号的存在与否都不能打断权力的运行。正是由于监视的不确定性,被监督者会时刻主动遵守规则。这使得权力得以独立运行。于是,“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1]。
权力的独立运行带来的不仅是秩序的有效维持,还有资源节约的最大化——无论是资金还是人力资源,都能被有效节约,从而用较低的成本来维持社会运行的秩序。
二、权力行使者也是被监督者
作为权力行使者,监督者并非是完全自由的,因为在监督他人的同时,监督者也在被监督。
在每个功能分区内,没有一个不被监督的人,也没有一个完全没有权力的人。例如在医院,医生和护士监督病人的同时也在被院长和病人监督。在现代的管理制度之下,权力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即相互的。医生可以约束病人,但病人也有权力监督医生——通过投诉或举报。在学校也是如此,老师监督学生的同时也被学生监督。哪怕是医院的院长或学校的校长也不是单纯的权力行使者,他们也被老师、学生、家长等人所监督。相应地,学生也不再是单纯的被监督者,而是同样拥有权力的监督者。又如当今无数的选秀节目,评委已不是唯一的权威,不仅观众投票能改变局势,媒体舆论也能左右评委对其权力的行使。所以,在全景敞视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处于一种监督且被监督的境地,既拥有权力也被权力制约。全景敞视主义有利于权力被持续且公平地使用,“在任何一种应用中,它都能使权力的行使变得完善”[1]。
全景敞视主义的当代表现形式带来的不仅是权力的合理运用,也会造成权力的不合理运用。例如在媒体舆论的压力下,作为权力行使者的选秀评委可能会违背公平原则,为了迎合公众舆论而做出不公平的评判。这表明一个事实,即权力的运行并非具有理想的独立性,它也受到众多外界因素影响和制约。所以,一定情况下,全景敞视主义会对权力的独立和合理运行造成阻碍。可见,全景敞视主义并非是一种完美的规训手段。
三、无意识的被监视者和权力行使者
荣格对“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都进行了详细论述。“集体无意识是精神的一部分,他与个人无意识截然不同,因为它的存在不像后者那样可以归结为个人的经验,因此不能为个人所获得。构成个人无意识的主要是一些我们曾经意识到,但以后由于遗忘或压抑而从意识中消失了的内容;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从来就没有出现在意识之中,因此也就从未为个人所获得过,它们的存在完全得自于遗传。”[2]在实践着全景敞视主义的当今社会,这一理论被体现得很明显。作为功能分区中的个体,人们并非能时刻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监督权,也未必能时刻意识到自己被监督着。
从个人无意识角度来看,例如病人就医时,通常意识到的是渴望生命得到救治,而不是自己可能因患有传染性疫症被监督和隔离;一个在专心自习的高中生未必能意识到自己被摄像头另一端的某个人所观察;一个随地吐痰的人也未必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被一个拍客用手机拍下并传到互联网上。然而,作为被监督者,无意识更体现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即主体对于规则的自觉主动遵守。各个功能分区的人并非刻意遵守所在功能分区的纪律或规则,实际上,这些纪律或规则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习惯,就如同这些功能分区的划分一样,是得自于“遗传”的,被人们无意识地接受。这是全景敞视主义长久以来持续运作的后果。也正是由于被监督者对于规则遵守的无意识,权力才能持续独立运行。
相应的,人们对权力的行使也是无意识的。观众意识不到他们的监督使明星在公众面前刻意成为大家想看到的形象而非真实的自我;学生意识不到老师为了适应他们的接受能力而不断调整自己的授课方式。所以,观众可能会拥有一个理想的“偶像符号”,但却不了解这个“偶像符号”的本质。全景敞视主义可能导致表象与本质的分离——即被人们所看到的可能只是一种表象,而本质则是全然不同的。如罗兰·巴特在其著作《S/Z》中对于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的分析,作为表象的人物肖像画背后,作为本质的人物竟然是不存在的。[3]所以人们不得不开始怀疑视觉获取的信息究竟是否真实。这使得笔者对权力的独立运行产生了担忧——权力的独立运行造成的表象与本质分离的后果是否会使我们对真相的认知遭遇更多障碍?总之,无论是作为被规训者还是作为权力行使者,一定程度地意识到自己在行使权力以及意识到权力运行的独立性将有助于我们认知事物的本质。
参考文献:
[1](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
[2](瑞士)米歇尔·福柯.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法)罗兰·巴特.S/Z[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