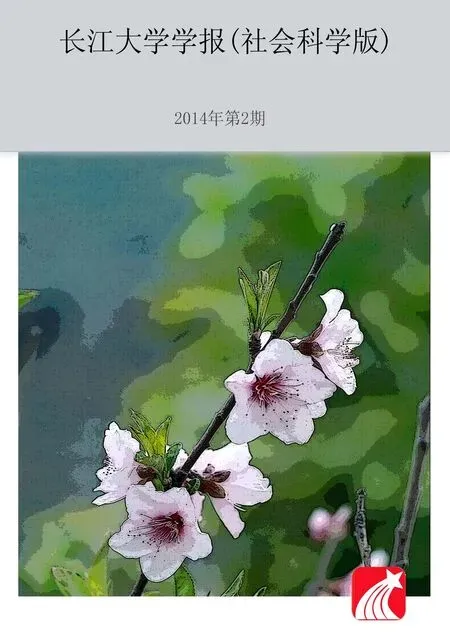从林语堂译《板桥家书》看译者主体性之扬抑①
殷培贤
(西北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100)
《板桥家书》是乾隆十四年(1794年)刊刻的郑板桥亲手书写的16封家书,信是写给其堂弟郑墨的。书信的主要内容,涉及了郑板桥对人生、事业、自然、社会等的一系列认识,重点陈述了其为人处世的标准和读书行文的理念,强调了其对世间生命的尊重和可贵的人人平等理念,以及反对为富不仁,以贵傲贱的思想。这部作品中所凸显的内容,能够使西方人士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理念和处世原则,有全新的理解。而这一切,正是林语堂选译这部作品的原因所在。
翻译主体性,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显现出的一种本质属性。主体性体现在译者的一系列行为中,首先,译者本身的喜好会决定他对文本的选择;其次,译者的文化架构和知识水平,决定了其对原文的理解,这具有主观性和唯一性;再次,在译者翻译过程中,译者始终在操控文本。以往的翻译理念强调以原作者为中心,这种研究范式,彻底否定了译者的主体性,要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做到隐身。事实上,译者主体性贯穿于其翻译的整个过程中。韦努狄也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无法隐身的。[1](P245)勒弗维尔在其著作中也认为,翻译中极端的忠实,就会导致极端的不忠实。[2](P28)而林语堂先生译《板桥家书》,实际上是其身为译者,其主体性之扬抑的再度诠释。
一、 译者主体性之扬
林语堂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独特的教育经历,决定了他的翻译理念。因其父为教会牧师,林语堂自幼开始接受西方教育,就读于教会学校,但同时,他的少年时代又生活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两种文化时时在他的脑海中发生碰撞。青年时期,林语堂先后留学于美国、德国。多年在外生活的经历,使得他从更深层次上,审视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社会一贯的偏见,以及西方社会对中国社会所抱的猎奇心理。在其一生中,他始终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抱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对中国文学和老庄思想,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领悟。林语堂的双语能力,以及始终处于中西方文化交集之中的生活,使他对西方的政治体制、文化思潮和价值标准,都有准确的把握。这些经历,使得他对翻译有着极其明确的目的和看法。后殖民主义代表人物爱德华·赛义德曾指出:西方人类学者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虚构出一个东方的形象,而这个形象总是落后的、野蛮的、蒙昧的,而且是必将向着西方的模式发展的。林语堂始终想要打破西方社会的这种偏见,所以其对于文本的选择,更多地取决于他自身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取决于他自身想要在西方社会中构建一个怎样的中国形象的努力。《板桥家书》的翻译,正表现了他内心对自然的崇尚,对性灵文学的推崇。
在译介这些作品的过程中,林语堂解构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社会的刻板印象,彻底颠覆了西方视域下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模式,在世界范围内重塑了中国形象,使得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找到了栖身之所。林语堂有针对性地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向西方读者传播,这充分凸显了其译者主体性之扬。比如,在《板桥家书》第一封《雍正十年杭州韬光庵中寄舍弟墨》中写道:“谁非黄帝尧舜之子孙。”林语堂译文为:“one in the world who is not descendant of the Yellow Emperor,and Yao and Shun.”[3]将黄帝尧舜直译为“Yellow Emperor”、“Yao”和“Shun”。这样的翻译,不能不谓之对中国文化之扬,期望西方读者对此接受,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物有所了解,并得以构建中国传统文化。再如《板桥家书》第八封《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中写道:“夫天地生物,化育劬劳,一蚁一虫,皆本阴阳五行之气絪緼而出。上帝亦心心爱念。而万物之性人为贵,吾辈竟不能体天之心以为心。”林语堂译为:“Now nature creates all things and nourishes them all. Even an ant or an insect comes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forces of the yin and yang and the five elements. God also loves them dearly in his heart,and we who are supposed to be the crown of all creation cannot even sympathize with God’s heart. ”[3]通过林语堂的翻译,郑板桥思想中的人人平等,万物生命皆是上天所赐,作为世间主宰的人类更应当尊重生命的理念,就此呈现在西方社会之前。而原文中的阴阳之概念,被直译为“yin”、“yang”两词,实在是借此让西方读者接受一个新的中国概念。
二、 译者主体性之抑
翻译始终在追求异质同构的和谐,始终要求译语读者能够接纳认同原语文化。构建对原语文化的理解,是翻译的终极目的。文化势差是向西方社会输出我国文化的一个前提,更是一个背景,而这种文化势差,更是林语堂在当时社会所面临的状况。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林语堂更多地使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这使得译本的读者在构建对中国社会文化认知的过程中,障碍更小。这不得不说是林语堂翻译《板桥家书》时作为译者所抑之处。比如对于题目《板桥家书》的翻译,林语堂只用了“Family Letters of a Chinese Poet”[3]这种简单明了的归化翻译方式,使得译本读者很快明了书中内容应当是书信来往,而写信之人是诗人这样的阅读背景,但是对于郑板桥是何人,其成就为何,皆无介绍。这不能不说是为了迎合西方社会的理解视域,力求文本内容和读者的视域融合,而作为译者主体性中所不得不抑的部分。再如第一封《雍正十年杭州韬光庵中寄舍弟墨》信中,对题目的翻译,用了“To brother Mo,From Taokuang Temple,Written in 1732”[3]这样的表达,而没有过多地解释雍正十年是什么概念。这样的归化翻译,可以让译本读者更容易接受,而且这种归化方式,并没有因为缺少对译,而减少意义的建构。在第一封信中,“非其数十代以前即自臧获婢妾舆台皂隶来也”,“臧获婢妾舆台皂隶”,是中国社会中特有的说法。在这里,林语堂先生并没有在翻译的时候,过多地阐释所谓“婢妾”、“皂隶”是何等人,而只是选择用slave girls、concubines和drudge去描述,将其翻译为:“There is no it would be wrong to assume that their ancestor were slaves,slave girls,concubines,drudge and lowly laborers in generations ago.”[3]这样的翻译,会使译本读者迅速构建出自己的理解,而这正是林语堂翻译之首要目的,即吸引西方读者关注中国文化,重构中国印象。
林氏作为译者本身,在其主体性之一扬一抑中,构建出了中国文化的概念。一扬,更多地体现在他对原文本的选择,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固有概念的直译上;一抑,则使得其译文更符合译入语的文化特征,能让西方读者更加直观形象地理解原著的意思,使得译者视域与读者视域得以完美融合。在他的译文中,一些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词汇,都转换成了在西方视域中可以重新构建的意义。这样的译本,能够更好地阐释原著的文化内涵,在译语读者那里,达到了译本与原著视域的完美融合。林语堂曾经说过:“上识之士,以现代文化为世界共享共有之文化,本国文化,亦可熔铸为世界文化之一部,故能以己之长,补人之短。 ”[4]“以己之长,补人之短”之理念,应当是我国在现阶段,对中国典籍外译的基本理念之一。
参考文献:
[1]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Lefevere,André.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林语堂.板桥家书[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4]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