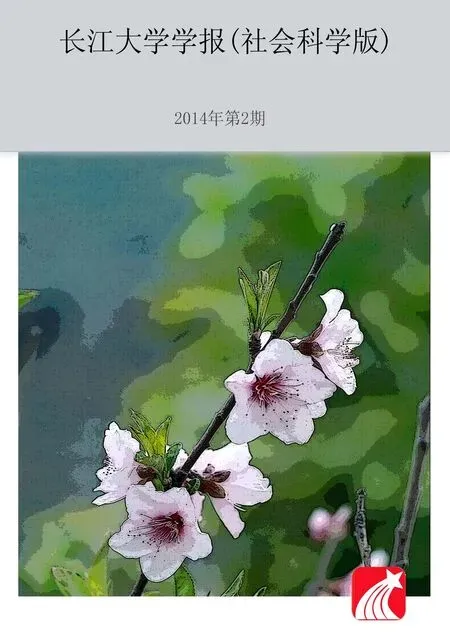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探微
张晓娟
(山西大同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元杂剧中公案剧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这些公案剧中的清官又多以包拯为主人公。“包公”这一艺术形象曾经出现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文学样式中,但总体说来要数元杂剧中的包公被塑造的最为丰满生动。元杂剧中出现过包拯形象并流传至今的剧目共十一种,分别是关汉卿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智斩鲁斋郎》、郑廷玉的《包龙图智勘后庭花》、李行道的《包待制智赚灰阑记》、曾瑞卿的《王月英元夜留鞋记》、武汉臣的《包待制智赚生金阁》,以及无名氏的《包待制陈州粜米》、《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叮叮当当盆儿鬼》、《神奴儿大闹开封府》、《鲠直张千替杀妻》。这些剧作大多见于明代臧懋循编的《元曲选》。在这些元杂剧中,“包公”的形象具有清廉正直、不畏强权、智谋出众、讲究策略、心系百姓、亲民爱民等特点。
一、清廉正直,不畏强权
清官与贪官、赃官相对,是否清廉应该是衡量一个官员是否为清官的最基本准则。在元杂剧“包公”戏中,有多处体现了包拯的清正廉洁。在《包待制陈州粜米》一剧中就通过侍从张千之口侧面道出了包拯的清廉:“你不知这位大人清廉正直,不爱民财……一日三顿,则吃那落解粥。[1](P258)包拯在看出张千意图凭着势剑金牌去陈州大吃大喝时,还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在包拯眼里,为官的如若贪得一点民财便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重罪,官员应时时处处恪守为官之道。在《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一剧中也有“他清耿耿水一似,明朗朗镜不如”[1](P287)的有关清廉品质的描述。为官清廉,始终是包公断案公正的坚实基础。
包公不仅清正廉洁,而且面对皇权、强权,他也毫不妥协退让,敢于为民主持公道。在很多“包公”戏中往往有这样一类人物——豪强权贵。他们倚仗自己拥有的或攀附的权势肆意为非作歹,欺男霸女,害人性命。《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的鲁斋郎就是一个自称花花太岁的恶霸,他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 骄奢淫逸至极。他先后抢了银匠李四与孔目张圭的妻子,硬生生拆散了两个无辜的家庭。可是这个动不动“挑人眼,剃人骨,剥人皮”的恶霸却得到皇权的庇佑。即使面对皇权,包拯也绝不退让,最终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将这个恶霸斩杀了。《包待制陈州粜米》中自称“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 的刘衙内,他出生于权豪势要之家,打死人都不用偿命。他的儿子刘德中、女婿杨金吾经常仗着刘衙内的权势为非作歹。他们被派到陈州粜米时,借着开仓放粮的机会盘剥饥民,他们大称称金,小斗出米,还在米中掺进砂石。当地饥民张憋古气不过前来找他们理论时,被刘德中用朝廷御赐的紫金锤残忍打死。面对这两个把穷苦百姓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豪权势要,包公决心除掉他们以平民愤。面对刘衙内“论官职我也不怕你,论家财我也受用似你”[1](P255)软硬皆施的威胁,包公毫不畏惧,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谋略为民众铲除了这两个吃人肉喝人血的贪官佞臣。
二、智谋出众,讲究策略
元杂剧中的包公查案并非主观臆断,而是讲求证据,作风务实。如在《包待制智赚灰阑记》一剧中包拯在查阅卷宗时察觉出张海棠一案可能有冤情,但他却没有妄下论断,而是暗地里派人去寻找原告、证人,搜集证据,并以灰阑外抢子的实验验证了谁才是孩子真正的生母。当证据确凿时,包拯方才定案。又如在《神奴儿大闹开封府》一剧中,包拯从李阿陈口中得出的供词与状子上的不符,觉得其中必有蹊跷,但并没有根据自己的臆想立即下论断,而是想着怎样搜集证据。从这些事例不难看出包拯断案时讲求真凭实据而非主观臆断的务实作风。
元杂剧中的包公审理案件时不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而是讲究策略方法,凭借聪明才智审理案件,让元凶自动浮出水面。因而元杂剧中的包公又常常体现出智慧过人的一面。在《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一剧中,作恶多端的鲁斋郎受到皇权的庇佑,智慧的包公在向皇上奏过鲁斋郎的罪行时,将鲁斋郎的名字写成“鱼齐即”。皇上看到“鱼齐即”的滔天罪行时怒不可遏,当即批了个斩字。次日包拯在奏折上“鱼”字下边添了个“日”字,在“齐”字下边添了个“小”字,在“即”字上添了一点,就这样凭着自己的智慧借皇帝之手把罪大恶极的鲁斋郎斩杀了。在《包待制智赚生金阁》一剧中,包拯已经对案情一清二楚,只是缺了庞衙内的供词和证物生金阁,于是包拯宴请庞衙内,以“一家一计”的圈套先是让庞衙内放松对他的警惕,然后又以“一家一计”说自己得了个宝贝,从而赚得生金阁取得物证,最后使庞衙内毫无戒心的招认了罪行。
不仅在对付权豪势要时,包拯体现出过人的智慧,就是在处理家庭纠纷案件中,包拯也讲究一定的策略手段。如在《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中,刘安住的伯母为了私吞家财,不仅拒绝承认刘安住是自己的亲侄子,还骗走了能证明刘安住身份的合同文书。包拯为赚得合同文书,先是假装将刘安住下在死牢中,后又命人假报刘安住因为头被刘氏打破而得了破伤风死在牢里了,接着包拯吓唬刘氏让其偿命,在刘氏吓得肝胆俱裂时,包拯提出一种解决方案:如果他们是亲戚关系,刘氏就不必偿命了。刘氏被唬的连忙承认刘安住是自己的亲侄子,并主动拿出合同文书证明他们的关系。就这样,包拯不费吹灰之力便赚回了刘安住的合同文书,使其能够认祖归宗,夺回家产。
包公的智慧还体现在他在断案时知道并运用人性特点。如在《包待制智赚灰阑记》中包拯就是抓住身为人母会不惜牺牲一切来保护自己孩子的心理特点来判断谁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包拯让张海棠与马氏于灰阑外争抢孩子,谁能把孩子拉到自己身边谁就是孩子的生母。张海棠作为亲生母亲自然不忍自己的亲生骨肉受到拉扯之痛,于是放弃了争抢,而马氏为了占有家财,只是一味拉扯灰阑内的孩子,丝毫不理会孩子的痛楚。就这样包公根据母亲疼爱自己亲身骨肉的心理特点巧妙地断了案子。
三、心系百姓,亲民爱民
包公为官真可谓在其位谋其事,兢兢业业,亲民爱民。他把为民众主持公道、伸冤昭雪作为自己应负的责任。他时时刻刻心系百姓,不是被动等待而是主动为民众解决遇到的问题。在《包待制陈州粜米》一剧中,年事已高的包拯宦海沉浮了三十多年,他早已看清了官场中的风风雨雨,本想就此辞官,安度晚年。但当他得知陈州大旱,百姓颗粒不收,前去开仓赈济的官员却借此机会盘剥饥民,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他又打消了辞官的念头。强烈的责任感使得包公主动前去陈州“和那有势力的官人每卯酉”,[2](P73)解救百姓。又如《包待制智赚灰阑记》一剧中,包拯在查阅案宗时,察觉本已被定案的张海棠一案含有冤情。此时受害人并没有前来诉苦伸冤,而包公却主动提出重查此案。再如《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一剧中,鲁斋郎夺人妻女,将张圭、李四两个无辜的家庭拆散,罪大恶极。张圭和李四并未前来向包拯申诉,他是在无意间收留了两家失散的孩童后了解了此事,并将此事一直记挂心中,最后终于用计谋斩杀了鲁斋郎,使得两家人得以团聚。从这些都不难看出包公对百姓怀有极强的责任心。他热爱民众,不忍奸邪者逍遥法外,无辜者受害。
元杂剧中的包公作为清官的代表,体现了中国人民追求正直与智慧的审美理想,所以元杂剧中的包公可称得上是文学典型,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范嘉晨.元杂剧包公戏评注[M].济南:齐鲁书社,2006.
[2]胡金望.《陈州粜米》中包公形象的塑造及其审美价值[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