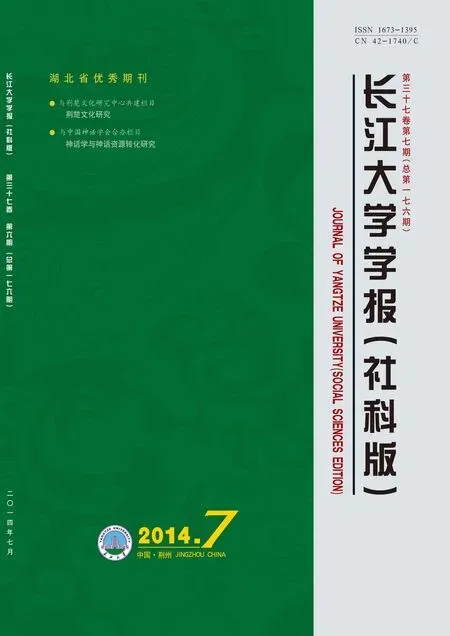论实质正义下强行法的法律规避效力
丁陈
(安徽财经大学 法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规避是国际私法法律适用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始于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对鲍富莱蒙(Bauffremont)案的判决。法律规避是指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故意制造某种连接点,以避开原来的连接点所指引的准据法,通过适用新的连接点所指引的准据法来实现对自己有利的结果。
基于对法律规避的价值评判,有必要就法律规避起源的案件——鲍富莱蒙案进行分析。
该案原告是法国的鲍富莱蒙王子,其配偶鲍富莱蒙王妃原为比利时人,因与鲍富莱蒙王子结婚而取得法国国籍。鲍富莱蒙王妃后来打算离婚,以便与一位罗马尼亚人结婚。但当时的法国法律禁止离婚,而德国法律则允许。于是王妃只身移居德国并归化为德国人,随即在德国获得离婚判决,然后在柏林与罗马尼亚的比贝斯哥王子结婚,婚后她以德国公民的身份回到法国。鲍富莱蒙王子在法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宣告王妃在德国的入籍、离婚以及再婚无效。依据法国冲突法,离婚依当事人的本国法,这时王妃已经取得德国国籍,但法国最高法院认为她取得德国国籍显然是为了逃避法国禁止离婚的规定,因而构成了法律规避,判决她在德国的离婚和再婚均属无效。法国法院根据这一判例确立了一项原则,即在国际私法上用规避法国法的方法而完成的行为是无效的。
法律规避无效的理论来源一直备受争议。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则必须以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为基础,法律规避构成要件有“三要素说”、“四要素说”、“六要素说”,三种观点的内涵并没有本质差异。笔者以最为普遍的“四要素说”为分析依据,即:当事人主观故意规避某种法律;规避的法律为本应适用的强行法;采用制造或变更某种连接点的方式通过冲突规范适用准据法;规避的目的得以实现。[1]
一般来说,在这些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中,影响法律规避效力的主要有如下两个观点:第一,基于“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的原则,法律规避中当事人故意选择适用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是不能够得到支持的,尽管当事人的意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合法的目的不能使非法的行为合法,目的不能为手段辩解。第二,变更连接点规避的是一国的强行法,而一国的强行法更多的是维护本国的公共利益,承认法律规避的效力,允许当事人基于自己的利益选择法律,是对擅自撼动一国社会文化底蕴行为的鼓励,这有损于一国的主权,是对法律权威的破坏。
然而,法律的价值应是正义,当事人故意制造连
接点这一行为一定是“欺诈”么?强行法所维护的公共利益本质上是国家正义的实现,而当事人自由权利的正义难道就一定是下位于国家的正义么?国家权力是由全体民众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的集合,并不当然具有超越个人的权力。国家是由民众组成的整体,这个整体要求不能伤害其中任何一个成员,对任一成员的伤害就是冒犯了整体,伤及整体,[2](P13~14)个人的正义实 现应 当是与国家法 律 价值导向具有同一的途径。回顾国际私法中冲突法的历史发展,从巴图鲁斯(Batoruls)的“法则区别说”到萨维尼(Savigny)的“法律关系本座说”,都旨在解决冲突正义实现的方法问题,构建一个合理完善的规则选择适用法律,这是从结果出发的方法。对于法律规避的效力问题也应当忽略规则的构建,而要从实质的具体的事件中寻求正义。
二、法律规避效力的决定因素
法律规避起源于14世纪巴图鲁斯“令人厌恶的规则”和“招人喜爱的规则”,各国的社会环境与价值选择不同,违背法院地司法的道德、经济和法哲学基本标准的外国法不应被适用于争端的解决。因而需要构建一系列的冲突规则指引适用法律,使得涉外民商事争端解决能形成一个可预测的具有稳定性的规则体系。“而这些解决方法之所以是正确的,并不仅仅因为它们公平调解了相互冲突的各州的政策,而且还因为它们对于卷入各州政策相互冲突问题之中的个人提供了公平待遇。”[3](P74)无论何时,法律的正义性都不应当被忽略,应当在现实的法律适用中寻求均衡。每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体现着其所需要维护的特定社会价值,而选择适用法律则应立于一个更高的价值层面来考量各个连接点所指向的准据法对于当事人正义的保障,这是冲突正义摆脱规则的束缚,实现实质正义的要求。实质正义理论的前提是,多边案件与纯国内案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审理有涉外因素的案件时,法官仍有公平和公正地解决争议的责任。[4](P396~397)实质正义作为法律选择的最根本价值取向,尊重当事人自主选择法律,对具体案件法律适用的选择不应囿于僵硬的冲突规则。
(一)故意是否即为欺诈
明确何为欺诈,是判断法律规避行为无效的前提条件。“欺诈”一词的内涵不应局限于表面的概念型描述,而应对这一名词背后的含义进行辨析。就前述鲍富莱蒙案而言,王妃出于“故意”,为摆脱法国婚姻法而将自己划归为德国人,而这种“故意”被认为具有欺诈性。自然人作为国际私法的主体,是为寻求私人利益实现的过程,个人拥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有自主选择法律的权利。既定的法律体系如果是正义的秩序,那么,个人只需遵从法律的指引,而不需要谋求另一种途径。在看待私法领域的个人存在时,不应当将法律所拥有的制度规则与之分离,即法律适用规则是为自然人服务的,如果个人在寻求正义时遇到不合理的制约,则其通过自我的能力实现正义的行为不具备过错的可评价性。上述案例中,王妃因社会赋予其婚姻自由的权利,这是个人所享有的自由,不可被阻碍,其实施的改变国籍行为的“故意”是不能够被评价为欺诈的。欺诈的内涵要求个人行为的不正当性具有破坏现有规则,达到非法目的的意图,而王妃的行为是自由意志的表达,是对正义的积极主动实现,不具备非法目的的要件,否则,任何自由意志的表达都是非法的、欺诈的,因而故意的规避行为不能被认定为欺诈。故意改变连接点的行为在国际私法领域中并非总被认定为具有法律规避的欺诈性质,[1]法律规避效力评价不在于当事人主观的故意,根本的问题是被规避的一国强行法是否涉及国家的公共秩序。
(二)强行法中公共利益的内涵
法律规避问题中核心的评判标准是一国强行法是否涉及公共利益,这是判断法律规避效力的关键性要素。公共秩序是一个国家具体文化背景下的道德、文化及政策,对公共秩序的维护是为了追求“更适当”的实体结果,是关注具体案件中两国法律的价值选择。首先必须明确一点——即公共秩序所代表的社会价值,公共秩序价值的选择一般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或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而这不可避免地有着不合理性。如同前述案例中,1878年法国婚姻法不允许离婚,而到了1922年佛莱(Ferrai)案时,法国法已经是准许离婚的。公共秩序是随着时间变化的,而个人却因为这一并不具有绝对正义的制度而丧失了婚姻自由权,这是对法律存在的合理性的挑战。法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社会中个人正义的集体表现,不能超越个人的自由权利。如前所述,个人所享有的自由平等权应当被合法保护,尽管法律具有权威性而不能被任意僭越,但这并不表示个人不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寻求正义。在鲍富莱蒙案中,王妃所享有的离婚自由权不能因其是法国人而当然丧失,而法律的权威性又不得擅自更改,因而王妃基于对自己个人权利的保障而实行的法律规避行为具有正当性。法律不允许僭越,也不允许欺诈,但王妃的行为是在遵从现有法律制度下的法律选择,其自主选择法律行为的故意不能被认定为欺诈。
法律适用问题是当事人利益与公平的考量,不能以满足主权者的需要为追求。尽管个人自由选择法律应当受既定的法律限制,然而这种受限是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的价值选择,而法律规避中所涉及的公共秩序则是一个很小范围内的社会理念,这不能阻断个人自由权利的实现。在前述鲍富莱蒙案中,法国禁止离婚的规定且不论之后的法律价值选择改变,就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只是一个国家主权者根据国家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所作出的立法,而事实上离婚这一行为只是私人之间情感的决断,并不会影响第三者或者公众的利益,如果仅仅因为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国籍就剥夺其对婚姻的自由选择,这是违背人类最基本的情感诉求的,无疑是对正义的背弃。一个国家强行法无论是否涉及公共秩序,都有其特定的价值选择,而评价行为人的规避行为效力主要是看行为人是否能够无偿获得该价值维护所提供的利益。
(三)法律规避的根本性问题
法律规避的核心在于行为人所规避强行法维护的价值利益能否被行为人无偿获得,如果行为人能够无偿获得这些利益,那么规避的行为则是无效的。利益的获得要求在能够履行义务时履行义务,如税收是为了国家的公共设施建设或者其他公益性事项,而行为人作为一国国民能够无偿获得这些利益,因而在其能够履行税收义务时规避法律是不符合正义的,法律规避行为当然无效。而对于涉及公共秩序的强行法维护的社会价值,如果没有在社会生活中给予行为人无偿的利益获取,这种规避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有效。公共秩序中单纯的双方关于自身的决定是不能够无偿赋予利益的,而具有普遍性正义价值的公共秩序——国际公共秩序,因维护的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规则,诸如诚信价值的规则,能够形成一个公正公平的生活环境,使得行为人在人际交往中获得利益。国际公共秩序维护的价值利益是行为人能够无偿获得的,因而对于涉及国际公共秩序的强行法的规避亦属无效。
法律规避的无效性不在于行为人故意选择法律,而在于被规避的是否为一国强行法,这时的规避行为主要是对强行法内容进行具体分析,从而认定规避行为的效力。若强行法中涉及公共秩序,也不是一味地对其进行维护,公共秩序内容宽泛、模糊,并不具有恒定性,为有利于法律发展及个人正义的实现,法律规避效力更应当就案件的不同情况遵从上述规则,做出合乎正义的判断。众所周知,法律规避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法律体系中“劣法”、“坏法”的淘汰,法律是一定社会价值选择的产物,并不具有长久的正义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的滞后性不可避免地导致法律规避行为。基于人的趋利避害性,更多的有利的法律会得到普遍认同,并以此促进法律的进步。当然,国际民商事交往中个人的正义需要被维护,但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权利无限制无疑会导致非法的目的得以实现。在这样的环境下,各方价值的均衡则是必需的,即并不是所有强行法的规避都必定导致法律规避的无效。在一个宏观的价值层面,给予当事人无偿享有利益的强行法包括涉及国际公共秩序的强行法绝对不能被规避;而仅仅是一国社会价值的选择——国内公共秩序的强行法,则可以基于当事人的自由权利而被规避。[5]
三、结语
在涉外民商事领域,法律规避现象普遍存在,因而对于法律规避效力的认定具有重要的价值,而对于法律规避决定因素的认识则是必须加以明确的。随着社会交往的紧密,实质正义应当是众多争议性问题中的衡量标准,且法律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公正有序而创设的,法律适用的选择更应尊重正义的导向规则。法律规避应当站在实质正义的角度,根据被规避的强行法的深层内涵以及最终享受利益的主体进行判断。
[1]许光耀.略论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制度[J].法学评论,2012(6).
[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陈红玉,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
[3]邓正来.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4](美)西蒙妮德斯.20世纪末的国际私法——进步还是退步[A].宋晓,译.黄进,校.张春良.冲突法的历史逻辑[C].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5]徐崇利.法律规避制度可否缺位于中国冲突法——从与强制性规则适用制度之关系的角度分析[J].清华法学,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