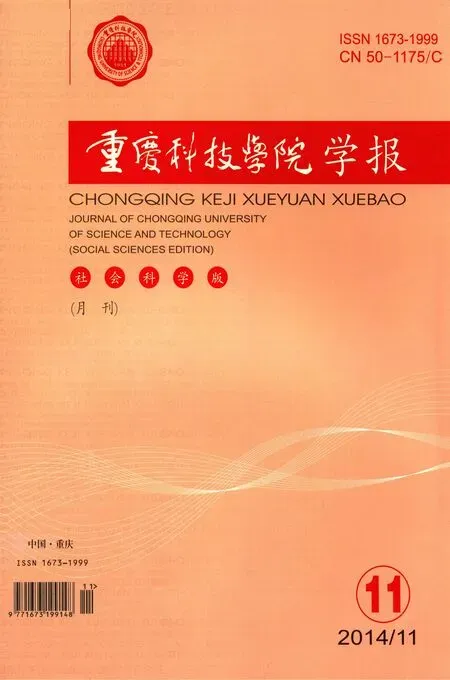流亡知识分子的归来——评V.S.奈保尔的《魔种》
周文静
在奈保尔荣获200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仅两个星期,他的新作《浮生》(Half A Life)问世。尽管在此之前,他已经七年没有出版过虚构作品,但这部小说却没有给大家带来惊喜。因为,作者没有提供任何新鲜有趣的东西,反而遭来了众多评论家的不齿。正如南非作家库切(J.M.Coetzee)所说:“如同拦腰斩断的一部书的前半部,而这本书也许可以叫作《圆满一生》。”[1]5的确,小说的名字以及人物的命运都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于是,时隔两年,奈保尔推出其“续篇”《魔种》,称其为“封笔之作”。 小说中,他继续探讨了以他为代表的流亡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流亡、身份、文明的不确定性等主题。但他却一反常态地放弃了尖锐、批判的态度,转而使用细腻,温和的描述,并对群体流亡知识分子的生活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积极探讨现实生活,直面问题,完成了一个游子的归来。同时,在精力逐渐衰退,创作源泉逐渐枯竭的古稀之年,《魔种》的出版也算是为他自己的文学生涯进行了一番总结,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一、从虚妄的理想中归来
作为《浮生》的姊妹篇,《魔种》继续讲述威利下半生的生活。逃离非洲,寄居在德国妹妹家,威利过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无忧无虑,但他一如既往的毫无目的,无所事事。按他自己的话说:“我从来就是个局外人,现在也一样。”[2]1但威利在德国的签证时间已到,续签无望,他必须得走了。这让过于安于现状的威利无所适从。在左派妹妹的循循善诱下,他决定追随坎达帕里和甘地的思想去做一个改变历史的伟人。如果说威利在前半生面临重大抉择时无可奈何,这一次却有本质上的区别。他选择背井离乡去伦敦求学,是因为对落后殖民文化的鄙视;离开伦敦去非洲,被安娜供养是为自己找一个暂时的栖身之处;逃离非洲去德国是为了自己的压抑之旅有个喘息的机会。这一次,在妹妹的指导下,他发掘了自己的理想:解放被压迫的人们,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一想起自己即将去印度参加游击战这个伟大的事业,“他那难以描述的过去所经历的种种痛苦,全都泯灭在一种崭新的崇高理想中。 ”[2]25
到达印度后的所见所闻让威利大大失望。破旧矮小的候机楼,趾高气扬的海归客,肮脏破旧的设施,骨瘦如柴的乞丐,一切都显示出印度的贫穷和落后。但,这些对心存远大抱负的威利不算什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更坚定了他革命的信念和即将成为伟人的虚荣感。但现实的虚无和可笑很快破灭了他的美梦。奈保尔对游击战的叙述一开始就很模糊,时间和地点交代不清楚,游击战也给人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威利没有参加轰轰烈烈的战斗,反而从事侦查和地下工作,对自己的身份,收入支出不甚了解,据说是上面有人给。他甚至连自己崇拜的偶像坎达帕里也没见几次。反而,在这个伟人身上他看到的更多是平凡的东西,还有虚伪。革命者要用暴力消灭阶级差别的初衷与革命的实际相去甚远。威利越来越感受到这种革命的虚妄性。“参加革命这段时间以来,他一直生活在对农村和森林田园牧歌式的幻想之中,而这种幻想就是革命运动的思想基础......根据这种田园牧歌式的幻想,农民辛勤劳作但却深受压迫。可是村庄里——就像他们在行军途中解放并且有一天也许侥幸再次解放的那些村庄一样——到处都是心胸狭窄,品行不端,野蛮成性的不法之徒。他们的存在与身边的环境十分相称,与劳动和压迫的观念则没有丝毫联系。 ”[2]125
革命仿佛就是一场闹剧,是发泄个人情绪的一种借口,这是一直处于幻想并受到命运摆弄的威利始料未及的。然而,根据小说的叙述,威利在幻想破灭后仍然没有离开游击队,而是更加执着于自己的崇高理想。这或许是因为他身上残留的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惯性作用。值得庆幸的是,威利从这次教训中获得了成长的经验。他开始尝试着去面对现实。他承认了游击战的荒唐,还破天荒地教育起自己的妹妹:“你从一个极端走入了另一个极端......我感激你让我直面自己和我的出生。我认为这是生活的馈赠。”[2]130这是小说中的一抹亮色,也大大地区别了奈保尔众多小说中虚无、怨天尤人等人物的形象。威利从对生活的迷茫变成感谢生活,务实认识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折射出奈保尔对流亡知识分子生活的反思。诚如萨义德所言,“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精于生存之道成为必要的措施。”[3]45如果说此前威利不善于懂得生存之道,那么,从这次可笑的革命中,年过半百的威利应该知道生存和生活的含义。
二、回归生活
根据奈保尔设置的情节,伦敦似乎会成为威利流亡生活的目的地,因为他在印度监狱里获得特赦的条件就是要永远待在英国。这似乎使得之前许多模糊不定的问题终于有了明确的答案。他被迫成为英国公民,居住在英国,并接受英国文化。这就为他能够理性地对待伦敦生活中所遭遇的单调、无聊、虚伪和尔虞我诈埋下伏笔。
威利对伦敦的生活适应得非常快。抵达伦敦的第二天,威利就与朋友罗杰的妻子帕蒂塔上了床。他听从内心人性的召唤,完成了他三十年前未敢实现的欲望。罗杰带他出入伦敦的上流社会,有所谓高雅的文艺沙龙,也到银行家彼得家去拜访、聚会。贵族们小心翼翼维护自己的地位,艺术家们乐此不疲地谈论自己所谓的艺术作品,还有有钱人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发财梦。所有这一切都透着一股俗气和虚伪。但威利已经习以为常。小说中,奈保尔精心安排了罗杰这个人物,他就像一个循循善诱的导师,以自己为教材,给威利上了精彩的一课。他自己的婚姻名存实亡,为了在房地产大赚一笔,他巴结彼得并容忍他与妻子的不正当关系,到头来还是在生意上一败涂地,生活几近崩溃。罗杰的故事深深刺激了威利,让他最终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这或许坚定了他要脚踏实地生活的决心。在罗杰的安排下,威利有了一份工作,是一本建筑杂志的编辑。他乐于接受这样一份工作,毕竟,这是他生存的基础。他也以积极的态度去学习从未涉足的领域。至此,威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解除了对身份、文化等不确定性的疑惑,回到现实的生活中来。
值得一提的是,《魔种》的结尾很有意思,两个婚姻不幸的人参加了马尔库斯儿子的婚礼。马尔库斯是一个非洲的外交官,他在伦敦有一个宏大的理想,就是让自己的子孙以白人的身份融入到宗主国。他的理想终于实现了。这是《半生》和《魔种》里唯一一件成功的事情。婚礼前的一个场景颇有寓意,宾客们朝着豪宅附近的场地聚集:“这时可见两股泾渭分明的人流,一股是黑肤色,一股是白肤色。不久,两股人流紧张不安地开始汇合,然后汇成一股,继续向前流动……”[2]161在《浮生》及奈保尔的多部作品中,非洲的原始落后野蛮暴露无遗。以《河湾》为例,在奈保尔的笔下,非洲的去殖民化进程,非但不是历史的进步,反而成了历史的倒退,“偷窃,腐败和种族主义的骚动”由此产生[4]。对待非洲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出奈保尔对种族差异的理性思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其说用暴力的手段将它们殖民化不如说用非暴力的手段与它们融合,对于殖民地是这样,对于宗主国也同样。很显然,在全球化语境下,奈保尔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姑且不论这种构想有多大的可行性,但体现出奈保尔回归现实的态度。威利要生活在伦敦,马尔库斯也想要生活在此地。同样具有流亡的身份,如果他们要想在伦敦生活幸福,融入到主流,变成他们当中的一份子或许是一种务实之举。
三、结语
要准确理解《魔种》就必须要了解《浮生》中威利的上半生。有人说,前一部小说是“一本关于失败的书。”[5]180那么后一本小说就是关于走出失败,回归生活的书。奈保尔在古稀之年出版这两部作品,特别有寓意。一方面,人年老了给自己的一生做一个总结也是人之常情;另一方面,“他在过去五十年间一直紧追不放的主题——流亡、身份、文明的不确定性”究竟有没有确切的答案[6]14?这值得读者期待。令人欣慰的是,奈保尔通过威利这个人物,对这些问题都给出了比较明确的答案或暗示。关于流亡,他选择安居乐业,毕竟安定平静的生活是人人都向往的,对一位老人来讲尤其如此。关于无根的身份,文化的悬垂,他没有过多纠结这类问题。这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大多数人必然会遇到的困惑。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碰撞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所谓流亡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解决之道不是怨天尤人或内心彷徨,作为个别的主体介入到新的和巨大的全球现实才是要义。由此,奈保尔在《魔种》中塑造的人物最终不再虚无与悲观,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现实,融入到生活,并找到其中的乐趣。从流亡到停下脚步歇息下来,从知识分子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到回归平凡,威利完成了一个游子的归来,奈保尔也完成了一个流亡知识分子的华丽转身。
[1]Coetzee JM.The Razor’s Edge [J].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01(17).
[2]奈保尔.魔种[M].吴其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3]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2.
[4]Elizabeth Hardwick.Meeting V.S.Naipaul[J].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1979(5).
[5]Bruce King, V.S.Naipaul[M].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3.
[6]James Atlas.A Passage to India[J].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