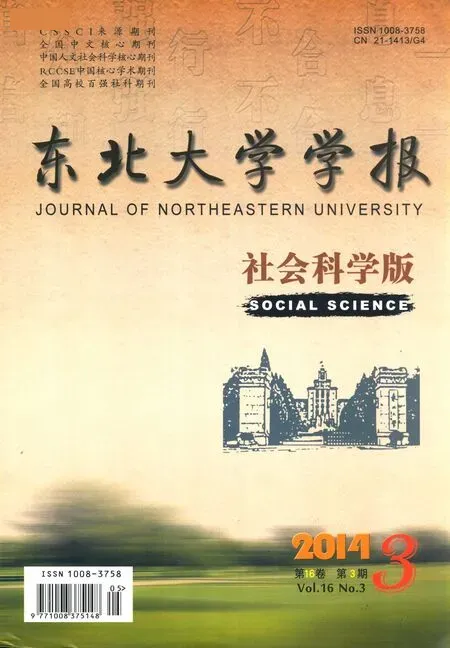“公正可持续发展”:一个新的研究范式与框架
张晓杰,耿国阶,孙 萍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当代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其基本内涵是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保证人类的世代繁荣。然而,该“经典可持续发展”理论因其精英主导式、单一的环境保护取向和缺乏社会正义关怀等特点而沦为“贵族阶级的政治”,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不利于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一个环境保护与社会公平并重、贵族化与平民化兼具、区别于“经典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新范式——“公正可持续发展”呼之欲出。
一、“公正可持续发展”范式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环境质量与人类平等的关系愈来愈密切[1],以及环境正义话语的渐趋成熟,应将环境正义纳入可持续发展政策议程的呼声日渐高涨。环境正义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聚合关系也愈见明朗,这主要是通过全球进步的非政府组织、学术研究机构和地方社区组织的活动实现的。环境正义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协同效应也被英美两国相关政府部门所理解、关注与运用,他们努力寻求将环境正义作为发展目标和评价指标之一纳入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2002年,美国学者朱利安·阿吉曼(Julian Agyeman)、罗伯特·布拉德(Robert D.Bullard)和英国学者鲍勃·埃文斯(Bob Evans)在追溯环境正义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理论根基的前提下,认为经典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缺失社会公平和正义原则,由此提出了一个操作性的基于正义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并阐释了环境正义之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基于此,阿吉曼首次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新的研究范式与框架,即“公正可持续发展”范式(just sustainability paradigm)[2]。
二、“公正可持续发展”范式的理论内核
自2002年首次正式提出“公正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之后,阿吉曼等人在《地理学报》(The Geographical Journal)、《空间和政体》(Space and Polity)等学术期刊发表了系列研究论文,并出版了两本专著[3-4],系统阐发了“公正可持续发展”范式的理论内核,包括基本概念和核心因子——环境正义的形成、发展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贡献。
1.“公正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有关“增长极限”的争论和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80年,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简称IUCN)在《世界自然保护策略》(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一书中首次对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定义,即“强调人类利用生物圈的管理,使生物圈既能满足当代人的最大持续利益,又能保持其满足后代人的需要与欲望的潜力”。1987年,以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简称 WCED)的成员们,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经过四年研究和充分论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而系统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模式。
然而,阿吉曼等人研究认为,WCED和IUCN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界定都没有具体提及平等和正义原则,而平等和正义既是可持续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科林(Collin)教授也认为,如果可持续发展中缺少草根声音,尤其是少数民族社区的声音,那么可持续发展将把我们带入“白色人种——绿色地带,有色人种——棕色地带”的“生态法西斯主义”。因此,“除非将以往环境不公正的补偿问题纳入考虑,否则任何可持续发展的定义都是不可接受的”①2000年,美国杰克逊州立大学举办了主题为“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正义”的第一届年度自由专题讨论会。罗伯特·科林教授在座谈会上发表了该观点。。基于此,阿吉曼等人提出了一个操作性的基于正义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即“通过公正和平等的方式保证所有人在生态系统允许的范围内获得较好的生活质量”[5]。阿吉曼等人的概念界定主要关注四个领域,即生活品质、当代与后代、公平和正义的资源分配、生存于生态极限。他们认为,可持续发展并不仅仅是一个绿色或环境问题,尽管环境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应将社会需求、社会福利和经济机会等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与生态系统强加的环境约束形成有机的联系。如果一个社会不努力寻求实现较高水平的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那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将难以实现[5]。
2.“公正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子——环境正义
(1)“环境正义范式”的凸显
作为应对环境非正义现象的新型话语,环境正义既是草根组织和社会民众为实现平等环境权利而寻求政治机会、进行政治动员和付诸政治行动的话语武器,又是指导公共决策的政策原则。环境正义运动发源于美国,起源于美国公民反对在有色人种聚居区落户有毒废物或危险和污染性工业。1983年的美国联邦政府会计署报告和1987年的基督联合教会种族平等委员会的报告——《美国种族与有毒废弃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公众对环境种族主义的认识,并由此引发了对“环境不正义”的传统界定,即由于缺乏参与决策和政策制定过程的途径,有色人种被迫承受不成比例的环境公害和与之相关的公共卫生问题及生活质量负担。此外,研究表明有色人种不仅更易居住在环境退化和危险的地方,而且他们获得的由美国环境保护署提供的环境保护和公共卫生服务也比白人和富人少很多[6]。环境正义的倡导者认为,只有当环境不公平现象的受害者参与有关危险废物和污染行业选址的决策过程中时,他们才能获得与其他人同等的环境保护服务[7]。
分配正义和程序正义是环境正义的两个核心要素。分配正义指的是环境公益和环境公害如何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群体中分配。例如,低收入群体和少数民族社区是否承受了不成比例的环境公害?或者富人是否享受了更多的环境公益?程序正义指的是公民参与环境决策的权利。例如,是否所有居民都有机会参与其居住社区附近的公共设施选址决策?社区人群是否能够对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环境立法施加影响?环境法规在不同地区的实施是否一视同仁[8]。
美国的环境正义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其倡导者的环境正义诉求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有效回应。包括1991年美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峰会对17条“环境正义原则”①1991年10月,有色人种环境领导峰会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召开,来自美国50个州的600多位代表参加了此次峰会。该峰会的重要成果是提出和采纳了环境正义的17条原则。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突出反映了有色人民的要求,指出了发生在有色人民身上的“歧视和偏见”和“环境非正义”;第二,针对实然的环境非正义现象提出了救济的原则,其核心要求是公平地分配环境费用和负担,维护全体人民的环境权;第三,给予了地球、非人生命体法律人格并保护其权利,以及对人与自然进行整体的完整保护。这些原则为美国环境政策和社会正义政策的制定和评估提供了标准。的采纳,1992年环境保护署环境正义办公室和1993年国家环境正义咨询委员会等相关政府机构的设置,1993年阿肯色州《在环境影响强烈的固体废物处理设施选址中实现环境公平法》《1993年平等环境权利法案》②该法案用了较长篇幅介绍了美国存在的针对少数民族的环境非正义现象,其提出的主要法律措施是赋予“环境状况恶劣的社区”居民提出禁止修建废物处理设施的请求权。,1994年克林顿总统的《第12898号行政命令》③12898号行政命令名称为“解决少数族裔人口和低收入人群环境正义问题的联邦行动”,该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在实施项目、制定政策和采取行动时确保少数民族社区不受环境公害的严重影响。,1994年《环境正义模范法典》等四部相关政策法规文件的颁布实施等。这标志着环境正义正式进入美国政府的政策议程。
美国环境正义运动所取得的成效得益于主流环境保护运动与民权运动的联盟。主流的环保运动又被称为“贵族阶级的政治”[9],他们主要关注荒野保存与保护,而对贫穷的少数民族社区内的环境保护则毫无兴趣;民权运动则关注少数民族群体的基本人权,如就业保障和公共卫生等。两个运动的联盟催生了环境正义运动。随着环境正义运动的不断发展和环境正义研究的不断深化与拓展,环境正义逐渐成为区别于主流环保运动并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显性范式。主流环保运动是精英主义的和环境保护取向的,而环境正义运动是平民主义的和社会公平取向的。传统的主流环保运动常被指责过多关注环境质量问题,比如自然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而对基本的人权和社会平等等问题并未涉及[10]。环境正义运动则从社会正义的视角关注环境问题,比如环境公益和环境公害的分配、公民的环境决策参与权等。环境正义运动成功地将环境与社会正义纳入一个主框架,并由此产生了强大的“环境正义范式”。正如Taylor所说的,“环境正义范式首次实现了将环境、种族、阶级、性别和社会正义融入一个显性的分析框架”[11]。
(2)环境正义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环境正义范式与可持续发展话语体系自产生以来一直是平行发展,虽曾有交集,但其在价值、理论框架和理念等方面缺乏互相渗透。Dobson认为,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正义是相互冲突的,因为环境正义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平等问题,而可持续发展重在环保问题[12]。阿吉曼批判了Dobson的观点。他认为,环境正义和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且相互依存,环境正义是可持续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可持续发展主要是平等问题[2]。因此,将环境正义与可持续发展割裂开来的观点无论是对环境正义的实现还是可持续发展的达成都是无益的[5]。总结阿吉曼的观点,可以将环境正义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环境正义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阿吉曼通过相关文献研究提出,环境掠夺与环境恶化通常与社会公平、平等、权利以及人们的生活质量等问题相联系。例如,Torras &Boyce的研究表明,较平等的收入分配、更大的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以及较高的素养水平通常与较高的环境质量相关[13]。Boyce等的调查研究表明,权力分配的不平等通常导致较宽松的环境政策和较高的环境压力[14]。Morello-Frosch等的研究认为,高度的收入不平等、种族隔离和社会阶层隔离与有害空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相关[15]。由此可见,种族间、社会阶层间的权利、收入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是导致环境质量恶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因此,要缓解环境恶化的趋势,提高环境质量,以至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必须首先实现社会公正,保护人们平等的环境权利。正如Middleton &O'Keefe认为,发展分析要始于分析原因和社会不公,否则任何发展都是不可持续的[16]。Elkin等提出,可持续发展不仅包括环境保护,而且包括社会平等,除非将平等和正义置于可持续发展话语的核心位置,否则实现可持续发展将成为空谈[17]。Goldman不仅认为环境正义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与实现途径,甚至提出“可持续发展很有可能被视为是环境正义运动的下一个阶段”[18]。
第二,环境正义有利于增加可持续发展话语体系的包容性和易接近性。自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以来,可持续发展问题已成为部分国际会议(如1992年的地球峰会和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第一届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研讨主题和世界多国政府政策议程的重要内容,也成为诸多企业、思想库和非政府组织议事日程和行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环境正义问题主要是由于草根组织的宣传和行动而受到人们的重视,只被极少数国家政府和部分非政府组织列入议事日程。可持续发展政策议程是一种精英的或自上而下的政策进路,更具排外性;而环境正义运动是一种草根的或自下而上的政治回应,更具包容性。
因此,精英主义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与举措将从环境正义理论的公正与平等的诉求中获益。环境正义话语更具包容性和易接近性,那些受到环境污染不平等对待的社会群体可直接运用环境正义话语维护自身权利。而可持续发展话语是未来导向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捉摸、难以理解和遥不可及的。因此,将环境正义纳入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设置和评价指标体系将使可持续发展话语更加平民化和更具包容性,并实现由精英式的可持续发展向平民化的可持续发展转变[5]。
三、“公正可持续发展”范式的政策设计与实践进展
1.国际组织践行“公正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设计
环境正义纳入可持续发展政策体系的国际呼吁主要聚焦于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其中,代内公平传统上是指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和北半球的发达国家之间的环境公平问题。人们运用环境正义概念回应跨国公司不可持续的自然资源开采行为。环境正义倡议者认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掠夺行为和自然环境的污染行为是对当地民众的一种人权侵害行为,部分学者将这一行为描述为“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19]。他们认为,享受清洁、安全的环境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人权,不能因种族、阶级、民族、社会地位的不同而不同[20]。
Adeola提出应将环境权利作为人权的重要构成[19]。对人类环境权的承认导致了一系列相关国际环境法和人权法的出台。1972年斯德哥尔摩的《人类环境宣言》、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和1999年的《奥胡斯公约》等国际条约都承认了人类环境权。其中,《奥胡斯公约》首次通过对环境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设计来确保公民的环境权。
明确将环境正义原则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国际组织行动体现于2000年由来自40多个国家的地球宪章委员会修订的《地球宪章》。它要求全球合作,认识到地球上所有生命和文化的共同命运,为当代和后代人的幸福健康培养一种全球责任感。其中设置的原则反映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环境正义理念的内在必然联系。它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为:尊重和爱护社区生活,生态完整性,社会正义和经济公平,以及民主、和平和非暴力。
2.英美践行“公正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行动
在非政府组织和政策企业家的推动下,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话语在英美两国得以重构,由主要关注“绿色”或“环境”的议程框架转向关注生活质量,并更多使用正义、权利和平等等环境正义话语[21]。2000年以来,美国部分城市开始将环境正义纳入可持续发展政策规划和指标设计之中。Warner在2002年对美国77个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进行研究表明,有5个城市(包括阿尔伯克基、奥斯丁、克利夫兰、旧金山和西雅图)将环境正义纳入本地的可持续发展规划中,其中旧金山最全面地将环境正义纳入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政策体系,不仅包括对环境正义的概念界定和历史回顾,而且包括环境正义的政策声明①政策声明指旧金山将环境正义纳入可持续发展规划的承诺。和执行策略②执行策略指旧金山在可持续发展规划中提出了环境正义的促进方式,包括适当设计、使用环境正义指标,以及参与式规划。[22]。
Pearsall &Pierce在2010年进行了与Warner相似的研究,其结果表明,在美国107个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中,80个城市制定了可持续发展规划,其中31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规划中提及了环境正义;在31个城市中,有24个城市的规划具有评估和实现环境正义的目标和具体行动计划。在13个设置了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的城市当中,有8个城市(包括波特兰、阿尔伯克基、纽约、图森、波士顿、明尼阿波里斯、圣地亚哥和旧金山)将环境正义纳入了评估指标体系,共计10类27项环境正义相关指标。10类指标分别为:生物多样性、社区和公民参与、就业、环境设施、环境公害、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安全、运输和森林覆盖面。这些指标中的绝大多数都体现了分配正义原则[23]。由此可见,越来越多的美国城市开始将环境正义纳入可持续发展规划,并由单纯的概念界定到目标设定直至评估指标体系的设置。
英国政府在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设置的可持续发展部门建立了一个环境民主部门,该部门主要负责促进英国政府践行《奥胡斯公约》的相关条款。这是英国政府在可持续发展政策框架内履行环境正义原则和推动公民参与决策的承诺,也体现了英国政府对《奥胡斯公约》主旨和精神的坚持,更注重程序正义。1999年,英国政府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该战略的指导原则是“以人为中心”。尽管该战略注重环境可持续发展,但它也将消灭贫困和社会排斥作为目标之一,具体表现为促进公众参与过程,以及实现正义和人权。
四、“公正可持续发展”范式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公正可持续发展”范式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丰富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使其更具包容性。经典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主要关注的是自然和生态保护,是一种精英主导式的“环境可持续发展”理论,其倡导者多为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人士。然而,该经典范式对贫穷的少数民族和社会下层人士所居住社区内的环境保护却毫无兴趣,这使得经典范式沦为“贵族阶级的政治”,对广大社会大众而言是难以理解的。“公正可持续发展”范式将环境正义理念与诉求纳入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与经典可持续发展相对应,环境正义关注的是平民社区内的环境保护,尤其是人们平等的环境权利,其更具基层性和社区性。因而,融入环境正义要素的“公正可持续发展”不但是“贵族阶级的政治”,更是“平民的政治”。因此,“公正可持续发展”范式的提出使可持续发展理论更具全面性、包容性、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公正可持续发展”范式的提出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它有利于各国政府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经典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倡导者主要为社会上流人士,而“公正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倡导者主要为中下层社会人士。因其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并不与经典可持续发展理论相冲突,而是形成有机结合,因此,该理论也得到上流社会人员的认可和支持。因而,融入环境正义要素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必将得到全社会成员的支持与推动,从而有利于各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它有利于环境正义的实现。因环境正义运动的组织主要是基层性、社区性和地区性的,其力量相对来说十分弱小,很难找到政治支持者和代理人,因而其对政府环境政策制定与执行不能形成足够的压力。当处于弱势的环境正义理念与处于主流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形成有机结合时,环境正义便顺其自然地进入主流社会,融入主流话语体系,并进而上升到国家政策议程。因此,“公正可持续发展”范式也有利于推动环境正义在现实社会中的实现。
“公正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新范式,其理念与框架对我国政府制定与完善可持续发展政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我国的环境正义问题不容忽视。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日趋严重,污染承担者逐渐呈现城乡与区域的不平衡,“污染下乡”和“东污西进”等污染转移现象使我国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居民承担了较多的环境污染。这对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由污染转移引发的多起环境群体性事件并导致社会无序和重大经济损失就是例证。我国的环境非正义问题已产生了高昂的发展成本,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将环境正义原则纳入我国各级政府的可持续发展政策体系对于解决当前的环境非正义问题,实现公正的、包容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达成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Agyeman J.Black People,White Landscape[J].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1989,58(12):336-338.
[2]Agyeman J,Warner K.Putting“Just Sustainability”into Place:From Paradigm to Practice[J].Policy and Management Review,2002,2(1):8-40.
[3]Agyeman J,Bullard R,Evans B.Just Sustainabilities:Development in an Unequal World[M].London:The MIT Press,2003.
[4]Agyeman J.Introducing Just Sustainabilities:Policy,Planning and Practice[M].London:Zed Books,2013.
[5]Agyeman J,Bullard R,Evans B.Exploring the Nexus:Bringing Together Sustainability,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Equity[J].Space & Polity,2002,6(1):77-90.
[6]Lavelle M,Coyle M.Unequal Protection:The Racial Divide in Environmental law[J].The National Law Journal,1992,15(3):1-12.
[7]Faber D.The Struggle for Ecological Democracy: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M].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1998.
[8]Pearsall H,Pierce J.Urban Sustaina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Evaluating the Linkages in Public Planning/Policy Discourse[J].Local Environment,2010,15(6):571.
[9]菲利普·沙别科夫.滚滚绿色浪潮,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M].周律,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232.
[10]Agyeman J.Ethnic Minorities in Britain:Short Change,Systematic Indiffer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Planning,2001,3(1):15-30.
[11]Taylor D E.The Rise of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Paradigm:Injustice Framing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s[J].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2000,43(4):542.
[12]Dobson A.Justice and the Environment:Conceptions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Dimensions of Social Justic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3]Torras M,Boyce J K.Income,Inequality and Pollution:A Re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J].Ecological Economics,1998,25(2):147-160.
[14]Boyce J K,Klemer A R,Templet P H,et al.Power Distribution,the Environment,and Public Health:A State Level Analysis[J].Ecological Economics,1999,29(1):127-140.
[15]Morello-Frosch R,Pastor M,Sadd J.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Southern California's “Riskscape”:The Distribution of Air Toxics Exposures and Health Risks Among Diverse Communities[J].Urban Affairs Review,2001,36(4):551-578.
[16]Middleton N,O'Keefe P.Redefin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M].London:Pluto Press,2001.
[17]Elkin T,McLaren D,Hillman M.Reviving the City:Towards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M].London:Friends of the Earth,1991:203.
[18]Goldman B.Not Just Prosperity.Achieving Sustainability with Environmental Justice[M].Washington,D.C.: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1993.
[19]Adeola F O.Cross-national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Issues:A Review of Evidenc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J].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2000,43(4):686-706.
[20]Hartley W.Environmental Justice:An Environmental Civil Rights Value Acceptable to All World Views[J].Environmental Ethics,1995,17(13):277-289.
[21]Agyeman J.Environmental Justice:From the Margins to the Mainstream?[M].London: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ssociation,2000:8.
[22]Warner K.Linking Local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s with Environmental Justice[J].Local Environment,2002,7(1):35-47.
[23]Pearsall H,Pierce J.Urban Sustaina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Evaluating the Linkages in Public Planning/Policy Discourse[J].Local Environment,2010,15(6):569-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