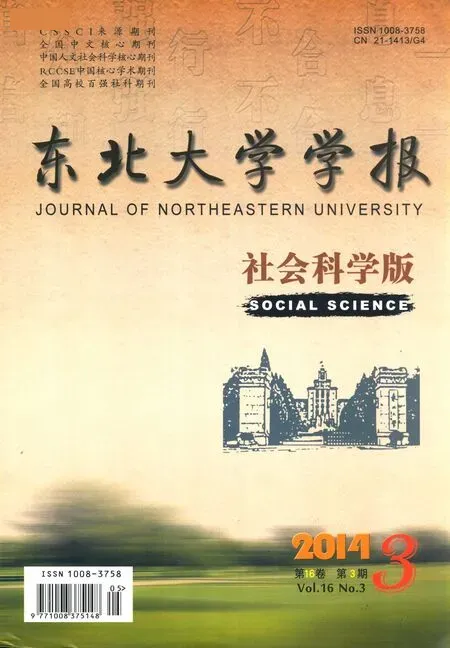身份认同的缺失与追寻
——解读《鸽子飞去》
张 莹,张宛初,冯菲菲
(1.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 110819;2.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 110136)
身份认同的缺失与追寻
——解读《鸽子飞去》
张 莹1,张宛初2,冯菲菲1
(1.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 110819;2.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 110136)
在欧洲一体化的语境中,“身份认同”已然成为德语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获得2010年德国图书奖的移民小说《鸽子飞去》便深刻地反映了这一主题。小说着重描述了主人公对自己边缘生存的焦虑和身份认同的困惑。在瑞士主流文化面前,作为移居的少数族裔因缺乏认同感使主人公感到愤懑;同时在南斯拉夫-匈牙利文化面前,主人公同样遭遇身份焦虑。基于身份认同理论,剖析了主人公对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追寻的思想历程,展示了欧洲一体化中当代欧洲移民的真实心态和混杂身份。
身份认同;身份焦虑;族裔散居;欧洲一体化;混杂身份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移民文学已经成为许多作家笔下的主旋律,从反映第一代移民抱怨与愤懑到第二代移民的漫游与迷茫及第三代移民的个性与多样[1],移民作家笔下的人物在不停地寻求身份认同,寻求精神栖息的家园。获得2010年德国图书奖和瑞士图书奖的小说《鸽子飞去》真实地反映了这种移民心态。本文尝试从身份认同的视角来分析小说主人公依迪科的心理历程,以期管窥欧洲一体化政策下当代欧洲移民的生活和心理状况。
一、身份认同的理论内涵
身份认同是个复杂的概念,涉及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等多种领域,近年来更是受到后殖民主义的特别青睐。身份认同用英语表述为“identity”,具有“本身、本体及相同性、一致性”等含义。一般认为,“身份认同是个人或者集体界定自身处于某一特定语境中自我身份的标志”[2],将身份认同用于个人时,是指“人的自我心理认识,特点为主体的自我等同感和整体感,是人对于自己与某种类别、范畴(社会地位、性别、年龄、角色、范例、规定、团体、文化等)之同一性的认识(部分是有意识的,部分是潜意识的)”[3]。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流动的、不断被建构起来的。正如Paul Giltoy的主张:“身份是由一种环境激发的认识和被认识所促动而表达在一定环境中的互动过程。”[4]环境包括家庭、社会阶层、媒体及周围群体等多种外部因素及个体的心理因素。在这种互动中,身份在时间、空间、历史和文化的转换中不断变化游移,既可能断裂、破碎,又可能成为建构在许多交叉的话语、行为和状态中的组合。因而身份可能呈现出模糊性和多样性,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现代社会,大规模的移民和随后的族裔散居(diaspora)使身份认同早已失去了稳固性和明确性,以致个体产生观念、心理和行为的冲突及焦虑体验,也就是身份认同的焦虑。
任何一个移民者,无论他来自哪个国家,在移民国都会产生“我现在是谁”的身份认同问题。尤其是来自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的移民,其与生俱来的民族属性和文化身份,在移入国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面前,会成为弱势的“他者”。移民处于这种弱势的边缘地位,在缺乏归属感的迷茫中往往产生身份认同的焦虑,这些激励着他们去思考和寻找并重建身份。在《鸽子飞去》中,来自塞尔维亚的柯奇士(Kocsis)一家人虽定居瑞士多年,但身份认同的焦虑始终如影随形,一家人不得不在文化和意识的夹缝中渴求一致,在“边缘”与“中心”中探寻和建构自己的身份。
二、身份认同的缺失
《鸽子飞去》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作者梅琳达·纳吉·阿伯尼(Melinda Nadj Abonji)生于前南斯拉夫(现塞尔维亚伏依伏丁)的一个匈牙利少数民族家庭,童年时跟随父母移居瑞士,曾在苏黎世大学主修德国文学与历史。作者根据自己的经历,以真实的双重视角描述了柯奇士一家人的移居生活和心理历程:从初到瑞士时艰难谋生到终于入籍瑞士并拥有了位于黄金地段的咖啡店,一家人遍尝艰辛,始终吃苦耐劳、低调隐忍,努力获得瑞士社会的认可。尽管如此,斯拉夫人的标记总让他们感到作为外国人的与众不同。百味杂生的经历和边缘生存的境遇令“我”时时感受到身份认同的缺失,并由此产生深深的焦虑。
《鸽子飞去》描述了两个国度在语言和习惯等方面的多种文化差异。如果从这些差异介入分析,读者不难体会作为流散群体的“我们”由于“原有的”和“陌生的”文化碰撞与冲击造成的身份认同缺失。
对于移民来说,语言不仅是表达的工具,更是身份认同的最直接象征。迷路的马米卡(Mamika)在瑞士的大街上求助,但带有匈牙利方音的“Todistrass”(Tödistrasse)无人能懂。她感慨道:“只差那么一点点儿,我就迷失在这个世界里了。”无独有偶,父母初到瑞士时的蹩脚德语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迷茫;而达格娜(Dragana)因语言障碍,只能在德语世界里长久保持沉默。公开场合,“我们”努力用好德语,以得到瑞士本土人的认可;但私下里,“我们”却只说匈牙利语,“我”甚至还将匈牙利词汇直接翻译成对应的德语,比如将“seggfei”说成“Arschkopf”而不是“Arschloch”,来证明自己的民族属性。
在瑞士长大的“我”力求“我的事情,我做主”,却总是遭到家长观念根深蒂固的父亲的阻拦。“我”最终选择历史专业,却始终不敢告诉父亲。对于子女的寻求自我,身在瑞士多年的父母仍然无法理解。父母甚至为“我”的配偶设定了诸多条件:最好是同族人伏依伏丁的匈牙利人,有稳定的“正当”职业等等。无独有偶,由于家人的反对,表妹希拉(Csilla)与恋人私奔,她父亲视为奇耻大辱,一整天不吃不喝,发誓要扭住她的脖子。显然,“我们”遭遇的成长烦恼并不能简单归因于代沟,还源于两个国度间思想与意识的冲突。
多种文化差异汇集起来,造成身份认同的断裂与交叉,从而给“我们”造成了心理上的游离感和不适应。“我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逐渐变得模糊。如果说文化的差异造成了身份认同表层的缺失,那么家乡概念则进一步反映了流散群体对身份认同的深层精神追求。对于流散群体来说,家乡不仅是居住地,更与历史和记忆紧密联系,因而家乡也是一种身份认同的空间。《鸽子飞去》数次通过“我”对家乡的拷问来表现身份认同的缺失。“朋友问起家乡对‘我’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沉思良久,首先想起故乡伏依伏丁美味的饮料Traubisoda,然后是诺米的哭声,祖母的吟唱,夜晚的蛙鸣,还有绽放的野花,炎炎烈日和焖洋葱的味道。”[5]1920“我”记忆中的故乡如天堂般令人向往。然而当一家人衣锦还乡时,虽然“一切都没有改变”,却无法完全找回曾经魂牵梦萦的故乡的亲切感。面对这“铁皮小屋、邋遢的小孩、垃圾山、流浪汉,生锈的路牌”[5]7及故乡人或冷漠或尖锐的目光时,“我”感到深深的失望。亲朋将“我们”看成有钱的西方佬,他们的疏离令“我”内心的幸福感消失得无影无踪,故乡在“我”的心中逐渐变得陌生。在边境,“我们”又遭遇警察的反复检查,不得不一次次证明自己的无辜,这让“我”感到自己已被远远排斥在故乡之外。
如果说在故土的失落让“我”感到迷惘的话,那么在新家园里,默默忍受权力话语的羞辱和歧视以致不知所措,就不能不说是一种“牢笼之境”了。在“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新家园瑞士[5]73,柯奇士一家时时感受到“二等公民”的社会处境和作为“他者”的困惑,这种境遇让他们既感到愤懑,却又无力改变。当一家人得知拥有了黄金地段的咖啡馆时,欢欣鼓舞,“赢得”对于“我们”来说就如鱼儿会飞一样不可思议,因为“我们”不是“瑞士人”[5]44-46。柯奇士一家人不得不感慨自己作为“外国人”的幸运。咖啡店开张前,所在的村庄贴出了海报赞扬这一家人“从前的南斯拉夫人很好地融入了本地生活,并在6年前加入了瑞士国籍”[5]53。看似赞扬和肯定的海报却像一个屏障,分隔开了瑞士本土人和移民。这让“我”想起了一位老师,自称公正,不会以种族论人,却时时不忘说起“我”是来自专制国家的斯拉夫人。斯拉夫人的特异标签就像看不见的绳索,牢牢控制住了“我们”。成为瑞士公民,拥有了苏黎世湖边的咖啡店,柯奇士一家在故乡人的眼中无疑是成功的,然而外表的光鲜无法排解心中的苦恼。“我们必须要过得更好,……在这儿我们没有正常人的命运,所有的一切要靠我们自己争取。”无法成为瑞士的主人,那么得到本地人的认可,就成了“我们”的终生奋斗目标。为此,柯奇士一家不得不默默忍受当地客人的挑衅甚至侮辱,“涂粪”事件终于让“我”出离愤怒。一位顾客将脏内裤扔在卫生间的地上,还在墙上用粪便写上了辱骂外国人的话。“在蒙蒂尔从来没人称我们是狗屎外国人,我们的客人也多是衣着整洁,体面的人。……我终于明白这种和蔼、体面和节制只不过是一张面具罢了。”[5]283“涂粪”事件的作祟者不仅有着主人般的居高临下,更昭示了其对异族的排斥和“我们”这些外来移民的“他者”地位。
无法真正融入移居地并进入主流社会正是移民的真实生存写照,因而他们永远也无法摆脱自己的寄居心态。远离故土多年,新家园瑞士早已深深感染并渗透了“我”,让“我”无法再彻底归属伏依伏丁,而瑞士并没有完全接纳“我”,“我”不得不感受着自己的边缘存在。经历着两个家园的双重陌生和排斥,“我”难以找到精神的归属,产生了身份认同的焦虑和困惑。在经历了恋人的离去、“主人”的歧视等一系列令人希望破灭的遭遇后,“我”的心理状态不断发生着变化。我到底是谁?我从何处来?将向何处去?别人眼中的“我”是新家园的南斯拉夫人,故乡伏依伏丁有钱的西方佬,而“我”在这种“凝视(gaze)中感到焦灼不安。面临着边缘生存和身份的双重困惑,“我”的这种焦虑即使在熟练应用德语,定居瑞士多年后也没有减少。“我”似乎一直在旅途中,在寻找久违的家的感觉,不断地追寻和思考自己的身份。正如萨义德所述的知识分子的心灵流亡,“我”的身份认同永远在寻找的路上。
三、身份认同的追寻
“涂粪”事件中一向谨小慎微的父母表现懦弱,“我”对父母的一味隐忍退让感到无比愤懑。“我”终于离开了父母和咖啡馆,住到位于市中心东西干道上的一间小公寓里。这似乎暗示着“我”拒绝成为任何人要求或希望“我”应该成为的样子。“我”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不愿再被双重的他者身份所折磨,希望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和生活,找到真实、现实、更稳定的身份认同。在逼仄的公寓中,“我”透过窗户,经常和双层巴士里的乘客对望,猜想不断前行的乘客来自哪个民族。正如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和不断前行的乘客,“我”一直在追寻身份认同的路上。这也正代表了多数移民的心声,他们不知道自己该属于哪一块土地。
重新思考身份的建构,是缓解身份焦虑的必然途径。“我”并没有认同作为“他者”的身份和处境,“我”努力通过自救重建自己的身份。流散群体如何完成自己的身份认同建构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一般认为,流散群体既不能完全坚守故土文化,也不能彻底抛弃民族文化完全以移入国文化取而代之。霍尔认为:“认同使我们所做的不是无休止的重复解读,而是作为变化的同一来解读。”[6]因此,面对流散群体多重的生活和情感体验,对其的身份认同的建构也是不断变化的。《鸽子飞去》中“我”的身份认同也是在迷惘、波动中逐渐建构起来的。在不断审视、批判和质疑的过程中,“我”对故乡的美味、淳朴的田园生活和匈牙利语仍然情有独钟。“我”心中的家园还是度过了美好童年的伏依伏丁,这些形成了“我”相对稳定的身份归属感;而瑞士语境也客观地赋予了说着流利的德语、深受瑞士文化影响的“我”的瑞士身份。事实上,“我们”的生活里已经处处体现出瑞士特色,如“我”不断寻求自我的瑞士性格,“我们”的咖啡店里纯瑞士口味的食品,瑞士化的服装等等。正是种族归属感及移民地“主体”的反馈加上“我”的主观意愿等多种因素互动才构建了“我”的双重身份,并使“我”在这种矛盾与一致中努力前行。庆幸的是,“我”并没陷入哈姆雷特式的孤独与矛盾,而是选择了听凭内心的召唤,继续追寻并努力建构自己的身份,不断寻求精神出路。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身份的认同变得既非此非彼,又亦此亦彼。后殖民理论学家霍米·巴巴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杂交性身份”理论。他认为不同的文化之间不是分离迥异的而是相互碰撞的,这就导致了一种文化的综合、合成的模式。杂交性是一种融合,描述了文化间对话性的互相阐明与转译[7]。巴巴认为,身份的建构会经历否定、磋商以至杂交的多个过程。《鸽子飞去》中“我”的身份建构便遵循了巴巴的观点,面对身份认同的缺失,“我”经历了迷茫、质疑、否定和融合的心理路程,终于完成了自我思辨,建构了自己的杂交身份。
四、结 语
小说作者笔触细腻,娓娓讲述了柯奇士一家人的移民经历。与移民文学常见“急于认同异国文化却又排斥在外,抵制本族文化却又无法与之割离”的旋律不同,小说通篇讲述“我”对故乡的思念及在瑞士和塞尔维亚生活的遭遇与心灵体验。“我”的身份认同经历了复杂的心路历程。“我”一直怀有一种作为“他者”的孤独情绪并渴望宣泄自己的迷惘和愤懑,“我”不断醒悟,终于摆脱了受辱者的自伤自怜心态,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由被动接受转为积极探寻,以证明自己的合理存在。
“我”的身份认同的缺失和寻找的过程也是南斯拉夫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和追随。透过小说中多个人物的描写,欧洲一体化中的人们的心理状态可见一斑。在全球同处一个“地球村”的今天,移民并不是简单的时间和空间的移动,对于多数人来说,移民更是身份认同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移民地原有居民与移民互动与磋商的过程。无论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三代移民,完全地融入迁入国是非常艰难的,因为移民的民族烙印和历史记忆是无法磨灭的。同时,在移民国里固守原有的民族特性和文化特征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在各民族混杂、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各个民族和国家早已超越了地域的界线,在文化和意识领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值得回味的是,作者梅琳达用德语书写小说,在德国图书奖颁奖典礼上却选择用匈牙利语致辞,在谈到自己的童年经历时,梅琳达哭诉初到瑞士时,因不会德语,只能在幼儿园的“白雪公主”表演中被老师安排扮演画成绿色的没有一句台词的树。事实上流散群体的心理移民任重道远,因为欧洲真正走向文化和心理一体化,完全和谐共存的路途还很遥远,这需要全体欧洲人更开放更包容的心态。
[1]陈民.德国移民文学的发展[J].当代外国文学,2009(3): 121-129.
[2]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M].王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3.
[3]王盈.魂归何处——身份焦虑中的俄罗斯作家阿·金[J].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2012(1):70-74.
[4]钱英超.自我、他者与身份焦虑——论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其文化意义[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0,22(4): 4-12.
[5]Abonji M N.Tauben Fliegen Auf[M].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2013.
[6]斯图加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09.
[7]贺玉高.霍米·巴巴的杂交性身份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54.
Lack and Pursuit of Identity——Interpreting Pigen Flew
ZHANG Ying1,ZHANG Wan-chu2,FENG Fei-fei1
(1.Foreign Studies College,Northeastern University,Shenyang 110819,China;2.College of Liberal Arts,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136,China)
In the contex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the identity of diaspora groups has become a major concern.Winning the 2010 German National Book Award,the immigration novel Pigeon Flew deeply reflects this theme,which highlights the hero’s concerns of marginal survival and the puzzles of identity.As a former Yugoslav who moved to Switzerland many years ago,the hero has been indignant with diaspora groups’lack of identity in face of the Swiss mainstream culture;meanwhile, exposure to the Yugoslavia-Hungarian culture has impacted her identity as well.Based on the theory of identity,the novel explores the hero’s concerns as she pursues her identity in her new country and reveals the true state of mind and hybrid identity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immigrants in the cours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dentity;anxiety of identity;diaspora;European integration;hybrid identity
I 106.4
A
1008-3758(2014)03-0327-04
(责任编辑:李新根)
2013-10-23
张 莹(1976-),女,吉林省吉林市人,东北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德国文化与社会、德国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