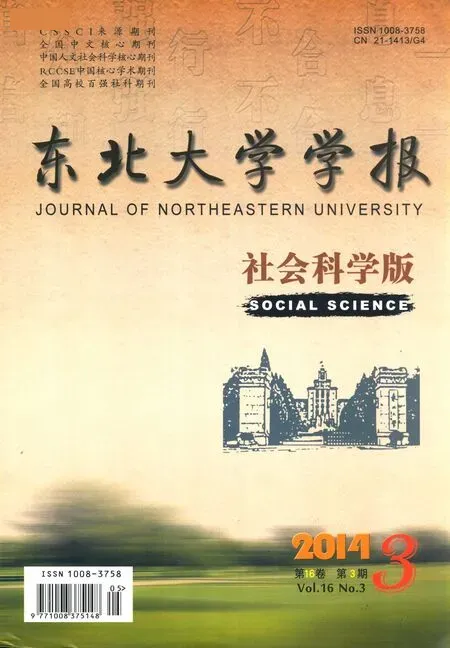文化管控能够持续提升企业绩效吗?
——来自金融业集团的经验证据
梁尔昂,张玉明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文化管控能够持续提升企业绩效吗?
——来自金融业集团的经验证据
梁尔昂,张玉明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集团企业面临管控模式改革的巨大压力。文化管控作为新型管控模式逐步受到企业管理者的重视。来自60家金融业集团的经验证据表明:在规模、年龄、性质、企业家等因素之外,集团文化管控对子公司绩效具有显著的、增加的解释力;但两者并非简单的正向或负向相关,而是呈现倒U型的曲线关系。此外,在高不确定性的环境下,集团文化管控对绩效的影响更加突出,这也意味着文化管控是能够发挥持续性作用的有效管控手段。
文化管控;企业绩效;环境不确定性;集团企业
集团企业在运行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内部沟通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如何进行有效的集团管控一直是困扰大型集团企业的管理难题。通过文献梳理不难发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伴随着大规模企业的产生,集团管控模式问题就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在早期的研究中,韦伯的官僚行政控制模式处于主流地位,受到学者和集团企业的推崇[1],但此种模式将员工视为不会出错的“理性经济人”,甚至是毫无创新动力、严格照章办事的“机器”[2],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员工的积极性和潜力,难以对集团管控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及内部管理的日益复杂化,官僚行政控制模式的弊端越来越明显。20世纪70年代,日本一些跨国企业开始尝试采用非正式的、较为人性的“文化管控”取代制度性的、严格理性的“官僚管控”,结果非常成功,跨国企业的凝聚力和综合实力获得极大提升,从而引发学术界对于文化管控模式的普遍关注[3]。然而由于尚无成形的集团文化管控量表,集团文化管控机制能否提升集团绩效这个问题虽然提出20多年了,但却一直难以通过大样本实证检验来获得支持。
近年来,经过国内学者的努力,基于中国情景的集团文化管控量表开发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4-5],这为进一步研究集团文化管控对绩效的影响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金融业集团样本的实证分析来回答“文化管控能否提升企业绩效”这一理论界悬而未决的问题,并进一步探讨“如果能,它以何种形式作用”,以及“这种作用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文化管控与企业绩效
与行政官僚管控不同,文化管控将员工视为“自我实现的社会人”[6],更注重在非正式制度下母子公司之间展开关于发展目标、共同价值观和一致性行为标准的探讨和交流[7]。从理论上而言,集团文化管控能够通过实现母子公司的价值融合和制度协调[8],直接提升子公司的绩效,并最终提升集团的整体绩效。相关研究表明:文化管控不仅在实质上加强了组织文化的凝聚、导向、激励等一般功能,还具有降低管理成本[9]、推动组织变革和技术创新[10]、提高知识获取能力[11]等作
2.文化管控的非线性作用形式
尽管从理论上而言文化管控对企业绩效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本文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一方面,从文化管控程度的两个极端考虑。若管控程度太低甚至可以忽略,则文化管控对企业绩效几乎无促进作用;若管控程度太高,则母子公司之间需要花费巨大的沟通和交流成本,而且完全的文化控制无异于消除了母子公司之间的文化差异,此时的子公司实则成为母公司的一个部门,由于失去独立性而丧失活力。可见,文化管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作用实际上呈现两头底、中间高的倒U型。另一方面,文化管控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复杂的作用机制。首先,文化管控并非直接影响企业绩效。文化管控首先影响的是组织的人力资源整合,而后才能影响企业绩效[1415]。其次,文化管控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众多影响因素。已有研究表明,除行业属性外[16],母子公司间的文化[17]和业务[18]差异,以及母公司外派经理人员的灵活变通能力[19]等均会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假设2:集团文化管控与子公司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是非线性的。
3.文化管控作用的可持续性
以上分析表明,从理论上而言文化管控能够影响集团企业绩效。然而更进一步,文化管控的这种影响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即文化管控能否帮助企业实现基业长青和长寿成长?现代企业本质理论表明,企业其实是具备“生命人性特征”的类生命体[20],其长寿成长同样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15]。因此,集团企业实现长寿成长的关键在于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文化管控的作用如果是可持续性的,那么它应该能够帮助集团企业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生存。换言之,在不确定的市场经营环境条件下,文化管控对集团企业绩效的作用应该更加突出。笔者认为,适度的文化管控具备这个能力和特性。适应性文化理论指出,只有那些能够使企业适应市场经营环境变化的企业文化才会与企业绩效的联系更为持久[21-22]。文化管控可以从两个方面造就集团企业的适应性文化。首先,正如前述理论分析表明,文化管控使得母子公司的文化相互契合并共享价值观[9],有利于整合、学习和变革[11]。其次,集团企业高度契合的文化使得母子公司的理念、价值观与战略目标、行动能力高度一致[13]。基于此,提出假设3:集团文化管控对子公司绩效的影响具有可持续性,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越高,集团文化管控与子公司绩效的关系越强。
二、研究方法
1.样本与数据
本文选择金融业集团作为研究样本进行数据采集。首先,因为单行业分析能够避免跨行业带来的集团企业间文化、行业和业务差异过大,已有研究指出这些方面能够对文化管控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1618]。其次,这也是考虑了文化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转型期我国金融文化建设的基本现实。研究表明:信任[23]、宗教信仰[24]等文化因素与一国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密切相关。我国金融业长期处于以儒家哲学为基础的传统文化的浸染之中,而以“孝文化”和“家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体系极易产生官僚主义和虚假民主,这是导致我国金融业发展无序和无效率的深刻文化背景[25-26]。因此经济转型期我国金融业实施文化改革的愿望更为迫切,以之为样本研究文化管控问题更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意义。
由于对集团管控模式和环境不确定性的评价需要综合考虑母公司和子公司的意见,因此本文在进行数据采集时,同时向母公司和其第一子公司(规模最大或业务最为类似)的高层管理者发放调查问卷,取平均值为最终研究数据。本文向全国范围内的金融业集团及其第一子公司随机发放调查问卷200份,收回有效问卷120份,中国人寿、中国人保、国泰君安、东北证券、中信银行、齐鲁银行等60家样本企业的数据可供研究使用。
2.变量测量
调查问卷主要包括基本信息、文化管控和环境不确定性三部分。其中基本信息部分主要记录样本企业的基本情况,需要被调查者根据实际填写。文化管控和环境不确定性部分的问项,需要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感知和判断选择1~5之间的数字作答,分别表示完全不认同、不认同、基本认同、认同和完全认同。
基本信息部分包含实证检验需要的集团子公司绩效和其他控制变量的测量。本文用销售收入衡量企业绩效,分为小于1 000万元(11.5%)、1 000万元~3 000万元(21.8%)、3 000万元~1亿元(30.4%)、1亿元~3亿元(22.6%)、大于3亿元(13.7%)五个档次。此外,还对员工人数、企业存续年限、所有制性质、企业家学历及政治关联等可能影响绩效的变量进行了测量。在有效样本中,企业家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样本占30.0%,且54.4%的企业家具有政治关联。企业平均存续年限为54年(SD=6.7),国有独资或控股的样本占83.3%。
关于文化管控部分的问项设计,陈志军等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4]。为进一步提升可靠性和准确性,参考O’Donnell制定的跨国集团公司文化管控量表的特点[27],本文从陈志军等构建的量表中选取因子负荷最大的题项构成文化管控部分的测量条目,包括:①母公司经常开展对子公司员工尤其是新进员工的文化培养和技能培训工作;②子公司的管理工作主动参考母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和价值观;③母子公司之间具备通畅的项目合作渠道;④子公司经常依据母公司的要求进行制度修订和完善。关于环境不确定性部分的问项设计,主要参考Miller等的环境量表[28],包括“市场需求变化之快企业很难适应”“所需资源难以有效获取”等6个测量条目。
3.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工具为PASW Statistics 18和EViews 6,使用分层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在开始正式的数据处理之前,需要考虑可能存在的同源偏差及其影响。基于EFA的Harman单因子检验结果表明,未经转轴的第一因子方差贡献率仅为36.1%,低于50%的统计学标准[29],这表明同源偏差并非一个严重问题,不会对检验结果带来实质性的影响。以往研究证实交互项与交互项的构成变量之间往往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30],本文采用“中心转换法”来克服这样的问题。
本文采用分层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提出的理论假设,具体步骤为:第一,依次将控制变量组(员工规模、企业性质、企业家学历及政治关联等变量)、文化管控、文化管控的二次项置入方程,对子公司绩效进行回归,考察上述变量拟合系数的符号、显著性,以及对因变量的解释率增加情况,从而检验集团文化管控对子公司绩效的影响及作用形式。第二,继续依次将环境不确定性及环境不确定性与文化管控的交互项置入方程,对子公司绩效进行回归,考察拟合系数的符号、显著性,以及对因变量的解释率增加情况,从而检验文化管控作用的可持续性,即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三、研究结果
1.描述性统计与简单相关分析
表1给出了集团文化管控对子公司绩效影响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
从表1中可以看出,除企业家学历(r=0.05, p>0.05)与所有制(r=0.09,p>0.05)外,子公司绩效与其余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不难发现,子公司绩效与文化管控的相关系数及显著性(r=0.11,p<0.05)低于其与员工人数(r=0.76,p<0.01)、存续年限(r=0.58,p<0.01)、政治关联(r=0.39,p<0.01)等控制变量相关系数及显著性。这种相关模式为本文的研究假设1和假设2提供了初步的证据,提示我们集团文化管控与子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可能并非直接和线性。同时,子公司绩效与环境不确定性的相关系数及显著性也相对较低(r=0.20,p<0.05),预示着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并非直接,环境不确定性很可能如假设3指出的那样是以调节变量的形式出现。另外,所有制与子公司绩效之间并未体现出显著的相关性(r=0.09,p>0.05)。
2.集团文化管控对子公司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形式
表2给出了集团文化管控对子公司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形式的分层回归结果。
由表2可知,在控制了企业存续年限、员工人数、所有制、企业家学历,以及政治关联的影响之后,集团文化管控对子公司绩效方差变异的增量解释率为5%(b=0.11,p<0.05),且F统计量的值也得到显著增加(ΔF=6.26,p<0.01)。这表明集团文化控制与子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的假设1得到了支持。
更进一步,在加入文化管控的二次项后,分层回归模型的方差变异解释率再一次增加了8%,F统计量的值也相应再次显著增加了7.84。这表明与简单的线性关系相比,曲线关系更适合体现集团文化管控对子公司绩效的作用形式,并且由于文化管控二次项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b=-0.58,p<0.01),这种曲线关系呈现倒U型。这种形状意味着集团文化管控存在程度上的阈值,超过该值之后,集团文化管控程度的增加会对子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尽管集团文化管控对子公司绩效的提升是有价值的,但应该遵循适度原则,避免过犹不及。由于事先对相关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因此虽然模型中存在同一变量的一次项和二次项,VIF值仍在2以下,并未导致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3.集团文化管控对子公司绩效影响的可持续性
在表2的基础上继续依次加入环境不确定性变量及其与文化管控的二次项,以考察集团文化管控对子公司绩效影响的可持续性,即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表3给出了分层回归结果。
从表3可以看出,环境不确定性变量对子公司绩效也具有显著的解释力(ΔR2=4%,ΔF= 5.73,P<0.01),但其影响却是负向的(b= -0.19,p<0.05),表明子公司所处的经营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进一步加入环境不确定性与文化管控二次项的交互变量之后,模型的方差变异解释率(ΔR2=6%)和F统计量(ΔF=6.89,P<0.01)都有了更为显著的增加,且交互项的系数显著(b=-0.12,p<0.05),表明环境不确定性对文化管控与子公司绩效之间曲线关系的调节效应是存在的,即集团文化管控对子公司绩效的影响是可持续的,从而研究假设3得到支持。调节效应的示意见图1,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越高,文化管控与子公司绩效之间的曲线关系越陡峭,根据数学中曲线斜率的概念,这意味着集团文化管控对子公司绩效的影响越突出,从而充分表明集团文化管控对子公司绩效作用的可持续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为规避特殊制度背景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风险,寻求规模经济和内部经济的集团企业得到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以母子公司管理体制为特征的大型集团企业面临集团管控体系的构建及管控方式的选择问题,因此迫切需要中国情景下集团文化管控绩效效应的相关理论研究以提供决策支持。本文基于60家金融业集团的实证结果表明:①集团文化管控能够显著地影响子公司绩效,但这种影响并非简单的正向或负向相关,而是呈现倒U型的曲线关系。作为一种隐性的、非正式管控方式,适度的集团文化管控能够促进母子公司的文化相互契合并共享价值观,从而促进集团的协调发展。但集团文化管控程度超过适度水平之后,母子公司之间不但需要花费巨大的沟通和交流成本,子公司的经营行为也会受到母公司的过度约束,极易由于失去独立性而丧失活力。②环境不确定性对文化管控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越高,文化管控与子公司绩效之间的曲线关系越陡峭,这意味着集团文化管控对子公司绩效的影响越突出,表明文化管控的作用是具有可持续性的。集团文化管控不但能够通过促进价值观的共享来增强集团企业的动态能力,而且通过保持战略目标和行动能力的高度一致落实动态能力,从而持续地促进集团企业适应环境的变化,实现基业长青。
对于实践中的集团管理者,本文的启示在于文化管控对于集团绩效具有显著的持续性影响,因此应该实行适度的文化管控。首先,适度的文化管控应该是适应环境的。集团企业实现长寿成长的关键在于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只有充分考虑了母公司和子公司行业环境的文化管控才能够有效地培育集团适应性文化,从而转化为具有持续性作用的核心竞争力。构建具有环境适应性的文化管控机制,就是要寻找达到母公司文化、子公司文化和外部环境之间动态平衡的途径及其影响因素。对子公司而言,这不应该是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要在客观审视自身文化环境适应能力的基础上,主动学习母公司文化的优秀之处,同时对其不合理的文化灌输进行积极反馈。其次,适度的文化管控需要认识到并尊重文化管控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的复杂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了文化管控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并非简单的正向或负向关系。已有研究表明,人力资源整合是文化影响绩效的关键中介过程。因此文化管控首先影响的是组织的人力资源整合,而后才能影响企业绩效。在认识和尊重复杂作用机制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文化管控需要准确把握文化管控程度的阈值。这就要求集团在实行文化管控之前对管控对象的文化特征进行详尽的调查,以提高文化管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第三,适度的文化管控应该追求恰当的方式和途径。适度的文化管控应以体现人文关怀的方式进行,拒绝冰冷死板的行政官僚式控制,更注重在非正式制度下母子公司之间展开关于发展目标、共同价值观和一致性行为标准的探讨和交流。从文化管控的内容维度中不难发现构建适度文化管控模式的可行途径:加强母子公司间关于价值观的交流和探讨,明确共同的目标和追求;构建母子公司之间高效的、轻松的和非正式的交流沟通平台,通过这一平台促进母子公司之间决策行为和业务活动的协作融合;更为重要的是,母子公司都应设立专门的文化管理部门,通过制定完善的制度,举办有针对性的文化培训和交流活动,使母子公司员工都能够感受到相同的文化激励。
[1]Ouchi W G,Maguire M A.Organizational Control:Two Function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75,20 (4):559-561.
[2]Ouchi W G.Markets,Bureaucracies and Clan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80,25(1):129-141.
[3]王晓静,陈志军,董青.基于业务相关性的母子公司文化控制与子公司绩效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9): 81-88.
[4]陈志军,董青.母子公司文化控制与子公司效能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1,14(1):75-82.
[5]谢洪明,王晓玲,蓝蕙芳.东道国母公司的文化控制和人员控制对IJVs学习能力的影响华南地区企业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9(9):147-153.
[6]Carol A R.Corporate Culture:The Last Frontier of Control?[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1986,23 (3):287-297.
[7]Jaeger A M.The Transfer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Overseas:An Approach to Control in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3,15(1):91-114.
[8]Denice E W,Lawrence S W.Commitment for Hire? The Viability of Corporate Culture as a MNC Control Mechanism[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06,15 (1):14-28.
[9]Baliga B R,Jaeger A M.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Control Systems and Delegation Issu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4,15(2):25-40.
[10]Bartlett C A,Ghoshal S.跨边界管理跨国公司经营决策[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2.
[11]Steven R L,Liliana P N,Abdul A R.Parental Control:A Study of U.S.Subsidiaries in Mexico[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09,18(5):481-493.
[12]Efferin S,Hopper T.Management Control,Culture and Ethnicity in a Chinese Indonesian Company[J]. 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2007,32(3):223 -262.
[13]Ambos B,Bodo B S.Innovation in Multinational Firms: Does Cultural Fit Enhance Performance?[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2008,48(2):189 -206.
[14]Schein E.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M].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85.
[15]李海,张勉.企业文化是核心竞争力吗?文化契合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J].中国软科学,2012(4):125-134.
[16]Batrol K M,Srivastava A.Encouraging Knowledge Sharing:The Role of Organizational Reward System[J]. Journal of Leadership&Organizational Studies,2002,9 (1):64 76.
[17]Wilkinson J,Peng Z,Beamish B.The Diminishing Effect of Cultural Distance on Subsidiary Control[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08,14(1):93-107.
[18]Gupta A K,Govindarajan V.Knowledge Flows and the Structure of Control With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1,16(1):768 -792.
[19]Paik Y.Sohn J D.Expatriate Management and MNC’s Ability to Control International Subsidiaries:The Case of Japanese MNCs[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04,39 (1):61-71.
[20]田奋飞.企业演化研究:从“生命物性”到“生命人性”[J].社会科学家,2008(1):59 62.
[21]Gordon G G,Di T N.Predicting Corporate Performance from Organizational Culture[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1992,29(6):783-794.
[22]科特,赫斯克特.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3]Guiso L,Sapienza P,Zingales L.Does Culture Affect Economic Outcomes?[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6,20(2):23-48.
[24]Stulz R M,Williamson R.Culture,Openness,and Financ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3,170 (3):313 349.
[25]顾肃.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文化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 1999(3):110-117.
[26]朱正元.儒家思想与中国中央银行制度变迁[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1(1):73-77.
[27]O’Donnell S W.Managing Foreign Subsidiaries:Agents
of Headquarters,or an Interdependent Network?[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0,21(5):525-548. [28]Miller D,Hriesen P H.Strategy-making and Environment:The Third Link[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83,4(3):221-235.
[29]Podsakoff P,Organ D.Self-reports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Problems and Prospects[J].Journal of Management,1986,12(4):531-544.
[30]Aiken L S,West S G.Multiple Regression: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M].Beverly Hills:Sage,1991.
(责任编辑:王 薇)
Can Culture Control Sustainably Improve Enterprise Performance?——Empirical Evidence from Enterprise Groups in Finance Industry
LIANG Er-ang,ZHANG Yu-ming
(School of Management,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In the transitional economy circumstance,enterprise groups in our country are confronted with huge press of control model reform.Based 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60 enterprise groups in finance industry,the paper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excluding the elements of enterprise scale, age,nature and entrepreneur,group culture control significantly reinforces the performance of subsidiaries.However,the relationship is not simply linear but curve,showing the form of inverted U.Besides,in the environment with high uncertainty,the effect of group culture control on performance is more obvious,which means that culture control can serve as an effective control method through performing sustainable influence.
culture control;enterprise performance;environment with high uncertainty;enterprise group
F 270
A
1008-3758(2014)03-0243-07
2013-09-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12AZD09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12YJC630297)。
梁尔昂(1986-),男,山东菏泽人,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集团公司治理与中小企业融资研究;张玉明(1962-),男,山东济南人,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集团公司治理与中小企业成长研究。用。若使用得当,必然会促进集团内部的协调一致,形成气氛融洽、员工忠诚度和积极性高的工作环境[12],而上述因素正是组织绩效提升的有效途径。例如,Ambos等的经验研究表明母子公司的文化契合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母公司从文化的适配性角度出发分配给子公司的任务更能够被接受且很好地完成[13]。而来自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也表明,作为一种隐性的、非正式管控方式,集团文化管控在集团管理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依据上述理论分析和国外实践经验,提出假设1:在规模、年龄等控制因素之外,集团文化管控对子公司绩效具有增加的、显著的解释力。